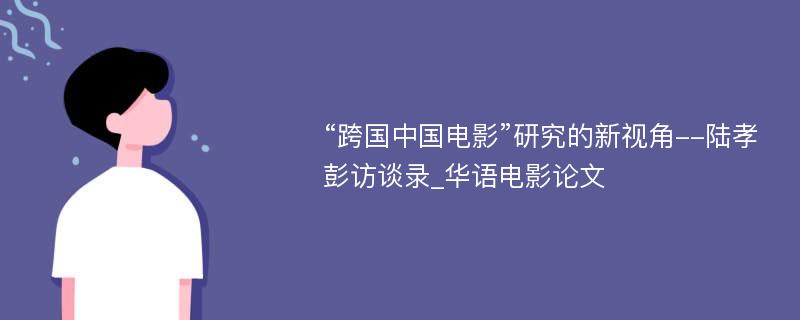
“跨国华语电影”研究的新视野——鲁晓鹏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语论文,新视野论文,访谈录论文,电影论文,鲁晓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晓鹏1979年赴美留学,1990年获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在匹兹堡大学任教多年,2002年起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比较文学系教授。他曾创办该校电影系,并任首任系主任。研究领域包括世界电影、后社会主义电影、跨国华语电影、中国现代文学与视觉文化、中国传统叙事学、文化理论、全球化研究、东西方比较诗学等,出版了《跨国华语电影:身份认同、国家、性别》、《华语电影:编史、诗学、政治》、《中国,跨国视觉性与全球后现代性》、《中国现代性与全球生命政治》、《从历史到虚构:中国叙事诗学》、《文化·镜像·诗学》等中英文论著、编著多部。
“华语电影”:概念之争的背后
李:您这次来参加南加州大学的“中国电影百年”学术研讨会,并主持其中一场讨论。这次会议是把1905年作为中国电影起点的。但您1997年曾写过一篇《中国电影百年的断代问题》,文中根据“具有深远影响的全球性事件和民族性事件”,把中国电影史的百年断代界定在1896~1996年之间。在您看来,把1896年作为起点,是因为从那一年开始,中国电影消费与销售开始具备跨国家的性质;而把对于中国三个地区(内地、台湾、香港)的电影的探讨下限定在1996年,则是因为1997年7月香港回归中国后,地缘政治变化对后殖民的香港电影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事实上,您和很多学者都提到,中国民族电影史的开端,可以始于1905年拍摄的第一部中国影片,或是1913年拍摄的中国第一部故事片。因为您的上篇文章写于1997年,十年过去了,上述断代是否应有变化?电影断代的尺度到底是什么?换言之,中国电影的分期能够构成一个理论研究问题吗?
鲁:纽约市立大学斯坦顿岛校区的朱影和南加州大学的骆思典(Stanley Rosen)在2005年和2008年分别开过“中国电影百年”的会议,他们都是从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算起的。而我十年前提出“中国电影百年”的概念,可能跟当时着意于探讨“跨国电影”有关。我当时提出中国电影百年始于1896年,其实指的不是中国电影的生产,而是从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在中国放映开始算起,那实际上可以看做跨国电影的销售,我当时从建构跨国电影理论框架这个角度出发,所以觉得从1896年算起是合适的。而百年的终点定在1997年,因为香港要回归,当时谁也不知道回归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朱影比较注重中国内地电影的研究,我不知道她编的论文集中有没有收录研究台湾电影、香港电影的论文。骆思典也是,这些年每年都去北京做有关中国的研究。张英进有本书叫《中国民族电影》(Chinese National Cinema),英文书名是出版社定的,因为这是一套包括德国民族电影、法国民族电影在内的丛书中的一本,所以只能取这个名字。但实际上这本书并不只是探讨内地电影,其中—些章节还专门讲到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从这些来看,大家在中国电影分期及研究概念方面还是有—些不同的处理的。
李:您刚才提到“概念”问题,这恰是个令人头疼但却也十分有趣的问题。比如,“Chinese Cinema”一词,就可以同时翻译为“中国电影”、“华语电影”或“汉语电影”。因此,往往要联系“Chinese Cinema”一词使用的上下文,才能明确该词所指称的对象。事实上,概念的命名与争议,正反映出海外学者面对“华语电影”这一复杂对象时,在研究立场、指涉范围、学术取向及思维方法等方面的分歧。所以您后来又在“Chinese Cinema”两词中间加上“-language”,似乎是很明确地限定从“华语语言”这个角度去探讨华语电影?
鲁:这样一来,像新加坡的华语电影也可以放进来。有朋友批评说这是“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ation),对此我不大赞同。在我看来,这不仅是语言的问题,还包含着文化、意识形态这些层次的问题。把李安拉进来,新加坡的华语电影也拉进来,这不光是从语言角度考虑,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对大中国文化圈的思考。中国文化其实目前扩散得很快,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边界,海外的一些华语电影,可以从边缘来颠覆中心的一些东西。像在新加坡的华人经历和在北京的华人经历不—样,而李安从台湾到美国跑来跑去,非常怀旧,像《色·戒》这种华语电影,早已超出一般的语言问题,而涉及广义的文化政治领域了。
李: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所做的跨国中文小说研究,其实跟您这个“华语电影”研究颇有对位性。他也是从“中文”这种语言入手,但所探讨的问题牵涉到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边缘——中心、身份复杂性等。探讨概念本身看来无聊,实质上非常重要,里面包含着研究的基本立场、取向和方法论问题。我们中国人很早就讲“名正则言顺”,名实要相副。在过去十几年海外有关于中国电影的研究中,英文语境中出现了一系列指称性的概念,如Chinese cinema、Chinese national cinema、Chinese-language film、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comparative Chinese cinemas、Sinophone cinema等,有些概念还有单复数之分;与之相关,中文语境中则出现了“中国电影”、“中国民族电影”、“华语电影”、“中文电影”、“汉语电影”、“跨国华语电影”、“比较华语电影”等。这些概念大多数是先以英文在海外学术界出现,然后辐射到国内的;而中英文词义的不对等性,则加剧了概念转换的难度。这里面的一个分歧点就在于把研究范围限于中国之内还是扩展到中国之外的“华语”文化区域。我注意到,您在2005年与叶月瑜主编的论文集《华语电影:编史,诗学,政治》(Chinese-Language Film:Historiography,Poetics,Politics)所撰的导言《华语电影之概念:一个理论探索》中,专门分析了其中一些概念分歧的实质。您倾向于将“华语电影”定义为主要使用汉语方言,在内地、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社区制作的电影,其中也包括与其他国家电影公司合作摄制的影片。“华语电影”概念的提出首先因应的是什么样的事实?它出场的语境是什么?
鲁:最初,台湾学者李天铎、叶月瑜、郑树森想把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电影放在一起谈,但找不到合适的词汇,于是提出“华语电影”这个概念,时间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有些著作就以“华语电影”来命名。现在看来,他们当时想解决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中国电影”这个概念容易引起争论,因为过去谈到中国电影,台湾人将台湾、内地、香港三地的电影分别叫做“国片”、“内地片”、“港片”。这样一来,内地学者就不能接受了:什么叫国片?内地是主体,我才是国片,台湾电影怎么能叫“国片”!这样一来,台湾学者跟内地交流时,就不好意思再把台湾电影叫做“国片”。反过来,台湾学者也不希望内地学者把台湾电影看做仅仅是中国电影的—个部分,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才提出“华语电影”,就是希望能让内地学者、台湾学者坐在一起,从语言共同体的角度来谈论华语电影,这样尽量能坐下来说到一块,我想这是他们的初衷。那时“华语电影”作为一种说法在港台的中文学术圈首先出现,但在海外主流的英语学术界没有对应词,没有引起注意。是我和叶月瑜把“Chinese-language film”这个概念推出,在英语学界把它理论化、主流化的。我们那个集子2005年出版,到了今天“Chinese-language film”概念已被广泛接受和应用。
李:这反映了“用一个以语言为标准的定义来统一、取代旧的地理划分与政治歧视”所做的努力。事实上,这种命名的调整还出现在诸如华语歌曲、华语传媒、华文文学等概念中。您还说过,应该对有关于地理、文化、民族、身份认同及国籍同构性的简单假设进行质疑。这样看来,“华语电影”概念的出现是因应了地缘政治变化的复杂情形,或者说它是一个文化妥协的产物?
鲁:确实有这个问题,地缘政治的变化加上文化自身的变化,必须要找到一个大家能够一起讨论的问题。这既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际问题,就像刚才说到的,台湾学者老说自己的电影是“国片”,那样内地学者就没法跟他说话了;但内地学者认为台湾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一部分,台湾学者也没法跟内地学者沟通了。当时首先是要解决交流过程中的这个实际问题,否则大家连话都没法谈了。
李:事实上,海外学术界,在面对中国境内外以汉语为电影语言的电影时,其所用的概念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比如您提到,在裴开瑞(Chris Berry)1991年编著的《中国电影面面观》(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nema)中,该书名里的“中国电影”虽为单称,但它分章节对中国内地、台湾、香港电影一一做了研究。在1994年出版的尼克·布朗(Nick Browne)等人合编的《中国新电影:形式,身份,政治》(New Chinese Cinemas:Forms,Identities,Politics)一书中,中国电影显然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地区三个在内的复称实体。该书编者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三个地区电影业的差异,但仍保留了“中国”这一统称。而您本人1997年主编的《跨国华语电影:身份认同,国家,性别》(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Identity,Nationhood,Gender)一书则加上了限定词“跨国”以表示对那些常常为民族电影研究者所忽略的纷争不断的地区的关注。1998年出版的《牛津电影研究手册》(The Oxford Guide to Film Studies)也在“世界电影”的总标题下分列了中国电影、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几个条目。海外学术界对“华语电影”命名的变化反映了什么?
鲁:海外学术界也有一个摸索的过程,当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合适的表达模式,只能是不断摸索。像你刚才提到的,尼克·布朗等人在《中国新电影》中特别用复数的cinemas来强调内地、香港、台湾所分别代表的中国电影的多样性,这说明他们一直在摸索着表达的概念。坦率地说,我是挺满意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跨国华语电影)和Chinese-Language Film(华语电影)这两个概念的,因为它们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但这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概念,像你说的,“跨国电影”或者“华语电影”概念确实能解决很多积留的问题。但现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史书美教授又提出一个更新的概念——Sinophone(华语语系),这个也是周蕾教授经常用的词汇,这里面包含了比较强的意识形态立场,就是抵抗中国中心主义的“去中心化”的倾向。其实这里面的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比如他们常用李安的电影作为分析的文本。李安是台湾出生的导演,被作为Sinophone cinema的代表人物;但李安拍电影用的演员是章子怡、邬君梅这些来自中国内地而又具有跨国性质的演员,电影拍摄的场所又是在中国内地境内,而拍摄资金常常又是国际化的,这种多元性已非常复杂。不能说一个人出生在台湾,他就是Sinophone的代表人物,这样反而忽视了复杂性。
李:您讲到Sinophone cinema,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近年来会引起较大争议和讨论的一个概念,这一点从2007年12月哈佛大学开的一个Sinophone学术会议上就能够看出来。Sinophone这个词到底怎么翻译比较好?我问过史书美教授,她回答说,针对不同的概念,可以采用不同的称呼:针对文学,可以讲华语语系文学;针对电影,可以叫华语电影;针对音乐,则称华人音乐。但她针对的核心,就是您刚才讲的,是中国中心主义,因此她的Sinophone意识中,是不包括中国内地的。这一点王德威教授跟她的立场不太一样,认为无论如何应该将中国内地包括在内。刘禾教授的说法更明确,她认为目前美国大学的东亚系都在教中国现代文学,还没有一所是在教所谓的不包括中国内地文学在内的华语语系文学的。
鲁:华语电影可以有点变化,我认为它可以包括中国内地电影。实际上最初台湾学者提出这个概念,目的也是要让内地、台湾、香港几个地方的电影谈到—起,如果照现在某些学者对Sinophone的理解,将中国内地排除在外,那不如像原来一样直接叫国片、内地片得了。不过从这里也显示出,海外学术界一直在探索新的概念和阐释模式,因为我们中国既存在着地缘政治和文化的复杂性,同时又面临着全球化语境下“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削弱——老是用“国家”概念,讲不清楚什么事;而现在又确实存在着文化上的合资生产,像《还珠格格》,内地、香港、台湾的演员在一起,三地的观众也都喜欢看,完全是泛中国化的文化现象。邓丽君的歌曲也是这个问题。我曾经说过,地理、文化、民族、身份认同及国籍同构性的简单假设是值得怀疑的。文化与地理疆界并不同质,最传统的民族国家理论是将文化和地理套在一起的,比如我们过去是在中国疆土范围内谈论中国文化、中国电影,但现在这个东西分开了,这是新现象,值得研究。
李:我看到您的“Dialect and Modernity in the 21st Century Sinophone Cinema”一文被翻译为《21世纪汉语电影中的方言和现代性》,在国内学术杂志上发表。但Sinophone cinema等同于“汉语电影”吗?“汉语”比“华语”的范围好像要窄一些,包括很多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都可以用来表现上述的文化现象。
鲁:还是“华语电影”比较好,“汉语”在内地用得多,台湾用“国语”。“华语”较为中性,大家都能够接受。
李:“汉语”、“国语”的争论,变成了政治主体建构的一个象征方式,这是很有意味的。如果寻找到一种较为通属的概念,这个并不容易。但不管怎样,概念的命名本身是值得分析的,命名者的主体意识本身都可以构成一个学术话题。
鲁:这就涉及命名者的“身份政治”。你从哪里来?从内地、台湾,还是香港?你的经历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的立场,这个非常明显。史书美谈Sinophone,其实她所参照的phone的研究有两个模式:一个是Anglophone(英语语系),这个概念比较好,包括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在内所有讲英语的地方;另一个是Francophone(法语语系),只包括法国以外讲法语的地区,如北非、越南、魁北克,他们把法国以外叫Francophone Literature(法语语系文学),法国国内的叫French Literature(法国文学)。史书美的Sinophone选择的是Francophone(法语语系)的模式,而不是Anglophone(英语语系)的模式,因为后者把英语文学全部都包括在内了。我最近写了一篇很严肃的书评,跟她探讨这个概念的缺失。
“跨国华语电影”研究:国族·语言·文化
李:“跨国华语电影”(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主要是由您提出来的,我注意到这是一个复数概念,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几年过去了,对这个概念的认识有什么变化吗?您说过,存在“一些既不在中国境内拍摄、也不是由中国制作,而是由境外投资制作并主要是在国际电影市场上发行的跨国华语电影。因此,华语电影是一个涵盖所有与华语相关的本地、国家、地区、跨国、海外华人社区及全球电影的更为宽泛的概念。语言与国家之间的不等同性和不相称性表明了当今世界华人之间在国家和文化联系方面既存在一脉相承之处,同样也存在着裂痕与分歧”;您还说过,“种种迹象显明,似乎只有在恰当的跨国语境中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民族电影。人们必须以复数的形式提及中国电影,并且在影像制作发展过程中把它称作跨国的。中国个案中的跨国主义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做观察:第一,19世纪以来,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分成了三个地缘政治实体——内地、台湾、香港——由此而来,这三个地区之间出现了中国的民族电影、地区电影的竞争与合作。第二,在20世纪90年代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国电影的生产、销售、消费的全球化。第三,电影话语本身对中国及中华性的表述与质疑,即对内地、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中个人或群体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族群认同以及性别认同的交叉检验。第四,一次对中国‘民族电影’的重新回顾与审视,就好像是在回顾性地阅读跨国电影话语的‘史前史’。这一过程旨在揭示民族电影话语的政治潜意识——电影的跨国根基与条件。这些是任何一个民族电影规划必定要克服与超越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免受实际的或假想的帝国主义的危害,或是为了迫使少数民族保持沉默来维持国家统一”。
鲁:用复数比较清楚。其实,单数也并不是单数,它实际表示一个集合体,里面包含着不同的区域,以及各种各样的影响力量。所以即使说单数,也要知道跨国电影不是死板一块。当然我认为用复数更好一些。
李:目前海外学术界对使用这些概念达成某种共识了吗?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目前在国内学界“华语电影”还不是一个完全合法化、有确定含义的概念。海外学者对该概念的理解与内地学者的理解有很大差异。
鲁:“跨国华语电影”(translational Chinese cinema)这个词现在已非常流行了,电影研究界基本上不假思索的使用,甚至说用得太滥了。从这一点来说,大家在研究术语上也基本有了一点共识。像张英进教授写的几本书也用这个概念,裴开瑞最近要为一个杂志编一个专辑,也在用“跨国电影”这个概念;另外,我和台湾及香港学者提出的“华语”(Chinese-language)这个概念,大家也基本上接受了。目前大家还在做这个领域的研究,所以上述两个概念还是产生了一些共鸣的。毕竟,使用“华语电影”,所指的范围更广一点,也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我也觉得不能老是重复以前说过的概念,应该尽量不断地将研究向前推进,去发现和思考一些新的现象。既然要出一本新书,就要做出新的努力,看能不能把一些问题引入新的层面去探讨。
李:由内地、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社群所构成的“华语电影”的整体性研究视角,对过去单独研究“中国电影”,提出了哪些新的课题或挑战?
鲁:一个是在范围的描述和界定上,跟以前讲“中国电影”不一样了;还有就是在一些具体的研究论题上,也有了较大变化,像您说到的“国族”概念、语言问题、身份认同问题等等,都重新提出来了。运用“跨国电影”或“华语电影”这样的概念,比起以前简单地从语言、民族、文化疆界的同一性角度去思考问题,显然更加复杂,也更有可能解决现代的问题,因为到了现在的全球化时代,人在流动,身份也在变化,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一个人可能有好几种身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王爱华(Aihwa Ong)教授就提出“灵活的公民”这个概念,就是说有些人有两个护照,你很难确切地说他是加拿大人还是香港人,因为他的身份在变:他要做生意,就说是香港人;他要获得福利,要上学,就说是加拿大人。看似机会主义,实际上反映出全球资本主义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就是要不断积累财富,寻找机会,扩大生产。所以使用“跨国华语电影”这些新概念,更能描绘当今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而且可以跳出传统单一的“民族国家”的概念,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民族国家会消失,今年我们看奥运会,觉得民族国家依然很重要。
李:今年我的一个研究生在做有关海外华语电影研究中的跨文化批评问题的论文,希望借助于对海外华语电影研究成果的专题整理,透视这一研究领域的趋向和实质。我提醒她注意从本尼迪克特的“想象的共同体”角度去探讨海外华语电影研究中的“国族想象”和身份认同问题。那么,在您看来,“国族想象”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为海外华语电影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大家对此的探讨形成了哪些意见?
鲁:“国族想象”绝对是海外华语电影研究中非常中心的—个议题,对于海外华人学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切身的实际问题,比如说到我鲁晓鹏的身份,如果我一直生活在北京,那身份非常简单,但现在在国外这么多年,身份问题就有点不清楚。所以说句不好听的话,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大家多少都有点精神分裂症,你有时会有好几种身份:早上九点我给美国学生上课,身份是美国公民;晚上九点我打开电脑上网看中国消息(我90%时间喜欢上中文网站),那时我的身份是什么?起码在文化意义上我是中国人。早上九点上班跟晚上九点上网时的身份认同差异这么大!电影有时就是探讨这些身份问题,不是像我一直住在北京那么简单。香港、广东那一带人,来来往往,出出进进,也有同样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跨境的流通越来越频繁,所以华语电影研究的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跟现实生活有关的问题。
李:说白了,就是一个文化和身份的认同问题,这一点在海外华语文学的写作与批评中也表现得极为明显。就华语电影而言,这种“国族性”的身份认同是极为复杂的,除了涉及不同时期的差异之外(比如,30年代面对日本侵华时所拍的中国电影跟80年代走向世界的中国电影的认同是不一样的),即使在每个时代内部,它还跟电影生产的各种复杂背景紧密相关。谁的电影、谁的国族、谁的认同等问题就自然出现了。到底谁在制作,拍给谁看,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您怎样看待华语电影在海外华人文化认同(或者有时还表现为相反的“离散”)中的作用?海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分歧是否很大?
鲁:我觉得分歧还是很大的,因为移民当中,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学者之间也不太一样,大家一般不愿回到简单的单一的民族国家这个程度上,这样一来就非常复杂。拿最近的例子讲,李安拍《色·戒》,就引起很大争议,美国人可能不觉得里面有什么,但是在华人社区争议特别大,因为这里面涉及汉奸问题,而这个又反映出我们今天的身份认同问题。你是不是中国人?面对历史,你的立场是什么?这个牵涉到很多人内心深处的问题,虽然隔着几十年,但对中国人来讲,依然是—个核心问题。
李:您说得对,美国人不会去关心和理解中国人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对电影中的性表现不太感兴趣。我是去年11月份在洛杉矶看的《色·戒》,当时电影院里只有不到十个人,其中只有两三个美国老人,大概还是冲着里面的性描写去看的。我跟国内同事聊起看这个片子的感受,有些认为在艺术上是有探索的,但也有不少人对制作者的立场表示反感,认为这是在为汉奸正名。这就回到您刚才说到的问题,到底这个电影想表现什么?
鲁:当然这里面有表现人性的主题——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通过做爱,做成了人性问题;但这里面更有民族问题。我是去年12月份在香港城市大学旁边的“又一城”看的《色·戒》。我研究电影,看电影很少流泪,但这部电影最让我感动的是,前半段青年学生在香港示威游行演话剧,王佳芝对邝裕民说,她哥哥抗日死掉了,哥哥就像你,妈妈天天想他。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的民族情结特别浓,那时候我流眼泪了。虽然现在我是美国公民,但我对历史有自己的看法,即使是美国人对历史也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李:您后来还讨论了华语电影方言与区域现代性的关系,认为“是否运用本土和地方方言,这是电影文化想象——台湾的本土认同、内地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历史——文化中国——的重要标志”。您分析了当代中文电影生产中的方言样式,以及它们在地方、民族、亚民族、超民族和全球等几个层面关涉到当代中文电影的身份建构。不仅跨区域(内地、香港、台湾、海外华人社区)的华语电影研究的复杂性凸显了,中文世界内部以及中国内地内部因方言而产生的主体性理解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在您看来,方言可能构成当代华语电影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吗?它是否引发了“杂语共生”的多元格局?主体性的建构还可能吗?
鲁: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国民党时期就颁布过禁止方言的电影政策,电影中不许讲广州话;后来内地广电总局有时候也下通知不许用方言演,可能这个政策贯彻得不太彻底,有时候一些电视剧、电影还是在使用方言。但方言不等于地方意识,比如贾樟柯的电影确实在用山西方言,但并不是说他的电影有山西意识。贾樟柯的观众是全中国观众,同样,赵本山小品的观众也是全中国观众,不只是东北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的是地方方言,传达的精神却是全中国的意识。我有时在想,有没有一种方言,它传达的信息是真正区域性的?可能真正地道的粤语确实有这个味道。香港电影就使用粤语,这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没有粤语,香港特色就差得多了。不懂粤语的内地人最陌生的就是香港电影,因为粤语的使用增强了电影的地方性,使用台语的台湾电影也有这个问题。虽然我听不懂这些方言,但它嗯嗯呀呀的调子,能让你真正感受到那种乡土气息,这是真正的区域性的东西。贾樟柯的电影没有太多区域性的东西,他电影里的方言只是一种摆设,他讲的是全中国的生存状况,现代化的反差,像《小武》活灵活现的人物,但那个故事可以发生在中国任何地方。所以从方言研究华语电影,有时也会觉得很有意思。
李:能否介绍一下海外华语电影研究中的“性别”视角?这已成了大多数电影研究学者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像张真《银幕艳史》、崔淑琴《镜头里的女人:百年中国电影中的性别与民族》等书就对此作了集中探讨。您在《中国电影史中的社会性别、现代性、国家主义》(《民族艺术》2000年第1期)中提到,中国电影中国家主义的建构从一开始便与社会性别构成密切的联系,通过性别化了的话语将中国的历史与国家主义性别化是中国电影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后来,阶级意识掩盖了性别身份。在中国新电影中,社会性别差异的重新发现与个性的重新发现是同步的。
鲁:女性研究学者可能对这个问题会有更好的解答,因为她们更关注这一问题。在我编的那本《跨国华语电影》的论文集里,有一辑专门谈性别问题。性别研究确实构成了中国电影研究的重要视角。从中国最早的上海电影,女性就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化身,通过女性的身体,来探讨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什么《神女》、《体育皇后》、《三个摩登女性》……中国早期的女性电影太多了,后来也是这样。美国电影也有这个问题,可以说,任何电影都希望通过性别来阐述更大的问题。但是我们男性学者有时候要注意:你是要用女性的身体去讲更大的问题呢?还是真正关注女性的身体呢?有时候我们喜欢用女人去讲民族问题、国家问题,讲翻身闹革命的问题;这时候有些女性学者会说,你们不要利用女性身体讲其他问题,你就看女性的生存状况本身,关注女性的身体本身。性别问题我觉得非常值得研究,这方面我也非常尊重周蕾、史书美这些女性学者,觉得她们有时候生气,也有道理。比如周蕾有时候非常生气,你读她的文章,字里行间确实对中国父权社会表现出强大的愤怒,有时候话说得非常激进,但是我可以理解。
中国电影产业:现状与出路
李:在目前的情形下,西方电影节对中国民族电影发展的影响仍然巨大。在您看来,学术界对这一关系的反思是否足够?能否从跨国电影生产角度,评价一下电影节对第六代导演的未来影响?
鲁:我觉得很可惜,西方电影节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仍有很大的影响,到现在中国影人还没有走出这个限制,比如某部电影在戛纳电影节或威尼斯电影节得奖,还是对这个导演的地位或这个电影的命运、对电影的发行传播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文化资本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上海电影节做不到像西方大的电影节那么大的影响,台湾的金马奖目前在华语电影研究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但还是不行;香港的电影节也还不行,目前还是西方在控制话语权,一时还很难超越。话语权非常重要,它对电影发行影响很大,如果某部电影得到金熊奖,那么它的全球发行就好多了,这个现实目前还没有太大变化。但是现在出现了另外一个现象,像张艺谋的《英雄》,并没有得什么大奖,但是它非常好看,它不需要得什么大奖,也能在全球放映,甚至成了美国外语片中票房最高的一部电影。它不需要戛纳电影节,电影节也不会给这种电影颁奖,因为它不是艺术片,这是个值得考虑的新现象。而像冯小刚这样的导演,关注的是中国观众,他的片子做得再好,却不能吸引西方观众,这也是个悲剧。其实,西方观众也不一定不愿看冯小刚的电影,问题是目前没有人去推广,西方人也不愿意去炒作它,这一点很可惜,电影发行商应该多加关注。
李:冯小刚本人对此倒是想得开,他这次在南加大研讨会上说他就是在为中国观众拍电影,因为中国观众群体实在太大了,这也不失为一个思路。您刚才提到张艺谋,我注意到您曾在《民族电影,文化批判与跨国资本——张艺谋的电影》一文中,针对中国本土批评家指责张艺谋模式的电影在国际上贩卖中国民族文化这一批评,作了这样的分析:“考虑到国内日益萎缩的电影市场、电影审查制度以及中国电影产业的变化,所谓的‘东方主义’,也就是逃到全球文化市场上去,这未始不是中国影人一种生存和再生的策略。”您表达出这样的信息,即像张艺谋这样的影人,是借助跨国资本继续他们的文化批判的。在这里,我有这样一个疑问,在您看来,这个时候真正吸引国外观众的,究竟是导演本身的深刻意识形态,还是东方主义的细节这一表层?
鲁:我觉得这两者都有。西方世界对中国有一种认识,认为中国就是像张艺谋电影所展示的那样古老而神秘,这样一来,为了让西方人接受,中国的艺术家就会生产一些电影来迎合他的认识,不然西方人就不看,因为他们的认识还没有达到你想要的那个程度。当代西方的—些媒体,像CNN,也有这个问题,它播放的关于中国的节目,总是有个定式,所以想一下子改变西方人的认识并不容易。聪明的导演可能知道这一点,他就生产出一些容易被西方人接受的电影。我希望有一天,冯小刚的电影,像《一声叹息》、《手机》,也能在西方放映,让西方人看看当代中国人的生活,而不要总是《英雄》、《十面埋伏》或《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所叙述的那个古老的世界。但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有时候我教课时想给学生放映《手机》,但它没有英文字幕,美国学生看不懂,我只好放弃。我不明白很多内地电影为何连英文字幕都不打,而任何一部香港电影都有双字幕(英文和中文),也许商人们觉得,冯小刚的这种都市电影只限于国内,美国人不会看,但可以试一试嘛。
李:涉及西方的还有独立电影问题,这也是国内电影研究的一个新兴话题。据我了解,海外学术界对中国独立电影是十分关注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刘禾教授这个月初还主办了一个关于中国独立电影的展映和研讨会。海外对中国独立电影的态度似乎肯定居多,这表明了什么?里面是否包含了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立场?在这种跨国文化资本运作下产生的独立电影真的可以“独立”吗?
鲁: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中国独立电影过去的确存在因为使用跨国资本而带来的“不独立”的问题。不过这几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民间投资进来了。我出版《跨国华语电影》一书是在1997年,十年前中国民间的资本还不够,但现在有些独立制片人已不需要跨国资本,他自己在社会上就能弄到钱。张艺谋现在也可以不需要跨国资本了,这件事情过去是做不到的,像他拍《大红灯笼高高挂》必须要跨国资本,而现在他拍电影,国内的民间资本足够支持他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所以现在我可以说,跨国资本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现在中国内地民间资本很多,独立制片人不是官方指定的,他拍什么、怎么拍,由他自己决定,因为他用的是自己的钱,或是他朋友的钱,或者谁给他的钱,而不是荷兰人、法国人、日本人或美国人给的钱。有些题材官方不会让你拍,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电影探索一些被忽视的东西,还是值得支持的。当然如果还是用跨国资本,拍摄的思维方式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李:这种民间资本越来越多的投入,会慢慢改变中国电影的生态吗?
鲁:我觉得会。十年前,我们不会探讨这件事,因为那会儿中国人没钱,或者有钱也没有意识去投资电影艺术。比如《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的拍摄,都有跨国资本在里面,中国人当时没有那么多钱,没有人愿意给陈凯歌或张艺谋一亿人民币拍电影,现在可以了,给你三千万或一个亿,没有问题。《英雄》的拍摄用的就是民间的钱,不是跨国资本,是张伟平他们自己的制片公司出的钱。这样一来,就不一定非得走国际路线了,张艺谋不要国外的票房,在国内也能挣些钱;像冯小刚用社会制片这种做法,也就把票房纪录慢慢积累起来了。这也说明中国电影在进行一些新的尝试,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电影产业会渐成规模,这也是华语电影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新领域。反过来说,这些不走国际路线而完全依靠国内发行的电影,在社会反思和社会批评功能的层次上,就要做出极大的妥协。
(说明:本访谈稿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项目“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海外视野”相关成果,并经鲁晓鹏教授本人审阅。限于篇幅,访谈稿的另一部分《从比较文学到电影研究》另文发表。刘丰果、王永志等协助资料整理,特此致谢。)
标签:华语电影论文; 华语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语言论文; 台湾内地论文; 新视野论文; 色戒论文; 台湾论文; 剧情片论文; 综艺节目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