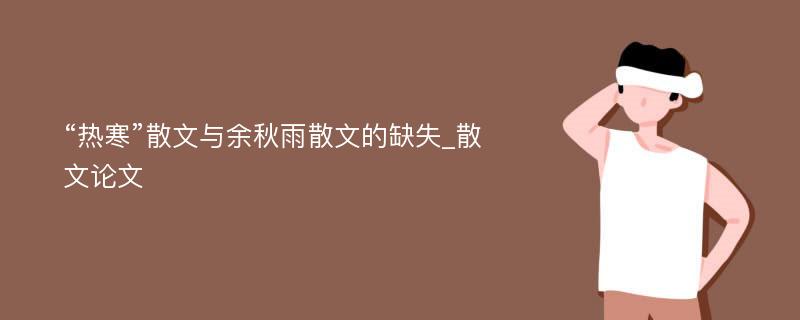
散文的热与冷——兼及余秋雨散文的缺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缺失论文,秋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说热,诗歌热,如今轮着散文热了。这是从写作者一面说的,若从阅读者一面说,应当是小说热,传记热,如今轮着散文热了,因为从阅读者这面说,诗歌从来就没有热过。对眼下的散文热,好些人都作过分析,有的说是快节奏的生活,不容许人们读大厚本的小说,篇幅短小的散文便乘虚而入,填补上这个空档。有的说,人们厌恶虚情假意的社会风气,连带的也对虚构的小说也失去兴致,这样一来,以写真情实感见长的散文便受到青睐,交了桃花运。
这样的分析,只是事先的搪塞。平心而论,我们的生活节奏是比过去快多了,但还没有快到读不起小说的程度,小说不光有长的,也有短的,何以短篇小说更不景气?若说写真情实感便走俏,新诗中不是没有写真情实感的,何以老也走不进寻常百姓家?
以体裁论长短,终不免偏颇。什么时候都有好些的小说,也都有好些的诗歌和散文。什么时候,也都有些人爱看小说,有些人爱看诗歌或者散文。我不否认,这两年散文确实够热的,写的人多,读的人也多。和先前的小说热、传记热比较一下,或许看得更为清楚。先前的小说热,热的不是小说这门叙事艺术,而是它的别的负载,即对不允许肆意揭露的社会现实的肆意揭露,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刚粉粹“四人帮”后的伤痕文学。同样的道理,传记热也并非人们都想做伟人,而是长久的封闭,人们总想对伟人的深层生活一探究竟,看看他们和常人有何不同。眼下的散文热又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呢?我看,反映的是人们闲散的心理,不是太忙了,而是太闲了。正经事不做,看闲书(小说)又看不进去,东抓抓,西摸摸,还是看点小有情趣的散文混日子吧。
这是从社会心理上说的,从文学发展上说,又不同了。
必须看到,我们的文学,经历过将近三十年的隔绝,粉碎“四人帮”后,好些人“拿起笔作刀枪”所凭恃的,不是艺术的追求,也不是文学的功底,更多的是激情,是义愤。这一点,从当时作家素质上,不难看得出来,大多是中学毕业生,尤以知识青年为多。他们受的屈辱多,要倾吐的欲望也就强烈。
如今看来,有一个现象是值得玩味的。那就是,这些人写小说,写诗,写创作谈,但很少有人写评论、写散文。这是什么呢?不可否认,有对这两种文体的不屑的成分在内,同样的不可否认,也有这两种文体不那么好写,或不容易写好的成分在内。不屑和不能是有区别的。写评论你得有点理论素养,写散文你的文字功力要更强,还得有点文化素养,至少也得有点文史方面的知识,才不至于出乖露丑。这就不是刚放下农具,从田野上走来的知识青年作家们轻易敢问津的了。
这些年,情形大变。一是当初那批写小说或诗的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文化素养也在不断的提高,已不满足于仅仅写小说或诗,有了更多的人生感悟或闲情逸致,需要用散文这种文体来表达。二是随着整个社会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的文化知识和生活情趣都在提高,舞文弄墨的人多了,作为初起步的练习,或仅仅作为生活兴趣并不打算进入文学殿堂修行,那么,写散文自然是最明智的选择。三是散文这一文体,毕竟可以直接地反映眼下的生活现实,可以便当地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当然,读者的需求,也是个不小的促进。
将社会心理和文学发展两方面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就知道这两年的散文热,绝非无源之水,而是其源有自了。
说了散文热形成的原因,再来说散文的写作与欣赏。我是把写作与欣赏混在一起说的。因为两者实际上是一致的。会写作的人,也必然会欣赏,欣赏品位高的人,若动起笔,也差不到哪里去。这只是一般而论,不是说没有只会写不会欣赏,或只会欣赏而动不了笔的。
这个题目太大了,只能从戒忌的角度来谈。等于是说了热再来说冷。
一戒畏难。这是把写散文,甚至整个写作看得太高太难的缘故。写作,到了一定水平后,能否更上一层楼,全在你的心态,你的思想境界。写散文尤其是这样,可以说,从一起首,就看你的心态好不好。心态平和自然,笔下就轻灵生动;心态躁急做作,笔下必然生涩板滞。写作者是怎样的心态,笔下是瞒不了人的。
有个文学现象,或许有人已注意到了:一般来说,专门写散文的作家写出的散文,大都不太好,反倒是小说家、诗人、学者,也就是那些不是专门写散文的作家写出的散文,更胜一筹。解放后,专门写散文的作家,或者说较早地专门从事散文写作且声名昭著的,一是杨朔,一是秦牧,他们的散文,从品相来说,都不算太高。只能说各人都还有各人的特色,不失为一家之尊。过去的中学课本上,选了杨朔的《泰山极顶》,这是一篇典型的杨朔写法的散文。去泰山看日出,没有看到,看到了人民公社这轮朝日在齐鲁大地上的冉冉升起。我们上学时,课本上还选过他的《海市》,写的是去长山列岛,以为该看到海市蜃楼的模样,结果看到的是人民公社化了的新渔村,比虚幻的海市还要美丽。记得还选过他的《荔枝蜜》。公允地说,杨朔这类散文,是适宜于中学生,尤其是初中学生模仿练习的。选上一篇也就行了,选这么多,让学生以为这就是散文的正途,只会提倡一种矫情的文风。顺便说一句,我觉得中学课本上选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也太多了。
现在的中学课本上,已没有《泰山极顶》这篇散文了,换上去的是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也许编者不是这样一下一上考虑的,可实际的效果,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撤下一篇换上一篇的。这篇散文就不同了。写的都是生活的真实感受。作者毫不讳言他登泰山遇雨的失望,时间有限,不能再来,只好冒雨登山,所谓慰情聊胜于无。日出是肯定看不上了,看到的是雨中的山色,雨中的云烟,那景色也是很绚丽,很动人的。譬如写山中飞瀑的一节——
明明有水流,却听不见水声。仰起头来朝西望,半空中挂着一
条两尺来宽的白带子,随风摆动,想凑近了看,隔着宽阔的山沟,
走不过去。我们正在赞不绝口,发现已来到一座石桥跟前,自己还
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细雨打湿了浑身上下。原来我们遇到另一类
型的飞瀑,紧贴桥后,我们不提防,几乎和它撞个正着。水面有两
三丈宽,离地不高,发出一泻千里的龙虎声威,打着桥下奇形怪状
的石头,口沫喷得老远。从这时候起,山涧又从左侧转到右侧,水
声淙淙,跟我们到南天门。
曲折尽意,又生动传神,不愧是大手笔。这里须订正一下,第一句“明明有水流,却听不见水声”,应是“明明有水声,却看不见水流”之误。按常情推断,看见水流是毋须听见水声的,只有听见水声,才会寻找水流,寻找只能是往下看,往山沟里看,找不见,再抬头观望,没想到那水是挂在半空中的,两尺来宽的白带子,且随风摆动。一惊一乍,写出了飞瀑的奇妙。李氏写字潦草,有“天书”之称,文稿多是其家人抄录,或许是抄录中的笔误吧。
李健吾是个戏剧家,翻译家,写这篇散文,在他是不经意而为之,心态好,感觉好,如实写来,就成了千古名篇,一点不比姚鼐那篇《登泰山记》差。晚年,李健吾和一位晚辈谈到这篇散文的写作时说:“我那篇《雨中登泰山》忽然受到重视,入了中学课本。当初也不过是一时若有所感,把当时的感受如实地记下来罢了。”
再譬如评剧演员新凤霞,过去是个文盲,解放初嫁给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后才开始学文化,“文化大革命”中下半身瘫痪了,在丈夫的帮助下开始写散文,写自己的身世,写自己的生活感受,文笔清新自然,别有一种朴素的美。至今已出版二十多本书,成为一位独具特色的散文作家。
二戒随便。这一条,正可与上一条互相发明,互相制约。心态好,随意些,并不是说随随便便,越不正经写越能写好。那样理解,就错了。在各种文体中,无论从篇幅上说,还是从写作技巧上说,散文都是最容易写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好些年轻人,一上手总是先写散文,尤其是女孩子,更是这样。当然,也有的是先写诗歌。学写作如同学艺,凡是入门容易的,深造必然艰难;凡是入门艰难的,深造相对就容易些。在写作领域里,散文和诗歌,都是入门容易而深造难的。有人年轻时偶尔写了一篇好的散文,得到世人的称赞,便以为写散文很容易,说不定自己是个写散文的天才。直到晚年方才醒悟,原来人生并不如自己设想的那样美妙。这可说是上了散文的当,大点说是上了文学的当。
有些名家的散文,一看就是精心写出来的,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影》。有些名家的散文,看起来很随便,似乎就是那么信手胡乱写出来的。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作者才气绝对的大,随便写出来,也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样的人是天才,我们凡人是不可比拟的。再就是,他追求一种随意的风格,这是他的聪明,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要让人看起来像是漫不经心写出来的。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很愚蠢吗,骡子卖了个驴价钱。不以成本定价,不以市场规范行事,这也正是艺术所以为艺术的地方。
这两年,余秋雨的散文很走红,真可说是到了谈散文不谈余秋雨就是不识货的地步。他最初的散文集子叫《文化苦旅》,说的大都是他趁讲学之便,去各地作文化古迹考察,以及考察中生发的种种感慨。或许正是因了这书名和这内容,人们给他的散文起了个高贵的名目,叫“文化散文”。似乎先前的散文都是没文化的,独有这一家的是有文化的。实际上,过去这类散文另有个名字,叫学者散文。譬如“文化大革命”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内蒙访古》,就是一边写自己的游踪,一边对眼前所见到的古迹作历史考察或考证。只能说余秋雨的散文,更偏重于文化意义上的考察与阐述,因而也更能激起对这种文体感到新鲜,对古代文化知之甚少的年轻读者的兴趣。
他最著名的一篇该是《道士塔》了。写的是当年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将大量经卷卖给外国探险者的事。作者的描画很细, 感慨也很深。譬如,说到当时政府的腐败,绝不可能保护这些经卷,也绝不可能开展郭煌学的研究,几乎是呼天抢地的说——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
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
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
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这义愤是很有感染力的。和《内蒙访古》相比,我们就会发现,后辈人更会写文章了,仅仅根据一些简单的文字记载,他就可以推想出当时的具体情形,且绘声绘色地将这些写下来。譬如对王道士用白灰涂佛像一事,作者是这样写的——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
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
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来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第一遍石
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究个干透。什么
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
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
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
了刷把。
这哪里是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若老一辈学者,写到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于史无征,断然不敢这样信口雌黄,因为那些洞窟里的雕像,固然有被涂了石灰水的,可你凭什么说就是王道士做的?为什么不会是多年后的一个李道士,或者说是当时政府为了保护雕像不被风蚀而特意涂上去的?——是想象,是推测,也得说在明处,别把什么都说成是真的,就像亲眼见过似的。
这篇文章布局很精巧,共四段,每段都不太长,行文也自然有致,该描述的地方描述,该议论的地方议论,没有化不开的痞块,也没有过多的游离于主题之外的笔墨。然而,读过之后,我的感觉是,作者写这样的文章肯定不轻松。这一点,从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也不难看出。他说好些年以前他写过一些史论专著,曾有记者撰文说他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种自己给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一提笔就感到岁月徒增。而他的这些散文,就是当做史论写的,比写史论更难的是,他还得编造莫须有的情节,还得使整个文章像艺术的创造。这该有多难,怎么能轻松得了。记得不久前看一则报道,说是余秋雨对人说,他今后不再写这类文化散文了。往后再也看不到这么有文化的散文了,这该多么让人伤心,看来那句“圣人不出,其如苍生何?”得改为“圣人隐去,其如苍生何!”
我却只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为我们的文坛悲哀,为我们的年轻读者悲哀。哪有作家风头正健时,突然宣布搁笔的道理?急流勇退,是有这种说法,可那说的多是官场,文坛又不是官场,怎么将官场的运作方式搬到文坛上来了?——莫非真的意识到,再写下去会有什么凶险?笑话,这样的盛世文章,谁敢说有什么违碍的地方?
说白了,是余秋雨的散文原本就不是什么创造,不过是一个也还有些才气的读书人的精心结撰。时间一长,就陷入自己制造的模式之中,难以摆脱,也就难以为继。宣布搁笔,算是一种最体面的逃遁。
你会说,哪些是真的有绝大才气,“从心所欲”就能写出上好散文的作家呢?我举两位,一男一女,男的是郁达夫,女的是张爱玲。这两位都是以小说出名的,但他们的散文也都自成一家,那真叫好。
三戒因循,即落入自己或他人的套子中。文学写作所以称为创作,就是因为它是以创新为标志的。这也正是文学写作的迷人之处,任你有天大的本事,都能使得出来。今天看到韩少功的一篇文章,叫《第一本书之后》,是写给一个文学朋友的信,其中引用了一位作家的话:“什么叫创造?创造就是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来一个决定性的推倒。”这话说得太对了。不是我苛刻,报刊上的散文,大多是平庸之作,没什么新意,甚至没什么意思,只能说是看了一串字。偶尔看到一篇好文章,那是能让人眼前一亮,精神为之一振的。凡是好的散文,总是有所创新的,或是意境上,或是形式上,往往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
最近我注意到一位散文作家,叫卫建民,常在报刊上写些关于文化考察与思索的散文,应当说是位青年学者了。他的文章,我看的不多,最初是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一篇写的《平阳的落日》,不久又看到一篇《寻访丹枫阁》,前者大气磅礴,后者沉郁饱满,一看就是高手。更为可喜的是,从文章中看出,他是山西洪洞县人,知道我们省有这样年轻、这样够水准的文化人,我是很高兴的。不久前,在临汾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我见到了他,比我想象的要大些,有四十岁了。原是学财会的,如今在北京一家商业出版社工作。闲谈中得知,近一年来,他请了长假,在全国各地漫游,领略风土人情,观赏山水与文物,有所感悟,便写成文章,在固定的两三家报刊上发表。眼下正在写的一组文章叫《三晋纪闻》,打算将来出本书。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的那两篇,就是这个系列里的,还在《作家》杂志上发表了三篇。我说回去要找来看看。
从临汾回来后,找见这三期杂志,上面的三篇文章分别为《阎锡山这个人》(《作家》1995年第7期)、《乔家大院》(《作家》1995 年第8期)、《天下无二裴》(《作家》1995年第10期)。我都看了, 确实写的不坏。和余秋雨的路数相近,却又不太相同,他有余秋雨对文化的热心,又多了一份审视的冷静,有余秋雨的博览与博识,运用起来更为节制,也发些感慨,总是那么审慎,不像余秋雨那么义愤填膺,大而不当。最大的不同或许在于,我相信我的这位老乡不会在某一天突然宣布搁笔。他有毅力,更有功底和技巧,会永不停歇地写下去。只有别人不让他写,不会他自己不去写。
详细分析卫建民的散文,得写一篇长文章。这里,我只想说说他写文章的注重技巧,不落俗套。《天下无二裴》,全文不足四千字,写的是他去山西闻喜县裴柏村,寻访有名的河东裴氏。这个家族,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望族,两千年间,将相辈出,仕宦如林,正史立传的有六百多人,位居宰相的五十九人,大将军五十九人,进士六十八人,还出过二十一位驸马。裴家最为显赫的时期是晋代与唐代,如今的裴姓,可说成了极普通的姓,与张姓李姓没有差别。天下无二裴,是说普天下的裴姓,都是从裴柏村的裴家繁衍出去的。如今的裴柏村里,连裴姓也不多了。说是寻访,究其实不过是去裴柏村里走了一遭。
我们且看他是怎样写的。一起笔先是——
您贵性?
不敢!免贵,姓×。
在中国人的日常交往中,初次见面问对方的姓,已成了一种习
惯,一种礼仪。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人的名字无关紧要——
他顶多是一个符号,一个父母的昵称,一个时代的投射。它主要属
于个人和小小的家庭。人的姓呢,则比名字古老。它是一个人的历
史血型,一个家庭的社会属性。——当一个人说出姓什么时,他就
说出了一部凝重的家族史。
任谁,尽管对作者一无所知,仅凭这一段“开场白”,也会一下子就被作者这样工巧的开头,这样精辟的见识所折服。
接下来是几段论述,主要是说,出身对人的重要,出身不明,就像人身上有暗疾一样,向来讳言。在中国,凡是著名的大姓望族,都必然在历史的进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世人有“南林北裴”之说,那么,今天裴姓的人流逝在何方,河东裴姓安在哉?行文至此,作者才说,“二月里,我乘上同蒲线的慢车,在礼元下,专门去了一趟裴柏”。
由此说到裴柏村的现状,那么好的风水,又那么贫瘠。他去裴氏祠堂,工人们说,钥匙在村支书手里。
按说该写去找村支书要钥匙了,不,他荡开笔,这才写裴氏在过去两千年间的功业,由三支五房,具体地说到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书》,出资为柳宗元安葬的裴行立,再往上推到南北朝时的历史学家裴松之、裴骃、裴子野,再拉回唐代,说了平靖淮西的裴度。又由裴氏的世代英贤,想到此中会不会有社会学、遗传学上的原因。即使裴氏灭绝,也令埋在深层的化石,保存着生命的基因。
这才写找到老支书范怀喜。他说自己刚从夏县来,看了司马光墓,老范的儿子马上接过来说:“他们那里就出了一个宰相,我们这里出了五十九个。”领着作者去祠堂的路上,老范得意地对场里劳动的村民说:“专从北京来的!”写到这里,作者找补了一句:“把我这天涯独行客介绍给了他统治下的小民。”一路上还有些别的描写与对话。末尾一段是这样的——
我跟着裴柏村的支书,在光秃秃的峨眉岭上展望未来,四处巡
视;然后来到简陋的祠堂土墙外,来到大门前,听老范打开了一把
大锁,推开两扇沉重的大门……
读到这时,你不能不佩服作者行文的巧妙。反始为尾,又非通常的倒叙,一下子就将我们推进了黑洞洞的历史,而他,这聪明的家伙,却轻轻地放下了手中的笔。
这样的格局,看似信手写来,全不经意。我不那么看,没问过建民,不知他这格局是怎么来的,不过,我想,即使是飘然而至的灵感,在确定之后,他也会反躬自问,这样奇崛的格局,别人能接受吗?管他呢,就这样吧。这最后的敲定,才真正见出整个人的学识和才气。
别的戒忌,还能说几条,主要的,就这么三条。我不敢说记住了这三条,就能写出好的散文作品,就能品评出一篇散文作品的好坏,那得看各人的资质与功底,还有各人的心性与偏嗜,但我可以说,记往了这三条,肯定会在你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提高你写作的技巧,提高你作品的品格,至少也会对你遇到的散文作出恰当的判断,若好,能说出好在哪里,若坏,也能说出坏在哪里,不会让人家懵了你。
1995年1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