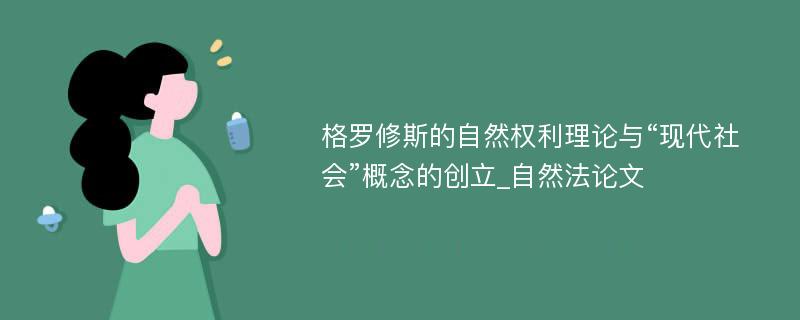
格劳秀斯的自然法权学说与“现代社会”理念的创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权论文,现代社会论文,说与论文,理念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512(2013)12-0138-12
荷兰思想家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凭借其在大航海时代所撰写的《海洋自由论》以及在三十年战争时期所写作的《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被后人视为现代国际法之父。尽管如此,格劳秀斯并不是一位仅仅着眼于具体法律问题的法学家。格劳秀斯的著作能够流芳百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理论分析建立在一种新颖的自然法学说之上。这个自然法学说重新说明了人类的基本秩序原理,不仅为国家间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思路,而且将道德哲学与政法哲学带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国际法领域外的学者投身到对格劳秀斯自然法学说的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格劳秀斯的自然法学说通过借鉴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的方法,重新构建了一种不同于中世纪思想的全新道德政治学说。他们将其界定为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世俗主义、个人主义、激进主义的现代自然法学说。萨拜因、卡西尔、登特列夫、基尔克等人均持这一观点。①随后,许多学者发表了与此不同的看法,给出了更为谨慎而保守的判断,格劳秀斯的现代特征被大大降低了。考克斯指出,虽然格劳秀斯的自然法学说具有某种现代色彩,但是他“仍然主要是朝向古代经典”。②西格蒙德指出:“很难说,格劳秀斯的论点标志着自然法与神学的分离……他并没有在神学预设之外来发展他的学说。”③笔者认为,格劳秀斯自然法学说的原创性在于,面对现代怀疑论的语境,阐发了一个具有高度现代性特征的“社会”理念,将其作为人类各个层面之行为的规范性框架。这个思路引导了后来的现代自然法思想家,其所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成为现代自然法的核心问题,其所面临的内在困难成为了现代自然法不得不去处理的难题。
一、格劳秀斯自然法权学说的语境:现代怀疑论
在探讨格劳秀斯的具体思想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它是在怎样一种道德政治局势下被提出来的,它是为了应对怎样一种道德政治问题,即它的“语境”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格劳秀斯提出其自然法权学说的“意图”是什么,才能理解他的论证策略,把握其自然法权思想的独到之处。④格劳秀斯处于一个与古典时代和中世纪颇为不同的现代语境。根据塔克的研究,格劳秀斯的对手是亚里士多德与卡尼阿德斯,前者指向传统政治思想,后者指向十六世纪晚期的现代怀疑论。就当时的语境而言,格劳秀斯对现代怀疑论的批判更为重要。格劳秀斯在《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的“导言”中写道:“由于如果不存在法权这样一种东西,那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徒劳的,所以为了说明我们这项工作的有用性并将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在这里简要反驳非常危险的一个错误做法。我们不能同时处理大部分人,让我们来处理那位倡导者吧。还有谁比卡尼阿德斯更为合适呢?……他说,法律是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创建的,因此,法律具有不同的样态,不仅不同的国家因为不同的习俗而有着不同的法律,就是同一个国家的法律随着年代的变迁也是变动不居的。关于所谓的自然法权,那不过是个种幻想而已。自然激发所有人乃至所有动物去寻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根本就没有正义,即使有的话,那也是极端愚蠢的事情,因为它教导我们损己利人。”(IBP,79)⑤
塔克所提到的卡尼阿德斯(Carneades,214/3-129/8 BC)是一位古希腊怀疑论者。同时,塔克指出,格劳秀斯真正的靶子是米歇尔·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和皮埃尔·萨隆(Pierre Charron,1541-1603)为代表的现代道德怀疑论。在16世纪早期,基督教世界发生了宗教改革。基督教神学丧失了构建道德政治秩序的权威与能力。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甚至连最基本的和平共处关系都无法维持。宗教改革运动与反宗教改革运动在西方世界的各个角落点燃战火,内战与国家间战争此起彼伏。中世纪自然法学说不仅无力而且不利于构建一个普遍道德秩序。面对基督教世界的崩溃,以蒙田和萨隆为代表的道德怀疑论应运而生。他们主张人类的道德与法律信条及相应的实践活动具有根本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任何普遍道德原理。显然,道德怀疑论不仅无法为西方的道德秩序奠定规范性基础,而且忽视甚至敌视这项工作。⑥
现代怀疑论不仅反映在伦理学上,而且也反映在政治学上,产生了当时占据欧洲主流的国家理性学说。国家理性学说的思想教父是马基雅维利,它摧毁了中世纪的国家学说与传统的公民哲学。根据维罗里的研究,在十六世纪中晚期,“国家理性”学说最终获得了对公民哲学的胜利。博泰罗与博卡利尼为国家理性学说提供了具有理论高度的正当性论证,使之名正言顺地成为“政治”的新内涵。⑦在“国家理性”学说的逻辑中,“国家的必需”(necessity of State)具有无可置疑的主导性地位。这使得任何实定法则、道德法则、宗教法则都无法获得能与其对抗的平等地位。虽然,在“国家理性”的诞生地意大利,之后几个世纪都没有人能够成功地恢复公民哲学的政治话语,但是如果放眼整个欧洲,我们就会发现,就在十七世纪早期,已经有一位思想家开始对抗这种学说。他就是格劳秀斯。⑧
道德怀疑论与国家理性学说支撑着一种看待国家间关系的现实主义立场。当格劳秀斯着手写作《捕获法》,试图阐述国家间法权秩序时,他开始反思现代怀疑论的立场,因为如果道德相对主义是人类行为的唯一标准,如果国家理性学说是国家行为的唯一标准,那么就很难从根本上为国家间的正当行为规范提供一个证明。国家间秩序问题其实就是万民法权问题,但是在十七世纪三十年战争时期,万民法被主流的现实主义者视为可笑的东西,因为他们认为国家之间不可能存在规范战争与和平行为的法权关系。格劳秀斯发现,现实主义立场是当时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主导价值。他写道:“我观察到,整个基督教世界在战争问题上都不守规矩,即使最野蛮的民族也会对此感到羞愧:他们基于非常琐屑之事,甚至有时无任何理由,就兵戎相见。而当战争一旦发动,就法权的尊重就荡然无存。”(IBP,106)在当时的欧洲,不仅没有任何法权规范在各国的对外政治实践中起作用,而且知识界对法权的研究也颇为冷清。格劳秀斯写道:“市民法(无论是罗马的还是其他民族的)已经有人对其加以研究……但是那些对许多国家或许多国家的统治者来说共同的法律,无论它是来自于自然法,还是由神圣命令所建立的,还是由习俗和默示同意引入的,却鲜有人触碰。”(IBP,75-76)
格劳秀斯的语境是现代怀疑论,这是中世纪自然法思想所不曾面对的问题。它包括道德怀疑论、国家理性学说和现实主义国际立场。现代怀疑论用利益与力量取代了正义与法权,这造成了欧洲国内外秩序的混乱。格劳秀斯试图说明一种国家间法权规范,用以调整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和平事务,反驳“在大国中,较为强大的一方就是正义的一方”,(IBP,76-77)即现实主义国际立场。同时,他试图阐述一种国家法权规范,用以调整公民与所在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和平事务,反驳“对一位国王或独立的城邦来说,只要是有利可图的事情就不是不正义的事情”,(IBP,76)即国家理性学说。格劳秀斯完成这两个任务的方法是提出一种可以对抗道德怀疑论的自然法权学说,将其作为国家间法权和国家法权的基础。这个语境说明格劳秀斯的自然法权并不是为了解决所有的传统自然法思想问题,它甚至不关心人们如何做出最好的道德行为和如何过一种最好的道德生活这些自然法重大问题。其自然法权的特定目的是:用一种以自然法权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理念,在持有不同的道德(宗教)观念的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基本行为规范,以保障和平有序的共同生活。格劳秀斯完成这项任务的首要工作是修正“法权”(ius)这个基本概念的内涵。
二、法权与自然法权
现代怀疑论认为法权仅仅是人们各自利益与意志的产物,因而不具有自然基础。格劳秀斯必须在多变的利益和任意的意志外找到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第一原则作为法权的自然基础,说明自然社会正义原理。这个自然基础就是“社会性”。格劳秀斯在援引了卡尼阿德斯的怀疑论观点后接着写道:“人类的确也是一种动物,但是他却处于一个较高的位阶上。……有许多行为只能恰当地显现于人类身上。例如,对社会的欲望是人类所特有的,就是与他的同类共同生活的确定倾向。这并不是说以任何方式一起生活,而是和平地生活于一个共同体中,并根据他的最佳理解力来调整这个生活。因此,斯多亚学派将这种倾向称为‘Оιкειоσιυ’,所以那种随处可听到的称每种造物都依其本性最求自己的好处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概略描述的这种社会性,或者说依照与人类的理智之光相符的方式来关心社会的保存,是真正的法权(ius)的源头。”(IBP,79-86)
社会性是“真正的法权的源头”,那么社会性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对社会的强烈欲望”与“关心社会的保存”意味着什么呢?格劳秀斯接着写道:“这种法权要求戒取他人的财产,归还任何属于他人的东西(或从中所得的利益),要求自己遵守诺言,恢复自己的不践行义务而造成的损害,应当接受人们的惩罚。”(IBP,86)法权的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戒取他人的财产,归还我们手中任何属于他人的东西(或从中所得的利益),要求自己遵守诺言”的正面要求;“恢复自己的不践行义务而造成的损害,应当接受人们的惩罚”的反面要求。“反面要求”将留至本文第四部分分析,我们先对“正面要求”追问以下三个问题。首先,为何它仅仅针对个体间相互行为的消极关系(“戒取”、“归还”、“遵守诺言”),而非对人类整体的正当关系的积极安排?其次,为何它具有如此有限的内容,而不包括人类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最后,它如何获得作出“要求”的规范性效力?为了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需要对照格劳秀斯从三个角度对法权内涵的阐述。
法权的第一重含义是指“正义的东西,而这里的正义是消极意义上的而非积极意义上的正义……而不正义是指与理性动物所构成的社会的本质相冲突的行为”。(IBP,136)法权的第二重含义来自于第一重含义,但是却与之不同,因为它“直接与个人相关”。它是指“个人所具有的一种道德品性,使之能够正当地拥有某物或做某事”。(IBP,138)这种道德品性分为两种:“如果这种道德品性是完备的,就被称为特权(faculty),如果是不完备的,就被称为倾向(aptitude)。就自然事物而言,前者对应着行为(act),后者对应着能力(power)。”(IBP,138)只有指向具体行为的“特权”才是准确意义上的、严格意义上的法权。法权的第三重含义“具有和律法相同的含义(在律法最宽泛层面上而言),它作为道德行动的规范,责成我们去做好的和值得赞扬的行为”。(IBP,148)法权的这层含义包括两个方面。就形式而言,法权具有约束力,因而不同于建议。就内容而言,“这个意义上的法权并不仅仅属于正义之事,它还属于其他德性”。(IBP,149-150)
由此可见,法权具有“正义”、“个人法权”和“法”这三重含义。法权的内涵可以分为法权的实质(内容)与法权的形式(约束力)两部分。其中,“正义”与“个人法权”中的“特权”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法权严格意义上的内容。格劳秀斯指出,我们只能从不正义入手来分析正义,而不正义的核心内容仅仅是对他人“特权”的侵犯,而不涉及人的其他德性问题。这里的“特权”是具有高度主观性的个人权利。格劳秀斯认为,如果我们从“严格意义”上来谈论法权的话,我们可以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解释正义。⑨但是,正义并不可以被纳入到个人权利范畴中,正义依然超出完全“个人主义”性质的个人权利,而落在“社会的本质”上。⑩这里的“严格意义”是那些指向人的“行为”(包括对物的行为和对人的行为),具有对应义务,并且可以通过强制手段加以维护的个人权利,那些可以被“法律化”的个人权利,而非孤零零的个人权利。(11)法权的正面要求指向的不是囊括人类所有德性的共同体的美好生活(积极的),也不是有关个人权利的自由生活(积极的),而是具有法律性质的自然社会生活,因此正面要求仅仅针对个人间的消极关系。
如果社会性是法权的源头,那么它就能够为这种法律秩序提供具体内容,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社会性的具体内涵,即法权(社会性)的正面要求为何是“维护他人的财产,归还任何属于他人的东西(或从中所得的利益),要求自己遵守诺言”(IBP,86)这一特定内容以及法权义务为何仅仅包括这几点和格劳秀斯在这里所省略掉的“他人的身体和生命”、“遵守契约和誓言”等内容。格劳秀斯写道:“社会的设计是,每个人应当在整个共同体的帮助下,借助于整个共同体的联合力量来安享他的‘属己’(suum)。我们甚至可以轻易地发现,即使我们所说的财产权还没有被引入时,为了自我防卫而诉诸暴力的必要性也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的生命、肢体和自由,依然是我们的‘属己’,不可能在不违反正义的情况下被侵犯。使用共有的东西,消耗这些东西,只要是自然所要求的,就是首先拥有者的法权,如果任何人试图阻止他,那么这个人就犯下了一桩实在的侵犯。”(IBP,183-184)
从表面上看,法权的内容是人的法权义务,但是这些义务并非来自某个更高的义务,而是来自于个人权利,来自于人的“属己”,即正当地属于一个人自己的东西。它包括一个人的肢体和生命,一个人的所有物(财产),一个人的债(即他人的所欠,debt)。从原初意义上讲,“属己”仅仅包括一个人的“生命、肢体和自由”,但是这里的“(自然)自由”意味着人具有控制自己正当行为的自然能力。它包括人是否实施这个行为的自由,也包括将这一能力转让给他人的自由(确立起一项法权关系)。“属己”这个元概念具有非常特殊的含义。一方面,“属己”发挥着“权利”的作用,类似于一种“准权利”。另一方面,“属己”与“权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前者属于自然范畴,后者属于道德范畴。除了“保卫自己肢体和生命的法权”外,其他自然权利是“属己”通过某种契约(基于人的自然自由)而扩展出来的。契约能够肯定、扩大或缩小一个人的“属己”,从而形成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权利义务关系,完成“社会的设计”。(12)这个权利义务关系的重点(并非全部)是一种以财产权为核心的社会结构,而非完全的个人权利或个人利益。格劳秀斯是通过对财产权起源的契约论来说明这个问题的(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法权具有“社会性”这个自然来源,格劳秀斯指出:“法权还有另一个来源,即上帝的自由意志。”(IBP,90)法权的这两个基础之间是什么关系?在回答法权的内容时,格劳秀斯没有谈及上帝,因为社会性是上帝赋予人的。在回答法权的约束力问题(即法权的第三重含义)时,他不得不直接处理上帝的自由意志。如果法权的约束力不仅仅是利益权衡的结果(怀疑论的观点)的话,它就必须具有内在的义务性。基于这个内在义务性的不同来源,格劳秀斯将法权区分为自然法权与意愿(voluntary)法权。(13)意愿法权的义务性来自于人或上帝的意志,分别对应人意法权(人为实定法)和神意法权(神圣实定法)。市民法权和万民法权是典型的人意法权,摩西十诫是典型的神意法权。自然法权则较难理解。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自然法权与神意法权在法效力问题上的隶属关系。如果自然法权的法效力来自于意愿法权的话,那么自然法权就与上帝的自由意志有直接的关系,自然法权的形而上学神学基础这个理智论与意志论所争议的问题就无法回避。事实上,格劳秀斯并没有认真对待或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格劳秀斯认为神意法权的法效力来自于自然法权的话,那么他就持有一种完全世俗主义的立场。但是,格劳秀斯认为神意法权可以使得某些自身不具有义务性的事情具有义务性(IBP,153)。因此,这两种解读都是不正确的。
格劳秀斯指出,自然法权是“正当理性的规则和命令,它根据与一个来自于社会性的理智本性是否相符,显示了任何行为中的道德缺陷(deformity)或道德必要性,因此,这一行为要么是被上帝(自然的作者)所禁止的要么是被上帝所赞许的”。(IBP,150-151)自然法权的基础是“正当理性”,是“社会性的理智本性”。自然法权所指向的行为“本身就是义务性的或者非法的,因此而必须被理解为受到上帝的要求或禁止”。(IBP,152)上帝仅仅在此基础上施加约束,而不是反过来。显然,上帝的意志在自然法权中的重要性被大大削弱了。自然法权本身就具有“义务性”,上帝只不过在此基础上添加上“禁止”或“赞许”。
格劳秀斯曾指出:“确实,我们上面所述必将会发生(即自然法权的存在——笔者注),即使我们承认——不顶着最深重的罪名就无法承认——上帝并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不会关注人类事务。”(IBP,88)许多学者据此将格劳秀斯的自然法权学说定性为世俗主义,似乎是有所根据的,但这绝非一种彻底的世俗主义。自然法权基本上独立于上帝的意志,但不并完全独立于上帝的意志,更没有高于上帝的意志。在法层级上,上帝的意志高于人,神意法权依然高于自然法。自然法权的独立是通过“神意法权的许可”来实现的。格劳秀斯指出,摩西律法所明确要求的戒律与自然法权必然是一致的,但是摩西律法还包括一种许可,特别是一种“不完整的”许可,它“最好是诉诸自然法权的原则来发现”。(IBP,176-178)
自然法权不仅要具有独立性,还需具有自足性。这个自足性包括其效力上的自足性和内容上的自足性,它们来自于社会性以及“来自于社会性的理智”所显示的“任何行为中的道德缺陷或道德必要性”。对此,我们有必要追问,社会性要求的是何种意义上的社会和何种性质的社会规范关系?另外,社会性如何能够在不直接借助于上帝之意志的情况下带来“道德缺陷或道德必要性”?具体到格劳秀斯所倚重的财产权概念,我们可以追问:财产权起源的契约论和自然法权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三、财产权的起源与社会的历史结构
社会性是一种“正当理性”,但是按照传统基督教神学,“正当理性”是上帝的理性,而非人的理性。在自然状态、堕落后状态与恩典状态这三种不同状态中,人的理性是不同的。堕落后的尘世状态涉及意志论者所强调的原罪问题。如果人没有原罪而是道德完善的造物,那么正义就是多余的。如果人有原罪的话,人的理性必然是有所欠缺的。托马斯为了拉近这两种理性,打通这三种状态,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启发,提出了一种具有目的论色彩的“自然倾向”概念。意志论者则坚持,人类是无法完全具备正当理性的,因为这种理性是基于上帝的自由意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格劳秀斯试图用财产权来打破这种不同状态之区隔,用财产权的历史来重新解释人类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重新说明人和自然的关系。财产权表征了人的权利,财产权的历史为人类的社会生活秩序设定了严格法律性的自然法权结构,人类的正当理性完全可以证明其必要性。因此,理解以正当理性为基础的自然法权,我们需要考察格劳秀斯对财产权起源的重述。“属己”是人的自然所有与自然能力,“法权”是人的法定所有与法定权利义务。两者的内容基本相同,但是前者指向每个个体,而后者则指向个体所组成的社会。因此,“社会”这个规范空间如何产生的问题也就是“属己”构成的自然图景如何转化为主要由财产权所构成的法权图景并获得自然法权效力的问题。格劳秀斯也是通过对财产权起源的说明来回答这两个问题的。
首先,我们需要注意格劳秀斯对“财产权”的界定。格劳秀斯重构了“财产权”(do minium)这个概念的内涵,将其限定为一种与任何性质的财产共有(或包容性财产权)无关的排他性私有财产权(包括自然使用权与严格意义上的财产权)。格劳秀斯在《海洋自由论》中指出:“如今,dominium严格来说意味着,属于某个人的东西不能以同样方式属于另一个人,而我们所说的共有是指,通过排除其他人的睦邻关系和协议来给予一些人以所有权……在远古时期,共有就是指那些与私有(proprio)相反的事物。而dominium是指使用某种共有之物的正当或合法能力……如今被称为法律上的使用或依权利的使用是某种所有权(propriety),或者说(我以他们的方式来说)是对他人的排除。(14)
格劳秀斯是在自然法权的范畴中论证这种财产权的。神意法权并没有直接说明财产权的起源,并要求确立财产权。在格劳秀斯这里,财产权的直接来源不是上帝的神意法权,而是自然法权。尽管如此,自然法权其实并没有直接要求财产权,财产权的产生无疑与人的意志有关,而非完全自然的产物。但是,格劳秀斯认为,财产权的确立是符合自然法权的,即我们可以在自然法权的范畴中谈论财产权的起源问题。那么,自然法权是以何种方式对财产权做出法权要求的呢?这涉及“什么属于自然权”这个问题。格劳秀斯认为,有些事物是自然法直接要求的,有些事物则是以“化约的方式”(Reduction or Accommondation)被归属到自然法中,或者说属于“许可性自然法权”。格劳秀斯写道:“这种方式是指,自然法权并不与这些事物相矛盾。正如我们将某些事物称之为正义,是因为它们不含有不正义。……这里所讲的自然法权并不仅仅与那些独立于人类意志的事物有关,而且也与许多人类意志行为的结果有关。因此,以现在所讲的财产权为例,财产权是由人的意志所带来的,而一旦财产权被许可(自然法告知了我们这一点),那么违背一个人的意志夺走恰当地属于他的东西就是一些邪恶的行为。”(IBP,153-154)
“许可性自然法权”使得财产权可以在自然法范畴中,通过某种方式得到证成,获得其内容与约束力。“许可性自然法”是自然法传统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财产问题密切相关。十二世纪的教会法学家最早提出了“许可性自然法”,来解决格拉提安的《教会法汇要》中有关“自然法要求财产共有,而人类的习俗和实定法要求财产私有”这个矛盾。他们认为“许可性自然性”使得人们可以在自然法没有硬性要求的情况下,享有实施某些行为,确立某些制度(例如确立私有财产或其他形式的财产制度)的自由。(15)与此不同,格劳秀斯(与苏亚雷斯一样)认为,“许可性自然法”不是一种自由,许可意味着约束力的命令。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格劳秀斯是如何来具体说明财产权的起源,并赋予其约束力的。
格劳秀斯依然在基督教的神圣历史中来谈论财产权的起源问题。上帝将世间万物赐给所有人享用。每个人基于“所有人共有的使用法权”,“使用自己需要的东西,消耗那些需要被消耗的东西”。(IBP,420-421)。自然法的基本戒律是,给与每个人属于他的东西。“没有人可以正当地夺走他人首先得到的东西”,(IBP,421)即其他人的“属己”。“属己”是自然使用权的基础,自然使用权在内容上起到了财产权的作用,(16)界定了人类原初的生活规范。如果人类停滞于这种原始阶段,人心不会生出各种孽端,那么自然生活其实是不分你我之物的完美生活,财产权也就是多余的东西。但是,人类历史表明,人类社会必然会向“前”发展。农业与牧业日渐发展,物品日渐增多,人心日渐不古。其中最糟糕的是人的奢望之心,它带来了妒忌、抢夺、谋杀等等。因此,人们必须通过契约来对界定你我各自的财产权。(IBP,420-427)格劳秀斯总结道,财产权“来自于某个约定或一致同意,要么是明示的,例如通过一种划分,要么是默示的,例如通过占据”。(IBP,427)格劳秀斯从两方面重塑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一方面,人和自然的关系仅仅是某种财产关系,而非任何目的论性质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的核心是排他性的个人私有财产权,而非某种具有内在关系的人类整体财产安排。另一方面,人和自然的财产关系并非一种纯自然关系,而是建立在契约这种人类合意行为上,其具体方式取决于不同的历史与习俗。那么,这种合意行为的约束力从何而来呢?
笔者认为,格劳秀斯的确为自然法权找了一个新的必然性来源,但是它不是一种“逻辑的必然”,而是财产权起源中的“历史的必然”。财产权是格劳秀斯从自然法权角度,重新阐述人类的处境与人类应当去实现的目的的切入点。这是财产权起源问题的真正意义所在。在格劳秀斯看来,财产权的历史是人类的历史(特别是社会的历史)的核心。财产权的自然史能够为人类行动设定规范性框架,建构起一种普遍社会秩序原理,即战争与和平的法权原理。
格劳秀斯所讲述的财产权起源史是一个整体。在他看来,这个历史并不是偶然的,不是任意的,而是必然的。人类的发展是必然的,人类的恶也是必然的。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必然处境。社会的历史结构为法权提供了必然性,因为它限定了人类的特殊处境,也限定了人类应对这个处境的特殊方法,限定了人类社会的特殊组织方式。“社会性”正是从这个历史中获得其正当性,获得其法权基础的地位。(17)社会的构成并非源于托马斯的自然理性和自然倾向。格劳秀斯需要在摆脱托马斯的神学目的论和实践理性立场的同时,克服原罪问题带来的人的不同状态之区隔,将社会奠定在普遍性的抽象法权原则之上。格劳秀斯找到了一个既能表征所有人在任何时候的法权地位(即具有普遍性),又能滤去原罪(即具有世俗正当性)的东西来以之证成一种世俗规范,即财产权(的历史)。(18)同时,格劳秀斯为正当理性探寻自然法提供一个基本可靠的途径:考察历史。两者结合在一起的结果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法权结构,即自然法权的社会结构。对现代人来说,这个社会法权结构越清晰越精细,则他们的生活就越和平越舒适。
其次,社会的历史恰恰是个人权利逐渐构成的历史。也就是说,社会的历史与个人的历史是相互建构的。原初的社会形态由于人的“反社会性”而无法维持,而新的社会形态恰恰是通过将这些“反社会性”欲望落实为规范性权利而非通过重建某种“相互的爱”而形成。这意味着现代社会的构成并不旨在于消除人的“反社会性”(及其带来的暴力),而在于将其加以限制和规范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将自然法权的重心从自然法转移到自然权利(财产权)后,暴力问题就无可避免地成为自然法权需要回应的一个重要问题。格劳秀斯写道:“正当理性和社会的本质,并不禁止一切形态的暴力行为,而只是禁止与社会相违背的暴力行为,即剥夺他人权利的暴力行为。因为社会的目的就是每个人在整个共同体的帮助并借助于整个共同体的联合力量来享受它自己生命与财物。”(IBP,51)这涉及下面要讨论的惩罚问题。
四、惩罚法权与社会的强制力来源
与格劳秀斯一样对欧洲战争乱象深感悲痛的人还有以伊拉斯谟为代表的和平主义者。伊拉斯谟在在多部反战作品中指出,战争是一种赤裸裸的罪恶,没有任何正义性可言。万民法是荒谬的东西,不可能存在所谓“正义战争”的概念。格劳秀斯非常清醒地看到,这种高贵的和平主义道德除了发出道德谴责外,对于国家间秩序的重塑毫无益处,而且它还隐含着一个危险的观点,即战争是无法受到法权制约的,人类不可能对战争进行立法。(19)如书名所示,《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不仅包括关于和平的法权秩序,也包括关于战争的法权秩序。格劳秀斯不仅通过财产权说明了社会的道德基础,而且通过惩罚法权说明了社会的暴力来源,或者说强制力来源。
法权除了正面要求外,还包括两个反面要求:“恢复自己不践行义务而造成的损害”和“应当接受人们的惩罚”。“损害”是指“一个人享有的东西少于他的法权,无论是仅仅来自于自然的法权,还是来自于某些加上去人类行为,例如财产权建制,契约或法律”。(IBP,885)“惩罚”是指“基于我们自己所做的恶而遭受恶报”。(IBP,949)“恢复损害”是侵害人的一项义务,它直接与被害人对其肢体和生命、财产及债的权利相关,其目的是为了复原被害者的个人权利。惩罚与此不同,它是一项独立的法权。它对接受惩罚者来说是一项义务,对施加惩罚者来说是一项权利。格劳秀斯指出:“对惩罚的起源和本质的误解导致许多错误的产生。”(IBP,949)“惩罚的起源和本质”是指如何在自然法范畴内来理解惩罚,主要包括惩罚法权的性质和内涵、惩罚法权的目的与惩罚法权的主体。
并不是任何错误的行为都会导致惩罚。惩罚的前提是侵害他人的不法行为(即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的发生。格劳秀斯认为,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考虑“侵害他人的不法行为”。就受害人本身来说,根据自然正义,侵害人应当“恢复损害”;就规范这种行为的公共之法(例如自然法)来说(就侵害人与所有其他人来说),侵害人“应当接受人们的惩罚”。侵害人虽然没有侵害受害人之外的其他人,但是由于他侵犯了所有人共有的法,他应当受到所有人的惩罚。换句话说,侵害人负有“恢复损害”这一私人性义务和“接受人们的惩罚”这一公共性义务。如果侵害人不主动遵守这两条义务,那么发动战争的两个正当理由就出现了:“为了恢复我们自己的东西,为了施加惩罚。”(IBP,395)(20)
因此,在侵犯他人法权的行为发生后,接受惩罚作为一项自然法义务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它属于格劳秀斯所讲的矫正正义。就像自愿订立交易契约的人一样,“犯下罪行的人自愿地将自己置于某些惩罚之下”。(IBP,954)同时,惩罚的实施要求“做出正当惩罚的人必须享有惩罚权利,这项法权来自于违法者所犯下的罪行”。(IBP,953)也就是说,惩罚法权的社会结构包括接受惩罚的自然法义务和施加惩罚的自然法权利。这涉及“哪些人享有惩罚权利”这个问题。
格劳秀斯指出,自然法并没有指明哪个人自然地享有惩罚权利。传统上人们认为,“上位者”(如父母、主人、官长)最适合成为惩罚主体,但格劳秀斯指出这并不是“绝对必然的”。他认为,所有那些没有犯下相同罪行的人其实都可以成为惩罚的主体,从而享有惩罚权利。“自然法赋予每个人以惩罚权利”,(IBP,972)因为“一个人去救助另一个人这是自然的事”。(IBP,976)(21)尽管如此,格劳秀斯并没有像洛克的“自然法的执行权”学说那样在这个问题上保持非常明确的立场。(22)惩罚的前提必须是已经发生了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而不可以是先发制人,更不可以是为了惩罚而惩罚。(IBP,959-960)格劳秀斯虽然认为惩罚在理论上可以由所有人来实施,但是他总是马上接着指出由于人的偏私性,只有交由公共官员来分析相关事实,确定惩罚的比例,才能保证公平。(IBP,968,974-975)也就是说,在正常的政治生活中,惩罚权利应当由国家享有。虽然格劳秀斯倾向于“惩罚权内在于并独属于共同体”这种传统自然法观点,但是就惩罚权利的来源而言,惩罚权利无疑是人的自然权利。这是他与托马斯、苏亚雷斯等人的一个重大区别。而且,与其他的自然权利不同,惩罚权利不是一种可以被让渡的自然权利,而是一种自然自由。(IBP,970,1021)(23)格劳秀斯所讲的大部分自然权利最终都被他的绝对主义国家所吸纳,但是惩罚权利却依然隐藏在日常政治生活之中。他说:“自然法权起初所给予我们的这种古老自由,只要在没有正义法庭时,就仍然发生效力。”(IBP,970)政治生活的强制力不是被国家完全垄断,私人的和社会的强制力在某些时候亦具有正当性。
格劳秀斯的惩罚自然法权学说的革命性还体现在惩罚的起源与公民权力(civil power)的起源和性质之间的关系上。格劳秀斯最早在《捕获法》中分析了这个问题。160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在马六甲海峡捕获了葡萄牙商船“卡特里娜”号及船上的所有货物。有不少人对此提出异议(包括部分股东),因此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邀请格劳秀斯做法律辩护。在法庭辩护结束后,格劳秀斯在《捕获法》一书中具体陈述了他的整个观点。格劳秀斯的一个主要立论是,葡萄牙垄断东印度的海上贸易是违背自然法的,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为此发动战争是正义的,因此东印度公司享有对捕获物的正当法权。为此,格劳秀斯首先说明了捕获“卡特里娜”号及其货物这种惩罚行为的正当性。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东印度公司并不是“主权国家”,而依照当时“大部分人的观点,惩罚的权力只能属于国家……私人对强力的行使似乎被完全排除在外”。(DJP,133)因此,格劳秀斯接着说明了私人性质的实体在没有司法救济的情况下(如海上冲突发生时)享有惩罚法权。也就是说,根据自然法,“在惩罚权由国家掌控之前(同样没有司法救济——笔者注),归私人行使”。(DJP,137)
《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基本上延续了上述基本观点,只不过明确区分了“恢复损害”和“惩罚”,并在论证上运用了他成熟的自然法权学说。无论如何,格劳秀斯始终坚持一个论点,即在某种“自然状态”下,惩罚权利被赋予每个人及任何联合体,无论其是否文明开化,信奉何种宗教。这种自然惩罚权限于国家惩罚权。这个学说的初衷是为了反驳萨拉曼卡学派的主流观点,证成东印度公司的海上武力行为,确保其海上权利的实现。但它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这个学说使得格劳秀斯所列举的自然法权成为了“异常牢固的权利,具有不容背离的特征”(24),因为自然法权肯定了维护这一法权规范的暴力。自然法权将暴力这种生物性行为纳入到法权范畴中,在证成惩罚权利的同时限定了惩罚权利的范围。格劳秀斯的自然惩罚权学说限制了国家惩罚权,并为公民的私力自救和反抗国家行为保留了一定的空间。(25)
自然惩罚权凸显了格劳秀斯的“现代社会”理念的独特内涵。强制力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自然法权说明了政治的全部实质,那么它就必须要说明强制力问题。如果像格劳秀斯那样坚持认为自然法权是一项和平法,社会性使得人们“和平地生活于一个共同体中”,坚持认为惩罚并不是自然法的唯一约束力,也不是自然法的定义性要素,(IBP,96)那么惩罚权就只能由符合自然法要求的公共权威者垄断。格劳秀斯出于现实原因,并没有遵循这个传统思路,而是赋予任何人以自然惩罚权。问题在于,这里隐含着一个滥用惩罚权的问题。由于理性与非理性并存在人类本性中(格劳秀斯赞同这一点),正当的惩罚与不正当的惩罚很难被严格区分开来。如此一来,自然惩罚权无疑消解了自然法权所构筑的自然社会的政治性,因为自然社会包含着赤裸裸的暴力这一非政治因素。格劳秀斯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虽然格劳秀斯仅仅将战争看作是一种偶发现象,而非一种状态,但是自然惩罚权所带来的暴力因素无疑将破坏自然法权作为和平法的解释力,从根本上挑战自然法权与自然社会的同构关系。(26)在随后的自然法思想家(特别是霍布斯)那里,暴力与社会性之间的内在构成关系被进一步解释出来,暴力成为自然法的一个内在构成要素。(27)
格劳秀斯从“社会”这个角度赋予“自然法权”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概念以新的理论生命力。他以“社会性”为出发点,将“法权”限定为以权利义务对应结构为基础的严格法律概念,抵制宗教和道德分歧对“法权”概念的侵蚀。通过重新界定自然法权与神意法权,他将自然法从神学束缚中适度解放,获得规范世俗社会秩序的独立性和自足性。他的财产权起源学说和惩罚法权学说分别说明了这个“现代社会”的规范结构和社会的强制力来源。格劳秀斯的“现代社会”理念作为理解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范畴,同时赋予国家和国家间的和平行为与战争行为以规范性,回应了国家理论学说和国家间关系现实主义学说。
格劳秀斯的自然法权面向西方的古典传统与基督教传统,并在多个关键问题上对它们做出了批判,例如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阿奎那的自然理性与自然倾向学说,意志论所强调的意志对自然法权的决定性问题,萨拉曼卡学派的惩罚权理论等等。同时,格劳秀斯的自然法权带动了整个现代自然法的发展。如何从自然法、从财产权、从暴力问题来理解“现代社会”的本质(或者说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后世霍布斯、普芬道夫、洛克等自然法思想家反复探讨的核心问题。格劳秀斯所试图确立的规范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领域”成为了现代法理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集中探究的领域。
①Georgre H.Sabine,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Henry Holt and Company,1948,p420-4335.Ernst Cassirer,The Myth of the State,Yale University Press(Sep 10 1961),pp163-175.A.P.d'entrè ves,Natural law:an introduction to legal philosophy,Hutchinson & Co.,Ltd,1951,chapter 4.Otto Friedrich von Gierke,Natural law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1500 to 1800,Beacon Press,1958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 1934),p36.
②Richard H.Cox,Hugo Grotius,in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Edited by Leo Strauss and Joseph Cropsey,Rand McNally & Company,1963,p352.
③Paul E.Sigmund,Natural Law in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MA.:Winthrop,1971),p62.
④关于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意图”等问题,参见以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相关研究。
⑤“IBP”代表《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后面的数字代表页数。引文由笔者译自以下英文版:Hugo Grotius,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Tuck ,from the edition by Jean Barbeyiac.Indianapolis,Liberty Fund,2005.以下标示不再注释。“DJP”代表《捕获法》,后面的数字代表页数。引文由笔者译自以下英文版:Hugo Grotius,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prize and booty,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rtine Julia van Ittersum.,Indianapolis,Liberty Fund,2006.以下标注不再注释。
⑥具体分析参见:Richard Tuck,"Grotius,Carneades and Hobbes",in Grotius,Pufendorf and Modern Natural Law,ed.Knud Haakonssen,Dartmouth Pub Co(January 1999),pp85-93:Richard Tuck,"The 'modern' theory of natural law",in The 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Modern Europe,ed.Anthony Pagde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107-109; J.B.Schneewind,The Invention of Autonomy:A History of Modern Moral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December 13,1997),pp 37-57.
⑦[意]莫瑞兹奥·维罗里:《从善的政治到国家理由》,郑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⑧格劳秀斯并没有直接评论“国家理性”学说,但是他批评了一个与“国家理性”学说颇有渊源的法国思想家博丹。
⑨格劳秀斯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的矫正正义。格劳秀斯用亚里士多德的矫正正义为形式,用他所讲的个人法权为内容,确立起了他自己的正义学说(IBP,118-121,142-144)。格劳秀斯的正义具有两个特点。首先,正义仅仅具有消极意义。它不规定什么是善的(如德性),而仅仅规定什么是恶的,即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其次,正义最终落实在个人权利上。具有“个人主义”色彩的现代个人权利,而非共同体的整体安排成为法权的核心内容(虽然不是全部内容)。
⑩格劳秀斯曾指出,为了避免巨大的危险,自然法权允许将一个无辜的人牺牲给敌人(IBP,1152-1155)。由此可见,自然权利并不是第一原则。在这一点上,《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与《捕获法》有着明显的不同。
(11)社会性的内涵也回应了法权的这个内涵。第一,社会性不是人的自我保存(或自爱自利),而是某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社会性是法权的自然基础,但是这个“自然”不是物理法则或生物法则意义上的自然。第二,社会性并不是人的自然倾向(或自然欲望),而是人特有的一种“理智原则”(IBP,82-83),“一种依照普遍原则来认知和行动的能力”(IBP,85)。社会性指向一种普遍性的,而非个体性的行为准则。
(12)参见乌里韦克罗纳的分析:Karl Olivecrona,Appropriation in the State of Nature:Locke on the Origin of Propert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35,No.2(Apr.-Jun.,1974),pp213-4.
(13)这意味着,就法权的内容而言,我们没有必要区分自然法权与意愿法权。
(14)Hugo Grotius,The Free Sea,trans.Richard Hakluyt,Indianapolis,Liberty Fund,2004,pp20-21.
(15)关于“许可性自然法”问题的思想史参见:Brian Tierney,Permissive Natural Law and Property:Gratian to Kant,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62,No.3(Jul.,2001).
(16)按照《捕获法》中的说法,自然使用权是“某种形式的财产权,但是它是一种普遍的、不确定的所有权”(DJP,317)。
(17)关于社会性与自然法的关系的叙述以及针对格劳秀斯对两者关系的认识的评论参见:Stephen Buckle,Natural Law and the Theory of Property:Grotius to Hum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9-20.
(18)格劳秀斯的这个论证其实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当他将“不含有不正义”的东西纳入到“许可性自然法”中,将财产权确立之前的“妒忌、抢夺、谋杀”视为不正义时,他其实预设了一个实质性的正义观。我们知道他并没有这样一个正面的正义观,而只有一个基于个人权利的消极正义观。因此,这里无疑存在循环论证的嫌疑。回头去看,由于格劳秀斯已经提出了法权的个人权利内涵,他似乎可以完全采用自然权利的角度来重塑财产权的起源,而无需借助于“许可性自然”和“历史的必然”,但是这样做就需要一个更强的自然权利立场,例如洛克的劳动财产学说。
(19)林国华:《鱼果·格劳秀斯的若干问题:〈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导言”研究》,《北大法律评论》2010年第2期。
(20)发动战争的另一个理由是“为了防卫”(IBP,395)。“这项自卫法权直接来自于对我们自我保存的照料(自然将其赋予每个人),而非来自于侵害者的不义或罪行”(IBP,397)。
(21)格劳秀斯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有一个思想转变,参见:Gustaaf van Nifterik,Grotius and the Origin of the Ruler's Right to Punish,Grotiana 26-28(2005-2007).
(22)参见洛克《政府论·下篇》第7-13段。
(23)参见尼夫特瑞克的分析:Gustaaf van Nifterik,Grotius and the Origin of the Ruler's Right to Punish,Grotiana 26-28(2005-2007),pp410-415.
(24)Benjamin Straumann,The Right to Punish as a Just Cause of War in Hugo Grotius' Natural Law,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thics 2(February 2006),p15.
(25)格劳秀斯所讲的自救和革命仅仅是一种审慎考量之举,而非基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政治行为。这是因为,格劳秀斯所论证的自然法权社会结构具有较强的历史与习俗特征,而他的契约论又采用了绝对意志论的逻辑,这使得自然权利无法成为挑战政治合法性的宪法性基本权利,无法充分证成人民的反抗权。尽管如此,它无疑启发了后来的宪政主义著作家(如洛克)。
(26)解决这个困难的一个方法是用一个非(前)政治的“自然状态”来同时容纳暴力和自然法。霍布斯和洛克都提出了一个“自然状态”概念,并将暴力和自然权利看作是自然法的两个最重要要素,从而彻底消解了传统政治思想的“政治生活是自然的”这个命题。格劳秀斯的“社会性”(“社会”)概念同时说明了人的自然秩序、国家秩序和国家间秩序。在某种意义上,三者具有相同的自然法“社会结构”。这个逻辑显然容不下一个与“政治状态”相区别的“自然状态”。参见扎克特对托马斯、苏亚雷斯、胡克、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执行权学说的分析:Michael P.Zuckert,Natural Rights and the New Republican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222-240.
(27)参见李猛:《“社会”的构成:自然法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