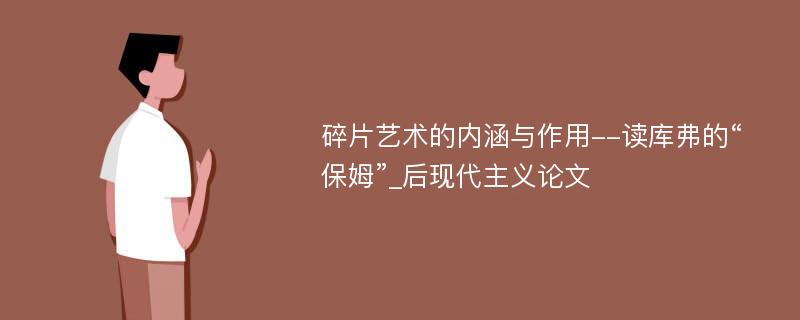
碎片艺术的内涵与效果——读库弗的《保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碎片论文,保姆论文,内涵论文,效果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0)04—0052—06
雅各布·科歌(Jacob Korg)在《现代文学中的语言》一书中说:“实验性作品常常看似毫无形式, 倒像由断裂的碎片构成。 ”(注:Jacob Korg,Language in Modern Liter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Limited,1979),p.120.)他说的“实验性作品”显然指的是后现代主义作品。从书的标题看,他说的是现代主义文学,但从内容看,他的讨论涉及后现代主义文学,只是他未明确地划分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罢了。这不奇怪:许多批评家在六七十年代常把后现代主义文学放在现代主义文学下讨论,将前者冠以“实验性文学”。
科歌的这句话道出了后现代主义作品的形态特征之一,虽然现代主义作品里也出现碎片,但碎片断裂到如此张狂的地步——通篇由碎片构成,则只有在后现代主义作品里才能见到。而且,现代主义作家很少有人宣称如何爱好碎片,但后现代主义作家不同:巴塞尔姆:“碎片是我信赖的唯一形式。”
(《赏月》)
费德曼:“我偏爱不连贯性……我在混乱中打滚儿,我的整个一生都是为它而存在的,是通向混乱的一次旅行!”(《是取还是舍》)
冯尼戈特:“我们周围的世界没有秩序……
相反,我们必须就范于混乱的要求。”
(《冠军的早餐》)
苏可尼克:“现实已成为不折不扣的混乱了。”“我靠混乱而兴旺起来。”(《小说之死》)
加斯:“我们的世界……缺乏意义;缺乏连贯性。”(《虚构与生活中的人物》)
“碎片”(fragment)一词,原指已“脱离”主体、与之“分裂的部分”(a part broken off,detached,见《韦氏新大学词典》),“分裂(break)是它的基本内涵。碎片总是与dissociated(断裂的)、discontinued(中断的)、discontinuous(间断的)、 disconnected(分离的)、 disjoined (不连贯的)、 disjunctive (脱离的)、interrupted(打断的)等这类词联系在一起,这是它的属相。因此, 碎片所显现的(我们不说“表现”,因为“表现”一词已带上了人的意识)是“混乱”,是“不连贯性”,“缺乏连贯性”,一言以蔽之,是与中心分离。
与中心分离意味着中心被分解(de-centred)。没有中心便“没有秩序”:中心在,各组成部分就被聚拢在一起。反之,组成部分离中心而去,中心就骤然瓦解。结果,“仔细一看,我们发现它的全部意义事实上在于,所有的东西仍处在混乱之中。”(注:罗森伯格语,转见于塞奥·德汉:《美国小说和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载《走向后现代主义》,弗克马、伯顿斯编,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心的有无,是现实主义作品、现代主义作品和后现代主义作品的分水岭。可以说,现实主义作品时时处处维护着一个中心,从线性式情节到线性式叙述,从情景的描写到人物的刻画,无一不如此。碎片在它那里是见不到的。
在现代主义作品那里,中心虽不那么赫然在目,但却依稀可辨。它没有现实主义作品中的那种情节结构,它也运用碎片艺术,例如福克纳的《献给埃米莉的玫瑰》,情节结构不是直线的而是环形的——头尾相结,五个部分也大致可看作五个碎片——此处最好说片断,因为其叙述明显存在一定的联系。如第一部分结束时叙述到埃米莉将那些向她要税的人赶跑了,接着第二部分开头就说:“就这样,她把他们彻底击败了,就像三十年前,围绕着那股臭气她击败他们的父辈一样。”但是现代主义的这种运用与后现代主义的运用却是截然不同的。就拿拼贴画这样一种碎片艺术来说,尽管现代主义的拼贴画包含了也许本无干系的各种形象,但却被技巧的整体一致性串联了起来;通过使用同种风格和同种油彩,并根据对称和预先确定好的结构,这些形象可以串联起来。对观者来说,现代主义拼贴画给人以同时性印象;他从不同的角度观看一样东西。而一幅后现代主义的拼贴画,拼凑到油布上的各类碎片却原封不动,每一块都保留了自身的物质性。(注:罗森伯格语,转见于塞奥·德汉:《美国小说和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载《走向后现代主义》,弗克马、伯顿斯编,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257 页。)在《献给埃米莉的玫瑰》中,虽然“臭气”、“毒药”、“死尸”这些事件被分割成碎片,但是读者还是可以将它们串联起来,从中窥见故事的整体性,所以中心还是依稀可辨的。
而在后现代主义作品里,中心荡然无存。碎片突兀而立,“这些片断在基本原理的阐述下望远拼凑不成一体。”(注:罗森伯格语,转见于塞奥·德汉:《美国小说和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载《走向后现代主义》,弗克马、伯顿斯编,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257 页。)加斯的《国土中心的中心》就是一部完全由碎片构成的作品。它共有30节,每节有一个标题,如“一个地方”、“气候”、“我的房子”、“一个人”等等。仅从标题看,就知道各节之间没有连接因素。正如塞奥·德汉所言,“加斯的故事,什么也无法‘聚合起来’;的确无情节、无主题、无人物。”(注:罗森伯格语,转见于塞奥·德汉:《美国小说和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载《走向后现代主义》,弗克马、伯顿斯编,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255页。 )巴塞尔姆的《看见父亲在哭泣》也一样,整篇小说由35个碎片构成,每节都无标题,各节之间用星号隔开。故事中,叙述者说他的父亲被一个贵族驾车撞死,想追查事因,但是他一再看到的是父亲在哭泣,这实际表明存在着两条情节。然而它们不是主、次情节,因为二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小说的最后一节只有“Etc.”(等等)一词。“等等。”实际是“无”,因为“等等”什么也没说,至少没说出什么新东西。换言之,这是篇有头有身却无尾的故事或小说(story),是篇“反小说”(antistory)。而有头有身无尾的故事或小说即是无中心的故事或小说,因为所谓中心(centre),乃是圆圈之中心,这是centre一词告诉我们的。有头有身却无尾就构不成一个圆圈,而圆圈不在,焉有中心乎?
最能体现小说中碎片艺术之内涵与效果的,恐怕要算库弗的《保姆》。《保姆》包括标题共有108节,每节也以星号隔开。 上下节之间的叙述看不出内在联系,事件与事件之间也见不到因果关系,加之故事情节采用了叉(Y)式结构,因此“这些片断在基本原理的阐述下永远拼凑不成一体”,不能形成一个整体,一个中心,也就是失去了一个圈定范围的圆圈。而圆圈不在,封闭则不存。因此碎片形式实际就是种开放形式。从《保姆》看,它至少具有以下一些效果:
第一,碎片艺术给作家带来无限想象空间。托尼·坦纳(TonyTanner)说过:“碎片形式是种开放形式,这种开放形式对打乱和重新安排想象言听计从。”(注:Tony Tanner,City of Words:American Fiction 1950-1970(London:Jonathan Cape Ltd.,1971)p.400.)由于《保姆》采用了叉式情节结构,所以它充满可能性,作品中的事件虚实、真幻难分,作者的想象几至天马行空。仅举《保姆》第61节以资说明。
将车停在两栋建筑以外。悄悄走近房子,朝他家的窗户往里瞧了瞧。果然不出所料。她的外衣脱了,少年的衬衫解开了。他看着他俩缓慢、笨拙、稚气实足地相互摸索着解对方的衣服。我的天,他们要解到什么时候啊。“有个宴会!”“是你说的!”待他们快脱光时,他走了进去。“喂!这儿怎么回事?”他们脸色吓得苍白如乳酪。呵呵!“小伙子,瞧你那儿凸出来的小玩艺,是什么东西呀?”“哈里,规矩点!”不,他不让这少年穿衣,要叫他光着屁股回家。“光着屁股!”他为此举杯祝酒。“我保证,我保证,”主人太太说,“我保证把衣服寄给你,臭小子!”他注视着躺在沙发上一丝不挂的小姑娘。“看来,你我之间有个秘密要保了,宝贝。”他冷静地说。“除非你想跟你男朋友一样光着屁股回家!”对自己突口而出的俏皮话,他咯咯地笑了。他倾身朝她偎去,解开自己的皮带。“我们蛮可以弄它两个秘密,对吗?”“我的天,你在胡说什么呀,哈里?”他手执酒杯摇摇晃晃地走出那儿,寻找他的汽车去了。
在这一节里,笔者划线部分所叙述的“世界”完全不同于未划线部分所叙述的“世界”。前者是小说人物——塔克先生、塔克夫人、宴会主人的太太等——所处的“世界”(在宴会上),后者是塔克先生的幻想“世界”(幻想回到家中碰见保姆与其男友鬼混、自己想乘机揩油的场面)。如果说前者是“真实的”,那么后者是“虚幻的”,这虚、实的相交就展现出作者无限想象的空间。
第二,碎片艺术否定了“现实”的确定性。虚、实相交不单展现出一个无限的想象空间,更在否定现实的确定性,这是后现代主义作品与现实主义作品的根本差异之一。还以上一节为例。读者读这段文字,从“将车停在两栋建筑以外”开始,到“我的天,他们要解到什么时候啊”,便被渐渐带入文本所创造的、塔克先生的幻想世界。然而接下一句:“有个宴会!”“是你说的!”,就令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读者想:“这突然的一句对话来自哪里呢?绝然不是来自塔克先生与保姆,也不是来自塔克先生与其夫人或主人的太太。可能是来自保姆与其男友吧。可谁能肯定呢?”这就是说,在读者刚刚进入塔克先生的幻想世界时,他或她对自己的本体地位便产生了怀疑。如果读者将此对话视作来自保姆与其男友,那么他或她就还算是在塔克先生的幻想世界里,也就是说还确立在这个世界里。但是,当读者继续读到“哈里,规矩点!”时,便明白塔克先生是在宴会上。由于他幻想时情不自禁地说出了粗话,所以受到了夫人的批评。然而也就是这句批评,将读者拉出了塔克先生的幻想世界,同时又将他抛至其所处的“现实”世界里。读者再读下去,又进入塔克先生的幻想世界,但读到“他为此举杯祝酒……”,又被拉了出来。接下一句“他注视着躺在沙发上一丝不挂的小姑娘”,又将读者带进塔克先生的幻想世界,直至读到他夫人说“我的天,你在胡说什么呀,哈里?”读者如此三进三出塔克先生的幻想世界,使“现实”(即真实性,reality)的意义不能确立。
“一般说来,小说的读者习惯于把作者虚构的事件当成现实。”(注:沃尔夫冈·伊瑟尔:《作为现实主义小说结构成分之一的读者——萨克雷〈名利场〉作用美学分析》,载《最新西方文论选》,王逢振、盛宁等编(漓江出版社,1991),第47页。)这种情形自然有读者自身的心理因素,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在小说的因素本身,尤其是以再现客观现实为其宗旨的现实主义小说。这类小说中存在着许多成分,如线性叙述、完整的情节结构、“典型的”人物、“典型的”环境,它们都具有巴尔特所说的“真实效果”,其作用在于肯定读者的一个期待:即“通过与文本接触,
可以辨认出文本所营造或指涉的世界”。
(注:Jonathan
Culler, StructuralistPoetics:
Structuralism,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and Henley: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5),p.192.)这也就是说,这些成分“肯定了模仿契约,确保读者能够将文本读为关于一个真实的世界”。(注: Jonathan Culler,Structuralist Poetics: Structuralism,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and Henley: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5),第193页。)但是,碎片结构妨碍了读者的认知过程,故而读者不可能经由文本而进入一个世界。在上述的例子中,我们看到每当读者进入塔克先生的幻想世界时,便被拉了出来。所以读者对“现实”的认知,始终是不完整、不确定的。
读者进入世界的道路被阻,也就是说他不能将文本读作一个真实的世界,遇此无奈,他该将文本读作什么呢?“将文本读作一个自治的语言客体”。 (注: Jonathan
Culler, StructuralistPoetics:Structuralism,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London and Henley: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5),第193页。)这就是碎片艺术的第三个效果,即碎片艺术显现“语言言说”。
在《保姆》的108节中,跟上述例子一样的还有第28节、36节、 45节、51节。如前所述,读者阅读它们时,每次刚进入一个世界便被拉了出来。这是从单个的“节”(即单个叙述单元)而言。如果从节与节的关系看,那么读者读了一个单元(进入一个世界)接着读另一个单元时,他又被拉了出来。读者读完整个作品时,他这样进进出出就有上百次了。例如,读者读完第二节(第一节是小说标题)便随保姆一道进入塔克先生的家,读第三节时便被拉出并同时被带进“他”(后来读者知道“他”是塔克先生)的幻想世界。第三节与第二节或许有一定的联系,因为读者可以假定——只是假定——“他露齿微笑,微微地向她点了点头”是塔克先生见到她(保姆)进来时点头打招呼。但第四节与前两节却毫不相干:读者被带进杰克在街上一面闲逛一面幻想着自己的女朋友(即保姆)的世界。第五节与第二节联系最紧,可以说读者读它时又被送回到塔克先生家。但是,读第六节时,读者就不知道给带进什么世界了。可能是男孩吉米的想象世界吧,然而能作出这“可能”的判断,也只是在读到第13节知道吉米搔了保姆的痒时方能作出的猜测。读者的期待不能实现,他穿梭于种种世界之中,而且是矛盾的(毫不相干的)、不确定的(可能)世界,如此,读者的注意力则被迫一次次地“移离信以为真的客体(supposed object)而转向写作过程本身”, 也就是说读者“被迫认识到所涉及的现实即是写作本身的现实”。 (注:
Jonathan Culler,Structuralist Poetics:Structuralism,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and Henley: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5),第193页。)就是在这层意义上,像《保姆》这样的后现代主义小说被称为“自我反省的”(self-reflexive)元小说(metafiction)。罗伯特·奥尔特(Robert Alter)、 迈克尔·博伊德(Michael Boyd)、温奇·奥曼德森(Wenche Ommundsen)、马塞德·扎瓦扎德(Mas'ud Zavarzadeh)和罗伯特·西格尔(Robert Siegle)都使用了这一形容词来描述元小说。帕特里夏·沃(Patricia Waugh)和拉里·麦卡弗里(Larry McCaffery)使用了self-conscious (自我意识的)一词来描述,
而琳达·赫琴恩(Linda Hutcheon )则用narcissistic(自恋的)来描述。虽然措辞不同,也有人在它们之间作出些区别, (注:劳曾(SarahE. Lauzen )在“Notes onMetafiction:Every Essay Has a Title ”一文中认为:“‘自我意识’小说带有一个污点:琐碎、自注(self-absorbed)、颓废。 ‘自我反省’可能与‘元小说’同义,或者它可能缺乏一所指对象(referent),但无论如何,它不相同于自我意识小说,自我意识小说是元小说的一个更精细的分类。 一个文本不必是自我意识的也可能是自我反省的。”载 Larry McCaffery ed.,Postmodern Fiction : ABio-Bibliographical Guide (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6),p.94.)但其基本内涵却一致:无论是“自恋”、“自省”还是“自我意识”,所“恋”、所“省”、所“意识”的,均是小说乃是用语言构成的虚构物这一本质。
也许,self-reflexive一词更恰当地反映了元小说这类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内涵。奥曼德森分析了reflexivity一词(reflexive的名词形式)的词义。该词源于拉丁词flectere(弯曲),加上前缀re-(再, 重),所以这个词的意思是“弯回来”或“再次弯曲”。同时奥曼德森引用麦克尔·博伊德对于“日常”所指意义(denotation)和“反身”(reflexive)所指意义的区分,说明“反身”是指向语言本身。 (注:参见Wenche Ommundsen,Metafictions?Reflexivity in ContemporaryTexts(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93),p.17.)我们阅读《保姆》,所处的正是能指回头指向能指本身的情形,也就是说我们所能看到的,除了能指还是能指。能指不能通向所指,言不能通向“物”(things),言还是言,在说的是言在说。所指不能出场,“物”不能出场,那么说语言具有表达功能不就成问题了吗?由此推而论之,说小说——由语言堆砌而成的东西——能再现一个客观世界不就更成问题了吗?
第四,碎片艺术打破了线性叙述结构。初略说来,叙述话语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线性式的,一种是水平式的(horizontal)。前者多为现实主义作品所采用,后者多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品所采用。线性式叙述又可称为封闭式叙述, 因为这种叙述最终导致一个封合(enclsosure),借以确保故事的所谓“真实”。水平式叙述与此相反,它没有封合,呈辐射状,其最重要的标记是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尾”,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小说,有的甚至有几个“尾”,如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有三个。有的干脆就用“等等”来结尾,如前面提到的巴塞尔姆的《看见父亲在哭泣》。《保姆》根本没有“尾”,第108 节可以算个结尾,但第107节也可以,第104节也一样。《保姆》因由108 个碎片构成,所以线性叙述无法存在。由于碎片本质使然,这108 节碎片(或说叙述单位)不呈历时性结构而呈共时性布局,所叙述的事件在某一时间点(可能)同时发生。保姆进塔克先生家时,杰克也可能正在街上闲逛;塔克先生在宴会上幻想时,保姆可能正在与孩子们玩耍,或正与杰克或马克鬼混,而这些事件又可能与电视机里的事件同时发生。《保姆》中所有的事件,都是采用现在时来描述,这仿佛是,一切都发生在现在,因为时间永远是一个现在点。七点四十是现在,八点也是现在,九点、十点还是现在。如果说时间有个延续(duration),那么这个延续就是由无数个现在点连合而成的,不是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保姆》的108节, 都可以看作由七点四十至十点这一延续中的现在点。由于这108节能独自成为单个叙述单元, 所以在各节之间见不出时间顺序,绝对时间或称历史时间不存在,存在的是种关系时间。这里,“时间随时对人人都作为‘现在、现在、现在’来照面。”(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第489页。)
第五,碎片艺术有利于读者的积极参与。由于碎片结构打破了线性式情节结构,读者便有了自由想象的空间;由于它打破了线性式叙述,读者也获得了积极参与的条件。情节结构和叙述模式都规范着读者的作用。线性式情节牵着读者鼻子走,线性式叙述亦然。《保姆》抛弃了历史性时间而采用关系性时间,所以时间与事件是“共同扩张的”(coextensive)。关系性时间重复着“现在、现在、现在”。 伊丽莎白·迪兹·厄马斯(Elizabeth Deeds Ermarth )称关系性时间为“节奏性时间”(rhythmic time),以此来指涉后现代叙述时间。她说:
后现代叙述语言破坏历史时间,取而代之以一种新的时间性结构,我称此结构为节奏性时间。这一节奏性时间……取消了笛卡尔式的在思之自我(cogito),代之以一种不同的主体性,这一主体性的宣言则可能是科塔扎(Cortazar)的“我动故我在”(I swing, therefore Iam.)。(注:Elizabeth Deeds Ermarth ,Sequel to History:Postmodernism and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al
Tim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14.)
这里,动是晃动,即是说“我”——主体——面对着“现在、现在、现在”依旧是我,但却不是“同一的” (identical)的我。她说:由于节奏时间是种探索性的重复,由于它结束了就是结束了,并只为它的延续而存在,然后消失于另一节奏里,所以“我”或自我或cogito也只为这相同的延续而存在,然后带着显著的改变而消失或者改变至一种新的存在状态。(注:Ermarth,Sequel to History,p.53.)
她认为,“呈节奏时间的叙述使读者有机会在时间里获得一新的栖居地,即一种停留在叙述之现在的方式——在文学中或效果里常常停留于现在时,而这种方式要求有种种新的注意行为”。(注: Ermarth,Sequel to History,p.53.)读者读这种叙述,就被限制在现在时当中,因而就被限制在连绵不断的、不停地抹除过去与将来的现在当中。可见,“时间成了读者的时间,现象的时间;简言之,时间成了一种位置作用。”(注:Ermarth,Sequel to History,第60页。)读者读《保姆》进进出出上百次,每次都进入一个“现在”,然而此“现在”非彼“现在”,因此读者实际是每次都要采取新的“注意行为”,也就是说要调整自己的“位置”(或“栖居地”),而读者就是在这种调整中作了积极参与。
雅各布·科歌只是说“实验性作品常常看似毫无形式,倒像由断裂的碎片构成”,他没有说“由断裂的碎片构成”的作品是没有形式。实际上,实验性作家是把碎片本身当作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所显现的就是与中心分离。有些批评家认为,当今的世界(当指西方世界)是一个破碎的世界,而最能再现这个破碎世界的,莫过于破碎的形式。这种看法自然有其道理。然而,这种观点用来评论运用碎片艺术的现代主义作品可能更为合适,对于后现代主义作品,恐怕就不那么贴切了,因为后现代主义作家不言“再现”。在碎片艺术的运用中,现代派作家与后现代派作家的确存在着差异。前者“尽管不相信任何单一的原则或等级制度,却仍然试图勉强提出一种主观臆想的制度”,后者则“似乎接受一个由随意性、偶然性和破碎性支配着的世界”,而他们所信奉的“一条与对世界的这种看法相一致的基本构成原则,是‘离开中心’原则。”(注:厄勤·缪萨拉:《重复与增殖:伊塔洛·卡尔维诺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手法》,载《走向后现代主义》,佛克马、伯顿斯编,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165页。)毕加索奉劝艺术家说, “要把现实撕得粉碎”,现代派作家似乎听从了这一劝告,但后现代派作家却无所谓听从,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本来就是支离破碎的,用不着你去撕裂。毕加索又奉劝看画人,“要用眼睛把它们放到各自的位置上去”。(注:转见于毛崇杰:《存在主义美学与现代派艺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第74页。)我们作为看画人(读者)听从这一劝告,“把片断的意识‘放到各自的位置上去’”,结果,在福克纳的《献给埃米莉的玫瑰》中,能够“理出时间顺序、空间位置,找出人物关系和情节发展线索”。(注:转见于毛崇杰:《存在主义美学与现代派艺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第74页。)但在库弗的《保姆》里,我们理不出、找不到这些东西,只看到突兀而立的碎片,并由此而明白小说的虚构本质以及体验积极参与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