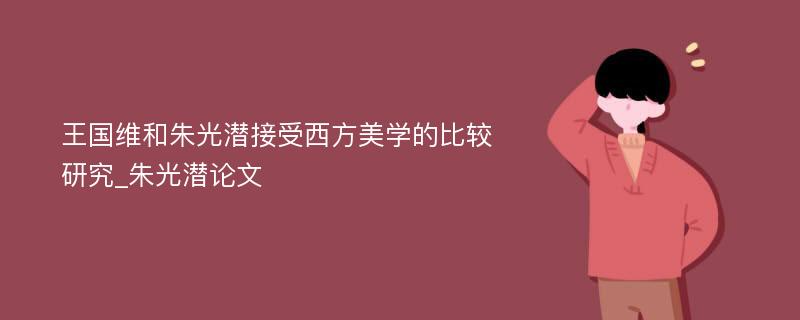
王国维朱光潜接受西方美学方式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王国维论文,方式论文,朱光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国维和朱光潜在分别接受叔本华和克罗齐的过程中,显示出接受方式上的基本差异,当然也具有某种相似性,尤其在对传统的顾盼上。这些差异一方面由于他们处于西学东渐的不同阶段,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性格、思维方式各有不同。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更能清楚地把握他们的接受方式及其后果——他们的成就和局限。下面我们依次从接受的总体特征、过程特征、禀赋及文化传统对接受的影响等几方面进行探讨。
总体结构特征
从总体结构而言,王国维的接受具有明显的单一性,而朱光潜则几乎一开始就表现出折衷综合的倾向。所谓单一性是指王国维对叔本华、康德及其他西方哲学家的接受中,没有刻意融合不同的理论以形成自己的综合性体系。而所谓综合性,是指朱光潜在接受过程中有不完全自觉地融合各家美学观念于一体的倾向。王国维的时代,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引介正处于初始阶段,接受的方式比较简单,一般都只是以西方某一家为介绍或评述对象,报纸杂志上频繁出现的标题是“某某的学说”如《卢骚之学说》、《卢骚之政治学说》之类,即使是这样简单的标题下介绍的内容也往往是道听途说,极不准确。王国维在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理解和研究上远远超出同时代人,但在接受方式上,仍然停留在单一性接受的水平,从他的各篇论文标题上即可看出,如《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书叔本华遗传书后》、《汗德之哲学说》、《尼采氏之教育观》等等。在进一步的具体运用中,他一般也只取叔本华一家之说,如《红楼梦评论》、境界说,单纯性特征非常明确。《叔本华和尼采》虽涉及叔、尼两家,但他是在进行比较研究,并无意综合两家形成自己的理论,只有《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在形式论上,略有贯穿几家,自树一帜的倾向,但这几家具有明显的内在一致性,所以并没有显出融合的倾向。事实上,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主要来自叔本华,至于康德、尼采、席勒等,他所选择的基本上是与叔本华一致的观念。接受的单纯性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时代性的局限,但就接受过程而言,也自有其优势,那就是更容易准确地把握接受对象,不致因为要融化各种观念而产生牵强比附的缺失,而这种缺失是综合性接受中经常出现的。
从美学史的角度看,王国维是最早自觉地接受并运用西方美学观念的,因此缺乏历史积累,而且因为他只在有限的几年内以部分精力涉及于此,接受上的单一性是很自然的。但美学发展到朱光潜的时代,引介的西方观念逐渐积累,研究者大量涌现,美学译著和论著出版数量急增,而且综合性论述比纯粹介绍西方某一家美学的论述更为常见,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前未统计),在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1936)出版前,美学译著已达47部,相当一部分本身已经是综合性论著,不只是一家之言,而美学论著也达41部,光是以《美学概论》或《美学》为名的著作就有吕澄、范寿康、陈望道、李安宅等四家,大部分论著都表现出融各家观念成一家言的倾向,尽管做得不是太成功。(注:蒋红等编《中国现代美学论著译著提要》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10 版)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中,朱光潜很自然地选择了综合接受的方式,对克罗齐的接受尽管重要,也只是诸多构成因素之一。应该说综合式接受是美学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所以在接受方式上,相对于王国维而言,朱光潜已显示出时代的优势,但这种接受方式的运用本身并不足以导致成功的理论体系产生,二、三十年代虽然出现不少具有综合性接受特征的美学著作,但大都相当幼稚,近于轻率组装后的转手倒卖,相对而言,《文艺心理学》显得鹤立鸡群,因为朱光潜毕竟留学英法,直接阅读了大量原著,就总体而言,他对当时欧洲美学界的理论及发展趋势比较清楚,对某些流派的美学观念理解准确,而且能够以流畅的白话进行阐释,叙述得有条不紊,所以是少数至今尚在再版的美学著作之一。《文艺心理学》大致看来似有一个理论构架,不过严格说来并没有形成有内在一致性的体系,真正理论体系的创立需要作者的创造力和自觉性,前者不论,即后者而言,朱光潜也自认并未用力,他说:“他(朱光潜自指)的目的并不要建立一个以思辨哲学为基础的美学体系,而是想用通俗的方式介绍现代西方美学界的一些重要派别思想,在中国美学界起一点‘启蒙’作用。”(注:《朱光潜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1993版第10卷 页552)这意味着他对克罗齐的接受仍处于移植和运用的层次上, 没有达到自觉的创造性转换。《文艺心理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丰厚的审美经验以及独到的诗论概念去印证、补充甚至替换西方美学观念,显示出中西文化合流的学术趋向。当然,由于朱氏传统审美经验的“前理解结构”,哪怕只是简单的介绍和应用,其实也包含了创造性误读。只是他并未意识到而已。但一般而论,他在对西方美学接受上的综合尚未达到内在和谐,反而不时出现折衷调和而不够成功的现象(尽管他自认为没有着意于折衷)。虽然如此,《文艺心理学》仍然足以代表那个时代美学的水平,尤其在对西方美学的接受和阐释上。
过程特征的差异
王国维接受叔本华美学和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从内在逻辑来看,其接受过程颇为不同,这种不同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的性格、心智和学术追求。
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是带着激情的,他初读叔本华哲学的片断文字,即为其倾倒,及直接读到叔本华主要著作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叔本华的天才论和悲观主义气质引起他强烈的共鸣,其认识论尤使他心折,而“搜源去欲,倾海量仁”的同情伦理学,使他甚至想“奉以终身”。(注:《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2版
页172)这就简直有点宗教的虔诚了。 王国维最初接受叔本华哲学是全面的,甚至包括其教育学、遗传学,他虽也注意却并未注重其美学,即使文学评论如《红楼梦评论》,主要的理论框架并非叔本华的美学,而是其伦理学,其悲观主义的人生观,美学是次要因素,当王国维在对叔本华进一步研究时,他觉察到叔氏本体论和伦理学的内在矛盾,这时他渴望能够在哲学上有所创造,因为他自视极高,不愿只停留在对别人的研究上。可是,对西方哲学史的了解既激起他的雄心,又淹没了他的信心,想在哲学上独创一格谈何容易,而人生的痛苦与其他感情需要发泄,他于是致力于词创作,甚至还想搞曲创作。但要作诗人,他又自觉理性太强,美学既能充分运用其理性,而又直接与文学发生关系,于是他对叔本华的接受由面到点,叔本华哲学的矛盾得以消解,而尤可注意者,王国维以词话的方式和捉摸不定的境界概念来表述叔本华美学的核心观念——理念,使有可能针对叔氏美学提出的尖锐批评都找不到落脚点,境界也就和美本身一样即迷人而又难以确切把握,恐怕正是这样才如此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显出长久的魅力。这样王国维从全面接受叔氏哲学到集中接受其美学,最后把叔氏美学化入传统背景和审美经验,在接受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至少在已完成的文学批评史或美学史上是如此。
朱光潜接受克罗齐先以美学为主,实际上很大程度并非朱光潜与克罗齐有什么深刻的契合,而是因为克罗齐美学当时风靡欧洲,朱光潜多少有些被动地卷了进去。克罗齐美学与其哲学关系密切,他把精神当作一个整体,美学只是对精神活动的一种形式的研究,把握其哲学对理解其美学相当重要,所以当朱光潜发现自己没能准确领会其美学时就转向整个哲学,甚至克罗齐哲学的渊源,使接受达到一个新层次,最后又由对哲学的理解和批评转向集中批判其美学,这样走过了与王国维接受叔本华完全不同的历程,朱光潜最初接受克罗齐时也非常佩服,但从来没有达到充满激情的程度,所以他既不象王国维那样能马上深入接受对象,也不象他那样,激情一退,就转向另外的方向。朱光潜的接受过程是韧性的持久过程,这对于他最后在整理西方美学史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是必不可少的。学者各人禀赋不同,寻求最适于自己的学问方式对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以取得成就至关重要。不过就接受克罗齐和其他西方美学家而言,朱光潜一直存在着纯粹学术以外的动机,也就承受着不利于学术的压力,这成为他取得更大成就的障碍。
接受中的转化
王国维和朱光潜的接受方式有一个相似的特征,那就是缩小了叔本华和克罗齐美学的范围,并把抽象性转化为具体性。中国传统文化习惯于以具体的例证表达抽象的观念。就传统文论而言,除了《文心雕龙》以外,其他几乎都是在对文学作品的具体鉴赏中表达文学观念,诗话词话这样的体例就体现了中国文论的典型的文体方式;这是西方所没有的。即使是《文心雕龙》,也多在对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的论述中显示作者的观念,极少有人抽象地去探寻美的意义和本质,更不会把对美的探索当成哲学探讨。叔本华和克罗齐美学都是在最广义的范围中探讨美的本质的。叔本华的美在理念论是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他的美学一直探讨的不只是文艺形式,而是对一切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哲学把握,文艺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而且理念这一概念并非为了美学而提出来的,而是为他的本体论提出来,构成意志本体和现象之间的中介,来解释本体意志的单一性与现象世界的杂多性之间的矛盾。尽管这种解释并不成功,(注:参看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2)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10版 页378)但足以说明他的理念论所覆盖范围之广泛, 而美学即对理念的研究也就几乎无所不包了。克罗齐的美学是对直觉的研究,直觉是认识的最基本方式,不限于对文艺作品的论述——不过克罗齐的艺术也和直觉等同,远远超出一般艺术的范围——这样,使他的美学实质上相当于一种哲学认识论,而且他确实是把美学当作对认识而不是对美的研究,尤其不是对普通意义上的文艺之美的研究。王国维除了对叔本华的纯粹介绍外,他所接受的叔本华美学思想一般体现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极少抽象地谈论美,即使《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带有抽象性,他也是着眼于文艺,古雅之美的提出则完全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审美特征的总结,因此可以说他对叔氏美学的接受过程是一个具体化和集中化过程。朱光潜对美的抽象探讨相对多一些,但他曾提出一个著名论点,那就是美学应该以研究文艺为主。事实上,除了对克罗齐的直接介绍和批评,即使在对美进行理论论述的时,也不断地以文学和艺术为例证,并不象克罗齐那样作哲学认识论探讨。不过有段例外的时期,那是五十年代的美学论争时期,美学作为哲学在争论,他自己后来为此而看轻当时的论争。总的来说,他的美学也落在文学艺术作品上,明显地缩减了克罗齐美学所指的范围。而朱光潜试图以经验心理学来阐释克罗齐的思辩性美学,也可以看作接受中的具体化过程的另一种表现。
传统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一个越来越引起注意的论题是现代学者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对待传统的态度,以及对学术传统的具体继承和突破。现代学者的成就一方面体现在以西方学术方式和具体观念对文化材料进行整理和阐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自身对整个文化传统的深厚素养。我们曾涉及王国维和朱光潜与传统的关系,这里再从他们接受叔本华和克罗齐的方式上探讨这一问题。
王国维和朱光潜在对待传统价值观的态度上,即使在最亲近西方文化的时候,批评也是相当温和的。他们在接触西方文化前,都打下了较深厚的旧学功底,尤其伦理价值观,他们在传统的薰陶中几已定型。尽管王国维在一些文章中曾发泄过“天才的愤懑”,显示出对环境的强烈不满,甚至在崇信叔本华时期还以西方价值标准对国民及传统审美趣味进行了贬斥,但他从来没有对作为理想的儒家价值观这一文化核心进行过批评。朱光潜除了五十年代以后出于压力批评过传统价值观——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人而言,仍非常温和——以外,一直很少表现出对传统的批评态度。但是在刚接触西方学术的时候,他们都对传统学术方式给予了相当低的评估。而且试图以西方学术改造传统。王国维《哲学辨惑》中认为西方学术优于中国传统:“余非谓西洋哲学之必胜于中国,然吾国古书大率繁散而无纪,残缺而不完,虽有真理,不易寻绎,以视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步伐严整者,其形式上孰优孰劣,因不可掩也。……且欲通中国哲学,又非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注:《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2.版 页5—6)
他自己在对西方哲学史尤其是对康德、叔本华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后,确实致力于以西方学术的眼光来整理评价中国哲学史,最著名的是他以性、理、命这三个哲学范畴为线索研究哲学史的《论性》、《释理》、《原命》三文,他以叔本华、康德的哲学对几个概念进行阐释,再对中国哲学史上各家见解进行评价。从几年前发掘的一些佚文看,王国维还用系统方法对从先秦诸子(老子、孔子开始)一直到清代的戴震、阮元的哲学进行了研究,这些论文大都概念清楚,条理分明,与传统哲学大为不同。在接受叔本华时期,他还从学术心态和治学方式方面对传统进行了否定。《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认为中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主要是因为传统文化过于注重实用,而不重视纯粹的真和美的研究,他在论及孔子这样的哲学家,杜甫这样的诗人都想当政治家,而国人的观念也不允许独立的哲学家和诗人存在后说:“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于哲学则如彼,于美术则如此,岂独世人不具眼之罪哉,抑亦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而葸然以听命于众故也。”(注:《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页102)
王国维从思维方式上对传统学术的批评无疑几乎达到了全盘否定的程度,他认为中国学术尚未进入自觉阶段:“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骋诡辩耳,其于辨(按:当为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之所不论,而亦其所不欲论者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之地位也。 ”(注:《静庵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页98)
我们在这里探讨王国维与传统的关系对接受叔本华的影响,却论及他在接受叔本华后对传统的评价,似乎有些离题了,实则不然,这种评价虽然形成于接触叔本华以后,却又反过来对接受方式产生影响,因为接受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时间断面。这种影响既表明也使他对西方的接受不是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而是着力于学术方式的接受,其中包括叔本华的论证方式和抽象分析的方式。尽管王国维疏离叔本华以后的史学、小学研究,很大程度得益于乾嘉学派的具体成果和治学方式,也得益于西方汉学家如伯希和、沙畹、斯坦因的研究成果,但如果注意他论证问题的思路和总体把握对象的能力,确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而“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注:《王国维遗书·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三》)因此可以说对传统学术的深刻批判助成了对西方的深刻接受,最后成就了国故研究的功业。
如果说王国维的时代,接受叔本华多少要克服一些阻力,那么朱光潜的时代要想不接受西方文化,那得承受更大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是新文化运动引起的。事实上,王国维主动地投入西方学术和叔本华哲学的怀抱,而朱光潜是相当被动地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的。他曾自述对待“新文化运动”的认识问题。“那时我是处在怎样一个局面呢?我是旧式教育培养起来的,脑里被旧教育所灌输的那些固定观念全是新文化运动的攻击目标。……你想我心服不心服?尤其是文言文要改成白话文一点于我更有切肤之痛。当时许多遗老遗少都和我处在同样的境遇。他们咒骂过,我也跟着咒骂过。《新青年》发表的吴敬斋(按:当为王敬轩)的那封信虽不是我写的,却大致能表现当时我的感想和情绪。但是我那时正开始研究西方学问。一点浅薄的科学训练使我看出新文化运动是必需的,经过一番剧烈的内心冲突,我终于受了它的洗礼。”(注:《朱光潜全集》第3卷 页444)
这种洗礼确使他接受了一些重要的西方观念包括价值观念,但另一些传统观念仍旧保留了下来。新文化运动兴起,新的主导性学术话语实质上已经对学术构成一种普遍压力,就象在王国维的时代传统学术话语构成一种压力,朱光潜不是那种惯于和时代主流对抗的学者,而且西方学术本身也吸引他的兴趣,在二十年代留英前他主要致力与传统关系不大的西方现代心理学,无疑是纯粹西方学术。1924年,朱光潜写下了他的第一篇美学论文《无言之美》,完全是发挥严羽《沧浪诗话》中不涉思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审美观念,并大量列举中西文学作品印证其观念。朱光潜踏进爱丁堡大学的校园,开始其美学研究时,他并没有否定传统审美趣味,却对中国文学研究带有明显轻视。他到英国后不到一年,写了《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1926)一文,该文虽然不时把西方文学的发展史当作常态来衡量中国文学史,但在审美趣味上,明显地更偏爱传统,尤其是抒情诗。在学术上,他倾服西方,否定传统。他作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假设陶渊明生在英国或法国,那里的学者会怎么去研究他,以此来说明西方学术如何精密、系统,而中国学者大都贪多务得,笼统庞杂。这就能够充分预示他以后的学术道路,在研究方式上完全是西方的,而美学观念却部分地与传统接近,甚至传统显得处于更基础的层面。他对克罗齐的接受正是在这种学术心态中开始的。朱光潜对传统的诗论和美学观念既熟悉而又欣赏,但正是在当时的心态下,他不愿以传统的方式表露出来,却试图以西方方式表达出来,接受克罗齐的最初他未必有意用克罗齐的概念和命题表达传统的观念,然而实际上,传统审美观念使他在接受中不断地产生变形,而到后来,朱光潜越来越有意识地以西方学术话语表达传统美学观念,他从误译到改变克罗齐文字来为自己所继承的传统美学观念辩护,这就显示了传统对他的接受方式具有强大的制约作用,这也是为什么长时间他无法准确理解克罗齐的真正原因。然而毕竟由于时代不同了,朱光潜对传统美学与文化的依恋情绪相对而言处于被压抑状态,尽管他早就说明传统给他的影响是一贯的。而王国维的时代却引诱甚至促使他完全回复传统——当然,只是在观念上和感情上。
王国维对叔本华的接受进入怀疑阶段后,主要还在从事西方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和翻译,但从美学观念上看,古雅说显露出向传统趣味靠近的趋势。尽管我们已论述了境界说与叔本华美学的关系,但表现方式的改变确也显示着接受中的变形与创造,既意味着与叔氏的疏远,也意味着与传统的亲近。《宋元戏曲考》本身是接受叔本华的结果,因为叔本华看重叙事文学,王国维自承受其影响,而对悲剧的高度评价也要归根于叔氏美学,但《宋元戏曲考》中对文学传统的评价与深受叔氏影响的时候相比已发生极大改变。1906年的《文学小言》中说:“上之所论,皆就抒情的文学言之(《离骚》诗词皆是也),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诗、诗史、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注:《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续编·文学小言》 页30)而《宋元戏曲考》中却截然不同:“(元曲)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注:《王国维遗书·宋元戏曲考》页73—74)对戏曲价值评价的陡转反映了文化心态的急变,后来更进一步,对西方文化在总体上予以了否定评价。其拟上退位的宣统帝《论政学疏》草稿云:“原西学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臣尝求其故,盖有二焉:西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挟其奇技淫巧以肆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厌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此皆由贪之一字误之。此西说之害于心术者一也。……臣观西人处事皆欲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圆,往而不知反。此西说之弊根于方法者二也。”(注:《海宁王忠悫公遗书》 罗振玉《王忠悫公别传》页4)
王国维对西学的最后评价既有其独到的深刻之处,也显示其根源于文化的偏颇,说明他于西方文化之精神了解并不透彻,更不用说彻底接受,也正说明王国维受传统浸润极深,他对传统的疏远只是出于青年时期的激情,而生活在痛苦的环境与时代,可望而不可及的传统总给人以幻美——人们难以悟透这种虚妄,即使是王国维这样相当深刻地理解了叔本华的人——不,或许最终王国维已经真正悟透了?只是悟透之后,仍然对这个世界无能为力?
标签:朱光潜论文; 王国维论文; 美学论文; 叔本华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哲学家论文; 文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