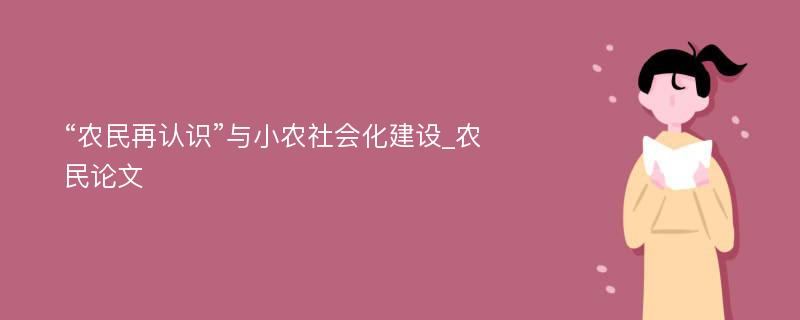
“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农论文,农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456(2006)03-0002-07
现阶段,中国仍然有近2.5亿农户。中国将长期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体制。农户不仅是农民的基本生产单位,同时也是基本的生活、交往单位,还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政治单元。因此,农户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细胞”,也是认识和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出发点。但在相当长时间里,家庭经营因其生产规模小而被称之为小农,由小农构成的经济被视为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则被视之为落后的代名词,是改造的对象。根据这一理论逻辑,家庭经营就缺乏基本的理论和现实根基。而这一理论逻辑是建立在传统的封闭的自然经济形态基础之上的。如果从历史变迁过程的角度考察,我们会发现,当今的小农户已不再是局限于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而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来,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进入到社会化小农的阶段。农户生产、生活和交往的社会化过程大大提升着农户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同时也产生了内在的矛盾,需要以新的思路应对变化之中的农户及其需求。
一、小农之“小”与社会之“大”
近年来,国家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各种方案和措施。其基点有两个方面:一是维持家庭经营体制长期不变,一是重视解决农民的增收、就业、保障等问题,为农民提供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由此就会产生两个理论问题:一是家庭经营属于传统的小农经济范畴,在现代社会,家庭经营是否有生命活力,能否长期延续;二是如果家庭经营属于传统的小农经济范畴,那么为什么需要解决农民的增收、就业、保障等非传统小农经济范畴的问题,并提供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这说明,运用传统的小农经济范畴已很难解释当下的农村社会,在对农户的认识方面发生了“范式危机”。为此,需要引入新的分析范式重新认识农户。
我们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认识,长期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农经济学说。小农经济主要依据的是农户在小块土地上经营,并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下生活和交往的一种经济社会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法国和德国的小农经济有过较多论述。马克思在论述法国小农时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1] 马克思对小农经济的描述应该说是相当精辟的,具有相当的普适性。
在马克思看来,小农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生产效率不高,二是政治保守,三是思想狭隘。小农经济因此必须加以改造。恩格斯通过对法国和德国农民的考察,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在小农生产方式下,“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庄则更是如此。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经济,货币几乎根本不需要。”而“资本主义生产借助于货币经济和大工业结束了这种状况。”因此,“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2] 面对这一状况,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通过合作改造小农经济。20世纪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和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着力于改造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就指出,“在像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实现“由个体小农经济到共耕制的过渡”[3]。斯大林则直接强调,“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应该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4]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悠久,也是一个小农经济形态最完整和持久的国家。农户构成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费正清对此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从前,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的成分。”“中国是家庭制度的坚强堡垒,并由此汲取了力量和染上了惰性。”[5] 1949年,中国沿用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及前苏联的经验,将小农经济视之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可能走向资本主义的土壤,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毛泽东表示:“中国农业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6] 其出路就在于集体化。由互助组、合作社发展到后来的人民公社都是集体化的组织形式。当时,对小农经济的改造有两个基本点:一是认为组织规模愈大,愈能提高生产效率,克服小农经济的低效率。因此,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最后发展到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又要求不断扩大基本核算单位,开始是生产队,后来要求过渡到生产大队。二是将集体生产组织提升到是否社会主义的高度加以规定,只有超越农户的集体生产才是社会主义,否则就是非社会主义。
尽管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初期,负责中央农村工作的邓子恢提出农民有个体和集体两个积极性,并一度支持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条件下实行分户经营,但受到了严厉批评。农村生产经营体制以“家户”为界,任何经营核算单位都不能“退”回到家庭单位。[7] 只是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中,人民公社体制被废除,实行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体制。农户重新成为农民生产、生活、交往的基本单位,成为负责任的政治单元(如各种政府行为都以农户为对象)。
在实行分户经营之后,农户成为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必然会使人联想到小农经济。迄今在许多论著中仍然沿用着小农经济的提法。这就需要我们正视这一理论和现实问题。
毫无疑问,如果从组织规模看,当今的农民仍然属于“小农”,而且这种“小型化”的趋势更加突出。小农之“小”主要表现为:
其一,农户耕种的土地规模小。土地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小农之所以被视之为“小”农,而不是“大”农,主要根据就是小农耕作的土地数量小,无法进行规模化经营。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没有效益就没有投入,没有投入就更难以走出低效农业的陷阱。所以,小农经济成为落后的代名词。而在现阶段,中国农户耕种的土地规模数量日益趋小。首先,在传统中国,土地的占有极不均衡,有土地占有极少的小户,但也有土地占有较多的大户。而农村改革中实行分户经营,土地基本上根据人口数量平均分配,各个农户经营土地的数量差别不大。其次,在现阶段,一方面是土地的总面积日益减少,另一方面是农村人口不断增多。20世纪中国的总人口才四亿多,而进入21世纪时,仅是乡村人口就达九亿多(户籍人口)。农村人口的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不断缩小。2004年,我国总耕地资源面积为130039.2千公顷,农村人口9.42537亿,平均人均占有耕地资源面积2.07亩(实际占有耕地面积2.00亩)。所以,如果从农户耕种的土地规模看,我国农民仍属于“小农”。
其二,农户的家庭人口数量小。劳动人口是农业生产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小农之所以视为“小”,而不是“大”集体,另一个根据是其劳动人口少,无法进行分工和协作。没有分工和协作就无法提升生产效率。所以,实行集体化就是改造农业经营单位人口太少的问题。人民公社因此被称之“大集体”,相对于小生产而言。而在现阶段,实行分户经营,农业生产单位的人数更少。在传统社会,尽管也有分家析产,但一般农户还是尽可能维持一个大家庭。因为人口多,不仅生产能力强,而且“人丁兴旺”,社会声望高。“大户”人家一般属于“四世同堂”,甚至于“五世同堂”家庭,即使是“小户”,也是“三世同堂”。但在现阶段,随着计划生育和观念变革等因素,农村的大家庭日益减少,核心家庭日益增多,“三世同堂”的家庭都已少见。2004年,我国农村总人口为9.42537亿人(户籍人口),农村家庭为2.49714亿户,农户家庭平均3.8人。
如果单就小农之“小”而言,从理论上看,家庭经营是没有出路的。这也是农村改革以来,不断出现“再集体化”要求的重要原因。但为什么当今的分户经营仍然有活力,农户仍然将长期成为农村人口的基本生产、生活和交往单位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今的小农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变化,小农户所处的和面对的却是一个大社会。传统的小农经济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地域性社会。小农与外部世界是隔绝的,村落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而在现阶段,农户已愈来愈广泛和深入地进入或者被卷入到一个高度开放、流动、分化的社会里,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日益社会化,不再局限于村落世界。正是在这种社会化的变动之中,新的生产、生活和交往要素进入到农户的活动之中,改变着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并由此汲取了“力量”,改造着中国传统家庭的“惰性”,使农户的行为能力得以提升。
表1 中国历代家庭经营规模与人口规模
(按照全国人口和户数平均)
年份 户均耕地 人均耕地 户均人口
(亩) (亩) (人)
1393①11.98 2.11 5.68
1578 9.88 1.73 5.71
1910②15.90 2.99 5.29③
1947④16.70 3.10 5.39
1982 5.34 1.46 4.43⑤
2004⑥5.60 1.50 3.44
表2 中国历代家庭经营规模与人口规模
(按照乡村人口和户数平均)
年份 户均耕地 人均耕地 户均人口
(亩) (亩) (人)
1949⑦16.25 3.06 5.31
1978 10.83 1.89 5.74
1982 8.35 1.83 4.57⑧
2004⑨7.81 2.07 3.65
(一)生产方式的社会化。生产方式的社会化通常包括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和生产产品的社会化。在传统小农经济形态下,农户的生产局限于家庭和村落的范围内,而无需与村落以外的世界发生联系。而随着农村村落与外部世界日益紧密的联系,“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8] 在当下,无论是生产资料、生产过程,还是生产产品都不同程度地社会化了。首先,农民的种子、肥料、农药、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大都以从外购买的方式获得。可以说,除了土地以外,农业生产的大多数生产资料都是从家庭和村落以外获得的。从生产过程看,尽管农业生产主要是以农户为单位进行的,但是农户之间的互助合作日益广泛,特别是在大量农民外流的情况下,农户之间的互助合作更加紧密。不仅如此,农户还寻求村落以外的帮助,如专业收割、专业浇水等。生产过程由一系列的个人行为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你挑水,我浇园”的家庭内部分工日益为家庭内外的分工所替代。由于生产资料来源社会化了,生产过程表现为家庭内外的分工,使得生产产品也社会化了,它从农户创造的产品变成了许多人共同劳动创造的社会产品。在当下,没有一个农户能够说,其产品只是他一个人生产的。与外部世界日益广泛和深入的联系,使农户的经济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生产产品不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主要是进行交换,由此才有了农业产业化和“专业户”。农户的工作不再只是农业领域和当地村落,而出现了跨行业和跨区域的流动,农户的兼业化趋势日益明显。据不完全统计,当下中国有1亿多农民外出务工,可以说一半以上的农户都有成员在外从事农业以外的职业。
(二)生活方式的社会化。传统的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人们的生活基本上可以在家庭和村落内完成。直到2005年,笔者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时,还可以发现一些村落,除了向外购买食盐以外,所有生活资料都是自行获得。但这种情况已非常少见。在绝大多数农村,农户的消费资料和行为已日益社会化。他们获得的生活资料不再只是与自然交换而更多的是与社会交换。长期以来,农民习惯于自己种什么吃什么,但是,当下的农民食品消费不再局限于自己的生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向外部购买。如雪糕等以往只有城市人群消费的食品也大量进入农村。仅仅只是20多年前,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区别一眼就可以看出,即农村人口一般穿着自己纺织的“土布”,而今,“土布”几乎已“绝迹”,农村人口在衣着方面的消费已完全依靠向外购买。住宅对于农户十分重要。传统农家的住宅一般称之为“土房”、“土屋”,即农民完全依靠就地取材建立起住宅。农村改革以后的最大变化就是“土屋”的消失,农户的新居用材、建筑等有相当一部分从村落以外的社会取得。传统农民的“行”主要依靠的是走路。在当下中国,已基本实现“村村通”公路,乘车已取代步行成为农民的主要交通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以往根本不可想象的自来水、电、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家用电器等也进入农户的生活领域,甚至成为其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交往方式的社会化。小农经济形态的重要特点是相互封闭和与外部世界的隔绝,农民的交往范围十分有限。十年前,笔者在四川省大巴山区调查发现,四十岁以上的农民一生的活动空间不超出十里路的范围,他们生活在一个天天见面的“熟人社会”里,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极少。当下的农民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广度和深度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首先,交通和信息将封闭的农户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农民的信息来源不再只是依靠“张家长,李家短”的口头传递,而是多样化的信息来源。特别是电视的普及,给农民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其次,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社会化,使他们处于高频率、跨区域的流动之中,他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熟人社会”,而是一个充满机会和风险的“陌生人社会”。祖辈传递的生活经验已远远不够,他们必须获得新的知识,依靠自主的判断选择和支配自己的行为。
由此可见,当今的小农户已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如果我们仍然将当下的农户称之为小农的话,那么他们已成为迅速社会化进程中的小农。“小农”处在或者面对的是一个开放流动的“大社会”。
二、“小农”与“社会化”的张力
在传统理论看来,社会化总是与大生产相联系。而在当下,一方面是小农愈来愈“小”,另一方面是社会化程度愈来愈高,由此构成“小农”与“社会化”两极。这看似极不对称的两极有何意义,它预示着什么呢?
(一)它展示着农户仍然有强大的生命活力
社会化大生产是以工业生产为参照系的。通常理解的大生产主要指生产规模大。这正是组织农民,进行集体经营的重要依据。但这种划分的假设是农业和农村是一个分散、孤立、封闭的产业和社会,先进的生产要素因为分散、孤立和封闭而难以进入农业和农村,小农经济因此效率低下,缺乏生命力。但是,现实状况表明,作为传统小农经济存在条件的分散、孤立和封闭的状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种子、化肥、农药、机械、自动灌溉、专业分工、社会协作、商品经营等现代生产要素日益广泛深入地进入农业领域,从而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并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以往我们更多的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认识小农经济,以为只有将土地交给劳动者或者由劳动者个人集中到集体,扩大组织规模,就可以提高生产能力。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理解。传统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的要素简单,只有简单的劳动和土地要素。“脸朝黄土背朝天”,就表明了农业生产受大自然制约,只有土地和劳动要素。在没有先进生产要素进入农业领域,无论是多么大的组织规模都难以提高生产效率。奴隶制生产组织规模大,但效率并不一定比小农经济高。所以,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是生产要素的改变。当下,中国农村虽然以农户为经营单位,但由于生产方式的社会化,使愈来愈多的先进生产要素进入到农业生产领域,并推动着生产效率的提高。我们注意到,1978年以来,中国的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用于农业生产的时间处于不断减少的趋势,耕地面积也处在一个不断减少的趋势之中,农业生产总量却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单位生产面积的产量在不断提高。[9] 这说明,农户经营并不天然排斥先进生产要素进入农业生产领域,而当先进生产要素不断进入农业领域,又会增强农户的生命活力。
在以往的理论看来,小农经济的落后性还在于其脆弱性。因为小农经济的生产剩余十分有限,“小生产者是保持还是丧失生产条件,则取决于无数偶然事故,而每一次这样的事故或丧失,都意味着贫困化,使高利贷寄生虫得以乘虚而入。对小农来说,只要死一头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8] 这里,马克思的论断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农民只依靠小块土地谋生,而小块土地的有限收入根本不可能抵御自然和社会风险。在相当长时间里,我国主要是借助于生产集体共担自然和社会风险。那么,实行农户经营以后,集体共担风险能力减弱,从一般逻辑看,农户的抗风险能力趋弱,并会加速贫困化。但是,现实状况是,虽然实行农户经营,农民耕作的土地十分有限,但农民的收入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农民的生活不仅基本实现温饱,而且开始趋向小康,有的甚至相当宽裕。从整体上看,农户并没有陷入“贫困化的陷阱”。那么,这其中的奥秘何在呢?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当今的农民已进入到一个开放的社会体系之中,农民的兼业程度愈来愈高,农民的收入愈来愈多样化。据国家部门统计和我们的实地调查,当下农户的现金收入主要依靠外出务工经商。换言之,愈是那些没有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户,愈难以抵御经济和社会风险。依靠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外出务工经商而不断增长的现金收入,提升了农户的抵抗风险的能力,使他们仍然得以顽强地生存和不断地再生产。
在以往的理论看来,小农经济是没有活力的经济。分散、孤立、封闭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小农生活索然无味,“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10] 但是,当今的农户也进入到一个开放的社会体系中,交通信息的发达、市场经济的渗透、高频率和跨区域的流动、教育的普及、国家赋予农民以平等权利等各种因素,改变了分散、孤立和封闭的状态,农民的头脑不再只是局限于小块土地和小村落之中,他们不再是传统规则的奴隶,而且正在表现出伟大的历史首创精神。这种精神的动力在相当程度来自于农户。正是在农民的要求下,中国实行了以分户经营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营体制,发展了以家户为基础的乡镇企业,产生了以农户经营体制为条件的村民自治。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被视为中国农民的三个伟大创造,而这三大创造都与农户密切相关。所以,日益加快的社会化为中国古老的家庭制度注入了活力,改变着其惰性。
(二)社会化的小农使农民面临新的压力
小农的社会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但这一过程带来的并不都是美丽无比的图景。它在为农户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压力,使农民进入或者被卷入到一个更不稳定、风险更大、更不具有确定性、更具挑战性的社会之中。
小农与社会化作为两极,存在着三大内在的矛盾:
其一,生产条件的外部化与自我生产能力弱小的矛盾。
传统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户生产主要依赖家庭和村落自我提供的条件,对外部的依存度很低。当下农户的生产方式趋向社会化,其重要后果就是越来越依赖于外部条件,生产条件的外部化程度越来越高。如果离开了种子、化肥、农药、水电、农机具等外部条件,农户的生产很难正常进行,仅仅是依靠农户个体,已很难完成生产的全部过程了。但这种外部条件的提供却大都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的,即农民需要以现金与外部交换生产条件。相对外部条件的不断改进而言,农户的自我生产能力则较为弱小,甚至被戏之为“386199部队”,即从事农业的主要是女性、小孩和老人;与日益扩大的外部生产条件的支出相比,农户获得外部条件的购买能力却相对弱小。为购买外部生产条件的货币支出成为农户生产中的最大压力,并成为其行为选择的主要动机。由此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循环:外部生产条件价格愈高,农户购买能力有限,就愈是会寻求出外务工经商;农民愈是外出务工经商,农户的自我生产能力就愈弱。外部条件的现代化与农户自我生产能力的现代化不能同步增长,同时也会制约农民收入的增长。如近几年,尽管国家免除农业税得到农民的积极拥护,但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实际“好处”被抵消。免除农业税后,尽管一度出现农民大规模返乡要田的现象,但是不久,许多农民重新步入外出务工的轨道。道理很简单,务工只是支付劳动力却能获得比农业生产更高的收益。
其二,生活消费的无限扩张与满足需要能力有限的矛盾。
传统农民的生产剩余有限,生活开支充分计划,精打细算,勤俭节约。随着农户生产方式的社会化,他们的生活消费早已超出自我生产。而相当部分的消费品都需要从外部获得。特别是已作为日常生活重要部分的教育、医疗等完全依靠于外部。与教育、就医等开支迅速上升相比,农民的支付能力却相对不足。“吃得饱饭,读不起书,看不起病”成为相当多数农民的实际生活写照。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社会化造成农民消费欲望的急剧扩张,大众传播媒体的广告将各种消费信息传递给农民,使他们不再只是根据自己的生产能力和生活实际需求支配自己的生活,在相当程度是来自于外部消费的刺激。与急剧扩张的消费欲求相比,农户满足消费需求的能力又十分有限。
其三,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与集体行动能力不强的矛盾。
传统小农的生活范围小,并生活在一个村落为根基的熟人社会里,能够形成相互间的合作共济,集体行动的能力相对较强。随着农民交往方式的社会化,交往的范围和空间急剧扩大,农民生活的领域愈来愈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而当社会化将农民抛到一个陌生人社会里,他们的集体行动能力又显得十分弱小。他们外出务工经商一般都是个体行为,外出后也分散在各个城市和厂矿,相互间缺乏多种多样的横向联系。尽管外出务工者已达1亿多人,但他们仍然只是一个自在的而不是自为的群体。他们不能联合起来维护和追求自己的利益,在陌生人构成的大社会中孤立无援。所以,当他们的工资被拖欠时,只能寻求政府援助,或者以非常的方式获得。更重要的是,社会化的开放世界改变了农民的观念,他们不再是以村落熟人社会中的“人情、礼俗”等作为行动规则,从而获得集体行动能力,而是以现实利益,更直接的是现金收入作为支配他们活动的规则,超越农户的社会组织困难,其集体行动更为困难。
以上三大矛盾集中起来,就是社会化给小农带来的是货币化的压力。货币收入因此成为他们行为的主要依据。他们的行为动机和行动方式都可以从这一压力中寻求答案。如果说传统小农是以获得实物产品为主要目的,那么,社会化小农则是以获得现金收入为主要目的。而现金收入的获得相对实物产品而言,其稳定性更弱,不确定性因素更多,风险更大。所以,当下的农户已进入或者被卷入到一个更高风险的社会之中。
由此可见,“小农”与“社会化”这两极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构成影响当下农户的动力和压力。这种张力,既赋予农户以生机活力,同时又使他们面临新的困境。
面对社会化给农户带来的困境,需要寻求新的出路。一方面要在社会化进程中,不断提升农民的自我生产、生活和交往的能力,为农民提供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服务来提升农民自身的能力。在发达国家,一般都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场制,直接从事生产经营的人并不多,但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大增强了农户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应对一个变化和开放的世界。另一方面要将农户纳入统一的国家支持和保护体系。当下的农民已进入到一个统一开放的社会化进程之中,面临着与其他人一样,甚至更多的风险,尤其需要国家提供支持和保护。如农民生产、生活和交往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与公共产品需要政府提供。农民的收入、就业和保障等问题已成为当下农户的紧迫问题,需要国家纳入到统一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体系中统筹考虑。这也是农民作为统一的国家公民享受统一的国民待遇的重要体现。
重识农户,有利于我们将认识和研究农村社会的支点引向农户这一社会“细胞”,更好地理解当下的农村和农民;社会化小农的建构,有利于我们从历史的变迁过程去理解和考察当下的农村和农民。将社会化的视角引入农村研究,更主要的是开发出新的“问题域”,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范式。至于这一范式能否成立,还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注释:
①1393、1578年的数据来源于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二卷265和272页。
②1910、1933年户均耕地数据来源于《剑桥中华民国史》第91页,最终来源于《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2页。
③1910年户均人口借用1911年的数据,人均耕地根据户均耕地与户均人口予以推算。
④数据来源于侯杨方著的《中国人口史》第六卷27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⑤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
⑥2004年数据中户均耕地和户均人口是根据《新中国统计资料五十五年汇编》和《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获得,户均人口是来源于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⑦1949年的人均耕地是根据《新中国统计资料五十五年汇编》计算获得,户均人口借用1948年底的数据,户均耕地是根据人均耕地和户均人口计算获得。
⑧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
⑨2004年的户均耕地和人均耕地是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相关计算获得,户均人口第五次人口来自普查资料。
标签:农民论文; 小农经济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三农论文; 农村论文; 经济论文; 生产方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