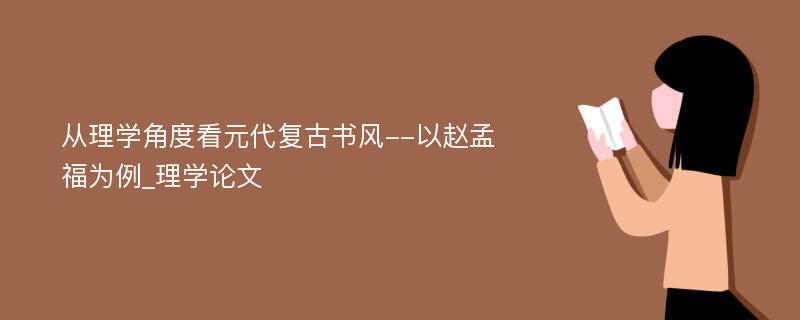
从理学角度看元代复古书风——以赵孟頫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为例论文,理学论文,角度看论文,赵孟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元大德、延祐年间开始的对晋人书法风貌的模仿与推崇是在对南宋末书风的批评基础之上确立的,赵孟頫凭借书坛领袖地位对当时书风的确立和定型无疑具有先导之功。这其中,理学作为元代艺术形成和发展的文化背景,一直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它是赵孟頫及以他为首的元代复古书风的精神底蕴。
元朝由崛起于漠北的蒙古游牧民族所建立,统治者为适应中原地区高度文明的封建社会,建立长期有效的统治,不得不采取汉法,接受以儒学为主的汉族思想文化。成熟于宋代的理学作为新儒学,自赵复首传于北方后,儒士大夫姚枢、刘因、许衡、窦默、郝经等皆得闻以广其传,再经由他们的递相传授,理学在社会上迅速传播开来。从此,理学的地位日渐上升,上至公卿大夫,下至乡邑文士,无不以讲读、精研理学为尚。延祐二年(1315),朝廷开科取士,理学最终定为国是,列为官学,成为元代的一种统治思想,其政治与社会影响超过了宋代,波及明清。
赵孟頫生长于宋末,二十六岁以后进入元朝,他所生活的从至元到“海内翕然”盛世的大德、延祐年间,正是元代理学大流行之际。尽管作为封建时代的士人,从牙牙学语即读经史,思想上接受儒学传统教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赵孟頫不一般,在他的学术、艺术成长历程中,理学在其身上打下的烙印尤为鲜明:年轻时拜福建名儒敖继公为师,接受理学洗礼,质问疑义,经明行修,打下结实的理学基础。我们从其此时所著的《尚书集注》一书,可以看出他对理学的热爱与精研。又常和当地儒林逸士相往还,与钱选等被称为“吴兴八俊”。“吴兴八俊”虽以诗、书、画鸣世,但理学见长者不乏其人,如钱选著有《论语说》、《春秋馀论》、《易说考》等书稿,尽管后来因决意归隐全被他自己烧去,但其深厚的理学修养可见一斑。又如牟应龙出身理学世家,学承南宋后期理学家魏了翁,“一门父子,自为师友,讨论经学,以义理相切磨。于诸经皆有成说,惟《五经音考》盛行于世。”(《元史·列传第七十七·儒学二》)赵、牟彼此旨趣相投,不在话下。至元二十一年(1284),赵孟頫和著名学者戴表元相识在钱塘江畔,“莫逆而相与为友”。戴表元家乡浙东自来陆学独盛,其于陆氏心学,有地方学术与家学之渊源。后从方回学朱熹之学,方回自视为理学家,学问议论,一尊朱子,崇正辟邪,不遗余力。期间还受教于宋元之际著名理学家欧阳守道。戴表元兼综各家而服膺朱熹,这对莫逆之交的赵孟頫应该影响匪浅。至元二十三年(1286),赵孟頫又与同时应诏出仕的元代三大理学家之一的吴澄相友善,有条件再次接受理学辐射。其他与赵孟頫私交深厚的名士如周密、牟巘、方回、袁桷,以及深受其影响的元中期文学、书法大家虞集、杨载、揭傒斯等都是理学名家,持身严正,修养深厚,非常人所能及。理学文化浸润了一个时代也浸润了赵孟頫,由此出发,赵孟頫掀起了书法复古的巨大风潮,成为有元一代书法的最典型的特征,影响极为深远。
元代前期的书法家情况比较复杂,有由辽入元者,如耶律楚材等;有由金入元者,如刘秉忠、郝经、鲜于枢等;有由宋入元者,如赵孟頫、邓文原等。他们皆自小接受理学教育,并与当时理学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或自身就是理学家(如刘秉忠、郝经等)。而著名的元代三大理学家刘因、许衡、吴澄等在书法创作及理论上也都颇有成就。书法家成分的复杂化带来了创作上的多样性。犹如此时南北理学有所冲突、交融一样,这个时期的书法创作也是处于南北书风交错、冲突、融合的时期,书坛上呈现出多样化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此时既有以元初三大书法家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为首的江南书法重二王的审美追求,也有北方以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为首的辽、金书坛学习颜、苏、米的遗风,同时南宋末期放纵恣肆书风的亚流虽已走上末路但在士林中仍有不少市场。正如虞集所说:
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出遂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方知古法,而长睿所书不逮所言,绍彭最佳而世遂不传。米氏父子书最盛行,举世学其奇怪,不惟江南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书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千湖之险,至于即之之恶谬极矣。①
在赵孟頫等扭转金及南宋末季书法流风之前,这种现象尤为普遍。赵孟頫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秋即其仕元的第三年,他给杭州朋友王子庆(芝)的一封信中写到:
自度(渡)南后,士大夫悉能书,纵复不至神妙,去今人何啻万万。盖少小握笔,便得曲肖神情。今人童幼学书,为师者悉皆恶书之人,以及省事,稍欲学古,俗气以渐入,恶体不可复洗,岂不可叹也哉。若今子弟辈,自小便习二王楷法,如《黄庭》、《画赞》、《洛神》、《保母》等帖,不令一豪俗态先入为主,如是而书不佳,吾未之信也。近世又随俗皆好学颜书,颜书是书家大变,童子习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种拥(臃)肿多肉之疾,无药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实。尚使书学二王,忠节似颜,亦复何伤?吾每怀此意,未尝敢以语不知者,俗流不察,便谓毁短颜鲁公,殊可发大方一笑。至元二十六年九月七日,信笔书去,子庆必不以为过也。②
此信向后人透露了这么几个消息:1、说明元初北方流行具有刚烈色彩的颜真卿书法,但在赵孟頫看来是“俗”。2、为“不令一豪俗态先入为主”,提倡自小便习二王楷法,以回归二王为指向。3、“书学二王,忠节似颜”。
从理学角度观察,上述三点既体现了理学家所强调的“体用”关系,又具有浓郁的儒家道德教化内涵。其中第三点与元代理学倡导者郝经的书论不谋而合:
故今之为书也,必先熟读《六经》,知道之所在,尚友论世,学古之人其问学,其志节,其行义,其功烈,有诸其中矣,而后为秦篆汉隶,玩味大篆及古文,以求皇颉本意,立笔创法,脱去凡俗。③
“学古之人其问学,其志节,其行义,其功烈,有诸其中矣”,这才是学古的本质所在。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赵孟頫所再三强调的:
右将军王羲之,在晋以骨鲠称,激切恺直,不屑屑细行。议论人物,中其病常十之八九,与当道讽竦无所畏避,发粟赈饥,上疏争议,悉不阿党。凡所处分,轻重时宜,当为晋室第一流人品,奈何其名为能书所掩耶!“书,心画也”,万世之下,观其笔法正锋,腕力遒劲,即同其人品。所惜溺意东土,放情山水,功名事业,止是而已。抑以晋室之气数有在也?晋之政事无足言者,而右军之书,千古不磨。④
右军人品甚高,故书入神品,奴隶小夫,乳臭之子,朝学执笔,暮已自夸其能,薄俗可鄙!可鄙!⑤
在赵孟頫眼里,王羲之是“骨鲠”、“恺直”的,是“不屑屑细行”的,是“无所畏避”、“悉不阿党”的,这些精神是在“议论人物”、“与当道讽谏”、“上疏争论”中表现出来的。“观其笔法正锋,腕力遒劲,即同其人品”,笔法锋芒中映现着书家人格心灵。赵孟頫用理学的眼光和思维看到了中国文化中的某些更为本质的东西,这种东西即是中国文化中的精神与道德的关怀。他的学古,表达或追求的是一些吸引人性的中心价值。这是他大力推崇二王并为儒林及为儒林所影响的书法界所认同的基础与核心。郝经就说过类似的话:
羲之正直有识鉴,风度高远,观其遗殷浩及道子诸人书,不附桓温,自放山水间,与物无竞,江左高人胜士,鲜能及之。故其书法韵胜遒婉,出奇入神,不失其正,高风绝迹,邈不可及,为古今第一。其后颜鲁公以忠义大节,极古今之正,援篆入楷;苏东坡以雄文大笔,极古今之变,以楷用隶,于是书法备极无余蕴矣。盖皆以人品为本,其书法即其心法也。故柳公权谓“心正则笔正”,虽一时讽谏,亦书法之本也。苟其人品凡下,颇僻侧媚,纵其书工,其中心蕴蓄者亦不能掩,有诸内者,必形诸外也。若二王、颜、坡之忠正高古,纵其书不工,亦无凡下之笔矣,况于工乎!先叔祖谓:二王,书之经也;颜、坡,书之传也;其余则诸子百家耳。⑥
“盖皆以人品为本,书法即其心法也。”郝经书论直可视为赵孟頫书论的母版。当然他们皆承唐人“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乃可谓书法即心法”(柳公权)之说。但问题是郝经认为颜真卿忠节鸣世书亦工,“若二王、颜、坡之忠正高古,纵其书不工,亦无凡下之笔矣,况于工乎!”北方书坛名家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等皆善颜真卿书法,为何赵孟頫又认为学颜就“俗”了呢?赵孟頫的解释是:“颜书是书家大变,童子习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种拥肿多肉之疾,无药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实。”原来是“慕名而不求实”,不知“颜书是书家大变”的缘故,所以造成了“一种拥肿多肉之疾,无药可差”的局面。臃肿多肉则乏力、不清新、不典雅、不遒劲、不简淡、不闲静,总之不雅观,不符合儒家所规定的“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宣尼德性,气质浑然,中和气象也”⑦的美之实质。而二王书法却“韵胜道婉,出奇入神,不失其正,高风绝迹,邈不可及,为古今第一”,自然被理学家推为“书之经也”。故此赵孟頫开出的药方是“自小便习二王楷法……不令一豪俗态先入为主”。这里一方面强调了书法的入门学习问题:元初书坛凋敝,自南宋末年以来学北宋苏、黄、米书法者皆“学其奇怪”,全无大家风范;学唐颜真卿书法者则“成一种拥肿多肉之疾”。唐、宋之书皆无可救药,因此赵孟頫针对时弊,提出将学习二王法书的重点放在法度上,这是十分明智的。此举及时、有力地勒住了奔自南宋末期、“意造无法”失去控制的书法之野马,将当时缺乏法度羁束而不断滑向虚无深渊的书法逐渐拉归到本体之内,“使海内书法为之一变”,功莫大焉。另一方面,赵孟頫强调了学习书法一定要名实相符、体用一致,将蕴含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形态和道德理想的人格追求真正落到实处。
赵孟頫的“复古”思想是全面而深刻的,它贯穿于赵氏的所有艺术审美观之中:其“作诗文皆从李、杜、韩、柳中来,顿扫旧时之气习”⑧;画要“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⑨;印章则提倡汉魏印章取其“典型质朴之意”,抨击“新奇相矜”、“不遗余巧”的世俗审美观;书法“当则古,无徒取于今人也”⑩。所谓“则古”,即以古法为准则;所谓“今人”,则显然是针对前述南宋以来本朝书家以意为法的风气而言的。
“书法不传今已久,楮君毛颖向谁陈”、“千古无人继羲献,世间笔冢为谁高”,(11)赵孟頫怀着改变书风流弊的强烈愿望和明确的目的,号召继承和发扬晋代的书法传统,找回那久已丢失的二王法度。他以自己对二王体系书法技法的精研和孜孜以求,为世人树立了典范。赵汸云:“汸往岁游吴兴,登松雪斋,闻文敏公门下士言,公初学书时,智永《千文》临习背写尽五百纸,《兰亭序》亦然。”(12)宋濂亦云:“赵魏公留心于字学甚勤,羲献帖凡临数百过,所以盛名充塞四海者,岂无其故哉?”(13)
如此刻苦尽心的锤炼技法,与“朝学执笔,暮已自夸其能”的“奴隶小夫,乳臭之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君子固欲深造也,岂能一蹴而遽造于深也哉?”(吴澄《自得斋记》)理学大师吴澄的话成了赵孟頫进行严格技法训练的最好注脚,说明掌握魏晋笔法的途径只有认真、踏实地临习古人法帖,此外别无他途。吴澄又云:“天下之理非可以急迫而求也,天下之事非可以苟且而趋也。用功用力之久,待其自然有得而后可。”(14)“用功用力之久,待其自然有得”,赵孟頫书法复古走的就是理学家所提倡的践履笃实、深造自得的路。它不可一蹴而就,需要一个长期涵泳的过程。它是自然的获取而非刻意的安排。赵孟頫说:
文章所以明理也,自六经以来何莫不然,其正者自正,奇者自奇,皆随其所发而合于理,非故为是平易险怪之别也。后世作文者不是之思,始夸诩以为富,剽疾以为快,狡诡以为戏,刻画以为工,而于理始远矣。(15)
说的是文章,书法岂不亦然。从这个角度看,一些人认为赵孟頫及元人缺乏书法创新力度固然有其客观的一面,但这种指责颇有隔靴挠痒之嫌疑,因为赵孟頫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所谓的主动创新上,尽管以他的天资、学力完全可以一如宋人那样以意为法,快意为书,他追求的是振兴晋法和自然而化。“无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功夫到则自造微入妙,穷神知化矣。”(16)学以明理、书以载道,由于自得所得的对象属于道德的而非仅仅是学问、书法的,所以它在求晋法的追寻过程的同时也是一个人格完善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不能是急迫的而只能是从容的、适然的。
赵孟頫的复古书风是归于平易、简淡的审美理想和时代风尚。当时代将赵孟頫的书法复古的个体选择最终推向大众并为大众所选择时,以二王为指归的元代复古书风的统领地位也就确立了。这里表层原因是赵孟頫高超的书法水平深深的为当时的士大夫所折服:赵书数体兼善,篆、隶、真、行、草,无所不能,无一不精。他以精妙绝伦的书画赢得元世祖恩宠和朝野的好评,荣际五朝,官居一品,其特有的“匀净平顺”的书法格局,吸引了无数的追随者,即连由金入元的鲜于枢,也受到赵氏本人的浸染,力主归宗二王,并成为复兴近代书风的中坚。其深层原因在于赵孟頫将“兼撮众法,备成一家”的天真遒媚但技法复杂高超的二王书法平易化,让人可亲、可近、可学。平易化书法审美背后是这种书风契合理学的中正要求,人们通过书法达到实现自我。这种风格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易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即连“书宗颠素”(陶宗仪语)的理学家、书法家姚燧也以为:“惟所性中正宏厚者,故能优柔而明炳,洞畅而温醇,斯大雅君子,言符其德者也。”(17)“大雅君子”乃“儒者气象”,理学中人称作“圣贤气象”,表现于为人是一种精神风貌,表现为书法则是一种书法风格。对于这种气象的追求,在平易书风的形成中,起着潜在的但却是决定性的作用。虞集在谈到这种风气时说:“以平易正大振文风、作士气,变险怪为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烂为名山大川之浩荡。冲淡悠远,平易近民。”(18)“平易近民”所探求的是普通的、一般化的东西,而不是个性的东西;表现的是人类的生命,而不仅仅是个体的生命;是理性或直观的清晰,而不是感情的横溢。赵孟頫的书法复古,代表了一种价值的观念,达到了一种超历史的存在。为此,他在书法形式上极为重视笔画之间的搭配,注意点画结构的左右向背,上下承接,迭相顾搰,端正稳定,示人以平正楷模,引人入门径,极宜学者取法。
风格整暇,意度清和自然平易近民。赵孟頫对晋人书法下过极深的工夫,但晋人书法中精妙的用笔,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体现;或者说,他将晋人笔法的精微之处大大加以简化了。这一点也是元朝书法共有的特征。(19)赵孟頫临摹的拓本字帖,与钟、王、智永原写本的神采也已有距离。这样,赵的书法有古人的影子,但不可能是古人的再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宋末元初时的理学背景缺乏东晋人那种以玄风为背景的风韵。加之晋人席地而作、悬空书写,与元代端坐高椅、据案书写的姿势截然不同,书写效果判若有别。另一方面,仍跟赵孟頫崇雅尚平易有关。他在自著《印史》序中就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态度。(20)
赵孟頫通过提倡“典型质朴”的“古雅”来矫正士大夫中“新奇”与“巧”之“流俗”。理学家都认为文(艺)渊源于道,随道而形成,则好的书法也是随情理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必要雕琢奇巧,刻意为书。一般来讲,质朴的主要形式要素是平、简、淡、拙等,它们与藻饰相对。可是,又必须有适当修饰,否则就不能合“典型”。这个度的把握相当难。赵孟頫在笔法、结构、章法上将二王的书法平易化,力矫宋人的新奇偏执为秀润中正,弃绝唐人颜、柳的顿挫之笔而增以风姿流动之势,试图将平易、简淡与秀润合为一体,并确有成效。当然,在笔法丰富性上,赵尽管简化了二王,但跟唐人相比或又过之。难怪连一向对赵孟頫抱有成见的董其昌也不得不承认“自右军、大令后,直接宗派,非唐人所及也”。(21)这说明平易、简淡并非苍白浅陋,而是经过了绚烂多彩后达到的纯熟的表现,是在平淡的形式中包含深厚的内蕴。他也并非完全如董氏所云“虽己意亦不用”,而如宋濂所评的那样,“笔意流动而神藏不露”。而从艺术角度来看,这是一种素朴自然、平和淡远、无意于刻削雕琢的艺术风格与境界。这也是赵孟頫对如陶渊明、王维等再三赞叹不已的原因之一。恰如朱子反对音阶跳跃幅度大的尖厉、高亢之音乐,而喜欢平和、中节、浑厚的音乐一样,赵孟頫用笔精熟,笔圆停匀,流畅活泼,用笔虽有些变化,但决无大起大落之举,堪称中和之致,符合儒家所规定的美的实质。
赵孟頫提倡的复古书风用意在于力矫时弊,同时也是对一种新颖独特的艺术境界的创造,其中所蕴涵的美学意义是十分丰富的:它既强调严酷的书法本体的功力修炼,又关注着平易、简淡的意兴,更呼唤传统价值的回归,从而达到“有以致其道”的境界。在书法史上赵孟頫是使以二王为代表的魏晋法度得以传承不绝的关键人物,他崇尚魏晋书法的思想和实践大大影响了元以后书法史的发展方向和进程。从维护和继承书法传统上来讲,他的功绩是最不容抹杀的,尽管其平易、简淡书风曾遭后人诟病,那也是后人不明其理、不善学习之故。
注释:
①[元]虞集著,《道园学古录》,卷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
②[元]赵孟頫《与王子庆札》,载《书法从刊》,总第29期《宋元名人诗笺册》。
③崔尔平选编、点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第175页。
④[元]赵孟頫《识王羲之〈七月帖〉》,转引自任道斌著《赵孟頫系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25页。
⑤同注③,第179页。
⑥同注③,第175页。
⑦[朋]项穆著,《书法雅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第538页。
⑧[明]长谷真逸辑,《农田余话》,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39册,齐鲁书社,1995,第315页。
⑨[明]张丑著,《清河书画舫》,《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第335页。
⑩同注③,第196页。
(11)[元]赵孟頫著,《松雪斋文集》,卷五,〈论书〉、〈赠张进中笔生〉,《四部丛刊》本。
(12)[元]赵汸著,《东山存稿》,卷五,〈跋赵文敏公临东方先生画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
(13)[明]宋濂著,《文宪集》,卷十三,〈题赵子昂临大令四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
(14)[元]吴澄著,《吴文正集》,卷二十四,〈自得斋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
(15)同注(11),卷六,〈刘孟质文集序〉。
(16)同注③,郝经〈叙书〉,第172页。
(17)[元]姚燧著,《牧庵集》,卷三,〈樗庵集序〉,商务印书馆,1936,第192页。
(18)同注①,卷四十。
(19)这种现象在其他书家身上同样存在,如由金入元的鲜于枢可说是赵孟頫古典主义书法风格的推行者。和赵孟頫的艺术主张一样,鲜于氏的书法亦绝去两宋时风而直追晋人,小字学钟繇,草书步武怀素。虽然他学的是唐朝人怀素,但他的字里,更多的是元朝人的东西——无论是笔法的丰富性,还是节奏的复杂性,都比怀素有所简化。这一点是元朝书法共有的特征。
(20)同注(11),卷六,〈印史序〉。
(21)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赵孟頫研究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第8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