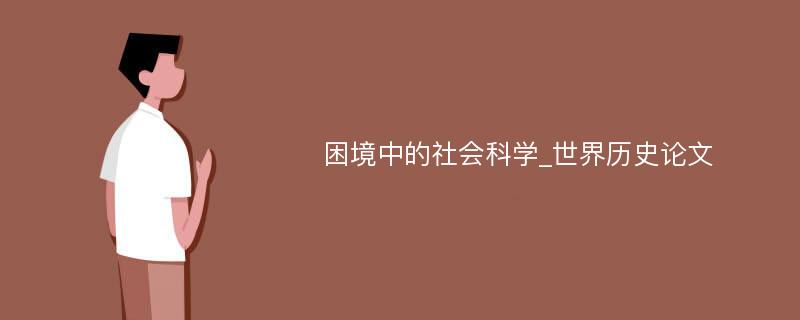
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退两难论文,社会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科学在其制度化的过程中(即在大学系统内建立起讲授社会科学的院系以来),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这一点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社会科学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物,而欧洲中心论则是现代世界体系中地缘文化的构成部分。此外,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结构,社会科学主要发源于欧洲。欧洲这个概念在这里,主要是在文化的意义上说的,而不是在地域的意义上说的。在这个意义上,在关于过去二百年的讨论中,“欧洲”主要是指西欧和北美。实际上,至少直到一九四五年,社会科学诸学科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国家: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即使在今天,尽管社会科学作为一种活动在全球传播开来,但是绝大部分社会科学家依然是欧洲人。在欧洲支配整个世界体制的历史过程中,社会科学作为对欧洲问题的回应应运而生。而社会科学对其主题的选择,它的理论的形成,它的方法论、认识论,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使它产生出来的这个大熔炉的种种制约。
但是,一九四五年以后,亚洲和非洲的非殖民化,加上非欧洲地区的强烈的政治意识,不仅影响着世界体系的政治,同样也影响到知识界。今天,并且实际上至少在最近大约三十年里,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社会科学的“欧洲中心论”受到了严厉的抨击。这种抨击从根本上说是有道理的,而且毫无疑问,如果社会科学要在二十一世纪取得任何进步,就必须克服欧洲中心论这一遗产,因为它已经歪曲了社会科学的分析及其应付当代世界的各种难题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要这么做,我们就必须格外小心地审视欧洲中心论是如何构成的,因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欧洲中心论是一个九头怪,它的具体表现也是多方面的。
要想迅速打败这个怪魔不是很容易的事。如果我们不小心从事,那么很有可能在貌似与它的斗争中,会用欧洲中心论的前提来批判欧洲中心论,从而增强它对学者群体的控制力。
社会科学被认为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至少有以下五种方式。这些方式并没有构成逻辑上一整套严密的范畴,因为它们含糊不清地重叠在一起,然而,考察一下这些题目及说法将是有益的:一、编史工作;二、普遍性;三、(西方)文明;四、东方主义;五、进步论。
一、编史工作。这是指借助一些特殊的欧洲历史上的具体成就来解释欧洲对现代世界的支配的正当性。编史工作对其他解释似乎具有根本性的作用,但是它也是最简单化的解读,而且,这种解读的有效性是最容易受到质疑的。欧洲人在最近两个世纪中无疑屹立于世界之巅。从整体上说,他们控制着最富有和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享有最先进的技术并且是这些先进技术的原创者。
这些事实似乎是无可争议的,而且实际上也很难有可能与之竞争。问题是用什么来解释欧洲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在实力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别。一种答案是欧洲人做过一些值得赞扬的并且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民所做的事情。这是持“欧洲奇迹论”的学者的解释。欧洲人发起了工业革命,创造了持续增长,他们还引发了现代性,资本主义,科层制和个人自由。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特别谨慎地定义这些词,看一看是否确实是像想象中那样,欧洲人创建了这每一个新奇的东西,如果是,具体又是在什么时候创造的。
但是,即使我们赞同这些解释和如此确定的时间,并以此谈论眼前的现象,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说明什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是欧洲人,而不是其他人造就了上述现象,并且为什么他们恰恰是在历史上某一段时期做成了这一切。在寻找这样的解释时,大多数学者都会本能地追溯到历史上假定的先行者。如果说欧洲人在十八世纪或十六世纪做了X, 那么很可能因为他们的祖先在十一世纪或者在公元前五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做了Y。 一旦我们确立了(或者至少是断定了)那些在十六——十八世纪欧洲出现的现象,我们就可以并且还会进而促使我们上溯到欧洲祖先早年的不同时期,到那里去寻找决定性的变量。
这里有一个其实并不隐蔽的前提,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对它进行过讨论。这个前提是,无论人们认为欧洲在十六至十九世纪创造的是什么,它们都是好的、是欧洲应该为之自豪的东西、是世界其它地区应该羡慕或至少应该欣赏的东西。这些东西被认为是一种成就,不计其数的书籍都证明了这种评价。
目前关于世界社会科学的编史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上述这种对现实的感觉。这种感觉无疑可以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这些质疑在最近几十年里越来越强烈。人们完全可以质疑:十六至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这幅图景是不是准确?人们当然还可以质疑:对于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一切,所假定的文化前提是不是合理?人们还可以把十六至十九世纪的故事放到更长的时间段里,从六七百年到上万年。于是人们通常会论证说,欧洲在十六至十九世纪所取得的所谓“成就”并不是那么奇迹般的,它倒更像是一种循环变异,而不像是能够给欧洲带来声誉的成就。最后,人们还可以承认确实有新奇事物,但是这些新奇事物的积极后果甚至还不如它们的消极影响。
这种修正性的编史工作在细节上通常是令人信服的,而且也肯定带有积累式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还具有昭示性乃至解构性,成为一种反理论性的东西。比如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编史工作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变化就是这样,在这里,一种一百五十年以来一直支配着人们写作的所谓社会性阐释正在受到挑战,并且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被推翻了。在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的编史工作中,我们也许正在进入这样一种所谓的范式转换。
但是,不论何时发生这样一种转换,我们都应该先停下来,退后两步,正确地估价一下新选择的这些假设是否确实更有理,特别是它们是否真正脱离了从前占支配地位的那些假说的基础性前提。这是我想联系假定欧洲在现代世界中取得成就的欧洲编年史工作而提出的问题。编史工作受到了攻击,那么,拿什么来替代它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考察对欧洲中心论的其它的一些批评。
二、普遍性。普遍性是这样一种观点,它认为存在着在所有时间和空间中都有效的科学真理。欧洲近几个世纪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很强的普遍性。这是科学作为一种知识活动而在文化上取得成就的时代。科学取代哲学成为具有权威性的知识模式和社会话语的仲裁者。我们这里谈论的科学是牛顿—笛卡儿式的科学,它的前提是,世界受线性均衡过程这样一种决定律支配,因此,把这种规律表达为普遍的具有可逆性的方程之后,我们只需要附加关于初始状态的一些数据,便可以推测将来或者过去任何时刻的状态。
这对社会知识意味着什么,似乎是清楚的。社会科学家有可能发现解释人类行为的普遍过程,而且任何他们能够证实的假说过去都被认为是跨越时空的,或者说应该以适合一切时空的方式来阐述它们。学者的角色与实际的社会过程是不相干的,因为学者的活动是在作价值中立的分析。而且,如果数据得到正确的处理,那么具体的经验证据源自何处基本上可以被忽视,因为社会过程被看作是恒定的。即使一些学者的方法比较看重历史与个人的特殊性,但只要他们假定存在着构成历史发展的基础模式,那么结果也与普通性阐释没有什么两样。所有阶段论式的历史阐释理论,都假定眼前是最好的时期而且过去必然会导致眼前。而且,即使是那些非常经验主义化的历史著作,无论它们声称多么憎恶理论构造,也下意识地体现着阶段论的潜在逻辑。
欧洲的社会科学,无论是表现为社会科学家所使用的非历史(时间可逆)的形式,还是表现为历史学家的历时性的阶段论的形式,都具有普遍性的特质,因为它断定,无论在欧洲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发生了什么,都代表了一种普遍适用的模式,要么因为它是人类的一种不可逆转的进步的成就,要么因为它通过消除人为的障碍而满足了人类的基本需要。人们今天在欧洲所看到的一切,不仅是美好的,而且是未来遍及世界的图景。
上述种种普遍性理论总是受到抨击,因为处于特定时期和地点的种种特定情况似乎并不适合这种模式。也总是有一些学者论证说,普遍概括从本质上说是不可能的。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对现代社会科学的普遍化理论还提出了第三种抨击:这些自封的普遍性理论实际上不是普遍的,而是体现了一种被宣称是普遍的但实际上却是西方的历史模式。许久以前,李约瑟就指出:“欧洲中心论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它认为事实上本来是植根于文艺复兴的科学和技术具有普遍性,并且,由于这一无言的假定,它还宣称凡是欧洲的都是普遍的。”
鉴于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特殊性的情况,人们一向指责它是欧洲中心论的。不仅如此,它还被说成是狭隘的。这使社会科学痛不可忍,因为现代社会科学尤为自豪的是摆脱了狭隘性。如果说上述指责是有道理的,那么它所表明的,远远不仅是断定普遍性的命题尚未以一种足以说明所有情况的方式被表述出来。
三、文明。文明指与原始或野蛮形成鲜明对照的一系列社会特征。现代欧洲认为自己绝不仅仅是几种文明中的一种“文明”形式,相反,它认为自己是(唯一或至少特别)“文明的”。什么是这种文明阶段的特征的标志,并没有形成明显一致的意见,即使在欧洲人中也是如此。有人认为,文明包含在“现代性”中,就是说,包含在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之中,以及包含在存在着历史发展和进步这种文化信念之中。还有人认为,文明意味着相对于其他所有社会成员,比如家庭、团体、国家和宗教机构,“个体”增长了自主性。还有一些人认为,文明意味着日常生活中非野蛮的行为,最广泛的意义上的社会礼仪。或者认为,文明意味着降低或缩小法定暴力的范围以及拓宽对残酷的理解。当然,对许多人来说,文明涉及了所有或部分上述特征的组合。
十九世纪,当法国殖民者谈论文明的丧失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说,通过殖民征服,法国(或更一般地说,欧洲)会把文明的这些定义所包含的价值规范强加给非欧洲人。在本世纪初,当西方国家各种各样的团体谈论对世界各地(几乎总是非欧洲地区)的政治环境中的“干涉权”时,他们恰恰是以这样的文明价值的名义而主张自己具有这种权利。
这样的一系列价值,无论我们称它们为文明的价值,还是人类世俗的价值,或现代的价值,它们正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在社会科学中随处可见,因为社会科学是相同的历史体制的产物,这个历史体制把这些价值抬高到价值系统的巅峰。社会科学家把这样的价值融入了他们认为值得探求的问题(社会问题,理性问题)的定义,他们把这些价值融入了他们创造出来的用于分析这些问题的概念,并且融入了他们用来衡量这些概念的指标。毫无疑问,社会科学家一般都坚持认为,他们追求的是价值中立,因为他们声称,他们并不是由于他们的社会政治取向而故意曲解或歪曲数据。但是,这种所谓的价值中立根本不意味着在对所观察现象的历史意义作出判定的时候价值是不出现的。当然这是李克特(Heinrich Rickert)关于他称之为“文化科学”的东西的逻辑特性的核心论证。在评价社会意义的问题上,人们不能不考虑“价值”。
可以肯定,西方的或社会科学的关于“文明”的假设不是完全不受“文明”的多重性这个概念影响的。每当人们提出文明的价值的起源这个问题(即它们最初在现代西方世界中是如何出现的)时,回答几乎必然就是:它们是西方世界中过去长期存在的和独特的潮流的产物,或者换句话说,它们是古代和基督教中世纪的遗产,希伯来世界的遗产,或者是这二者结合的遗产,有时候后者又被重新命名并被标榜为犹太教—基督教的遗产。
对于这一系列假定,人们可以提出(而且已经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所谓现代世界(或者说现代欧洲世界)是文明的,意思是否就是在欧洲话语中所使用的“文明”这个词的意思,这一点受到了质疑。圣雄甘地有一个著名的讽刺。当有人问他“甘地先生,你怎样看待西方文明?”时,他回答说:“这个嘛,也许会是一个好主意。”此外,人们对以下断定也提出批驳,这种断定认为,古希腊罗马或古代以色列的价值比其他古代文明更有助于奠定所谓二十世纪现代价值的基础。而且,现代欧洲人是不是有理由声称古希腊罗马或古代以色列就是其文明前景,最终也不是自明的。其实,在认为希腊是文化起源的人或认为以色列是文化起源的人之间,长期以来争论不休。争议的双方都否认对方说法是有道理的。这种争论本身使人怀疑:产生这样的分歧究竟是不是有道理的。
无论如何,有谁会论证说日本能够根据古代印度文明是佛教的发源地,而佛教已经成为日本文化历史的核心而声称古代印度文明是其前景呢?难道当代美国在文化上与古代希腊、罗马或以色列的联系比日本与印度文明的联系更紧密吗?毕竟,人们可以强调说,基督教远非体现一种延续性,而是明确地标志着与希腊、罗马和以色列的决裂。确实,直到文艺复兴,基督教徒恰恰是这样论证的。而且,与古代的决裂今天不依然是基督教会的学说的一部分吗?
然而在今天,关于价值的争论集中在政治领域。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一直坚持认为,亚洲国家能够并且应该“现代化”,同时也不接受某些或全部欧洲文明的价值。他的观点得到其他亚洲政治领导人的广泛响应。这种“价值”争论在欧洲国家本身之内,特别是(但不仅仅)在美国之内,作为一种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也已经成为中心话题。随着学者(他们对被称为“文明”的东西是单一的这个前提持否定态度)云集的大学内部结构的膨胀,当前的这种争论对制度化的社会科学确实产生了一种主要影响。
四、东方主义。东方主义指一种关于非西方文明特征的独特而抽象的陈述。它是与“文明”这个概念相对立的概念,并且自阿伯德尔—马里克(Anouar Abdel—Malek)和赛义德(Edward Said)的著作问世以来,成了公众讨论中的一个主要论题。不久以前,东方主义还是一种荣誉的象征。如今,东方主义是一种知识模式,它植根于欧洲中世纪,其时一些有知识的基督教修道士为自己确立了一项任务,这就是学习非基督宗教的语言和仔细阅读非基督教宗教的文本,以此更好地理解这些宗教。当然,他们依据的前提是:基督教的信念是真的,而且企图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愿望也是真的。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真地把这些文本看作是人类文化的表达,无论这些文本被他们曲解得多么厉害。
当东方主义在十九世纪变得世俗化以后,其活动的形式也没什么特别不同。东方主义者继续学习这些语言和解释这些文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继续依赖一种二元的社会观。对于基督教徒/异教徒的狭隘区别,他们以西方/东方或现代/非现代的区别取而代之。在社会科学中出现了许许多多著名的两极倾向:军事社会或工业社会,礼俗社会或法理社会,机械团结或有机团结,传统立法或理性立法,静力学或动力学。尽管这些两极倾向通常并不直接和与东方主义有关的文献相联系,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些两极倾向中最早的一种两极倾向是所谓的身份制和契约制,而这种两极倾向是在比较印度和英国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做出来的。
东方主义者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他们竭尽全力对非西方文本进行广博的研究、以便理解非西方文化,以此他们孜孜不倦地表达他们对非西方文明的富有同情心的恰当评价。他们以这种方式所理解的文化当然是构造出来的,一种由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所作的社会构造。现在正是这些构造的有效性受到了抨击,而且是在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受到了抨击:这些概念不符合经验现实;它们过于抽象,因此消除了经验世界的多样性;而且它们是带有欧洲人偏见的推论的产物。
然而,对东方主义的这种抨击绝不仅仅是对贫乏的学识的抨击。它也是对这样一种社会科学概念的政治后果的批判。人们说,东方主义确立了欧洲占支配地位的权力的合法性,它在为欧洲帝国主义在现代世界体系内的作用进行的意识形态辩护中,确实起着一种主要的作用。对东方主义的这种抨击已经成了对物化的一般性抨击,而且与解构社会科学叙事的多重努力结合起来。
五、进步。进步,其现实性与不可避免性,过去一直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论题。有些人会把它一直追溯到整个西方哲学的全部历史。但无论如何,它成为十九世纪欧洲的共识,而且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也依然是如此。随着社会科学的建立,它也深深地铭刻上了进步论的烙印。
进步成为对世界历史的基础性的阐释,而且成为几乎所有阶段论的基本原理。据说,我们应该研究社会科学以便更好地了解社会世界,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明智更确实地加快世界范围的进步,或者至少帮助消除进步道路上的种种障碍。进化或发展的比喻并不仅仅是在试图描述进步,它们也激励人们对进步作出规定。社会科学成为政策制定者的指导,包括从边沁的圆形监狱和社会政治,到各种政策咨询报告和无数其他政府委托的项目,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后关于种族主义的丛书,到柯曼(James Coleman)关于美国教育制度的系列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欠发达国家的发展”这一题目是一个显著的标志,它表明,非西方世界的社会和政治重组把具有各种政治主张的社会科学家牵涉进来是有道理的。
进步并不仅仅得到假定或分析,它也被强加于人。这也许与我们在“文明”的标题下所讨论的情况没有特别的不同。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当(主要是一九四五年以后)“文明”开始成为一个失去其清白而受到怀疑的范畴时,“进步”作为一个范畴却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它绝不仅仅是取代“文明”,它甚至还更有深意。进步这个范畴的作用似乎是欧洲中心论的最后堡垒,是其退却的最后堡垒。
当然,进步的观念总是受到保守的批评家的批评,尽管他们的反对气势在一八五○年到一九五○年这一时期已经大大减弱了。但是,至少从一九六八年以来,对进步这个观念的批评又一下子卷土重来,不仅在保守派中充满了新的活力,而且在左翼中更充满了新的信念。人们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抨击进步这个观念。例如有人指出,一直被称为进步的东西是一种假进步,但是真进步是存在的,因此他们论证说,欧洲关于进步的说法过去是一种欺骗或一种欺骗的企图。也有人说,因为“原罪”或人性的永久性循环,因此不可能有进步这样的东西。还有人说,欧洲确实获得了闻名于世的进步,但是它现在试图阻止世界其他地区也享有进步的成果,一如某些生态运动的非西方批评家所论证的那样。
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对于许多人来说,进步这个观念已经被标识为一种欧洲式的观念,因此被置于对欧洲中心论的抨击之下。然而当其他非西方人努力运用进步这个观念,因而只是把欧洲而不是把进步也从思维图景中清除出去时,他们这种抨击常常是自相矛盾的。
(本文是作者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在汉城召开的“亚洲社会学的前景”研讨会上的讲演稿,经作者同意特由本刊发表。原文是英文,雪君译,下期续完。)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进步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