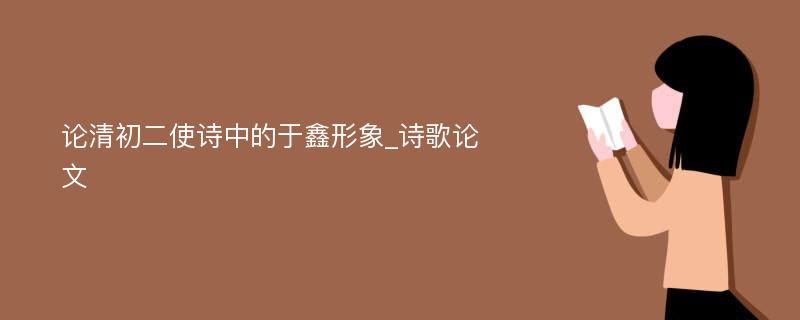
论清初贰臣诗人诗歌中的“庾信意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贰臣论文,清初论文,意象论文,诗人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3)-03-0018-04
所谓“贰臣”,是指封建社会改朝换代时身仕两朝的官员。乾隆皇帝在四十一年正式提出编纂《贰臣传》,分甲乙两编,收录了明末清初在明清两朝为官的人物共120余人。《贰臣传》乙编上列名的人物,多为当时著名文人,如钱谦益、吴伟业等。乾隆从政治、道德角度出发,贬抑这些人为“大节有亏”而“为清流所不齿”之人,以后遂成官方定谳,后世亦因之而轻“贰臣”其人其行,甚至于其文。
乾隆初年浙江山阴人沈永壶撰《重麟玉册》八卷,用纪传体裁来记述南明诸王的史事,书中《李映碧传》后有附记说:“当时钱牧斋、吴梅村、龚芝麓、陈素庵、曹倦圃为‘江浙五不肖’,‘皆蒙面灌浆人也’。”[1]钱牧斋即钱谦益,吴梅村即吴伟业,龚芝麓为龚鼎孳,陈素庵为陈之遴,曹倦圃为曹溶,这五人都是清初著名的贰臣诗人。
其实不需时人及后世的谴责,“贰臣”本身对自己也没有放松过心灵上的鞭挞。翻开他们的诗文集,充斥于眼的多是悲、愧、恨、悔等字眼,这些词语不同程度地表现他们内心的自责、自惭、自愧之情。[2]赵园先生说:“读吴伟业文集,你不难感知那自审的严酷,与自我救赎的艰难。这一种罪与罚,也令人想到宗教的情景。”[3]吴伟业在成为贰臣后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把全部情思都集中于自悔自忏、自责自讼的哀叹中。马积高先生也说:“明而又仕清的人即使看来是失节,除了一些廉耻丧尽之徒(他们多不是诗人)外,都不免有内心的自责、痛苦和悲哀,对故国旧友(特别是死于抗清者)不免有所怀念。”[4]抑郁低回的“失路之悲”成为贰臣诗人群体诗歌创作中的一大主题,而表现手法是多借“庾信”意象来表达这种失路之悲。
庾信本为梁臣,出使北朝被强留,历事魏周两朝,成为身不由己的贰臣。从草长莺飞、柳暗花明的江南来到风急天高、苍凉偏僻的黄土高原,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其多乡关之思,身仕两朝的贰臣身份又使其多自悔之调,这种共同的人生遭际使南方贰臣诗人与庾信思接千载,成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异代知音,他们用“庾信”这个意象浓缩了自己的思想、情感世界中的种种愧疚与忧愁、失落与沉重,此亦是一个时代所特有的文学现象。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庾信”意象极为恰当好地表达了贰臣诗人的经历境遇及其思想感情。其中既含寓着家国覆亡的黍离之悲,又包蕴着身世浮沉的难言之痛,说尽了贰臣诗人曲折掩抑的心事,也是他们借史事舒展隐蔽心态的一种表达方式。庾信无论是从身份、文才还是出处境遇上,都与贰臣诗人相暗合。
早在唐代文人笔下,就已出现“庾信”形象,不过那还只是单纯就其文采而言,并没有涉及庾信的身世出处。如杜甫就有“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等语论其文学成就。在宋代,庾信形象多见于宋词中,如黄庭坚《减字木兰花》:“无处重寻庾信愁”,贺铸《浪淘沙》四首之第三首:“兰成老去转无聊”,周邦彦《宴清都》“始信得、庾信愁多,江淹恨极须赋”,葛立方《满庭芳·泛梅》:“庾信何愁,休文何瘦,范叔一见何寒”,姜夔《霓裳中序第一》:“动庾信、清愁似织”,词例虽多,但取意单一,都是用庾信之愁的表面意思,而舍弃了庾信何以为愁的深层意蕴。而清初“贰臣”诗人重新拈出庾信形象,不再仅仅局限于愁绪的表层意义,而是暗中运用其故国之思与失路之悲的双层含义,这样无疑比宋词中庾信形象更具深意,也更具感染力。
时人常以“庾信”来比贰臣诗人。如遗民耆宿钱澄之在《寄吴梅村宫詹》七律组诗中就把吴伟业比做庾信:“秣陵烟树已全空,回首登临似梦中。祗课诗篇销晚岁,别填词曲哭秋风。同时被招情偏苦,往事伤怀句每工。却忆清江杨伯起,屡辞麻诏荐娄东。”(《寄吴梅村宫詹·其二》);“娄水扁舟忆昔游,遥怜风物汉时秋。山涛启事真无故,庾信哀时岂自由?音乐解来翻引恨,壐书征后迥添愁。淮王仙去遗鸡犬,佳句频吟涕泗流”。(《寄吴梅村宫詹·其三》)[6]吴伟业自己在《听朱乐隆歌》诗中也自称“庾信”:“楚雨荆云雁影还,竹枝弹彻泪痕斑。坐中谁是沾裳者,词客哀时庾子山。”[7]遗民吴骐在李雯诗后题有:“胡笳曲就声多怨,破镜诗成意自惭。庾信文章真健笔,可怜江北望江南。”[8]宋琬也有《重晤李舒章》:“竞传河朔陈琳檄,谁念江南庾信哀?”[9]都把贰臣诗人比做庾信。李雯在他的《甲申夏日写怀》其四中也自伤:“江南庾信诚摇落,此日无家胜有家。”姜埰有《广陵遇嘉禾友感赋》诗:“朝罢西华并马还,龚曹昔日此鹓班。人留天宝风尘后,客在雷塘雨雪间。连岁丧亡哀白马,几年离别惨朱颜。娄东学士三词伯,身世伤心庾子山。”[10]诗中便把吴伟业、龚鼎孳、曹溶三人比作由南入北的庾信,同情他们的“身世伤心”。姜埰在明时为礼科给事中,龚鼎孳为兵科给事中,嘉禾友人指曹溶,均为姜埰在明时同僚,明亡后龚曹两人仕清,而姜则以遗民终老,虽然在明清易代之际,三人的政治选择不同,但姜埰并没有对成为贰臣的龚、曹两人给予讥斥,而是表达了惋惜与同情,足见友情之深。
但值得一提的是,“庾信”在当时仅指南方贰臣诗人,这点无论是时人还是南方贰臣诗人本身都认同这种比喻,而北方贰臣诗人既没有用此典自比,时人也没有用此典比喻他们。如北方贰臣诗人彭尔述,为河南邓州人,崇祯十三年进士,在明官至阳曲知县。入清官至贵州巡抚、云南左布政使。在籍贯上彭尔述与周亮工是河南同乡;在政治身份上,两人都是由明入清的贰臣,两人在地望、出处上均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彭尔述却把周亮工看作南方人,并且以“徐陵、庾信”视之,而自己却丝毫没有此感,他的《寄周元亮》诗云:“北风淅沥杂征尘,犹记衣冠南渡身。自许徐陵初使邺,岂知庾信竟留秦。十年梦对江东酒,万里鸿归海角人。芜没梁园宾客尽,宋家陵寝大河滨。”[11]不光是别人以庾信来喻南方贰臣诗人,就是他们自己也常用这个典故来自比。
南方贰臣诗人学识渊博,诗中多咏历史人物之作,但他们的作品中对庾信却最为钟情,庾信是在他们作品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历史人物,对庾信的感情的投入也都是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庾信的悲痛,只有与之出处身世相近的南方贰臣诗人才能道出,才能感觉到;也只有庾信,才能切合入微地表达他们内心复杂的情感,一个看似简单的艺术符号,往往牵系着一个民族丰富的历史经历和心灵世界。南方贰臣诗人把自己难言的身世之感寄托于庾信,所以他们的作品一再出现庾信的名字,把庾信故事融入自己的诗文中。“庾信”意象表达了南方贰臣诗人的家国覆亡之叹、身世浮沉之悲,具有深刻文化意蕴。
龚鼎孳在《唐髯孙诗序》说:“髯孙少年名家子,……守贞不字,季女斯饥,岁月悠悠,何能便老。吾伤其遇,行自伤也。夫髯孙慷慨投笔之岁与仆不幸成名之年,数适相等。吾腼颜视荫又几何时矣。江淹本是恨人,庾信平生萧瑟,然则吾自伤耳!”[12]文中充满了对唐髯孙遗民气节的敬佩,以庾信自比并表达了对自己行为的羞愧。龚鼎孳诗中用“庾信”意象也很多,如他的《正月二日……上人集寓斋分》诗其六:“百年歌苦望知音,庾信伤多只至今。玉马铜仙何代事,银樽锦瑟可怜心。”及《怀方密之诗》:“怪汝飘零事有诸,白衣冠又过扶胥。渡江功业推王谢,失路文章自庾徐”。在七绝《为沈郎玉卿题便面》中又说:“雕笼鹦鹉闭芳年,玉树明镫宛转前。名下易增沦落恨,子山词赋已风尘。”[13]一个庾信,道出龚鼎孳多少难言的心事。龚鼎孳不仅在友朋面前以庾信自比,甚至在亲人面前也是如此,他的《从淮阴幕府得舍弟孝绪到杭州消息喜寄三首用少陵韵》其二曰:“南望吴天烽火深,北来鸿雁晚霜侵。六桥烟柳愁中路,双桨秋虫乱后心。入洛士龙犹健在,无家庾信只哀吟。连床何夕沧桑话,细剪寒灯泪不禁。”
熊文举在《朱遂初南还近诗序》中说:“子美曾和庾子山咏怀二十七章,予再一讽诵,谓此枚叔十九,阮公咏怀,子山未能拟也,如吾子美则不惟拟议而且成其变化矣。子美和子山,或有深意,然开府老作北朝词臣,后人以杨柳一篇,哀其所遇之穷,每多恕论。异时倘以予与子美为徐庾其人,或者藉砥柱之鸿词,一洗飘零之绮业,是予所谓附骥以千里者也。舟过南流,涤砚书此以志作者之意。孝升、秋岳与予握手河梁,风期耿耿,他日抚膺实获,能无有感于予言。”[14]熊文举此文中便把自己与朱徽(字子美)并比为“徐庾”,希望能够得到后人的谅解。曹溶在《铁山自香山来晤赋赠》诗也以庾信自伤:“一叶随风度越台,又传消息素交来。读书隔代桓荣老,山海联床庾信哀。机尽乍看溪鸟下,官贫细数瘴花开。留君共住三冬暖,肯使南天半草莱”。[15]伍铁山,广东人,与曹溶为举人同年,入清不仕,以遗民终老。曹溶在诗中以拒仕王莽的桓荣比铁山,而自比庾信,显露出自惭不如之意。曹溶又有《仲春八日即席送客同舒章芝麓限韵二首》其二:“芳夜开樽汤玉箫,海棠无力上柔条。满堂珠作三千履,旧事莺啼十二桥。游爱春芜调骏马,坐愁燕阙换金貂。关山休厌归与晚,庾信平生语自骄。”又卷三十五《同张鞠存王雷臣陈海士集陈阶六恭恕堂限韵》:“故人斗酒长相命,足写平生庾信哀。”
一个“庾信”,写尽了南方贰臣诗人的黍离之悲、身世之苦,使读者数百年后读起来还有心酸之感。值得一提的是,只有那种具有强烈道德感的人才会为自己言行是否合乎道义在内心交战,才会不断地自我折磨,也才会从中获得人格的升华,达到精神上的救赎,这也是南方贰臣诗人以“庾信”自比的精神内涵。
与“庾信”意象意义相近的还有“李陵”意象。如朱彝尊作于康熙元年的《送曹侍郎备兵大同》诗:“司农论议朝端重,副相声名辇下闻。岂意尚烦西顾策,翻教暂领朔方军。河边远道人千里,天外乡书雁几群。到日关城春色早,李陵台畔柳纷纷。”[16]诗中隐将曹溶比作李陵,曹溶自己也有此感:“季鹰潦倒别渔矶,三月春风骏马肥。行尽江南芳草路,李陵台上雪初飞。”[17]与屈大均“遥寻苏武墓,不上李陵台”相比,还是看出了身份的差异。
南方贰臣还常用“天宝”与“新亭”意象来表现他们的沧桑之感和故国之思。钱谦益有《辛卯春尽歌者王郎北游告别戏题十四绝句》诗:“可是湖湘流落身?一声红豆也沾巾。休将天宝凄凉曲,唱与长安筵上人。”诗中把优伶王郎(当时著名艺人王紫稼)喻为经安史之乱而流落的李龟年,自己则暗比杜甫,有沧桑之感、难言之痛。“天宝”被用在明清之际的战乱中,很切合当时历史背景,清也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与安禄山的民族背景相似。“天宝”这一意象有两种含义,一寓兴亡之感受;二寓胡汉纷争之变故。
南方贰臣诗人集中也常出现“天宝”意象,如前文曾提到过的曹溶《戊子初春试笔》诗:“世法从灰冷,都无往日情。礼难调末俗,天宝误书生。晴罢闻幽鸟,春来对古城。回看名利域,锋镝太纵横。”[18]初读此诗,似不过是叹惜官场险恶、世路坎坷之意,但“天宝误书生”一语却道出其深处心事,曹溶此诗以在“安史之乱”中接受安禄山伪职的王维自比。从诗题上看,此诗作于戊子年,时为顺治五年(1648),当不是为降李自成之事而作,再有“安史之乱”也是异族入侵,而李自成则是同族操戈,所以应为降清而作。诗中作者自比为王维,感叹自己被乱世所误,与王维同病相怜。曹溶在顺治十一年写的《甲午春彦升芝麓招看韦祠海棠,余病不及赴遥同……》诗其二:“燕脂山下颜应好,天宝宫中恨较多。同是旧时憔悴客,可堪斜日听笙歌”,也表达了同样思想感情。
“天宝”在龚鼎孳诗中出现的次数也不少,如“相逢何意落花边,不记曾经天宝年。”[19]更为大胆的是,龚鼎孳在御宴上无所忌讳,直用天宝故事。他在卷十七《春日同金岂凡少宰刘玉孺司马曹秋岳太仆吴雪航侍御讌》其二中这样直笔写到:“绮筵三月敞兰亭,垂柳还依御苑青。槛外晴沙分鸟梦,西来山色入渔汀。凤笙队尚喧名部,雉尾得偏染昼檽。一座春愁天宝客,曲终未许落花听。”周亮工也有《丁亥侍叔父酌秦淮同张淑士舍弟靖公分得田字,时邻舟有盲女琵琶声》:“星河云影澹相连,桃叶依然旧渡边。盲女琵琶天宝事,羁人词赋帝京篇。宁知此会是何夕?剩有新愁入去年。始信情根堪万劫,鹊桥今古不桑田。[20]“天宝事”与“帝京篇”切合鼎革世事。天上鹊桥年年不变,人间却免不了沧海桑田,故国之思油然而生。熊文举有《侯大司农公子朝宗以诗见示》:“自写新诗诠注脚,居然天宝话兴亡。”[21]侯朝宗即侯方域,也是明清鼎革的亲历者,所以对天宝兴亡也是感同身受。
“新亭”意象在明末清初遗民诗中常出现,但南方贰臣诗人多具有遗民心态,故也常用此典。“新亭”这个典故来自《世说新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惟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新亭”之泣表达的是国土沦丧之悲,后世常用来指遗民怀念故国。钱谦益在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时曾这样写到:“颂系金陵忆判年,乳山道士日周旋,过从漫指龙门在,束缚真愁虎穴连。桃叶春流亡国恨,槐花秋踏故宫烟。于今敢下新亭泪,且为交游一惘然。”[22]钱谦益在辞官回乡后,积极参加南方的抗清活动,并为此两次入狱,所以他临终之时才说自己“于今敢下新亭泪”,觉得自己有资格成为遗民而发出的欣慰之语。
龚鼎孳集中多用“新亭”之典,如其卷六《再叠前韵》诗:“酒泣新亭事不同,庭花苑草总成空。名香昼省销银鸭,宝钿横塘冷玉虫。有客琉璃裁砚匣,谁家鹦鹉散屏风。赋成杨柳愁偏剧,何限心情一叹中。”卷八《长干秋兴》其五:“新亭杯酒后,哭叹已无人”、《雪后诸同人集斋送与治尔止伯紫半千还白门》其二:“移舟莫向新亭路,王谢河山叹亦稀”。卷二十五《青溪中秋诸子燕集吴咏亭》:“河山烟树旧新亭,钟阜云偏对酒青”、卷十九《雪后诸同人集斋送与治尔止伯紫半千还白门》其二:“移舟莫向新亭路,王谢河山叹亦稀”,这都充分说明了南方贰臣诗人身仕新朝,身在故国,“新亭”一典是他们心事的最好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