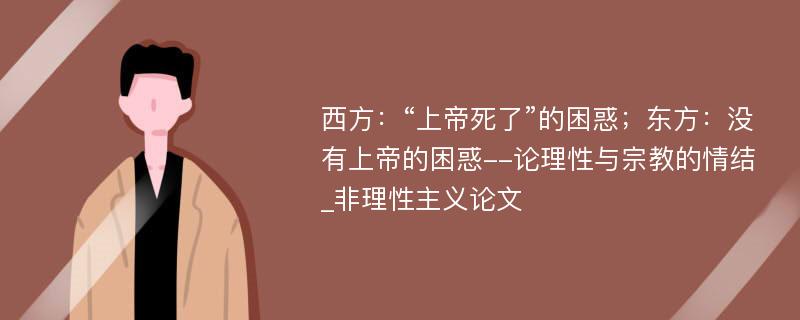
西方:“上帝死了”的困惑;东方:没有上帝的迷茫——续论理性与宗教的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帝论文,论理论文,死了论文,情结论文,困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期基督教既是犹太教和希腊哲学的融合,也是古代东西方文明汇合、交流进程中的产物。不了解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也就难以了解西方世界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同样,不了解东方文化对整个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影响、以及这两种文化在许多方面相互对立、相互补充的关系,也很难了解东方世界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西方基督教神学包括教会性和人文学“两个基本的言述维度”。欧美基督教神学近百年来发展的基本趋向是人文学方面的日益扩展和教会性方面的日益衰微。“神学的人文学扩展表现为神学与现代人文学术各种分化的学科(哲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的具体结合”(刘小枫:《金陵与神学》,《读书》1994年第6期)。基督教神学的人文学方面与教会性方面出现的这种二律背反关系,从知识学方面来看,则表现为知识理性与信仰经验之间的张力和冲突。神学的人文学方面的扩张,使基督信仰经验的独特性难以维系,使神学日益丧失其在现代多元知识处境中的权威性。于是西方的神学家与哲学家都致力于神学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协调。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尼采的“上帝死了”的呼喊。
“上帝死了”的思辩产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包含着理性的人类对宗教信仰的动摇,更包含着动摇了宗教信仰的人类对曾经神圣、曾经令人振奋的自由意志和理性力量的怀疑。”(杨慧琳:《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神学倾向》,《文艺研究》1994年第3期)实质上,“上帝死了”揭示出西方社会“从‘非理性’到二十世纪的自我怀疑”的精神历程中的基督教日益人文学化的特色。它体现着现代基督教从“神证”向神学、从笃信型宗教向文化型宗教的靠拢。从根本上说,神学所寻觅的“上帝”,哲学所探索的“永恒的本质”,蕴含着相似的价值取向。西方在神学的人文学方面日益扩展的趋势下,作为一切传统价值的终极象征,“上帝”已经难在具象的、实体的意义上被现代人所接受,但“上帝死了”并不意味着现代人不再信仰基督。仅仅是在“实在”的意义上否定上帝的存在,这种否定的指归是在“终极”的意义上肯定上帝的存在,使上帝成为超验的、没有任何“实在内容”的代表人类的一切终极追求。因此,“上帝死了”只能是抛弃基督教自称拥有一种绝对真理的“教会性”的神学“传统”或神学“权威”。所以,弗洛姆认为,不可能像感知实际存在的事物那样感知上帝,而“只能从否定的方面去认识上帝的属性”,“人越认识到上帝不是什么,人关于上帝的知识就越丰富。”(见《爱的艺术》)所以,“一切关于基督的表达,不仅是说他曾经是谁,现在是谁,而且是说他将是谁以及从他盼望什么”。(《希望神学》)这样看,“上帝死了”,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非理性”思潮和信仰危机的产物,他启开以怀疑和反叛为特征的、用新的理性自觉取代外部权威的新教精神的路;另一方面,它又成为更加合理的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为现代神学家和思想家建构一种能被现代理性所认可的神学提供了条件。是否可以这样说,“上帝死了”,实际上是沿着康德的那个被理性所“设定”的上帝,去寻找“上帝”以及它所象征的一切终级价值的本质。
西方的“上帝死了”决不仅是西方人的事,也深刻地影响着东方近现代精神文化的发展。有人断言:“西方人无法摆脱的苦恼和困惑,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是可摆脱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愚以为,在古代可以这样说,在近现代不能这样说。因为在世界性的工业化运动中,东西方在经济、文化、宗教诸方面被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仅仅着眼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是不完整的认识,必须看到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共同点,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并立与互补的。
基督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它没有像佛教那样比较容易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而中国化,因此它在中国的发展很缓慢。自清末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则与欧美资本主义向东方扩张息息相关。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这段时间内,基督教神学的人文学方面与教会性方面基本上是齐头并进和谐与共的。但是,一九四九年之后,在大陆,基督教神学的人文学方面被排斥在知识界之外,大学中的宗教学系被取消了。神学人文学的发展受到抑制的同时,教会性方面也被限制在极狭小的社会层面上。马克思学说在中国广泛的传播和做为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为无神论的社会思潮的迅猛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最优越的条件。无神论思潮做为一种社会意识必然冲击所有宗教在大陆的活动,包括佛、道等本土宗教。这样,基督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的互释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基督教中国化基本上处于停止状态。进入八十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给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但从目前的状况看,“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教会界,神学的处境化或中国化课题,还没有引起充分关注和讨论”。(同上文)这不仅与现政权推行的宗教政策有关,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也密节相关,这也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上帝死了”——非理性主义者的一声断喝,为人类开扩了新视野
韦伯曾经为如何走出现代文明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律背反”的迷宫而作了不懈的探索,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韦伯的思辩。于是产生了当代西方人文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向,就是从理性主义转向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既是现代社会里的一种社会思潮,也是一个泛文化的概念。现代西方学者在文化危机与学术批判的过程中,把全部人类生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加以重新审视,从文化一元论转向文化多元论,同时又从理性主义转向非理性主义,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和学术背景下,作为文化整体中的一种价值观念的宗教信仰势必成为西方人文主义者探索的一个精神热点。“突破个人局限的痛苦挣扎就是精神成长的痛苦挣扎”,西方人在“精神成长的痛苦挣扎”中,“由他(们)的最高愿望唤起的神性便会日益发展”,人们用虔诚的心态祭起了上帝的亡灵,“神性”成为他们构筑自己的人生信念的基石。
非理性主义的源头仍然在古希腊,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来看,整个西方文化本是共同源于古希腊的传统。柏拉图的“智慧之光”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引导西方文化哲学沿着两条迥然不同的道路发展:一是把哲学看作人生的向导,作为开启生命意义之门的钥匙;一是视哲学为理性的标志,用作探求自然之理的工具。就是说,人生与理性在古希腊哲学中就是难以解答的“二律背反”。中世纪的基督教把古希腊哲学中的“二律背反”宗教化、神学化。尽管在欧洲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柏拉图主义从未完全分开,在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之中就存在着浓厚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成分,但这二者的基本倾向性和他们所代表的发展方向还是异常鲜明的。反映在中世纪神学里,则成为理性的进步与堕落所构成的深刻矛盾,当然也是中世纪以后西方人再三思索的自然与发展、爱欲与文明、人道与科学的永恒冲突。
如果说文艺复兴借助于人性与理性这两般武器,那么启蒙运动则仰仗理性,把理性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真正的人生目的应该超越理性的单一的和决定性的规范。而至少在古典主义之前,人们把理性当成人的区别于其它生命的根本原因。于是人类被界定为理性的动物。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裁决权,而理性的极度膨胀最终必然走向其自身的反面,即韦伯说的,成为一种“暴政”。这也是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反对理性主义的历史原因。
法国启蒙主义运动思想家们对理性本身能力的高度确认,在思想上乃是源自笛卡尔的怀疑哲学。在当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休谟(Darid Hume)、佛格森(Adam Ferguson)就曾指出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对理性的看法是把理性肥肿化了,是对理性的误解与滥用。从笛卡尔始,尔后的哲学家把理性看作可以创造一切。“但把理性提高到这个层次以后,人的思想很易滑落到认为理性乃是肯定人间文明的一切的标准。人间文明中任何不合理的东西便都是不合理性,换句话说,道德、文化、思想、社会规则各方面都必须合乎理性,而理性乃是唯一合理的创造力——只有理性创造出来的东西才能够合乎理性。事实上,这一思辩逻辑是把‘理性’提高到相当于‘上帝’的地步”。(林毓生《从苏格兰启蒙运动谈起》,《读书》1993年第3期)
历史的进程由启蒙运动的近代历史时期把西方推进到现代,理性的异化使人类逐渐看到人的本质并不完全在于理性,把理性提高到相当于可以创造一切的“上帝”的层次,反而限制和缩小了人性的范畴。理性一旦变成一种创造一切、统治一切的“暴政”,必然要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对人性的极大压抑,于是非理性主义者应运而生,他们在批判理性主义的绝对权威时,为人类自身的认识又开辟了一新的视野。
体现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理性主义的功绩与历史局限性在上文已作扼要揭示,造成理性主义历史局限主要是近代学者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处理人文科学,造成科学主义吞蚀人文主义的恶果。本来理性主义精神就是近代自然科学发达的产物,因此近代一些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对自然科学方法观念盲目崇拜也是很自然的历史现象,到十九世纪后期就有一大批思想家发现理性主义的局限性,要求人文科学研究摆脱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寻求一种适合于人文科学研究对象的新观念、新方法,实现一种“观念的超越”,如胡塞尔、海德格尔、卡西尔、拉康,福柯等学者的研究倾向,都有超越作为理性主义观念主导精神的自然科学方法论观念,从这一视角看,可以把“非理性主义”规定为“理性主义”的对立面,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一种反叛意识。
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一书中把尼采和海德格尔作为非理性主义者的两个代表人物来批判,尼采(包括叔本华、居友、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意志哲学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对个体化生命价值的积极肯定和对于主体精神的追求,反映着西方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的一种道德文化变更,尼采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和教条化的基督教道德文化彻底否定,力图使西方道德摆脱理性教条化的凝滞状态。尼采认为代表强盛时期希腊精神——“生命冲动与宇宙文化融合”的湎神精神,自苏格拉底以后日趋衰落了,他批评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背叛了非理性的多神论文化而为日后的基督教神学开路,但是他对传统价值观采取全然否定的态度,却用颠倒的方法去看待历史,他认为从基督教出现以来,人类历史就是人类文明日益堕落和退化的历史。主张彻底砸碎传统宗教信仰,并试图为人类确立一种新的信仰对象,他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说:“上帝死了,现在我们祝愿超人诞生。”他以“幻象”或超人取代已经死去的上帝。尼采说超人是一种与现代人、善人、基督徒以及别的虚无主义者正相反对的人,超人实质上就是他的“强力意志”的新型人生哲学的代名词,洋溢着崇高艺术魅力和人生风范的“湎神形象”,是从人的生命本体中开掘出使人类生命存在挣脱传统桎梏的一种原始力量,是进取性和主体化全新意识和创造意志力的“英雄道德”境界。历史地看,尼采的“超人”思想对于克服西方传统道德的信仰主义和绝对理性主义是有进步作用的,西方后现代思潮的主要代表和创始人福柯(Michel Foueault)把尼采认作后现代思潮的先知,因为尼采宣布上帝(神)死了,以上帝(神)为寄托为依附的人也死了,未来处于无价值无意义而自身创造价值和意义的“超人”所支配。而后现代意义下的人,就是这种“超人”。“超人”绝不是神(上帝),也不是神(上帝)的宠儿或更接近神,恰恰相反,“超人”是神的杀手,是只承认自身价值和意义的真正的人。其实,尼采并没有把上帝逐出生活意义的断裂层面,他杜撰的取代至高无上的上帝的“超人”,所具有“深奥的意义”全在于超越客观现实条件,由于“出诸伦理之破坏者查拉图斯特拉之口”,他不可能成为对人类的生存提供一种终极意义和终极价值的至高目标。“超人”只能是“精神狂人”,“纳粹元凶”与“湎神形象”的杂种,是西方社会精神危机的哲学表达。所以荣格说:“无疑我们必须以昨天或明天的西洋人中某些特别聪明的样本为例外——他们是一些超人。他们的上帝死了,因此他们自己成了上帝,即成了理智主义的笨头笨脑而且是冷漠无情的假冒上帝”;“尼采在他开始得精神病看到上帝在Fcce Home显圣时,经验过这个。他过去用一种绝望的怀疑主义武装起自己并从正面加以反对的上帝,当时却从背后降到他身上”。(转引自黄盛华《信仰缺失:世纪之交无法挥去的一种迷茫》,《求是学刊》1993年第2期)尼采的超人哲学亵渎了“上帝”,“上帝”却从背后开他的玩笑,有些大谈尼采如何攻击基督教,却没有认真发现他思想中基督教的因素和渊源,艾略特(T·S·Eliot)说:“只有基督教文化,才会产生伏尔泰和尼采。”(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陈常锦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海德格尔很赞赏尼采的“上帝已死了”的这声断喝。他认为从柏拉图起的西方历史是不断上升的存在遗忘的历史。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与技术理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说:“技术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作为真理的一种形态滥竽充数”。(《报告和论文集》第80页,弗林恩1954年版)在现代社会里,由于人已经“着魔于技术”形成了“人的形而上学的利己主义”,(海氏手稿《技术》,转引自S·维塔《海德格尔批评国家社会主义和批评技术》第93页)面临着毁灭的危险。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所面临的文化危机在于“传统的哲学把人规定为理性的动物,但这理性又变成了工具性的理性,人是总是谋算和算计(rechnen)事物,成为‘技术动物’。”(《哲学论文集》第98页,法兰克福出版社1989年版)他说人不要总是当理性的动物,当前的现实是:人作为理性的动物(即作为进行劳动的动物)还在地球的荒芜之中流浪,人的劳动使一切在场物无条件地对象化,一切在场物都处在人的意志之中,被打上形而上学印记的世界在倒塌,从形而上学中发源出地球的荒芜,而倒塌和荒芜之发生是与形而上学的人(理性的动物)被确定为进行劳动的动物相对应的,这一确定证明了人还极度昧于“存在遗忘”。不难看出,海德格尔把形而上学看作是西方唯一的和必然的厄运。他把尼采看作由柏拉图开始的形而上学的历史的终结。晚期的海德格尔力图超越传统的人学,(包括尼采在内的人学),反对西方哲学史中的人本主义,他指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人不是存在者的主宰,人是存在的看护者。”(参见《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3页)明确声称“反对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心中说”(同上书117页)人类中心说就是形而上学,他说:“人类中心论‘指的是与形而上学的开始,展开和终结结合在一起的过程”。“形而上学在柏拉图思想中的开始,同时是‘人类中心论’的开始。”(《路标》法兰克福版1978年第234页)
在“人”的问题上,笛卡尔有一句理性主义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海德格尔以反理性主义传统的态度提出一个针锋相对的口号:“我在故我思”。他批判西方哲学史中从柏拉图开始的人类中心论(即形而上学)的主要矛头对准了近代自笛卡尔以来的主客两极化。从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开始到当代法国最活跃的哲学家“后结构主义”(或“消解学”)的代表人物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西方思想正在经历着背离自身传统的深刻变化,海德格尔同西方的许多哲学家一样,所面临的也是“理性”、“科学”“自由”的挑战。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人类奠定了一个全新的自我确证的基础:人是自身的“自我意识”。康德虽然狠狠批评了笛卡尔这一命题,指出不能用“思”来证明“在”,但实际上他在自己的“表象论”中却不可避免地容忍了这个命题。可以说,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已孕育了康德的那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即把立足点从客体(在)转向主体(思)来,这是自培根开始的西方哲学史上由本体论(存在论)向知识论的转化过程中的重要标志。在康德的“表象论”“知识论”中,“思”和“在”是统一的。笛卡尔、康德的贡献在于确立了“经验世界”为知识之对象和领域,使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颠覆与裂变,人不再是冥冥中的上帝或任何不可知的神秘之物,世界对于人类来说也不再是一个充满迷魅或巫术的存在,否定了以往神学家把宗教问题构造成一种知识体系的虚妄。但在康德那里,“经验”是“我思”建立的,“我思”不在“经验”之中,这是康德的知识论中的一个矛盾。“我思”是“空”的,又是有限的。
海德格尔一反笛卡尔、康德以来的所谓主体性原则的传统,将思考的重心从知识论转向存在论,使西方哲学对人的理解从“逻辑的人”真正过渡到“历史的人”,使人成为具体的、历史的“存在者”,主体与客体一起消溶于“这个存在”(Dasein)之中。海德格尔使胡塞尔的“先验的自我”、“生活中的主体”有了一个历史的归宿,也使新康德主义以来关于人的人类学、文化学方面所作的努力,在一种非形而上学的存在论(本体论)思路中得到改造。海德格尔Dasein的出现,在包括福柯在内的所谓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应意味着十九世纪历史主义思潮之完成和终结。
人本主义,人文主义(Humanism)是一种人类中心论。人为万物之灵,灵就灵在人是有思想的,而思想、精神是神圣的。精神与肉体之分化,是西方古代自苏格拉底以来就确立的一种传统。灵魂一直被认为可以和神打交道。发展到近代,所谓纯精神之“我思”亦是“人性”中“神性”的表现。康德限制“我思”于现象、表象界,实际上是排除将信仰转变为知识的可能性,使人、神彻底分离出来。然而,康德为信仰留下的地盘,仍是人的理性的纯粹的思和想,“我思”在不受感性(对象)制约、规定和刺激时,则为意志自由,则为神性。于是,理性仍是人性中神(圣)性的部分。胡塞尔曾批评康德抽象的“我思”,他的“先验的自我”不是概念化的理性,而被看成是前科学之“活的体验”(Living-experi-ence)但他的现象学的基本原则是“纯(即不杂经验、自然科学)心理的”。因而,在后现代派看来,现象学的人仍可以从“意义的裁体”方面来理解,而“意义”又是独立于个人之外的,人只是“意义”的传达者,所以现象学就是一种解释学,而人仍与神相通。
正如叶秀山先生所说的那样:“从对人的理解的角度来看,解释学仍将人置于与神相沟通的地位,人是神的意义(思)的传达者,尽管这里的神被理解为自然或他人。历史首先是他人的历史,我说的话首先是从他人那里听来的,我在历史中,亦即我在他人之中。列维纳斯(Levinas)说,他人的绝对化就是神。我和他人是可以交往、沟通的,因此我也是可以和神交往的、沟通的。我的意义来自他人,来自神。历史被理解为这种意义的延续。我是要死的,但只要他人存在,意义是会绵延、永存的。他人、历史代替了过去的宗教和信仰,给人以慰藉、寄托,给人以价值、意义。这是西方思潮中一直到海德格尔表现出来的一种非常坚定的信息。”(叶秀山《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18页)
二、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都没有与上帝脱离关系
人与上帝的关系不仅是基督神学的根本问题,而且是西方文化问题的结症所在,西方文化中理性与宗教信仰的矛盾统一关系,最终得触及上帝存在与否这一最为困难的问题。
有人说理性主义者虽然否定上帝的存在,但毕竟还给上帝留下“存在”的席位,而非理性主义者则把这“留下”的席位彻底掀翻了,从尼采和萨特以来,“上帝死了”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如果人们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圣经上的上帝着眼,到理性的上帝,再到世界和历史的上帝,再把眼光转移到无神论和虚无主义,认真地追寻一下上帝在西方几百年思想文化史上所走过的艰难历程,不难发现基督教与哲学有一种共存共荣的微妙关系。对于神学家来说,肯定上帝是他的面临无神论、虚无主义的必然抉择,而对理性主义者来说,他们的启蒙理性不仅驳不倒上帝,相反,对上帝的信赖更须理性地承担责任。虚无主义是由形而上学引导出来的,“上帝已死”是由理性哲学与非理性哲学的“上帝”引导出来的,而在所有西方人眼里,上帝的证明最终不在理性主义者与非理性主义那里,而在圣经中的亚伯拉罕、撒和雅各那里,在耶酥受磔刑的十字架上。因为,西方人认为他们的文化传统的本根不在中世纪,而在更早的古希腊和希伯来人那里。古代希腊人的理性与希伯来人的信仰才是充实的,它承担了人们生活实践各个方面的说明与引导。原来刻在古希腊德尔菲神庙墙上的那句“认识你自己”的神谕,现在却成了近现代理性哲学家与非理性哲学家们思考自己命运的启示录。
中世纪以后的西方哲学家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即在获得第二次堕落(人在亚当堕落后又因理性的狂妄而想变成“神”)中误入自然主义的歧途。在现代科学的诞生时期,以培根为代表的新生力量根据圣经宗教的观点主张人对自然的控制和作用,培根并没有否定人作为上帝自由制造的世界的承受者的观点,他曾“敦促他的同时代人,为了上帝和自己的同胞,重新取回上帝赋予他们的权利,恢复上帝指派给人类的对自然的支配权。”他也曾说:人的过错是“在神的造物和作品上清晰地打上自己的印记,而不从中谨慎地观察和认识造物主的印记。”(转引自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中译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现代科学的开创者伽利略和开谱勒等的“数学经验论”,颇能代表基督教徒科学家的立场。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经验,才能发现上帝创世的数学模式。西方的科学家虽然主张科学脱离神学,但他们都是信奉基督教的经验论者,至于牛顿在这方面的态度,可从他从事圣经神学的研究中看到底蕴,他的科学方法仍带有宗教信仰的印记。关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科学家兼宗教家的帕斯卡认为,神的启示对科学中的事实,不论其是否符合理性的预期,也应予以承认。我们可以看到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思想中有利于科学的一面,更可以看到哲学家培根、科学家波文耳和文学家弥尔顿等等,都在呼吁人们用科学知识去促进人间的公正和幸福,以迎接“上帝之国”,认为“智慧之光”即“上帝的灯”。甚至在宗教上持不可知论的赫胥黎(1825-1895)也认为科学所传授的真理“正是体现在完全服从上帝意志的基督教观点之中”。
本世纪提出拒斥谈论上帝的主张的两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从始至终都不曾否定过上帝的存在,相反,他把上帝保持在神秘之域来加以维护。因为他主张对神秘的、不可言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上帝的存在即属于不可言说的神秘之域。在谈到象征语言是什么语言时,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都作回答,这就是祈祷和诗,维特根斯坦曾在独自的沉思笔记中写到上帝意味着生命的意义、世界的意义,祈祷就是思索生命的意义。这里,我们重点谈谈海德格尔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
有人说,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1927)一书里采取了克尔恺郭尔关于人的观点,但带有无神论而作基督教的见解。也有人说,“海德格尔的一切努力似乎旨在通过一种适当的逻辑或语言去限制普遍化的技术的‘框架’,以有利于在天、地、神和有死者的“四重性”中获得不同经验。“(珀格勒(海德格尔的思想之路》,弗林恩,1990年第343页)也有人说“他之所以象荷尔德林那样诉诸神、神灵和宗教,是为了借神的权威,给西方无限制的技术化划定一条界限”。他幻想靠艺术和宗教去解决技术世界中的问题”。我想,无论把海德格尔的哲学视为有神论还是无神论,都会违背哲学的本意。不可否认的是,“海德格尔的哲学与神学有着极为紧密又极为隐秘的内在联系”,“神圣的东西在他那里更加富有神圣性,以致到了不可触及的地步。”
海德格尔在中学时代,就受到十九世纪末期基督教哲学家弗朗兹·布伦塔诺的影响,在弗赖堡大学时,研究过基督教神学和中世纪经院哲学。他与基督教神学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
最令人感兴味的是,海德格尔的新本体论思想竟成为神学家论证“人格的上帝”的存在的理论基础。神学家H·奥特的著作《人格的上帝》中采取了海德格尔的思想所暗示的思想道路。H·奥特从一种新的角度重提上帝的人格性,坚持从人的生存出发走向人格的上帝,奥特尤其关注海德格尔的后期著作,“他从海德格尔那里获得的是重新提出本体论问题——本体论的转向,并将它引入到神学领域”。“人格的上帝或上帝的人格性这一传统论题,完全是在海德格尔的新本体论基础上重新予以考虑的。神学最终是要促使人作为一个活的存在站在作为绝对的你的上帝面前,与上帝对话。H·奥特在《上帝》(cott kreuz-verlag 1971)一书中论述一个与海德格尔一样的观点,认为只有通过对被歪曲了的上帝认识的批判,才能使真实的上帝为人们所理解。海德格尔在其被称为“日益回到神学的晚期”(Hans Ebeling)大谈诗的语言功能和本质,与蒂利希、利科、奥特对语言的象征功能的神学讨论——即以语言的象征来谈论上帝是那样合拍,这些论说的确深深地同时也极为隐秘地浸润着神学的意图。
海德格尔的哲学影响了二十世纪的神学家,而他明显地受十九世纪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影响,这位神学家所说的“信仰的飞跃”(leap of faith)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所主张的在上帝面前保持沉默的意蕴是相同的,对于情况不明的客观事物特别是基督教对上帝的信仰,克尔恺郭尔认为,上帝与人迥然不同,在上帝和人中间有一鸿沟,只有信仰才能使人跨过这条鸿沟。他既反对黑格尔的理性化的基督教,也反对基督教正统派从理性证明基督教信仰。克尔恺郭尔认为宗教真理不能从客观上证实,只有通过意志的活动才能掌握。克尔恺郭尔的这些观点在海德格尔哲学中留下鲜明的轨迹,后者“神圣的东西”、“祈祷与诗”都与前者的“隐喻”“信仰的飞跃”有着极为隐秘的内在联系。克尔恺郭尔对黑格尔主义的激烈批判更直接影响其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
哲学家萨特,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呼喊,几乎是在同时,神学家自朋霍费尔开始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后的英美“激进神学”派也相应地提出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论题:“上帝之死”。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在德国纳粹集中营里提出了著名的“非宗教的基督教”构想,这构想成为战后激进的“世俗基督教”(secular christianity)和“上帝已死神学”(Diecottist Perosonliche cott 1969 Vanden hock & Ruprecht verlagtot·Theologie)的理论基础。当然“激进神学”家谈的“上帝之死”不具有无神论的内涵,但是它又明显具有超逾有神论的意图。然而,不管是在尼采那里,还是在激进神学家汉密尔顿(W·H·Hamilton)那里,“上帝之死”绝不等于“上帝不在”、“消失”等等,上帝的存在问题不是被取消了,而是上帝存在的神秘性和不可言说性得到加倍的强调。“作为人,我们不能谈说上帝,作为神学家,我们必须谈论上帝”,这是神学家卡尔·巴特早就说过的话,这是西方现代人的生活环境中的一个悖论,这一悖论又恰恰是西方现代哲学的思考中所蕴含的丰富成果——西方哲学的根本性思考背后总是隐藏着关于上帝的思——得到同样有成效的神学上的反应。拯救人的当然并不是上帝,而是人以心造的幻影激发起隐藏在最深处的爱心。这是几百年西方文化积淀而成的幻影——爱心,在哲学家与科学家那里,在所有西方人那里,上帝与人类间的鸿沟,彼岸与此岸间的阻隔,就此填平。(待续)
标签:非理性主义论文; 基督教论文; 尼采哲学论文; 超人哲学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上帝已死论文; 读书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超人论文; 笛卡尔论文; 康德哲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哲学史论文; 现象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