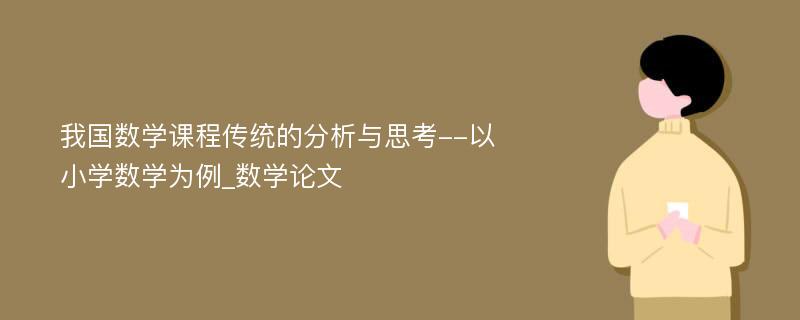
关于中国数学课程传统的分析与思考——以小学数学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中国论文,小学数学论文,传统论文,数学课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的道路上总会有一些困惑,对数学课程来说,在“改不改”、“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上始终存在争议.比较大的争议围绕在如何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方面.无疑,改革应该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但就数学课程与教学而言,什么是传统却经常让人心里没有底.常有未经思辨就大体上认定数学新课程在“抛弃”传统,而对数学课程的新理念以及与“经历、体验、探索”有关的新要求却或多或少地被判定为“舶来品”或“洋理念”的情形.所以,围绕数学课程与教学进行必要的历史回顾与反思,有助于澄清哪些是中国数学课程的传统,哪些是纯粹的“舶来品”,哪些值得今天的改革借鉴和继承,哪些则是今天改革必啃的“硬骨头”.文章依据《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体现的新精神,围绕这些问题做了一些粗浅的分析与思考.
因为现代教育意义下的中国数学课程最初是从小学开始,且考虑到篇幅问题,故文章仅以小学数学课程为例谈起.虽仅例及小学,研究得出的结论与思考同样适用于初中、高中,是就整个数学课程而言的.
一、厘清现代教育意义下中国数学课程的历史脉络
作为学校教育内容的数学课程在中国的历史不长,也就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体会,把这一百多年时间中国数学课程的发展演进大体划分为3个阶段:稳定期(1902—1952)、转折期(1952—1983)、改革期(1983—).其中的“改革期”以邓小平提出“三个面向”为起点.因为始于这一时期的改革仍在持续进行之中,且这一时期的亲历者众多,研究空间相对较大,故本文未予涉及.
1.稳定期(1902—1952)
1902—1952是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50年,也是一个世代更替、内忧外患、战乱不息的动荡年代.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中国的数学课程反倒没怎么动荡,运行的比较稳定,不仅理念和要求比较先进,而且与那时的世界相比,中国数学课程发展的起点似乎并不低.在50年的时间里,中国小学数学从国家标准和数学家的信念方面,始终:
(1)关注数学与儿童现实生活的联系.
(2)关注数学学习与儿童心理发展的关系.
(3)关注归纳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
(4)关注计算的快速与准确.
这几个“关注”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大,延续性明显,并具有稳定的特征,基本上符合“传统”应当具备的那些社会要素.
显然,“四个关注”这样的传统与研究者们通常认为的那个讲究“熟能生巧”、注重记忆、重复、逻辑演绎的传统有了很大不同,但它们有与时俱进的空间和活力.对这一点只能间接地做些说明.
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中国,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的人非常有限,在一个战乱不停的环境下是否能落实上面提到的“关注”值得怀疑,当时会遇到怎样的挑战难以想象.不过,那个时代是中国现代数学教育的初始阶段,只要有机会在学校里学习数学的人,应该或多或少都在“四个关注”这样的氛围里受过熏陶.而且可以肯定的是,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陈省身、华罗庚、冯康、陈建功、吴文俊等世界公认的大数学家的数学世界都是在那时开始建立的.以他们的成就而言,迄今能与他们比肩、达到他们的影响和高度的中国数学家还不多.这些人的童年和最初的数学教育都是在中国接受的这一事实,至少提供给研究者们这样一个思考的角度:“四个关注”应该有助于留住兴趣、保持好奇、孕育智慧,它们可能是产生初步创新意识的温床.
遗憾的是,接下来的年代中国再没有孕育出新的数学大家.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但中国数学课程在1952年出现的转折,应当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因素.
2.转折期(1952—1983)
1952年,新中国百废待兴,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速度,采取了全面学习前苏联的国家战略.这在有些领域,如经济、国防方面无疑是必不可少和十分有效的,但完全摒弃了中国数学课程在差不多50年时间里积累的一切,完全照抄照搬前苏联的数学课程,则几乎彻底颠覆了中国数学课程稳定发展的道路.这一重大转折的产生,源自新中国在1952年颁布的《小学算术教学大纲》[1].这个大纲是当时教育部根据前苏联小学算术教学大纲编译的,换句话说,新中国的数学课程始自前苏联教学大纲的中文版.
该大纲反映出前苏联小学数学课程的基本理念:接受式教学,灌输书本知识;教师是整个教学过程的权威,教学过程中强调训练和纪律;强调学生的刻苦和专心,等等,其提法和要求与中国原有的提法截然不同:从以儿童为中心转向知识中心;从重视归纳转向重视演绎;从强调综合的数学转向强调算数本身的系统性;从循循善诱转向严厉苛责,几乎每一条都与中国数学课程在稳定期的提法“拧着”来,差不多是针锋相对.在当时中国面临许许多多远比教育重要得多的现实困难急需解决的环境下,采取照抄照搬前苏联“老大哥”的做法“应急”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把中国的数学课程建立在前苏联的课程基础之上,并且方向掉转的如此剧烈,甚至视同己出、因循至今,就不那么让人理解了.因为前苏联大纲的缺陷与局限十分明显,如:使教育脱离社会实践和儿童的生活实际;忽略儿童的自由活动以及完善人格的自然发展,等等,都背离了中国数学课程较长时期内稳定发展的轨道.当时的无暇独立思考,为中国数学课程的后续发展种下隐患,今天改革必须面对的许多“硬骨头”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
以应用题为例,中国自己的传统提法是“算数的应用”,讲究“从实在的需要出发,使数目的计算有相当的依据”,重视应用的“真实感”,同时注重“正确而迅速的计算”.前苏联的大纲则突出“演算式题”、“解各种整数应用题的技能”,并规定了应用题的类型,开了中国数学“题型教育”的先河.由于这些类型大多属人为编造,与真实的应用无关,教学往往演化成“条件+题型=问题答案”的模式,学生忙于“对”类型,记结语,套公式,形成的多是“条件反射”,反思的余地不大.对此,弗赖登塔尔的评价很中肯:“把文字题的范例在结构上加以修饰,概括出题型,看起来好像很有用,但不会成功,因为这些假的题型丝毫无助于解决由文字叙述的那些实际问题.”[2]
从1952年开始,中国的数学课程跟着前苏联走上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这一走,之后的二十多年,包括与前苏联关系交恶,中国也没有走出自己的新路.后来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完成的1963年的《全日制小学算术教学大纲》[1]虽然在理念方面强调了算术与“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的关系,但在具体内容的要求方面基本上沿用了前苏联大纲的提法,“归一、行程、工程、和倍、差倍、和差”等题型就此融入中国的课程体系,而且渐渐地被认为是自己的东西了.
新一轮数学课程改革以来,仍有许多人未经思辨就把“应用题的类型”看成中国数学课程的传统,把《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不提应用题了看成是“摈弃了传统”、“削弱了双基”,把《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提出的两个“重要的数量关系”认知为应用题的回归,等等.容易看出,1952《小学算术教学大纲》产生的转折与造成的隐患到今天挥之不去.
二、结论与思考
基于上述梳理与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及其思考:
1.“四个关注”是中国现代数学课程与教学的传统
虽然新一轮的数学课程改革已经十多年,实质性的收获难说丰厚,距实现终生学习、创新意识、实践能力等目标尚远,期待的变化还没有真正出现.究其原因,数学课程与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之间的关系仍未厘清、数学课程标准的理念浮于表面应是主因.人们在理念面前的迟疑,与这些理念常常被冠以“舶来品”有关,因为“舶”的意思是新课程的理念与中国的数学课程的历史传统无关,仅仅是西方的洋理念的中文版而已.研究表明,这些无数次被斥为“洋理念、舶来品”的理念,曾经从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数学课程的上空徘徊过五十多年.时隔五十多年之后,那个年代倡导的“四个关注”又再次回归中国数学课程,成为中国数学课程理念体系的主体.这一结果说明:关注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关注数学学习与心理发展的关系;关注归纳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等等,无论是借鉴别人舶来的、还是传统固有的,对数学课程而言,其中蕴含的普适价值,都是一个正处于改革时代、逐步走向强大的中国数学课程的不二选择.“四个关注”是现代意义下中国数学课程起步阶段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又在面向21世纪的改革历程中发扬光大,符合“传统”要求的那些社会要素,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数学课程与教学的传统.而且,再没有什么与数学课程有关的传统比它们的历史更久、时间跨度更大,如果这些还称不起传统,差不多就是说中国没有现代教育意义下的数学课程与教学传统了.
当代人中,亲身经历过六七十年前的基础教育的已经不多,对这一事实的追本溯源,不仅在听到关于“舶来品、洋理念”的议论时会有思辨的意识,而且有助于澄清中国数学课程有过什么样的传统,增加人们锐意改革的底气.
2.“舶来品”要融入中国的数学课程传统
仔细考证一下,除珠算之外,现代教育意义下的中国数学课程内容差不多都是“舶来”的.不过“舶”的方式有不同:一种是一成不变的照抄照搬,如1952年的大纲;一种是把舶来的东西纳入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如“四个关注”.舶来品完全可以融入中国的数学课程,洋理念完全可以为我所用,成为中国人自己的传统.只要“洋理念、舶来品”,有助于中国成为一个人力资源大国,有利于把中国建成一个创新型国家,研究者们都应该积极借鉴、分享,何乐而不为?
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的一切领域都在走开放之路,在数学课程领域里拓宽国际视野,正在为中国的数学课程建设提供新的资源和推力,难言有什么负面影响.当前数学新课程的理念已经明晰,但从理念到教学实施的具体环节上仍面临课程资源匮乏、题材不够深入、参照系单一等问题的挑战,究竟什么样的课程资源能有助于引导学生经历探索过程,什么样的题材有益于搭建现实与抽象之间的桥梁,研究者们的确显得有些经验缺乏、手忙脚乱.而国外在这些方面的经验远比中国学者丰富.所以,适当地借鉴、引进这些经验对中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正在进行的数学课程改革而言,“洋理念、舶来品、新潮”等不应成为评价数学新课程的贬义词,哪怕有些尝试不那么成功、不那么有效,也要多几分爱护,少一些苛责才好.须知,现代意义下的中国数学课程的传统就是伴随着它们一点点孕育成形.
3.能与时俱进的传统才是优良传统
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每一历史时期的数学课程都把“正确而迅速的计算”这一条作为数学课程的目标,今天的数学课程标准甚至对“迅速”的含义做出了具体描述.大概就是因为长期以来始终坚持“又对、又快、又准”的原因,中国的数学教育在世界上常常赢得赞誉,无论是PISA还是其他大大小小的国际对比测试,中国除非不参加,参加了成绩就遥遥领先.研究者曾经对“又对、又快、又准”的提法感到困惑,觉得对、快、准的尺度如果把握不好,其结果可能是加重学生学习负担,教育价值并不大.这篇文章的分析,帮助研究者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正确而迅速的计算”确为中国数学课程固有的传统,在当代各国的数学课程标准中,很难找到类似的要求.从今天数学教育的现状看,在“四个关注”当中的“正确而迅速的计算”是所有传统当中最为有效的,受重视的程度远远高于其他.所以中国的数学课程无论经历怎样的改革进程,“正确而迅速的计算”这一条不能丢.
值得注意的是,“正确而迅速的计算”这一传统面临着与时俱进的挑战.
虽然中国学生的计算能力鹤立鸡群,但OECD(经合组织)对中国在PISA取得的成绩分析报告中认为:“中国的教育是以考试为导向的教育.学生的学习受到在考试中取得高分的压力.学校的基本的活动依据考试的需要展开……学生的成绩是通过延长学习时间,甚至是占用周末和法定休息时间取得的……付费的课余补习愈演愈烈……”《美国教育周刊》则评论说:“中国PISA的成绩再好,我们也学不了,因为美国青少年不会接受基于加重课业负担的教育改革……”这些声音虽然有些“酸葡萄”的味道,但是他们所做的分析不无道理,能提醒中国学者客观看待“正确而迅速的计算”这一传统.
的确,幼时的那些唾手可得的赞誉并未在成人社会里延续.计算是中国学生的长项,但计算能力对重复、记忆、机械训练的依赖难说不是增加学生负担的主因;“又对、又快、又准”是好东西,但弗赖登塔尔“人就是算得再快,能快过计算机吗?”[3]的疑问又在提醒学者们该从什么角度思考计算能力的教育价值问题.更进一步,在清楚计算是中国学生的长项的同时,更得看看什么是我们中国学生的弱项,把精力匀一匀,在弥补弱项上多下一点工夫.因此,在保持“又对、又快、又准”的同时,要注意克服在计算问题上用力过度的倾向,要认真研究重复型、机械性、速率式训练的科学尺度,要在理解算理、发现算法上多下工夫.这样做,“正确而迅速的计算”这一传统才会发扬光大,成为与时俱进的优良传统.
4.以“抛弃传统”的理由评估新课程其思路值得商榷
伴随着对新课程是“洋理念、舶来品”的质疑,对新课程批评较多的是“抛弃传统”,而对“抛弃传统”举例最多的是新课程破坏了数学课程原有的体系,把数学课程体系搞的“支离破碎”,等等.
根据文章的研究结果,在1952年之前的五十多年里,中国的小学数学课程基本上没有构建什么课程结构,“体系”或“系统”这样的词没有出现.而现实遇到的情况往往是在把数学新课程的大部分理念判定为“舶来品、洋理念”的同时,却把体系认定为中国数学课程的传统.这样的认知值得思考与澄清.
“体系”自1952年起才从前苏联“舶”入中国的课程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描述是“无论如何不应为联系各科而破坏算术本身系统性”.这一提法最先从小学提起,开创了直线式课程结构[4]的先河,而后“体系”逐渐成了这类直线式发展的课程结构的代名词且一发不可收.客观地说,在体系进入中国之初,确实为教师开展教学提供了方便,它有助于数学面貌简洁、清晰,环环相扣地展现,使数学好教了.在20世纪以农业、人口密集型、高能耗产业为主体的时代,体系也没有给数学课程造成明显的伤害.所以经过差不多两三代人的传承,人们就渐渐忘了它们的缘起,把它们认同为中国数学课程的传统.但它们的确是成了今天改革必啃的“硬骨头”.
前苏联课程标准中强调的“系统性”,不仅排斥了数学与社会和其他学科的联系,甚至排斥了数学内部各科之间的联系.而新一轮数学课程改革的最重要目标是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惟大力拓展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索的空间和多提供动手、交流的机会而无其他良方.这就意味着,数学课程的立场要从教师的好教向学生的乐学、宜学转变.正因如此,数学新课程才不提应用题、倡导算法多样化、重视情景的使用、把过程看得和结果同样重要、增设实践与综合应用领域、推动归纳、合情与演绎推理并重,等等.如果体系太过严密清晰,这里提到的一切就无从生长,新课程的“新”也就无从谈起,改革也就没什么可改的了.另外,单就体系而言,当今世界数学课程领域“体系”林林总总,学科课程、经验课程、情景课程、联系课程、必需课程、核心课程、广谱课程,等等不胜枚举.每个课程都有自己的体系,它们在不同的国度里都有数不清的学习者,也没见在哪里坏过事.可见,体系不是天生的而是“人造”的,不同的教学理念会演绎出不同的体系,归根到底,体系是要为教学服务的,而不是教学要服从什么体系,本来就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体系,为什么在这里“体系”就成了摸不得、碰不得的雷区了呢?
其实新课程尚未对所谓“体系”产成实质性的冲击.虽然课程内容多了许多情景,虽然编排方式有了螺旋式上升,但那个直线式的“体系”仍在,在课程标准中设置了全世界独有的“实践与综合”领域的目的,就是试图沟通那几个以直线式存在的不同领域.一旦真正实现了课程结构的综合,“实践与综合”领域就没必要存在了.笔者希望能打碎,但实践证明还不具备“打碎”的能力和条件,数学新课程现在还完全谈不上“彻底砸碎了数学的逻辑系统,从而把数学大厦变成了一堆瓦灰石沙……”[5].
数学新课程需要不断完善,批评也是对新课程的一种呵护方式,问题是要把问题找准,以“抛弃传统”的理由苛责新课程,其思路值得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