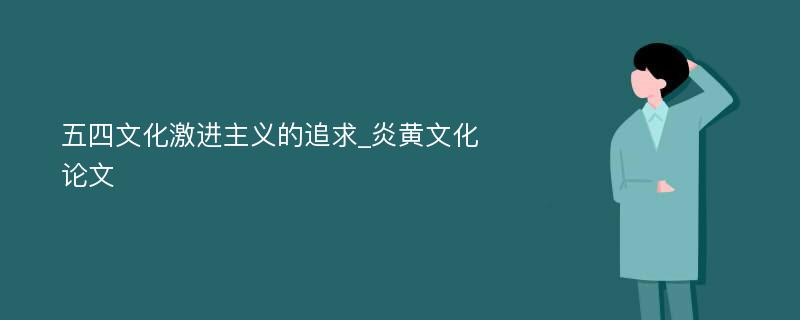
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寻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主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1)03-0104-08
文化激进主义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乃至颠覆做为寻求文化新生的策略。这种运思方式和迫切的心态在“五四”时期达到一个巅峰,成为五四时代精神的表征之一。尽管这种文化激进主义在五四先驱诸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身上体现为不同的样态,但做为一种时代的情绪,它的总体特征却是一致的。表现为向权威和传统大胆挑战的勇气和魄力,也就是时人所总结的扎硬寨、打死战、不退让、不妥协的斗士精神。
一、文化激进主义的潜在文化基因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冲击—反应的模式来解释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启动。我认为这是把复杂的历史等同被动而机械的生物反应的观念,使这一过程中东西、古今之间互动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固然与西方的刺激关系重大,但更缺少不了中国文化自身现代化萌动的内驱力。作为推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最主要的动力——文化激进主义,也有必要沉潜到传统文化的深处寻找它的动力源泉。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以正统的儒家文化为非的叛逆性格。“叛逆”是对于正统和权威的大胆挑战。由于正统与权威的稳固和强大,这种叛逆又往往体现为偏至的思想与行为。中国文化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文化叛逆浪潮,迄至五四演变为荡涤一切旧物的大波,传统文化才真正脱故孳新,获得了创造性转换的强力。
魏晋以还,文人崇尚谈玄,祖述老庄,“非汤武而薄周孔”[1](P1336-1337),构成对文化的第一次冲击波。由于缺少异质文化价值的比照,时人始终是以朴素的自然本性做为批判的依据。在这一点上,魏晋名士直接承继了老庄。还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老子就对儒家思想有所贬斥,以朴素的自然本性与儒家的礼教分庭抗礼。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38章》),只有摆脱了这些人为的束缚才能不为物累逍遥自适。儒学被定为一尊后,这种驳斥也就自然被斥为异端。但这种异端品格却在魏晋名士身上大放异彩。嵇康、阮籍就是远承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适性任情,在言行上对礼教大胆驳斥。嵇康认为正是这些礼教违反了人的自然本性:“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性,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谦生于争夺,非自然之出也”。[1]因此嵇康激烈地斥“仁义为臭腐”“六经为芜秽”。[1]主张顺从自然,废弃智慧,屏绝一切对外界的欲求,只求“意足”。但他们返朴还纯泯绝是非的自然主义人生观已丧失了昔日老庄的潇洒,而是涂上了浓重的厌世色彩。这自然有他们特定的时代原因,当时“司马氏篡魏当日,抗节之士进不欲苟合,退不能自保,故称述老庄,归本王何,其玩世不恭破毁礼法,造成一种颓丧或堕落的人生观盖有激然……。”[3](P30)魏晋名士以高蹈的姿态对抗时俗,破坏常理,表现出极端真率和适性的行为。然而细细分析他们的“非毁典谟”并非诚心针对礼教本身,而是针对那些看似“唯法是修,唯礼是克”,实际却“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阮籍《大人先生传》)的伪君子(如贾充、何曾之流)的痛斥。在中国传统社会,礼教与政治是互为支撑的,因此抨击礼教必然会指向礼教的最大的受益者——君主。稍后的鲍敬言进一步抨击了儒家“君权天授”的思想,认为人君的设立是由于强者凌弱者诈愚的结果。人性是以自然、自由为尚,立君则违反自然,束缚自由,故不是人性的要求即不是民意。(葛洪《抱朴子》)他们激进的无政府思想自然是源于当日人君的弊政以及曹氏和司马氏互相争夺所生的纷乱。正所谓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是痛恨主子。
历史的辩证法表明,当事物发展到极端时它的对立物也就应运而生。就在礼教达到鼎盛而严酷的时代,反抗也达到新的高度。宋以来正统儒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天理之公与人欲之私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境地,并成为个体必须遵循、服从、执行的绝对命令,从而导致晚明文人对于礼教压制下的感性生命的放纵性追求也达到极致。被明清多数学者视为异端的李贽等人站在礼教的对立面,把处于负面的人欲、私、利等概念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认为“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上”,显示出离经叛道的挑战者风范。其实李贽也并非真心反对礼教,而是针对那些“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假儒(《李贽文集》第10卷P72)。所以李贽称自己“故虽落发为僧而实儒也……然则善读儒书而善言德行者,实莫过于卓吾子也。”(《李贽文集》第5卷)并提倡以真诚的“童心”对抗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的虚矫。与历代具有反叛思想的名士一样,晚明文人的放浪形骸大多出于对乱世或暴政的失望和恐惧。
理学一方面成为宋以来历代王朝大力提倡奖掖的正统学说,另一方面也日益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从而招致一浪高过一浪的抨击。明清之际的戴震指出“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一语道出了礼教的实质。此时持有强烈反叛思想的人物还有黄宗羲。他的思想一直被视为中国民权思想的源泉。但这种民权思想并非舶来品,而是“在他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以中国思想的传统形式锐利地开始表述了近代民主政治思想。”[4](P284)黄宗羲提出“客君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梁启超评价为“此等论调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12](P70)梁启超给予黄宗羲如此之高的评价,关键在于当礼教还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突破了君臣纲常的儒家政治,具有了中国土生土长的近代民权思想。然而历史的造化总是给予后人以开阔的眼光,同时把伟大的前辈局限于时代的门槛以内。黄宗羲也不例外,他所向往的仍是“三代之治”,肯定古之圣君“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不享其利”。他虽重申“汤武革命”的思想,但可以预见革命所设立的自然是为民而设的圣君明主,这几乎是历代传统文人的最高理想。
清末以来对于传统礼教的反叛,成为五四文化大批判最直接的思想资源。康有为、梁启超与谭嗣同由于受到西方的感应,其思想已具有了新的质素,已经站在了中古与近代的边际线上。实际上自刘逢禄、龚自珍到康有为以来的今文经学,本身就带有异端色彩和叛逆性。虽然梁启超也认为乃师的《新学伪经考》“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但仍被他称为晚清“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5]关键是此书的价值不在于精审的“考”“辨”,而在于动摇了清学正统派的立足点,打开了人们重新认识、估价一切传统典籍的闸门,从而冲击了正统学术文化,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价值观念。因此引起了守旧士大夫的恐慌,帝师翁同龢称此书为“说经家野狐禅”。随后他的《孔子改制考》,更以现代的政治观念和进化论思想重塑孔子和儒学。而他“密不示人”的《大同书》,对于没有等级差别一切平等的大同理想的憧憬,正是对于等级森严的纲常名教的一种叛逆。虽然其中不乏中国儒家传统的道德的印痕,但更透露出西方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色彩。此二书被梁启超称为“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5]康有为虽然是“托古改制”,但并不能掩饰其思想中与儒学相背离的激进趋向。康有为的追随者谭嗣同较之有过之而无不及。谭嗣同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名教的核心思想:“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愚黔首之术,故莫以繁其名为尚焉!”[6](P14)这可以说揭示了礼教制造出“名”来禁锢人心的实质。认为五伦当中“夫惟朋友之伦独尊,彼四伦不废自废”。因为只有择友之道“不失自由之权”。[6]同时谭嗣同猛烈抨击君主专制,认为“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6](P55)谭嗣同直接主张流血革命这种激进的态度,超过了以往前辈,直接成为五四文化革命的先声。那么这种革命是否具有了现代意义呢?不尽然。他虽具有了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仍囿于传统期待贤明君主的出现,“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废其所谓民主而择其国之贤明者为之民主。”[6](P76)“君”作为国家的统治权威的地位是始终未被动摇的。我认为文化激进主义者们所做的对正统文化的反抗,只是限于体制之内,他们或以儒家文化之外的思想作为批判尺度,或以自认为正统的儒家思想去批判非正统的儒家思想,总之都限定在儒家文化框架之内。即便这样,这种叛逆品格做为一种文化基因,却一直潜沉在民族文化心理的底层,直到近现代终于得到激发,被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继承、张扬并赋予了新的质素,从而给予传统礼教以致命地打击。二者在深层上的精神联系以及在运思方式上的继承关系,是不可不明察的。
二、现实积聚的焦虑
中国近代所经历的“赤县神州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奇劫”,给近代以来的知识者以巨大的精神震撼。现实的逼迫,促使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走了一条越来越激进的道路。
西学东渐早在明末已经开始,到清末已具规模,但国人仍处于“徒知侈张中华未睹瀛寰之大”(魏源《圣武记》卷12)的天朝大国的迷梦当中,陷于一种“集体孤独症”,自认为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当时西方传教士利马窦来中国,带来了世界地图。在西方人眼中,世界已分为五大洲,中国只是其中一洲的一部分,而且被画在地图的一个角落下,结果立即引起中国士大夫的不满、嘲笑和攻击。利马窦只好做了修改,把地图上的子午线的位置移动,将中国置于全图的中心,以满足中国士大夫的自大心理。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小部分人觉醒,开始主动吸取西学,但这仍只是林则徐、魏源、徐继畲、李善兰等一小部分洞烛机先之士的共识。此时的一般士大夫对西洋人不是全无所知,就是一些毫无根据的偏见,甚至认为中国的大黄、茶叶是夷人维持生命的东西,一旦禁运他们将无以为生。[7](P282-284)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触动是微乎其微的。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长久以来一直是向外传播的源头,在认同异质文化时显示出巨大的文化惰性,把鸦片战争还是当做以往的倭寇、夷敌的骚扰。迟钝的文化反馈系统没有接到更多的危险信号。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终于惊醒了天朝迷梦。对近代中国面临的严峻情势,李鸿章作出了代表性地总结:“今东南海疆万余田,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里,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瞬息千里,军械机器之精巧力百倍,炮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亡国灭种的恐惧在当时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焦虑。这种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心理状态,主要通过社会思想文化的载体——知识分子表现出来,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深处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蕴藏在民族文化深层的文化基元[8],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已经成为促使中华民族奋斗、抗争的动力。这种忧患意识在传统士大夫身上,主要表现为对天道自然的深沉思索和对政权兴衰的深切忧思。尽管在不同时代它的内涵有所不同,但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是深深值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血脉之中的,也就是顾炎武所总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近代中国面临着外敌入侵内政腐朽的民族危机,由深广的忧患意识所激发的具有近代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救亡图存”思想,成为近代知识者的共通情态,并促成了在危机中变革的强烈要求。最早意识到变法迫切性的是龚自珍,认为“祖之法无不敝”,“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之”。(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译第7》)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变法思想在清末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随之而来的洋务运动,以对危机的认同,以国家富强、中兴为鹄的赋予变法以实践性品格,并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转型的序幕。但这种变革还只是浅表层面的旨在维护制度的深层结构和精神内核。洋务派中坚张之洞所提倡的“中体西用”(虽然不是他首创,但他是集大成者),正体现了新旧交替时变法者的心态:希望“既免于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张文襄公文集》卷29)中体西用论虽以伦常名教为本,但亦为西学的引进找到了合法依据。虽然洋务运动由最初的器械逐步深入到西学,但始终未能触及封建文化的精神内核。在他们心中“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兽之大防。”(张之洞《劝学篇》)“天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而对于维新派变法理论中的民权思想的攻击是不遗余力的:“今日愤世疾俗之士……倡为民权之义……嗟乎!安得此招乱之言哉!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四起。”(张之洞《劝学篇》)所以“西用”的范畴虽不断扩大,由技艺到经济到政治、教育,但并未触及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层面。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体用、道器的变与不变上显示出一种悖论心态。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以牛为体以马为用”的扞格不通。洋务运动在历史上因被贯以卖国的恶谥而被排除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之外,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冤枉。黑格尔曾指出,对于历史来说,重要的不是人们想做什么,而是通过人们的努力实际做了什么。洋务派主观上也许并没有要促进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意识,但文明作为一个整体,一旦这个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那么这个进程就不是谁能左右得了的了,并构成一个连锁反应,器物的、制度的、观念的各个层面会一个接一个牵扯着浮出历史表面。洋务派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无疑是要巩固清廷的统治,但实际上由这一动作带来的连锁反应恰恰导致了大清帝国的最终灭亡。正如张之洞在武汉实施的一系列强有力的军事、工业改革措施,最终使之成了反清革命的策源地,他本人也因此屡遭诟病。洋务派的失败自然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局限,但更重要的是历史条件的规约,使其难逃悲剧的命运。
中国人焦虑意识达到顶峰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一败而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相对而言,英法是西方强国,情有可原,而今是败在同文同种历来被中国士大夫鄙夷的东瀛小国,这种震撼和羞辱是空前的。同时多年经营的强国梦,在一日间破产了。船坚炮利是国人坚信不移的摆脱危机的不二法门,而今恰是在船坚炮利的情形下败于弹丸小国。中国士大夫群体觉醒,救亡之声盈于朝野。戊戌变法就是这种焦虑心态的一次爆发。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正是以“大变、快变、全变”的急切心态主张变法的,“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8](P211)当荣禄问如何改革,康有为答:“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9](P322)同时极度的焦虑又与盲目的乐观构成一枚硬币的两面。康有为认为:“大抵欧美以300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30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3年而宏规成,5年而条理备,8年而成效举,10年而霸图定矣。”
而恰恰是这种近乎天真的慷慨激昂、乐观、峻急的精神,给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精神萎缩和文化惰性以巨大的冲击。变法的失败与其归罪于保守势力的强大,或康有为等人的空想,还不如说封建专制体制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已经失去了进行自我调适、获得新生的能力,发生在其内部的技术修补措施注定要以失败告终。[10](P52)推翻这个无力而无效的统治成为历史的必然。失败所导致的是更激进的心态和更剧烈地变革,“今欲求避祸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之一法。”(P173)辛亥革命就是在“毕其功于一役”心态推动下的政治革命。但革命并未成功。“在每一次革命中政府被砍掉了脑袋,它的躯体却依旧完好无损地活着。”[11](P234)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但社会腐败,积弱依旧,复辟的丑剧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制度万能的迷信。与帝制相表里的尊孔逆流甚嚣尘上,显示出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文化的症结。没有文化心理的变革,没有深层的价值层面的改造,人们所企盼的“共和”不过是一场闹剧。更大更深层的文化革命于是又在孕育之中。
20世纪中国历史所进行的现代化转型,需要经济、政治、文化三种基本因素的全面综合实现。由于条件的限制,这种全面综合实现又是以某一历史因素的单向度突进来完成的。但历史的综合性要求却不会简化,使每个单一维度的变革或迟或早地置身于悖论境地,从而又催生着新的选择。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就是在这种悖论性的历史结构中一一宣告失败。正如梁启超所总结:“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而思返,觉得社会变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11]件件落空给国人造成极度失望、落寞的情绪,经过短期的蓄势,终于以更深刻、更凌厉之势爆发为五四新文化革命。
由洋务运动到新文化革命,这是一个层层深入的过程,最终触及到最深层的价值系统层面,没有彻底而坚决地革命激情不足以扫荡千年的积弊。并不是陈独秀们选择了文化激进主义,而是时代选择了陈独秀。历史发展自有其内在的依据,历史选择某个人或某件事,归根结底还是历史的一种蓄势找到了它得以发展的现实性力量和方式而已。
三、西方世界的示范效应
国门大开以来,面对西方世界的强大和中国的积贫积弱,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心中形成一种痛苦而急进的现代化情结。“西化”在当时成为现代化的另一种表述,西方物质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和中西文化的巨大落差,启示着中国知识分子作出全盘借鉴西方的抉择。五四以后梁启超所归纳的由“器物上感觉不足”到“制度上感觉不足”再到“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12](P833-834),显示了中国人以西方做为示范步步深入地借鉴学习的进程。而在观念变革的时代,西方有如潮涌的各种哲学、社会思潮,如尼采、康德的哲学,如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被争先恐后地引进中国,也成为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直接的理论资源。
世纪之交指引中国人寻求出路的是19世纪末的进化论思潮,几乎主宰了戊戌变法前后直至五四前后的思想界,滋润哺育了几代人。当时有人描述:“我们放开眼光看一看,现在的进化论已经有了左右思想的能力,无论什么哲学、伦理、教育以及社会之组织,宗教之精神,政治之设施,没有一种不受它的影响。”[13]曾负笈英伦的严复以开阔的眼光对进化论进行的创造性地译介中,强调物竞甚于天择,不但使之与中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元典精神相契合,从而为国人广泛接受。更重要的是,输入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和思维方式,打破了中国古老的循环历史观,代之以一往无前的进化史观,使后来的革命者获得了新的动力和凭依。正如艾森斯塔特指出的:“古代中国社会只有在帝国政治结构内的调适性变迁和边缘性变迁,而未产生导致制度转型的整体性变迁。”[14](P328)而现代化的变革源于现实的震荡和西风的感召。同时无论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其它思想都从中找到了自己发展的支援思想。就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也是以进化论作为自己出现的合法依据的。原因在于进化论的世界观契合了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中国近代盛行的进化论思潮,一开始便为社会进化预设了一个至善至美的终极目标社会,“向善”论成为一代人的共识,进化论因此为人们培育了一种一往无前的乐观主义信念和奋斗不息的精神。同时,进化论也为人们引进各种西方思想批判旧传统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在进化论的创造性译介中,严复把物竞天择作为天演的基本动力,尤其突出了物竞。这是与当时救国保种的社会心态相吻合的。但严复所主张的是一种循序渐进式的进化,不可躐等反对革命暴力。但竞争与革命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严峻的现实危机使人们很快把竞争置换为“革命”。并把革命提升为一种价值,极言革命对于摆脱民族危机的重要性。邹容曾大声疾呼:“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离满洲人之羁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20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15](P651)革命是那个时代先进的人们为解救亡国灭种的危机而作出的明确的选择。人们甚至相信“革命多而猛则社会进化速而大”[16](P1021)。带有浓烈激进色彩的革命借助进化论的现代母体,逐步成为深入人心的观念。人们坚信中国的社会进步必须诉诸革命。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人们却愈挫愈奋,把辛亥革命的失败归因于革命的不彻底而重新酝酿着更为彻底的革命。同时人们把这一观念贯彻到包括文学在内的各个领域。陈独秀在著名的《文学革命论》中的言论,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一种普遍心态:“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革命的豪情中首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进化论一方面给予了困境中的人们巨大的奋斗的动力,另一方面它所提供的线性思维又容易把复杂的现代转型简单化,从而剥夺了一些特殊领域的生动个体。
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帝国和农业社会在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心理层面积淀了根深蒂固的保守性,并直接导致了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迟滞。近代以来政治和文化日渐峻急的激进主义,正是对这种深固的文化惰性的反动。文化激进主义在打破旧文化的禁锢,迎受世界现代化的洗礼,实现传统价值系统的更新过程中,以对传统文化义无返顾地批判,昭示着中国启蒙时期的时代精神,显示出文化变革进程中矫枉过正的历史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只有沉潜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结合中国的现代化语境才能辨清。
收稿日期:1999-12-04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康有为论文; 革命论文; 国学论文; 叛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