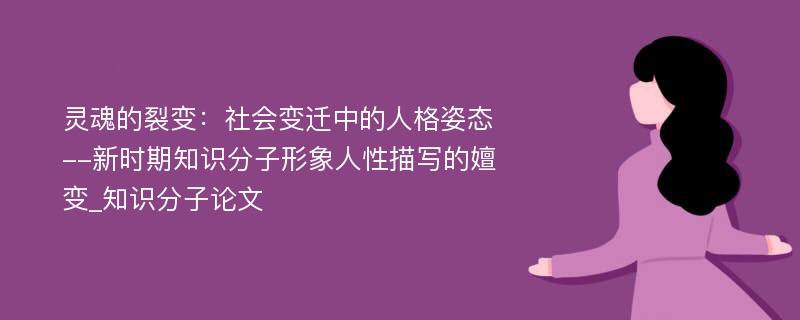
灵魂的裂变:社会变迁中的人格姿态——新时期知识分子形象人性描写之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知识分子论文,人格论文,姿态论文,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1)11-0078-06
一
通常说来,无论就现实世界还是艺术世界而言,知识分子的内在心灵往往要比普通人来得丰富和复杂。作为人类文化传统、道德理念、价值理性的承载者,知识分子在相同的社会环境和人生际遇中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情感态度乃至行为准则,较之普通人来说往往会体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和形态。知识分子由于承袭人类文明的种种思想和智慧,经由自身的思维活动而形成独立的观念体系——当他置身于具体的现实境遇中,这一观念体系便将左右他整个内心情感活动和价值判断,支配他的心理轨迹和行为走向,从而显示出非同寻常、矛盾复杂的人格姿态来。换言之,无论知识分子身处怎样不同时代环境而具有怎样不同的道德准则、价值观念,其面对无可回避的现实处境时,灵魂深处种种理念的相互纠葛、厮缠和冲撞,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从而格外充分地体现出人性结构中本能欲望与意识倾向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在小说家笔下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由于对象本身的内在丰富性,往往包含着深厚的人性底蕴,吸引着作家们去作深度的开掘。
当然,我们认定知识分子形象往往含蕴着丰富的人性内涵,这只是从理论上说的。就小说作品而言,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否具有丰富的人性内容,则不仅关涉到作家的艺术观念和现实理性认知,而且关涉到作品的创作背景——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往往决定着人性表现的主导形态和模式。对此,我们可以从新时期小说对知识分子形象描写的历史轨迹中获得佐证。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思想解放和西方哲学、文艺思潮的大量涌入,中国的知识界经历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启蒙运动,这一时期作为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承载者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文化心理还是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由于这一时期经济体制的改革尚未真正触及计划经济的根基,尽管思想文化领域格外活跃甚至有些超前,人们的观念体系也确有变化,可总体而言仍未越出传统价值观的范围。因而,这一时期小说对于知识分子形象的人性表现,便呈现出内在精神气质、价值追求与传统人格姿态的基本一致性。在传统的视域中,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具有某项知识专长的人,而且是必须对文化、社会和人类文明的繁荣与健康发展负有职责和使命的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从来都是知识分子的核心任务。然而,知识分子更应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与捍卫者,他一方面根据这些价值观念来批评社会的不良弊端,另一方面则努力促成这些价值的全面实现。因此,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外,尚需对人类公共利益怀抱崇高的热情与拥有真挚的关心,无私无畏、勇于承担”(注:张岩泉:《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三题》,《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8年第1期。)。很显然,传统观念框范下的知识分子,就其普遍的价值理性追求而言,通常总是与公众性事业或与国家、民族相维系的,并且这一追求往往并非是外在力量的强迫所致,而是知识者内在的、自发和自觉的愿望。产生于这样一种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小说,其知识分子形象所体现出的人性形态,便具有较为单一和相对平面化的特征。
几乎在整个80年代所出现的一批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所体现的人性内涵,几乎都具有这样一种特点:个性心理特征的相对模糊、价值理性以及情感追求的单向性与执着性。宗璞的《我是谁》、《三生石》;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谌容的《人到中年》、《散淡的人》;王蒙的《春之声》、《杂色》;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第一批作品中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也经受着种种的内心痛苦和灵魂煎熬,但这些痛苦多半是由于客观外界的压迫使然,而并非人物自身内在的矛盾冲突的结果。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你虽然能见到诸如情爱、生存欲望、价值追求等人性情感,但这些原本十分个人化的人性情感往往由于知识分子对既成的角色地位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认定,而与道德感使命感紧密相连,形成一种单向静态的人性范式。《春之声》中出洋归国的岳之峰由于出身问题而做过“没完没了的检讨”,依旧痴心不改地对祖国怀着深挚的热爱;《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女作家钟雨,出于道德感的约束而与所爱恋的人保持精神之恋,她那终其一生、痴心不改、永难忘怀的爱情,几乎成了其唯一的人性内容。不难看出,作家笔下的这些知识分子形象,不仅其价值理性追求具有单向性的特点,同时也缺乏内在生命欲望与价值追求的对立冲突,而且他们的价值追求所体现的道德理性内容,皆与传统观念所要求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品性相符合。在这些形象身上,我们很难看到出于一己私欲的世俗情感,也看不到委琐卑微的低贱灵魂,更看不到本能欲望无所顾忌、放任不羁的表演,相反,他们的人格品性总是与崇高、神圣、纯洁、执着、伟大等字眼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的灵魂世界中,任何琐屑、卑贱的人生欲念几乎没有容身之地,即便偶有抬头,也总是会被灵魂中的圣洁之光所驱逐。他们不论身处怎样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困扰,始终保持着一种矢志不移、洁身自好的人格姿态,不仅像上帝一样思考,同时格外注重将种种世俗行为与价值追求融为一体,保持二者的一致性。因此,在他们身上,尽管也时常要经受种种现实人生的困扰和折磨,但这些困扰和折磨往往来自外界客观境况的制约,而非内在精神的自我矛盾与厮缠,因而也较少人格的分裂。很显然,这类知识分子形象所显现出的人性内容相对而言比较单一,亦缺乏丰富的蕴涵,这既是那个时期政治文化语境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意识形态的特点使然,也是作家当时的思想观念、价值准则的内在规约的结果。从人性表现的角度而言,其厚实底蕴的缺乏是显而易见的,其由内心两极心理的对立冲突所构成的人性深度也是有限的。
二
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由于市场经济体系开始逐步确立,商业浪潮迅速掀起,社会形态开始实现真正的转换,以此为背景的知识分子形象之人性表现,亦发生了显著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异于80年代初、中期的小说,同时也异于更早甚至更久远的小说。此前的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不是秉承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人格规范,便是成为某种民族陋习和人性弱点的承载者,抑或是新社会道德精神与人格品质的体现。随着经济转型,尤其是转轨中的第一个冲击波所带来的最初的震荡,给整个社会固有的道德精神、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结构造成的冲击,使尚未建立起新的价值体系的知识分子,一时间不仅坠入迷茫,而且陷于人格坚守与跻身世俗的两难境地中,其灵魂的挣扎便显示出一种新的人性内容和人格姿态。
作为知识分子,其内心是否平静、灵魂是否安宁,常常与其所恪守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的是否失范紧密相连。当其所尊奉的人格操守受到冲击、平衡被打破时,维系精神世界的支柱势必受到动援而陷入迷惘、焦虑与痛苦。在视精神价值高于生存价值的知识分子那里,精神世界的失衡与崩塌所带来的幻灭感,是最容易将他们逼入绝望之境的,因而也就最能展示出其灵魂的搏杀。这种搏杀,其诱因虽来自于外部世界,但事实上是主体对自身价值认同危机的一种表现,体现出内在价值取向的紊乱和失调,由此构成对平静的心理状态的破坏性搅扰,从而导致精神的困顿。这一时期社会人文环境对知识分子人格姿态构成最大影响的,是日渐兴盛的物质主义潮流。而这股潮流之所以会构成巨大、深刻的影响,就在于它几乎一夜之间让所有的人都感到物质基础对于生存的重要性:物质财富的多寡不单是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人的物质性需求,而且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从而直接成为人的价值评判标准。这就打破了既往以知识与精神境地作为价值评判的社会规则,重新确立了一个以物质财富作为社会价值评判的标准,并为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可。在这样一种价值标准下,处于社会中心或自以为是处于社会中心的知识分子们,便一下子被抛向社会的边缘。价值失落的深切痛苦,不仅来自于他们所尊奉的道德观念和人格姿态遭到社会现实的无情嘲讽,而且来自于他们一向引为骄傲的文化优势在商业社会面前竟成为生存劣势。当习惯了处于社会中心的知识分子被汹涌的商潮抛到社会的边缘,甚至在边缘也需有一番挣扎才得以有容身之地时,他们的内心深处无疑要经历一场激烈的灵魂风暴。
在商业社会物质主义潮流的裹挟下,被抛向边缘而又不甘处于边缘的知识分子们,虽然还一时无法抛却曾经尊奉的价值准则,但对物质利益的普遍趋赴风尚所昭示的一种新的价值原则被愈来愈多的人所认可时,他们也不得不屈从这种原则,不得不将高贵的身躯探向世俗,为重新获得社会确认开始他们艰难的跋涉。这种跋涉的艰难性,对于尚未完全放弃传统的角色认定的知识分子而言,显然是双重的:当他们的道德理念、行为准则还停留于传统的框范里时,跻身世俗社会的现实行为和努力常常难以获得预期的结果;同时现实的行为选择与依旧恪守的人格姿态之间的冲突,也成为困扰他们灵魂的重要因素。这样,不仅是在现实的层面,还是在精神的层面,他们都无法获得自由,甚至无法获得灵魂的安宁——不得不选择趋向世俗的现实行为和难以舍弃的价值追求之间的深刻矛盾,使他们的人格处于分裂状态。从人性角度而言,人格分裂现象事实上反映了人的个性意识倾向的紊乱和内在矛盾性。通常说来,完整的、统一的人格,总是具有稳定、一致的意识倾向,其行为动机、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当社会环境、经济结构、文化背景发生变化,动摇了既成的价值体系所倚赖的基础时,人的个性意识倾向便会发生变化以致紊乱,形成内在的矛盾性。
旭峰的中篇小说《王谢堂》中的王谢便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作为贵族世家出身的知识分子,王谢禀承了知识者具有的自尊、清高的精神气质和敏感、脆弱的情感特点。然而,当这些建立在一定的经济保障和社会氛围(即某种价值体系)基础上的人格姿态,一旦失去了依托,便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王谢人格姿态的倾斜正是始于其家道中落且社会价值取向发生深刻变化之际。就王谢所恪守的人格姿态而言,他是不屑于涉足俗世、参与俗务的。由于知识分子的自我角色认同使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任何与世俗的牵连都会令其感到羞愧与耻辱。然而,生性清高的知识分子毕竟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也毕竟不可能置身于社会的真空之中,当生存的危机逼到眼皮底下,当社会价值体系发生悄然变化的时候,知识分子人格操守的把持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动摇。在生存困境的逼迫面前,王谢不得不下海经商,开起了饭店。王谢虽然身在商海俗世中,但精神纽带却依旧连着往日的母体:一方面屈从于现实的逼迫而从事着俗务;另一方面不愿放弃的价值观念又在不时地否定着自身的现实行为。这种由意识倾向的摇摆不定乃至相左所导致的人格分裂,构成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主要的精神特征。这一知识分子的人格姿态,我们还可以在方方的《行云流水》、《无处逃遁》;光汝松的《多恼河》;戴厚英的《脑裂》等作品中看到。
如果说上述作品是表现了商品经济兴起的最初几年里,知识分子在涉足俗世、与外在现实发生直接联系时导致人格姿态的倾斜,那么李贯通的《天缺一角》等作品里,则表现了知识分子自闭的内在心灵与外在世界物质主义潮流的尖锐对立,主人公对自身文化立场毫不妥协的坚守以及他以生命捏卫文化的举动,深刻昭示了文化人格与世俗人格难以相融的事实。在商业社会物欲横流的世俗风尚的裹挟下,芸芸众生对于物质利益的狂热趋赴,使昔日象征着社会地位和风光人生的文化,顷刻间便被人遗忘和抛弃,而视文化价值的守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也于一夜之间成为社会的边缘人。小说中作为文化馆员的于明诚,面对喧嚣的物质化的外部世界,身处冷清寂寞的文化馆这一方天地,他始终恪守着文化人的精神操守,不为世俗的欲望所诱惑。然而,尽管文化在他眼里其价值依然如故,也尽管他始终没有屈从世俗而丧失自身的文化人格,但当整个外部社会不再承认文化的价值,文化仅仅成为诸如于明诚一类少数知识分子自我认同、孤芳自赏的对象化参照物的时候,于明诚对于文化价值的坚守并不能求得内心的平静。社会对于文化的遗忘和否定,事实上也意味着对文化人的遗忘和否定,这就形成知识分子内在人格与外在价值评判的截然相反,构成知识分子与整个世界的对立局面。不难看出,不论是王谢的涉足商海而与外部世界发生直接的冲突,还是于明诚固守精神家园而构成的内在心灵与外在世界的对立,只要知识分子不放弃自身的文化立场,抑或是部分放弃,都难以摆脱价值失落的迷惘、困惑和痛苦。而作家以转型社会价值体系转换为背景对人物个性意识倾向内在矛盾的揭示,则从特定的层面透视出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所表现出的人性内涵:人对自身的角色认定,不仅取决于其所接受的文化观念,而且取决于其置身的社会环境所奉行的价值准则。换句话说,角色认定不仅是自身价值的自我肯定,同时也离不开外在于己的社会力量的评判与首肯。由此可见,人的心理意识不是一种静态的孤立存在,而是随着个人的认知经验和社会演变而发展变化,始终处于动态的过程中,并与外部世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由此体现出来。现实的物质利益诱引着人们去进行形而下的追求,而知识分子的良知又时时告诫他们必须固守形而上的信念,但由于形而下诱惑的强烈,致使形而上信念的固守时常被动摇,这就形成了灵魂的内在拼搏。在价值信念处于左右摇摆、难以定于一尊的境况下,灵魂的拼搏常常是最为激烈的,人性的表现也因此而显出深度。
三
9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建立,人们的价值观念体系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如果说90年代前后,在商品经济汹涌浪潮的最初冲击下,知识分子因一时无法接受骤然而至的价值失落而手足无措,陷于文化立场的摇摆状态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新的价值观念的确立,知识分子的人格姿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这一时期,由于市场经济不可阻遏的推进,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接受,也同样以不可阻遏之势构织着新的价值体系。当这一新的价值体系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时,对它的接受与否便决定着人们的现实生存状况。不甘处于社会边缘的知识分子,在意识到一味固守传统文化立场只能与社会更加疏离,永远处于边缘地位时,他们便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着自身的人格姿态。这种调整,或显现为对现实妥协和积极参与,或体现为角色认同的疏离和淡化,从而以一种新的价值认定和情感态度,成为商业社会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族群。不难看出,知识分子人格姿态的调整,鲜明地表现出人性在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时亦将随着发生变化,人性虽有相对稳定性,但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人性的具体形态总是由特定主体先天的个性心理状况与后天社会生活和人文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所决定的。一般说来,个性心理与社会历史环境互为作用所形成的意识倾向,即一定的情感态度、道德理性、价值观念等,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管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仍会固守既有的意识倾向,但随着这种固守因不合时宜而招致种种困扰以及新的社会价值形态为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旧价值观的消弥也就势所必然,由此,知识分子人格姿态的移变也就成为这一时期作家所热衷捕捉的人性焦点。
梁晓声在这一时期涉笔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主要有两部中篇:《学者之死》和《山里的花儿》。《山里的花儿》中的主人公A君无疑是置身于商业社会且实现了人格转换的知识分子形象。《学者之死》中的吴谭则是不同于A君的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就吴谭的个体生命而言,缺乏内在的生命热力和激情,缺乏超脱凡俗的傲然勇气,导致他在困窘的现实面前,显露出委琐、卑微、怯懦、脆弱的个性心理,向人们展现了一种有一定普遍性的知识分子的人格范型。与吴谭卑琐而艰难的人生跋涉不同,《山里的花儿》中同样出身于农村的A君,则全然是另一种样态的人性显现。他非但没有像吴谭那样始终背负着世俗生活的重担,而且活得春风得意、潇洒超然,在转型社会的价值体系里如鱼得水、从容自如。不过,对于A君这一形象,作家不只是表现其适应商品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的外在的行为特点,更着力于其内在复杂心灵的揭示,从而深入剖析和开掘了这一形象所蕴含的人性内容,展示了置身物质主义洪流之中知识分子极其复杂微妙的人格姿态。《山里的花儿》这部长达五万余字的中篇小说,就其情节构思的意蕴指向而言,显然是围绕着对人物的人性开掘落笔的:不仅摹写人物的表层心理,而且透视人物的深层心理,将被种种人性情感所遮蔽的人物深层心理动因作了深刻的揭示。在小说中,作家试图通过两种道德取向以及与之相应的现实境况的对比,映衬出A君现实人格姿态的真实面目,同时揭示现实社会中一种为人们所习焉不察的人性存在,即一种伪诈之风的盛行。A君现实人格姿态的形成并非偶然。商业社会以利益为中心的运行机制,势必将其所尊奉的价值准则强力推及至所有社会成员,虽然社会成员不会尽数接受这些准则,但由于商品经济所固有的特征及其对社会成员的巨大影响,仍会使相当一部分人服膺于它的魔力之下,成为汇入物质主义洪流的支脉。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在虚与逢迎、八面玲珑才有利于维护自身的地位并获得好处时,一些知识分子便于自觉不自觉中摆出了趋赴名利的人格姿态,从而将自己应负的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抛在脑后。由此可以见出其人格姿态已然完全发生了与商业社会价值取向相一致的变化,这种变化昭示出物质主义对于知识分子人格结构的重组,也展示出变革时代人性演化的复杂样态。
王石的《雁过无痕》同样描写了知识分子的现实人格姿态,所不同的是,这部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处世态度虽与商业社会的价值准则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不像A君那样明白直接地趋赴于物质利益,而是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富于现代精神内蕴的人生态度,呈示出更为宽广的表现内容。小说不仅摹写了学术权威与学界新秀之间的角逐争斗,也展示了两代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价值观念的变化,将当代部分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新的生存状态形神毕现地勾画出来。《雁过无痕》中的三位研究历史的知识分子,在人格姿态上与传统知识分子迥然相异。传统学者往往治学严谨,视学术为一种神圣的事业,并以拥有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为自豪。与此相连,在现实生存态度中,表现出对世俗世界的不屑和疏离,在精神价值的追求上体现出对真理的执着探索和学术良知,同时在人格风范上呈现出一种儒雅、庄重甚至多少有些清高的气度。而在作家笔下的人物身上,活跃在他们情感和精神领域里的,不是那些僵滞的观念和理性,而是一种活生生的人性涌动:他们不是在浩繁的历史事件及其关系中进行机械的被动的梳理,而是站在今人的立场上,从某种需要出发去主动地编排历史;他们没有被淹没在历史的烟尘里,而是在对历史的观照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在这里,学问不再以其严谨性和神圣性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牵绊,学问也不是作为一个人知识修养的标志,学问几乎成为人们谋取声名利益乃至人生快乐的一种工具和途径。小说中的几个人物,既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也缺乏一种对学术研究事业的追求精神;他们的行为,更多地受到一种功利和欲望的驱使,人们在他们身上所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庸常人生的文化表现。他们不仅在历史之外,也在历史之中实现着自身的人生追求,满足着种种与世俗世界并无二致的情感、精神及生活需求。
这一时期作家对知识分子人格姿态移变的描写,还体现在基于现代观念的情感形态的表现上。人类的情感世界从来就是历代作家所热衷于描写的,只是他们所涉笔的情感形态常常体现着各自时代的特点,与各个时代的思想观念、生态方式和生活氛围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映射着社会经济变革中人们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的悄然变化。情感作为人性的重要构成,不仅体现着人的个性气质,而且体现着人的观念意识。祁智《纸婚》中的李杉,被作家描绘成一个置身于90年代后期新潮生活圈中,在情感形态上远离传统意识的知识分子。在既往的小说中,知识分子的性爱情感往往受传统道德的影响和框范而呈现出一种稳定、专注的特征,富于道德感和责任感,虽然也存在一些由于客观和历史原因导致不幸婚姻而出现婚外情的有违传统伦理的情况,但即便如此,人物在情感上也不会走得太远,而常常被控制在发乎情止乎礼的范围内,并且这种情感本身也具有明确、稳定的旨归。但《纸婚》中的李杉却全然是另一种情感形态:飘移不定、无所归宿。李杉婚后不久便在妻子与另外两个女人——苏维维和唐敏之间周旋。依照传统的眼光,李杉的行为无疑要被置于道德批判的矛头之下。然而作家显然无意于描写一个情感上自由放纵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而是在基本上放弃了道德批准的企图,着重表现李杉那种看似朝三暮四实则茫然困惑的情感和心理,以期揭示当下社会的一种精神状态。
如果说祁智《纸婚》中的李杉表现出情感选择的迷惘的话,那么蒋韵的《现场逃逸》则是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多元化格局的商品经济时代价值取向的茫然。小说中的主人公林则作为一名为人师表的高校教师,其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本应是明确的,至少也是隐约存在的。然而,在作家笔下,林则却生活得很茫然,甚至还有些混沌。从人性角度观之,林则事实上已处于个性意识倾向的泛化乃至虚无状态,价值与意义的缺失,在某种意义上即意味着灵魂的虚空,也就无所谓人格姿态了。在此,作家展示了转型社会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人格姿态中的一个特例,这个特例的存在,其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了转型期的某种后现代特征,而且在于提供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形象所具有的一种人性形态。
就9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创作的总体状况而言,如果说林则这样的价值虚无的知识分子还只是一个特例,那么,梁晓声笔下的A君、王石笔下的几位历史学研究者以及祁智笔下的李杉之类的知识分子,他们所表现出的人格姿态便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事实上,在我们脱离小说文本而返观这一时期现实境况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时,同样能给予这一普遍性以确认。这批知识分子人格姿态的形成,既是商业社会以物质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成为社会价值主流的结果,也是知识分子对于自身价值准则自觉不自觉或被迫调整的结果。这种调整由最初的步履维艰、痛苦挣扎,到逐渐习以为常、不足为怪,从而实现了人格姿态的重大转移。其结果是,知识分子的人格更加契合了时代的价值需求,也更加趋同于大众的、世俗的精神趣味。这似乎是知识分子在转型社会中寻找到的一种较为理想的人格姿态。这种姿态即如黄书泉所期许的那样:“也许,知识分子新的人生、新的人格只能产生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之中。这种新的人生和人格,既不是‘拒绝世俗’,也不是‘躲避崇高’,既不是对终极价值的虚设,也不是解构一切,而是让飞扬律动的生命过上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真实的生活。”(注:黄书泉:《喜剧时代的悲剧人生》,《小说评论》1998年第3期。)但问题在于,当知识分子自愿或不自愿、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价值取向、人格姿态上趋向于社会时尚、世俗需求时,虽然他们的灵魂已趋于平静,内心不再有价值冲动或价值迷惘,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忧虑、思考,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对于理想境界的探索及由此而来的痛苦,这些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派生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良知禀赋,真的就会随着人格姿态向现实世俗世界的倾斜而永远丧失殆尽吗?也许,面对商业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新的价值体系的确立,人们完全可以将知识分子的这种人格姿态的选择,视为新的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的一种明智之举——既然社会已形成追求物质利益与感官快乐(顶多也就是浅层次的精神享受)的时代风尚,知识分子又何必守着良知,与寂寞、孤独为伴呢?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所尊奉的这种人格姿态,难道不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的精神指向吗?人性的可变性虽然与具体的社会环境直接相关,但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精神财富的承载者,其知识结构中所包蕴的众多人类有史以来的精神文化的承传,必然要对其现实的个性意识倾向发生影响。这样,知识分子的现实人格姿态如何,事实上便是由其内在精神结构中传统文化价值质素与现实社会价值质素的互为作用的结果所决定的。至于知识分子应有怎样一种人格姿态和社会角色地位,是保持精英精神,还是融入世俗社会,抑或二者兼备,则取决于在什么立场上来看待这一问题。
从传统文化立场上看,A君、李岑们的走向世俗,无疑不再具备知识分子的独立文化人格;而从现代商业社会的角度看,他们显然又是具备了以自身拥有的文化资本去获取社会地位的能力,虽然不再具有独立的文化人格,但却有了独立的人格自由。不同立场、不同时代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姿态会有不同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不存在相对稳定的内容。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他可以在现实中有自己的偏于精英或偏于世俗的人格姿态,但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而言,知识分子理应对历史、社会、人类的现实生存状况保持一种审视、反省和思考的状态,理应在现实的社会行为中体现出必要的道德良知。否则,在人们受技术主义和物质主义潮流裹挟而身不由己地茫然前进时,谁来洞悉和把握社会发展是否偏离了健全人性需要的轨道?更具体地说,谁来指出和预示社会发展趋向中那些正在或有可能危害人类自身利益的种种因素,并给出消除或预防这些因素的措施与方案呢?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人格姿态不论怎样变化,都不能丧失这个群体在社会中所应保持的基本角色定位。失去了这种定位也就失去了作为这个群体的基本特征。从人性的角度而言,知识分子所应有的人格姿态则可视为这一群体相对稳定的人性内质,表现出这一群体基本的独特的人格风貌。作家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描写,通常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中,以这一基本的特征作为显在或隐在的参照,从而勾画出种种不同人格姿态的人物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