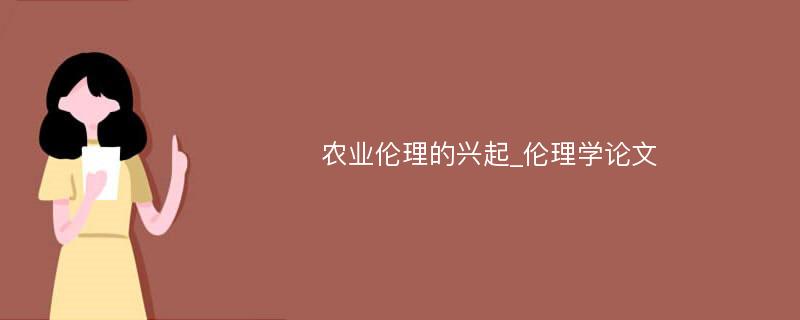
农业伦理学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业是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产业部门,以土地资源为生产对象的部门,通过培育动植物生产食品及工业原料的产业。农业属于第一产业。利用土地资源进行种植的活动部门是种植业,利用土地空间进行水产养殖的是水产业,又叫渔业,利用土地资源培育采伐林木的部门,是林业,利用土地资源培育或者直接利用草地发展畜牧的是牧业,对这些产品进行小规模加工或者制作的是副业。对这些景观或者所在地域资源进行开发展出的是观光业,又称休闲农业。 哲学主要探讨人类的知和行。伦理学是道德的哲学研究(概念分析、论证),道德是人类行动的社会规范,在历史上人类行动规范是根据权威人物或经典典籍规定的,往往无需辩护或论证。伦理学要用例如概念分析、价值权衡、论证等理性的方法研究人类行动规范。人的行动有三要素:行动者、行动和行动后果。主要的伦理学理论是后果论和义务论,这两种理论是人们在伦理推理中不可或缺的,人们不能不考虑行动后果,也不能考虑基本的义务。它们各自有其优缺点。为弥补它们的缺点,哲学家为设法把它们结合起来做出不懈的努力,例如规则效用论和效用义务论的产生。人们根据实践经验,参照主要理论,形成了一些伦理原则,构成评价人的行动或决策的伦理框架,例如在生命伦理学中的不伤害、有益、尊重和公正等原则。由于伦理学是规范性学科,必须考虑价值,单靠观察实验不行,因为从“是”中推不出“应该”,二者之间无逻辑通路,所以主要靠论证、反论证、概念分析、价值权衡、反思平衡、思想实验、判例法等。 农业伦理学有无必要和可能?那就要看农业有没有伦理问题,包括应该做什么的实质伦理问题和应该如何做的程序伦理问题。如果我们仔细读一下2014年中央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2014),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伦理问题。农业中的伦理问题可包括例如与食品(粮食)保障、食品安全有关的伦理问题,与对待动物有关的伦理问题,与环境安全有关的伦理问题,与可持续性有关的伦理问题,与代际伦理有关的问题,与三农政策有关的伦理问题。 为什么农业伦理学似乎有些滞后?农业中伦理问题非常之多,对这些伦理问题的解决往往有多种选项,我们必须做出合乎伦理的选择,但很少主动对我们的行动从事伦理分析,或能够提供我们所做选择的伦理学理由。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没有去注意发展农业伦理学?从事农业的人往往认为从事农业本身就是合乎道德的。他们没有认识到:伦理难题会不断产生,而不存在一劳永逸地解决伦理问题的情况。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例如从战胜自然转变到与自然建立和谐关系);新技术的应用往往会产生没有预料的后果(如DDT、绿色革命、基因技术);新观念进入人心,如善待动物、保护自然环境这些观念现在已日益深入人心。 农业伦理学为谁而设?为从事农业的专业人员而设。专业与一般的职业不同,职业为谋生计,专业是系统知识,现代农业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专业人员有社会责任。我国前现代医学大家非常明确地将医学看作专业。如李杲(1180-1251)说:“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李时珍(1518-1593)说:“医本仁术。”徐大椿(1693-1771)说:“救人心,做不得谋生计。”赵学敏(1719-1805)说:“医本期以济世。”形成专业的要素有:具有独特的系统知识作为知识基础,这种知识在大学获得认可;获得这种知识和技能需要较长时期专业化的教育和训练;不是仅为自己谋生,而是应社会需要为他人服务,与它服务的人形成特殊关系;服务于社会和人类,有重要贡献,因而声誉卓著;有自己的标准和伦理准则,有自主性(包括自律); 专业人员的形成和壮大是文明礼会的标志、中产阶级的主体、社会的中坚。 在国际上我们看到农业伦理学已经得到学界重视,出版了一些优秀的农业伦理学论文和著作,农业伦理学的名称也多种多样,如agriculture ethics,agricultural ethics,ethics of agriculture,agricultural bioethics等。 农业是社会和国家基础,也是其他部门的基础。“民以食为天。”同时,现代农业依赖工业、商业、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在历史上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这种两分法已经过时,重农抑商或重商抑农都不对。但如何平衡?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这涉及资源宏观分配公正问题,包括资源在农业与其他部门之间如何公正分配,以及在农业各个部门之间如何公正分配。 当代农业的基本伦理问题是,如何在养活90亿人口与为未来世代保存地球生产食品的能力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保持平衡?农业伦理学探讨的主要问题可有: 农业的意义/农业的模型/科学和技术在农业中应用的伦理学/与农业相关的食品伦理学/与农业相关的动物伦理学/与农业相关的环境伦理学。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探讨:农业的模型、科技在农业中应用的伦理学,以及与农业相关的食品伦理学问题。 一、农业的模型 农业已经超越温饱,而要为其他部门、其他地方,以致其他国家提供粮食。农业已成为生产性农业(production agriculture)。农业的作用是以最低的成本向消费者供应丰富的安全又富营养的食物。为实现此目标,农民不断采用新技术来增加生产,这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是农业唯一可能的前景吗?农民和消费者开始质疑一些技术,尤其是杀虫剂和基因工程作物,他们要知道它们是否符合人类健康、土地的守护,以及地球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生产主义(productionism)。在生产性农业中逐渐出现一种称为生产主义的倾向。生产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潮,认为生产是在伦理学上评价农业的唯一规范。在生产食物和纤维方面的成功,既是评价农业的必要条件,又是充分条件。生产主义的标准就是“生产越多总是越好”的原则,其口号是:“就是太多也不够”(Too much ain't enough)。然而,人们越来越对生产性农业提出了质疑。我们的农业系统高度依赖灌溉、单一作物和使用肥料、杀虫剂、除草剂、农用机械等,忽视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规律和稳定农业生态环境。我们的许多做法对环境有消极影响和严重的后果。除了生产我们对其他价值全然不予考虑。虽然生产是重要的目标,但我们面临的21世纪的挑战是要从生产性农业过渡到可持续性农业。这种过渡要求实质性的体制革新。 农业守护(stewardship)。人们试图用守护这个概念来补充生产主义。农民早就有守护土地、照料土壤、植物和动物的观念。大多数农民接受或原本承诺照料自然的责任。但对这一概念的伦理预设和价值需要进行批判评价。守护概念来自宗教,宗教要求人们有义务保护和促进上帝创造物的美和整体性。问题是这传统的农业守护的义务从属于生产,难以约束生产主义。守护概念应成为农业环境伦理学的一个成分。John Passmore(1914~2004)在1974年发表的《人对自然的责任》(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一书中论证说,迫切需要改变我们对环境的态度,人不应该继续无限制地剥削自然,但他反对抛弃西方的科学唯理论传统,反对深层生态学家对伦理框架的过激修正。按照他的看法,守护一方面是人类关怀自然的责任,与人类有权剥削自然相对立;另一方面,守护虽反对剥削自然,但仍强调使用自然,与保存(preservation)相对立,保存要求为自然本身保存自然。(Passmore 1975)所以守护这个概念一方面虽然反对生产主义,但另一方面它并未充分承诺环境的价值。因此,这个朴素的守护概念需要立足在更为坚实的伦理原则基础之上,将它重建为普遍的伦理规范。 整体论(Holism)。有些学者提出,不能把生态系统视为其中个体或生命体存在或繁荣的工具,而是其本身拥有价值(内在价值)。对环境问题的探讨不能仅在于个体水平,而应在物种或群体的水平。James Lovelock(1919- )提出Gaia假说,强调整个地球是一个“有机体”或是一个“超级有机体”(superorganism),其中生物和无生命部分形成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和自我调节的系统,以希腊女神Gaia命名。因而仅仅依靠力学和化学来说明生物学是错误的。整体论也叫新活力论。(Lovelock 2000)创立生态中心或整体论伦理学的Aldo Leopold(1887-1948)的格言是:保存生命共同体(biotic community)的整合性、稳定性和美的事情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Leopold 1949)整体论的困难在于,按照整体论观点,农业要保存生命共同体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美,然而除了露天开矿和城镇化外,农业也许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中最具侵入和破坏性的,如果其完整性、稳定性和美要保存的是野性自然,那么就会不允许农民利用土地去从事作物和动物的生产。 可持续性作为指导概念的出现。1962年Rachel Carson(1907-1964)《寂静的春天》一书(Carson 2000)的出版是标志性事件,说明我们的农业做法对环境和我们健康有害,我们目前生产食物的方法是不可持续的。20世纪后半世纪,出现了一个不同的农业模型:可持续的和多功能的农业。所追求的不仅是低廉的食物,而是对土地的守护,农民和农场工人的健康,生物多样性,农村社区的价值,以及农业景观的价值。可持续性的规范意义在于,其目的是既要满足目前世代的需要,又不牺牲未来世代满足他们需要的能力;承认自然本身有价值,由此必然推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人类利益可为生态价值而牺牲;认为生态平衡是重要的,因为它具有为人类(包括未来世代)使用的工具价值。这种可持续性思想可减少农业与环境伦理学之间的紧张。对可持续性概念可提出以下问题:可持续的是什么?是农业所用资源,还是生态可持续性或Gaia自身?除了生态考虑外是否有社会的可持续性?农村社区结构的可持续性?当我们说我们要使农业可持续时我们指的什么意思?生产性农业是不可持续的,然而放弃它,目前影响到穷人和发展中国家的口粮。那里人口压力大,驱使维持生计的农民去开垦生态脆弱的地区。他们应该如何平衡短期需要(生产)与未来时代的长期需要?我们如何帮助他们和我们自己走向一个可持续的未来?发达国家农业可持续性可能也依赖于发展中国家增加食品生产,使得他们不再需要压低商品价格的农业实践。(Thompson 1996;Chrispeels & Mandoli 2003) 二、科学和技术在农业中应用的伦理学 农业中应用机械化和化学技术已经250年。现代农业基本上是一种技术活动。农业实践中的技术革新不断进行。农业革命不亚于工业革命。每当引进新技术,总是有得有失。我们应权衡利弊得失,政府的政策必须考虑:谁受益,谁受害,如何使受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如何使公民公平地享有科技带来的受益,而不能拿纳税人的钱资助科技研究应用后,仅让有钱人受益,要特别关注穷人、命运不济的人,对他们采取优惠或救助的政策;关注动物的福利,如何善待动物;关注环境所受污染和破坏,如何保护环境。 如何评价使用常规技术的农业?让我们将使用常规技术(农机、电气、化肥、杀虫剂、除草剂、杂交、人工授粉等)的现代农业、前现代农业(尚未利用化肥、农药)与有机农业(拒绝利用这些)之间加以比较,评价标准是它们如何对待人、饲养动物、自然环境,及其对各方的影响,那么结果会怎样呢? 对人:现代农业提高生产率,使农民和非农民大大受益。美国在1910年—1980年间产量增加300%,农民人数仅3%(美、德),但比其他人更富裕,文化也比较高。农药残留通过严格和有效管制可减少到不影响健康的程度。人民不愿意退回到前现代耕作方式,除非强迫。也不应该要求发展中国家也这样做。有些NGO谴责绿色革命是欠考虑的。有机农业在美国只有1%,欧洲4%,因此只是例外不是常规。有机农业成本高,营养并不见得更好。非洲许多农民是前现代的有机农业,生产力低,贫穷不堪。 对饲养动物:使用常规技术的现代农业对饲养动物在伦理学上非常糟糕。人们似乎认为人类对饲养动物的义务只是比驯化植物稍微多一些。虽然屠宰方式已经改进得比较人道一些,但其他方面饲养条件非常不人道,尤其是采取集中动物饲养法时;对饲养动物的福利不关心,没有专门的立法保护。 对环境:所有农业都损害自然环境。现代农业与前现代农业比较,前者造成化学污染,但其生产率高,耕地缩小,美国1920年以来耕地面积减少了50%。印度如果不进行绿色革命,耕地还需要增加3600万公顷。而《寂静的春天》之后,美国农民减少使用农药,改用降解快的农药,改用抗虫、抗杂草的种子,用GPS精确施肥,对环境的污染已有所减轻。现代农业与有机农业比较,由于有机农业产量低(一般低60%~70%),需要更多的耕地。如果欧洲靠有机农业养活,需要增加2800万公顷耕地。(Paarlberg 2009)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陆续涌现出一些新兴生物技术,重组DNA(GMO等)、标记辅助选择(MAS)、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纳米技术、合成生物学等。这些新兴的生物技术有一些特点,使得我们将它们应用于农业时需要注意。它们的特点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歧义性(ambiguity)和转化潜能(transformative potential)。(NCB 2012) 不确定性是不知道可能发生的种种后果如何或每一种后果发生的概率。当我们谈论风险或受益时这些后果是能够鉴定的,其概率是能够给出的。不确定性包括:技术应用后难以预测对健康和环境非意料之中的和不合意的后果;最难预测和控制的以及积累时间最长的是社会后果,即技术对人群内个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影响;除了非意料中的后果,还有不受控制使用的后果,包括双重使用(dual use),如合成病毒有助于研究病毒,但也可能被反社会或恐怖主义者恶意利用;不确定性还包括不知道什么不知道(unknown unknowns)。这种情况下风险分析是没有用的,甚至严重误导的;因为在做风险评估时我们知道风险后果发生的概率,但在不确定性时我们对后果发生的概率一无所知。不确定性说明我们不知道未来事态的真正决定因素,这些决定因素过于多样、复杂、相互依赖而无法把握,因而对未来事态不能完全知晓。这就严重限制我们有可能精确预测有关生物技术决定的正面和负面后果,以及限制我们控制这些后果的努力的有效性。这使引入这些技术于医学、工业和农业的政府感到决策、管理上有困难,尤其是在有累积效应、仅在时间较长后才显示出来(如氯氟烃、DDT等)的情况下。 歧义性是指对可能后果的意义、含义或重要性缺乏一致的意见,不管这些后果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歧义性说明,对生物技术的实践、产品和后果有着种种不同的且可能不相容的意义和价值。技术应用会有得有失,得失如何可得到辩护,失者如何得到补偿?对此意见不易达到一致。对新兴技术还容易产生扮演上帝角色(Playing God)的反对意见,如文特尔的合成生物、创造人与非人动物混合体、含人基因的动物等,认为这样做跨越了可接受的界线,但对这条界线在哪里,意见很不一致。对某一现象可有两种或更多不相容的意义,使得我们对生物技术的前景、实践或产品难以达到一致的理解或评价,从而做出得到各方支持的决策。在现代多元社会,不同社会集团有不同的利益和价值几乎不可避免,新兴的技术可将这些分歧极化。不认真对待歧义性,不过是转移了这种歧义的后果,歧义性会在其他方面表达出来。过分狭隘地基于证据的决策程序,而不考虑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层面,会使公众对科学意见和决策的不偏不倚性产生怀疑。例如欧洲最初20年支持引进GMC,引起公众反弹,就是由于在技术治理这一政治问题上过分夸大科学的作用。 转化潜能指的是新兴生物技术改变现存社会关系的能力,或创造先前不存在的或甚至不可想象的新能力和新机会。这些后果也许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或不是人们谋求的。新兴技术被称为颠覆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ies)。这种新技术与现存技术没有联系,但能产生新产品到市场,它们更便宜、更简单,使用更方便,或能开发以前不存在的新市场。对这种技术革新,我们关注其两个后果:其比现存技术更有效地完成其功能的能力;完成新技术出现前根本不可能的功能的能力。然而,转化潜能不仅是指达到一定目的时功能方面的优点(速度、成本和效率方面),而且是思维方式和实践可能性范围方面的革新,是建立一个全新的范式(paradigm)。 这些特点使得我们对新兴技术做出理性决策成为困难之事。如果我们不能确定新技术提供我们谋求的好处的概率,或者我们对应用后产生的是否是好处没有把握(还有可能产生哪些风险,风险多大,发生概率多大?对该技术的意义和价值的歧义等),我们如何做出应用它的决定? 这需要我们采取反思的进路(reflective approach),当我们思考新兴技术时,我们要思考我们如何思考它们。 基于这些特点,一些学者认为对应用这些新兴技术采取占先原则(proactionary principle)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强调干起来再说,时不等人,赶紧抢占制高点。占先原则是一种“无罪推定”政策,即在没有证据证明对健康和环境有害、对社会有负面影响时就不应限制它们的应用。人们认为这种原则适用于常规技术,对新兴技术不适用。对新兴技术应采取防范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该原则强调要有证据证明对健康和环境没有有害作用时才能进行研究和应用,这是“有罪推定”政策。然而如果我们不着手进行研究和试验,如何知道其对健康和环境的可能影响呢?因此对于新兴技术(基因、纳米、合成生物)的创新、研发、应用,采取“积极、审慎”的方针,“摸着石头过河”也许较为合适。 这里比较大的争论是转基因作物和食品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提出以下的伦理考虑:(1)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粮食或食品问题唯有靠转基因技术解决,可得证据证明它可能是重要的解决办法之一。(2)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尤其的累积效应需要证据,证据的获得需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随机对照试验,包括动物和人;经验不是证据,至少不是充分的证据,以传统医药为例,服用数千年的药物一直以为安全可靠,可是一作临床试验,发现既不安全,又不有效。(3)对环境的影响如何也需要证据,对照法本来就是农学家发明的,后来移植到医学,大放异彩,成为“黄金方法”,为什么我们不用它来获得可靠的证据呢?(4)标识是imperative(绝对至上命令),这是尊重消费者的选择,与安全性问题无关。即使GMF安全,有些人就是不愿意吃,我们不能强迫他们吃;而且你不标识,非转基因食品会自动标识。(5)要关注农民可能受的影响,不能任其利益受损,有人说,过去采用新技术,农民就是可能要破产的,然而过去对农民利益受损不作为,不能成为我们现在可以不考虑他们利益的辩护理由。(6)应该让其他利益攸关者(人文社科专家、社会组织、公众代表)与转基因的科学家、转基因公司(不包括外国公司)以及行政管理官员一起参与决策。对于主粮特别需要慎重,这有什么不对吗?毕竟没有一个国家主粮是转基因,争这个第一有必要吗?另一方面,我们对GMO应采取理性的态度,理性的态度要求“摆事实,讲道理”,如果证据证明我们的看法有误,就应该修正,这也是开放的态度。(Pence 2002) 三、与农业相关的食品伦理学 与食品相关的伦理关注有:食品保障(全球、国家和个体层次)、食品无保障、资源和技术的可持续性、食品安全、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壤和水的保护、转基因作物、生物燃料、食品浪费、农业—食品科学的研究资助和人才流失、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平等机会和全球贸易、利益攸关者的参与、知识产权制度、公平竞争、食品价格等待。其中有些问题与农业有关,有些则无关。 食品是伦理关注的焦点。这丝毫不令人奇怪,因为我们本身的存在依赖于安全的、有营养的食品的供应。目前世界食品或粮食的情况是,发达国家的多数人不仅有足够的东西吃,而且有许多选择,大概还吃得太多。但其他人,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东西吃,也没有那么多选择。我们周围的生态系统是地球上植物和动物生命之源,提供给我们一切东西:我们饮的水,吃的食物,以及穿衣、用品和木料等的纤维。到目前为止,食品产量还赶得上人口增长:1997年农业提供的人均食品比1961年增加了24%,尽管人口增长了89%。(EGE 2008) 处于第一优先地位以及在农业中应用任何技术必须坚持的指导原则是如下目标: (1)食品保障food security (2)食品安全food safety (3)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21世纪食品方面的挑战是要求从生产性农业过渡到农业可持续性。这要求实质性的体制创新。最近10年世界人口(13%)、全球收入(36%)、肉食消费量(牛肉14%、猪肉11%、鸡肉45%)的快速增加是需求增加的主要推动力。对付这一挑战基本上有以下选项:(1)增加耕种面积,这会进一步加大对剩余土地的压力,包括边缘土地和森林;(2)增加已开垦土地的生产能力,这是较为可持续的选项;(3)改善农业产品的分配,使它们在合适的时间用在合适的地方;(4)改变吃得太多的人的消费习惯,进行再分配;(5)大大减少食品浪费。据估计,食品浪费占食品生产的百分比,美国为30%~50%,日本为40%,英国为30%,荷兰为15%,每年浪费的食品,美国为2590万吨~5290万吨,日本为2000万吨,英国为670万吨,荷兰为300万吨。(EGE 2008)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家粮食局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生产的粮食中有35%被浪费;据有关专家估算,我国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食物约合2000亿元,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2014年10月19日新华网) 现代农业现在喂养60亿人,下一个世纪食品生产必须翻一番才能喂饱世界人口。过去40年全球粮食生产翻了一番,但增加了水、肥料、农药、新作物品种以及与绿色革命相关的其他技术的使用,世界人口增长使食品保障问题永远存在。 1.食品保障 最近50年全球收入增加7倍,人均收入增加3倍多,但财富分配不均。在1990s初,大约20%的世界人口,大多数在发达国家,收入占世界的80%,而最穷的20%人口收入只占1.4%。发达国家消费世界能源的70%,金属的75%,木材的85%和食品的60%。因此食品保障和可持续性是21世纪农业必须满足的特殊需要。农业在提供足够的食品给所有人的作用,以及需要保证公平可及食品资源,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2006年粮农组织关于食品保障政策的介绍,目前表征食品保障的主要概念是:(1)食品可得性(Food availability),足量具有合适质量的食品可得,由本国生产或输入(包括食品救济)供给;(2)食品可及性(Food access),为获得适宜的食品以供有营养的饮食,个人应拥有充足的资源;(3)食品的使用(Utilization),借助充足的饮食、洁净的水、卫生条件和医疗卫生,使用食品以达到营养安康的状态,各种生理需要得到满足;(4)食品的稳定性(Stability),为使食品有保障,人群、家庭或个人都必须时时刻刻有充足的食品,不因突然事件(经济或气候危机、季节性食品无保障)而中断。因此,当所有人一直都要在物质上、社会上和经济上可获得充足、安全和有营养的食品,以满足其饮食需要和食品偏好,过一个积极而健康的生活时,食品保障问题始终存在。 2.可持续性 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Brundtland提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可持续发展定义:发展要满足现在世代的需要,而不破坏未来世代满足他们自己需要的能力。(Thompson 1996;Chrispeels&Mandoli 2003)。食品生产的水平和环境的状态取决于土地利用的方式。目前,大约全球一半已经使用的土地是用于耕种和放牧的,这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农业将显著的、有害环境的氮和磷引入生态系统内。此外,大多数最好的土地已经用于农业,要增加土地利用必定是边缘土地,产量不可能高,且容易退化,因此必须利用科学技术来改进品种,使之耐旱耐盐。 3.范式转换:从食品保障到食品安全 由于以下问题,人们越来越担心食品的安全性:新出现的病原体,如引起疯牛病的朊病毒、SASS、禽流感、艾滋病、埃博拉等都与食品有关;世界范围内爆发食品引起的疾病;食品加工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奶粉、油、肉类等);食品生产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农药残留、重金属(与工业污染有关)、激素、抗生素、添加剂(与大规模饲养有关)。于是,食品安全和消费者权利成为食品政策的关键要素。农民和消费者也开始质疑技术,如作物的害虫控制和基因工程技术是否影响人体健康、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EGE 2008) 4.食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食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即评价食品领域行动或决策的伦理框架可建议如下: (1)食品权(right to food)是最基本人权 意义:每个人都拥有食用食品的权利,有了足够数量和一定质量的食品,人才能生存,才能健康,才能从事其他活动,才能履行社会的只能,才能有美好生活(wellbeing),才能有人的尊严。 含义:每个家庭、机构和国家都有义务使得每个成员都能拥有食用食品的权利。 (2)无伤害(Non-maleficence) 意义:在食品的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储存各环节都要防止危害健康和环境的因素侵入。 含义:个人、家庭、机构,尤其是食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储存各部门,以及政府有(问责的)责任防止食品引起的对人、动物健康和环境的伤害。 (3)知情选择(Informed choice) 意义:食品消费者有权获得有关他们食用的食品的信息,并根据自己的价值、文化和偏好做出自由的选择。 含义:将食品提供给消费者的部门以及政府有责任确保消费者能够做出知情选择(food consumers' empowerment)。 (4)分配公正(Distributive justice) 意义:食品在人群和个人之间的分配要平等、公平。基本食品的分配应按需要分配,对贫困人群要救援或救济;非基本的、奢侈食品可按购买力分配。 含义:负责分配食品的家庭、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政府有责任确保公民能在平等和公平的基础上享有食品权。 (5)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 意义:保护社会中最边缘、最贫困的人群,倡导机会均等,确保公平的国内和国际食品贸易。 含义:政府有义务对最边缘、最贫困的人群进行救援、救济和支持工作,消除国内食品贸易壁垒;各国有义务确保公平的国际食品贸易。 (6)代际公正(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意义:保护未来世代的利益,避免因目前世代的过分开发而使自然环境丧失生产食品的能力。可持续性概念包含代际公正原则。基于对公正的广泛理解,未来和过去世代对现在世代拥有权利要求,或现在世代对未来和过去世代负有义务。未来世代对现在世代有分配公正的要求,即如果代际发生利益冲突,公正的考虑要求现在世代有义务不去执行只为自己谋利而牺牲生活在未来的人的政策。 含义:政府有责任采取为了现在世代利益适当利用自然,同时应积极采取措施防止过度开发自然,破坏环境的政策,尤其在控制人口、生产结构的调整、脆弱环境的特殊保护、濒危动物的救援等方面。 (7)共济(Solidarity) 意义:人与人、社群与社群、国与国之间要互助团结。为了社群、社会和人类的利益,大家互相帮助,而不计较可能的回报。尤其在食品方面,食品富裕的家庭、社群、国家要帮助匮乏的家庭、社群和国家。 含义:各国政府建立食品救援、救济的机制,各国之间有义务通过国际组织或在各国之间进行食品方面的救援、救济工作。(Korthals 2004;EGE 2008) [收稿日期]2014-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