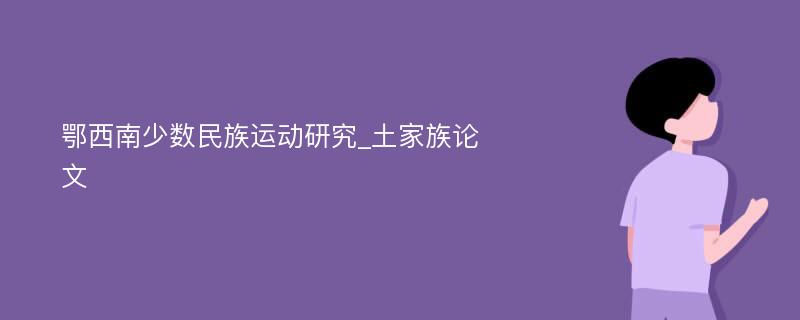
鄂西南族群流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族群论文,鄂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04)01-0057-06
鄂西南位于湖北省西南部,本文特指今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土家族自治县所在的广大区域。由于鄂西南位于祖国腹地,自古就是我国西南边疆地区通往中原的一条重要通道,承东接西,扼长江中上干流之咽喉,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同时它既是古代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的发祥之地,又是周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融汇之地,因而自古以来族群流动就十分频繁。鄂西南历史上的族群流动自先秦至今,按其时代特征大致可分为先秦时期、秦汉至唐宋时期、元明至清初时期、改土归流至清末时期、民国时期、社会主义时期等6个大的历史阶段。长期和频繁的族群流动,对鄂西南地区的民族形成、发展,以及民族结构、民族分布和民族关系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历史影响。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鄂西南地区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有利于人们认识该地区的民族结构、民族分布和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状。
一、历史阶段
1.先秦时期。这一时期鄂西南族群流动十分频繁,其中以土家族、苗族先民早期的大迁徙为主,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迁徙途径多样,其中以沿清江、酉水、长江等河流通道自东向西迁徙为主,族群互动格局初步形成。
鄂西南历史上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族群流动是巴人的西迁和南移。据《世本》、《后汉书》记载,居于武落钟离山赤黑二穴的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五个部落,通过掷剑和赛土船决胜负的方式,推举廪君为五姓部落联盟首领。其后,他们在廪君率领下,沿夷水(今清江)西迁,战胜盐水女神后,称君夷城(今长阳渔峡口,一说今恩施)。廪君立城之后,其后裔溯清江而上,一部分巴人经五峰、鹤峰、巴东、建始、恩施而至利川;一部分则留居在恩施,并陆续向西部和南部流动,即沿忠建河,经宣恩,至来凤、咸丰等地,布满清江、酉水及巫山余脉。约春秋战国时期,起源于长阳资丘容米峒的容米部落(清江南岸),又溯清江西上,沿支锁河,进入鹤峰溇水流域。
巴人以鄂西南为根据地,向川东南、湘西北发展,逐步遍及湘鄂川黔毗邻地区。关于巴人西进入川的路线,李绍明先生认为,巴人在鄂西壮大后,可通过两径入川:一途为自鄂西沿长江上溯,经奉节、云阳、忠县、丰都而达到涪陵;另一途为自恩施南下至宣恩、咸丰,沿阿蓬江而自黔江、酉阳顺乌江至彭水而达涪陵。[1]巴人由鄂西南进入湘西北的路线亦有两途:一途为沿忠建河,经宣恩、来凤至龙山;另一途为自鹤峰沿溇水至桑植。迁徙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鄂西南有巴人之日起,或稍晚一些,湘西北便有巴人进入,是自愿的,即自然扩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在春秋战国年代,由于北方与中原族类的强大,如秦人楚人,他们被逼着更大量的,也比较匆遽的,向湘西北推进。
鄂西南的巴人在势力强大时还向东、北两个方向扩张,其活动地域一度延伸到整个清江流域和峡江地区。
由此可见,巴人在鄂西南的大迁徙以溯夷水(今清江)西上为主线,以沿忠建河、支锁河南移为支线。其活动地域从清江流域逐步延伸到酉水流域、溇水流域和唐崖河流域和峡江地区并由此遍及川东南、湘西北和黔东北地区。
继巴人西迁之后,部分“三苗”遗众陆续迁入鄂西南地区。炎黄战胜蚩尤后,九黎部落部分退回南方,建立“三苗”部落,主要活动于江淮、荆州一带。夏禹时,“三苗”战败,其遗众一部分留居江汉,后逐步融合于华夏族;大部分继续迁于湘西沅江流域、黔东南清水江流域和鄂西南的酉水流域。其中迁入鄂西南的一支苗族先民与土家族先民巴人相互杂居,被统称或混称为“南夷”或“南蛮”。由于这支苗族人数较少,且受土家族文化的包围和涵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多数已融入土家族之中,但仍有一部分居处深菁、与土家寨相对孤隔的苗族一直延续至今。这部分苗族主要居住在五溪之一的酉溪发源地——宣恩县的椿木营区和沙道区,以苏、黄、李、张四姓为主。显然,三苗遗众西迁主要是因为战争原因,迁徙路线是从江汉平原至湘西,再沿酉水进入鄂西南,但并未像巴人那样遍及整个鄂西南地区,而局限在酉水流域的部分地方。
此后,部分濮人又陆续迁入鄂西南地区。濮人是商周时期属于“南蛮”系统的土著民族。商时,濮在“商之正南”;[2]西周时,濮为“周之南土”;[3]春秋时,“濮在楚之西南”。[4]由于楚在江汉地区的崛起。早期濮人与巴人受楚攻逼,故从周代到春秋战国,濮人大批向西南迁徙。其中一支向湖南沅水、酉水一带流动,后逐步遍及湘西、鄂西南、川东南、黔东北等巴人地区。考古材料证实,恩施自治州境内的悬棺遗迹多达40余处,集中分布在三峡地区、清江流域。其时代最早者在战国时期,迟者在唐宋以后,其族属多为濮僚族系。这说明濮人迁入鄂西南的路线基本上跟“三苗”遗裔的一致,即自江汉平原经湘西沿酉水西进,所不同的是他们还从酉水流域进入了清江流域和峡江流域,形成了和巴人大致相同的活动地域。定居于鄂西南地区的濮人长期与巴人相互杂处,彼此交往,相互影响,其中大部分融入土家族之中,成为鄂西南土家族的早期先民之一。
此外。这一时期巴国和蜀、楚、秦等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也导致了一些小规模或短暂的族群流动。如巴国进犯蜀国时,蜀王为了平息战事,“结好饮宴,以税五千人,遣巴蜀廪君”,[5]故建平信陵县有税氏,其迁徙路线应是沿长江东进,迁徙范围仅限于今巴东县境。公元前361年,巴人原据有的汉中、巫、黔中等地,都被楚占据。公元前316年,秦又夺取被楚占据的巴人故地—一黔中、巫等地。公元前276年,楚以重兵反攻秦军,又夺回秦置黔中郡,直到公元前223年,秦灭楚,该地遂为秦占据。秦人和楚人对巴国疆域的反复争夺,加速了鄂西南地区族群流动。
2.秦汉至唐宋时期。这一时期,鄂西南的族群流动由先秦时期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转为小规模的移民活动,处于相对平缓的态势。
秦灭巴后,定居于鄂西南的巴人,虽然经历了历代王朝更迭和战争变乱,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大的迁徙,一直比较稳定地生活于这一地区,繁衍生息,绵延不绝。尽管如此,一些小规模的移民活动仍然时断时续,时强时弱。东汉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南郡潳山蛮”雷迁等巴人反抗东汉王朝的统治,东汉王朝派刘尚率军镇压,并将7000多人迁往鄂东江夏(东汉郡治在今云梦县东南)一带,[6]被称为“沔中蛮”。由于鄂西南和湘西北的巴人相互往来频繁,因而既有鄂西南的巴人迁徙至湘西北,也有湘西北的巴人回流至鄂西南。据同治《咸丰县志·氏族志》载:“……又永乐二里,有覃氏,自湖南澧州来,当与安毛、耳毛之后,别为一支。澧州今慈利县,即古溇中地,澧州之覃氏,当为儿健之族裔。按覃氏谱:有伯圭、伯坚二人为覃氏最初分支之鼻祖,湖南、湖北覃氏,各祖其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促进了鄂西南地区的族群流动。东晋司马睿南迁以后,南郡、巴东等地已成为军事重镇,部分汉族陆续迁入鄂西南地区,与土家族彼此交往,相互影响。唐宋时期,鄂西南地区的施州及边地出现土汉杂处地区,使该区受汉文化的影响较之他处更大,土人中有人能用汉文著作。宋代,施州地广人稀,人口严重缺乏。当时施州的羁縻州官为了增加人口,采取了招人垦荒和掠夺人口的措施。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施州富豪之家诱客举室迁徙。宋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施黔等州就掠去700余户。[7]但由于宋王朝采取了阻止逃移、赎买或武力夺回人口的相应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族群流动的规模,从而未形成大规模的族群流动。
3.元明至清初时期。这一时期,鄂西南的族群流动十分频繁,且规模较大,形成鄂西南自先秦以来的第二次族群流动浪潮。这一时期大规模的族群流动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的族群流动。这一时期,鄂西南及其周边地区的战事十分频繁,既有朝廷对少数民族地方的武力征服,也有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武装反叛;既有各民族的农民起义,也有朝廷官兵和各少数民族军队相互参与的血腥镇压;既有各土司相互之间的势力扩张,也有地方割据势力对这一地区的武力争夺,还有东南部沿海的抗倭斗争。频繁的战事,促进了鄂西南和周边地区之间的族群互动。一方面,朝廷为了征服鄂西南地区,并实施有效的军事控制,平息诸土司的反叛,先后调派大批军队进驻鄂西南。另一方面,鄂西南诸土司的土兵或被朝廷频繁征调,以平息周边及沿海战事,或与周边土司进行武力争夺,从而形成鄂西南地区和周边地区之间大规模的族群互动。因此,这一时期与战争有关的族群流动主要发生在土司地区。
朝廷对鄂西南地区的武力征服和对土家族首领反叛的武力镇压,以及对土司的军事威慑,导致大批蒙古、汉等族军队进驻鄂西南地区,形成了大规模的族群流动。元朝建立后不久,即派遣大批蒙古族、汉族军队对鄂西南土家族地区进行武力征服,直到至正二十一年(1284年),元王朝对鄂西南地区的统治才最终确立下来。鄂西南土家族首领归附元朝的同时,又伴随着反叛,因而元王朝不得不派遣部分蒙古族、汉族军队长期驻守该地区,以加强对该地区土司的监视和威慑。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元朝命时任夔路镇守副万户的大将军石抹按只“领诸翼蒙古、汉军三千人戍施州”平叛。[8]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七月又巴、散毛再次举行大规模的反抗,元世祖“赦荆湖、四川两省合兵讨又巴、散毛洞蛮”。[9]时任四川南道宣慰使之李忽兰吉,奉命与参政曲里吉里、佥省巴八、左丞汪惟正等合兵攻打,兵分四路,分别从黔中、思州、播州、澧州、夔门攻入又巴、散毛等地。“至元二十一年,(石抹狗狗)以蒙古军八百人从征散猫(即散毛)蛮,战于菜园坪、渗水溪,皆败之,壁守石寨一月余,散猫降,大盘诸蛮亦降。”[10]宣武将军、管军总管塔海贴木儿随行省曲里曲思帅师征讨,擒诸蛮首领,“杀其酋长头狗等”。[11]这说明元军从四川、贵州、湖南三面大规模进驻鄂西南,加剧了鄂西南土司地区的族群流动。明王朝为了限制和削弱鄂西南土家族土司的发展,防范和镇压土家族土司的反叛,于明初设立了施州卫与大田所,派驻了大量军队长期驻守鄂西南地区。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置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后并施州入卫。调整后的施州卫领左、中、右三千户。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置大田千户所,隶施州军民指挥使司。“命千户石山等领酉阳土兵一千五百人,置所大水田镇之。”[12]
相反,鄂西南的参加反叛的部分土司及土兵却被强行迁徙他处。“施南宣抚土官覃大胜作乱,凉国公蓝玉移兵讨之,擒大胜及其党羽男女八百二十人,械从京师。”[13]
朝廷频繁的征调活动和农民战争很大程度上加速了鄂西南和周边地区之间的族群互动。鄂西南各土司,接近祖国腹地,易于征调,故被征次数最多,尤以明代最为频繁,被征达20余次。有时征调部分土司,有时征调全部土司。被征的土兵,有时去镇压其他少数民族,有时去镇压农民起义,有时去防御外侮。鄂西南的土兵,常常被征调去镇压湖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地土司,而这些地区的土司又被调来镇压鄂西南诸土司,使鄂西南土家族地区和周边其他民族地区的族群互动十分频繁。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后,鄂西南土家族土司积极听从明朝政府的征调,参加到镇压李自成农民军的战斗中。唐崖十三、十四两世土司相继从征镇压农民军。十三世土司覃宗尧,调往荆州征剿“流寇身亡”;十四世土司覃宗禹又奉调去川东,以抵御张献忠进川。[14]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容美土司奉调征剿农民起义军,土司田玄派其子田霈霖、田既霖、田甘霖及属官唐邦镇、唐承祖、刘起沛等,率兵万人,征战于房县、竹山、光化、谷城、襄阳等地,并征调守荆州卫。[15]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至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容美宣抚使田九霄率土兵10000开赴东南抗倭前线,配合官兵肃清倭寇。
鄂西南土司的势力扩张活动和反叛斗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鄂西南和周边地区的族群流动。清初,鄂西南土司和周边土司之间的争斗劫掠比较频繁,多次将周边土司的土民劫掠至鄂西南地区。如容美土司曾掠桑植土民千余口;[16]“明如(即田旻如)请中峒司过境,奏会欢饮,密遣人往袭掠,所获民人,系以情麻索。”[17]又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田旻如“掠白崖、洗罗地方男妇百余人以归”。部分土司在反叛过程中,往往将斗争范围扩展至周边地区。“湖广龙潭安抚司土夷黄俊、黄忠等作乱,占据奉节、云、万三县土田,聚党千余,杀土夷居民以百计”。[18]
地方割据势力对鄂西南地区的争夺,也是加速鄂西南族群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明玉珍是元末农民领袖徐寿辉的部下,原在湖北地区活动,元代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由巫峡入川,乘机占领鄂西南地区,统治鄂西南地区达14年之久。清军入关以后,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在川东、鄂西之间活动,号称夔东十三家。农民起义军因攻荆州失败,转入施州卫,在此活动时间近20年。这些年地方割据势力大多没有直接进入土司地区,一般只局限于清江以北的非土司地区,与朝廷军队直接进入清江以南的土司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二,与朝廷移民政策密切相关的族群流动。明、清两朝相继实现了大规模的移民,以平衡各地区的人口分布,使汉族在元末至清初出现了两次大的迁徙活动:第一次是元末农民起义战争后,由于全国人口不平衡,朱元璋进行了大量的移民,史称“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一部分来自湖广、江西的移民迁入鄂西南清江以北地区。第二次是明末农民起义战争后,清王朝在康熙年间,将湖北的荆州、湖南洞庭湖地区的大批移民迁入鄂西南。其中多是汉族,但亦有部分少数民族,多迁到清江以北地区。道光《施南府志》载:“建始自明季寇乱,邑无居人十数年,迨康熙初年始就荡平,逃亡复业者十之一二,嗣是荆州、湖南、江西等处流民竞集。……户口较前奚啻十倍。”
第三,与政治避难、逃避镇压或自然灾害等多种原因相关的族群流动。南明政权建立后,包括夷陵相国文安之、黄太史、华容孙中丞、公安伍世部等在内的大批明朝遗臣即迁入鹤峰境内。田玄死后,其子霈霖、既霖、甘霖相继为容美司主,仍如其父招纳明朝士大夫,“公子王孙之流,避难容美,不可胜数。”[19]通过这些分散的移民,容美土司成为明朝公子王孙避难的世外桃园。
苗族、侗族在这一时期的迁徙活动也较为频繁。约元末明初,来自湘西的一支龙姓苗族因自然灾害从湘西迁入施南府建始大洪寨和巴东铜锣坪。其中迁到建始的这支龙姓苗族在明末农民起义战争爆发后,随南明帝迁云南数十年,后于清康熙年间回流至建始。清康雍年间,湘西、黔东北的部分苗族因战乱迁居鹤峰县的麻寮所。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大批侗族从湖南的沅州(今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贵州的玉屏(今玉屏侗族自治县)、广西的三江(今三江侗族自治县)因战乱或自然灾害陆续迁徙到鄂西南地区。恩施《杨氏族谱》记载着从恩施到新晃的路线,并记有75处“路引”。
但是,封建王朝为了限制土司势力扩张,在鄂西南与汉区交界的边地竖立“土汉疆界碑”,并以“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加以约束,极大地制约了鄂西南地区与周边汉族地区的族群互动,严重影响了土家族和汉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尽管如此,一些小规模的民族迁徙活动仍然时有发生。一是有部分来自汉区的农民和商人陆续迁徙到土司地区,其中许多汉族商人还变成了地主。如明末清初,在今来凤境内,便有汉族富豪购得土司地又转租数百汉民,成为地主、巨商。二是一些汉区的名儒相继迁徙到容美、施南、卯洞诸土司及巴东等地,立县学,兴书院,传播汉文化,从而诞生了一批对汉文化有造诣的土司、土官。
4.改土归流至清末时期。这一时期,以大量土司被强迫外迁与汉族、苗族、侗族、蒙古族、白族、回族内迁形成的族群互动,形成了鄂西南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族群流动高潮。这一时期的族群流动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清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改土归流后,原土司地区改由流官执政,大量招人开垦荒地,清王朝遂将湖南洞庭湖滨各县、沅州、辰州,贵州东北、北部及四川边沿地区的大批移民陆续迁入鄂西南。这次移民大部分是少数民族,主要迁到清江以南地区。同治《来凤县志》载:“改土后民人四集,山皆开垦”,甚至出现“无荒可开”的现象。与此同时,清政府将鄂西南诸土司改流后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东乡、忠建、施南等强行改流的调至孝感、汉阳等地安插;对容美土司及其属下中支持或反对改土的,根据不同情况作了不同的处理。田旻如自缢后,“置其妻子于陕西,置其党羽冒阍人于广东”,将呈请改流的15土司,调至孝感、汉阳、黄陂等地安插。如忠洞、忠孝、忠路、金洞、大旺、漫水、东流、卯洞、散毛、木册、百户等11个土司安插至孝感,将龙潭、高罗、沙溪、唐崖等4个土司安插至汉阳,将腊壁土司安插至黄陂。可见,改土归流后,汉族大量向鄂西南移居,一部分土家族人口也迁出原土司地区,形成汉族人口与土家族人口的不平衡对流。
第二,各民族自发的迁徙活动。这一时期,大批苗族、侗族、蒙古族、白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相继从湖南、贵州、广西等地继续北上,与西行的汉族汇聚于鄂西南地区,形成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改土归流至清末,湘西、黔东北苗族因起义失败遭到官兵镇压,大量迁入鄂西南,其中尤以清乾嘉年间为盛。此时,清政府对湘西和黔东北的苗族进行不断的镇压,其中以对苗族石柳邓起义的血腥镇压最为残酷。同时,清统治者又对苗族横征暴敛,征收军米钱粮,加之部分苗区发生自然灾害,致使大批苗族逃往鄂西南。从湘西逃往鄂西南的苗族大姓有宣恩小茅坡营的石、龙、冯,咸丰的陆姓,利川文斗的米、罗、杨姓;从黔东北迁来的苗族大姓有利川安家山的杨、周、王、刘、郭、高姓,三望庆的董、李姓,咸丰的白、杨姓。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7年),湖南澧州的一支蒙古族在其进山始祖部锡侯带领下,迁徙到鹤峰境内,后向恩施、利川等地流动,其中大部分居于今鹤峰县中营乡和北佳乡。清乾隆初年,今咸丰高乐镇水淹坨李氏和清坪区艾蒿坪、尖山区双河乡老李湾的马氏等回族,陆续从湖南常德迁徙而来。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湖南桑植部分的“民家人”(白族自称)陆续迁徙到鹤峰,以谷、王、钟三姓为主。
第三,与军事活动有关的族群流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石达开率太平军转战鄂西南,得到土家族、苗族、侗族和汉族人民的支持,形成了一次规模大、持续时间短的族群流动。
各民族大量迁入鄂西南地区,使该地区的户口和人口剧增。据统计,整个鄂西南地区自乾隆初年至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的90多年间,户口增长6.2倍,人口增长7.6倍。
5.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战乱不息,灾害频繁,各族迁徙相当频繁,并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一次民族迁徙的高潮。鄂西南的土家、苗、侗等族青年因求学而至武汉等都市,有的为了革命需要又返回鄂西南。土地革命时期,鄂西南同湘西的土家、苗、白等族群众随贺龙进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鄂西南大量的土家族、苗族、侗族青年随红军北上抗日,以后返回原籍的很少。抗日战争时期,北方诸省的满族为避难迁入建始的苗坪和细沙等地。武汉沦陷后,湖北省政府西迁恩施时,大量的汉族迁徙到鄂西南民族地区,随之迁徙的也有部分回、满、蒙古、侗等少数民族人口。与此同时,湖北各类学校也迁入鄂西南各县,大批汉族教师和学生随之迁入鄂西南地区,加之大批来自沦陷区的难民涌入,使恩施地区汉族人口剧增。仅以恩施城区为例,抗战前人口不过3000人,自武汉、宣昌沦陷后,至1940年6月,思施城区人口骤增至15万人。后虽有一部分陆续向西南后方迁徙,到1943年9月,恩施城区人口仍达79331人。[20]抗战结束后,虽然大部分人迁回原地,但仍有一部分人留在这里安家落户。
6.社会主义时期。解放后,鄂西南地区的族群流动更加频繁,以不间断的迁入迁出为其主要特征。解放初期,政府派出大批汉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到鄂西南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及土地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断有汉族知识分子到鄂西南从事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全国各地的人口流动。鄂西南地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除到附近的城镇务工外,还大量地到东南沿海等地打工,形成了大规模的“打工潮”。同时,大批汉族和少数民族因经商、求学、分配、婚配等多种原因,陆续迁入鄂西南地区,使该地区的族体剧增。随着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和水布垭水利枢纽工程的开工,鄂西南地区还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一部分被异地安置,一部分则就近安置。
二、历史影响
长期而频繁的族群流动,对鄂西南地区的民族形成、发展,以及民族结构、民族分布、民族关系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它对鄂西南地区的民族形成、发展有重要影响。巴人大规模的西迁和南移,对这一地区巴族和土家族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首先,它有利于巴族和土家族共同地域的形成。经过长期和频繁的大迁徙,巴人从其发源地长阳进入整个鄂西南地区,并通过继续西迁和南移,逐渐遍及川东南、湘西北、黔东北地区,从而形成了以湘鄂川黔交界地区为主体的共同地域,奠定了土家族共同地域的基本格局,为巴族和土家族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它有利于巴族和土家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形成。在西迁途中,盐水女神留廪君共居盐城,但廪君却射杀盐水女神,坚持西行,并称“我当为君,求廪地,不能止也。”[21]廪,《说文》注曰:“谷所振入也”。段玉裁曰:“谷者,百谷总名。中庸注曰:振,犹收也。周礼注曰:米藏曰廪”。因此,巴人西迁的主要目的在于“求廪地”,即寻求适合农业耕作的土地,反映了巴人的经济生活已逐步从渔猎向原始农业的过渡。这次举族大迁徙,无疑适应了巴人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需求,奠定了巴族和土家族农耕兼事渔猎采集的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由于巴人有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因而逐步形成了共同语言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之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最终形成了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巴族,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融合当地其他部落、民族和迁入该地区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形成了一个新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土家族。因此,巴人的西迁和南移不仅直接促进了巴族的形成,而且对土家族的形成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陆续迁入鄂西南地区,对土家族的发展壮大有直接影响。土家族在形成之后又逐步吸收了迁入该地的部分蒙古族、苗族和汉族,逐渐发展壮大。如元代贴木乃耳率领的一支蒙古族军队在镇压散毛叛乱之后,长期驻守于今咸丰唐崖一带,建立了唐崖军民千户所,在当地土著覃氏的长期包围与涵化之下。逐步被当地土著覃氏所融合,形成了唐崖覃氏,建立了唐崖土司,至今在其族谱、民间传说、民间信仰及风俗习惯中还不同程度地保存了蒙古族的痕迹。[22]此外,迁入鄂西南的部分汉、苗等族在同土家族的长期交往中,亦逐步融合到土家族之中,促进了土家族的发展壮大。
鄂西南的族群流动同样促进了该地区苗族的形成和发展。先秦时期迁入鄂西南酉水流域的部分“三苗”遗裔,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形成了该地区最古老的苗族,其中小部分延续至今,即前文所说自称“老苗子”的苏、李、黄、张四姓。由于他们人数少,且长期处于土家族的包围和涵化之中,族体发展缓慢,直到明清以后从湘西、黔东北迁入了大量的苗族之后,鄂西南地区的苗族人口才迅速增加,族体日益发展壮大,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体民族之一。
另一方面,它又延缓了该地区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如改土归流后,鄂西南地区的大量土司、土官被强行迁往外地安插,不仅使该地区土家族的人口剧减,而且使土家族文化的传承、发展的链条一度中断,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土家族的发展壮大。
2.它对鄂西南地区的民族结构有重要影响。鄂西南地区的民族结构随着该地区族群流动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呈现出逐渐多元化的历史趋势。该地区的民族结构中除汉族、土家族、苗族等主体民族外,还包括其他20多个少数民族。这种民族结构是在长期而频繁的族群流动中逐步形成的。
考古资料证实,鄂西南地区是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距今约一二百万年前属于人科的“南猿”,已在鄂西南的建始、巴东一带生活;距今约10万年前的“长阳人”,生息于鄂西南的古夷水(今清江)一带,但其族属至今尚未判明。新石器时代,鄂西南地区的东北角相继为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所叠压,但其族属目前尚难断定。这说明在巴人迁入鄂西南地区之前,该地区已生活着一些族属未定的古人类。巴人从长阳迁徙到整个鄂西南地区后,逐渐发展壮大,成为该地区的统治民族,从而形成了以巴人为主体,包括部分土著部落的民族结构。随着“三苗”遗裔、濮人及少量汉人迁入鄂西南,该地区的民族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族体结构中增加了“三苗”遗裔、濮人、汉族,但仍以巴人为主体。秦汉以后,汉族陆续迁入鄂西南,经过明初、清初、乾隆年间和抗日战争等多次大迁徙,人口逐渐增加,成为人数最多的主体民族,从根本上改变了该地区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人口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人口结构。明清以后、湘西、黔东北的大批苗族迁入鄂西南地区,使该地区的苗族人口剧增,从而使苗族成为该地区的主体民族之一,其人口仅次于汉族和土家族,位居第三,进一步改变了该地区的民族人口结构。清代以后,陆续迁入鄂西南的侗、蒙古、白、回等少数民族,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该地区的民族成分结构,而且更进一步改变了该地区的民族人口结构,经过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延续和发展,最终奠定了鄂西南地区民族结构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以汉族、土家族、苗族为主体,包括20多个少数民族的多元性民族结构。
3.它对鄂西南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具有重要影响。鄂西南地区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是在长期而频繁的族群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
先秦时期,鄂西南的民族分布格局由最初的巴人与土著部落共居,逐步演变为巴人、“三苗”遗裔、濮人等相互杂居,其中各部族又有相对独立的聚居区。秦汉至唐宋时期,随着部分汉族陆续迁入,先秦时期的民族分布格局开始发生渐变,在施州及清江以北的边地已出现土汉杂居区,清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仍为巴人及后裔土家族、苗族的聚居区。元明至清初时期,清江流域以南为土司地区,杂居着部分来自周边地区的汉、苗、侗等族,出现了多民族杂居的格局,但仍为土家族聚居区;大批蒙古、汉等族军队征服鄂西南土司地区后,在原土司地区设立了施州卫和大田军民千户所,长期驻守于此,形成相对独立的卫所地区;在清江以北的部分地区,大批汉族移民相继在此安家落户,形成一定范围的汉族地区。改土归流至清末,随着大批土司迁出鄂西南土司地区,大量汉、苗、侗、蒙古、回等族迁入土司地区,原土司地区、卫所地区和汉族地区之间的界限被彻底打破,族群互动频繁,逐步形成了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经过民国时期和解放后的多次族群流动,这种分布格局逐渐稳固。
4.它对鄂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具有重要影响。野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随着该地区的族群流动变化而不断发展演变,呈现出由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发展的历史规律。
先秦时期,鄂西南地区频繁的族群流动,以及当时周边地区诸侯国林立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当时鄂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巴人进入整个鄂西南地区后,逐渐成为当地的统治民族,与稍后迁入的“三苗”遗裔、濮人等,形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使后者逐渐融合到前者之中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同时由于巴人不断西迁和南移,遍及湘鄂川黔毗邻地区,族体不断发展,势力日渐壮大,建立了颇具实力的巴国,成为当时诸侯国中重要的一员,因而与中原王朝及楚、蜀等邻国接触频繁,势力互为消长,初与楚、蜀相争,时战时和,继为楚所败,后为秦所败,终为秦郡县之编民,进一步沟通了和中原华夏先民的联系。
秦汉至唐宋时期,鄂西南的族群流动相对平缓,民族关系远不及先秦那样错综复杂。但一些小规模的移民仍对当时的民族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一方面,中央王朝相继在此设立郡县和羁縻州县,促使一批汉族官员和军队进入该地区,并与土家族相互杂居,相互影响,促进了土家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使汉族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传播到土家族中,故宋代时施州土家族受汉文化的影响较之他处更大,并出现了一些对汉文化有造诣的土家族文人。正因为如此,一直比较稳定地生活于该地区的巴人,才能够在吸收部分汉族文化的基础上于宋代形成土家族。另一方面,宋代,各羁縻州采取从汉区招人垦荒、掠夺人口等办法,增加该地区的劳动力,但朝廷相应地采取了阻止逃移、赎回或武力夺回的措施,这种族群流动加剧了各羁縻州与朝廷之间的矛盾,使羁縻州与朝廷的关系在整体上既相互利用,又有矛盾。
元明至清初时期,频繁的族群流动使鄂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土家族与蒙古族、汉族、满族等统治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有土家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还有鄂西南境内土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土家族内部的关系。一方面,与朝廷对鄂西南地区的武力征服、镇压和征调有关的族群流动,加剧了鄂西南土家族与统治民族及其周边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对抗。每当朝代更替,朝廷便派军队征服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从而形成土家族与蒙古族、汉族、满族等统治民族之间的对立关系,反叛与镇压便随之而来。明代从鄂西南周边地区调集大量汉族、土家族军队进驻鄂西南地区,并在此设立施州卫和大田所,以加强对诸土司的军事威慑和镇压,形成土司和卫所两大对立的阵营。朝廷征调鄂西南的土兵,以镇压周边地区的土司起义,又以周边土司镇压鄂西南土司起义,从而加深了鄂西南土家族和周边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与朝廷移民或政治避难、逃避镇压及自然灾害有关的族群流动,又促进鄂西南土家族与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对土家族的经济、文化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密切了民族关系。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对汉文化有较深造诣的土司、土官,涌现了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的“田氏诗人群”,反映了土家族已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在鄂西南接近汉区的边地,出现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萌芽,反映了土家族已受到汉族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影响。同时,土家族的传统文化对迁入该地区的各民族亦有积极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互动。
改土归流后,鄂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出现了新的格局。首先,土司这一特权阶层被彻底废除,并被大量强行迁往外地安插,使原土司地区土司与土民及其他民族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从此消失,改变了土司时期鄂西南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其次,“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民族隔离政策被彻底废除,形成了鄂西南内部及其与周边地区之间大规模的族群互动,打破了过去的地域界限,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交往。一方面,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土家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影响日益加深。在政治制度上,鄂西南土家族地区的土司制度被流官制度所取代;在经济上,鄂西南各族人民的封建领主制经济被汉族的封建地主制经济所取代,逐渐接受从汉区带来的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在文化上,鄂西南各少数民族(尤其是土家族)的传统文化发生深刻的变迁,汉文化的影响日渐加深。如土家族逐步接受了汉族的语言、文字、服饰、伦理道德等,本民族传统文化中渗透了大量的汉文化因子。另一方面,鄂西南土家族的传统文化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交融。经过长期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各族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个突出的现象便是土家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之间由松散的地缘关系演变为密切的血缘关系,彼此通婚现象日益增多,民族家庭开始形成。但是,各族人民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依然存在,有时甚至愈演愈烈,形成各族人民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斗争。民国时期的族群流动对鄂西南民族关系也有重要影响。一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为各族人民团结、合作、友好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大批汉族迁入恩施地区,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为各族人民之间广泛的文化交流和经济交往提供了一次历史机遇。
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汉族干部和知识分子进入鄂西南地区,帮助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建立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鄂西南各族人民则在更加频繁的族群流动中,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更加巩固。
综上所述,鄂西南历史上长期而频繁的族群流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每个阶段皆有各自不同的时代特征。这些长期而频繁的族群流动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它不仅影响了该地区土家族、苗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逐步形成了该地区以汉族、土家族、苗族为主体,包括侗族、蒙古族、白族、回族等20多个少数民族在内的民族结构,而且逐步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最终形成了各族人民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收稿日期:2003-0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