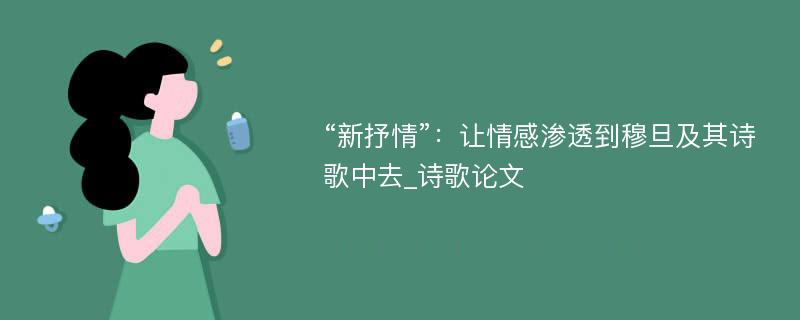
“新的抒情”:让情感渗透智力——论穆旦和他的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他论文,的诗论文,抒情论文,智力论文,情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9)01-0136-07
抒情传统的再认
20世纪30年代一些现代诗人对诗歌本质的强调和对抒情传统的疏离,曾被穆旦准确地理解为主观抒情成分的隐退和对智力的倚重,在1940年写的《〈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这篇书评中,他写道:“在二十世纪的英美诗坛上,自从艾略特所带来的,一阵十七十八世纪的风掠过以后,仿佛以机智来写诗的风气就特别流行起来。脑神经的运用代替了血液的激荡,拜仑和雪莱的诗今日不但没有人摹仿着写,而且没有人再以他们的诗作鉴赏的标准了。这一个变动并非偶然,它是有着英美的社会背景做基地的。我们知道,在英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中,诗人们是不得不抱怨他们所处在的土壤的贫瘠的,因为不平衡的社会发展,物质享受的疯狂的激进,已经逼使得那些中产阶级掉进一个没有精神理想的深渊里了。在这种情形下,诗人们没有什么可以加速自己血液的激荡,自然不得不以锋利的机智,在一片“荒原”上苦苦地垦殖。把同样的种子移植到中国来,第一个值得提起的,自然是《鱼目集》的作者卞之琳先生。《鱼目集》第一辑和第五辑里的有些诗,无疑地,是新诗短短路程上立了一块碑石。自五四以来的抒情成分,到《鱼目集》作者的手下才真正地消失了,因为我们所生活着的土地本不是草长花开的原野,而是: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①穆旦明确指出了卞之琳的《鱼目集》与重视知性的英美现代派诗的关系:它们都是从牧歌式的抒情走向“荒原”上的垦殖,而在诗歌的特点上则呈现为抒情成分的消失。在这里,需要首先分辨的,是徐迟在1937年也曾提出“抒情的放逐”这一主张。这一点,穆旦在文章中也触及到了:“从《鱼目集》中多数的诗行看来,我们可以说,假如‘抒情’就等于‘牧歌情绪’加‘自然风景’,那么诗人卞之琳是早在徐迟先生提出口号以前就把抒情放逐了。这是值得注意的:《鱼目集》中没有抒情的诗行是写作在1931年和1935年之间,在日人临境国内无办法的年代里。如果放逐抒情在当时是最忠实的生活的表现,那么现在,随了生活的丰富,我们就该有更多的东西。……为了使诗和这个时代成为一个热情的大和谐,我们需要‘新的抒情’!……强烈的律动,洪大的节奏,欢快的调子,——新生的中国是如此,‘新的抒情’也该如此。”徐迟提出“抒情的放逐”与穆旦提出“新的抒情”都基于民族抗战的共同语境。表面上看,徐迟援引艾略特关于诗歌的客观性,即诗歌不是表现感情而是逃避感情的观点,也是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诗歌的发展;而穆旦面对卞之琳消失了抒情成分的诗,主张“新的抒情”,是从现代主义后撤。实际的情形却正好相反:徐迟所指的“抒情”是30年代戴望舒、何其芳式的面向个人记忆和幻想的抒情诗,认为它们不过是披着“风雅”外套的“闲适者的玩意儿”,中国的诗只有“放逐感情”,接纳大时代的现实生活才有出路,——这其实是一种走出感情和想象的世界,反映现实和面向大众写作的诗歌观点,与艾略特的诗观完全是南辕北辙,倒是更接近五四平民化的写实主义文学主张。而穆旦提出“新的抒情”,却不否定“抒情”本身的意义,只是反对“牧歌情绪”加“自然风景”的旧式抒情;他并不认为“放逐感情”就是诗的本质,他把英美的现代诗和受英美现代诗影响的卞之琳的知性写作,都看成是“荒原”上的垦殖,一方面认为它们“在当时是最忠实的生活表现”,另一方面,也希望诗与时代有“热情的大和谐”,——这里显然包含着反思和超越现代主义的渴望。
同样是面对民族抗战的现实中国语境,同样面对30年代的现代主义创作面貌,却有不同的评价,提出的方案也不同。这个不同既体现了对现代主义的不同认识,也表现了不同的诗歌立场。虽然同是寻求诗歌的现代性,但徐迟所持的现代性,是与社会现代化潮流相一致的“现代性”,而不是感觉和想象方式的现代感。因此他30年代的现代诗,尽管描写了摩天楼和握着网球拍子的城市青年,但并不能深入现代人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甚至直到80年代,他也仍然搞不清文学的现代性与社会现代化的区别,提出什么“文学也要现代化”。从根本上看,徐迟不过是一个始终跟随着时代不断改变自己的诗人,而不是有自己的现代诗学主张并一以贯之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在“新诗”史上,决非个别。而穆旦,虽然也从诗与时代的关系考虑问题,却无意用现在的时代语境否定过去的时代语境,尤其不愿以时代的要求否定诗歌的特点。他理解与同情英美的现代诗和30年代卞之琳们有着冷静与灰色调子的诗,他并不认为这些诗不好,只是指出,这样的诗不应该体制化,“随了生活的丰富,我们就该有更多的东西”。
穆旦提出“新的抒情”,包含着对非个人化的现代主义诗歌的深刻反思,触及到两个非常重要的诗学观念问题,这就是诗的情感与境界的问题。首先是,诗可以不可以完全置之于感情之外?这在王国维看来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情感态度是文学的“二原质”之一,他说:“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自一方面言之,则必吾人之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即客观的知识,实与主观的情感为反比例。自他方面言之,则激烈之情感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而观物与其描写之也,亦有无限之快乐伴之。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言文学之事。”②一般的文学尚且不能没有感情,就不用说诗是否可以逃避感情了。当然,诗歌无可避免的情感介入,却不意味着必须直接表现感情。在感情的表达上,王国维认为是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不同的。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③
按照王国维的理论,卞之琳30年代的现代诗,实在不是取消感情,而是类似“无我之境”追求。这一点,对现代主义诗歌有深切了解的穆旦是看到了的,因此非常肯定它超越“牧歌情绪”加“自然风景”的旧式抒情的意义。然而,他为什么又提出这种客观性的诗歌需要加入新的抒情成分?文中直接的理由是中国现实语境的改变(“然而这是过去的事情了。七七抗战以后的中国则大不同从前。”),更实质性的方面则是不满现代主义诗歌对“知性”过分倚重:因为现代主义是一种“荒原”上的垦殖,内心充满着虚无,“没有……血液的激荡,自然不得不以锋利的机智”,这既与眼前的现实中国语境脱节,也与中国诗的抒情传统相背。穆旦希望中国的现代诗不要停留在“脑神经的运用”上,而是追求一种“渗进了情感的‘机智’”。
穆旦不希望诗歌只是智力的运用而主张情感对智力的渗透,实际上也是意识到情感与境界有关。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英雄主义,最大的特点是想通过艺术的独立性和智力的运作,寄托个人内心的孤独与混乱,与平庸的现实世界相抗衡,这使它过于重视内心感觉而不大在乎真实的世界,过于专注文本的秩序却有意无意忽略了文本与社会、文本与读者的交往和沟通。所以非人格化的现代主义最终“让位给了现代社会已经丧失了人性的机械世界”④。30年代的中国现代诗远没有西方现代主义诗歌那样走到文本体制化的地步,但像何其芳那样“思想空灵得并不归于实地”,沉醉在人生各种姿态的欣赏里(“对于人生我动心的不过是它的表现。”),沉醉在语言的颜色、姿势、节奏和结构的抗拒与偏离的效果里(“我倾听着一些飘忽的心灵的语言。我捕捉着一些刹那间闪出金光的意象。我最大的快乐或辛酸在一个崭新的文字建筑的完成或失败。”)⑤,是否走进了艺术的象牙塔?艺术的好坏有感觉和智力运用的技术问题,但艺术的伟大与否却与情怀、胸襟相关,不是单靠智力能实现的。卞之琳后来认为:当时自己是“小处敏感,大处茫然,面对历史事件、时代风云,我总不知要如何表达自己的悲喜反应。这时期写诗,总像是身在幽谷,虽然是心在峰巅。”⑥——这种现象,是否正说明了现代主义艺术体制确有某种排他性?卞之琳30年代中期的诗,就艺术而言,很少人的创作能与之相提并论,但它们大多是精致的盆景而不是有壮阔气象的山河。
中国诗歌的新质
穆旦的诗,实际上“综合”了五四以来“新诗”中的许多质素,包括浪漫主义从情感出发的英雄气质和扩张性,现代主义富于知性的冷凝和内敛,东方式的直觉和西方式的分析等等,都被织进了他充满矛盾分裂又有艺术的统一性的诗歌世界。用强烈的抒情而不是通过“距离的组织”来表现非常丰富的矛盾冲突的感情经验,是穆旦创造的诗歌奇迹。因此,最早的一篇的评论文章说穆旦诗歌是一个谜,穆旦诗歌真正的谜却是: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在别的中国诗人是模糊而像羽毛样轻的地方,他确实,而且几乎是拍着桌子说话。在普遍的单薄之中,他的组织和联想的丰富有点近乎冒犯别人了。而同时期的诗人唐湜也强调了这一点:“读他的文字会有许多不顺眼的滞重的感觉,那些特别的章句排列和文字组合也使人得不到快感,没有读诗应得的那种喜悦与轻柔的感觉。可是这种由于对中国文字的感觉力,特别是色彩感的陌生而有的滞重,竟也能产生一种原始的健朴的力与坚韧的勃起的生气,会给你的思想、感觉一种发火的磨擦,使你感到一些燃烧的力量与体质的重量,有时竟也会由此转而得到一种‘猝然,一种剃刀似的锋利’。”⑦
这些“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剃刀似的锋利”而非温柔敦厚的啮心效果,以及丰富而非纯净的美感,正是穆旦给现代汉语诗歌带来的新的“诗质”。它与其说是非中国的,毋宁说是非古典中国的:非“牧歌的情绪”加“自然风景”的,非单线因果和起承转合的,非和谐统一的;而是揿入血肉的矛盾分裂的感觉、意识与潜意识里的恐怖与渴望、寻求超越的追求与挣扎。许多人都从穆旦的诗中读出了“丰富的痛苦”,但真无的谜底却在意识到现代生存的矛盾分裂又想“伸入新的组合”:“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这是作者《春》这首诗的第二节。第一节写的是“春”的苏醒,精神的和欲望的苏醒,因而让人明显感受到“春”的象征性,是对“春天”读解又是对“青春”的想象与体认。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也写到“二十岁”,“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的二十岁,犹如“泥土做成的鸟的歌”一样的二十岁,然而却一点也没有前面提及的徐迟《二十岁人》那样单纯和快乐。相反,当“紧闭的肉体”被打开,当生命的热情被点燃,却如同被抛到一片荒原,无处藏匿,无处归依。应该说,像徐迟诗歌那样单纯快乐的现代青年毕竟少而又少,戴望舒、何其芳们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也是无处归依的,甚至闻一多诗的抒情主人公也是无处归依的。无处归依几乎是进入现代以来中国诗人共同的感觉:自从我们被迫加入世界“现代化”的行程以来,不仅认同了西方现代的政治经济体制,也放逐了本土文化的原质根性,知识分子游离在一个崩离破裂的文化空间里求索、叩问:传统文化的凝聚力没有了,但能安顿心灵的新文化在那里?在旧的已被放逐到边缘,新的又还不能在人们心灵里生根的情况下,实际上新旧都无法彻底认同。人们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生活在文化虚无与文化错位的时间、空间中,生活在文化失真与文化融合的持久的矛盾与分裂中。时间之伤和精神之痛是共同的,破碎感是共同的,犹如秋夜的凝露,你清晨起来发现每棵草尖上都有一滴,好像是泪珠。于是我们在《我》中读到了一个如此残缺破碎的自己,——这首诗写“我”却没有出现一个我字,是对汉语传统语法灵活性的致敬,还是为了强调个我的普遍性,让每一个正在阅读的“我”置身其中?全诗如下:“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遇见部分时在一起哭喊,/是初恋的狂喜,想冲出樊篱,/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这里是分裂、残缺,孤独、隔绝,无法融入历史,不能与整体取得和谐,无法在回忆中找回自己,也不能在幻象得到慰藉,内寻与外求都通向“更深的绝望”,因而“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在结尾之前,诗的说话者又再次强调了这种感受,而且,绝望转化成了仇恨,“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
穆旦与他的前辈现代诗人不同,他不同于闻一多,后者凭着浪漫主义气质和古典主义的艺术趣味,在一片破碎中还能想象一个金光四射的《奇迹》,他也不同于戴望舒与何其芳,返回记忆与梦境,诉说着美丽的忧伤。我们很难从传统诗歌甚至以往的“新诗”中发现这样的诗歌主题,而在分行诗歌之外,似乎也只有鲁迅的《野草》和个别小说才深入到如此深邃的自我世界。不过,穆旦仍然与鲁迅不同,后者虽然也深入到个体生命真正的梦魇,但《野草》中的梦魇更多表现为人与环境的紧张,并且直接寄托在梦的情境中,而穆旦诗中的梦魇,既有环境的因素,也有生命中非言语能够照明的“本我”因素。穆旦把这种因素寄托在“野兽”或类似的意象中(如《野兽》、《旷野》、《童年》、《诗八首》),是“泥土做成的鸟的歌”(《春》),“春草一样地呼吸”(《诗八首》);相对于理性秩序,它是“紊乱”,相对于文明,它是本能、原始的自然力;它为现代时间和现代文明所囚禁,所伤害,创痛激烈地挣扎,并“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穆旦在现代汉语诗歌现代性寻求进程中的无可替代的意义,他“新的抒情”真正新的地方,正在于他脱掉了幻想、回忆和梦境的衣裳,潜入到了“自我”的深海,接触到现代生活中“自我”与“本我”、文明与自然的矛盾与紧张,从而像拉奥孔雕像那样赤裸出了现代生命的痛苦与挣扎。于是,他诗歌中的城市也就不仅仅具有道德上的不洁感,而是对生命的排斥,它是一种“灿烂整齐的空洞”,生命无法居留:“……然而我们已跳进这城市的回旋的舞,/它高速度的昏眩,街中心的郁热。/无数车辆都怂恿我们动,无尽的噪音,/请我们参加,手拉着手的巨厦教我们鞠躬:/呵,钢筋铁骨的神,我们不过是寄生在你玻璃里的害虫。//把我们这样切,那样切,等一会就磨成同一颜色的细粉,/死去了不同意的个体,和泥土里的生命;/阳光水分和智慧已不再能够滋养,使我们生长的/是写字间或服装上的努力,是一步挨一步的名义和头衔,/想着一条大街的思想,或者它灿烂整齐的空洞。”(《城市的舞》)而现代时间的旋转、钢铁的切割和辗磨,所带给每一个生命的,就是自我完整性的终结,就是自己的永远不能完成,就是不断的变形、扭曲、分裂,“直到我们追悔,屈服,使它僵化/它的光消殒”(《诗二章》)。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面对爱情的时候,穆旦也丝毫没有浪漫主义诗歌的“牧歌的情绪”的原因。相反,从另一双超越的眼睛,看见的是“一场火灾”,“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生命在“自然的蜕变程序里”永远是隔绝、偶然、变动和危险:“水流山石间沉淀下你我,/而我们成长,在死底子宫里。/在无数的可能里一个变形的生命/永远不能完成他自己。//我和你谈话,相信你,爱你,/这时候就听见我底主暗笑,/不断地他添来另外的你我/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而这种“危险”的本质就在于两颗情愿的心都必须面对矛盾分裂的自我,面对变动的世界和时间:“相同和相同溶为怠倦,/在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是一条多么危险的窄路里,/我制造自己在那上面旅行。//他存在,听从我底指使,/他保护,而把我留在孤独里,/他底痛苦是不断的寻求/你底秩序,求得了又必须背离。”
穆旦的这首《诗八首》,当是“新诗”中最杰出的爱情诗之一,它最大的特点是从生命与存在的角度去想象爱情,而对生命的认知,又深入到了非统一性、稳定性和充满矛盾的“自我”世界,从而更新了“新诗”抒情形象的单一与线形发展的特点,更新了诗歌的主题和内容,并由此出发实践了许多新的整合矛盾经验的语言策略和修辞手段。
经由穆旦深入到矛盾复杂的“自我”世界对现代生存的反观,现代“诗质”得到了非常丰富的表现,也呈现出了诗歌掘入现代经验、情绪和意识的诸多可能性。穆旦曾在《出发》一诗中把现代生存比喻为“在犬牙的角道中让我们反复行进,……而我们皈依的/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底痛苦”,这种“丰富的痛苦”不仅在中国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20世纪中国诗歌的抒情和想象方式,把现代主义的疏离现实的倾向,转化成了矛盾经验与情感个人化呈现,从而更有力地介入和观照了现代生存。穆旦综合了诸多优秀质素的“新的抒情”,弥补了诗歌与现实的裂痕,体现了苦难年代中国诗歌的新质,可以用《五月》中几行诗来比喻:“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它们能给我绝望后的快乐,/对着漆黑的枪口,你就会看见/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我是得到了第二次诞生。”
“荒原”的独特见证
不过,中国诗歌在历史的苦难中得到了新的诞生,诗人却似乎命中注定要在历史中受难。穆旦以“丰富的痛苦”为底色的“新的抒情”并没有在新的时代得到延续,这不是新的时代没有痛苦,而是人们被告知“新时代”只要单纯不需要丰富、只有欢乐不存在痛苦。虽然穆旦为了“向大海相聚”,也“一再地选择死亡和蜕变”,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翻译中,以本名“查良铮”和笔名“梁真”发表文学理论译作和译诗,但他最萦绕于怀的一定是能够继续写诗。要不,1957年上半年短短几个月的“百花齐放”,他不可能一下就写出7首诗,更不会有哪首“只算唱了一半”的《葬歌》:在这首典型体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挣扎的诗篇里,诗中的说话者多么愿意面对“现实”与“希望”,“以欢乐为祭”埋葬自己的“回忆”和“骄矜”。但是,面对“洪水淹没了孤独的岛屿”的新生活,他又对属于“个人”领域的许多美好的东西有所眷恋,因而不能不心存恐惧与怀疑:“‘希望’是不是骗我?/我怎能把一切抛下?/要是把‘我’也失掉了,/哪儿去找温暖的家?”然而,“哦,埋葬,埋葬,埋葬!”不待穆旦唱出另一半的葬歌,时代却“埋葬”了他的自由与生命:1958年“反右”运动中,穆旦被定罪为“历史反革命”,这一“错误的决定”直至1980年才得到“改正”。
穆旦在1976年1月骑自行车时摔伤骨折,因怕连累家庭延误了治疗,于次年2月接受手术前突发心脏病死亡。他是带着“历史反革命”这顶莫须有的“帽子”离开这个世界的,“归来”诗人中他是一个只有作品而没有身影的归来者。但是,无论作为一种精神现象,还是从诗歌的艺术水准看,穆旦于1976年写作、1980年后才陆续与读者见面的诗,当是“归来”诗歌家族中最真诚、最值得重视的部份。从1949到1975的26年间,连同英文诗在内,穆旦只写过12首诗。可在1976年,他的诗有27首。在行将与这个世界诀别的最后一年,诗神何以如此热烈地拥抱着这个带“罪”带伤的人?而这个带“罪”带伤之身,何以如此热切拉着诗神的手不放?是诗神要抚慰这个伤痕累累的圣徒,还是圣徒只有在诗神身边才能诉说心事、安顿灵魂?
穆旦晚年诗歌在“归来”诗人家族中无可替代的意义,是以真切的当代经验和人生感受见证了“自我”的分裂和灵魂的挣扎:这是一切都被剥夺殆尽,通往自由、健康、友谊的大门都被关闭,仿佛置身于人生荒原的歌吟,“留下贫穷的我,面对严厉的岁月,/独自回顾那已丧失的财富和自己。”(《友谊》)面对严峻的岁月,穆旦诗中的说话者在生命的黄昏不断地辨认自己,探讨“自我”的形成与变化,冥想“永久的秩序”与生命的关系。他回顾生前,想像身后,不仅意识到人生的的奔波、劳作、冒险“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而且发现存在与生命的独特关系。其中1976年3月写作的《智慧之歌》最让人震撼,它是人生的反省,也是时代的见证:当人“走到了幻想底尽头”,曾经蓬勃发绿的树木落叶飘零,所有枯黄都堆积于心,我们的诗人发现:“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每天在惩罚自己过去的傲慢,/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遣责,/还有什么色彩留在这片荒原?//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在这里,穆旦又一次提到了他二十几年前提及和想像过的“荒原”,提到了没有“血液的激荡”的机智(“智慧”)。但是,在“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遣责,还有什么色彩留在这片荒原?”的时代,与痛苦相伴的日常生活所惩罚的正是不能被规训的激情与“傲慢”。于是,茫茫荒原上“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智慧”——这被苦汁培育、嘲弄生命的本真和热情的株植——成了荒原一个独特的见证。
自从艾略特的《荒原》出版以来,有许多诗人想像现代“荒原”的景象,但没有人像穆旦那样以“智慧之树”对生命的嘲弄具体见证这种“荒原”对人类的扭曲。人们都以理性、智力、智慧、聪明为荣,只有穆旦卓然不群地发现了它们对生命、血性、激情和艺术的伤害,怀着无奈和咒诅的感情,把它想像为现代荒原上的恶之花。
穆旦晚年的诗忧郁而沉静,情感的表达非常节制,诗句的节奏从容而有规律。它与其它“归来”诗歌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是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当代体制化文艺观念和时代风气的影响。这是被“严厉的岁月”逼到绝境的孤独的个人,“独自回顾那已丧失的财富和自己”时通过诗发出的最真诚的声音。它们几乎摒弃了现代主义诗歌的表面原则和技巧,纯粹以灵魂的“自白”和“自我”抒情的方式见证着个体生命对时代的承受。尤其是《春》、《夏》、《秋》、《冬》等几首隐喻人生过程的诗,仿佛“流过的白云与河水谈心”,是“远行前柔情的告别”,虽然以秋冬的意象为主,有“荒原”的色调与气息,但迎着历史的悲情和生命的秋凉升起的,仍然是一面有着“血液的激荡”的“生的胜利”的旗帜。
一如穆旦在青年时代自觉拒绝了浪漫主义的“牧歌的情绪”,他晚年也在绝境中拒绝了感伤主义和冷嘲热讽。他一生都在用激情与热血融化现代主义的冷凝,实践着“新的抒情”——感情与知性平衡的诗歌理想。
注释:
①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香港:《大公报》,1940年4月28日第8版。
②王国维:《文学小言》,《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79页。
③王国维:《人间词话》,《〈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1页。
④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52页。
⑤何其芳:《梦中道路》,《何其芳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62~63页。
⑥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页。
⑦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穆旦诗集(1939-1945)》,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