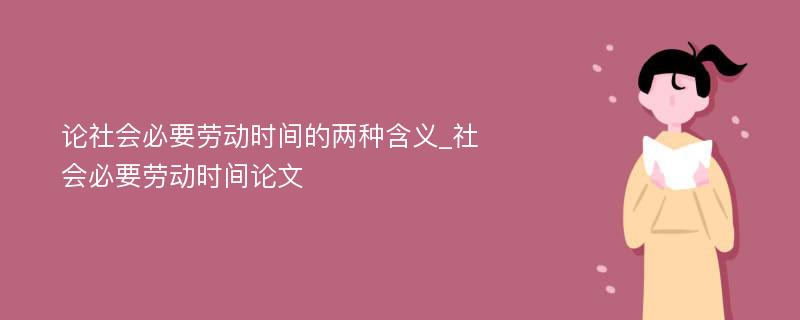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提法浅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提法论文,含义论文,时间论文,社会必要劳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供求一致"是否分歧的关键所在
宋则行先生认为,两种认识分歧的关键所在在于是否承认"供求一致"。实际上,供求"从来不会一致",马克思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内在规律""纯粹地实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12页。),的确是作了"供求一致"等等的假定。姜启渭先生对此亦并未否认,要不他怎么会提出"政治经济学在研究价值本质时为什么说要假定供求一致呢"(注:姜启渭:"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的关系及观察所谓'实现'问题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劳动价值理论深层研究之二",《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3期。)这一设问?看来,问题只是出在如何理解"供求一致"这一前提上,在这里,集中体现在单位商品的使用价值究竟是否涉及"供与求的'量'"(注:宋则行:《关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答姜启渭先生》,《当代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上。
两种观点均引了马克思的同一段话以为证据,只是宋先生指责姜文在"引证时把这小段破折号内的至关重要的话"(注:宋则行:《关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答姜启渭先生》,《当代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即"它的量已经包含在它的价格中",用引号删去了。宋先生据此认为,马克思的"这段话,帮不了姜先生的忙,因为说对单个商品时,不是没有使用价值的量的问题,只是'它的量已经包含在它的价格中'"。(注:宋则行:《关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答姜启渭先生》,《当代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对此,我想可否作如下理解:首先,商品的使用价值确是质和量的规定性的有机统一,单位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例外。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显然不等同于仅仅单纯表示成"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327页。)的自然物质的使用价值。"这是由商品的自然性质和社会性质决定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过是"用其物质的外壳承载的社会生产关系"。(注:吴华章:《关于使用价值规定性的探索》,《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3期。)某一单位商品一定的使用价值的质的规定性,必然以一定的量化指标反映于价格之中。这就是马克思所说"当我们只是说到单个商品时,我们可以假定,存在着对这种特定商品的需要,--它的量已经包含在它的价格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06页。)可是,单位商品的使用价值涉及的"量"与总量商品的使用价值涉及的"量"是有着不同含义的。也就是说,只有总量商品的使用价值才涉及到供给与需求的"量"。这个"量",确切地指满足一定社会需求的单位商品的数量。而作为一定质和量的规定性的有机统一的单位商品体,其中的"量"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下相应于一定质的规定性的"量",而不是指表示商品个数的"量"。因此,马克思接下来说,"而用不着进一步考察这个有待满足的需要的量。但是,只要一方面有了整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会需要,这个量是一个重要因素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06页。)这样,即使不删去破折号内至关重要的话,也仍会得出二者并非一致的结论:作为第一种表述的单个商品价值形成的物质前提就是商品体本身,即该商品为人们所需要,具有使用价值,并不涉及商品体数量的规定;而作为第二种表述的总量商品价值决定的物质前提是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即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总量,量的规定是必要的要素。因此,第一种表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强调"
三个平均",而第二种则表述为: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22页。)
宋先生还借用恩格斯批评洛贝尔图斯的一段话以说明只存在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在我看来,反映在单位商品和总量商品上的两种表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不一致。第一种表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同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无关。它把社会上不同的具体劳动化为同质、等一的一般人类劳动,从而考察其对商品价值的关系;第二种表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同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直接相关。如果具体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不为社会所需或所需不多,那么第二种表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会受到直接影响。其实,一味强调两种含义完全一致的宋先生亦不得不承认两种含义"考察的角度有所不同"。(注:宋则行:《关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答姜启渭先生》,《当代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然而,两种表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具体规定的差异性,并不排除二者的一致性。尽管姜文始终坚持两种含义不同论,但文末还是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所谓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统一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的始终一贯"(注:姜启渭:《对长期争论难点、失误原因及问题的实践意义分析--劳动价值理论深层研究之三》,《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4期。)。二者的一致表现在:
第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说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另一种意义",是马克思对第1卷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的充实或完善。在第1卷中,马克思从狭义生产过程的角度来分析单个商品(或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的价值决定,对该商品是否为社会需要,供需是否平衡,及由此产生的为满足对不同商品的需求量,所需社会劳动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等方面的问题和因素,作了舍象和假定。所以,这里对价值决定的表述属于抽象的、基础层次上的,但在理论分析中却是十分必要的。在第3卷中,马克思从广义生产过程(生产总过程)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商品的价值决定,逐一加进在第1卷中舍象掉的因素,如供求经常的不一致、市场竞争等,使"另一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决定的表述更具体、更具有现实意义。第一种表述是理论意义上的、对现实社会关系设定前提、假定后的简单模型;而第二种表述则属于资本的表层现实运动。(注:姜启渭:《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的关系及观察所谓"实现"问题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劳动价值理论深层研究之二》,《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3期。)两种不同表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有阐述层次上的不同,实质上是一致的。
第二,在一定时期社会现有的正常生产条件下,无论从个别生产部门或从全社会来看,两种表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无二致。马克思根据资本构成将一个工业部门或各个工业部门的生产条件,区分为三类,即中位的、最优的和最劣的生产条件,而且任何生产条件只要它被绝大多数企业所具备即为社会正常生产条件。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一个工业部门,而且同样适用于各个工业部门之间。个别商品价值决定于"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所需的劳动时间,即决定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企业的一般生产条件,非专就个别企业而言;为社会需要的各工业部门生产的总量商品,其价值也须决定于大多数企业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可见,两种表述只有文字、重点之不同并无根本性的差别。
第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平均化,离不开对社会的整体考察。"平均"决不单指一个企业或一个工业部门,平均化只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作为劳动量自然尺度的劳动时间,以生产中投入的劳动(生产)为依据,而作为依据的劳动量必须通过交换(流通)予以确认。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生产者本人事先并不知道自己的劳动是否具备平均水平,只能依据经常的商品交换行为,根据历史的或习惯的验证,及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对照,社会契约式地被动地接受市场上形成的各类商品相交换的错综复杂的比例,而这种比例近似地反映了决定各类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平均化(形成)不可能由生产和流通两个不同性质的层次分别进行,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所谓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同时,这也是对"流通决定论"的根本否定。
总之,两种表述既联系又区别。两种认识分歧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承认"供求一致",而在于他们都未能全面、辩证地把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这就形成了虽然都只依据马克思的同样的几处引文,然而却得出相异结论的局面。"两种含义说"过分注重两种表述的差异,容易割裂不同层次上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定的本质联系,易使人误解为两个平行存在的概念。而且,这种划分也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事实上,《资本论》行文中绝没有"第一含义"和"第二含义"的字眼);"一种含义说"则过分突出两种表述的一致,完全忽视二者的区别,从而造成对价值决定这一深刻理论问题理解的偏颇。马克思在论述他的方法论时谈到,作为研究方法,要从实在和具体开始,对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笔者以为,第一种表述恰是做了更切近的规定之后达到的最简单规定,不妨称之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简单含义;第二种表述是在建立了最简单的模型基础上,逐步具体化、复杂化达到的几近现实的进一步规定,诚如姜先生所述,"作为叙述过程终点和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顶点,并且还要以许多规定来再现研究过程起点的具体总体价值概念......是更为确切更为丰富的价值范畴......也属更高一级的价值概念和范畴,就象高等动物以其发达的器官、系统、协调的机能,高于低等动物一样",(注:姜启渭:《创造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的两重含义的存在笥--劳动价值理论的层研究之一》《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可对应称之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复杂含义。二者如同数学中的公理和定理。公理是不证自明、永恒成立的,往往是对事物的较简单规定;定理则是加入若干限制条件后经证明而得到的有约束的结论,限制条件一旦发生变更,则结论相应变化。这也许有助于回答一些学者提出的"既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质上是一致的,为什么依二者计算,会经常得到不一致的结论?"这一疑问。
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为简单含义、复杂含义的理论意义
以简单含义、复杂含义的新提法代替第一种含义、第二种含义的旧说法,从文字表述上明确了这不过是针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层面规定,肯定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质上的同一,而且也使围绕"两种含义"问题展开的争论或迎刃而解或迷雾初开。笔者不同意樊纲《"苏联范式"批判》一文中所说,对"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的讨论,"天生地"难以获得真正的理论进展,却赞成樊文"必需另辟途径"探讨这一理论的观点。(注:樊纲:《"苏联范式"批判》,《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为简单含义、复杂含义的理论意义,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首先,它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区别于其它劳动价值学说,从而体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科学性。这表现在马克思揭示了创造价值的劳动所具有的特性:其一、在质上,只有在特定社会历史形式下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价值是这种劳动的历史表现形式;其二、在量上,创造价值的劳动量,必须是社会所必要的,而且必须首先是从总量上看符合社会需要。只有符合社会需要的劳动总量,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平均数才能形成相应的价值量。正如"自己同自己矛盾"。(注:姜启渭:《创造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的两重含义的存在性--劳动价值理论的深层研究之一》,《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的卫文所说,"单个商品的价值量,不过是总商品的价值总量的可除部分"。(注:卫兴华:《价值决定和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其次,它体现了马克思科学劳动价值论体系的严谨和统一,是对坚持"第二种含义"就会流为"供求决定论"的否定。马克思并没有通过所谓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引入"需求"而回到"需求决定价值"的观点(实际上他从未持此观点),从而使他的理论体系(如樊文语)"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逻辑上的矛盾"。其实,反而如樊文所说,马克思"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需求本来不决定价值,而只决定价格",看来"在有关需求与价值理论关系的问题上发生如此严重的逻辑矛盾"的决不是马克思本人。
第三,是对"流通决定论"的否定。价值,从实质上说,是生产和需要通过市场联系起来的社会关系。(注:王洪斌:《社会必要需求量是理解价值决定的枢纽》《经济研究》1986年第3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平均化也只能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价值的形成与同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成,必然都是在同一个完整的经济活动过程中实现。认为"第二种含义的必要劳动如能决定价值就必然要在流通过程中实现",因此"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流通决定论"的观点,显然站不住脚。
第四,是对"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决定价值的实现"说法的否定。无论是简单含义、还是复杂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是讨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的关系,是价值的质和量的确定问题,即价值决定的问题。而并不是讨论价值与交换价值(价格)的关系,即不是价值的实现问题。(注:曾昭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决定》,《经济研究》1983年第2期。)
标签: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