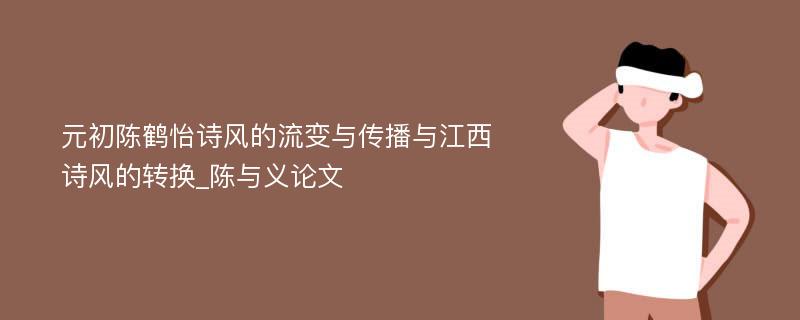
元初陈与义诗风的流衍与江西诗风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风论文,江西论文,元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7)04-0030-06
元初诗坛承宋季遗习,江湖、四灵诗风颇行其是,而江西诗派亦嗣响可闻,但是在新的“宗唐得古”的风气之下,也不能不有所转变。就江西诗风而言,即是对陈与义诗的崇奉、学习。
一、陈与义诗风在江西地区的流传
钱钟书《谈艺录》尝引吴澄《吴文正公集》所载及程钜夫《严元德诗序》之语,云:“合二人之论揣之,则简斋诗盛行于元初江西诗人间。然文献罕征,欲爬梳而未由矣。”[1](p.471)本文即欲就钱先生所论,对陈与义诗风之流传略加爬梳。
按吴澄,江西抚州人,他以一代钜儒,与朝廷大员如程钜夫、道教宗师如吴全节等均过从颇密。吴澄于诗极有见地,他评刘辰翁诗学云:“近年庐陵刘会孟,于诸家诗融贯彻,评论造极。”[2](卷一一)则其于时下诗坛亦具相当了解。由于吴澄特殊的身份地位,江西一地之习诗者,多请吴澄为之作序,其中有固守“江西诗派”壁垒者,有仿习李贺者,也多有崇尚陈与义者,颇可反映一时一地之诗歌风貌。只是元初变乱初息,诗文散佚太多,不能做更详细和明晰的描述。
关于陈与义诗,吴澄《曾志顺诗序》谓:“宋诗自简斋超矣。近来人竟学之。”[2](卷九)见于其诗序,可资证明者上述曾志顺为其中之一。又如同卷《董震翁诗序》载:
宋参政简斋陈公,于诗超然悟入……近世往往尊其诗,得其门者或寡矣。吾乡董震翁新学诗,观其古近体一二,不选、不唐、不派、不江湖,问曰:“君嗜简斋诗乎?”曰:“然”。夫学诗者各有所从入,终必有所悟。大音稀声,未必谐于里耳。君能不以人之好、不好为意,而嗜之不厌,其可畏也已。[2](卷九)
“近世往往尊其诗”,即“近来人竟学之”之验,而所谓“大音稀声,未必谐于里耳”,则简斋诗的风行,当然也是“四灵”、“江湖”之“当时体”的一种反拔。
又同卷《谌季岩诗序》载:
丁酉冬,见谌李岩诗,咏物工而用事切,谓曰:“诗诚佳,然吟诗必此诗,或非诗人所高尔。”壬寅春,观之,则体格与昔大异。问曰:“近读何诗?”曰:“简斋”。余曰:“得之矣。”[2]
丁酉,即元大德元年(1297),谌季岩诗“咏物工而用事切”,或流于俗熟;壬寅,即大德六年 (1302),谌氏改辙习陈与义诗。风气之转移或即在此时。
同卷《聂文俨诗序》载:
学诗者若有适也,适必于其道,则未至而可至;不以其道,则愈至而愈不至,清江聂文俨诗,不俗不腐,盖望参政陈公之门,而适之以其道者,余知其至者有日矣。[2]
卷一○《陈善夫诗序》载:
近年邦人类多学诗……陈家诗如履常如去非,家法自不待他求。[2]
卷一一《何敏则诗序》载:
近代参政简斋陈公,比之陶、韦更新、更巧,今观临江何敏则,句意到处,清俊绝伦。盖亦参透此机,彼钝根下品,孰敢仰视?点者、评者,一一摘抉示人矣,他日不新而新,不巧而巧,点者莫可著一辞,是又诗之最上乘。[2]
同卷《陈景和诗序》亦有类似的记载。由上所引可见,吴澄所言,当然是信而有征。吴澄留心文艺辞翰,他在《董震翁诗序》中说:“吾尝窥其(陈与义诗)际,盖古体自东坡氏,近体自后山氏,而神化之妙,简斋自简斋也。”其论陈与义诗,颇具卓识,而他于诗序中所言,大多亦能得其情实,非虚声漫誉可比。吴澄《胡印之诗序》谓:
近年以来,学诗者浸多,往往亦有清新奇丽之作,然细味不过仿他人形影声响以相矜耀。 [2](卷一一)
其中“奇丽”或指时人之模拟李贺诗风,而“清新”或即程钜夫、吴澄形容陈与义诗所谓“清俊”,至于“形影声响”云云,俗下人学诗,原本如此。
二、刘辰翁对陈与义诗风的推阐
陈与义诗风的流传,刘辰翁的推阐起了很大的作用。辰翁子刘将孙《须溪先生集序》言:
先生登第十五年,立朝不满月,外庸无一考,当晦明绝续之交,胸中郁郁者一泄之于诗,其鞶礴襞积而不得吐者,借文以自宣,脱于口者曾不经意,其引而不发者,又何其极也!然场屋称文自先生而后,今古变化议论沉著,皆有味之言,至于今犹有遗者;师友学问自先生而后,知证之本心,溯之六经。辨濂洛而见洙泗,不但语录或问为已足;词章翰墨自先生而后知大家数,笔力情性尽扫江湖晚唐锢陋之习,虽发舒不倡而能震于一世之上如前闻人,而家有其书,人诵其言,隐然掇流俗心髓而洗濯之,于以开将来而待有作。尝论李汉称韩公摧陷廓清之功雄伟不常,比于武事;东坡推欧公同于禹渎水,周公之膺惩,千载无异词。抑佛老,人知其为异端也,西昆体,世之所谓时文也,未有若文学之平沉而文学之澜倒也,且视韩苏,所遇为何如哉?而振拔一时至此,则先生之辞岂不有关于气运,力难而功倍,而其不幸则可感者在是[3](卷一一)
这与吴澄《董震翁诗序》所载正相吻合。就诗而言,宋末诗人沉溺于江湖晚唐陋习,刘辰翁乃振起于一时。刘将孙将之与韩愈排佛老、欧阳修反“西昆”相提并论,虽然处鼎革之际,事倍而功半,但“家有其书,人诵其言”,其影响仍是很大的。
刘辰翁尝取唐宋诸大家诗集一一评点,开我国文学批评史上评点之学的先河。流传至今的有王维、孟浩然、杜甫、李贺、陈与义、陆游等九种,所谓“词章翰墨自先生而后知大家数”即就此而言。而流传最广者,一为评李贺,一为评陈与义诗。程钜夫《严元德诗序》言:
自刘会孟发古今诗人之秘,江西诗为之一变,今三十年矣,而师昌谷、简斋最盛。余习时有存者。无他,李变眩,观者莫敢议;陈清俊,览者无不悦,此学者急于人知之弊也。变眩、清俊因非二者之本,亦非会孟教人之意也,因其所长各有取焉耳……会孟于古人之作,若生同时、居同乡、学同道、仕同朝,其心情笑貌依微俯仰,千态万状,言无不似,似无不极,其言曰:“吾之评诗,过于作者用意。”故会孟谈诗,近世鲜能及之。夫学者必求之古,不求之古而徒膠膠戛戛,取合于一时,其去古人也益远矣,其不为会孟所笑者亦寡矣。[4](卷一五)
刘辰翁论诗近于禅悟,自不主模拟[3](卷一—《彭丙公诗序》),其评诗虽以“大家数”示人,但也不是标举一家一派以为鹄的,他自己也说:
杜诗“不及前人更无疑,递相祖述竟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此杜示人以学诗之法。前二句戒人之愈趋愈下,后二句勉人之学乎其上也。盖谓后人不及前人者,以递相祖述,日赴日下也。必也区别裁正浮伪之体,而上亲风雅,则诸公之上,转益多师,而汝师在是矣。[5](卷六《语罗履泰》)
刘辰翁的评点,其用意亦如老杜,在于“戒人之愈趋愈下”,“勉之学乎其上”,导人以转益多师,则时人之主于一家一派因袭模拟,固不是刘辰翁的本意。但就其造成的客观效果言,又不能不说是刘辰翁开其流,导其源。
刘辰翁评点的唐宋大家有多种,除李贺而外,为什么独独陈与义能脱颖而出,成为人们师法仿效的对象呢?程钜夫在前引的《严元德诗序》中这样解释:“李变眩,观者莫敢议;陈清俊,览者无不悦,此学者急于人知之弊也。”这里其实包含两方面的因素,一者与陈与义诗歌自身的特点有关,再则也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就前者言,程钜夫称陈与义的诗是“清俊”,吴澄称赞学陈诗而谋其神的何敏则是“清俊绝伦”[2](卷一一)而对陈与义诗辨析详尽,且颇中肯繁的,则是评点过陈诗的刘辰翁,他在《简斋诗笺序》中说:
诗至晚唐已厌,至近年江湖又厌,谓其和易如流,殆不可与庄语,而学问为无用也。荆公妥帖排奡,时出经史,而体格如一。及黄太史矫然特出新意,真欲尽用万卷,与李、杜争能于一辞一字之顷,其极至寡情少恩,如法家者流。后山自谓黄出,理实胜黄,其陈言妙语乃可称破万卷者,然外示枯槁,又如息夫人绝世,一笑自难。惟陈简斋以后山体用后山,望之苍然,而光景明丽,肌骨匀称。古称陶公用兵,得法外意,以简斋视黄、陈,节制亮无不及。则后山比简斋,刻削相似,矜持未尽去也。此诗之至也。吾执鞭古人,岂敢叛去,独为简斋放言?或问:“宋诗至简斋至矣,毕竟比坡公何如?”曰:“诗道如花,论品则色不如香,论逼真香不如色。”[6]
“晚唐”、“江湖”不足道,刘辰翁将陈与义诗与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诗作了比较,“荆公妥帖排奡,时出经史”,但其缺点是“体格如一”;“黄太史矫然特出新意”,但缺点是“其极至寡情少恩”;陈师道“理实胜黄”,但缺点是“外示枯槁,又如息夫人绝世,一笑自难”。刘辰翁论诗主“自然”,曾有言:“诗无论拙恶,忌矜持。”[5](卷六《松声诗序》)黄、陈劣处,正在于“矜持”太过,造作太多。刘辰翁于宋诗诸大家如黄陈,其实是很尊重的,但也能洞见其优劣。
比较起来,陈与义诗学问胜于“晚唐”、“江湖”,变化多于王安石,与黄陈相较,则无“寡恩”或“枯槁”之偏失,其特点则如刘序所言:“光景明丽,肌骨匀称”,“望之苍然”,少矜持之意。
所以刘辰翁将陈与义诗与苏轼诗作了比较,他用了一个很妙的比喻:“诗道如花,论品则色不如香,论逼真则香不如色。”则辰翁虽评点陈与义诗,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却并不列入苏轼那样的最高品[5](卷六《赵仲仁诗序》)。刘辰翁诗论旨在于救“四灵”、“江湖”之弊,矫枉过正,或流为曲高和寡。而若金针度世,亦须使人有阶可寻,故辰翁于陈与义诗取其声色,取其“逼真”而已。程钜夫“陈清俊,览者莫不悦”,是看到了这一点的[7](卷—四)。盖山谷而至后山,愈益艰深婉曲,方回评其曰:“深奥幽远”[8](卷一○“诗评”)、“枯淡瘦劲”[8](卷四二“诗评”)在刘辰翁看来,却是“寡情”“枯槁””“矜持”太过,他们立论的立场不同,但都看到了黄陈诗的这些特点。而于陈与义诗,刘辰翁称之“光景明丽,肌骨匀称”,这在方回亦显于“梯危磴绝”之际,可“掬水而得月”了。只不过,方回由简斋入而钻之弥深,一般的江湖诗客得其浅而已。
元初诗歌创作的主体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江湖诗客,他们应该占到一个最大的比例。所谓“今之诗盛矣,不用立场屋而用之江湖”[9](卷一二《跋玉融林气遴诗》),这在元初更甚;另一部分是前宋进士转而攻诗者。前者不足论,多求之熟俗而已,就后者言,宋代自王安石科举改革后,诗赋乃为人冷落。因此他们其实于诗多无特见,亦无深见,吴澄《周立中诗序》言:“自进士业废,而才华之士无所用其巧,往往于古近二体之诗。然稍稍有能,辄自负曰:‘吾能是足矣’!岂知士之为士而出乎士之外者乎?”[2](卷一一)其所言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更为重要的是,宋末诗道沦为干谒之具[10](pp.37~39),诗人于诗着意于投世所好,为人所喜,吴澄在《张仲默诗集序》中说:“故其(张仲默)诗亦和平冲淡似其为人,读之可以见其志,固非世之务声音彩色以为诗,以炫于人而干于诗者所可同也。”[2](卷九)所谓“务声音色彩以为诗,以炫于人而干于诗”,在当时实是一普遍的现象,程钜夫所言“学者急于人知之弊也”,当含有这一层意思在里面。
因此,无论是江湖诗客还是前宋进士转而攻诗者,一般也无定见,往往一二大佬首倡推阐,即风行景从,群趋若鹜。前此叶适推勉“四灵”而“晚唐体”风行可以为例,后此虞、杨、范、揭宗唐复古而天下士人响应亦可为验。刘辰翁为元初诗坛巨子,影响所及,形成一时风尚,也是可以理解的。
若从更广的范围考察,江西而外,也尽有陈与义的推崇者,只是或许不像江西那样蔚成风气。前面提到的方回是从陈与义入手进据“江西”社坛的。方回是与刘辰翁是同时鼎足而峙的诗论大家,从现存资料来看,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二人有直接的来往,甚至相互间的影响,但二人立论实多相近之处。比如他们无论创作还是诗学观点,都倾向于“江西诗派”,至少是宋诗的一路,重“文人之诗”,又比如他们都将山谷、后山与简斋相提并论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方回能够进据“江西”社坛,是得益于对简斋诗的学习[11](卷一)。他在《送李景安诗作长句》中说:
独闻彭城陈正字(与义),向来得法金华伯(黄庭坚)……由陈入黄据社坛,当知掬水月在手……梯危磴绝不可近,尚有简斋横一枝。[7](卷一四)
白珽在宋末即与仇远同擅诗名,戴表元称其诗“甚似渡江陈去非”[12](卷八)。白珽诗散佚极多,但从他现存的诗作看,如:
国势已如此,孤忠天地知。死生同父子,奸冗系安危。晏月无封桧,栖霞有溢碑。中原遗老在,岁岁梦王师。[13](《岳武穆精忠庙》)
几年音问绝,此夕更关情。寒雨人孤坐,残灯雁一声。干戈犹故国,贫病向孤城。惟有琴堪诉,愁坐弹不成。[13](《山中怀友》)
等等,不矜持,无造作,不偏枯,不新异,格高调胜,恢张悲壮,确可得陈与义渡江诸作之神理。而戴表元自己,在《读陈去非集》中也称:“简斋吟册是吾师。”[12](卷二七)诗入“江湖”流品的汪元量,其诗如《南归对客》,刘辰翁亦批曰:“此诗学简斋。”盖宋元之际,杜诗、杜诗学为天下之公器,然学老杜不至,或有其悲愤,亦逊其沉著跌宕,乃多近于陈与义。而陈诗与杜本有相近、相通之处(这一层理路以为方回、刘辰翁打通,且揭橥出来),这也应该是陈与义诗为人所普遍接受的一个原因吧。
三、宗陈诗风的文学史意义
其实,对陈与义诗的推崇,不自元代始。陈与义生前即享大名,此后大诗人如杨万里,讲学家如楼鑰等,均对陈与义功业文章作出很高的评价,即对唐以来诗人少所许可的朱熹,于南渡后诗人予以揄扬的,除了陆游、赵蕃等有限的几人外,陈与义就是其中的一个[14](卷—四○《跋陈简斋帖》)。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虽称简斋诗体“亦江西之派而小异”,但仍将“简斋体”独标一目以见其影响 [15](p.122)。刘克庄之谓“及简斋出,始以老杜为师。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16](前集卷二)。而到元初,诗学简斋乃成一时风气。
若从文学、文学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如前所言,宋末元初,宋诗特征的“江西诗派”流弊尽显,“稍稍复就清苦之风”。而以唐诗自任而欲救“江西”之弊的“四灵”晚唐体也为人诟病,时人有意无意间都在进行着尝试和选择,“宗唐(盛唐)得古”当然代表了最主要的倾向,方回的重树“江西”旗帜也代表了一种选择,本文所言宗陈诗风自不例外。
陈与义是宋代诗人中少有的几个为宗宋者喜欢,同时也为宗唐者喜欢的诗人之一[17](pp.132~ 133),对陈与义的推重,在方回,在刘辰翁,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宗宋诗派对唐诗美学风味的某种程度上的调和和包容。而置于元代整个诗史嬗变的脉络下,则陈简斋诗似乎成为了元代宗宋派向“宗唐得古”风气过渡的一个环节点。就这一点言,王安石是一个可资类比的对象。有宋一代,凡濡染唐诗者,多喜王安石,甚或由之取径以进探唐诗。这个问题,张白山《王安石晚期诗歌评价问题》一文中有很好的论述,可以参看,此不赘述[18](pp.82~100)。而事实上,元代士人也颇取王安石诗。袁易《静春堂集》龚肃原序云:
一自士去科举之业,例无不为诗,北音伤于壮,南之失之浮,诗文不同宜极于古,故今人于宋诗少所许可,仅取王半山,以其逼唐也,然半山岂肯及唐而止……譬径登峰造极,循循来径,尚于此乎见之。[19](《静春堂诗集原序》)
士人有取于王安石,在于其“逼唐”,但还不止于此,其目的在于循此以臻于古。这在龚肃,为一理论上的自觉,而元初士人于陈与义的学习中,也不期然而然地走上了这条路。
最后一个问题是陈与义诗风流行的时间。有的学者将之定为“至元大德间”[20]。按程钜夫《严元德诗序》言:“自刘会孟发古今诗人之秘,江西诗为之一变,今三十年矣。”刘将孙《刻长吉诗序》载:
先君须溪先生于评诸家最先李长吉。盖乙亥避地山中,无以抒思寄怀,始有意留眼目,开后来。自长吉而后,及于诸家。[3](卷九)
如若从乙亥(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刘辰翁于避乱山中时评点李长吉诗——所谓“发古今诗人之秘”——起,三十年后,应是元大德八年,甲辰年,公元1304年。程钜夫说其时李贺、简斋诗“余习犹有存者”,则至大德八年,风气已变,仅存余响而已。而简斋、长吉诗的风行,更应在此之前。又吴澄《谌季岩诗序》载谌季岩学简斋诗有或是在“壬寅”年,即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亦与程钜夫所言相符。而前引《吴文正公集》卷九序中诸诗人多有习简斋诗者,其序大致作于同时,亦可见一时风气。如此说来,“至元大德间”的断限应是不错的。
收稿日期:2007-0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