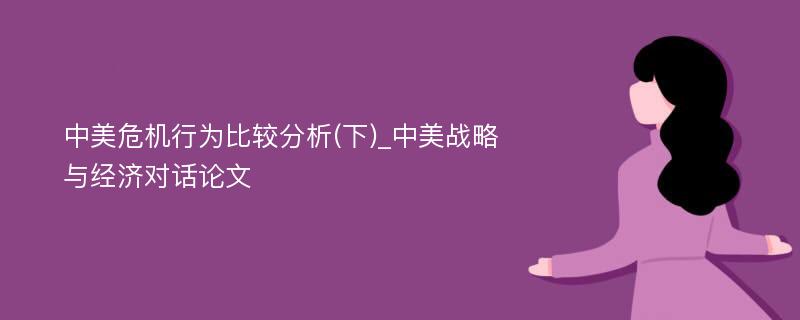
中美危机行为比较分析(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之二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总结历史经验,避免重大危机
国际危机的理论研究表明,危机及其管理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决策者对利益面临威胁、时间压力和战争可能性的认知。危机管理与战争行动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着眼于打赢,而前者的目的在于防止战争的同时维护或扩大自身利益。因此,成功的危机管理只能是在双方的利益冲突点和利益共同点之间找到某个妥协点,双方都无法、也不应该追求压倒对手的最高目标。恰恰相反,双方的决策者应该把导致危机及其升级的因素视为“共同的敌人”,并一方面给出己方可以妥协的底线,另一方面努力减少对方的危机感,降低其受威胁的程度和相互的敌意,给予双方相对充足的反应时间,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战争的行动,从而增大危机的可管理空间。
从朝鲜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到后来一系列危机的和平结局,可以看到中美两国的决策者在处理双方危机中的一条“学习曲线”。双方的行为从力图打赢战争向威慑对手转变,又从威慑对手向共同管理危机转变,危机的可管理空间逐步扩大。但是,管理危机能力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双方已经找到了防止再次爆发严重危机或者更为妥善地管理危机的思路和机制,也不能掩盖双方对以往危机行为和结果的认知差距。
美国应在中美危机中吸取什么教训,是一个重要问题,但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我们在这里思考得更多的是,中国方面在处理对美关系危机中,可以总结出哪些历史经验,以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或者在危机出现后更为妥善地管理,防止其发展为影响中国发展与稳定的重大危机。
首先,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是,中美危机预防与管理中间的首要因素是两国政治关系的基本状况。换言之,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是沟通信息、减少误判、降低冲突、达成谅解的前提。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对内政策,同争取稳定和改善对美关系的政策是一致并且同步的,因此管理中美危机的行为同执行“革命外交路线”的时期有明显的不同。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没有也不会再有毛泽东在发动1958年金门炮战时那种“意在击美”、“有机会就要整美国人一下”的战略意图。中国管理中美危机的出发点是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权益,又尽最大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因为中美关系的不稳定会带来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
但是,中美两国究竟是敌是友还是非敌非友的战略定位,至今不够清晰。(注:关于当今中美关系战略定位的一种分析,参阅王缉思:《美国大选后的外交政策走向与中美关系》,徐敦信主编:《新世纪初世界大势纵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246页。)今天两大国之间所谓“建设性合作关系”,究竟是掩盖对抗性矛盾的一种外交辞令,还是对双边关系现状的一种陈述?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愿景,还是经过双方努力可以达到的长远目标?在中国日趋强大,而美国继续保持其超强地位的历史时期,双方是否愿意实现并且可能实现一种双赢局面?中国希望世界走向多极化,是否意味着它愿意看到以至希望促成美国走向衰落?美国说要战胜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挑战,是否意味着它最终要与崛起的中国为敌?这是关心本国前途的中美战略家们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管理未来一旦发生的中美危机时不能不考虑的政治大背景。
其次,危机时期政府决策部门的相互协调,对舆论和公众情绪的引导,都至关重要。正因为中美战略定位的问题尚未解决,正因为许多人认为中美之间现在就是敌对关系,或随时可能成为敌对关系,或最终一定会成为敌对关系,今后一旦出现两国之间的危机(包括无意中的突发事件),人们所熟知的“敌人意象”就立刻会在一些政府部门、政治精英和公众中被激活,并且通过包括大众媒体在内的各种渠道,影响两国高层对危机的管理。
“敌人意象”被激活,很可能表现为媒体对中美敌对的历史和美国在炸馆、撞机等事件中的行为的追溯和谴责,以及学生和公众要求上街示威游行,要求政府采取更为激烈的抗美行动等等。实际上,根据多次调查,中国知识精英和公众近年来一直对美国和中美关系持相当客观冷静的态度,(注:参阅《环球时报》2005年3月4日发表的调查报告《五大城市民意调查:中国人如何看待中美关系》,http://cul.sina.com.cn/c/2005—03—04/113516.html;另可参阅赵梅:《中国人看美国》,陶美心、赵梅主编:《中美长期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页。)同官方对美政策是基本吻合的。因此,在危机期间“敌人意象”的激活和公众的激愤情绪并非必然,其关键因素在于政府有关部门和主流媒体如何相互配合,对公众加以引导,防止出现政府危机行为受表面上的“民意表达”制约的局面。(注:如果美国决心以中国为敌,挑起重大危机,需要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地应战,当然另当别论。)
虽然中美敌对时期中方的危机决策深受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内政策和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纲的外交路线的影响,但有一个优点不容忽视,那就是毛泽东能够在周恩来等少数高级干部的协助之下,做出最具权威性的决策,并且上下齐心,贯彻到底,基本上不受国内决策过程中官僚政治因素的拖累。中下层干部和普通民众谈不上知情权,而一旦被动员起来,就会自觉地、毫不迟疑地执行所有的决策。在许多情况下,正是毛泽东本人那种非凡的感召力、威望和收放自如的政治技巧,使人们无从发觉中方在危机中所做的妥协,发觉结果同初衷相背离的情况。这种决策过程简单明快、公众信息来源单一的背景,在今天的中国绝不可能再造。当任何未来危机出现时,人们从电子通讯和电视上得到多种不同报道、不同解读的速度,都将大大高于层层传达中央指示的速度。这就更有必要在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特别是对外关系的职能部门同对内宣传部门)、政府同媒体之间,建立相关的危机预警机制和信息传递系统,使最高决策者的意图在第一时间得到忠实的传达和贯彻。
再次,中美危机中的许多实例表明,美方的战略意图、决策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不但复杂,而且常常是混乱而自相矛盾的,因此要在“国家行为人格化”的理性模式之外,寻找对美国危机行为的更合理解释,改进应对措施。
国际危机方面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一个国家的战略家虽然深刻了解本国决策面临的诸多制约因素,却往往倾向于从理性的角度看待对手的危机行为,即假设对手的一切行为都是在全面了解双方意图、能力和手段等重要信息的基础上,根据己方利益的需要,经过精心策划而做出的理性决策。这就是所谓“国家行为人格化的理性假设”。但从被引为“经典案例”的古巴导弹危机,到冷战后的数次中美危机,都并不完全符合这种理性假设。
在美国,虽然危急时刻的权力主要集中在总统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少数成员手中,平时决策中司空见惯的官僚政治斗争可能有所收敛。但是,由于面临时间压力和战争风险,危机管理者往往需要在十分有限的时间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常常面临着“信息泛滥”或“信息不足”、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军事和文职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等一系列障碍。政府与国会的政治争斗和沟通不畅更是经常出现。
回顾给李登辉发放访美签证、炸馆、撞机等事件中美方的危机行为,可以看到许多由决策过程复杂、混乱和内部斗争所产生的非理性因素。根据事后所得到的情况再做综合分析,很难想象美国领导人在允许李登辉访美问题上出尔反尔、北约飞机轰炸中国大使馆和用美军侦察机同中国战斗机相撞,都是当时美国最高决策者基于长远的战略图谋而精心策划的危机。但当时对这些事件的一种解释,是美方故意“测试中方反应的底线”,并且将事件同当时的“中国威胁论”、美国的全球霸权野心膨胀、遏制中国的图谋等战略大背景联系起来,对美方行为的程序细节和技术细节则不做过多描述。实际上,对于对手的决策程序和危机发生的细节了解得越详细,越准确,自己的战略判断就越正确,危机的管理也越完善。
第四,纵观朝鲜战争以来的历次中美危机行为,能够发现双方之间在危机时期的信息传递和直接沟通是逐渐改善的,近年来更有了通过有效沟通防范危机的事例。例如,由于有了在朝鲜战争前期缺乏沟通的教训,中美双方在越南战争期间通过各个渠道达成了避免直接交战的默契,划清了出兵同对方作战的底线。中方在对美方发出信号、沟通信息方面,表现得更为主动和积极。(注:参见李丹慧:《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www.shenzhihua.net.)又如,中国政府对2001年撞机事件的处理,显然从1999年的炸馆事件中吸取了经验,从引导舆论到把握反应的力度都有了改善。中国在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前后对国际危机的处理,也同1999年科索沃战争前后的危机处理形成了对照,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中美关系恶化。更值得称道的是,中国政府准确地把握了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战略重点转移的动向,寻求中美之间在阻遏台独上的共同点,避免了中美之间的重大危机。由于过去的中美危机绝大多数涉及第三方,而今后中美之间的利益重合与矛盾的范围必将日益扩大到双边关系之外,两国在涉及第三方的问题和领域里越来越需要加强沟通,建立互信机制和危机防范机制。
第五,在吸取历史经验方面,无论是在中美战略家和学者的对话中,还是在中国方面旨在“知己知彼”的战略研究中,都有许多工作可做。以1996年的台海紧张局势为例,有一则不断被中方引用的报道说,由于军事演习期间美军指挥机构发现中国出动了多艘核潜艇,美方将已派遣到台湾东边炫耀武力的航母编队后撤了近100海里,以避免同中国海军接触。(注:参阅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750页。)美方则认为,向台湾附近海面派遣航母编队是向盟友和国际社会显示美国决心的必要措施,是履行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是告诫中国大陆不能对台湾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从而防止了危机升级。中美双方对过去危机的认知差距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中国的许多历史文献和教材中,对于中美危机中己方(特别是毛泽东等领导人)“战略上藐视敌人”的论述很多,“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论述看不到或者一带而过,一些读者从中引申出来的印象是,毛泽东比他以后的领导人在对美斗争中更有魄力,更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这种印象,客观上形成了对现行政策的压力。
在中国方面对历史事实的一些阐述中,不准确、不完整的事例也不少。例如,朝鲜战争时期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在1951年5月的一次听证会上指出,如果按照朝鲜战场美军指挥官麦克阿瑟的建议,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将犯重大战略错误。他说:“红色中国并不是一个谋求主导世界的强大国家。坦率地讲,在参联会看来,这一战略(即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引者注)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注:转引自Akira Iriye,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67),p.289.)然而中国的一般出版物一直把这一段名言解释为杜鲁门政府承认与中国在朝鲜进行的战争是错误的和失败的。实际情况是,美国官方从未在出兵朝鲜问题上进行过反思。但是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美国的国内争论至今没有结束。
最后,对于国际危机管理的指导原则和方法,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和“有理、有利、有节”都仍然有指导意义,但这两大原则都是对敌斗争中的原则,是敌方有意制造对抗时的对应原则,是在实力上尚未能压倒敌手时的行动原则。如果中国在对美关系中的指导思想是“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是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避免和化解重大危机,那么就需要对这些原则做出修改和补充,并且从微观上进一步完善预防危机、管理危机的机制。
标签: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论文; 中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