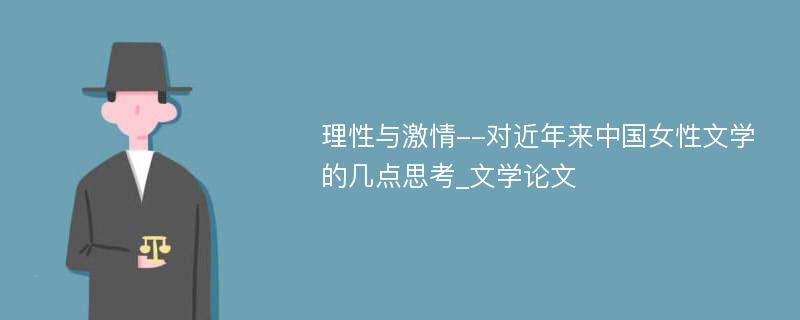
理性与激情——对近年中国女性文学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理性论文,近年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激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女性“浮出历史地表”与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与往事干杯”,接着开始了“致命的飞翔”,然而,飞往何处?中国女性文学向何处去?
一
有必要廓清几个概念。
我之“女性文学”,一般意义上讲,应为女性作家写作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理论评论和文化随笔,等等;严格意义上讲,应当是由女性写作的具备较鲜明或成熟女性意识的女性文本。
我之“女性意识”,含文学和文化两个层面。就文学层面讲,应当是自觉的独有女性视角、女性经验、认识和体验的语言范式;就文化层面讲,应当是以“非暴力”、“同情感”、“平等及和谐意识”等等为主要标志的女性特征,对抗和解构以父权制为主要标志的传统男性霸权文化,建构男女两性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谐·进步”的社会文化模式之意义和追求。
我之“女性主义”,则是指在对抗、解构乃至颠覆男性霸权文化之话语和叙事过程中,一种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女性立场,它不同于西方的“女权主义”,虽兼有社会政治色彩,但其主要涵义是文化的,文学的。
这其中,“女性文学”虽然在许多情况下,因坚持其女性视角而表现为“以血代墨”的所谓“身体写作”,但正如《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红楼梦》《白鹿原》等所有男性写作的被称作“史诗”的作品,他们充分男性经验和个人成长史之屐现,却并不意味着就是展览、裸露男性的“身体”;“女性文学”不等同于“性文学”,亦不是“隐私文学”,更不是以抒写、暴露女性“身体”为目的的文学。恰恰相反,那些以亵渎女性或渲染两性肉体关系、性过程、性场面,旨在刺激和诱发人们生理感官的“色情文学”,正是传统男性霸权文化对女性工具化、非人化、轻侮、把玩、狭妓心态的直接后果。
还应当说明的是,“女性意识”及“女性主义”并不一定是女性的专权,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男性的文化策略,男性同样可以在文化和文学层面上确认之,坚持之;换句话说,争取人类另一半在文化层面上的理解、共识乃至同盟,是女性主义者的奋斗目标之一。并且,“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本身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它是一个文化过程,它随着人类对于主客观世界的认识,对于人类文化的不断开掘,而丰满、完善和成熟;而作为一种概念,“女性主义”正象“女权主义”这个词,将随着更人道、更合理、更完满人类理想社会形式的实现,结束其历史使命。因此,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承认女性主义的某种乌托邦性质,——它先于现实社会政治层面,能够在话语中成立。
二
稍稍留意于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近年文学写作现实的人,都可以脱口说出一长串创作成绩卓著的女性作家的名字:王安忆、铁凝、张抗抗、方方、池莉、残雪、徐坤、徐小斌、陈染、林白、范小青、毕淑敏、迟子建、斯妤、翟永明、蒋子丹、王小鹰、马丽华……,亦可以随意举出一大批作品:《长恨歌》《玫瑰门》《情爱画廊》《双鱼星座》《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暗示》《左手》《出售哈欠的女人》《丹青引》《我爱彼尔》……,她们的名字和作品一再在新时期诸如“新写实”“新状态”“新现实主义”“先锋文学”“新生代”等等文学命名中被反复例举或者独领风骚;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则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从对包括上述作家作品在内的“个案诠释”之体察、感悟,转移到试图建构中国女性文学的理论尺度,从生吞活剥引进借鉴和摹仿西方的名类繁多的女性主义观念理论,发展到终于各就各位,以一种更清醒更科学更切近中国女性写作现实的态度,开始了更健康更自信的女性文学历程。
就女性文学而言,从八十年代关注与写作追求两性平等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方舟”“致橡树”,到九十年代开拓与肯定“与往事干杯”“致命的飞翔”女性“身体语言”的性别经验抒写,到重新对“黄泥街”“黑夜意识”颠覆男性霸权话语的再确认,到“厨房”“暗示”女性立场的困惑、迷失和展望,关注点的变化,证明和记录着女性文学理论与情怀的发展与成长,中国女性文学、女性文学研究之多元话语的格局之存在和其枝繁叶茂,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然而,如火如荼的背景后面隐含着危机,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强劲,一种女性主义或非女性主义的激情,部分掩抑了所有理论建构中不可或缺的理性,隔膜了女性文学与更大范畴对话沟通的关系,加重了现实文化层面的曲解、误会乃至敌视,亦客观丧失了在“人道主义”意义上曾经共同的男性同盟军。星星还在天上,女人的白夜已经开始。
加强理性,加强智性,加强科学性,重建女性话语之意义群落,庄严女性的责任,是丰盛和维护中国女性文学来之不易局面和成果的根本策略。
三
在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非理性的“激情”并非唯女性所独有。事实上,任何性别一方,执着一己的激情的一端,都会把自己引入陷落的泥淖。
首先,在社会政治局面,全社会的长期沉醉于“妇女能顶半个天”“男女都一样”“不爱红装爱武装”乃至“公关小姐”“女强人”之“妇女解放”的神话,把文化等同于社会政治,误认为中国妇女社会政治层面的解放即等同于文化层面的解放,误认为一提“女性文学”,即是两性对抗,是一个性别集团对另一个性别集团的压迫与施虐,或者视“女性主义”是“无事生非”,是“洪水猛兽”;或者以中国农村、政界等男女两性极端的例证,混淆中国“女性主义”文化执着的界限。
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回避本属社会政治层面的中国历史及现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中国女性在政治上翻身是共产党施政的基本国策:政府机构被强制规定纳入一定的女性比例;女性和男性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力,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力,工作的权力,同工同酬的权力,选择配偶的权力,结婚与离婚的权力,并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除了少数官僚阶层,中国的城市男性并没有在经济上与女性拉开距离显出多高的生存优势。因而,中国当代女性较少甚至没有经受封建主义乃至西方某些国家妇女正在蒙受的屈辱和历史,中国的绝大多数家庭呈现的是“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凑凑合合”“其乐融融”的假象,直到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近几年,之假象才被打破,女性因其性别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受到了建国以来最强烈的冲击。“下岗女工”几乎成了一个固定名词,“三陪”“包二奶”“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早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许多陌生的词汇又一股脑涌现出来,并在一些大众报刊变相兜售,甚至出现了以“三纲五常”等封建主义观点质疑中国革命女杰秋瑾的文字。
这里面不乏经济杠杆的作用。有句民谚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女变坏就有钱”,经济地位决定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在以“有闲”和“无闲”标志生存状态的竞争激烈的社会,缠绵绯侧的“爱情”只能是有闲阶层的奢侈品。一个风云于商场每日在看不见的刀光剑影中喘息的男人,会伸手几十万打发一个有碍于生意让他感到累的靓妞;一个时刻挣扎于商海不进则退不生则死被男人视为对手忘记性别的女人,同样也能为绝情一个可能对事业构成伤害死磨烂缠的俊男而割巨金了断。商业化进程大工业社会将人变成机器,阉割扭曲人灵与肉的双重功用,人们耳闻目睹的现实故事远比作家的文字叙事生动甚至激烈的多。
但是,我们在这里强调和想讨论的是,文化的关键作用。因为,正是由于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属性和毛泽东同志生前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使性别的两端面对同一个问题一同走入误区:一方面,是男性一端,尤其是在没有太多政治和经济优势可言为生计苦苦挣扎的部分文化男性那里,由于数十年来始终没能在“妇女解放”这面旗帜下公然“反动”或者“直起腰来”,他们对女性主义的声音不仅质疑甚至敌意,他们对卷土重来的封建主义父权制文化,对其文化最先给女性的打击和规定表现出若隐若现的欣喜;和其感觉相呼应的,是将女性工具化、非人化的文字在市场上时有出现,有时甚至成为热销的“卖点”。另一方面,是女性一端,曾有的历史和激烈的社会变革下,知识女性的反思表现为某种性别激情,新时期文学之初她们几乎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以传统女性“美德”否定既往的“中性”形象的策略,这一选择和否定,应当说,在客观上,或多或少的,成为后来现实中部分女性丧失自我丧失经济双重人格再度沦为男人性别依附的“帮凶”。
乃至我们重新捧读恩格斯“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任何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捧读秋瑾“人生在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女子更须培养学识,求自由,不当事事依靠男子”“恢复女子应享之权力与应尽之义务,实行男女平权,导女界生活与正轨”等等一个世纪的言论,竟不禁升腾起历史轮回文化怪圈的感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远比所有女性主义者想象的程度强大的多!
堪称可贵的,是少数女性书写者和女性主义者,她们以先行者的姿态,始终坚持在没有话语没有立场的性别尴尬之中,苦苦摸索,不屈不挠。她们“突出重围”的努力,除上述我们提到的已经取得的成就,业已取得了积极的经验:女性立场和话语的寻找和建立,远不是女性独有经验、历史的坦露与抒写,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女儿、妻子、母亲这些共同的角色和体验,以及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精神分析等等现成的理论,或者几次、几十次让人耳目一新的释诠所能解决了的。一大批没有经过文化转换的“脑袋”(男性的和女性的),加上商业化进程对人的扭曲,以重建话语为突破点,改变男女两性立场的对抗、隔膜、抵触乃至敌视,非一朝一夕!实践亦告诉女性主义者们:仅仅从性别出发的某些极端的“抗拒阅读”心态,只可能把正在发展的中国女性文学理论建构导入歧途。
四
“幸福”在哪里?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近几年中国富有代表性的女性写作文本,认真倾听由这些文本这些女性发出的声音,不难发现,其中绝少一例是与世界与异性为恶的作品;女性作家几乎没有一例某男性作家因了一只被成千上万只蚂蚁吞噬的雏雀就从此与整个世界“为恶”的意识和人生观;她们声声呼唤的,是美,是爱,是与世界与异性沟通和谐的愿望,她们以笔墨缓解着似乎与生俱来的与世界与异性的紧张关系,她们追求那种似乎永远无法抵达的幸福的彼岸而倍尝艰辛。她们也会以柔软的手绢窒息行将就木的“对手”,并因其不动声色的毒辣而让人毛骨悚然,但你得承认,它是为你所不知的女人世界的女人的“手段”,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战争,在她们那里,因其不流血而笼罩于一片“温情脉脉”之中。她们独有的视角、性别经验告诉人们关于“人”这个亘古之谜长期来不为人知的那一部分,完整着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
比较男女两性文本,同是“偷情”,在男作家笔下常成为一次“艳遇”一次“回忆”一次“智力游戏”或“幸运女神的光临”,在女作家那里则成为“创痛”“黑夜”“爱又如何”或者“生存策略”;同是“婚姻”,在男作家笔下是颠沛流离后的“向往”“温暖”和“避难所”,在女作家笔下则是“失望”“出走”和“懒得离婚”,女作家们以她们独有的性别经验向世界报告,她们对表现于“性别鸿沟”的自父权制以来的男性霸权文化的绝望和愤懑,控诉长久以来由男性霸权文化构造的诸多的神话将她们一再引入误区,伤痕累累的惨痛和失败。当她们以貌似冷静的笔触嘲笑“自我”,解构“幸福”,质疑“婚姻”,藐视“权力”的叙事一再面世,这些女性文本对于人类精神所可能面临的巨大危险的昭示,是多么的富有意味和弥足珍贵!
幸福是什么?
所谓幸福的感觉,那种在海洛因刺激下被称为“肽”的物质,正象海洛因可以把这在文学中一生一世追求的刻骨铭心的感觉浓缩为短暂的一瞬,“海洛因”嘲笑和解构了“人”一样,如果不能转变长期以来女性在父权制男性霸权中心文化下的不平等的失语状态,“幸福”对于男女两性都将因了人类另一半的缺席而不具有真实意义:“幸福”将成为仅仅写在纸上存活于口头上,在话语中游荡的字眼和学问。
东方的《暗示》徐坤的《厨房》蒋子丹的《炊烟为谁升起》等一类作品,不仅表达了中国知识女性对其现实境遇的这种清醒认识,而且表现了近乎形而上的女性立场的困顿与思索。因此,她们的女性文本,是置女性在传统男性文化中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从而取否定旧我涅槃再生的救赎之途。
铁凝的《何咪寻爱记》是执于同一视角的别一类叙事。故事流畅如一则寓言:女主人公何咪因了外界的改变和诱惑以及仿佛与生俱来的不安与好奇,她一次又一次离开(或称“背叛”)她的恋人,却又一次又一次在现实中受挫、被骗、失败;于是,“出走”“归来”成为他们长达数年的情感模式,及至,男人对这模式忍无可忍与另一个女人结婚,也依然未能抵御何咪归来时无遮无拦的彻夜长哭。故事结束,男人的法定配偶如偷了人东西般匆匆逃走,何咪与男人在众目睽睽下紧紧相拥。在这则故事中,一整套传统男性文化关于婚姻、家庭、爱情、廉耻、神圣等等或贬意或褒意的话语秩序土崩瓦解,“没文化”的何咪,因了没有文化的负担,在其追求幸福的人生历程中,之人性的自由,恣意、率真、得心应手。这则女性文本之意义指向十分明显,它跳出女性自怨自艾的窠臼,取“连眼睛也不翻过去”“视而不见”的解构策略、女性立场。它以似貌传统叙事文本的抒写,回避了“小女人”“私小说”“个人化写作”的指称,偷梁换柱般的,在传统男性霸权文化“边缘性”概念下扩张女性的智慧和发现,它以对自然真实人生立场的确认,嘲弄男性文化的尊严和文化女性的忧伤,因此,《何咪寻爱记》对于正在发展的中国女性文本无疑开拓了新的界限与文化视野,有别一番意味。
幸福在哪里?
以寻找和重建女性话语体系为突破口,旨在解构颠覆男性霸权文化的文学努力,正着看,方兴未艾,价值非凡;侧着看,步履维艰,几多辛苦;反着看,藐视经典,大逆不道:
——幸福的彼岸,或者就在脚下,身边;或者,遥不可及。……
五
依旧是先进的西方文明,建立在这种文明之上的宽容与理性,给陷入某种困顿僵持不下的中国女性主义以新意和福音。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理安·艾斯勒名为《圣杯与剑》的人类文化学著作,1993年在中国出版后,至到1996、1997年间,终于引起了中国女性主义者们的真实响应。这本发表后在美国及世界各国强烈反响和高度评价的畅销书,以大量令人信服的考据和事实,说明在父权制社会许多年之前的古代社会,东西方都有过一种没有暴力、更富于人道精神、生态更平衡的社会组织形式,作者称它为“给予生命而不是夺取生命,以权力促进别人的发展而不是压迫别人”之“女性特征”的男女平权的伙伴关系社会。该书的译介者在中文版后记中写道:“作者令人信服地描述了以女神手中的圣杯为象征的伙伴关系文化——社会模式和以男性武士手中的剑为象征的统治关系的文化——社会模式在各方面的差别。有力地证明这五千年发生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虐、独裁、专制,以至人类当前面临的各种全球问题,都同男性至上的统治关系的文化——社会模式有关”;这本被称为“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一再强调,对于史前女神崇拜(而非“母权社会”)时期的文化揭示并不是让男女两性互相敌对,而是要建立一个和谐、和睦、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社会;正如男人能有“女性”行为,诸如非暴力、同情感,女人能有“男性”行为,诸如暴力和战争一样,养育而不是破坏,给予而不是掠夺,和谐而不是压迫,合作而不是统治,等等,女性文化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共同财富”的意义引入女性文学我认为包括几层涵义:第一,正象人类历史上所有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文化遗产一样,女性文化并不因其是由女性所始发和创造就隶属于女性性别集团或具体某个人,它的基本含义是“共享”;第二,女性文学是检索女性文化的一个视角,是人类精神成果的一个部分,是构筑新型话语体系的一个思路和尝试,并且因了其学问的性质而可能是抵达更合理更完满人生境界的文化捷径;第三,女性主义是其文学努力中的一个过程,是一种必须的手段,女性因其自然的性别持有它,仅仅是强调女性在开掘这份人类共同财富的过程中,历史和现实形成的比较充分的话语资格与权力,随着两性真正和谐平等,伙伴文化关系的到来,女性主义将终有一天而归于消亡;第四,对女性文学、女性意识、女性主义的执着和研究,不是女性集团对男性集团,女性对男性的对抗或宣战,她是一种文化行为,是人类能够的智慧向所有尚未破解和抵达的自然奥秘的探索和最后冲击,她的意义不仅是非凡的,而且是深远的,因而是极富前景的。
如许,女作家以人为本执着于人类终极关怀的“超性别意识”写作,就不会再被“误读”为社会行为的“同性恋”,女性主义对非人道的男性霸权文化的解构和颠覆,就会多一分清澄和理性,少一分性别的偏执和激情,女性特征理想社会模式的努力和追求,就会变成全社会的自觉自愿的行动……
没有女性体验的历史,是不完整不真实的历史,与生俱来的性别并不决定后天品种的优劣,建立在人类另一半缺席基础上的“幸福”子虚乌有,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人类的未来不是破坏、污染、压迫、掠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尊重、和谐、平等、互惠的民主伙伴关系。
女性、男性,在确定女性文化是被忽略的人类共同财富的基础上,重建话语意义群落,天下兴亡,人人有责。
——是的,“或者毁灭我们自己,或者改变我们的观念。”
女性之人生,就是女性之责任的过程。
女性之文学,就是女性协调世界实施责任的方式和途径。
“我美丽,因为我温柔。”
“一个人的价值,完全在它自己。”
1998年夏季,我主持操办第四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泱泱过百,人员年龄构成年轻,而且多数是女性,其中,相当部分是正在就读学位的硕士、博士;——我提起它是想说明这样几个事实:一是女性文学在中国在现阶段基本上还是女性的事业,因而它是开放的,有待参与和开发的;二是“泱泱过百”和年轻及人员文化素质较高,说明它是发展的,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因此,承认它,关注它,爱护它,是文学发展的大趋势;我相信,包括本文,所有的为其正名的言说都将会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