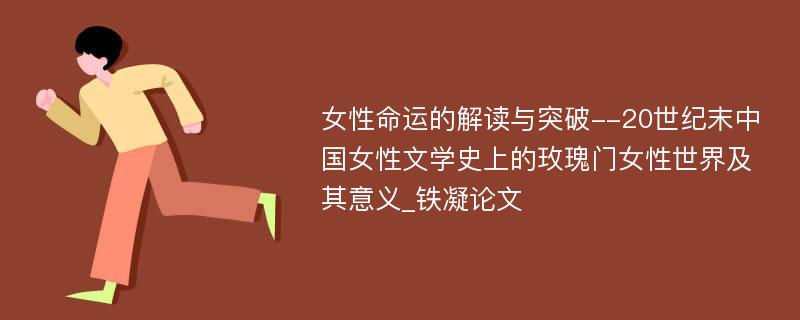
女性宿命的演绎与突破——《玫瑰门》的女性世界及其在20世纪晚期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史上论文,晚期论文,中国论文,宿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207.425 文献标识码 A
从80年代初开始,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终于迎来了繁荣与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文化、哲学思潮的涌入以及西方女权主义文化浪潮的波及,当代女作家们的主体意识空前觉醒和高涨。女性文学在追求“人的自觉”与“女人的自觉”结合的同时,注入了更多的女权色彩,“女性的解放”成了女性文学的重要关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女作家们开始把女人与女人关系的审视融入对男女关系的审视中,使女性审美既具先锋性,又富嬗变性,呈多元发展的态势。一些女作家还把女性之恶作为新的审视点,对女性正负面及其复杂性的认识逐渐深化,对女性人性的思考的穿透力度也日益增强,在拷问社会,“反省自我”的路上有了重大突破。女作家铁凝的首部长篇小说《玫瑰门》正是着力于对女性正负两方面的揭示,无论在表现的广度、批判的力度还是反思的深度上都体现了这一突破。尤其值得人们关注的是,《玫瑰门》不只是单纯表现“恶妇”司猗纹对女性宿命的演绎,而且铁凝还以自己独特的观照方式,以自己对女性世界的深刻领悟塑造了与司猗纹形象相对峙的苏眉形象,并通过苏眉对女性宿命的突破来表达自己对女性宿命的走向和女性解放的关注,从而使《玫瑰门》呈现出在突破之上的超越。
一、宿命的演绎——悲剧的世界
中国封建文化濡染了中国人畸形的女性观念,在几千年的中国大地上,女性世界成了封建文化残酷肆虐的重灾区。封建伦理纲常锁定了妇女的言行空间,也锁定了她们的思想领地,虽然她们努力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却仍然改变不了作为男性附庸的地位。当她们以温良恭俭让受到三从四德肯定的同时,她们作为人的自我独立意识也逐步丧失殆尽,于是,她们本就悲哀的生存格局更被罩上了文化宿命的怪圈。一代代的女人演绎着女人所有的屈辱和悲哀,也把女性生存宿命的悲歌从古唱到今。由于外来思潮的冲激和中国文化思想的历史性变迁,20世纪的中国呈现出女性走出宿命的曙光,一部分女性的精神上开始闪现出“自觉”的火花,但由于历史的惰性和传统文化的强度反弹,这些还显得稚弱的自觉者又被迫退回到自我生命抑制的无奈之中。即便那些自我欲望强烈的女人,因忍受不了这种无奈,而不得不以变态的方式释放这种无奈之后,仍然走不出女性宿命的怪圈。
《玫瑰门》中的女主角司猗纹就是这样的女人。在现代文明的诱惑下,司猗纹也有了一些生命自觉,但她的自觉却仍然不为封建意识所容,最终导致了她的悲剧性人生。对爱的绝望和仇恨使她像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一样,一步步地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这两个处于不同时代的女性的相似命运,表明了女性宿命的历史存在和现实显现。但毕竟司猗纹同曹七巧处于不同的时代,铁凝对女性宿命的感受和把握也不同于张爱玲。新的历史进程和人生际遇赋予铁凝对女性宿命以新的精神体认,因而,司猗纹对女性宿命的演绎也就有了新的显现形式。
爱情和婚姻的不幸是造成司猗纹悲剧的直接原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迫使她放弃爱情,违心地嫁入门当户对的庄家。但她的屈从没有给她带来侥幸的幸福,婚姻让她从此开始了炼狱般的生活。丈夫庄绍俭从新婚之夜就开始了对司猗纹的报复式玩弄和凌辱,使司猗纹最初的一丝不洁之感因此荡然无存。庄绍俭带给她的是屈辱,是性病,是女人最起码的尊严的丧失。好在庄家的衰落给了她转移痛苦和怨恨的机会,不甘人后的司猗纹勇敢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使庄家一次次地转危为安,显示出她作为一个女人难得的坚韧和魄力。然而,司猗纹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脱,她在庄家的孤立无援加速了她的悲剧。她的公婆并不承认她的功劳,从不就儿子的放荡向她表示一丝同情和支持,甚至庄老太爷出于男性可怜的自尊,还在日记里对能干的司猗纹百般诅咒。这样,司猗纹在情感上找不到寄托,在精神上又得不到安慰,物质世界的胜利同精神世界的惨败所形成的巨大反差让她那本就微弱的“自觉”火花终于异化成了仇恨的火焰,她走上了变态释放压抑、以自虐和虐人为游戏的道路,开始向亲人、向社会进行疯狂的报复。
爱的缺乏和饥渴导致了她汪洋恣肆的性欲渲泄。她调动自己全部的能量,同造成她悲剧的罪魁祸首庄绍俭纠缠、较量。对在这纠缠中产生的儿子庄坦,她一直怀着血缘的仇恨冷漠着。治好庄绍俭带给她的性病后,司猗纹以一场恸哭结束了她倍受煎熬的前40年,从此,“在毒水里泡过的司猗纹如同浸润着毒汁的罂粟花在庄家盛开着”,仇恨把她滋润得更加娇艳,也更加狰狞。她决定拿自己的肉体对人生对社会来一次疯狂的亵渎,在月朗风清之夜,司猗纹闯入公公房间,以恶作剧般的乱伦来实现了她的报复。报复的快感让她得到一种变态的满足,她像吸毒般爱上了这种生活方式,不知不觉中,她从受虐者变成了施虐者,成了传统文化压制女性的帮凶,对身边的女性、自己的后代也开始了习惯性的虐待和报复。在文革中,司猗纹丧失了生活的主动权,摆脱街道主任罗大妈一家的监视和欺凌,取得罗大妈的彻底认同成了她的生活目标。在交房子、交家具,对罗大妈百般讨好仍遭白眼之后,司猗纹想出了一个恶毒的阴谋;故意暴露寡居儿媳竹西同罗家大儿子的奸情以威胁罗大妈,她甚至不惜把自己未成年的外孙女苏眉派去充当捉奸的先锋。司猗纹凭着她非凡的精明,也凭着她变态的心理和扭曲的人性,终于从富家少奶奶摇身一变,成了革命群众的一员。
但是,司猗纹狰狞的背后,又有着难得的一点善良和柔情。她在差点成她第二个婆婆的朱母面前,是个无可挑剔的贤慧媳妇。她对初恋情人华致远一生都保存着最真最深的柔情,在调查华致远的人面前,不说对他有丝毫不利的话,甚至临死前还挣扎着去偷偷看他一眼。她这仅存的善对她所有的恶是无尽的讽刺,使我们憎恶她的同时又难免生出一丝同情。
在司猗纹形象的塑造中,铁凝大胆地引入了西方文化中的性爱观念,又巧妙地把传统道德的善与恶都交织在司猗纹身上,逼近原生状态地揭露了她变态的性心理及其隐型文化人格中的道德虚无主义和自渎倾向,从而使司猗纹形象超越了曹七巧形象的单纯恶性发展而更富立体感和现实性。铁凝曾说:“她无时不在用她独有的方式对她的生存环境进行着貌似恭顺的骚扰和亵渎,而她每一个践踏环境的胜利本身又是对自己灵魂的践踏。”(注:引自《〈玫瑰门〉·恳谈录》,转引自盛英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 铁凝篇》。 其它引文均引自作家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铁凝自选集·玫瑰门》。)因此,司猗纹最深刻的悲剧是,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最大的敌人居然成了她自己。司猗纹无疑是在封建文化的长期积淀和濡染下,疯长在文革前后的一朵“恶之花”,她不愧为当代文学女性形象中的“这一个”。然而,纵观司猗纹的一生,她只能以变态的方式对善良、母性的传统女性模式进行报复式的解构,只能以自己的悲剧对女性宿命来一次生动的演绎,她的生存环境和生命过程仅仅是历史文化语境的一次现实显现。她对女性宿命的演绎、对女性模式的冲击仅仅体现出批判性而缺乏建构性,她没有重建女性历史的自觉意识,自然也就无法担当起整个女性解放的使命。
二、宿命的突破——希望的世界
司猗纹折腾一生,最终还是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走进了女性宿命的怪圈。难道女人注定要永远生活在宿命的控制之下吗?女性如何才能在没有光的所在寻到可以突破宿命的亮点?张爱玲对女性悲剧的犀利观察和彻骨感受仅仅表现为一种无奈的揭示;铁凝则不同,历史提供了她对张爱玲作出超越的可能,使她得以通过司猗纹的塑造绝然地反叛传统的同时,又能满怀信心地寻找女性的出路。苏眉对司猗纹充满矛盾的审视和她充满生命自觉的自审,表明作者已将女性的生命意识置于主体地位,使苏眉在精神探索过程中突破女性宿命成为现实可能和历史必然。
在许多评论《玫瑰门》的文章中,司猗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普遍的关注,苏眉却一再地被忽视。的确,苏眉的外在形象不如司猗纹富有立体感,她显得单纯了一点;但铁凝却从精神层面发现并开掘出苏眉形象的价值。从苏眉的精神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试图以精神自觉拯救女性的苦心;从作者塑造这一人物形象的苦心,我们又可以看到作者对女性宿命的历史性感悟和现代性探索。
在文革和司猗纹的双重阴影下,苏眉是被惊吓着一天天长大的。幸运的是,生命力旺盛的舅妈竹西在不知不觉中启示着她,激动着她。如果说,文革和司猗纹让她成天生活在恐惧和颤栗之中,形成了她内在的不安全感和外在的沉默,那么,竹西则及时地给了她缓解那不明不白的生活压力的力量,给了她一方安全宁静的可以自由嬉戏的天空。竹西对生活、对爱的坦诚和热烈激发了苏眉内在的蓬勃的生命力,让她在那幽暗复杂的四合院里开始了生命意识的萌动和跳跃。于是,在苏眉12岁时的那个特别玫瑰的春天,那顶有着生命的娇艳的毛线帽“蓬松了她那板结的灵魂”,她对自己身体的变化感到莫可名状的欣慰,对春天里蓬勃生长的老枣树感到痴迷,她感到有一根不可抗拒的手指在指引着她的灵魂……在作品那欢畅抒情又惶惶不安的文笔中,正在孕育着的是性意识的萌动,生命意识的觉醒。因此,“玫瑰门”寓示着性意识的觉醒开放之门,生命意识的突发之门,也正是女性突破宿命走向希望的必经之门。苏眉正是靠着生命意识的觉醒,开始了自己充满希望的生命轨迹的建构。
作品中有“5”的章节是苏眉灵魂和精神的对话。 这六节对话是在成年苏眉和幼年眉眉之间展开的、是苏眉在向眉眉剖白一切,展示幼年眉眉对生活的一切惶惑和不解以及成年苏眉对女性宿命、人性本质的探索和穿透,完成成年和幼年不同意识的交流,使幼年眉眉和成年苏眉在心灵层次上达成了统一。六节对话通过苏眉对谎言、真实的深切体认,对人性本质的探索及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表达了苏眉对女性宿命的深切感悟,也刻画出苏眉的精神形象及突破女性宿命的心路历程。
在苏眉经历了那个特别玫瑰的春天,有了生命意识的萌动之后,苏眉在对话中是这样问眉眉的:
“你是在哪一夜被惊醒的?哪一夜粉碎了你又完整了你使你想粉碎这世界再将它完整?
为什么你愿意在树梢上行走?也许那不是行走那是一种擦着树梢的飞翔一种天马行空的热望一种遨游生命的苍穹的狂想。
你是在哪一夜被惊醒的?哪一夜告诉了你如果这是世界,那就在里面生活吧。
你终于走到里面去也可以说你终于走到外边来。面对一扇紧闭的门你可以任意说,世上所有的门都是一种冰冷的拒绝亦是一种妖冶的诱惑。”
司猗纹对女性宿命的演绎杂和在疯狂的文革中,无疑过早地“粉碎”了苏眉的童年世界,但这“粉碎”又促成了苏眉生命意识的觉醒,“完整”了她早熟的女性世界,使有了生命意识和女性自觉的苏眉走上了积极突破女性宿命重建女性历史的道路。如果说,“玫瑰门”,即女性突破宿命走向解放的必经之门,对变态的司猗纹是冰冷的拒绝,那么,它对觉醒了的苏眉就是妖冶的诱惑。在这妖冶的诱惑下,苏眉依靠那单纯美妙的真人体模特,终于改变了在文革中被强行灌注在无意识中的画领袖像的“特异功能”。这并不仅仅是苏眉绘画轨道的改变,这还意味着她人生轨道的改变,意味着她开始了绝对不同于司猗纹的另一种人生。
值得一提的是,铁凝同苏眉一样,文革时曾在北京外婆家过了几年寄居生活,她们两人的精神追求和心路历程也应该有着某种对应和同构。因此,我们可以把苏眉看作铁凝的艺术化身。六节对话中,铁凝对苏眉进行了毫不讳饰的精神剖析,也最大限度地表达了自己的主体意识,表达了对传统文化,人性负面的强烈批判,从而对司猗纹的形象也作了间接的批判。由苏眉推怀孕的母亲所找的借口,作者意识到人类的成熟“掩饰了卑劣也扼杀了创造”,在真实与虚假之间苦苦思索之后,苏眉发现撒谎才是人类后天不可逆转的捍卫自己的本性,而真实往往是难以被相信,难以交流的。然而,苏眉没有因这些人性的负面而沮丧,她抗拒着谎言和虚假,执着地追求着真善美。当她在草原写生时,认识到人的存在不过是个瞬间,唯有生命过程的灿烂辉煌才能最终超越死亡这一永远的悲剧。于是,她不像竹西或苏玮那样,幻想通过“绝育”来掐断生命,来斩断女性宿命的锁链。她明白女性的命运靠“绝育”是无法改变的,这只是软弱的拒绝和消极的抗议;女性必须直面自己、反省自己,敢于同既定的文化宿命抗争,这才是女性自救和重建女性历史的关键。她毅然赋予女儿以生命,正显示出她对女性宿命的深刻体认,对女性解放的坚定信念。此时,我们可以说,苏眉终于挣脱了司猗纹所演绎的女性宿命的阴影,真正实现了她对女性宿命的尽可能的突破,并且在《玫瑰门》的悲剧女性世界里构筑了一个希望的女性世界。
三、演绎到突破——宿命的走向
从对司猗纹形象和苏眉形象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玫瑰门》的女性世界是一个悲剧的世界。司猗纹苦心积虑地从报复中获取快感,却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没有意识到女人所处地位的屈辱和悲哀,她那被欲望所支撑着的,由清纯少女沦为变态恶妇的惨烈人生最终没能逃出女性宿命的怪圈。同时,《玫瑰门》的女性世界又是一个希望的世界,苏眉有着清醒的生命意识和女性自觉,她对女性宿命的突破已给司猗纹的悲剧世界带来一点亮色和一线生机。但是,这两个世界并不是遥遥相对、互不相干的,而是通过苏眉同司猗纹的纠葛相互纠缠又相互较量,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
可以说,影响苏眉一生最深的是司猗纹,苏眉对生活的审视是以对司猗纹的审视为基础的,她一直都在思索自己对司猗纹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她们婆孙俩7年相依相伴的生活中, 既有司猗纹对苏眉的种种压制、利用和暗暗的欣赏,又有苏眉对司猗纹深切的恨和不由自主的爱。
“她跟她第一次见面就不愉快”,苏眉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她那年轻漂亮、雍荣华贵的外婆,她心目中的外婆应该是像姨婆那样的,宽厚、仁慈,有着温暖厚实的胸脯。真正让她恨司猗纹的,是司猗纹对她的监视、出卖和肆无忌惮的利用。司猗纹的阴谋让她亲眼目睹了竹西和大旗的奸情,导致了她对司猗纹最深切的恨,也迫使她毫不犹豫地带着妹妹逃出了北京。然而,“每逢婆婆把外孙女激得走投无路她可以生出掐死婆婆的动机;但当婆婆走投无路时,这外孙女又愿意以自己的存在让婆婆获得安慰。”苏眉的早熟和善良的天性让她挣脱了平日对司猗纹的恨,在司猗纹被罗大妈打击之后,能体贴入微地照顾她、理解她,甚至不由自主地爱着她。正因这不由自主的爱,使苏眉成年后又不由自主地回到了她曾逃离的地方。面对司猗纹那被欲望滋润着的光华如初的脸和即将腐烂的躯体,面对司猗纹额上那记载她一生不幸的新月形疤痕,苏眉更多的是对司猗纹强盛生命欲望的本能感动,对她悲惨一生的同情和理解,甚至还有对冥冥中操纵女性的宿命的隐隐领悟和现实感受。
在分析苏眉同司猗纹的纠葛时,不能忽略的是她们之间那可怕的相似。“她不仅仅是婆婆的十八岁,她连现在的婆婆都像”。她们不仅外貌相似,连行为习惯也相似。苏眉出于对司猗纹的厌恶,故意克服着她们之间的相似,但她一次次地矫正自己后,又一次次地复原着自己,她们之间有一种被迫的亲近。铁凝让苏眉展示出司猗纹纯情的少女时代,引起司猗纹对苏眉的暗暗欣赏,但昔日自我的再现对畸变了的司猗纹是无情的否定,这又使她对苏眉暗含嫉妒和仇恨。而苏眉在司猗纹的变态人生和悲剧命运的震撼和启迪下,更深刻地认识到女性受制于宿命的绝望、悲哀和女性寻求解放的迫切性,也更清醒地认识到女性宿命的完全消解、女性解放的真正实现还是路途迢迢、满地荆棘。由此可见,铁凝写她们的相似不是一种偶然,而是要通过这种外在的相似强调她们在精神本质上的差异,揭示出这两种女性世界之间的对峙和承传的关系,表现女性宿命从演绎到突破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具体走向。因此,苏眉可以说是《玫瑰门》中潜在的主角,与司猗纹一样是《玫瑰门》的女性世界中不可缺少的支柱。铁凝通过苏眉形象,把女性在《玫瑰门》中毁灭的现实同女性解放的将来结合起来,以历史性的观照呈现出女性宿命在今天的发展态势,从而把女性宿命的历史本质和现实状态生动而又立体地建构起来,凸现了“玫瑰门”的象征意蕴。正是在这一点上,《玫瑰门》实现了作者的自我,也实现了在表现女性负面、揭示女性宿命的历史性题材上铁凝所作出的现代性超越。
女性宿命从演绎到突破的过程所呈现出的具体走向表明女性的解放是历史的必然。虽然女性解放的真正实现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我们已在苏眉身上看到了女性解放的希望之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苏眉突破女性宿命所呈现出的亮色必将激励更多的女性走上突破女性宿命、寻求女性精神解放的道路。或许,苏眉刚出世的女儿狗狗,也不再是女性宿命的又一轮循环,而是女性冲破社会藩篱和自身局限,实现消解女性宿命、重建女性历史这一艰巨任务的生力军。
回溯20世纪晚期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状况,我们知道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最初,随着人的解放出现的女性文学,表达社会理想和对一种新的人际关系的渴望,这和男性写作基本一致。如戴厚英的《人啊,人》。张洁的《方舟》是女性写作第二个阶段的起点,也是20世纪晚期中国女性文学的真正起点,妇女解放问题从人的解放问题中抽离出来,妇女问题从此成为女性写作探索的重点。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初出现并活跃至今的真正个人化女性话语时期,以陈染和林白为主要代表。
铁凝的《玫瑰门》于1988年9月面世, 这部小说告别了她早期小说的清纯和诗意,也走出了张洁小说《方舟》中男女性别对抗的模式,增强了对女性缺陷的自我审视和批判意识;独特的女性视角使《玫瑰门》呈现出女性世界的复杂和女性人性的本相。与张洁相比,铁凝的意义在于她表现了女性肉体的觉醒,以空前的胆识切入女性原欲世界,从性的角度考察女性本体,从而对女性的探究也就上升到了性心理层次和潜意识层次。这是个划时代的标志,是女性真正长大成人,面对性别自我,寻找女性出路的标志。因此,《玫瑰门》对20世纪晚期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的到来,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铁凝以性为视点的新观照方式和女人味极浓的叙事口吻无疑极大地影响了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个人化女性写作。铁凝对女性人性的拓展、对女性宿命的沉思以及对女性解放的呼唤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尤其在揭示女性欲望、探讨女性价值方面为90年代女性文学的发展作了功不可没的铺路作用。
此外,《玫瑰门》在女性宿命的发展形态上所作的思考和把握,也为女性文学实现女性解放的目的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虽然《玫瑰门》中没有直接提出妇女解放的问题,但司猗纹的变态人生和苏眉的精神自觉传达出的却正是妇女必须寻求自我解放的意味。苏眉虽然对女性宿命有了个人突破,她在作品中显示出的亮色虽然动人,也可以部分地唤醒尚处沉睡状态的女性世界,但还不足以与整个女性宿命抗衡。苏眉在突破女性宿命的过程中也感到疲惫和无助,甚至幻想回到母亲的子宫来逃避这种势单力薄的抗争,苏眉的女儿狗狗额上居然有“产钳”这一社会器械文明留下的如司猗纹般的新月形疤痕。这说明,除了女性自身的觉醒外,女性的真正解放还有赖于她们所置身的人际世界精神结构的改良和重建,还有赖于整个社会文化心理的良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