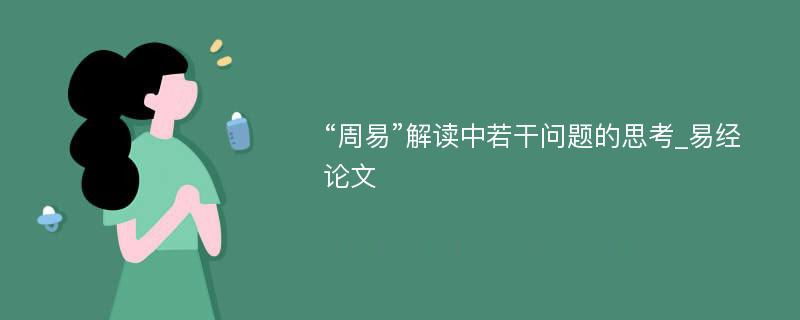
《周易》诠释若干问题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3)04-0373-07
《周易》作为中国诸经之首,二千多年来,诠释文字难以计数。然而,今人对《周易》的诠释仍然见仁见智,人言人殊。《周易》诠释的分歧涉及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如何评判《周易》的本质;二是如何正确处理象数与义理之间的关系;三是如何准确把握《易传》在诠释中的参考作用;四是能否用西方文化作为价值标准诠释《周易》。
一
《周易》这一诠释对象,究竟应该置于何种语境之中,才能保证诠释的准确有效性?
今人使用“《周易》”这一概念,往往与《易经》、《易传》混淆。其中之一,认为《周易》即《易经》;其中之二,《周易》包括《易经》、《易传》两部分。所谓的“狭义”与“广义”之分。现在看来,这两种说法都是有问题的。首先,《易经》是“上古三易”的总称,包括夏代的《连山》、商代的《归藏》、周代的《周易》。以前曾一度怀疑《连山》、《归藏》二易为子虚乌有,因而有《易经》即《周易》的说法。现在,我们从荆州王家台秦墓中发掘到的竹简中获悉确实存在《归藏》一书,而且其中大多卦名与《周易》一致,由此表明先人关于古代“三易”之说并非虚妄之辞;《周易》与《易经》便不能再视为二名一实。《连山》、《归藏》、《周易》分别为夏、商、周三代的《易经》,诠释《归藏》佚文,应将其置于商代背景之下;诠释《周易》,应将其置于周代背景之下。作为春秋末,战国初、中期文化背景下的《易传》,虽为《周易》的首次诠释,毕竟与《周易》不同,不应将其视为《周易》的组成部分;李镜池说:“《周易》分‘经’和‘传’两部分,内容性质有很大的差别。”[1]这种所谓《周易》广义之说,实属不妥。
《周易》即周代的《易经》,与《易经》、《易传》有联系也有区别。本文所说的关于《周易》的诠释,便是关于周代《易经》的诠释。
《周易》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这是决定将之置于何种语境之中加以诠释的关键所在。综观《周易》诞生以来的三千年间,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思想家似乎都对《周易》有所研究,都从《周易》中汲取营养。即便象明代的心学家,也都乐此不疲。但是,到了近代尤其现代,《周易》的学术地位急剧下降,不仅多卷本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全无《周易》的地位,而且所有的《中国哲学史》专著和教科书中,也仅仅将《周易》作为《易传》的附属品稍事提及,作为“中国古代思想的没落倾向”加以批判。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认为《周易》是一部占筮书。
根据最近30年的考古工作的新成果推断,《周易》中的符号系统即其六十四个卦象的前身,是数字卦;数字卦则直接产生于占筮。《连山》、《归藏》的具体运作情况,我们无法揣知,《周易》诞生之后的早期,确实与占筮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左传》、《国语》中记载有二十几个筮例,其中公元前七世纪的筮例,绝大多数是通过占筮获得相应的卦象、卦爻辞,进行决疑解难的推论。
由于有了这些历史的记载,认为《周易》是一部占筮之书的观点,便有了充足的理由。由此确定,卦爻辞是占筮的记录,吉、凶断语是“贞占”之辞,也便顺理成章。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易学专家发现《周易》卦爻辞的构成并非如此,其作用也不是为了满足占筮活动的需要。我国现代著名易学家李镜池在上世纪30年代时认为,“我们相信《周易》是卜筮之书:其起源是在于卜筮;其施用亦在于卜筮。”“我对于《周易》卦、爻辞的成因有这样的一个推测,就是,卦、爻辞乃卜史的卜筮记录。《周礼·春官》说:‘占人……凡卜筮,既事则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所占一定有一爻数占的,因而有数种记录。到了岁终,就把所占的各种记录汇集比对,而计其占之中否。所以卦、爻辞中,很有些不相连属的词句,这不相连属的词句,我们非要把它分别解释;若硬要把它附会成一种相连贯的意义,那就非大加穿凿不可。”[2]30年之后,李镜池对《周易》卦、爻辞的诠释已经有了重大变更。他在完成于1962年5月12日的《〈周易〉的编纂和编者的思想》[3]中写道:“《周易》的卦有不少是内容有组织联系的,并不是毫无系统的资料杂抄,每卦有它的重点,讲一个问题。”“由于每卦有一个中心问题,有内在联系,所以我们研究它,首先要找出它的中心问题,内容思想,不能孤立地本着一条一条卦、爻辞,或摘引个别辞句,随便解释或阐发其意义。”甚至还说:“《诗经》是抒情的,而《周易》是思辨的,思辨的著作,尤其值得我们去分析其中的哲学思想。”
对于卦、爻辞价值评判的这一重大转变,李镜池在同一年写作《周易卦名考释》时,写了一段补记:“最近写《周易通义》一书,才明白卦名和卦、爻辞全有关系。其中多数,每卦有一个中心思想,卦名是它的标题。”5年之后的1967年4月15日,李镜池在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再次表示:“据我的研究,《周易》是有组织体系的著作。古今说《易》者还没有注意到此点,但此点不明,对卦爻辞就很难理解,理解了也不一定对。”[4]
李镜池是少数几位毕生注力于《周易》阐释的前辈学者。他的上述思想转变,对于我们今天准确阐释《周易》本义,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周易》性质的重新确认,直接影响到在诠释《周易》时将其置于何种语境之中;对于《周易》卦、爻辞尤其是吉、凶断语的诠释,也就两种模样。如果把《周易》置于占筮书这一语境之中加以诠释,吉、凶断语就是一种“贞占”之辞;如果把《周易》置于以类比为其特点的思维工具书这一语境之中加以诠释,吉、凶断语就是一种关于某类事物情况的价值判断。
例如,《比》卦的卦辞:“比,吉,原筮,无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意思是说,人与人之间相亲相助必然吉祥,即便占筮问讯,也必大吉大利,不会有错。但是,如果这种相亲相助不是出自真心,而是因为看到别人都在相亲相助,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才违心地附和上去,其结果就会凶险。这一卦的初六、六二爻辞对“有孚比之”、“比之自内”亦即真诚的、发自内心的相亲相助作出了“无咎”和“吉”的评判和肯定。《临》卦中的初九、上六爻辞,通过“吉”、“无咎”的断语,对以真诚、敦厚之心治民的行为作出了肯定,而六三爻辞“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也”,则对虚情假意哄骗百姓的行为作出了否定。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唯《谦》卦的卦、爻辞,都是“吉”、“无不利”的断语,体现了《周易》作者对于谦逊美德的推崇。
通过卦爻辞与判断语之间关系的考察分析,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周易》作者的价值取向。整部《周易》的卦爻辞及其吉凶断语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是《周易》几千年来帮助人们思考问题、指导行动方向的重要功能。设若将《周易》视为占筮之书,将其置于占筮语境之中加以诠释,不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玄之又玄失却方向。
《周易》诠释中的语境问题,还有更深层面上的把握。如果说,将《周易》置于以类比为特点的思维工具书这一语境之中,将吉、凶断语视为一种价值判断加以考察,还不能保证《周易》诠释的准确有效性。这是因为,这样的语境定位还只是一种整体性定位。《周易》诠释还应包括下一个层面亦即每个重卦的语境定位。《周易》六十四卦分别拟象六十四种事类,因此,每一个卦象及其卦、爻辞,都处于一个特殊的语境之中。不仅所处位置相同的爻象所含之义不同,而且相同的卦、爻辞,因为语境不同,释义也就两样。例如,同为初六爻,由于所在卦的其他六个爻的阴阳情况及其阴阳爻所处位置的不一致,对初六爻象含义的诠释也就不一样;这种不一样的意义,也通过该爻象相应的爻辞尤其吉凶断语予以展示。例如,《升》卦的初六爻,与《井》卦的初六爻,相邻的第二、第三爻都是阳爻,所对应的第四爻都是阴爻,仅第五爻阴阳不同:《升》的第五爻为阴爻,《井》的第五爻为阳爻。然而仅此一爻之别,形成两个不同的语境:《升》为地下之木,形成木从地下生长、茁壮成长的“升进”语境;初六虽弱小,且处于最底层,然而如同幼小之苗,破土而出是其本性,也是必然的趋势。《升》的初六爻辞:“允升,大吉”,也正揭示了这一爻象的本义。《井》为水下之木,形成木桶入水、井水上升的语境:初六爻以阴居于井底,如同井底之泥,积之既久,人禽共弃。所以,《井》的初六爻辞说:“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总之,我们不仅要对《周易》这部书作出准确的语境定位,还要根据每一卦的特殊语境,对《周易》的卦、爻象及其卦、爻辞进行诠释,才有可能避免误诠的发生,才有可能接近《周易》,撩开其神秘的面纱,一睹真容。
二
《周易》作为一个以类比思维为特点的推理系统,主体是卦爻符号系统,卦爻辞是对卦爻符号的例说。象与辞之间的关系,近似于西方传统逻辑中六十四种逻辑式与其例说之关系。但是,由于《周易》的推类特点,卦爻符号不是纯净的“空架子”,卦爻辞在类推中的作用也远比“三段论”中的例说来得重要。
在二千多年的易学研究史上,关于卦爻符号(“象”)与卦爻辞之间关系的诠释,有两家精彩之笔。战国时期的《易传》作者,首开这一诠释记录: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
爻者,言乎变者也。
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而舞之以尽神。
初辞拟之、卒成乎终。
《易传》作者认为,在卦象之后系之卦辞是为告诉人们关于卦象所蕴含的吉凶情况;系之爻辞是为了卦象所反映的对象的变化情况,其中初爻之辞拟成事物的开端,上爻之辞说明事物的最后形成。
另一精彩之笔是魏晋玄学旗手王弼关于言、象、意三者关系的诠解: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略例》)
王弼从言、象、意等三个层面上诠释《周易》:言亦即卦爻辞产生于卦爻之象,其功用是“明象”,即对卦象所蕴含的意思加以说明。因此,当人们通过卦爻辞懂得了卦象之后,便应该将卦爻辞忘掉。如果心胸之间仍然记着那些卦爻辞,那就说明还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卦象。先人拟立卦象的目的是反映事物情况的意义,亦即事物情况发生发展的规律、道理。同一类事物情况的意义,可以用同一个卦象表示。当人们通过卦象懂得了它所象征的意义之后,便应该将这个卦象忘掉,而应记住它所象征的意义。如果不能将这个卦象忘掉,就说明对于它所象征的某类事物情况发生发展的规律性道理还未真正把握。王弼还特别指出,那些“明象”之辞都只是一种例说,不可被辞所拘,影响对卦象普通意义的理解。他说:
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质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以纪矣。(《周易略例》)
这段文字,是“得象忘言”观点的继续,认为对卦爻辞的理解,应该注重于譬喻背后的“义”,不可就事论事,仅仅根据卦爻辞所涉及的内容去狭隘地理解卦象的象征意义。
“象数派”与“义理派”的对垒是《周易》诠释健康发展的一大障碍。象数研究走向极端,无视义理研究的合理成果,无视《周易》古经的哲学本质;结果是在卦象之外别生种种枝节,使本来古奥难解的《周易》更加玄之又玄、神秘莫测,迷漫着浓重的占筮迷信色彩。“互体卦”便是一例。按汉代易学家的诠释,六爻卦体除了可分析为上、下卦(或曰内、外卦)之外,还可根据二爻至四爻、三爻至五爻构成两个三、四爻相交的“互体卦”,并以此诠释《易传·系辞》中的“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三与五同功而异位”等文字。不仅如此,汉代易学家还发明了“四面连互”、“五画连互”等互体卦。由于“互体”、“连互”的衍生,使得每一个六爻复卦出现了六种结构形式。这种“互体”、“连互”的诠释并非《周易》创始者的原意,是象数派对《周易》的一种误读。
象数派在诠释《周易》时虽有不少明显的误读,但是他们从卦象中努力寻找诠释卦爻辞的根据的方法,还是应予肯定。并且,他们运用这一方法对不少令人费解的卦爻辞作出的解读,也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是《周易》诠释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义理诠释是解读《周易》的一项重要任务。尤其是当我们确认《周易》的本质不是占筮而是以类比为特点的思维工具书,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书之后,解读《周易》的中心应在其义理而非象数。但是,《周易》的义理诠释决不能离开象数,尤其是处于诠释的第一阶段即对卦爻辞的解读时,一旦离开象数,就会迷失方向。因为,每一个卦所以能造就一个特殊的语境,就在于每一个卦都有其特定的象数构造,一旦离开了这一个特殊的语境,卦爻辞的解读尤其是释义就会缺乏明确的语境依托而发生歧义,陷入“流而离本”的变味状态,误读乃至错读也就在所难免。
由于象数派与义理派之间的“相轻”,未能很好地吸收对方的长处,因而诠释工作往往难以尽如人意,难怪清初学者顾炎武要发出“尽天下之书皆可以注《易》,而尽天下注《易》之书不能以尽《易》”的感叹了。“观其象玩其辞”,无疑是准确诠释《周易》的正确方法。只有象数与义理的结合诠释,才能准确把握和完整体现《周易》所蕴含的丰富思想。
三
虽然顾炎武有“尽天下注《易》之书不能以尽《易》”的感叹,但在汗牛充栋的诠释著作中,还是有不少可观之作的。其间最成功的一种,就是被称为“十翼”的《易传》。《易传》的问世,使众多学子能基本读懂《周易》。在二千多年的易学史上,这是最成功的一次诠释,在此之后的《周易》诠释,都以此为根据;今人讲《周易》,往往也将《易传》列入其中,形成了所谓广义《周易》的观念。
《易传》在诠释《周易》中的作用是任何一部著作都无法取代的。《易传》对《周易》的诠释阐微,充分发掘了《周易》中潜在的智慧,对中国文化尤其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起着极其深刻的作用,以致有人认为正是《易传》的问世,使《周易》由占筮书转变成为哲学书。在众多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专著或教科书中,更是只谈《易传》而不谈《周易》。
我们并不否认《易传》在今天的《周易》诠释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正因为如此,对于这部诠释著作更要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评判,找出其因时代等局限所造成的失误,以免以误诠误。
其一,关于“忧患意识”的误读。
许多学者都认为《周易》中充满着忧患意识,究其原因,乃《周易》作者的时代、个人经历使然。其实,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过忧患的历史;更有一些身处忧患之境的志士,将忧患当作“寻常事”,写下了“留得豪情作楚囚”之类充满乐观精神的诗篇。因此,在忧患的年代、忧患的处境中写下的作品,与作品有无忧患色彩,并无必然联系。
认为《周易》充满忧患意识,肇端于《易传·系辞》中记载有孔子的一句话:“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这本是一句猜测性的疑问之辞,而《系辞》作者却由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演绎: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王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始终,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系辞》凭借“衰世之言”这四个字,推测《周易》制作时间可能在“中古”,《周易》作者可能处在忧患之中;并进一步以“中古”推测“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以“忧患”推测“当文王与纣王之事”。从这些推测性的前提出发,得出了“是故其辞危”,乃至“惧以始终”亦即危惧忧患之词贯穿于《周易》始终这样一个结论。司马迁关于“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说法,正是从《系辞》这两段猜测之辞得出的结论。
《周易》是否真的是周文王囚于羑里期间所写这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周易》是不是如同《系辞》所说的那样,是一部“惧以始终”的忧患之作?
《易传》中,记载有孔子的一段语录:“危者,安其往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粗看这段文字,似乎满怀忧患意识,其实不然。孔子仅仅是根据《否》卦的九五爻辞“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而生发的议论,从正反两方面阐述危与安、亡与存、乱与治这三对矛盾的辩证关系,体现了古代哲人对于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处处蕴含着这种朴素的辩证思想,通过每个卦中的六个爻的自下而上的位置变化,既有从吉到凶的辩证分析,也有从凶到吉的辩证分析。不仅整个卦的发展规律是如此,而且爻的内部,也往往蕴含有吉凶转化的辩证因素,大致可以分析为三类情况:
一是按爻位及上下爻之间的关系,本来的不利因素被淡化乃至消失,这一类情况的断语以“悔亡”为标志。例如:《艮》卦六五卦,以阴爻居阳位而不正,本应有后悔之事,然而它又处在上卦的中位,有中庸德性,象征一个人虽处非位状态而能中肯待人,这样,后悔之事也就能够避免发生。所以,六五爻辞说:“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二是本来凶险的境遇,在发展过程中向着吉利的方向转化。这一类情况,比第一类仅仅是消灾的转化,更富有积极进取的精神。例如,《需》卦上六爻,不仅以阴居阴而阴柔乏力,而且处在《需》卦的极点,力与高位不相协调,因此身在上卦“坎”即险陷之境而不能解脱。但是,它与刚健的“九三”阴阳相应,只要“上六”保持其柔顺本性,恭恭敬敬地对待地位比较低微的“九三”,就能取得“九三”及其同类(上下两阳爻)的全力援助,所以爻辞说:“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三是本来吉利的境遇,在发展过程中向着不利的方向转化。例如:《小畜》卦上九爻,象征积累的极端,因而蕴含着向反面转化的趋势。爻辞便以积云过度便会成雨、积德走向极端便成虚伪,妇人的贞操一旦强调过度也会走向反面,月亮一旦近圆便会向着亏缺转化等一系列的譬喻,阐述了本为好事的积累一旦走向极端便会向着反面转化成为坏事的普遍规律:“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凶,月几望,君子征凶。”
在上述三类转化中,第二类即由凶转化为吉的内容为最多,第三类即由吉转化为凶的内容为最少。并且,在《周易》六十四个卦辞三百八十六个爻辞(包括乾、坤的用九、用六之辞)中出现的凶、吝、悔、厉一类断语有九十余处,吉、利、亨、无咎一类断语则有二百数十处,亦即言“吉”断语较言“凶”断语多出数倍。由此可见:《周易》卦爻辞中确有由吉而凶的忧患之言,但其目的在于揭示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而同样用于展示事物发展辩证规律的由凶而吉的卦爻辞则更多。后者展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向虽然与前者相反,但是所要揭示的事物发展规律的目的则一样。因此,“忧患意识”并不是《周易》的主要倾向,更不能说《周易》是一部忧患之作。《周易》中言“吉”之处远远超过言“凶”之处,这对于先人决疑解难、增强艰苦奋斗的信心,鼓舞战胜困难的勇气,起着十分重要的心理作用和积极行动的指导作用。正因为如此,《周易》才有历数千年而不衰的生命力。
由于《易传》作者片面地考察了由吉转凶的卦爻辞,因而误把辩证思维方法当作忧患意识,以致影响了后来的易学研究,干扰了对《周易》辩证思维方法的正常解读。
其二,关于占筮的渲染对后世诠释者的误读影响。
据文字记载,早在公元前603年,就有人不以占筮而直接援引《周易》卦爻辞推论吉凶。到了孔子生活的早期,这种直接援引卦象、卦爻辞进行预言和论说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孔子对于《周易》的兴趣不在占筮而在义理,他的“韦编三绝”显然是对《周易》义理的研究,而不是对“推蓍蹈龟”的练习。然而,《易传》尤其《系辞》对《周易》的诠释,却仍充满了占筮迷信的色彩。
《易传》的这一重大失误,根源于对先贤思想的误读。《彖》中有这样一句话:“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言必引“子曰”的《易传》,显然没有真正理解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没有认识到孔子的思想体现了对“神道”的淡化与对“人道”的重视这一特点,于是便千方百计对子虚乌有的“鬼神”进行探索:“精气万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系辞》)。把占筮与对《周易》的象数与义理的研究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将占筮视为君子的行为指导:“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将占筮定义为“极数知来之谓占”,视为认识事物的最高明的方法。为此,还不厌其烦地将占筮方法作了详细的叙述。
《易传》推崇占筮、渲染迷信的重大失误,助长了春秋末期以后渐渐淡化的卜筮风气,因而遭到了有识之士尤其哲学家们的批评。荀子认为:“相阴阳,占祲兆,钻龟陈卦,主攘择五卜,知其吉凶妖祥,伛巫跛击之事也。”[5]企图通过搬弄蓍草而决定自己的行动,其结果不会“吉”反而“凶”。他举例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霁,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6]事物的吉凶祸福,有其必然的规律;认识了这些规律,就能推知事物的发展趋势和最终的结局,而无须卜筮问神:“以贤易不肖,不待卜而后知吉;以治伐乱,不待战而后知克。”[7]荀子的结论很明确:“善为《易》者不占。”[7]
尽管有荀子这样的大思想家轻视乃至反对占筮,由于《易传》的影响,占筮在一定范围内依然相当活跃,尤其宋代理学家对此表现出空前的兴趣,朱熹不仅总结出一套占筮推理规则,还设计了一套祷告神灵的占筮程序。《易传》的这一失误,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关于《周易》思维方法的诠释,阻碍了我国科学思维方法的发展。
对于《易传》的上述两点失误,今天诠释《周易》时应该视为前车之鉴。
四
20世纪以来,中西方哲学与文化的比较颇为热门;用西方哲学诠释中国古典哲学原著,成为必做的一门功课。然而成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有人疑惑:用西方哲学理论诠释中国哲学原著,是否合适?事实是,不管合适不合适,许多中国古典哲学原著及其作者的思想,已经甚至反复地被这样诠释了,并且在西方哲学的坐标上,找到了他们所处的位置。例如,按照冯友兰的诠释,《老子》的思想被安置于“客观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庄子》的思想被安置于“主观唯心主义体系”;《易传》也被安置于“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所幸《周易》被近现代学术界一直视为占筮书而未曾正式列入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门墙,因而也未曾以西方哲学理论为解剖刀将其剖析并安置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坐标之上。
但是,当20世纪80年代以来“周易热”的兴起,诠释《周易》的著作不断问世,《周易》在越来越多人的眼里不再是占筮书,而是一部哲学书、一个符号推理系统的时候,究竟用中国传统文化还是用西方文化作为价值标准诠释《周易》,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加以认真讨论了。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检讨一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由于采用了西方哲学理论为价值标准而使中国先哲蒙受不白之冤的教训。因为涉及面太大,本文只讲一个例子:庄子生前是一个漆园小吏,因为流传下来一本《庄子》使他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继承老子一脉,历物崇道、汪洋恣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8],一语道尽了他的风貌。他善于观察事物而又不满足于一事一物之理;认为人的认识应该从“以物观之”的层面,上升到“以道观之”的层面。因而他从庖丁解牛的故事中引申出“缘督以为经”的普遍法则,向学生讲解“社树”的无用大用之理。“以物观之”是基础,“以道观之”是目的,所以批评惠施“逐万物而不返”。但是,今人既不注意他的“以物观之”,也不理解他的“以道观之”,却拿着西方哲学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等标签,硬要庄子对号入座。结果,“主观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两个标签,在庄子头上贴了几十年。
我们不会同意用西医理论诠释《黄帝内经》,也不会同意用西洋画理论诠释中国的水墨画,但是我们却热衷于用西方哲学理论诠释、评判中国哲学,这就难怪那些热衷于中西哲学比较的学者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找不到西方那种“本体论”,甚至否认中国哲学的存在。
对《周易》的现代诠释,同样存在着能否运用西方哲学、尤其西方符号学等理论剖析《周易》理论体系和如何评价其丰富思想的问题。就其理论体系的形成而言,以卦爻符号为主体的《周易》,确实具备了西方符号推理系统的诸要素:阴、阳爻画可以看作为“初始符号”,六十四个卦体可以看作为“对象语言”,卦、爻、位、应、爻变等可以看作为“语法语言”,“明象”的卦爻辞可以看作为“自然语言”。但是,外表形式的相似并不能说明两者在本质上的相同。用“风马牛不相及”形容西方符号推理系统与《周易》之间在本质上的差异是毫不过分的。
首先是初始符号方面的差异。西方符号推理系统中的初始符号,一类是不表现任何内容的字母,如p、q、r、s等,另一类是字母之间的联结符号,如∧、∨、>等,分别表示合取、析取、否定等。《周易》的初始符号—、--,则明确代表阴与阳两个类或两种属性;由阴爻、阳爻构成的八个经卦,也都各自代表着相应的物类。
其二,由于初始符号的确切的属性表达,由此构成的八个经卦所象征的物类的确定性,决定了六十四个重卦的“拟象”特点及其“尽意”功能。“以言明象,以象尽意”的隐喻特点,决定了《周易》符号系统是一个具有类比推理性质的符号系统,而且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类比符号推理系统,完全有别于西方那些演绎性质的符号推理系统;类比推理的性质,同时也决定了《周易》推理的结论具有或然性而不是必然性。
我们不必因为《周易》是一部类比性质的符号推理系统而感到沮丧。相反,我们应该为此而自豪。演绎思维是人类思维活动中最基本最简单的一种思维方式,而类比思维则是人类思维活动中比较生动、比较复杂的一种思维方式。我们的先人选择类比思维作为一种主要思维方式,而且通过《周易》规范和影响着数千年华夏文化的发展。现在,我们开展《周易》现代诠释的目的,不仅是要发掘《周易》蕴含的丰富的思想资源,还要将《周易》的类比思维方式从形式方面加以发掘、整理,为建立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思维特点的类比逻辑理论体系提供最直接的借鉴和帮助。
标签:易经论文; 易传论文; 易经六十四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归藏论文; 六爻论文; 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