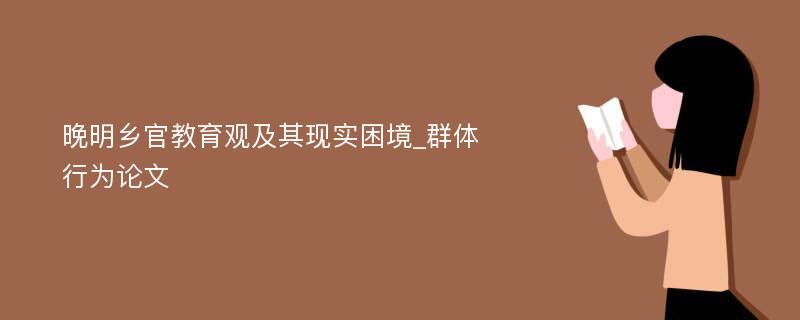
晚明乡宦的教化观及其实践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宦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传统社会,统治阶层往往将人心、风俗作为衡量时代发展的风向标,即“世之治乱,本乎风俗”①,“人心不古”、“风俗浇漓”则社会走向势必“江河日下”。围绕如何教化百姓,明廷也采取过诸多政策和措施。明太祖以循分守法作为教化宗旨,以刑罚作为后盾,以禁末作、华靡为原则,要求百姓各安其业,这在明初经济结构相对简单的状态下起到了安民化俗的作用,以至风俗醇美。但16世纪以后的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如种出土,城市化势不可逆,这与明初统治阶层教化观中慎终追远的肃穆气氛大相径庭。诸多教化组织渐渐流于形式,社会风俗亟待改良。明代社会的这一变化过程早已为人熟知。学界对明代的风俗变迁、民间教化组织的推行衍变也早有研究②,但总体看来,多倾向于考察正式的教化组织,如乡约、善会、社学、社仓、乡社等,关注有形的教化活动,对于教化过程中不同阶层的教化观、风俗观及其冲突与矛盾的讨论相对不足③。这成为我们考察晚明乡宦④的教化观及其实践的出发点。
由于晚明科举取士人数逐渐增多,大量官员转迁滞缓。通籍之士虽多,但“什三在官而什七在野”⑤。李乐也说,“今日贬秩诸公,百无十九在官”⑥。如袁宏道,“宦辄已十三年,然计居官之日,仅得五年,山林花鸟,大约倍之”⑦。因真正居官的时间远远少于居乡的时间,所以在基层社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乡宦群体。“居是乡也,则考是乡之利弊……有位无位,可以共陈,则惟乡邦之事”⑧。乡宦作为在野之臣、居乡之士,是贴近大众的最高知识阶层。明廷对于乡宦居乡行为的要求虽然因时而异,标准也在不断改变,但期望乡宦群体在地方教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想法始终未变。乡宦居乡的核心任务是作为一邑之望,师表一乡,教化地方,树立道德典范形象,成为一方百姓效仿的榜样,以达到敦德化俗的目的。“凡郡县有一善政及一切禁令,士夫皆当率先遵行,以为百姓之望”⑨;“士大夫家居,宜谨身循礼,以训子孙,式里巷”⑩。
不过官方对于乡宦的教化责任事实上一直停留在非强制的层面,作为一种愿景而存在,不管是对乡宦教化责任的具体内容,还是对教化对象的范围,都没有制度和法律上的严格规定。而且朝廷在赋予乡宦以教化资格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限制其过多干预地方事务,所以乡宦的教化活动大多既无组织,也无官方计划可言。对于其义务是否履行、教化是否到位也没有约束,乡宦会因为教化风俗而受到嘉奖,但也不会因未砥砺风俗而招致罪名。所以,他们既可能是最热心改良风俗的人,也可能是风俗日坏的始作俑者。作为居乡之官员,乡宦的仕宦经历、学问思想、社会地位、财富权力等,都使之与那些较低功名的举子生员在教化风俗的立场上有所不同,影响力也更大;作为士大夫,乡宦的教化观反映着知识阶层中精英群体的社会观、秩序观,所以对于乡宦群体在地方社会的教化活动,有必要进行单独的分析。在教化过程中,乡宦与民众时而处于合作的状态,时而呈现出对抗的场面,这种情况在有明一代随着社会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变化趋势,到晚明时,乡宦群体在教化领域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已经呈现出日益紧张的状态。
一 晚明地方教化组织的局限性
明代地方社会具有教化意义的措施丰富多样,较具规模者诸如乡约、保甲、善会、乡贤祠、社学等。但到了晚明,这些正式的、组织化的教化活动在矫正民众习性与改善社会风俗方面有着极大的局限性。
以乡约为例,嘉靖八年(1529年)王廷相上疏请“寓乡约以敦俗”(11),此后乡约盛行一时。据王崇峻统计,在明代举行乡约的87人中,以地方官身份主持的有64人,占74%,平民只有23人,而其中的乡宦更少(12)。王兰荫也认为,“明代各地仿行乡约,多由于监察官或地方官之提倡,间有由于邑民倡行者”。在他列举的11个实行乡约的地区,除龙岩县由“邑人王源”倡行外,其他均由地方官主导,没有材料证明乡宦参与其中(13)。从组织到集会到乡民应该遵守的事项全由地方官规划,乡民的自主性很低。乡约的领导人虽然大多数由民众自由推举,但乡宦常不大愿意出任这种吃力的工作,原因是不但会受到胥吏的恶意敲诈,地方官也不能以礼相待,所以乡宦并非晚明乡约运动的推动者,热心参与的更是少数,偶尔参与也会受到非议。如罗洪先劝致仕友人:“今所传乡约,公手笔也,其后谤腾于朝,谓公居乡专制生杀,台谏将纠论之。”(14)
同时,乡约教化风俗的作用并不显著。丘浚认为,在教化风俗时,朝廷应顺应民众“不从其令,而从其好”的特点,以命令的方式教化风俗难以成功(15)。而乡约因其强烈的官方主导色彩和朝廷的强制干预,违背了教化风俗“从民之好”的原则,故乡约虽然在弥盗政刑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其教化风俗的作用并不显著。如邹守益居乡时,就对乡约的效果持保留态度。邹守益指出,有司对待约长不以礼,致使“能者求退,而约几废。盗势日猖,讼风日滋”(16)。罗汝芳在腾越州做乡约训语时,坐中诸人就指出:“往见各处举行乡约,多有立簿以书善恶,公论以示劝惩,其《约》反多不行。”(17)所以至万历时期乡约的推行已明显收缩(18),教化风俗的功能已然趋弱。
早为学者关注的同善会也不是单纯的慈善组织,而是旨在教育开化。在各种善会的实际运作中,实是较低功名的士子起着砥柱作用,梁其姿提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扬州府志》对“善人”的定义为“布衣韦带之士”(19)。万历十八年(1590年)首创同善会的杨东明时任礼部给事中,属在任官员。而陈龙正、周丕显、魏学濂等人崇祯四年(1631年)建立同善会的时候,尚未进士及第。杨东明批评了乡宦对地方事务的漠然态度:“彼贩夫耕叟尚知结社捐资,共期为善,况缙绅冠盖之流乎?”(20)“士君子居乡,动以闭户养重为高,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为义。”(21)陈龙正认为,“有种人错认道字,谓道乃不涉事物者”(22);“彼居乡杜门,不预一事”(23)。再如天启年间在福建推行劝善活动的云起社,其发起人颜茂猷在去世前三年才获得进士身份,在云起社37名成员中,除颜茂猷是进士外,举人也才3人,其他成员功名更低,几乎找不到任何信息(24)。
当然也有乡宦积极参与同善会的建设,如无锡的高攀龙、刘元珍,吉水的李陈玉,嘉善的丁宾等,但刘元珍受到了非难,理由是卸任的官僚不应参与同善会的活动,因“林中人不应为蛇足”,所以这种活动“非林下人所宜”(25)。天启二年(1622年)致仕的丁宾成为嘉善同善会的支持者,然鉴于其时乡宦多以“近名为戒”,他认为自己“本无其实而横被其名,下以自欺,上以欺君父”,并反复请求免去表扬(26),同善会的经营几乎是由陈龙正一人担任的(27)。
再如乡贤祠,自嘉靖年间开始陆续迁入文庙,其教化作用更加凸显,成为教化之所关,乡人心悦而诚服。但后来乡贤祠逐渐渗入商业气息,钱谦益记,“世道下衰,风教顽敝”,乡里的妇孺“虽有伯姬、孝己之行,截发刲股,残肌损身,非其子孙富厚,竿牍游扬,卒皆草亡木陨,声销影灭”(28)。陈龙正在《乡邦利弊考》中也指出,乡贤祠“五六十年前入者甚少,人亦重之”,近来“贵而祠乡贤”,乡贤的入选失据,开始以财富为后盾,德行退居其次。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民以士为望,奸富可以得之,何为而不作奸”(29)?民众望其风而竞相攀比财富,世风日下便理所当然。伍袁萃也明言:“倘非正人君子而一概崇祀之,何以示训而章轨哉!”(30)乡贤之祠虽木主林立,但过者唾之,乡贤的教化作用因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而削弱,乡贤祠教化功能的纯粹性被破坏了。再者,虽然对于官方来说乡贤祠的功用莫大于教化,但是对乡民来说,因为供奉的都是贤明君子,在长期被崇拜、祭祀之后,乡贤祠和乡贤逐渐衍变为一种地方宗教信仰,“其乡先生之食报享祀无穷,而乡人之禳灾祈佑亦将有赖矣”(31)。乡贤祠因此转化成祈福之地,与乡贤祠的教化意图有所悖逆,祭祀乡贤成为更加现实的需求。
另外一些逸老社、耆英会、移风社等组织一度也有改良社会风气的作用,如成化年间莫震退归吴江加入叙情会,“所陈者山肴野蔌,所读者诗书仁义,而声色之娱,奢靡之奉不用也”(32),也并非单纯的宴饮之乐,目的都在于“接乡人于道”,正己教人,此是规恶劝善的儒家教化实践。更有直接参与移风易俗活动的,如成化年间桑桂归乡后,和里中好友相与结“移风社”,试图扭转风俗,曰:“平凉山水秀拔,人习淳朴,业惟耕读,确有古风。比年丧乱不古,俗信浮屠……桂等生长是邦,读圣贤书,浩叹颓风,思与易之,相为立礼社名曰‘移风’……虽然士君子立身,进则有功于君,退则有功于民。”(33)再如正德时期王鏊对宜兴一个乡宦社团(东丘会老)的记录:“凡归于乡者,岁时有会所,以敦契谊、畅情怀、崇齿德,而示乡人以礼也。示乡人以礼者所以接之于道,作敬上而远于斗办也……尊让洁敬而接乡人于道,斯君子之所重也,非特燕游之乐而已。”(34)宜兴这11名乡宦归乡后的社会活动意在教化乡民。此外宣德时乌镇的九老会、弘治时夏邑的十老会等也都有类似的化俗作用。
至晚明,虽然政治结社、诗文社、讲学会、宗教结社进入全盛时期,但社事活动由怡情自娱变为聚众成势、操纵风气,政治性倾向加强(35),以敦化风俗、安民教民为宗旨的会社则较少出现了。如焦竑感慨:“天顺、成化间汴中士风醇厚,卿大夫致政里居者,情好甚笃,绝无疾忌,而人品亦由是可见。郑中丞宁谢边事而归,与同时诸老为嘉乐会……公同会者十一人……幅巾藜杖,礼度雍雍,真有古者敦庞浑朴之风。嗟乎!今不可复见矣。里俗日偷,缅怀前辈为之怃然。”(36)
总体看来,利用民间教化组织、官方的教化措施,期以团体的力量、宣谕型的教化方式、制度化的教化活动并未能改变晚明风俗日坏的情况,晚明乡宦在这众多的教化组织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有限。风俗的移易起源于人心的变动,考之风俗、教化的议题,核心终究是个体的人,教化所关在“发民情”,而非施加命令以约束习性。教化不仅需要满足上位者对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的设计,也需要民众加以认同、配合,改变自身生活的惯性安排。“大约一、二人唱之,众从而和之。和之者众,遂成风俗,不可猝变。迨其变也,亦始于一、二人而成于众和。方其始也,人犹异之,及其成也,群相习于其中,油油而不自觉矣”(37)。这一上行下效的过程完成之后,风俗才成为社会化的东西,进而唤醒人心。而学术界大多数情况下关注的是“上行”,而忽视了“下效”,忽略了乡宦群体内部生成的教化观本身并不能成为风俗,必有赖于小民的模仿和推广,通过改变个人生活习俗来回应。这个回应的程度在不同时代截然不同。明代早期以农业经济为主,民众安于接受淳朴的生活方式,朝廷的教化措施得以顺利推行。然而晚明在货币经济的冲击下,民众的习性近利远礼,在民间社会中,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和敦厚质朴的习俗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乡民对于知识阶层以复古为趋向的教化观并不能完全接受,甚至拒斥,所以至晚明教化主客体间的互动并不成功。
二 乡宦以身倡率的教化观与民众认同之冲突
在改良风俗一事上,晚明乡宦在理论上更加重视以士风改民风,试图通过乡宦个人的倡率作用带动民众习性的改变。虽然传统教化本就依靠“风行草偃”的互动模式,如丘浚所说,“远近之人,闻其风而兴起,目其事而警戒,不徒行于一时,而其风声流传,且至千百世”(38)。但在晚明乡宦群体的教化观里更加强调本阶层在改良风俗中的地位,主张以士风改民风,由乡宦以身倡率,以个人魅力感化乡民,进而移易风俗。虽然“一县之内生齿不下十万,或科名为仕宦者不过数人”(39),但张采在《约同盟启》中还是强调乡宦虽然作为乡里的少数群体,但无疑是道德优势群体,“夫乡绅则惟吾党数人,吾党束身自好”(40),则乡里群小之恶习自当有所收敛。如何良俊断言:“今之仕宦,有教士长民之责者,此皆士风民俗之所表率。苟一倡之于上,则天下之人群趋影附,如醉如狂。”(41)陈龙正也强调“变合邑之奢为俭在邑侯……缙绅从则小民从矣”(42)。李廷机在其《燕居录》中围绕改良地方风俗的议题,更直接比较了官府与乡宦的影响力,认为:“或言风俗须得良有司,余曰不如乡宦。乡宦者,乡人所属耳目也。乡宦以澹约朴素持身训家,子弟童仆皆澹约朴素,则华侈者自将愧缩而无所容。”(43)邹守益也认为,“风俗侈靡,流而不返,躬行节俭,须自上始”(44)。诸如此类的论调不可尽言。
这种教化观源于中国传统思想赋予乡宦的责任与义务,但至晚明更加盛行的原因则在于社会阶层流动性的增强,士阶层地位受到冲击后亟待巩固。晚明四民社会逐渐松动,阶层之界限越来越模糊,作为士的优越地位渐被富商大贾所冲击,在服饰、出行、日用、财富等方面,民间皆出现僭越行为。乡宦居乡皆视此为风俗凋敝之种种,改良风俗的目的便指向还原四民应有之界限,维护乡宦群体在地方的道德优势地位,即风俗应由乡宦来导引,“风动”之源应是作为一邑之望的乡宦群体,而非其他阶层。兹举一例:李廷机居乡时谈到王锡爵致仕回到太仓,出行只乘坐小肩舆,由此“太仓人无大舆者”,强调乡宦在教化上的影响力,即不需参与具体的教化措施,仅靠乡宦的德高望重和个人风度便足以化俗。“太仓士夫不多,相公位尊,荆公望重,故其化益易……矫俗不嫌小过,先示之以俭,然后示之以礼耳。且闻章枫先生徒步里中即失体,而可以维风亦当为之”(45)。然而,从这些言论中,我们也隐约可以看出晚明乡宦群体为强化本阶层的优势地位,表现出对僭越风俗的戒备之心和危机感,在矫俗活动中迫切地寻求主导权。
风俗若要“反薄归厚,特非声音笑貌之所能为尔”(46),即乡宦的日常行为,包括言说、装扮、行动与居处等等。乡宦为乡人所瞩目,所以在化俗一事上还赖于日用人伦。在明代前期,乡宦能够通过个人风度改变乡里风俗,关键就在于他们居乡谨守礼义,乡民对乡宦群体持有一种崇敬的心理,对其个人品行是认同的,进而模仿其行为,听从其劝谕。如明初吴与弼居乡有法度,“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于人。或亲农事,弟子亦随而助其力,多不能堪。躬行实践,乡人化之”(47)。宋琰居乡,勇于行义,“时疫大作……躬治汤药,以全活之。卒者,出地葬之,乡闾为之感化”(48)。天顺初年,王直致仕家居,年逾八十,“春夏间,诸子集诸佃仆数百人插秧,击鼓唱歌,公与陈夫人各乘肩舆,循观于阡陌。午憩庄所,诸子孙更迭称觞上寿,宴乐终日,形诸咏赋,乡邑以为美谈”(49)。成化年间罗伦居乡,衣食粗恶,为善乡里,“以族属未化,谕之以约束,本之以律令,乡人化之。丧礼行,浮屠除,盗贼息,民业安,十余年间并不作,乡俗为之一美”(50)。正德年间徐问居乡,对于乡里的奢侈之风有所不满,经他劝说后,“里中从公之化,亦稍稍崇俭矣”(51)。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乡宦对地方风俗的改良往往是以乡人“化之”、“德之”、“感之”、“感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体现了民众对乡宦提倡的忠孝节义的自主认同。教化的主客体之间是一种合作与认同的关系,在整个乡党社会中便会出现“间有游惰侈靡者众共摈斥”(52)的景象。
然而到了晚明,教化过程中乡宦与民众之间的认同关系渐趋破裂。乡宦群体身上凝结的嘉言懿行越来越少,作为一邑之望的资格渐渐被质疑,民众对于其教化风俗的权威不再认同,对于乡宦的劝谕不加理会。乡宦与乡民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也阻碍了乡宦教化观的落实。如此一来,乡宦欲以士风改民风,试图通过个人影响风俗的计划只能停留在理论上,难以实践。造成双方认同关系破裂的原因大体有二:
首先,晚明乡宦对自身要求不严,虽然在言论上他们持复古的教化观和风俗观,但在实际生活中,士风先已坏,如李廷机所言,“今士夫日以华侈教人,风俗安得不坏”(53)。盛世之时,“天下物力盛,文网疏,风俗美。士大夫闲居无事,相与轻衣缓带,留连文酒,而其子弟之佳者,往往荫籍高华,寄托旷达”(54)。但在晚明,士大夫闲居无事却是一大害,陈龙正就说:“林下不求田问舍、不骄侈逸游,十不得一矣。夫何故?止缘无事可为……罢官而无事可为,必为多营,为行乐。”(55)诸如奢侈无度、僭越礼制、奔竞请托、隐漏钱粮、干谒公府、为害乡里、包揽词讼等等不可胜数。无怪乎万历时期赵南星将乡宦称为天下“四害”之一,认为“吏于土者不过守令,而乡官之中多大于守令者。是以乡官往往凌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稍禁戢,则明辱暗害,无所不至”,甚至需要皇帝下令“各抚按官严禁乡官在家者,勿倚势害民,勿飞语害有司。其怙终之尤者即行参问”(56)来禁革。
乡宦群体一方面在言论上试图打造个人的“乡先生”形象,教民化俗,另一方面却呈现出骄奢纵欲的豪绅形象。这种鲜明的对比反映出乡宦在教化理念与日常践行上的分裂,不仅造成民众对乡宦群体教化角色的漠视,更使得士风之坏蔓延至民风。乡宦的喜好和审美都成为一般民众仿效的对象,导致社会秩序向着更加混乱的方向发展。如华亭范濂曾说:“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57)湖州李乐就其家乡风俗的变化指出,“吾湖素以俭名,自有诸大宦豪一变而侈靡无算,中人家仿之,甚至立破,历历可数”(58)。而风俗之陋的根源便“作俑于大宦家”(59),所以明人大都认为风俗坏于士。如崇祯年间济南历城人刘敕就曾言:“士者,四民之首,士风醇漓,民效之;民风浇薄,士维之。古之风俗坏于民,今之风俗坏于士。”历城当地“嘉隆而前,(乡宦)磊磊若若。万历以后,不啻辰星”,原因就在于乡绅“不修君子之行”(60)。
其次,晚明乡宦群体与民众之间矛盾冲突逐渐加深,以士风感化民风的方式来教化风俗难以实行。晚明贫富分化、商品经济重压重重,百姓深重的无力感及渴望反叛的欲望膨胀,作为教化活动主客体的乡宦与乡民的关系逐渐破裂,成为对抗和攻击的两方,晚明民变中乡宦更成为打击的主要对象,乡民与乡宦的关系逐渐从以前的温情脉脉变得充满仇恨。以下两则材料形象地描绘出当时双方紧张的对立关系,乡民对于乡宦的暴力倾向显著:
上虞陈木生太史,居乡豪逞,贾怨闾里。壬午,家大疫,止一幼孙。召余姚医者史继烛,史至门,若神鞭其背,谓彼黩横不当疗也。因仆地而苏,幼孙殇绝(61)。
有士大夫平时多以官势残虐邻里,一日为仇人刃其家,火其屋宅,邻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熄之后非惟无功,彼更讼我以为盗取他家财物,则狱讼未知了期。若不救火,不过杖一百而已,邻里甘受杖而坐视其大厦煨烬,生生之具无遗(62)。
王世贞在《觚不觚录》“缙绅惨祸”条中也记载了不少士大夫罹祸的案例(63)。这种尖锐的对立和仇恨在明前期是很难看到的,但是到了晚明却成为普遍现象,整个社会下层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情绪,乡宦与乡民已成水火不容之势。教化活动所仰赖的沟通与劝服全然消失,“化之”、“感之”的效用再难出现。如耿定向所言,在晚明乡宦与乡民的关系实属“上下相猜,小大相嫉,此则化教不行”,“民散久矣”(64)。通过士风来感化民风实难推行,势必导致“郡县之远,闾里之间,乃详为之制,严为之法,则亦虚费文移,徒挂墙壁而已,安能戢其泛泛之心,杜其呶呶之议,而革其靡靡之俗哉”(65)。
三 晚明乡宦复古的教化观与商业发展之冲突
晚明乡宦群体的教化观中复古意味鲜明,他们的风俗观也多是打着复古复礼的旗号,对于古朴民风、农耕文化异常推崇,欲使风俗重返浪漫主义色彩的农业田园社会,呈现出复兴农耕文化的倾向,并试图将“春耕秋获”为固国安本之大计的重要性通过乡宦的亲身演绎传达给乡民。在晚明风俗日坏之时,倡导民众回归乡村质朴的农耕生活,引导其返璞归真、质性自然,希望乡民借由与土地的亲密接触涵养一种淳朴的性格。这种旨在维护传统的乡村道德秩序、抵御商品经济冲击的努力最终失败,正是“人情自俭而趋于奢也易,自奢而返之俭也难。今以浮靡之后,而欲回朴茂之初,胡可得也”(66)。
第一,乡宦在言论上认为士风必须靠近“古大臣之遗风”、“宜依古礼”。在晚明人的著作中,被记载的作为居乡典范的乡宦多是遵循了古朴风度,譬如“致政家十载,杜门谢客,足不履公庭,布衣蔬食,澹泊类穷约人”(67);如以野服示人,“葛巾野服延坐”(68)、“以野服从事”(69)、“角巾野服”(70)、“野服科头常聚首”(71)、“首戴箬笠”(72)等等;也主张躬耕实践,如“躬耕种秫以自养”、“且耕且蔬以养以育”、“日与田夫野老谈耕牧事”(73)、“尝身亲农事手披载籍为子弟式”(74)等。在文本上进而常以“三原之风”、“西桥之风”、“澹台之风”称之。譬如顾起元记其夫人之舅氏王少治居乡,“自罢珠厓郡归,闭户读书,门无杂宾……人谓有东桥先生之风,如是者十许年如一日”(75)。谨身守礼、着野服、躬耕、谈农事,这种古朴的世俗景致经常会被美化后出现于文献材料中。
但这些被记载的乡宦的嘉言懿行显然停留在文化象征意义上,晚明士大夫在反复提倡居乡勤俭时,在自身的物质实践中却首先妥协于商品经济和享乐文化带来的诱惑,奢侈僭越之事叠出。譬如出行一事,前辈士大夫居乡出门有骑驴者,“其在今日,则万万无舍车而骑者”(76);“祖宗朝,乡官虽见任回家,只是步行。宪庙时,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77)。再如日用宴饮,万历时就有乡宦穿戴皆蟒玉金紫,与现任官无异,所以沈德符说“失之远矣”(78),即与礼不合,僭越太过。郑廉说:“士大夫之家居者,率为楼台、园囿、池沼,以相娱乐。”(79)钱谦益对里居乡宦之间的话题也有过观察,说往日乡宦“未尝不访求天下大计,咨诹民瘼,盱衡太息,移日分夜以为常”,但近来大异于前,乡宦“宾筵促席,语刺刺不休,每屈指计某田宅几何,僮手指几何,贩谷及子贷金钱几何”(80)。黄宗羲也有类似的印象,说今日士夫“多市井之气……世风之下如此”(81)。
乡宦教化方面的道德严格主义在士风与民风上有着双重标准。如李开先归乡后“构一堂颇宏壮而鲜丽”,乡人“咸疑其素励清节”。而李开先却认为乡宦不需要对于修建园林这样的小事斤斤计较,“古有以隐为高,亦有以财自污者,调愈高而和愈寡,知我者稀,则我贵。吾尝以文自负,以兵自椎,有震荡一世之才,经营四方之志,一麾而不复出者,此堂也”(82)。可以说这种答案有种强辩的意思,何以经营四方之志和建园造屋之奢可以共处一室?
民风和士风本都是风俗之一种,但“同风俗”的对象多是乡民而非全体民众,并非在社会各阶层之间通行一种习俗。各安其俗便意味着即便在风俗日坏的时候,士风与民风也应有不同的分野,乡宦居乡奢侈与乡民日用奢侈在道德上性质不同。乡宦在教化乡民的设计中,往往将自身独立出来,作为优势阶层,而在士风的矫正方面却常常不能自知,故教化乡民与自身享乐同时可见。“民风士习如出一律,则天下之大,治平之基”(83)。然而乡宦作为社会上层,在修炼士风的时候更便捷地享受着商品经济带来的盛宴,其结果是作为风俗之一的士风,在浇漓的程度上似乎比民风走得更远,而民风汲汲仿效,风俗便如江河之下不可返了。
第二,在评断民风时,较之“农村式陋俗”,晚明乡宦更加重视改造“城市式恶俗”,批判更多的是商业文化、城市文化中产生的新习俗。在对风俗好坏的评断中,好的风俗体现在五教(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三事(食以养生、丧以送死、祭以追远)上,而坏的民风见诸四端:车马、衣裘、官室、饮食(84)。在汉魏学者对风俗的解释中,对于自发形成的原生形态的风俗,即“农村式陋俗”,他们大都觉得粗鄙、杂乱、朴野,尚不雅驯。而经过统治者整饬、改造之后就显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他们将其标举为良风美俗(85)。但在晚明,包括乡宦在内的整个知识阶层虽然对于长久存在的农村陋俗也不乏关注,但相比之下,他们更加急迫地想矫正的是“城市式恶俗”。在晚明地方志中,相比于“农村式陋俗”,如陋、粗、鄙、野,记载更多的是“城市式恶俗”,如薄、浇、漓、偷、浮、淫、奢、侈、黠、游等,集中在商品经济刺激下导致的奢靡、浪费、轻浮、艳俗、过度消费和违制等习性上。明嘉靖以后,在地方志“风俗”一项的记载中,“奢侈”开始成为记录者普遍的感受,如“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86);“正德以前风俗醇厚,而近则浇漓甚矣”(87)。编纂者一致认为,明初是俭朴淳厚、谨守伦常的社会,正德、嘉靖之后是风俗奢靡、世道浇薄的社会,而且这些恶俗无疑都是金钱财富导致的。对于好的风俗则多用淳、醇、美、厚、朴等含有农耕文化意味的词汇来表示。
但在晚明,要全部根除这些“城市式恶俗”,无疑是不可能的。
首先,在民众的消费需求方面,此时的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不仅表现在商品生产扩大、商品种类增多、农村市场贸易发展、江南市镇经济勃兴、城市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发达、货币使用广泛等经济领域中,更具深远影响的是民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市场、商业与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消费品,民众的消费欲望已经被刺激,消费观念有了巨大的变化。对于俭朴与奢侈的观念已与前代有所变化,不再苛责物欲,也不再鼓吹所谓的苦行主义。宋应星在其《风俗议》中就指出:大凡在承平之世,人心宁俭而不愿奢,但“今何如哉?有钱者奢侈日甚,而负债穷人,亦思华服盛筵而效之,至称贷无门”;自前数十年,“妇人之夫不为士者,即饶有万金,不戴梁冠于首……三十年来光景曾几何哉!今则自成童,以至九流艺术,游手山人,角巾无不同……日夜心痒,思聚金而走国门”(88)。整个社会风尚的诸多微妙变化,最终与金钱观念的膨胀密切相关。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期望以古朴之士风改功利之民风,无疑是毫无作用的。如王锡爵在致仕居乡时,本欲以“舍后治方塘一区,屋数楹,插以小竹篱落,家君拈花朵抱瓜蔓其中”,比照前代乡居士大夫确有古风韵致,但“邻翁见之以为寒俭可笑”(89)。顾起元也承认“弘、正间前辈风检,其深居简出,自重而不轻与人,犹是旧时矩度,在今日恐凝滞不可行矣”(90)。再如出行,前辈士大夫居乡可步行,但今日“若大老为此,人必以失体诮之矣”(91)。据李乐观察,在晚明,只要有人以俭朴自持,就会遭到人们的“诮让轻鄙”(92)。反之,如浙江灯市绮靡,甲于天下,但“人情习为固然”(93)。其实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有的风气实际上并不能归结为“风俗日坏”中的一种,譬如对于服饰饮食精致的要求,可以说是消费社会的正常现象,是乡民对于商业化、城市化的自然反应,也是整个社会风气从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推进过程中的表象。
其次,在人口结构方面,弃农从商、弃仕从商的人逐渐增多,民众对于土地与农业已经不像明代前期那样重视了。如万历时期林希元就认为:“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手游食者十而五六。”(94)从事农业生产与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比例出现重大变化,商人的数量逐渐增多,这使得逐利成为正常的社会现象,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乡宦无视这种人口变化,仍然试图将人口束缚在乡村社会,批判所谓“游”的风气。但实际上,江南地区“多奢少俭,竞节好游”的风俗正是晚明市民阶层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晚明诸多蕴含现代要素的新现象,譬如商业的发展、个体意识的发达、市民文化的勃兴、市镇经济的发展等等都有赖于这些“坏风俗”的刺激,复兴乡村道德秩序必然逼迫民众反其道而行之。
最后,在社会心理方面,社会流动性增强导致晚明消息传播和民间舆论发达,造成大众的“观赴”效应,一地之风尚趣味转而风靡全国。据张瀚记载:“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95)商品经济和市场化促使社会风气流动加速,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风气互通,明初化不出里塾的教化方式已然不适用于晚明。即便乡宦可以一时“式里巷”,但仍然抵不住外界风气的浸染。攀比效仿之风成为教化风俗的阻碍,民众的习性更易受到普遍的社会审美和价值观念的影响。
总体看来,风俗浇漓多含市井之气、功利之气,这与江南地区的城市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无关系。晚明乡宦复古的教化观便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与商业文化进行的较量,对于风俗的矫正便是对僭乱越制的社会秩序的拆解和重整。然而对于百姓而言,对于教化的认同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习俗必须与日常生活中的个人需求相切合。因此,推行教化和良风美俗必须以顺民情、民性为先。事实上,随着时代的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所难免,民众的生活观念日趋变化,风俗的薄与厚、奢侈与俭朴,很难一概而论,当然也不可能有一个定论。袁宗道便由此发出如下感慨:“所谓薄俗者,正今之所谓厚俗也。是非厚薄,宁有定论?”(96)但晚明乡宦却依然坚持返古复礼的教化观,即便在商品经济的洪流中依然要使民众坚守农业经济中的生活习惯与社会风气,如李廷机居乡时便坚持:“余每见人说古人难学,及见今人宅舍田园丧葬喜事浩大繁难,不觉望洋。向若而叹真是做不来,正是难学如古人澹泊简约,田止糊口,居止栖身,葬止封土,倒是容易,因教子侄莫学今人学古人矣。”(97)这当然是在逆时而行。
四 结语
概言之,特殊时代的教化活动一定是超越了矫俗本身,更深刻地指向社会变动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体现着变动时代各个阶层的发展趋向。伴随着城市文化和商品文化而生的新风俗往往是以“叛逆”、“泛滥”等形象出现的,乡宦试图以道德约束之,这与乡民的功利主义产生了矛盾,使得整个社会弥漫着紧张、躁竞的氛围。乡宦的教化观执著于怀念农业文化,坚持本群体在教化风俗中的绝对地位,而乡民的社会观倾慕于城市文化的丰富与华丽,个人自主意识也渐渐萌发,对于风俗有着自我判断,拒绝接受和认同乡宦的干预,这便是晚明教化运动的内在矛盾,最终导致“今之世风,上下俱损矣。安得躬行节俭,严禁淫巧,祛侈靡之习,还朴茂之风”(98)?乡宦对于“城市式恶俗”格外严厉的批评以及对于日益显著的社会差异和日益活跃的社会流动表现出的不安,也都源于其扰乱了既有的社会秩序。移风易俗的目的也不止于矫正习性,更在于重塑传统的四民秩序,恢复被打乱的阶层秩序。
民性本厚,之所以导于浇漓,大都是“诱于习俗而为物所迁”,然而乡宦的教化思路却落入“厚者既可迁而薄”、“薄者岂不可反而厚”(99)的怪圈中。所谓“坏的风俗”实际上大多是一种新的习性,在传统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民风质性的转变(从新入旧、从薄返厚、易奢为俭)非是一番社会大动荡是难以实现的,晚明乡宦改造风俗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而接续的明清易代却轻易地完成了这种质性的转变。
①龙文彬:《明会要》卷五一《民政二·风俗》,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第949页。
②具体研究情况见常建华《旧领域与新视野:从风俗论看明清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一文。
③胡成分析过清代中叶江南农村地区对教化的反应,详情参见《礼教下渗与乡村社会的接受和回应》(台北《近代史研究集刊》第39期,2003年3月)一文。
④学术界目前多以“士绅”、“乡绅”、“绅士”等统称在乡的官员和尚未通籍的士子。本文考察的对象仅限于有仕宦经历,但因致仕、养病、养老、省亲、罢官、弃官等原因而较长时间居住在乡里的官员。在明代文献材料中,这类群体通常谓之“缙绅”、“乡大夫”、“乡宦”,如“乡大夫致政里居者”(李濂:《佥都御史郑公宁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六三《都察院十》,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2703页);“乡宦者,乡人所属耳目也”(李廷机:《李文节先生燕居录》,四库禁毁书丛刊本,第674页)。然而到清朝,“缙绅”一词又偶指本地的现任官员,词意渐不明。较之“乡大夫”而言,“乡宦”意指更明确,故本文以此指称在乡官员。关于明清时期士绅称谓的演变,可参见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23页。
⑤丁鑛:《述意》,丁宾:《丁清惠公遗集》,四库禁毁书丛刊本,第5页。
⑥李乐:《见闻杂记》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898页。
⑦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三五《潇碧堂集十一·叙·识伯修遗墨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1页。
⑧陈龙正:《几亭外书》卷四《乡邦利弊考·小序》,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30页。
⑨何良俊:《四有斋丛说》卷一六《史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143页。
⑩李廷机:《李文节先生燕居录》,第670页。
(11)《明世宗实录》卷九九,嘉靖八年三月甲辰,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印本,第2336页。
(12)王崇峻:《维风导俗:明代中晚期的社会变迁与乡约制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13)王兰荫:《明代之乡约与民众教育》,《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台北,大立出版社1985年版,第279页。
(14)罗洪先:《念庵文集》卷六《杂著·纪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8页。
(15)丘浚著,林冠群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八一《崇教化·谨好尚以率民》,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690页。
(16)邹守益著,董平编校整理:《邹守益集》卷一四《书简类五·再复十二条》,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695页。
(17)罗汝芳著,方祖猷等编校整理:《罗汝芳集·文集类·近溪罗先生乡约全书·腾越州乡约训语》,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762页。
(18)关于明人实行乡约的时段分布可参见王崇峻《维风导俗:明代中晚期的社会变迁与乡约制度》第129页。
(19)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20)杨东明:《山居功课》卷一《同善会序》,转引自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6页。
(21)杨东明:《山居功课》卷一《筑堤捍水记》,转引自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123页。
(22)陈龙正:《几亭全书》卷七《学言详记》,四库禁毁书丛刊本,第653页。
(23)陈龙正:《几亭全书》附录卷一《陈祠部公家传》,第703页。
(24)吴震:《“云起社”与17世纪福建乡绅的劝善活动》,《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25)陈鼎:《东林列传》卷二一《刘元珍传》,明代传记丛刊·学林类三,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342页。
(26)丁宾:《丁清惠公遗集》卷八《书牍·与叶台山阁下》,第266页。
(27)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87页。
(28)钱谦益著,钱曾笺校,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卷二六《杂文六·吴中名贤表扬续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21页。
(29)陈龙正:《几亭外书》卷四《乡邦利弊考·学政关民习官方》,第362页。
(30)伍袁萃:《林居漫录·别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96页。
(31)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一一《脉泉李方伯祠堂记》,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40页。
(32)伍袁萃:《林居漫录·前集》卷六,第146页。
(33)谈迁著,罗仲辉等点校:《枣林杂俎·圣集·先正流闻》,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1页。
(34)王鏊:《震泽集》卷一六《东丘会老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02页。
(35)具体研究可参见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198页。
(36)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五《乡党》,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04页。
(37)叶梦珠著,来新夏点校:《阅世编》卷四《士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38)丘浚:《大学衍义补》卷八三《崇教化·严旌别以示劝》,第708页。
(39)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二一《投闲》,第529页。
(40)张采:《知畏堂文存》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本,第666页。
(41)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四《经四》,第31页。
(42)陈龙正:《几亭外书》卷四《乡邦利弊考·礼例十三条·变奢俗三》,第349页。
(43)(45)李廷机:《李文节先生燕居录》,第674页。
(44)邹守益:《邹守益集》卷一四《书简类五·再复十二条》,第695页。
(46)丘浚:《大学衍义补》卷八一《崇教化·谨好尚以率民》,第690页。
(47)(48)焦竑著,顾思点校:《玉堂丛语》卷一《行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4页。
(49)贺钦:《罗修撰伦墓志》,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二三《南翰林》,第968页。
(50)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二一《投闲》,第530页。
(51)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五《正俗二》,第320页。
(52)郭子章:《嘉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鲁源先生于拱墓志铭》,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五九《都察院六》,第2471页。
(53)李廷机:《李文节先生燕居录》,第674页。
(54)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七八《哀词·瞿少潜哀辞》,第1690页。
(55)陈龙正:《几亭外书》卷二《随处学问·无事可为之害》,第276页。
(56)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卷一九《敬循职掌剖露良心疏》,四库禁毁书丛刊本,第569页。
(57)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笔记小说大观第13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影印本,第110页。
(58)李乐:《见闻杂记》卷八,第707页。
(59)李乐:《见闻杂记》卷一○,第800页。
(60)刘敕:《历乘》卷一四《四民》,中国书店1959年影印本。
(61)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第619页。
(62)郑瑄:《昨非庵日纂》卷一七《方便》,笔记小说大观第14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影印本,第126页。
(63)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五《缙绅惨祸》,四库禁毁书丛刊本,第704页。
(64)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一八《杂著二·保甲》,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445页。
(65)丘浚:《大学衍义补》卷八一《崇教化·谨好尚以率民》,第697页。
(66)张瀚著,盛冬铃点校:《松窗梦语》卷四《百工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9页。
(67)佚名:《南京户部尚书潘公荣事略》,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三一《南京户部一》,第1292页。
(68)焦竑:《玉堂丛语》卷七《恬适》,第233页。
(69)(77)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五《正俗二》,第319、320页。
(70)(76)顾起元著,谭棣华等点校:《客座赘语》卷九《达官骑驴》,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9页。
(71)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二《敝箧集二·诗·归来》,第60页。
(72)焦竑:《玉堂丛语》卷一《行谊》,第4页。
(73)以上分别出自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二一《投闲》第526页、卷二二《高尚》第540页。
(74)韩邦奇:《嘉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西溪屈公直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五九《都察院六》,第2494页。
(75)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七《少冶先生里居》,第224页。
(7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四《礼部》,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367页。
(79)郑廉著,王兴亚点校:《豫变纪略·自序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80)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三五《序七·送瞿起田令永丰序》,第988页。
(81)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册《孟子师说》,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点校本,第157页。
(82)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六《孝廉堂序》,第19~21页。
(83)丘浚:《大学衍义补》卷八二《崇教化·广教化以变俗》,第707页。
(84)关于风俗的分类讨论,可参见岸本美绪《“风俗”与历史观》(台北《新史学》第13卷第3期,2002年9月)一文。
(85)萧放:《中国传统风俗观的历史研究与当代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86)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纪风俗》,第110页。
(87)伍袁萃:《林居漫录·畸集》卷一,第204页。
(88)宋应星著,丘锋等点校:《野议·谈天·论气·思怜诗》之《风俗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0页。
(89)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二一《投闲》,第528页。
(90)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七《少治先生里居》,第224页。
(91)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达官骑驴》,第279页。
(92)李乐:《见闻杂记》卷八,第707页。
(93)(95)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百工纪》,第79页。
(94)林希元:《林次崖先生集》卷二《疏·王政附言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458页。
(96)袁宗道著,钱伯城点校:《白苏斋类集》卷二一《杂说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页。
(97)李廷机:《李文节先生燕居录》,第683页。
(98)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百工纪》,第79页。
(99)丘浚:《大学衍义补》卷八一《崇教化·谨好尚以率民》,第6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