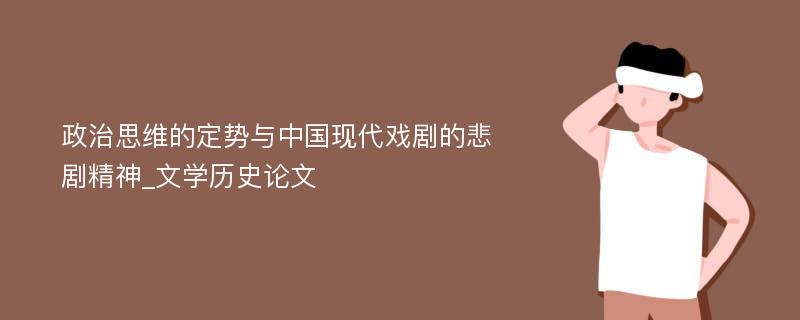
政治思维定势与中国现代话剧的悲剧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势论文,话剧论文,中国论文,悲剧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中国现代话剧作家的政治思维定势,在悲剧创作中表现为,从二十年代末起,创作主体因此而遵奉的历史乐观主义,结合着同是因此而被唤醒、激活的民族传统的中庸和谐精神所生成的异质力量,导致中国现代话剧悲剧精神的沉落。
Summary
Modern Chinese dramatists'thinking set of political type mainly shows in the tragic creations that since the end of 1920's,the different qualitative,forces,which were cultivated by the history optimism and the spirit of the golden mean and harmony in national tradition,have caused the declining in the tragic spirit of modern Chinese drama.
政治思维定势是指思维主体因现实政治环境和现实政治问题的刺激,怀着参与并企图变革现存政治体系的目的,所形成的思维准备状态,它将影响或决定思维主体在继起的思维过程中每一具体时刻的思维活动。中国现代话剧作家的政治思维定势,内在地制约并规定着中国现代话剧文学美学风貌的形成与嬗变。它在悲剧创作中表现为,从二十年代末起,创作主体因政治思维定势而遵奉的历史乐观主义,结合着同是因政治思维定势而被唤醒被激活的民族传统的中庸和谐精神所生成的异质力量,导致中国现代话剧文学悲剧精神的沉落。
一
政治思维定势和作为其运行极致的政治思维,与悲剧精神并非呈异质或对立状态。悲剧精神并非只是悲观主义,就其对包括政治进程在内的整个历史进程的总体看法而言,它是历史乐观主义与历史悲观主义的统一体。因受历史必然性与自身缺陷的制约,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进程本身就充满着永恒的悲剧性冲突。自由与必然、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冲突长期地困扰和折磨着人类的精神世界。所谓悲剧精神,就是指生命主体企图以自身的力量突破历史必然性的制约而又明确地意识到不能突破时交织着绝望与抗争的思维现象。它之所以具有历史乐观主义的内涵,是因为面对历史必然性的制约,生命主体相信自己与现实的抗争因合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具有历史正义性,而且只有弘扬悲剧精神才能使生命升腾出昂扬雄奇的实践活力。它之所以具有历史悲观主义的内容,是因为生命主体明确地意识到在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无法突破历史必然性的限制。历史乐观主义与历史悲观主义构成了悲剧精神的两翼,互相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单独抽出其中的一方面而保留另一方面都意味着抽出悲剧精神最基本的内核。
根据本文对悲剧精神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学是同悲剧精神绝缘的,与悲剧精神相异质的中庸和谐则是其主导的美学精神。中华民族这种传统的美学精神主要起源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哲学。儒家学说从维护和促进现存社会系统和谐稳定的目标出发,强调个体生命欲求必须符合社会伦理规范,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和谐统一,排除和反对个体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斗争、胜败成毁。这种哲学思想经历代官方通过各种手段的推广和实行,在中国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已经渗透在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抒情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中,它使中华民族获得并承续着崇尚中庸与和谐的共同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形象化与情感化的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同样以中庸与和谐为美。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它都强调把杂多或对立的元素组成一个均衡、稳定、有序的和谐整体,排除和反对一切不和谐、不均衡、不稳定、无序的组合方式。除此之外,作为儒家学说之补充的道家和佛学也同样以消解矛盾、调和冲突为目的。道家讲究人向自然回归、与自然合一而又超越自然,讲究无为寡欲、激流勇退、洁身自好,它实际上使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们麻醉在逃避现实的所谓超脱中而失去抗争的勇气和意志。佛学强调因果轮回报应,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磨难将会在来世得到补偿,面对现实矛盾只有退避忍让,泯灭哪怕是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抗争意识。生存于以儒家为主体、以道家和佛学为补充的文化氛围中的古代中国文学尽管偶尔有不平、有愤激,但却很快被儒家、道家和佛学所消解,更谈不上萌蘖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精神。即使是被国内某些学者视为优秀的古典悲剧作品如《孔雀东南飞》、《窦娥冤》、《赵氏孤儿》、《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等,虽然表现出创作主体在严酷现实面前某种无可奈何的人生感慨,甚至是对现存制度的愤怒控诉,但在这些作品中生命主体企图以自身的力量突破历史必然性的制约而又明确地意识到不能突破时交织着绝望与抗争的精神现象,却比较缺乏。直到十八世纪中叶《红楼梦》的出现,才打破这种局面。曹雪芹在这部未完成的杰作中表现出处于萌芽状态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历史必然要求,同这个要求在严酷的封建宗法专制思想统治下不可能实现的历史悲剧,石破天惊地敲响了封建社会的丧钟。《红楼梦》最显著的美学意义就在于它在暮霭沉沉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传达出变革民族传统审美意识的最初的信息。十九世纪中后期,华夏中心观念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舰击得粉碎。饱尝民族屈辱的先进中国人为了寻找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开始用异质的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来重新审视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奉为神圣经典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一八九八年戊戌维新失败后,由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把人们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的民族危机感提高到科学理论的高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竟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中华民族被淘汰的危险。而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则使先进的知识分子从美国黑奴的悲惨遭遇中,具体地感受到一个民族的历史悲剧,并从中得到警醒。在美学方面,王国维破天荒地将西方悲剧观念用于观照中国古典文学,虽然他还未能科学地阐释悲剧精神的特质,但是他第一次从理知层面上正视个体生命历程中无法避免且无法消解的矛盾、痛苦和不幸,打破人们对未来玫瑰色幸福天国的美丽幻想,启发了后来关注变革现实和确证个体存在价值的先进知识分子对社会人生的悲剧性的思考。随着历史的脚步迈进了中西文化大碰撞、大交流的“五四”时代,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才真正开始并初步完成了它艰难的历史性蜕变。以胡适、鲁迅、周作人、傅斯年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历史转型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在无情批判和彻底轰毁崇尚中庸和谐之美,编织团圆之梦,以“瞒和骗”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学的基础上,以西方文学的悲剧精神作为医治中国传统文学说谎作伪思想浅薄病症的“少年血性汤”,而且推而广之,把这种悲剧精神的觉醒作为在面临亡国灭种危机时,改造这个东方最古老国家的国民性和重铸洋溢青春活力的崭新人格的一种最基本的思想前提,作为中国现代化艰难进程中先进知识分子在个人与社会、传统思想与现代意识、理智与情感的尖锐冲突中顽强抗争的精神动力。可以说,对悲剧精神的热情呼唤和自觉的理论建构,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代作家正视社会存在和个体存在的悲剧性冲突的表现,是民族觉醒精神和自我意识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映。对悲剧精神的自觉建构当然是为了指导具体的艺术创造。作为中华民族新型美学精神孕育的结果,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在观察生活的角度、认识生活的参照系和评判生活的价值标准等方面都立足于对社会历史运动中矛盾冲突的审视和把握,在此基础上将悲剧精神与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悲剧体验相融合,创造出跟传统中国文学迥然相异的悲剧作品以及虽非悲剧甚至是喜剧但其中蕴含着悲剧精神的作品。
中国现代话剧的序幕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和总体文学背景下拉开的。悲剧精神的灌注使得中国现代话剧与中国古代戏剧显示出质的区别。话剧文学以集中表现矛盾冲突为主,因此我们考察其悲剧精神时必须从它对矛盾冲突的态度和解决冲突的方式入手。中国现代话剧文学是在“五四”时期正式确立其美学精神和艺术形态的。那时,历史黎明期的晨风唤醒了人作为生命个体的自觉意识,使刚刚从封建宗法专制统治的中世纪漫漫长夜中走出来的“人之子”提出“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受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的历史必然要求。作为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历史转型期的“五四”时代,其本身就是现代化历史必然要求在艰难曲折地开辟着自己的道路,和封建宗法专制主义仍在极为顽强地阻碍其历史进程的悲剧性时代。敏感着这种时代悲剧气氛的“五四”话剧作家敢于直面这种矛盾冲突,并且在解决这种冲突时持历史乐观主义与历史悲观主义相统一的态度。他们选择为争取人的主体性地位而斗争的个体与社会的矛盾作为剧作的中心冲突。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冲突实际上是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冲突。解决这种中心冲突的方式则是强调矛盾甚至强化矛盾,强调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和知其抗争不会获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失败仍然坚持抗争的悲剧心态。“五四”前夕,张彭春的《新村正》可以说是第一部体现这种悲剧精神的作品。嗣后,田汉、郭沫若、欧阳予倩、白薇和洪深为新兴话剧贡献出第一批悲剧作品。他们或者将悲剧冲突建立于觉醒了的生命个体与封建宗法专制主义的根本性对抗,或者从形而上的角度去探索生命个体在必然性制约面前无法摆脱的永恒的悲剧命运。在前一类作品中,新兴话剧作家从古典戏剧作家认为仅仅是悲惨、凄凉甚至是大逆不道的故事中发现其中蕴含的具有丰富历史内容的悲剧性。青年男女殉身爱情,不只是哀怨的故事,而是个性主义与封建宗法专制主义的对抗并被后者所吞噬的结果(《获虎之夜》)。艺术家殉身艺术已被挖掘出崇尚自由的艺术与宗法专制社会和金钱至上主义之间永恒的冲突(《名优之死》)。在郭沫若笔下,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的故事包涵着个性主义与封建宗法专制主义的悲剧冲突(《卓文君》),王昭君的远嫁匈奴也是出于要求“人”的尊严而对宗法专制禁锢人身自由的悲剧性反抗(《王昭君》),聂荌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则更是对不畏强暴的悲剧性献身行动的礼赞(《聂荌》)。古典作家笔下的淫妇形象潘金莲,原来也有“美人之隐衷”(徐悲鸿语):这是一个本能的要求着爱情自由、婚姻幸福并与时代观念相对抗的悲剧女性(《潘金莲》)。不仅是文化视角,就政治视角而言,中国旧民主主义时期革命党人的广州之役“在举事之时事已大不可为,而诸烈士明知其不可为而必为之,欲以警醒同胞迷梦”[2](《黄花岗》)。个性主义的思想和农民革命运动也与封建宗法专制主义的家庭和社会呈现出悲剧性的对抗状态(《打出幽灵塔》)。在后一类作品中,新兴话剧作家对人类命运和社会历史的悲剧思索,企图超越现实的层次而进入某种抽象的或形而上的境界。田汉在其作品中表现的是个体生命内部灵魂与肉体的永恒矛盾(《灵光》),生命与艺术永恒的冲突(《湖上的悲剧》),此岸与彼岸、现实世界与未知世界的对立(《古潭的声音》),个体生命历程中永远的流浪者不可能寻求到最终的停泊地的悲剧追求(《南归》)。白薇的诗剧《琳丽》表现的是理想的爱与现实的爱之间、永恒的爱与瞬间的爱之间的矛盾以及理想的爱和永恒的爱的失败的悲剧性结局。洪深的《赵阎王》里黑夜苍茫的森林,象征着铺天盖地而来的黑暗势力和不可知的命运;赵阎王走不出它的重围,象征着悲剧命运的不可摆脱。此外,朱之倬、陶晶孙、胡也频、高长虹、向培良和陈楚淮等人也加入了这种对人类永恒的悲剧性命运的咏叹。这里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是,二十年代的悲剧创作表现出强烈的唯美主义和感伤情调。唯美是文化-历史转型期的时代青年对美的追求的极端化的表现,感伤是这种追求碰壁之后所产生的悲剧性的情绪状态。“五四”时代曾经壮怀激烈的一代知识者,随着与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专制传统的数次交锋,很快就陷入理想与现实的悲剧性冲突之中。迷惘、彷徨和感伤也因此自然地成为那时青年的普遍的心态。而对二十年代的剧作家来说,唯美与感伤是表现他们悲剧性感受的普遍方式。那时爱尔兰作家王尔德极力渲染美的魅力的《莎乐美》,滋养了整整一代剧作家。田汉不仅将其译成汉语文本并搬上舞台,而且还将王尔德对美的神奇眩目魅力的向往化用在《古潭的声音》、《湖上的悲剧》等剧中,郭沫若、欧阳予倩、白薇、向培良和陈楚淮等人的剧作都有程度不同的模仿痕迹。由对美的追求到因追求而幻灭的悲剧性感伤是符合逻辑发展的。这时期田汉剧作的漂泊者形象系列对文化-历史转型期时代青年感伤心态淋漓尽致的渲染,则因表现出二十年代觉醒后的青年知识者悲剧性的现实处境而可以视作此时期悲剧文学的时代特征。整个二十年代的悲剧文学因对唯美主义与感伤情调的表现和追求,其悲剧精神显得阴柔、凄婉和悲凉,缺乏古希腊悲剧的博大、雄健和壮怀激烈的气魄。也就是说,贯穿于这种悲剧创作中的悲剧精神缺乏震憾人心的紧张感和更为深邃的哲学力度。但是,它毕竟能在对未来幸福天国玫瑰色幻想的否定中勃发出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表现出历史乐观主义与历史悲观主义的高度统一。正如当时有人在观看《古潭的声音》后给作者的献诗所云:“这里可以听你的幻灭的悲笳,同时可以听你的奋斗的军歌。”[3]总之,“五四”时期乃至整个二十年代,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悲剧创作因灌注着作为一种美学精神的悲剧精神,而给中国新兴话剧文学贡献出迥异于中国古典戏剧文学的崭新的美学风貌。
三十年代,悲剧文学创作被作为戏剧创作主潮的左翼文学所冷落。田汉在经过严厉的自我批判之后,决然告别早期唯美的残梦和青春的感伤。南国社抛弃演《莎乐美》而改演《卡门》。田汉根据梅里美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卡门》,将原作吉卜赛人争取个人自由的悲剧性抗争升华为反抗阶级压迫的革命精神。剧作刻意表现“流氓无产阶级的伟大的灵魂,他们的反抗的意志,他们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的极其健康强固的个性,潜藏在他们内心里的革命的力量,以及他们对于革命的一种朦胧的认识与要求,与朦胧的阶级的觉醒。”[4]但这样的艺术处理仍不符合左翼戏剧批评家的要求。他们认为“此剧的致命伤在写一种流氓无产阶级(Iumpen Proletariat)的革命,而在现阶段流氓无产阶级是担不起革命的责任的。”[5]他们质问作者“为什么不活泼的深刻的抓住一现代的革命的女性而必取一被她的阶级注定了命运的卡门以自苦呢?”[6]面对这种指责,田汉只好又转而创作表现中国现实政治革命的正剧。其他活跃于上一时期的悲剧作家也大都中止了悲剧文学创作。而新进的左翼剧作家更是着意向人们展现正义的进步的政治力量最终胜利的曙光。此时期只有曹禺和李健吾等为数甚少的自由主义剧作家的悲剧创作成为仍在赓续着二十年代话剧文学悲剧精神的一脉伏流。李健吾的《梁允达》表现梁允达因金钱拜物教而谋害父命的行为,和此后因残存的人性而产生的恐惧、悔疚之情以及因从善不能、从恶不甘而产生的内心冲突并最终导致精神毁灭。曹禺创作了《雷雨》和《原野》。后者表现中国农民对被奴役命运的挣扎与反抗,但却因有形的封建宗法专制主义的政治体系与更主要的是无形的封建宗法伦理观念沉淀在农民文化中所生成的集体无意识的包围与束缚而最终失败。《雷雨》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最成功的悲剧作品,它继承并发展了“五四”悲剧文学传统。如果说二十年代悲剧文学的特征是唯美与感伤,那么,到了三十年代的《雷雨》则开始有了深邃的思想和雄浑的气魄。《雷雨》是包含着神秘命运观念的伦理悲剧,无论是周蘩漪抑或是鲁侍萍、四凤,她们悲剧的发生,除去封建宗法专制主义对人性的摧残之外,尚有一种不可知和不可逃脱的命运的力量或曰“自然法则”的限制。这部剧作因此具有了现实的和形而上的双重悲剧意蕴。应该说,在三十年代为数不多的悲剧创作中,《雷雨》达到了整个中国现代悲剧文学的高峰,——这当然不只是指其艺术的娴熟,更重要的是指其中包孕的深刻的悲剧精神。
四十年代,历史悲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因现实政治的需要而得到繁荣。在大后方,以郭沫若的《屈原》、《虎符》、《高渐离》等为代表的战国史剧,以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和《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和陈白尘的《大渡河》等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史剧;在上海沦陷区,以阿英的《碧血花》、《明末遗恨》、《杨娥传》和于伶的《大明英烈传》等为代表的南明史剧;在共产党解放区,以阿英的《李闯王》和夏征农、吴天石、西蒙的《甲申记》等为代表的“政治警戒剧”,均构成整个四十年代前期历史悲剧的雄浑的艺术景观。郭沫若的“战国史剧”以打破奴隶制,把人真正当作人并使人性得以充分自由发展的历史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因现实的阻遏而不能实现的矛盾作为剧作的中心冲突,着重讴歌了在这种悲剧性的历史冲突中为理想而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精神。“太平天国史剧”从“天京内讧”,石达开出走、李秀成殉国等方面,表现农民革命队伍内部因野心家、阴谋家的离间和洪氏诸王的昏聩无能而带来的互相猜忌和互相残杀的悲剧。“南明史剧”表现的无论是民族英雄、或是风流才子、抑或是娇弱的歌女等江南各阶层人民在大敌当前,以国家民族为重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气节。解放区的两部取材于李自成农民起义事迹的历史剧,则是为了配合共产党内部整风运动而借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垂戒全党切勿重犯胜利后的骄傲的错误。四十年代后期的悲剧创作只剩下杨绛的《风絮》和路翎的《云雀》等屈指可数的几部了。
从悲剧文学创作上看,“五四”时期和四十年代前期出现大面积的丰收,三十年代剧减,四十年代末期凋零。从悲剧精神上看,“五四”时期的悲剧文学较好地做到了历史乐观主义与历史悲观主义的统一;而四十年代前期的悲剧文学则因历史乐观主义的比重远远高于历史悲观主义,其主导的美学精神则被淡化。因此,就总体而言,中国现代话剧文学的悲剧精神从二十年代末起就日趋淡化,至四十年代末则呈沉落之势。
二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既然悲剧精神与民族传统的美学精神互为异质,是否可以因此将悲剧精神的沉落直接归结为中庸和谐精神的复活呢?从逻辑上推论,这种假设当然是能成立的。但是,人们不禁会问,民族传统的美学精神为什么会复活呢?或曰它是在什么样的规定情境中复活的呢?既然中国现代话剧以集中表现矛盾冲突为主,那么,我们还得从它对待现实与历史中矛盾冲突的态度及其处理矛盾冲突的方式入手来考察中国现代话剧的悲剧精神究竟是如何沉落的。这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
中国现代话剧文学自其诞生时期开始,迄四十年代末,均是以正视历史与现实中的矛盾冲突作为实现其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最基本的起点。中国古典戏剧作家调和矛盾冲突的态度,已被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现代话剧作家所彻底抛弃。毋需详论,众所周知的中国现代话剧文学的现实战斗传统本身便是典型的证据。因此,我们将重点转移到对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处理矛盾冲突的方式的考察上来。
中国现代话剧文学的主流可以说是政治型或准政治型的文学,与此相对应,其中心冲突则是政治型或准政治型的冲突。从二十年代末起至整个四十年代,在处理这种冲突时,创作主体总是着意强调顺乎历史潮流并推动其前进的进步的政治力量最终将会战胜逆乎历史潮流并阻碍其前进的反革命的政治力量。这是一种典型的从宣扬历史正义观念的功利目的出发的处理政治型或准政治型冲突的方式。其具体表现形态可分为以下两种。
一、在开始时进步的政治力量在与反动的政治力量的斗争中虽处于劣势但却因其顺乎历史的必然要求而日趋壮大并取得最终的胜利。这类剧作,出现于二十年代末期,盛行于整个“红色的三十年代”,并延续至四十年代。二十年代末期,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革命处于两次高潮之间的低潮。就在这中国现代极为沉重的历史转折时期,左翼剧作家开始以乐观的历史创造精神鼓动人们扮演摧毁现存政治体系的历史主动者的角色。左明的独幕剧《夜之颤动》、《到明天》,叶秀的《阿妈退工》,袁殊的《工场夜景》和田汉的《梅雨》表达的都是这种政治信念。受着这种政治思维定势影响的欧阳予倩也创作了表现工人阶级觉醒与抗争必然胜利的独幕剧《车夫之家》、《小英姑娘》和《同住的三家人》。在这类剧作中,洪深的《农村三部曲》具有典型意义。其中的《五奎桥》、《香稻米》中虽然农民们拆掉象征地主阶级统治威权的五奎桥和火烧周乡绅房屋的行动属于自发性质的反抗,但考虑到作者在当时的环境中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这种“逼上梁山”式的结尾,实质上是暗示农民只有作为一个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宗法专制主义及其政治体系的统治。第三部《青龙潭》则企图从农民愚昧、迷信的精神状态与骚乱动荡的情绪的特殊视角,揭示如果缺乏正确的引导,农民自发的抗争只能失败。剧终当别人问李全生:“我们还能救活自己么?我们还有对的道路没有?”李全生回答说:“有决心,有信心,总会寻出道路的!”这里实际上是在暗示农民的觉醒,虽然需要一个过程,但终归走向胜利。在四十年代初期,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的剧情发生在艰苦抗战的漫漫长夜里,剧终却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标志预示祖国走向新生。四十年代后期田汉的《丽人行》表现的是三个性格、思想、遭遇不同的女性在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搏斗的艰难岁月中,逐步寻求到共同的生活理想。总之,这类剧作是以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正在为登上历史舞台而开辟道路的新兴的政治力量,并从具体的艺术描写中或明确表现或间接暗示这种政治力量必然由弱小发展到强大并最终胜利。
二、进步的政治力量在与反动的政治力量的斗争中虽然暂时失败,但却在剧作对历史必然性的暗示中透露出最终必胜的政治信念。这类剧作大体上出于三、四十年代左翼作家和受其影响的自由主义作家的手笔。由冯乃超与龚冰庐合作的独幕剧《阿珍》是作者为“献给社会由黑暗转向光明的途中牺牲了生命的成千成万的民众”[7]而创作的。阿珍的大姐二姐均为共产党员,先后为革命献出生命。剧作着重通过阿珍及其父母在经历血腥的教训后终于觉醒的思想过程的展示,表现出作者对一九二八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正通过重新积累力量孕育新的革命高潮并最终成为历史主宰的坚定信念。与此大体上类似的政治观念在非左翼作家曹禺的《日出》中也通过变换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建造大楼的工人们在日出时分正在创造着新世界的戏剧意象,传达着作者既是对现实,又是对历史的态度:新世界不属于陈白露这种被时代轧碎的意志薄弱者,只有劳动阶级才是新世界的创造者和历史的主宰者。如果说,三十年代的这类剧作,基本上是从现实生活中开掘题材,那么四十年代,在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旗帜下,则出现从历史中汲取改造现实政治激情的历史剧的创作潮流。郭沫若的《屈原》、《高渐离》,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即是典型的代表。《屈原》的政治理想虽未实现,但受其高洁的人格所影响,宫廷卫士营救他奔赴汉北,以图再起。剧作的结尾昭示以屈原为代表的抗秦派现以张仪、勒尚为代表的亲秦派的斗争因体现着历史上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而将最终赢得胜利[8]。《高渐离》的结局主人公虽然失败了,但作者对其视死如归的飒爽豪迈的情怀的渲染和赞美,却是建筑于对悲剧英雄所代表的体现历史必然性的政治力量最终必胜的理念的基础上。阳翰笙则从太平天国史实中发现与抗战现实有着某种内在的相通之处。《李秀成之死》所再现的天京保卫战虽然在内外交困的严酷环境下失败了,但是被俘的李秀成却依然通过回顾过去光辉的历史对未来寄寓希望。《天国春秋》则以国民党政治体系制造的“皖南事变”为艺术思维的触媒,将太平天国由盛至衰的转折点定位在“杨韦内讧”事件上。剧作特意突出这次事件在政治上激起了曾与韦昌辉同流合污的洪宣娇的觉醒:“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总之,这类剧作虽然在结局时正义的力量被非正义的力量所暂时压倒,但仍通过各种艺术手段和表现方式暗示前者因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最终必然胜利。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与第一类剧作在深层的历史观念上是一致的。
中国现代话剧文学上述两种处理中心冲突的方式在深层结构上都可以说是历史乐观主义的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现代话剧作家出于政治赞美和政治宣传鼓动的需要,对自己所归属或所认同的正为准备登上历史舞台而开辟道路的新兴的政治力量,持历史乐观主义的态度,是一种合情合理的现实选择。尤其是那些占剧作家绝大多数的政治剧作家,是他们所代表的革命的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源泉”[9]。正是这种以现实需要为宗旨的政治思维定势对创作主体的思维准备性和思维方向性的预设,使得中国现代话剧文学选择历史乐观主义来作为处理冲突的基本出发点。如果说,“五四”至二十年代末期,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在历史乐观主义与历史悲观主义的统一中建构着具有时代内容的现代悲剧精神;那么,此后它便开始偏爱历史乐观主义,其悲剧精神自然地也因丧失悲观主义的一翼而被消解。
这种历史性的转向是在整个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学时期完成的。一方面,当时的主流理论独尊现实主义,并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提出了“努力把握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10]、向无产阶级“指示一条改造社会的新路径”[11]的要求。另一方面,辩证法的历史发展观,则在左翼作家认识生活、评判生活诸方面发生着深刻的影响。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坚信:“历史的发展必然地取辩证法的方法(Dialektische methode)。因经济基础的变动,人类生活样式及一切的意识形态皆随之而变革;结果是旧的生活样式及意识形态等皆被扬弃(Aufheben奥伏赫变),而新的出现。”[12]由此出发,他们征引“必然性与偶然性”、“本质与现象”等哲学范畴,要求作家“扬弃”只作为“偶然的东西”存在的“黑暗的现实”,把“必然的”“乐观的现实”“提取出来,作为描写的题材”[13]。这种要求突出表现“必然性”和“本质”的思路贯穿于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先后被左翼理论家所介绍和提倡的“新写实主义”(又称“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或“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论内核中。周起应(周扬)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14]中对此作了系统的表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动力的(Dynamic),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在发展中,运动中去认识和反映现实的。”“只有不在表面的琐事(Details)中,而在本质的,典型的姿态中,去描写客观的现实,一面描写出种种否定的肯定的要素,一面阐明其中一贯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本质,把为人类的更好的将来而斗争的精神,灌输给读者,这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15]由苏联传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属于政治范畴,而非美学范畴。苏联文学的发展历史表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强调在革命的发展和运动中去认识和反映现实而给人以这样的一种暗示:现实必定是上升运动的,社会主义社会永远再不会有政治上的失误和任何背离战略目标的可能性;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出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16],随着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建立而不复存在。苏联文学因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而对时代悲剧持沉默的态度。即使偶尔触及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年代里的悲剧事件时,也特别地赋予其历史乐观主义的性质[17]。随着这种创作方法的引进,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中,并引起了其后文学风貌的变化。正是基于对表现“必然性”和“本质”理论的遵奉,此时期的主流理论家和作家对作为悲剧精神统一体中的历史乐观主义表示认同而排斥历史悲观主义。既然真实是飞跃的、发展的,是包含着斗争的明日的现实[18],那么,对明日持怀疑态度的历史悲观主义自然地被认为是不利于为争取登上历史舞台而战斗着的新兴的政治力量的。同时还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乐观主义的产生也跟三十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形势认识上的“左”倾激进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先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占主导地位的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曲折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而一味地强调革命的突变性。对此持怀疑态度,便被认为是政治上的悲观主义。这实质上从具体的政治操作层面上助长着历史乐观主义的声势。作为一种艺术样式的悲剧和作为一种美学理想的悲剧精神,在“红色的三十年代”就这样成为不受欢迎的缪斯。因此,当一九三四年中国自由主义作家大加评赞当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意大利悲剧作家皮兰德娄时,周扬就告诫人们皮兰德娄的创作因根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人悲观绝望的精神状态而绝无创造中国新文学所应该借鉴的价值。他认为“健全的文学将用乐观的,科学的观点去解决世界文学中一切悲观的问题。……在健全的文学中,连死也并不是那么可悲观的。”“我们需要……健全的乐观主义的文学。我们不需要比兰台罗(现通译为皮兰德娄——引者注)的悲观主义。”[19]随着这种认识的被普遍接受,到抗战时期虽因现实的刺激又重新回过头来呼唤悲剧创作和悲剧精神,而悲剧创作的确也在民族救亡的新形势下一度繁荣,但究其根底,仍然存在着对悲剧精神的实质和悲剧创作的特征的误解。比如抗战初期的一位剧作家强调为使观众感奋起来,必须“把英雄的抗战现实给以强化”,即使是悲剧的题材也应添加上振奋人心的乐观主义的结尾[20]。郭沫若此时期虽然没有提出系统的悲剧理论,但是他后来在阐释自己历史悲剧的意蕴时曾将其悲剧观念作了简要的总结。他认为悲剧生成的社会机制在于:“促进社会发展的方生力量尚示足够壮大,而拖延社会发展的将死力量也尚未十分衰弱,在这时候便有悲剧的诞生。”[21]而悲剧精神就是“悲壮的斗争精神”,“悲剧的价值不是在单纯的使人悲,而是在具体地激发起人们把悲愤情绪化而为力量,以拥护方生的成分而抗斗将死的成分。”[22]郭沫若认为悲剧精神的实质是一种历史乐观主义,因此,他认为悲剧精神的作用是“鼓舞方生的力量克服种种的困难,以争取胜利并巩固胜利”[23]。其实,无论是“红色的三十年代”对悲观主义的恐惧或是四十年代对乐观主义的倚重,都是对悲剧精神的误解。强调表现历史乐观主义,其实质则是将人类亘古以来就一直未能解决的诸种矛盾冲突作了一厢情愿的简单化的处理,这是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事实上,代表历史前进趋势的正义力量,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甚至某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未必能战胜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非正义力量。这是已被世界历史的发展所证明了的结论。反过来说,这种肤浅的乐观主义之所以盛行,也同样可以归因于长期的政治革命的需要。政治思维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败者为寇,胜者为王”可以说是政治斗争的基本法则。因此,政治谋略家最关注的是眼前的政治上的“成”与“败”、“得”与“失”。为了鼓动人们为现实的政治利益而行动时,宣扬某种乐观主义,甚至编造关于某种永恒的黄金世界的梦想,对政治操作者来说是非常必要事实上也是极为可行的。但是对追求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艺术创作来说,这种基于政治目的的乐观主义却是一种异己的精神存在。政治思维方式与艺术思维方式在这里表现出明显的质的区别。因此,上述三、四十年代那种单纯强调表现“必然性”和“本质”的肤浅的乐观主义发展至极致,必然导致鲁迅所批评的“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的“不敢正视社会现象”的创作倾向[24]。中国现代话剧文学这种对乐观主义的倚重在中国当代的发展,便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三
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被政治思维定势所唤醒所激活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学精神对消解中国现代话剧悲剧精神的作用。因政治思维定势而倚重的历史乐观主义,只有当与同是因政治思维定势所唤醒所激活的民族传统美学精神相契合时,悲剧精神才不仅在历史观上而且同时在美学观上受到创作主体的冷落和舍弃。
如前所述,中庸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学精神的核心,其出发点与归宿均在于消解矛盾、调和冲突,文学艺术中的“大团圆主义”即是其主要表现。政治思维定势使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的构思阶段就考虑通过选择何种方式去处理前进与反动两大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来表达历史乐观主义的信念。从美学理想方面来看,传统文学艺术中的“大团圆主义”则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从政治思维出发,前进与反动两大对立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其必然结局应该是前者的最终胜利。不管经受什么样的曲折与艰难,就总的运行趋势而言,前进的政治力量总是朝着最终胜利的方向开辟着自己发展道路的。这种政治信念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历史哲学基础之上的,是以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整个历史进程的总趋势为思维向度的。它忽视了整个历史进程中某一具体历史时期内,因自由与必然、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冲突而造成的人类悲剧性处境。换句话说,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持乐观主义信念的政治思维,实际上淡化了新生的政治力量在为登上历史舞台而斗争的时期所面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这种历史哲学,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历史乐观主义。而这种乐观主义,与中华民族文艺传统中的“大团圆主义”,有许多共通之处。“大团圆主义”相信正义的力量最终会战胜非正义的力量,在历史观上也属于乐观主义。为了表达先进的政治力量必将战胜反动的政治力量的历史乐观主义信念,中国新兴话剧文学发展到三、四十年代,在美学精神上又不自觉地重新认同被戏剧现代化先驱者所唾弃的“大团圆主义”传统。这种历史性的反复,对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而言,都是无意识的。如果说创作主体所信奉的历史乐观主义对造成中国现代话剧文学悲剧精神的沉落表现出自觉和表显的性质,那么,民族传统审美精神的历史积淀在这种特定的现实需要的情况下的被重新搅起和接受,则表现出非自觉和潜隐的性质。特定民族的美学精神是特定民族在其长期历史和文化实践中形成的,它以传统的形式先于每一特定世代而存在。对特定民族特定世代的每一成员来说,他一出生,就生活在该民族传统美学精神的特殊氛围之中。个体从幼儿到成年的心理发展,如同胚胎学和古生物学的关系一样,可以说在相当短的岁月里重复了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恩格斯指出:“由于它(指现代自然科学——引者注)承认了获得性的遗传,它便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每一个体都必须亲自去经验,这不再是必要的了;它的个体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它的历代祖先的经验的结果来代替。”[25]因此,作为整个民族文化的演化发展,并经过许多世代反复经验的结果的精神残存物的中庸和谐精神,通过世代相沿的“获得性的遗传”,已经内化并积淀在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了。虽然经过本世纪初期那场欧风美雨的冲击刷洗,悲剧精神已经成为包括话剧文学在内的“五四”新文学的主要美学精神,并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为数甚少的作品中得到延续;但因文化传播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它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来说,仍是异质的文化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因三十年代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和四十年代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战争的现实政治对历史乐观主义的需要,中庸和谐精神很快又被历史乐观主义的信徒在艺术创作活动中无意识地唤醒和激活并被不自觉地重新认同。另一方面,从文学观念的演变历程来看,三十年代上半叶以争取更多的普通民众为旨归的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中未能解决的困惑,又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重新提出来。后一次讨论因其中心目的在于解决新文学如何去反映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思想与情感等问题而更具直接的政治功利性。作为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作家开始自觉寻求传统文学乃至传统文化与新型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他们形而上学地将民族传统文化与人民性联系在一起,有意无意地忽略在封建社会里发展到高度成熟的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异质的精神特征。虽然不乏有识之士对新国粹主义倾向的警惕[26],但大多数论者却未能从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出发对民族传统文学乃至传统文化进行清醒的理性批判,以至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犁庭扫穴过的传统文化又开始借高扬民族精神的历史契机重新被时代所接纳所吸收。正是这种总体文化观念演变的背景造成了民族传统美学精神的历史性复归。文化观念的变化当然使作家为获取作品的人民性而表现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热情。因此,传统美学精神的复归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创的悲剧精神的沉落,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如果说悲剧精神贯穿于“五四”话剧文学作品的首尾;那么三十年代便出现了很多被标为悲剧实为正剧精神的作品,四十年代则在历史悲剧中从历史乐观主义和中庸和谐精神出发去寻找并透露进步的正义的政治力量必然胜利的历史信息,这样就使得悲剧虽为悲剧,但其悲剧精神却缺少了历史悲观主义的深度。这充分说明中国现代话剧文学悲剧精神的沉落,不仅表现在作为一种艺术样式的悲剧的减少,更表现在作为内在规定性的美学品格的削弱和丧失。这既是日趋政治化的时代对文学风貌的制约,又是创作主体从政治思维定势出发面对历史的自觉的选择。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黄花岗〉小序》,《田汉文集》1卷432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
[3]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田汉专集》第84页。
[4]钱杏村:《关于南国的戏剧》,出处同前引书第235页。
[5][6]《关于〈卡门〉之二》,《田汉文集》2卷434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
[7]见作者为《阿珍》剧本的题辞,《大众文艺》1930年5月第2卷第4期。
[8]郭沫若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秦楚两国皆具有统一中国的可能性。他甚至因此认为:“中国由楚人统一,由屈原思想来统一,我相信自由空气一定会更浓厚,学术风味也一定更浓厚。”历史没有走这条道路,不仅是楚国的悲剧,而且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剧”。《沫若文集》第12卷第32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3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10][12]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载《创造月刊》1928年1卷9期。
[11]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载《太阳月刊》1928年2月1日第2期。
[13]钱杏村《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问题》,1930年《拓荒者》1卷1期。
[14]载《现代》1933年11月1日第4卷第1期。
[15]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6页。
[17]苏联剧作家伏·维斯涅夫斯基1933年创作的《乐观的悲剧》即是一例。作家之所以将该剧命名为《乐观的悲剧》,是因为在这部悲剧里面的主人公,即使面临着个人命运的悲剧结局,却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与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不以个人命运对待悲剧的结局,而是革命事业在胜利前进。
[18]语出周起应(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载《现代》1933年11月1日第4卷第1期)所引的卢那察尔斯基在全苏联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第二次大会上的演说词。
[19]企(即周扬):《从比兰台罗说到文学上的悲观主义》,载1934年11月19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20]宋之的:《论新喜剧》,见《演剧手册》,重庆上海杂志公司1939年版。
[21][22][23]郭沫若:《由〈虎符〉说到悲剧精神》,《郭沫若论创作》第427-42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24]《鲁迅全集》第4卷第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4-565页。
[26]参见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载1940年4月10日《新蜀报》;田汉在“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载《戏剧春秋》1940年第1卷第3期;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重庆学术出版社1941年版。
标签: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话剧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雷雨论文; 美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读书论文; 屈原论文; 李秀成之死论文; 戏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