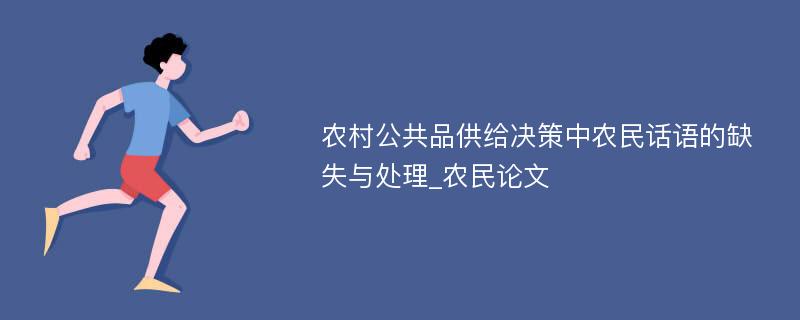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中农民话语的缺失及治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缺失论文,话语论文,物品论文,农民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540(2006)02—0025—02
农村公共物品是相对于农民或家庭自己消费的私人物品而言,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物品,主要包括农村交通、电网、农田水利设施以及教育设施等“硬”的公共物品;还包括信息、技术服务、技能培训、公共秩序维护、制度安排等“软”的公共物品。农村公共物品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大力加强农田水利、耕地质量和生态建设,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积极发展农村卫生事业,繁荣农村文化事业,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被摆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一、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
自城乡分立以来,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就在我国社会、政府、民众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变迁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解放后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三是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
虽然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和农村税费改革时期三个阶段的变迁,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的本质上都是只有一个决策中心的单中心体制,表现为:(1)政府是农村公共物品的单一供给主体。(2)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外筹资机制。(3)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物品决策机制。
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单中心体制下,公共物品的供给危机日益凸现:(1)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导致县乡财政失衡,削弱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极有可能陷入停滞的局面;(2)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农村税费改革后实行的“一事一议”制未能彻底解决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3)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一是受财政能力影响,农村公共物品的总体供给不足,二是农村部分公共物品供给过剩。
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中农民话语的缺失及原因分析
在古代,政府支出的决策权掌握早国王或皇帝手中,而且随着专制制度的加强,财政控制权的郡主独占行日渐稳固。受“权归于上”、“政出于一”这一思想的制约,皇帝掌握一切大权,包括财政支出权。除官俸、军费、皇室支出等政府开支的主要项目由国王和皇帝决定外,用于水利、道路、教育、赈灾等方面的支出也是秉君意行事,惟君命是从,决策权基本上归属皇室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带有君主和帝王的仁政和恩赐之举的意思。
人民公社时期,公共物品主要是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提供。出于农村政治稳定的考虑,党和政府采用集中动员体制,用政治力量控制农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以及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采取政治顺从型的决策机制。这个时期,公社基本上没有自己的集体利益,社员的个人利益基本上被抹煞,基层干部的任务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贯彻国家的经济政策。政治利益成为官员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在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决策中,社员偏好让位于上级命令。出于对党的感恩和个人崇拜,中国农民放弃了话语权,陷入了集体失语的状态。加上意识形态的刚性约束,政府理所当然的成为唯一的决策者,而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决策原则又保证了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的形成。
人民公社解体后,党和国家的力量从农村收缩,加上农民权利意识的萌发,农民参与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会明显增加。按理说,农民应该能把自己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表达出来,但这种自下而上的表达机制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往往不是由本辖区、本社区的农民的需求决定的,而是乡镇政府和上级政府硬性提供的。
在压力型体制下,数字化的任务分解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保持上级对下级的行政压力和控制,为了在上级政府的评价体系中获得好名次,有的乡镇政府不顾财力搞“政绩工程”,强调高速度、超水平,根本无暇顾及农民的需要,农民很少参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决策,导致农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偏离农民的意愿。而村民委员会既要办理村务,又要执行政务,扮演着双重角色。“政务”执行的强制性造成了对“村务”的冲击,致使村民委员会过度组织化,村民自治组织成了具有行政权力的“准政府”,难以准确地表达农民的意愿,也对公共资源的筹集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由于缺乏有效的供给谈判制度,农民无法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决策中体现自己的意志。这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外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制就导致了农民不能积极的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从而导致了农民话语的缺失。
三、农民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的重要性
当代公共行政越来越关注“公民导向”,即以公民的不同偏好为基础,以满足公民对“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特定需求为目标,重视公共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公民参与是一种广泛的参与,不仅包括公民的政治参与,还包括所有关于公共利益、公共事务管理等方面的参与。广泛的公民参与是民主社会的普遍现象,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是公共政策本质属性——公共性的内在要求,是政治民主化、行政民主化发展的需要,是政府治理工具选择转变的需要,是增强党和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并可以弥补政府决策的有限理性。
而农民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能够保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本质所在和制定依据。政府制定的政策必须服务于或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为政策的最高目标。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政策制定人员手中的权力为他们牟取私利提供了机会,或者是仅仅出于考虑各级政府的利益,并未顾及广大农民的利益。而农民参与政策制定,则打破了这种政府内部的政策制定人员对政策制定权的垄断,农民获得了部分政策制定权,农民参与使政策制定过程,决策过程透明化、公开化,政策最终的制定、出台也更加有利于农民利益的维护和农村社会的发展。
2、能够提高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的科学性。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使政策达到目的,实现价值的保证。要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必须具备充分的信息,创造性的思维和专业技术知识等条件。农民参与政策制定有利于提供实现政策科学性所要求具备的部分条件。农民参与为政策的最终制定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提高了公共政策的社会可行性,有利于降低政策的执行成本,更大程度上保证政策的顺利执行。
四、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体系的重建——多中心的供给决策机制
农村税费改革后,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已变的相当严峻。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应该责无旁贷的承担起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责任,当前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改变旧有的单中心体制,要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筹资机制、供给决策机制以及供给主体的多中心运行,构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多中心体制,从而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就是在这其中,如何构建多中心的供给决策机制尤显重要。
首先,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政府决策机制。各基层政府作为公共部门,作为政府公共权力的化身,负有供给公共物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非追求个人的私利,他们所决策组织的公共物品基本上是农民所急需的,而且不会因为提供的物品没有利益可图而不提供,这样有利于维护农村居民的利益。因而,我们实行多中心的供给决策机制,就要坚持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中政府决策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在关系农村发展大局的基础农田水利设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农村卫生事业等公共物品的决策中要不断完善决策程序,真正体现和维和农民利益。
其次,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积极推进农民参与,建立农民需求表达机制。正如本文指出的,我国传统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程序是“自上而下”的,这使农村公共物品的供求出现了供给不足或者结构不合理等失衡现象,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中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不健全,致使政府的供给决策出现了偏差。因此,要积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建立公共物品供给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程序由“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农村公共品需求的民主表达机制,积极推进农民参与,拓宽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表达管道、使多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以表达。这就要求:第一,改革农村社区领导人的产生办法。村级领导人和乡级领导人应真正由本社区居民民主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级组织部门安排。由于由选举约束,他们能真正对本地选民负责,对本社区负责,把增进本地选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第二,在村民委员会制度和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使农民的意见得到充分反映,并由全体农民或者农民代表对本社区、本辖区的公益事业进行表决。尤其是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产、生活的道路建设、水电基础设施、技术指导等区域性公共物品,应定期召开村民大会,如实反映农村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第三,建立起农村社区公共资源使用的监督制度。改革目前的仅有村一级的“村务公开、财政公开、民主理财”,实行乡、村两级的“政务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增加公共资源使用的透明度,定期向村民公布收支情况;第四,逐步使农民能够通过投票来表达对公共品的需求意愿,鼓励农民参与到农村公共品决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形成政府与农民共同决策的模式。同时建立起农民真正的自治性组织,使之拥有与政府谈判的实力和自我保护能力,能够真正代表农民与政府进行信息沟通与政策互动。
编辑:彭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