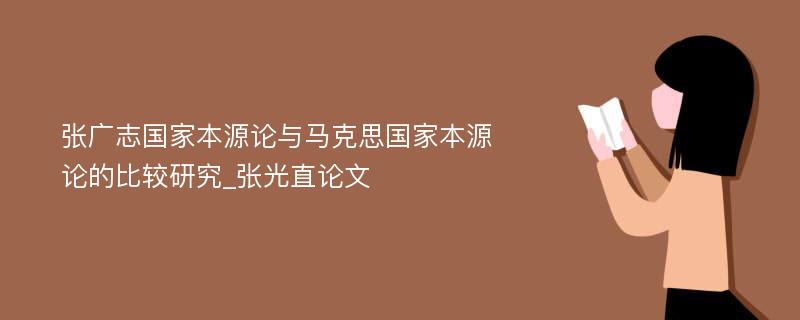
张光直和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起源论文,理论论文,国家论文,张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光直(1931-2001年)是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曾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从事历史与考古学研究。张光直对国家起源问题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他开创性地提出国家起源的两种模式:断裂——连续模式。张光直的一些理论对马克思也提出了重大挑战。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在总结西方国家起源过程中形成的,忽略了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具体情况,因而不具有解释力和普适性。他尤其反对马克思关于国家起源中的生产力基础地位的论述,认为巫术等宗教因素在国家起源中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张光直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重大反响,我们既要肯定他的理论创新,也要看到他的一些理论尚待商榷和推敲。
一、关于国家起源模式的理论
张光直提出,国家的起源,即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西方式的,其代表是两河流域苏美尔人(Sumerian)的乌鲁克(Uruk)文化和地中海的爱琴文明。它以人和自然关系的改变为契机,通过技术的突破,通过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的变化引起社会的质变。其特征是在兴起时突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束缚,并与旧时代发生断裂。西方式的国家起源中,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是积蓄社会财富的主要方式,生产技术是决定性的因素,社会组织结构中的地缘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因此,西方式的国家起源的特点是突破性的,也就是断裂性的。二是东方式的(或世界式的),其代表是东亚的中国,也包括美洲的玛雅文明。它以人与人关系的改变为主要动力,在生产技术上没有大的突破,主要是通过政治权威的确立开创新的时代。其特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连续的,它们的和谐关系没有受到破坏。东方式的国家起源中,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完成,城市与以前的氏族聚落也有连续性,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血缘关系从氏族社会延续下来,包容了新的地缘关系。因此,东方式的国家起源的特点是连续性的(注: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在阐述国家起源的两种不同模式(断裂——连续模式)后,张光直提出了一个震惊学术界、尤其是西方学术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国家起源模式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式的国家起源模式只是次要形态。因此,现代社会科学里自西方经验总结而来的国家起源理论的一般法则没有普适性。他明确指出:“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张光直进而提出:“一般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我们今后对社会科学要有个新的要求,就是说,任何有一般适用性的社会科学的原理,是一定要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验过的,或是在这个历史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退一步说,任何一个原理原则,一定要通过中国史实的考验,才能说它可能有世界的通用性。”(注: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5-56页。)
张光直的上述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对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也引发了许多学者的关注。2001年9月,美国罗莎·兰伯格-卡洛夫斯基(Marfha.Lamberg-Karlovsky)主编了《破裂——文明的起源》(The Breakout-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一书,有多位学者撰文讨论张光直提出的国家起源的断裂——连续理论。可见,张光直的学说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光直的理论有利于打破“惟西方的社会科学范式和理论独尊”的局面。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仅仅是基于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事实得出的,不可能用来解释人类各种文明形态尤其是东方文明中的国家起源进程。因此,现在是从总结普遍规律的立场出发来研究中国文明史的时候了。
当然,张光直将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酌模式概括为连续性模式,这种概括也有片面性。中国国家起源中,连续性和创新性有机统一在一起,我们既要看到前国家社会的氏族制度在国家社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也要看到国家社会实现了重大的制度创新。张光直的失误就在于对中国国家起源的这种连续性和创新性对立统一关系认识不够,进而将中国和玛雅视为一种同质文明类型。其实,中国国家起源和中南美洲的国家起源存在重大差别。其中,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在保持连续性特征的同时,不断实现经济领域的技术创新、政治领域的制度创新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创新。这种连续性和创新性的统一,使得中华文明始终具有连续进化、生生不息的稳定性和生命力。而玛雅文明则是连续性有余,创新性不足。譬如,她的国家制度始终徘徊在低级水平,保有浓厚的原始色彩。这也是看似强大的帝国大军在规模较小的西班牙殖民者面前很快就落败的原因。
二、关于国家起源动力因素的研究
(一)萨满巫教、艺术以及文字的作用
张光直根据《国语》中“绝地天通”的故事,认为萨满巫教(Shamanism)在中国国家起源中占有基础性地位。张光直指出:“它为我们认识巫觋文化在古代中国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关键的启示。……古代,任何人都可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白天地交通断绝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于是,巫便成了每个宫廷中必不可少的成员。事实上,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都认为:帝王自己就是众巫的首领。三代王朝创立者的所有行为都带有巫术和超自然的色彩。”他还为萨满巫教理论提供了另外两个论据:“如夏禹有所谓‘禹步’,是后代巫师特有的步态。……甲骨卜辞表明:商王的确是巫的首领。”(注: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张光直在萨满巫教理论的基础上,认为艺术和文字具有类似的宗教功能,都是攫取政治权力的手段。首先,艺术是攫取权力的手段。商周艺术中的动物纹样具有宗教功能,“带有动物纹样的商周青铜礼器具有象征政治家族财富的价值。很明显,既然商周艺术中的动物是巫觋沟通天地的主要媒介,那么,对带有动物纹样的青铜礼器的占有,就意味着对天地沟通手段的占有,也就意味着对知识和权力的控制。占有的动物越多越好;因此正如《左传》所说:‘远方图物’,所有的物都铸入了王室的青铜器之中。很可能王室的巫师和地方巫师所拥有的动物助手也是分层分级的。”(注: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其次,文字也是攫取权力的手段。张光直认为,无论商代还是史前的陶器符号,绝大多数都是家族、宗族、氏族或其分支的标记和祖徽。“古代中国的文字,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从祖徽(赋予亲族政治和宗教权力的符号)演变而来。我们由此可以推想:古代中国文字的形式本身便具有内在的力量。……文字的力量来源于它同知识的联系;而知识却来自于祖先,生者须借助于文字与祖先沟通。这就是说,知识由死者所掌握,死者的智慧则通过文字的媒介而显示于后人。”(注: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二)财富的增加依靠政治权力带来的劳动力增加,而不是生产力的作用
张光直提出,中国国家起源中,是政治权力导向财富,即由“贵”而“富”,而非由“富”而“贵”。在古代宗法制度下,政治权力由个人在亲族群中的地位而决定,而政治权力越大,统治者便可获得更多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财富。从考古资料上看,从仰韶到龙山到三代,在生产工具方面没有出现突破性的变化。中国古代国家财富的增加和集中,几乎全然是靠劳动力的增加、靠将更多的劳动力指派于生产活动和靠更为有效率的经营技术而产生的。换言之,财富之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积累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而达成的。(注: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74页。)
张光直的上述观点,揭示了政治手段在财富积聚中的重要作用,对于研究中国国家起源的特点有启发意义。张光直认为,三代时期的青铜器是作为祭祀的礼器和战争的武器,而没有大规模作为生产工具使用。他的这一观点被一些考古材料所证伪。1989年江西新干县大洋洲的商代大墓,出土商代中后期的青铜器475件。其中,青铜工具占18种、143件,并且形成了平分秋色的两个工具群:其中6种75件属于手工业工具群,12种68件属于青铜农具群。江西大洋洲出土的这70多件青铜农具表明,比较发达齐全的青铜农具群的出现,最晚是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殷商后期。这次考古发现,第一次以考古实物肯定了中国历史上的确存在青铜农具体系(注:王东:《中华文明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83页。)。
三、批判地回应
张光直关于国家起源模式和动力因素的有关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张光直对马克思的国家起源理论也提出了质疑,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批评马克思忽略了对巫术、原始宗教等因素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认为萨满巫术在中国国家起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二,批判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认为中国国家起源中并没有生产工具的突破性变化,财富主要靠政治手段来获得;第三,批评马克思的国家起源理论只是在总结西方国家起源的有关资料上形成的,因而对东方和中国国家起源缺乏解释力和普适性。
(一)关于巫术和原始宗教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问题
张光直注意到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巫”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生产力在中国国家起源中并不占据根本性地位,在“政治权力的获取和增加上,‘巫’这类人物和他们的作业与所代表的宇宙观,要发挥绝大的作用”(注: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91页。)。他进而指出,中国的青铜器主要是为统治者争取与维护政治权力发明制造的。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祭祀中巫师沟通天地的法器,而青铜器上面的动物纹饰也主要为了协助巫觋沟通天地。
关于青铜纹样的意义,《吕氏春秋》的解释较为准确。如《慎势》:“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意思是周鼎上刻铸物象,是为了让事理通达,而事理通达则是人君的行政处事之道。这些历史文献表明,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与巫术和宗教没有直接关系,其功用在于宣德训诫、垂范后世。再者,根据观察,虎食人纹上夹在兽口的人头,其面多露惊恐之色,这不应该是巫觋做法时的神情。
张光直的“萨满巫教论”之所以错误,在于他没能从根本上把握住三代政治“神道设教”的现实主义本质。学术界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三代政治尤其是夏商政治是一种神权政治,受占卜等巫术活动的主导。其实,在占卜过程中,并非是巫觋居于统治地位,而是统治者尤其是国王主体性的充分表现。殷人占卜敬神只是为了把国王的意志神圣化,国王借敬神统一思想,以达到加强王权的目的。譬如,盘庚曾借神权否定族众的“协比谗言”,下决心为国家的利益“震动万民以迁”殷。
张光直关于萨满巫教的理论,显然夸大了“巫”的作用,忽视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重要地位。所谓“巫”能通天的原理,远不如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观能更清楚地解释人与人、人与天相互之间的关系。
(二)关于生产工具、生产力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问题
张光直在《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早期国家起源的一项重要的特征,是政治权力导向财富。一般而言,增加财富的生产力,“不外两条途径:增加劳动力,或改进生产工具与技术。”张光直认为,中国国家起源中的财富集中,并不是象马克思等人所言的依靠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方式而达成。它几乎全部依靠操纵生产劳动力而达成的,靠将更多劳动力指派于生产活动和靠更为有效率的经理技术而产生的。换言之,财富之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而达成的。
张光直的上述论述有合理之处,但他对马克思的指责却是站不脚的。首先,张光直关于国家起源时期的“财富之相对性与绝对性积蓄主要靠政治程序而达成”的观点是缺乏经济学理论支持的。马克思在他的论著中,曾明确区分“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中,“资本积累”类似于张光直所言的财富的“绝对性积蓄”,它必须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改进物质生产工具等生产力手段来完成。“资本集中”则类似于张光直所言的财富的“相对性积蓄”,它可以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产权关系,制定再分配制度等政治手段来完成。张光直没能区分财富的相对性积蓄和绝对性积蓄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形式,因而错误地认为财富的绝对性积蓄也是主要依靠政治程序来完成。
其次,张光直怀疑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文明化的根本动力,进而怀疑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正确性。我们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出在张光直对“生产力”概念做了狭隘的理解。由于受职业习惯影响,一些考古学家偏爱从生产工具的角度去把握生产力的水平(因为生产工具能找到直接的物质遗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生产力是一个综合性指标,除了物质性的生产工具以外,还包括一些观念形态的东西。张光直所说的社会进步主要依靠“将更多的劳动力指派于生产活动和靠更为有效率的经营技术”,他没有能认识到生产活动的经营和管理也是生产力进步的一种表现。同时,伴随生产力的提高,直接要求生产方式社会化和生产组织管理的专业化、官僚化和复杂化,从而带动上层建筑的进化,导致国家制度的产生。因而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三)关于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的解释力和普适性问题
张光直认为,西方有关中国古代政治的理论,以东方社会(oriental society)这一概念为其核心。张光直认为,“无论马克思、韦伯还是魏特夫都没有掌握中国三代社会的考古材料;他们对东方社会特征的描述和对其形成原因的推断,是根据对后期历史,而且常常是转手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来的。”(注: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马克思对中国的论评正表明了……他对亚洲历史认识的最大局限。同样,马克思构想了一个静态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制度,并不符合我们所认识的古代中国城镇与城市的图像,这些城邑在一个不断变迁的经济与政治的分层系统中互相施加能动的影响。”(注: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00页。)
张光直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简单地归为纯粹的西方派,忽略了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其实,马克思晚年笔记中的国家起源思想,已远远突破了张光直批评马克思时所总结的几个特点。譬如,马克思在晚年笔记中,非常重视国家起源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制度在国家制度中的重要作用。遗憾的是,不知是没能看到马克思晚年的这些文献,还是出于其他原因,张光直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只字不提,仍然简单地认为马克思主张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就是地缘关系取代血缘关系。张光直还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是代表西方社会科学对古史分期的研究,而在这个古史分期之外,有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这代表了西方社会科学法则里所不能解决的若干东方现象”(注:徐苹芳、张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燕京学报》第六期。)。的确,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主要是以西方文明为研究范例得出的,但他也非常关注东方的社会历史发展。无论是在马克思的中期著作,还是在晚年笔记中,我们都能看到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所做的深入探究,而且,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也正是由马克思本人提出的,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解释中国国家起源较为合适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