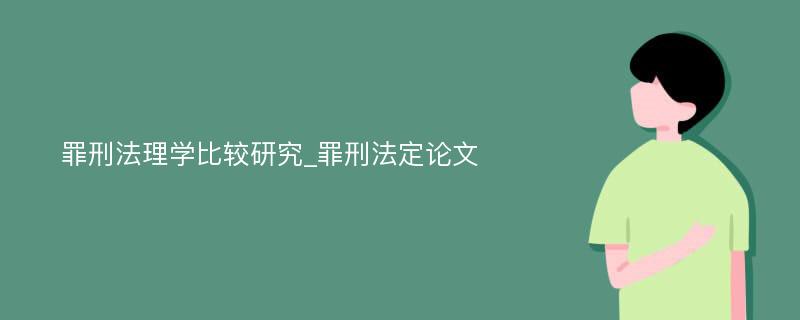
罪刑法定主义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刑法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罪刑法定主义的意义
所谓罪刑法定主义,是指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对这种行为处以何种刑罚,必须预先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的原则。对这一原则的表述,外国学者也不尽相同。日本学者金泽文雄说:“所谓罪刑法定主义是没有以成文的法律预告在犯罪之前的规定,就没有犯罪也没有刑罚的原则”。[1]中山研一教授说:“所谓罪刑法定主义是为了刑罚某种行为,在该行为实行以前,用法律将它规定为犯罪并且应当科处的处罚的种类与程度也必须用法律加以规定的原则。”[2]根据上述定义,罪刑法定主义具有如下特点:1.犯罪与刑罚必须由成文的法律加以规定;2.必须在犯罪以前预先加以规定;3.没有法律规定就没有犯罪;4.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刑罚,即不论对社会有多大危险的行为,如果法律没有预先将它作为犯罪规定时,不得处以刑罚;即使根据法律作为犯罪处罚时,也不得用法律预先规定的刑罚以外的刑罚处罚。
罪刑法定主义的观点,在十七、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就已出现。英国古典自然法学派代表之一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中,曾明确提出:“……以法律规定的刑罚处罚任何社会成员的犯罪。”[3]他认为只有立法机关才享有制定法律的权利,这种权利不能转让给任何他人。国家“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4]洛克的罪刑法定思想成为古典学派所主张的罪刑法定主义的先河。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里亚极力主张罪刑法定主义。他明确提出:“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只有代表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立法者才拥有这一权威。”[5]又说:“当一部法典业已厘定,就应逐一遵守,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6]被誉为近代刑法学之父的费尔巴哈,1801年在他的刑法教科书中,用拉丁语以格言的形式表述罪刑法定主义的三原则:“无法律则无刑罚”、“无犯罪则无刑罚”、“无法律规定的刑罚则无犯罪”。从此,罪刑法定主义被定式化,并且表示罪刑法定主义的三个格言得到广泛传播和引用。
罪刑法定主义是针对法国大革命前封建专制国家的罪刑擅断主义而提出的。“所谓罪刑擅断主义,是不以明文预先规定犯罪与刑罚,以如何的行为为犯罪,对之应当科处如何的刑罚,国家的首长或代表它的法官任意加以确定的主义。”[7]在罪刑擅断主义支配下,国家机关恣意行使刑罚权,人权丝毫得不到保障。罪刑法定主义则意图限制基于国家权力的刑罚权的恣意行使,而保护个人的权利,因而它具有自由保障的机能。所以“罪刑法定主义的本质,不是仅仅基于形式的概念而被维持的,勿宁说是基于限制国家的刑罚权而保障国民的人权的刑事人权思想而应予维持。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的命题,应当解释为在近代刑法的黎明期这一历史的背景下,刑事人权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8]正因为此,所以罪刑法定主义,被普遍认为是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或者如日本学者大野义真教授所说:“由于费尔巴哈,罪刑法定主义作为刑法的大原则,在刑法学上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9]
二、罪刑法定主义的沿革
(一)罪刑法定主义的早期渊源
根据德国学者修特兰达(Schottlander)1911年发表的《罪刑法定主义的原则的历史的展开》一文的研究,罪刑法定主义渊源于远在中世纪的英国大宪章。1215年英皇约翰在贵族、僧侣、平民等各阶层结成的大联盟的强烈要求下签署了共49条的特许状,这就是著名的大宪章(Magna charter)。其第39条规定:“凡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内国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这被修特兰达认为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渊源。这一观点为后世很多学者所接受,成为刑法学界的通说。
不过也有某些学者如泽登佳人、风早八十二、横山晃一郎等教授均反对这一见解。日本的横山教授对此说提出质疑说:“由费尔巴哈所确定的近代刑法的罪刑法定主义,如果认为起源于英国的大宪章,那么在成为罪刑法定主义渊源的英国,就要承认不成文的普通法是法渊,可是在英国直到今天近代刑法不是还不存在吗?其次,成为罪刑法定主义的派生原则的排除习惯法,与不成文的普通法为法源的英国刑法之间也存在着理论上的矛盾。的确,依照被费尔巴哈定式化的近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主义,要求以成文的法规明确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关系。这样限于以成文的法规为前提,是当然的结论,要求将不成文法从刑法渊源中排除。”[10]他的结论是英国的大宪章不可能成为罪刑法定主义的渊源。
但更多的学者如泷川幸辰、木村龟二、大谷实、大野义真等教授还是支持通说的观点。大野教授对上述质疑反驳说:“费尔巴哈在以前所主张的罪刑法定主义的概念,未必意味着罪刑的成文法规定主主义,勿宁说这个原则本身,只是一种伴随着历史的发展的意义的思想,求罪刑的法定这种情况的法,不必以本来成为成文法的性格为必要。”[11]同时他进一步论述说:“大宪章的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在英国法制史上开辟了新的一章,以大宪章为标志,根据宪法确立了法的支配这一事实。由于大宪章后世几次被确认,作为英国国法的不变部分占有确定不移的地位,并形成英国人权思想的分水岭而固定下来。……在它的历史的发展的意义上,大宪章成为近代英国中的刑事人权思想的历史的渊源。罪刑法定主义,在其本质上被刑事人权思想支配的范围内,大宪章的确可以说是罪刑法定主义的历史的、思想的渊源。”[12]在我们看来,大野教授认为费尔巴哈所主张的罪刑法定主义并不以成文法为前提,是不符合费氏的本意的,费尔巴哈明确提出:“没有法律,也就不存在市民的刑罚。现在的法律不适用时,刑罚也不能适用。”[13]这里所说的法律,自然是指成文法而言。所以日本学者正田满三郎说:费氏的学说,“应当称为制定法主义的刑法理论”。[14]因而大野的这一反驳不能成立。但他下面论证大宪章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渊源的观点,我们是赞同的。因为大宪章第39条毕竟具有保障人权的意义,而罪刑法定主义的核心被认为是限制法官的恣意、保障公民的人权。在这个意义上亦即从实质上看,说罪刑法定主义渊源于中世纪的英国大宪章,无可厚非。在日本,泷川幸辰教授1919年发表《罪刑法定主义的历史的考察》以来,以大宪章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历史的渊源的见解,已经成为通说。
(二)罪刑法定主义的发展
大宪章之后,罪刑法定主义的思想,伴随着人权思想的展开,在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Petition of rights)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Billof rights)中反复被确认。《权利法案》的宗旨主要在于限制王权,巩固和扩大国会的权力,从而它正式确立了国会主权的原理和法支配的原理,促进了罪刑法定主义在欧洲的传播。此后,罪刑法定主义远渡重洋,传到北美。英国在北美诸州的殖民地于1772年11月20日在波士顿举行集会,要求承认大宪章及1689年的《权利法案》中所规定的权利。1774年10月14日在费城召开的殖民地总会,发表了主题为“居民依据自然法,拥有不可侵夺之权”的宣言书,其中第5条揭示了罪刑法定主义。1776年5月16日在费城召开十三州的殖民地总会(又称大陆会议),决定宣布独立,由各个殖民地自行制定根本法。在此基础上首先出现的是1776年6月12日公布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其第8条规定:“……除了国家法律或同等的公民的裁判外,任何人的自由不应受到剥夺。”这一规定被誉为美国法律中最初的罪刑法定主义的原则的宣言,以后为许多州所仿效。同年7月4日,正式宣布成立美利坚合众国。1787年颁布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事后法的禁止(宪法第1条第9款第3项规定:“……追溯既往的法律不得通过之”),1791年生效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适当的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原则(修正案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罪刑法定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果说在以普通法为主体的英美法,罪刑法定主义主要从程序方面加以规定,那么它在实体上得到明确表现的,是1789年法国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通常简称为《人权宣言》,其第8条规定:“法律只应当制定严格地、明显地必需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违法行为之前制定、公布并且合法地适用的法律,任何人都不受处罚。”这一规定为法国1791年宪法和刑法典所采用。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继续采纳这一原则,其第4条规定:“不论违警罪、轻罪或重罪,均不得以实施犯罪前未规定之刑罚处罚之。”从此,罪刑法定主义成为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因而《法国刑法典》被认为是罪刑法定主义的直接渊源。《法国刑法典》的这一规定,以后为其他国家的刑法典相继仿效,成为许多国家刑法的共同原则。
三、罪刑法定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
罪刑法定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什么?学者们的看法虽然有不少相同之处,但也不尽一致。日本著名刑法学家泷川幸辰博士认为,支持罪刑法定主义的,有三种不同的根本思想:即第一是作为英吉利的自由的基石的大宪章思想,第二是宾丁所说的平衡理论,亦即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理论,第三是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分权理论。[15]在大谷实教授看来,为罪刑法定主义“提供理论基础的,从来都会举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和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现代的罪刑法定主义,应当解释为以将自由主义作为要旨的人权尊重主义为根据。”[16]本村龟二教授指出:“罪刑法定主义的原则是在两个思想的背景之上成立的,共同是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是作为国法的思想的三权分立论,另一是作为刑事政策思想的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17]大野义真教授则认为:“罪刑法定主义是以人权思想为支柱,追求个人自由的长期斗争的历史中培养起来的一个原则。它虽然是以已经成为过去的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理论为直接的契机在刑法上确立的,但形成这个原则的思想的基础不是基于单一理念的一元的,最后,支持这一原则的思想的不外是发自于大宪章的自由主义、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法治国思想(法的支配)及法的安定性的理念。而且在现代,除此之外,作为这一原则基础的,国民主权的原理(民主主义)或尊重人性的责任原理被正式提倡。”[18]比较上述诸说,我们认为罪刑法定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不是一元的见解是正确的;同时认为现代罪刑法定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由于时代的变迁,与罪刑法定主义产生的思想理论基础,确实有所不同,不应混为一谈。
关于罪刑法定主义产生的思想理论,我们不赞成大宪章思想是罪刑法定主义思想基础的观点。正如外国学者阿达木(G.B.Adams)所指出的:“大宪章不是打倒封建制度标榜近代意义的自由的文献,它不外是在封建制度内自古以来被承认的关于英国人的自由,阻止由于早被确立的王权的滥用,确认所谓封建的自由。从而大半可以看出,在它的条项之中,纯粹具有封建色彩的规定,或者意味着对封建的滥用的立法的修正的诸规定。”[19]据此,我们认为,就自由思想这一点而言,虽然可以说大宪章是罪刑法定主义久远的渊源,但不可能成为近代刑法大原则的罪刑法定主义产生的思想理论基础,因为罪刑法定主义毕竟是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刑法的产物,它产生的思想理论基础,只能求之于启蒙思想家的思想理论。参考上述诸家见解,我们认为,罪刑法定主义产生的思想理论基础,可以举出如下三个方面:
1.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 十七、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对当时的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们提倡理性主义,主张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等,对后世以很大影响。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他们之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大体上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倾向称为国家主义学说,另一种倾向称为自由主义学说或个人主义学说。这种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为罪刑法定主义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英国的洛克认为,人们原来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中人们是自由的、平等的,根据自然法他们享有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同时不能侵犯他人的这些权利,但每个人的这种权利经常会受到他人的侵犯。“为了有效地限制人的随心所欲,才相互订立契约,组成国家团体,以资保障权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们需要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给国家,国家必须根据各人委托人权利的总和——权力,尽力维持秩序。”[20]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国家拥有对违反者处罚的刑罚权,但国家的立法权和刑罚权的目的,只能是增进个人的幸福。对违反者只能按规定处以刑罚,而决不能用来损害个人的权利;否则就违反了人们缔结契约、结成国家的宗旨。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它的保障人的权利的思想,被认为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核心思想。因而可以说,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为罪刑法定主义提供了根本的思想理论基础。
2.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论 孟德斯鸠也是启蒙思想家,主张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但是他所提倡的三权分立论是罪刑法定主义在政治法律方面的直接思想基础。孟德斯鸠把政体分为三种,即共和、君主和专制,认为掌握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侵犯个人自由。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保障个人自由,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为此,他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由各个国家机关分别掌握,互相分立。他之所以主张三种权力分立,因为在他看来,“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权力。如果一个人或是……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21]所以三种权力必须分别行使,互相制衡。立法机关负责制定法律,裁判机关只能适用法律,并且必须受法律的拘束,法官则是机械地适用法律的工具,法律的解释属于立法权的领域,不允许法官解释法律。因为建立自由的,仅仅是法律,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个人的自由,避免法官的擅断。在刑事裁判上,犯罪与刑罚必须预先以法律加以规定,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的,法官不能论罪,也不能处罚。“这样的思想,导至确定罪刑法定主义的原则。”[22]
3.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 心理强制说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在它的主张者费尔巴哈时代被称为“法律理论”,费尔巴哈叫做“实定法的理论”,宾丁名之为“平衡说”。在此说的主张者费尔巴哈看来,人具有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本能。他指出:“人欲求快乐,所以努力得到一定的快乐,人又想逃避一定的痛苦。……因而人在可能获得较大的快乐时,就断绝较小的快乐的意念;而可能避免较大的痛苦时,就会忍耐较小的不快乐。基于欲望不满足的不快乐,使他因而避免这种不快乐,刺激要满足欲望。”[23]人们犯罪就是由于在犯罪时获得快乐的感性冲动而导致的,所以为了防止犯罪,就需要防止、抑制人的这种感性冲动。为了抑制人的这种感性冲动,就要利用犯罪欲求能力这种感性本身,采用成为感性害恶的刑罚,对犯罪加之以痛苦。详言之,为了防止犯罪,必须抑制行为人感性的冲动,即科处作为感性害恶的刑罚,并使人们预先知道因犯罪而受到的痛苦,大于因犯罪所得到的快乐,才能抑制其心理上萌生犯罪的意念。换句话说,行为人由于确信实施犯罪的欲望会带来更大的害恶,就会抑制犯罪的意念而不去犯罪。为了起到心理强制的作用,需要预先用法律明文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关系,以便预示利害,使人们知晓趋避。费尔巴哈主张的罪刑法定主义,正是作为心理强制说的结论而被确立的。
四、现代罪刑法定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
由于时代的变化,人们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尊重人权思想的加强,一些学者认为,罪刑法定主义已不能限于从形式上理解,因而它的思想理论基础,较之过去也有所不同。现代罪刑法定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可有以下两方面:
1.民主主义 大谷实教授认为,现代罪刑法定主义“第一,以什么作为犯罪,对它科处什么刑罚,应该以国民亲自决定的民主主义的要求为根据。”[24]民主主义原是西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民汲取法西斯独裁统治的血的教训,更加珍视民主主义,人民的这种要求在一些国家的宪法中也有反映,“主权在民”,人民参加国家的管理,不再是一种口号,在不少国家还不同程度地变成现实。根据民主主义的要求,犯罪与刑罚必须由国民的代表机关即议会制定的法律来规定。这就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恣意行使的危险,必须由民主制定的法律规定犯罪与刑罚。
2.人权尊重主义 大谷实教授指出,现代罪刑法定主义“第二,以为了保障基本的人权特别是自由权,必须将犯罪与刑罚事前对国民明确,能够预测自己的行为是否被处罚的人权尊重主义的要求(自由主义的要求)为根据。”[25]罪刑法定主义的核心,本来就是保障个人的权利,但经过法西斯专制统治一度对人权和人的尊严的践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人权的保障引起特别的关注。人们不仅要求在程序法上保障人权,而且要求在实体法上也保障人权;不仅要求在司法方面保障人权,而且要求在立法方面也要保障人权。根据人权尊重主义的要求,必须事前向国民明示什么行为是犯罪,并且只能在所预告的范围内适用刑罚;同时禁止从事以事后的法律处罚行为人,以保障其自由和人权。
五、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
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是什么?学者之间意见颇有不同。德国学者贝林格、修特兰达(Schotlander)认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包括如下四点:1.排除习惯法于刑法规范之外;2.刑法不承认溯及效力;3.刑法上不许不定期刑;4.不许类推。迈耶亦主张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有四点,但稍有不同:1.除非法律规定,不得科刑;2.习惯法从刑法的渊源中除外;3.刑法中不允许类推;4.刑法无溯及效力。[26]日本刑法学者内田文昭则认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包括:1.法律主义;2.刑罚法规明确性的原则;3.罪刑均衡原则——残虐刑罚的禁止;4.绝对不定期刑的禁止;5.类推解释的禁止;6.事后法的禁止。[27]内藤谦教授主张,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分为形式方面和实质方面。前者包括:1.法律主义;2.事后法的禁止;3.类推解释的禁止;4.绝对的不定刑的禁止。后者包括:1.明确性原则;2.刑罚法规正当的原则。[28]金泽文雄教授简要论述罪刑法定主义内容的演变说:“第一是成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的所谓派生原则的发展,从来可以举出:1.习惯法的排除(没有成文的法律则没有犯罪);2.刑法效力不溯及(没有事前的法律则没有犯罪);3.类推解释的禁止(没有严格的法律则没有犯罪);4.绝对不确定刑的禁止(没有法律则没有刑罚)四个派生的原则。在现代,对此增加,5.明确性原则(没有明确的法律则没有犯罪)作为新的派生的原则被承认;又6.判例不溯及的变更,即判例的不利的溯及变更的禁止的原则被提倡,进而,7.实体的正当原则(没有适当的法律则没有犯罪)也成为有力的,进而又8.重刑罚不溯及(没有事前的法律则没有刑罚)及轻刑罚的溯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1款后段)被承认。此外,罪刑法定主义也及于保安处分,效力不溯及原则也及于公诉时效,今日都作为重要问题继续被讨论。可以预料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的发展今后还将继续。”[29]我们认为,罪刑均衡和残虐刑罚的禁止,虽然可以认为属于实体的适当原则的内容,但它们不仅是罪刑法定的问题,而且涉及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即它们不仅在立法上体现,而且在司法上和行刑上体现,所以不宜认为它们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派生的原则。将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分为形式方面和实质方面两类,也未必妥当。如将明确性原则列为实质方面的内容,就值得研究。因为法律用语应当明确,也可以说是立法形式的要求。在我们看来,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过去曾经形成通说,现在又增加新的内容,因而可从以下两方面论述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一)传统的,(二)新增的。
(一)传统的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及其发展
从来的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或者说罪刑法定主义的派生原则,通说认为有以下四项:
1.排斥习惯法,即刑法的渊源只能是由国会通过的成文法。法院对行为人定罪判刑只能以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成文法律为根据,而不能根据习惯法对行为人定罪处刑。这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刑”的当然结论。《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35条规定:“在作有罪的宣告时,必须指明……适用的法令。”但一些学者认为,习惯虽然不能直接成为刑法的渊源,但对刑法所规定的一定概念的解释,常常不能否定习惯的意义。所以关于犯罪的成立要件和刑罚的量定,在不少情况下仍然要根据习惯、条理来决定。首先关于犯罪的成立要件,例如《日本刑法》第123条规定的妨害水利罪,成为妨害对象的水利,虽然必须是属于他人的水利权,但这种水利权,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根据习惯来认定。其次关于刑罚的量定,由于刑法对自由刑、财产刑的成文规定范围宽广,法官具有较大裁量的余地,在裁量刑罚时很可能根据习惯、文化观等量定刑罚。大谷实教授指出:“‘不违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习惯,限于法律没有规定的事项,与法有同一的效力’(法例第2条),这一规定对刑法是不适用的;但是在法律上有根据而且习惯、条理的内容是明确时,由于没有排除它的理由,所以关于刑罚法规的解释或违法性的判断等,习惯、条理具有刑罚法规的补充的机能,不应否定。”[30]
排斥习惯的提法,后来不少学者以法律主义或者罪刑的法定的提法来代替。论述的内容除排斥习惯法之外,还涉及政令与罚则、条例与罚则和判例的法源性问题。
政令与罚则:根据法律主义的原则,行政机关制定的政令本身不能独立设立罚则。《日本国宪法》第73条第6项但书规定:“但政令中除有法律特别授权者外,不得制定罚则。”据此日本学者认为,限于法律特别委任(具体的个别的委任)的场合,承认在政令中创设罚则。
条例与罚则:以条例设置罚则也被认为违反罪刑法定主义。但日本《地方自治法》第14条第5项规定:“普通地方公共团体除法令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在条例中对违反条例者可设置科处二年以下的惩役或者监禁、十万元以下的罚金、拘留、科料或没收之刑的规定。”日本学者认为,这一规定是对地方公共团体制定罚则的包括的委任,因而不生违宪问题,并且条例与行政机关制定的命令不同,是基于居民的代表机关的地方议会的决议而成立的自主的立法。在这个意义上,与“法律”同样,符合代表制民主主义的要求。条例实质上具有准法律的性质。[31]
判例能否成为刑法的渊源?大陆法系国家,一般持否定观点。作为法律主义的要求,判例的法源性自然应予否定。因为不是成文法的规定或者超越了成文法的范围,判例不能成为法源,是当然的结论。但也有些学者认为,“罪刑法定主义要求犯罪的定型化;不过,只以法律的规定,即使用多么精密的表达记述犯罪的成立要件,犯罪的定型也只能抽象地规定。由于就各个具体的案件法院所下判断的积累,犯罪定型的具体内容开始形成起来。承认判例有这样意义的形成的机能,不但不违反罪刑法定主义,实际上勿宁应当说是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此外,对否定犯罪成立或可罚性的方向的判例的机能,也与罪刑法定主义没有矛盾。”[32]因而认为判例在成文法规的范围内具有法源性。
2.刑法无溯及效力,即不许根据行为后施行的刑罚法规处罚刑罚法规施行前的行为,通常也称为“事后法的禁止”。如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4条规定:“不论违警罪、轻罪或重罪,均不得以实施犯罪前未规定之刑处罚之。”这是因为行为人只能根据已经施行的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所以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必须预告由法律规定犯罪与刑罚并公之于众,以便人们知所遵循。否则,如果以行为后施行的刑法为根据处罚施行前的行为,这对行为人实际上是“不教而诛”。不仅如此,既然行为时的适法行为,可以由行为后的法律定罪处刑,人们就无法知道自己的行为今后是否被定罪处罚,不免惶恐不安,无所措手足,这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所以刑罚法规,只能对其施行以后的行为适用,而不能溯及适用于施行前的行为。这也是实质的人权保障的要求。
由于承认刑法无溯及力的理由是刑法的溯及适用有害于法的安定性并有非法侵害个人自由的危险,因而西方学者从“有利被告”的原则出发,对刑法无溯及力的观点后来有所改变,即在行为时法与裁判时法有变更时,裁判时法如果是重法,没有溯及力;如果是轻法,则有溯及力。学者一般认为,这不违反罪刑法定主义。1871年《德国刑法典》第2条第2款规定:“从所犯之时到判决之间,有法律之变更时,适用最轻之法律。”根据1935年6月26日法律,该款改为“判决时施行的法律如较行为时施行的法律为轻,得适用较轻的法律,案件判决时,如此行为依法律已不处罚,得免予处罚。”尔后,轻法溯及得到广泛的认可。
3.禁止类推解释。类推解释是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事项,援用关于同它相类似的事项的法律进行解释。按照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行为之被认为犯罪和处罚,必须依据事先由法律明文所作的规定。而类推解释则是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事项创造法律,是由法官立法,从而根据类推解释的处罚,超越法官的权限,将导致法官恣意适用法律,侵害个人的自由权利,显然有悖于罪刑法定主义的原则。因之一些学者主张:禁止类推解释,实行严格解释。战前《日本宪法》虽然规定了罪刑法定主义,但由于牧野英一教授等强调自由法运动与目的论的解释方法,主张刑罚法规的类推解释,能够适应社会的进步,应当加以肯定,以致允许类推解释的观点,在日本一度处于支配地位。战后,由于日本新宪法强调罪刑法定主义,在日本对类推解释的观点复发生变化,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又成为通说。不少学者主张禁止类推解释,允许扩张解释,认为类推解释与扩张解释的区别在于是否超越法律文字可能的含意的范围。本村龟二教授即持此主张,他说:“类推解释与扩张解释的不同在于:扩张解释限于刑法成文语言的可能意义的界限内,相反地,类推解释超越其可能意义的界限,从而对成文没有规定的事项承认刑法规范的妥当性。”[33]与此相反,有的学者如植松正教授认为,不许类推,容许扩张解释不外是语言的魔术,明确主张“刑罚法令中的类推某种程度上必须允许。”[34]还有学者认为,类推适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原理的法律主义,即使是扩张解释也不允许。[35]根据罪刑法定主义的宗旨在于保障行为人的自由权利,所以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虽然主张加以禁止,但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则是允许的,即容许阻却犯罪成立事由、减轻、免除刑罚事由等的类推解释。所以有的学者如内藤谦教授明确提出:“不允许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是罪刑法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36]罪刑法定主义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禁止类推,而只是禁止设立新的刑罚和加重处罚这样的类推解释,而不禁止排除违法性、减轻或免除刑罚这样的类推解释。
4.否定绝对不定期刑。这一原则是由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对一定的犯罪规定刑罚的种类和程度而产生的。绝对不定期刑是在法律中完全没有规定刑期的自由刑。现代学派的学者认为,犯罪是由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所产生,刑罚是矫正、改善罪犯的主观恶性的手段;但对改造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要求多少时间很难预料,所以法律只能规定不定期刑。法官在判决时,只宣布罪名和刑种,至于究竟服多长刑期,则由行政机关根据罪犯主观恶性改造的情况来决定。这样确定罪犯的服刑期间长短的权力完全由行刑机关所掌握,这会丧失刑法保障人权的机能。所以不论法定刑或宣告刑都不允许绝对的不定期刑。但绝对确定的刑种和刑期,使法官不能根据具体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社会危险程度判处相适应的刑罚,只能机械地作为法律的“传声筒”,这不利于案件的正确处理。因而现代学派的学者提出相对的不定期刑的主张。他们从目的刑论出发,认为刑罚的目的是矫正罪犯,使之复归社会;但需要多少时间方能达到刑罚的目的,则很难预期,因而可以规定和宣告最长期限与最短期限,在这个幅度内,由行刑机关确定实际执行的刑期。对此,理论上有人认为法定刑幅度太广的刑罚法规,给予法官极端的裁量权,由于在各个场合科处怎样的刑罚不明确,因而不符合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但有学者明确提出:“相对的不定期刑……,不认为违反罪刑法定主义。”[37]事实上当前世界各国刑法典分则中的法定刑绝大多数为相对的不定期刑。因为它便于法官考虑各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裁量刑罚;当然过于广泛的幅度,有悖于罪刑法定主义的宗旨,实不可取。
(二)新增的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
1.明确性原则 刑罚法规的明确性,虽是罪刑法定主义成立当时的要求,但明确性原则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新的派生原则被承认,则是近来的情况。
明确性原则要求立法者必须具体地并且明确地规定刑罚法规,以便预先告知人们成为可罚对象的行为,使国民能够预测自己的行动,并限制法官适用刑法的恣意性。否则,如果规定的刑罚法规含混不明,就不能达到上述目的,是违棿罪刑法定主义的宗旨的,从而认为是无效的。所以明确性原则,又称“含混无效原则”。这一原则,通常认为是关于构成要件的问题。德国学者威尔哲尔(Welyel)、鲍曼(Baumann)进而认为,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也要揭示“法的效果的明确性”,即“刑罚法规明示可罚的行为的类型之同时,也要求以刑罚的种类、分量明示可罚性的程度。”[38]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完整地表述了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关于明确性的标准,提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如大谷实教授认为,“应当以有通常的判断力者能够认识、判断的程度为明确的标准。”[39]金泽文雄教授认为,“关于犯罪的构成要件,成为该刑罚法规的适用对象的国民层的平均人,根据法规的文字不能理解什么被禁止的场合,是不明确的、违宪的。”[40]我们认为这一标准是可取的,因为法律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只有通常的人能够理解,才能以之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
2.实体的适当原则,或称刑罚法规适当原则或者适当处罚原则 指刑罚法规规定的犯罪和刑罚都应认为适当的原则。原来罪刑法定主义只理解为“无法律则无犯罪也无刑罚”,只要有法律的规定,不管刑罚法规的内容如何,都被认为不违反罪刑法定主义。但60年代以来,由于受美国宪法中适当的法律程序原则的影响,日本一些学者如团藤重光、平野龙一、芝原邦尔等教授在提倡明确性原则的同时,还提出承认实体的适当原则为罪刑法定主义的新的派生原则。随后,这一原则逐步为日本刑法学界所接受。他们认为受美国宪法影响于1946年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第31条的规定是实体的适当原则的宪法根据。该条规定:“任何人非依法律所定程序,不得剥夺其生命或自由,或科其他刑罚。”在日本学者看来,该条规定不仅要求程序的适当,而且要求刑罚法规的实体内容的适当。刑罚法规的内容不适当时,被认为违反宪法第31条而成为违宪。团藤教授说:“宪法第31条如前所述是由来于美国的适当程序条款,从而虽然没有‘适当的’这种表述,但当然必须说要求罪刑的法定是适当的。在不仅程序而且实体必须适当这个意义上,美国所谓的‘实体的适当程序’的要求,我国宪法的规定也应当被承认。”[41]他们认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宗旨是保障人权;实体的适当原则体现着实质的保障人权原则,它符合罪刑法定主义本来的宗旨,应该说是当然的。至于这一原则应当包括哪些内容,看法颇不一致。团藤教授认为它包括刑罚规定的适当和罪刑的均衡。大谷实教授原来认为它包括刑罚法规适当的原则和罪刑的均衡,后来又认为实体的适当原则即刑罚法规适当的原则,它包括明确性原则、刑罚法规的内容的适当和绝对的不定刑的禁止。此外,还有一些不同见解。我们认为,大谷教授原来的观点,在论述刑罚法规适当原则时,涉及了什么行为值得处罚,这是可取的;但标题与实体的适当原则同义,是一大缺点。后来他作了修改,表明认识到原来的提法不当,但将明确性原则与绝对的不定刑的禁止列在实体的适当原则之内,也难认为妥贴。因为明确性原则是从语言表述形式而言的,实体的适当原则是就法规内容的实质而言的,不宜将两者混在一起。大谷教授曾说:“既述的明确性原则不能直接从这一原则(按:指实体的适当原则)导出。”[42]这是正确的。现分别阐述:
(1)刑罚规定的适当,指对某一行为作为犯罪规定刑罚有合理的根据。据此,刑法规定的犯罪,必须是以该行为确实需要用刑罚处罚为前提。“犯罪与刑罚即使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但其内容欠缺处罚的必要性和合理的根据时,成为刑罚权的滥用,实质上就会侵害国民的人权。”[43]那么,怎样判断刑罚规定得是否适当?大谷教授曾指出:“适当的标准应依刑法的机能,特别是与法益保护机能的关系而定。即以应保护的法益存在为前提,是否有以刑罚法规保护它的必要性成为是否适当的判断标准。”[44]这一见解虽然在该书1995年第4版中被删掉,但我们认为仍然值得参考。
(2)罪刑的均衡,或叫罪刑相称或者罪刑相适应,指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轻重相均衡。这一原则曾被认为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不限于只是刑事立法方面的问题,但首先还是在刑事立法上体现,因而现在被认为是实体的适当原则的一个内容。那么怎样判断罪刑的均衡呢?村井敏邦教授指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绝对报应主义作为标准是最明确的,然而作为标准无论怎样明确,根据禁止残酷刑罚的近代人道主义观点,不可能维持它。”[45]村井教授否定了同态复仇的标准,根据贝卡里亚的有关论述,主张“犯罪的程度可以根据社会侵害性的大小来决定。”[46]至于刑罚的尺度,村井教授认为:“在社会侵害性的程度中,自由侵害被认为中心的价值。这样,根据以自由为尺度,犯罪与刑罚进行比较成为可能。由于以自由为尺度的特点,刑法从单纯同害报复思想远离。考虑自由的重要,即使对生命,也能够说自由充分保持均衡。”[47]村井教授虽然认为,对财产犯,自由刑也可以说相适应,但随后又指出:“刑罚的适当性比包含其中的罪刑的均衡是重要的原则,从这个观点看,对盗窃案常以剥夺自由的刑罚相对应是否适当,是成为疑问的。”[48]我们赞同村井教授后面的观点,因为罪刑的均衡,除应当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决定刑罚外,还应当考虑犯罪的性质确定适用的刑种。如对危害生命或危害国家安全的特别严重犯罪,可以规定死刑(在废除死刑的国家可以规定无期自由刑);对危害健康、自由、财产、社会秩序或其他严重犯罪、普通犯罪,可以规定自由刑;对财产犯罪或经济犯罪,可以规定单处或并处财产刑。这将更好地保持罪刑的均衡。
对于上述两个标准,我们虽然认为比较可取,但总感不够妥当。因为它们只谈到刑罚的适当而未涉及犯罪的规定,不免失之于片面;且在刑罚规定的适当标题下,只是论述何种行为需要作为犯罪规定刑罚,实际是犯罪规定的适当。而罪刑的均衡标题下,又难以论述残酷刑罚的禁止。据此,宜更改为:①犯罪规定的适当,②刑罚规定的适当。在后一标题下论述残酷刑罚的禁止和罪刑的均衡,这可将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刑罚法规的适当完全加以概括,从而可以避免原来标题的片面性。
3.判例不溯及的变更。如前所述,美国宪法第1条第9款第3项规定,禁止通过“追溯既往的法律”,这样的规定是否及于判例?原来认为它只是对联邦和州的立法机关制定法制而言,判例不在此限。但是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包伊上诉案的决定中改变了从前的观点,宣布判例无溯及效力。[49]从“有利被告”的原则出发,判例变更无溯及效力,只限于不利于被告的判例变更。因为不利于被告人的判例变更,如果溯及适用,成为对被告人的意外打击,与根据法律溯及及处罚一样,会有害于法的安定性。因而在美国,于被告人不利的判例变更,对将来的案件适用,对该被告人不适用的“不溯及的变更”(Perspectiveoverruling)原则在判例中被确立。随后在联邦德国将不利于被告人的判例更作为“将来效力条款”(Von-nun-an-Klausel)在判决主文中宣告。在日本小暮得雄教授从承认判例是“间接(补充)法源”的立场出发,提倡将禁止判例的不利的、溯及的变更,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50]这一见解得到日本刑法学者广泛的赞同。
日本现行宪法第39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如其行为在实行时实属合法,……不得追究其刑事上的责任。”现在日本刑法学者认为,这一禁止溯及的规定,应当扩张适用于判例变更的场合,由裁判机关进行法律解释的余地很大,国民直接看条文很难达到同一的理解,而通过判例的解释,对刑法规定的内容能够理解的程度大大增加,从而国民可能利用这样的法律解释调节自己的行动。如果对被告人不利的判例变更适用于被告人,被告人对处罚就会感到意外且不公正。为了不使产生这种情况,日本宪法第39条的禁止溯及的规定,就应当适用于判例变更。这样,判例不溯及的变更被认为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新的派生原则。小暮教授考虑日本宪法第39条与日本刑法第6条的旨趣,引伸出如下解释:“变更判例上的旧解释,将从前认为适法的行为解释为违法,或者将认为应当符合较轻构成要件的行为解释为应当符合较重构成要件,且使依赖的行为者遭受其效果,是不允许的。”[51]日本学者认为,这一见解是妥当的,并已为日本判例明确采纳。这一原则为大陆法系国家所承认,表明了在罪刑法定主义问题上两大法系的互相渗透,使罪刑法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认为这是值得肯定的。
罪刑法定主义“在现代正成为许多国家的刑法的基本原则”,[52]并得到国际法上的承认。罪刑法定主义在立法上不断增加,在理论上日益完善,这是当代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
注释:
[1][29][38][40][50][51] 中山研一等编:《现代刑法讲座》第一卷,成文党,1980年版,第85、86、94、93、95、97页。
[2] 中山研一著:《刑法总论》,成文党,1989年版,第59页。
[3][4] 洛克著、叶启芳等译:《政府论》(下),商务,1964年版,第53、88页。
[5][6] 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3页。
[7] 牧野英一著:《日本刑法》(上卷),有斐阁,1939年第64版,第63页。
[8]—[12][18][19] [日]大野义真著:《罪刑法定主义》,世界思想社,1982年版,第13、9、35、36、48、237、120页。
[13][23] [日]山口邦夫著:《19世纪德国刑法学研究》,八千代出版股份公司,1979年版,第38、27页。
[14] [日]正田满三郎著:《刑法体系总论》,良书普及会,1979年版,第11页。
[15][20][26] [日]《泷川幸辰刑法著作集》(第四卷),世界思想社,1981年版,第40—41、17、31页。
[16][30][52] [日]大谷实著:《刑法讲义总论》,成文堂,1995年第四版,第61—62、67页。
[17][22][33] [日]木村龟二著:《刑法总论》(增补版),有斐阁,1984年版,第93、94、21页。
[21] [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6页。
[24][25][39][43] [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成文堂,1995年第4版,第62、69、70页。
[27] [日]内田文昭著:《刑法Ⅰ总论》,青林书院新社,1977年版,第44—48页。
[28][31][36][37] [日]内藤谦著:《刑法讲义总论》(上),有裴阁,1983年版,第27—39页。
[32] [日]团藤重光著:《刑法纲要总论》,创文社,1979年版,第46页。
[34] [日]植松正著:《刑法概论Ⅰ总论》,劲草书房,1974年版,第90页。
[35] [日]刑法理论研究会《现代刑法学原理(总论)》,三省堂,1974年版,第77页。
[41] [日]团藤重光著:《刑法纲要总论》,创文社,1979年版,第49页。
[42][44] [日]大谷实著:《刑法讲义总论》,成文堂1986年版,第81、83页。
[45]—[48] [日]村井敏邦著:《刑法》,若波书店,1994年版,第47页。
[49] 储槐植著:《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标签:罪刑法定论文; 大宪章论文; 费尔巴哈论文; 法律论文; 英国法律论文; 刑法理论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刑法基本原则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法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