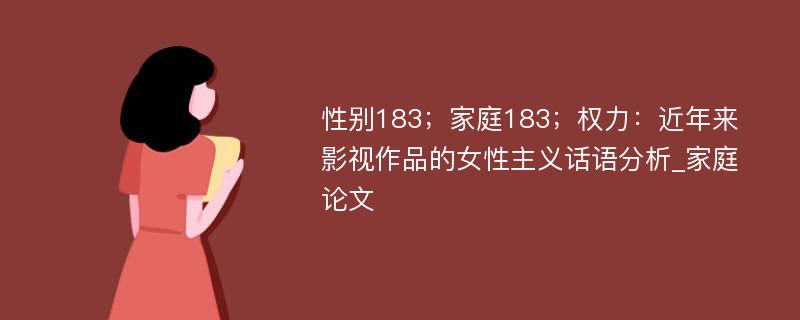
性#183;家庭#183;权力——近年来影视作品的女性主义话语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影视作品论文,话语论文,权力论文,家庭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中的权力取自福柯的用法,即“它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一种结构,也不是我们具有的某种力量,它是人们给特定社会中一种复杂的战略形势所起的名字。”(注:〔法〕米歇尔·福柯《性史》(第一、二卷)张延琛等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90页。)在福柯眼中,尽管“权力在组织机构上的具体化体现在国家机器、法律条文和各种社会领导权中,权力却首先是多重的力量关系,存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并构成自己的组织。”(注:〔法〕米歇尔·福柯《性史》(第一、二卷)张延琛等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91页。)本文主要涉及了权力在近年来影视作品中的两个动作领域:性和家庭。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话语体系,正如福柯于《性史》中发现的一样:19世纪“性的展布”(注:〔法〕米歇尔·福柯《性史》(第一、二卷)张延琛等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104—105页“性展布的存在并非因为它自我繁衍,而是它以日益细致的方式繁衍、更新、补充、创造和洞察肉体,并以日益周到的方式控制人口。‘它’是根据多变的、多形的、以及权力的随机应变的技巧而进行的。”)的四大战略走的都是家庭路线,家庭是性的展布的结晶。因此也成为性展布的“最有价值的战略成分之一。”但是,无论是在同时期的17到19世纪还是当代的中国社会,性展布和家庭远没有达到如此的契合,或者说,性的展布在中国的发展威胁到了家庭——这一旧的联姻结构的稳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社会逐步成熟,旧的联姻展布(注:〔法〕米歇尔·福柯《性史》(第一、二卷)张延琛等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104 页“一种婚姻体系,一种血亲纽带的固着与发展的体系,一种姓氏与财产的继承体系。”)在权力关系中的重要性逐渐降低,代之而起的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混合了各种商业目的的性的展布。过去曾在封建体制的权力关系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家庭的重新组合势在必行。
然而,如福柯所发现的,性话语的膨胀并不意味着人的解放,反而预示着权力对人的生命的全面掌握和调动,并形成了一整套以性为中心的知识与权力的特定机制。它们在权力的秩序中有效地起着作用。从女性主义的立场看,这种权力的新战略使女性处于被攻击的位置,处处限制着女性对自己的肯定和解放。那么权力是如何通过性展布限定了女性的自我认识和觉醒?权力在其中采用了什么技巧、手段巩固男权社会的准则?女性有无可能通过利用性话语达到对权力的置疑、反抗?这就是本文要涉及的问题。另一方面,长期处于我国权力关系运作核心的家庭,面对性的展布必定要作出反应,竭力保持它在权力关系中的重要位置。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和家庭的关系如何?这也是本文要讨论的对象。
一、男人的故事让女人搅黄了
43集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于春节前后在中央电视台隆重推出,收视率一路飘红,达到近年来的最高,而据此产生的毁誉之声也充斥报刊。偶然一翻,不禁就有了一个突出的印象:男人的故事让女人搅黄了。
众所瞩目,也是争论焦点的当然是原著里一连串淫妇形象的改编,不少专家于报端深恶痛绝的不外乎:潘金莲在三集戏里四次洗澡;电视剧《水浒传》为淫妇不同程度地正了名;最糟糕的是,这造成了与之相关的英雄好汉们地位的尴尬。如打虎英雄武二郎“却成了摧残爱情,扼杀人性的刽子手。”(注:韩振远《谁来代替施耐庵》载《文艺报》1998年3月21日。)总之, 电视剧为失足女性涂脂抹粉的结果竟使梁山好汉蒙上了性无能、昏聩、残酷、心胸狭窄的恶名。其实,编导们的一片良苦用心用总导演张绍林的话讲,就是”尽量做到老故事有新意,旧人物有新解释。(注:张绍林《实现古典与当代观众的再次对话》载《文汇电影时报》 1998年1月24日。)那么“新”在何处呢?如果说编导们是为淫妇正了名,不如说他们是为“性”正了名。
对性的描写本算不得新鲜事,明末性话语的泛滥成灾、肆无忌惮是很有名的。以明末资本主义萌芽为背景的性展布在原著中则主要体现在围绕淫妇刻划性心理、传达肉体快感的话语上,如王婆对西门庆的一番面授机宜就不亚于当代任何一本性心理学教材。另一方面,旧的联姻话语虽处于劣势——贤妻良母面目模糊,话语单调——却仍是正统礼教下的核心权力话语,并一直支撑着梁山好汉诛杀淫妇奸夫。原著中的淫妇与贤妻及女将们的区别在于其强烈的欲望,这使她们既在书中被连篇累牍地津津乐道,又被指认为坏人,并在男人的厮斗中被消灭。可以说,原著里的性同淫妇的遭遇是一样的。在这方面,梁山好汉们的态度引人注目,这些纷纷脱离家庭的好汉们不容置疑地担负起维护联姻制度的责任。在他们眼里,女人就是色(性),英雄不近色因而就包含着诛杀淫妇、离弃家庭。于是,排除了性乃至血缘关系的义跃为五伦之首,成为好汉们尊崇的价值观。由此看来,梁山好汉的壮举似乎可以视为男权社会的极端势力把伦理败坏、联姻展布衰落归之于女性的一次象征行为:弃妻别家集结成伙,竖立新的男性价值观——忠义——以此来警戒或启发耽于性欲的世人,昭示男性价值观的纯洁性。总之,原著里的淫妇作为性的代名词和标榜忠义的梁山好汉形成对立,好汉恰恰因为对性的无动于衷受人尊敬佩服。这里判断淫的标准是处于封建社会权力核心的联姻制度下的家庭伦理观念。
无疑,在当代性观念的观照下,编导们面临的难题首先是梁山好汉和性秩序的格格不入,换句话讲,必须解决梁山好汉和女人的鲜明对立。于是,淫妇的翻案就成为电视剧改编的关键;为性正名的结果势必需要重新调整梁山好汉对性的态度;而所有对性的润色终究要被纳入联姻制度中,以符合现阶段性展布和联姻展布相互依存的现状。
性压抑说的引入完成了潘金莲从淫妇向贤妻的脱胎换骨。她从勤俭持家到投毒杀夫的性格发展过程在剧中得到了细致刻画,俨然是一个封建体制下饱受性压抑之苦的不谙世事的女人,其杀夫之罪也被大半归之于王婆的贪财成性、阴险狡诈和西门庆的好色成性、心狠手辣;而原著里淫荡成性的潘巧云在剧中热情奔放、如饥似渴的偷情场面更酷似好莱坞影片里脍炙人口的爱情场景。最有意思的还是潘巧云面对杨雄、石秀证剧确凿的审问而发的一番豪言壮语,真情实感,勇气可嘉。更有甚者,原著里生性放荡的卢夫人在剧中竟成了被阴险奴才蒙骗终自杀示夫的烈妻。无论如何,电视剧《水浒传》里淫妇不淫、更像是封建社会性压抑下自觉进行性解放的先驱。如果说在编剧冉平眼里,这是些“拿自己没办法的女人(注:李元《该出手时就出手——访〈水浒传〉编剧冉平》,载《电影故事》1998年4月,第18页。) ”那么编导们却实实在在地对她们有了办法:从下意识即性所受的压抑方面讲,淫妇无罪。
对下意识的关注也直接导致了“水浒英雄变了味”(注:刘孝存《电视剧〈水浒〉失在丢魂魄》载《文艺报》1998年3月3日。)。原著中的杨雄在翠屏山,先审丫鬟迎儿,后杀淫妇潘巧云。丰功伟绩,人神共泣;而电视剧竟让杨雄用刀比划着石秀,对妇人讲:“如果没那事,就杀了石秀……。”执迷寡义,重色轻友!
这种倾斜体现出编导们对人物心理的细微揣摩和大胆设想。可以说,无论是从其出发点,还是在尊重女性欲望、挖掘侠骨柔情方面都表现出编导们立足人自身的欲望、追求的价值取向。但把性压抑作为为淫妇翻案、争取观众同情的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却把女性置于张扬自身欲望和因此被阐释、被追逐、被诛杀的矛盾中;演泄欲望是女性的权利,也无形中更触目地让她暴露在男性观看视野中,对她的追逐和诛杀则几乎成了一种大受鼓动和欢迎的围攻;而对梁山好汉之侠骨柔情的设想同样使他们两难于保持男性价值观的纯洁性和承认女人对自己的影响的矛盾中。杨雄的变味儿、走样充分说明原著里好汉的高大形象是完全建立在对女色的否定上的,编导的一厢情愿在某种意义上抽空了梁山好汉价值观的基石。絮絮叨叨的阐释反而使对立在缝合的努力中更加触目惊心。
最后,权力在唤醒了性之后,“总是不得不重新控制它,生怕它逃逸。”旧的联姻结构家庭在这里发生了改变,“成了性和联姻交流的场所。”剧中扈三娘和王英热热闹闹的婚事显示出编导们想把性欲的主题重新纳入联姻系统的努力——新郎新娘从庭院一直打到洞房,背对洞房坐着喝酒的李逵忽觉打斗声止,待看去灯也熄了,不由暗自一笑,扬长而去。这种快感在洞房外的延伸、性展布在家庭中的动作,充分体现出中西性展布和联姻制度关系的不同。在西方,性展布已集中到家庭本身,尤以关于家庭的性科学、性话语为发达;而家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动作最强有力的手段,在繁衍之外基本上是排斥性的。即使在西方性文化长驱直入的今天,家庭的性也只在人们嘴边吞吞吐吐,并没有出现西方以家庭为核心的性话语的泛滥。但是联姻展布和性展布都需要家庭在新的权力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因而剧中这种欲说还休的修辞手法就不仅在联姻制度中强烈暗示出性展布的快感要素,而且还用性的展布确保着男性在联姻中的地位。实际上,电视剧对这个婚礼的大作文章分明呼应了前此好汉们面对淫妇的张口结舌:淫妇的性压抑说无形中阉割了梁山好汉,而王英扈三娘的婚事无疑起到了反拨、补偿作用。
电视剧《水浒传》有一点值得一提,即对潘巧云之死的新解。剧中杨雄怀着最后一点希望问潘巧云,石秀的话是否是真的,并许诺只要答否,就再不追究。潘巧云却不仅拒绝了杨雄的诱惑:撒谎可免死,而且公开表明了她对丈夫的蔑视和不屑,这激怒了杨雄,一刀了结了这个淫妇。从某种意义上讲,死亡最终使潘巧云摆脱了男权的控制。原著里的淫妇在剧中体现的骨鲠之气不失为改编中的一个突破。
二、两个家庭的命运
如前所述,旧的联姻展布在性展布迅速扩张的情况下渐趋衰落,权力通过性展布发挥着越来越强的占有人的生命的功能。可以想见,旧的家庭观念必定因为难以适应当代社会权力运作重心的转变而趋于衰退。而女性因其长期被束缚在家庭中,价值也主要体现在家庭角色(贤妻良母)中,必将遭受更大的冲击。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对女性的影响,对女性主义者意义重大。另外,长期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旧联姻体制下的家庭将在当代继续它的影响,这首先是因为它在广大农村里的强大根基和早已牢牢内化于女人的思想深处的家庭观念。所以,现阶段权力关系呈现新旧策略犬牙交错、此消彼长又相互依存的局面,以下本文拟从《离婚了就别来找我》和《喜莲》来分析作为联姻结构的家庭和女性的关系。
《离婚了就别来找我》的最后一个镜头段落耐人寻味:师慧在公寓里绝望而冷漠地把前夫的书架和电脑全部捣毁,同时李浩明追赶着离家出走的恋人师红,他逆流穿过正在举行婚礼的人流,最后试图在街边拦住一辆面的。很明显,开放式的结尾显示了影片对家庭的质疑,情节中包含的结婚、离婚、复婚诸种因素使人思索家庭的意义何在;另一方面,师慧的家庭观念之发展对人颇有启示:她一直笃信传统家庭观念,克尽职守,当丈夫的固执行为使她从忍耐、愤怒、蔑视到离婚时,她的身心遭受到巨大的创伤。前夫的成功重新燃起了她对家庭的渴望:复婚!沉闷压抑的谈判却惊醒了梦中人:她漫不经心地肆意捣毁着男人的书和电脑,毫不留情地摔砸着键盘。这些在她最痛苦的离婚前后都不曾想到、敢做的事,如今却如此痛快淋漓地发泄出来:书和电脑正是这个自私自利的男人藉以逃脱家庭负担,获得爱情和事业成功的全部武器。如果说知识和男人的结盟曾使家里的女人痛不欲生、精神错乱,那么现在,师慧的破坏就是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复仇。与此同时,师红的出走何尝不是这个性观念开放的女人无意于家庭的宣言。而李浩明两难于两个女人之间的处境瞬间竟变成了他无家可归、独步街头、茫然失措的身影,这难道是旧的联姻结构崩溃后男性处境的一种写照?与此相对的,也许正是女性的一种解脱。《离》在把女人推至绝望境地的同时无比生动地敞开了女性摆脱家庭枷锁后无限宽广的自由。
如果说《离》对传统家庭体系提出了质疑,那么《喜莲》则通过农村经济致富的个例毫不含糊地重申着婚姻体系强大的生命力和家庭浓厚的感情色彩。
《喜莲》这部影片的难题实际上在于怎么处理一个农村女强人和丈夫的关系的问题。编导们竭力想在一个果敢自信一往无前的女辣椒大王和一个幸福家庭的贤妻良母间取得平衡。出路看来只有一条:喜莲在某些方面傻了,她似乎只有奉献毫无要求,甚至对丈夫世德和原来的相好扬青勾勾搭搭也毫无怨言。只是除夕夜看见丈夫被扬青拉走,独守辣椒棚的她才终于感到一丝寒冷和凄凉,一段至情至真的话让人肝肠寸断。于是,导演在展示这位朴实女性对丈夫的一往情深时,喜莲的“傻”竟变成了悲凉。同时这也触及到了家庭中的女性真实的处境——弱者和被遗弃者。
应当看到,影片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女性都处于被遗弃者的位置。她们性格各异,有一点却是相同的:最大的打击总是来自男人。奶奶长期守寡抚养两个儿子的结果竟然是老年后一度陷入被两个儿子的家推来推去的境地;厉害泼辣的环子在发觉丈夫世才对二虎老婆有意,开始反抗自己时,也不禁怨从中来,在众人面前流泪悲伤,感叹命运不好;杨青对世德的死缠硬磨、百般照顾又哪一点不透着寡妇的心酸和凄凉,最终也只落得和顺口溜浪迹天涯;似乎拥有最优越条件的漂亮贤惠的喜莲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给丈夫一个“惊喜”和一家幸福去学技术、拉土坯、种辣椒。如此辛苦也不免在除夕夜面对丈夫心酸落泪。可以说《喜莲》里的男人表面上处于劣势,实际上却是女人们簇拥下的家庭核心。而影片结尾处全家福里喜莲手中从天而降的孩子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了编导们对传统婚姻体系特点的心领神会。总之,《喜莲》以纯正浓郁的东北乡土气息烘托出旧的联姻体系下的一个幸福家庭,它的魅力主要来自几乎重复了“阿甘”身上所有成功因素的喜莲的出现。也许家里的女性的这种傻和聪明终于可以使家里的男人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
另外,饶有意味的是《离》在置疑家庭的同时,围绕李浩明和师红的互相吸引设置了不少情境加以渲染,如迪斯科舞厅的狂舞和烛火里的晚餐,这些无不暗示着性状态的浸透,饱含着对肉体快感的细致刻画,并直接控制着观众对性的想象和评价;相反,《喜莲》却以大棉袄、棉裤阻挡住了任何对肉体的关注和快感的想象,连孩子也只能以家族一员的姿态出现在全家福里,从而在竭力排斥性状态的展布下营造了家庭的温馨朴实。这种对立显示当前不仅性展布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努力占据着权力关系重心的地位,旧的联姻结构也在权力运作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预料,旧的家庭观念在衰落中一定会吸收权力运作的新策略——性展布,以形成、巩固家庭的现代形式使家庭继续在权力关系中发挥重要战略功能。
目前的现状是,家庭中的性仍然是禁欲主义长期盘踞的地方,大多数女性仍被旧的家庭观念束缚,她们在家庭中的卑下不稳定的地位并不随着经济上的独立马上改变,这首先是由于千百年来男权思想在女性身上的内化,并且还在于掌握着“我是村长”、“逻辑性”之类权力/知识话语的男性从来就不会放弃他们的特权地位,如何让女性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宽广的前景于是成为女性主义者最持久的工作。
在性话语迅速膨胀的今天,女性不仅没有获得所谓的解放,而且更醒目地出现在被攻击被阐释、被物化、被消费的位置。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是从女性自身角度出发的阐释,也往往出现南辕北辙的效果。比如电视连续剧《武则天》,编剧赵玫以女性细致而丰富的想象力,填补着历史上贤明残暴的女皇武则天攀登皇权宝座途中的一个个情感空白,解释了一个纯真娇柔的女人何以成为雄才大略、心狠手辣的皇帝。她以情取胜的策略使“武则天”赢得了观众的同情和认可。这无疑表现出女编剧对正史之男权话语的置疑和试图以女性的方式改写权力话语的努力。但是权力的无所不在首先就体现在这种对女性本质的先见纯然是以男性眼光为前提的;对“媚”的过份强调,更明显纳入了男性观看机制。又如《秦颂》虚构了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栎阳公主,她把女性欲望毫无避讳的渲泄作为向列祖列宗挑战的方式,也许可以把这看作女性在性话语中利用性话语反抗男权控制的手段。但是这个“征服欲很强的女人”(注:参见《周晓文说〈秦颂〉》,载《电影艺术》1996年第4期。)身上发生的性奇迹——强奸治好了栎阳公主的瘫痪——把权力在性的展布中对女性的掌握公开化了,性近乎赐予了女性第二次生命。权力通过性奇迹证明了它统治生命、强化生命的能力。
总之,权力在阻力点上生长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它们甚至是相互依存的,这种复杂关系决定了女性摆脱男权束缚的艰辛。而对阻力点作出战略性的统筹规划的能力完全取决于女性认识权力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尤其是对性展布这一权力最重要的战略手段。如福柯所讲“性并不是一种权力试图控制的天赐之物或知识试图去开拓的模糊领域”(注:〔法〕米歇尔·福柯《性史》(第一、二卷)张延琛等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103页。), “它可以作为一种历史结构的名称”(注:〔法〕米歇尔·福柯《性史》(第一、二卷)张延琛等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104页。), 是权力“一个巨大的表层网络”。(注:〔法〕米歇尔·福柯《性史》(第一、二卷)张延琛等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104页。)对女性主义者来讲, 性如同《赢家》里的残疾运动员常平的假肢,自己既无法揭示也无力遮隐。实际上任何一种举动都更增强了权力在性话语中的迅速增殖。这就象假肢和常平之间的关系并不因假肢被衣服遮挡起来或被单独取下而改变,只会因为这种改变而增强它的威力。女性主义者同样两难于作为假肢的性带来的耻辱和荣誉之间。而且女性无法成为女性,虽不仅仅因为性,它却是最为核心的难题。那么承认性展布中权力对女性的束缚、掌握就是女性主义者迈出的第一步。而分析、鉴别这种权力关系如何赋予或剥夺女性成其为女性的意义,则是女性主义者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