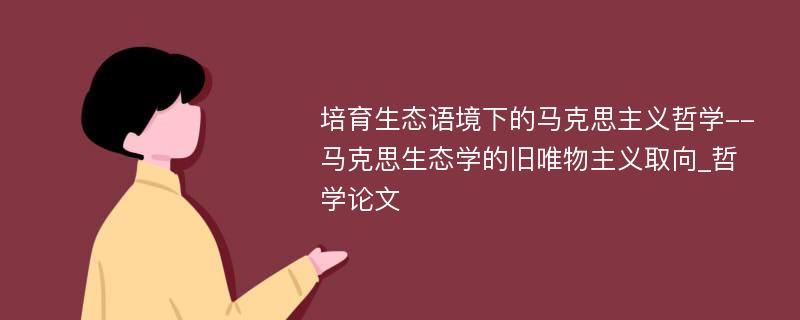
福斯特生态学语境下的马克思哲学——《马克思的生态学》的旧唯物主义定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生态学论文,福斯特论文,唯物主义论文,语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8)05-0057-08
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中,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把当今的生态学困境本质地归结为哲学基础的危机,并试图通过在哲学本体论的根基处重新诠释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境域,呈现马克思哲学的生态学维度,以此导引陷于困境的生态学运动。该书因之在生态学与马克思哲学诠释学的双重领域,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生态学》对于生态学困境与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性,并非由于其在浩如烟海的马克思文献中挖掘出了一些具有生态学色彩的只言片语,而是因为它的理论切入点完全发生于作为哲学根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马克思的生态学》所带给人们的意义与启迪,也并非由于它在哲学的根基处所取得的理论进展,而是因为它历史地呈现出来的理论界限。当福斯特在哲学的根基处指证着当代生态学的本质困境时,他意识到了重新诠释马克思哲学本质境域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但当他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于自然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综合,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诉诸“通过生产”所发生的“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新陈代谢”①的物质变换关系时,在这里出现的乃是福斯特对于把握马克思哲学之存在论基础的无能为力②。
一 当代生态学困境的哲学本质
福斯特敏锐地看到了“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在理论根基处的虚妄性——作为“空洞的抽象概念”之争,它们“仅仅是对诸如人类征服自然和自然崇拜之间的对立这样古老的二元论的重新阐述”③。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在作为生态学运动之哲学根基处所发生的切中理论要害的洞见。
在福斯特看来,尽管围绕这类争论已经取得了无数的研究成果,但是,“这里永远存在的二元论观念往往妨碍了知识和有意义的实践的真正发展。实际上,这种观念中所体现出来的二分法往往使‘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观念长期存在,而在很多方面,这种观念正是上述问题的根源。”④因而,只要生态学的理论与实践诉求依然在根基上滞留于人类与自然的“二分法”,那么,不论是作为“生态中心主义”之新的理论变形的感伤主义的“生态伦理学”,还是作为“人类中心主义”之新的表达形式的“弱人类中心主义”或“谨慎的建构主义”,都不过是“一种在圆圈内无休止地做圆周运动的倾向”,而其必然的理论天命则是“所有的分析又回到了起点,这对于解决真正的环境和社会问题起不到任何作用。”⑤
在生态伦理学中,当“生态问题首先而且最主要地被简化为一个价值问题”的时候,“理解人类与自然之间不断进化的物质关系(马克思称之为‘新陈代谢关系’)这个更加困难的问题也因此被完全忽略了”⑥。福斯特明确指出:“从一贯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相对立的问题——实际上,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在生物圈中存在的、真实的、不断变化的物质条件并无裨益……。仅仅关注生态价值的各种做法,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讲,就像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灵论,都无益于理解这些复杂的关系。”在此,福斯特借用马克思的说法,指出了本质性的出路:“与所有这些‘从天国降到人间’的观念相反,必须‘从人间升到天国’。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了解精神概念,包括我们与现实的精神联系,是如何与我们的物质的、现实的状况联系在一起的。”⑦所谓精神概念是如何与我们的物质的、现实的状况联系在一起,不过是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此,福斯特明确地把当今生态学的本质困境明确归结为:“其实,真正存在争论的问题是唯物主义对待自然和人类存在的方式的全部历史。”⑧
应当指出:福斯特把生态学的困境归结为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二元论”困境,并要求在哲学的根基处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这一见地乃是切中要害并发人深省的;当他把对人与自然之本质关系的反思历史地追溯到马克思,追溯到贯穿于马克思一生思想历程中的对“来源于人类劳动的人类和自然界之间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交换”⑨之思考的时候,他也为合理地解脱生态学困境开启了一条本质重要的探索路经,即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根基处,马克思所达至的哲学革命的本质何在。
二 福斯特对马克思哲学境域的双重误读
在福斯特看来,当代生态学的困境“说明了一种生态的唯物主义或一种辩证的自然历史观的必要性”,而马克思主义“对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都具有巨大的潜在优势”⑩,马克思的“物质实践”观——“我们应该通过行动,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物质实践来改变我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并超越我们与自然界的异化”——已经“创造出我们自己独特的人类一自然的关系”(11)。那么,马克思对人类一自然关系之诠释的独特性何在以及它何以构成解脱生态学困境之本质根据呢?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福斯特在恰当地切中问题之要害的同时却完全无力解决问题:他在马克思开启全新哲学境域的根基处徘徊一番之后,却又决定性地发生了最严重的理论退却——以实践唯物主义之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把马克思哲学诠释成了一个新旧唯物主义的大杂烩。
(一)“自然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
在作为理论根基的维度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生态学的意义,它也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在生态学的意义上,它衍生出建构主义与反建构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在哲学的层面上,仅就唯物主义而言,它历史地表达为自然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分别。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福斯特抛却了唯物主义的历史维度,把分属于不同历史样态、具有本质界限的自然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归属于同一个马克思,并视之为马克思哲学的“巨大的潜在优势”与“超乎寻常的巨大的理论力量”(12)。
正像福斯特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生态危机——引者注)都具有巨大的潜在优势,正是因为它所依赖的社会理论属于唯物主义:不仅在于这种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生产条件这个社会前提,以及这些条件如何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可能性,而且还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至少是在恩格斯那里,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全面考察马克思在这一领域中的思想发展,将为重新批判性地审视关于‘自然辩证法’的争论提供一个基础——始终承认正是在这里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空白。”(13)在福斯特看来:“尽管马克思在其后来的著作中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中思辨的、非历史方面的内容,但是,费尔巴哈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仍然回响在马克思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14)福斯特反复“强调外在的物理世界相对于思维的独立存在”(15)对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性,强调“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绝对没有忽视外在的自然王国”(16),一再要求人们“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将唯物主义转变成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的唯物主义——的总体责任”(17)。
据此,福斯特指责西方马克思主义——连同许多当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误解了马克思,因为他们“都逐渐拒绝了实在论和唯物主义,而把人类社会看做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之上的人类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简单地否定了不及物的知识客体(自然的和独立于人类和社会结构存在的知识客体)”(18)。福斯特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当中,这代表着向唯心主义方向的一种转变。特别是,人们普遍认为辩证法只与实践有关,因而也只与社会-人类世界有关。这种观点与恩格斯的观点相反,在马克思主义当中,好像只有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对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存在负责。”(19)
尽管我们看到福斯特努力把马克思哲学整合为一个完整整体的巨大企图,但是在这里发生的却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分裂,这个分裂发生在哲学的根基处,即发生在人与自然以及作为其相应理论形式的自然观与历史观、自然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结合部。当福斯特依据英国哲学家罗伊·布哈斯卡的分类法,把“作为一种理性世界观的理性的哲学唯物主义”划分为“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并认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既接受了“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自然唯物主义),也接受了“认识论的唯物主义”(20)的时候,在这里出现的乃是一个原则性的理论混乱或无原则的折中主义,是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本质境域所在的无原则的遮蔽。
必须指出的是:当我们指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时候,我们却不可以同时断言马克思既接受了“自然唯物主义”,也接受了“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毕竟,它们在本质上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哲学境域;而马克思在人与自然、实体与主体关系的根基处,以“感性活动”所发动的哲学革命恰恰在于他突破了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视域,从根本上与前康德的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开启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全新哲学境域。
正是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全新视域中,马克思从不侈谈“自然的先在性”,自然界与人的关系在本质上只能被理解为作为“感性活动”的“实践结构”,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发生的“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21)。在这种人与自然的实践结构中,所谓“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不过是“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而这个问题在本质上“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22)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彻底终结了旧唯物主义和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的可能性,因为这样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23)。这就意味着: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境域中,自然界与人的实在性问题,已经本质地转换成了“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问题,而“如果把工业(即实践、劳动——尽管是异化形式的)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24)因此,对于自然界与人的实在性问题,比如,对于“谁产生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的问题,马克思认为这就是“一个来自荒谬而使我无法回答的观点”(25),因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6)据此,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地把“感性劳动”、“生产”或“实践”作为人与自然界之关系的连接点与枢轴,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否定了“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或“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在马克思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着”。但是,它只有对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只有在人被看做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因为“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为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27)
因此,我们只要承认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本质,任何以拒斥唯心主义之名偷渡自然唯物主义的企图,都是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本质所在的误读,都不可避免地把马克思哲学再度推回到前康德唯物主义的理论境域中去。在康德哲学革命之后,任何侈谈“自然的先在性”的企图都必然把马克思哲学陷入到知性科学化的泥潭。当康德把“自在之物”本质地归之于实践理性之领域的时候,它意味着自然唯物主义关于“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的问题已经变成了真正的社会课题,意味着人与自然界的实在性问题已经变成了“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之课题,而这个问题只能被理解为实践的,由此诞生的也不再是马克思“对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总体责任”,不再是“强调外在的物理世界相对于思维的独立存在”,而是作为“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的“整个所谓世界历史”(28)。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至于所谓“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境域中,也已经“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29)。本质地说来,马克思的认识论就是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它绝非单纯地提供外在的认知方法论,而是在本质上彰显知识论路向的存在论根基。
因而,当福斯特在马克思那里既发现了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又指认着“费尔巴哈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仍然回响在马克思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30)的时候,他也就不得不设想出一个莫须有的马克思思想发展从自然向历史的“转向”(31),并由此强制性地引导出马克思哲学的历史维度。
(二)“实践唯物主义”与“新陈代谢”
在福斯特看来,当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关注点从自然转向历史”,马克思也就同时实现了“将唯物主义转变成实践的唯物主义”(32)。毋庸置疑,“将唯物主义转变成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乃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尽管福斯特戴着一副“自然唯物主义”的有色眼镜,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仅仅局限于社会历史领域,因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只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实践的特征”(33),但他毕竟正在切近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所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福斯特的诠释中,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独特的”实践特征本质何在?当福斯特指认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分析的力量在于他强调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性质,或者他最后所称做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通过生产”(34)的时候,我们再度发现福斯特完全没有能力与马克思对话。
福斯特认为:“新陈代谢”不仅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研究有机体与它们所处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论方法中的关键范畴”(35),而且也是马克思在“关于劳动过程的定义中”作为他的“整个分析系统的中心”;马克思“把对劳动过程的理解根植于这一概念之中”(36),并因为成为包括《资本论》在内的整个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范畴。在福斯特看来,如果说“自然异化概念在他的早期著作的批判当中居于核心地位”,那么“新陈代谢概念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表述自然异化(以及它与劳动异化的关系)概念的具体方式”(37);“马克思对人类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关系的许多讨论,都可以被看做建立在早期马克思试图更加直接地从哲学上解释人类和自然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之上”。不仅如此,而且“马克思后来的新陈代谢概念使他对这种基本关系——描述来源于人类劳动的人类和自然界之间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交换——给予更加完整而科学的表述”(38)。福斯特还指出:“在他成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正如《资本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马克思采用了‘新陈代谢’这一概念来定义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9)
我们认为,福斯特对“新陈代谢”的界定——通过“生产”所发生的人与自然界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物质变换”过程,完全错失了马克思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根基处所发动的哲学革命的本质境域;他对“新陈代谢”、“生产”、“实践”的把握依然滞留于人与自然、实体与主体之“二元论”的哲学境域中。实际上,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在哲学批判、经济批判双重维度上,彻底颠覆了人与自然、实体与主体的“二元论”模式。
就哲学批判而言,“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整个哲学的批判”之最为积极的成果就在于:在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原则”感性地确认着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伟大见解,但同时却无以说明实体何以即主体、自然界何以成为人之本质的时候,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化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40),从而本质地确定了“感性对象性活动”,即“感性活动”的原则,把“感性活动”作为实体与主体、人与自然、人与人之对象性关系的内在根据。正是“感性活动”才使得主体不再是纯粹的“自我”或“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而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41),而客体也不再是抽象的“物性”或与人无涉的纯粹的自然界,而是“主体性”之“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正是“感性活动”使得“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42)成为可能。
就经济批判而言,以“异化劳动”理论为主体的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成果乃是揭示了“劳动”的本质。正如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在本质上乃是哲学批判一样(43),“劳动”也不过是“感性活动”的经济学表达。如果说“感性活动”揭示了人与自然、实体与主体之本质性的原初关联,那么,“劳动”则展现出作为“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的人与作为主体性本质力量之对象化的自然,即劳动产品之间的本质关联。正如马克思的哲学批判致力于呈现思辨哲学意义上的“对象性”关系的本质根据一样,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也绝非单纯地陈述一系列异化的“经济事实”,而是要呈现作为“经济事实”的“异化劳动”的“现象实情”,彰显“劳动”的本质。在国民经济学家仅只看到作为“经济事实”的“工人”为“资本家”获取“商品”与“财富”而从事“生产”的地方,马克思所看到的则是作为现实个人的“劳动者”创造“劳动的产品”的“劳动”活动,即“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本质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只有“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才“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才“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44)。
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福斯特指认着“马克思对人类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关系的许多讨论,都可以被看做建立在早期马克思试图更加直接地从哲学上解释人类和自然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时候,他已经犯了双重性的误解:
第一,马克思对人类与自然界之关系的本质追问,并不存在所谓的“早期马克思试图更加直接地从哲学上解释”,而在“成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则从经济学上进行解释的“从自然转向历史”的断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初关联处,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与经济批判呈现出同一个理论境域。当马克思在哲学批判的意义上,把“感性活动”的本质境域集中表达为“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45)的时候,发生在经济批判中的对“劳动”之本质的呈现,不过是“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经济学表达。所谓“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不过是作为“现实的个人”的“劳动者”,而所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不过就是“劳动的实现”或“物化为对象的劳动”,即作为主体性本质力量之对象化的“劳动的产品”,而所谓“主体性”的“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即现实个人的“对象性活动”,它不仅生产出作为主体性本质力量之对象化的“劳动产品”,而且生产出作为“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的“现实的个人”,即“劳动者”,同时还生产出“现实的个人”的“类本质”,即现实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第二,在“感性活动”或“劳动”的本质规定中,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实体与主体之内在关系在根基处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再是福斯特所理解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所能表达的了。正如黑格尔所指责的那样,任何意义上的“相互作用”还都站在概念的门槛上。黑格尔因之坚决地诉诸“实体即主体”的伟大原则,而这一原则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以思辨哲学的语言,把握住了人与自然、实体与主体之“对象性关系”的根据,即“抓住了劳动的本质”。因而,在黑格尔哲学之后,在人与自然、实体与主体的关系上再度侈谈“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正犹如在康德哲学之后再度复活自然唯物主义的企图一样,都已经表现为不可原谅的历史倒退。在这个意义上去谈论“马克思自己的以实在论本体论(即自然的唯物主义观)为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对黑格尔的观念实现了一种辩证的超越”(46),在最善良的意图上,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因而,面对从雷纳·格伦德曼到维克托·费克斯,从迈克尔·劳依到吉登斯,对马克思“以人类征服自然为荣”的“对待人类-自然关系的‘普罗米修斯态度’”(47)的指责,福斯特唯一能做的辩护也就只能是向培根求助——“只有顺从自然,才能驾驭自然”(48)。然而,只要他依然滞留于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境域,无论他怎样把“顺从自然”设置为“驾驭自然”的前提,他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到的“自然力的征服”和“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49)所做的生态学矫正,都不仅不能逃脱出当代生态学的“二元论”困境,而且恰恰最深入地陷入人与自然“二元分立”的诠释框架中。因而,面对“新陈代谢”的“断裂”,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50),在其发生的根源处,他就只能归之于作为“资本主义核心问题的城乡分离”(51);在重新连接被撕碎的裂缝的解决方案上,他也只能是浮浅地重复马克思所说的“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52),而合理调节的路径则是不得要领地诉诸“通过‘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而“把人口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53)。
三 双重误读之症结:错失费尔巴哈
当福斯特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根基处本质性地切中生态学困境的哲学本质不过是“对诸如人类征服自然和自然崇拜之间的对立这样古老的二元论的重新阐述”,并因而试图重新诠释马克思哲学实践唯物主义本质的时候,当福斯特已经意识到作为症结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分立”,也已经把黑格尔“以抽象的观念劳动的形式”所发现的“历史中的劳动的异化”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环节——这一环节通过“实体即主体”之原则所本质表达的,恰恰是根本超越了单纯“相互作用”的实体与主体、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的时候,他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大门。但当他把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结构再度描述为“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时候,在实践唯物主义的根基处,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福斯特最终依然没有逃脱以“自然的先在性”为前提的“相互作用”的“二元论”命运,从而又收回了前进的脚步,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本质境域擦肩而过。在这个意义上,福斯特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本质境域的把握,在其最高水平上也只能表现为“自然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叠加。那么,这一不幸的理论事件是何以发生的呢?
我们认为,问题的症结乃在于福斯特忽略并完全误解了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的费尔巴哈环节。尽管福斯特也曾谈到马克思“在哲学上同黑格尔体系进行更坚决的决裂”是“通过研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而完成的”(54),但当他把伊壁鸠鲁和黑格尔作为烛照马克思哲学革命之路的本质光源的时候(55),费尔巴哈已经被伊壁鸠鲁的自然唯物主义之光所遮蔽,或者已经变成了第二个伊壁鸠鲁。因此,在福斯特看来,费尔巴哈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也就只在于他继承了伊壁鸠鲁拒斥“目的论”的“辩证的实在观”——“自然界的死亡就成为自然界的不死的实体”(56),并“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最脆弱的部分——自然哲学体系——实现了与黑格尔的决裂”,从而再度确立了感觉的真实性——“物质世界本身是现实存在的,包括其中的人类及其对世界的感觉”(57)。在此之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就是“空洞”的,“实际上,同伊壁鸠鲁相比,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更为抽象,更为直观”,因为它“只是黑格尔体系的倒置,没有任何自己的主张,因而将永远处于他所否定的巨大体系的阴影之中”(58)。在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的心路历程中,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积极影响也仅在于“费尔巴哈的自然哲学为马克思提供了自然及其异化观”(59),而“马克思继费尔巴哈之后认为,重要的是把客观世界以及人类的存在作为客观存在,也就是,真正的实在论和自然主义”(60)。我们认为,在这里发生的乃是福斯特对两个重要历史事实的严重误解:
第一,当福斯特把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源头追溯到伊壁鸠鲁的时候,他完全误解了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哲学立场的基本性质。我们认为: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在总体哲学立场上依然隶属于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61)。因此,马克思不仅接受了黑格尔对伊壁鸠鲁哲学“独断论”性质的基本评价,而且立足于鲍威尔的基本立场,明确指出:“只是到现在,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体系为人理解的时代才算到来了。他们是自我意识哲学家。”(62)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德谟克利特是一个怀疑论者,那么伊壁鸠鲁就是一个独断论者。马克思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间所看到的显然还并不是两个唯物主义者之间的不太重要的差别,而是具有实质性不同的实体哲学与自我意识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指出:“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在每一步骤上都是互相对立的。一个是怀疑论者,另一个是独断论者;一个把感性世界看做主观假象,另一个把感性世界看做客观现象。……把感性自然看做主观假象的怀疑论者和经验论者,从必然性的观点来考察自然,并力求解释和理解事物的真实存在。相反,把现象看做真实的哲学家和独断论者到处只看见偶然,而他的解释方法更倾向于否定自然的一切客观实在性。”(63)因而,如果谈论博士论文时期伊壁鸠鲁对马克思的影响,这种影响也绝非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在伊壁鸠鲁这里所发现的不过是对自我意识的自由的高度弘扬,是把自我意识作为解释世界的尺度,并以此声援现实的青年黑格尔派运动。
第二,当福斯特违背历史事实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前推到博士论文时期,以至于认为费尔巴哈1842年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的“批判思想与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观点相吻合”(64)的时候,他也就不得不把费尔巴哈看做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心路历程中的“伊壁鸠鲁第二”,并因而完全误解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本质贡献。费尔巴哈的理论贡献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绝非继伊壁鸠鲁之后再度确认或恢复了感觉论的自然唯物主义原则,而是在《基督教的本质》中空前巩固地确立了把握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感性对象性原则”(65)。
在“感性对象性原则”的理论视域内,自然界之于费尔巴哈已经不再是“不依赖于任何东西而自在地存在的、绝对的属人的实体”,而是“感性的”自然界;而“感性的”自然界在本质上乃是“人必然要与之发生关系的、否则就不能设想人的存在和本质的”自然界(6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明确指出:“人之对象,不外就是他的成为对象的本质”(67),“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68)。在这里出现的正是已经超越了“相互作用”关系的人与自然界之间本质性的原初关联,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实体即主体”之思辨原则的感性表达。当费尔巴哈依据“感性对象性原则”去进而透视人与人之关系的时候,它意味着“别人就是我的‘你’,……就是我的另一个‘我’,就是成为我的对象的人,就是我的坦白的内隐,就是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眼睛。只有在别人身上,我才具有对类的意识;只有借别人,我才体验到和感到我是个人,……才明白只有集体才构成人类。”(69)在这里出现的乃是费尔巴哈超越于自然唯物主义的又一个重要创见:人是“类存在物”,即社会存在物。因此,当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70)的时候,马克思是深刻洞悉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之精髓所在的。
但是,费尔巴哈有一个他自己无法超越的理论界限,即他无以提供“自然界”与“他人”何以构成“人”与“自我”之本质的根据。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所抓住的“劳动的本质”(71),从而决定性地把“感性对象性”的直观性原则上升到“感性活动”,即“实践”的高度,初步开启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全新理论境域。在这样的理论境域中,关于人与自然界之外在“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任何理解都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然而,当福斯特认为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中的论证除了令人感到吃惊之外并没有任何其他新的内容”(72),并因而把费尔巴哈作为第二个伊壁鸠鲁与黑格尔一起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之环节的时候,这个“继承了黑格尔哲学和辩证法中的积极因素,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则不可避免地再度构建出“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并把人与自然的实践结构再度拖回到“相互作用”的“二元论”框架中。在这里出现的乃是一个作为自然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大杂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的旧唯物主义定向。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30)(31)(32)(33)(34)(35)(36)(37)(38)(39)(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4)(72)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第127页;第21页;第21页;第21页;第12~13页;第13页;第13页;第176页;第20页;第8页;第16页;第22页;第90页;第8页;第127页;第8页;第9页;第9页;第3页;第90页;第126页;第126、8页;第9页;第127页;第178页;第174页;第176页;第176页;第174~175页;第73页;第149页;第154页;第151页;第158页;第155页;第158页;第153页;第77页;第6页;第6~7页;第78页;第123~124页;第85页;第87页;第7页;第78页。
②在这个方面,吴晓明关于卢卡奇的评析,为我们合理评价福斯特的理论贡献与理论界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参见吴晓明:《卢卡奇的存在论视域及其批判》,《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1)(22)(23)(24)(25)(26)(28)(40)(41)(42)(44)(45)(70)(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31页;第131页;第131页;第128页;第130页;第178页;第131页;第163页;第167页;第131页;第91页;第167页;第158页;第16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第40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16页。
(43)参见拙作《马克思经济批判的哲学境域》,《哲学动态》2006年第5期。
(61)参见拙作《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哲学立场及其与鲍威尔的潜在差异——兼与罗燕明同志商榷》,《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6期。
(62)(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286页;第207页。
(65)参见拙作:《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真正意义与‘感性对象性原则’》,《新疆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66)(67)(68)(6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第521页;第38页;第29页;第193页。
标签:哲学论文; 费尔巴哈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生态学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哲学家论文; 人与自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