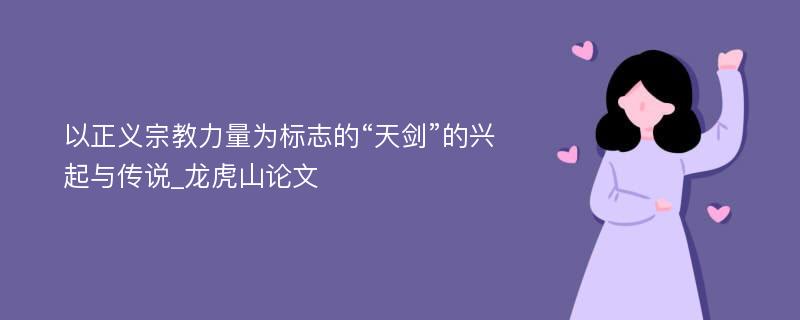
正一教权象征“天师剑”的兴起与传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师论文,象征论文,教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4)03-0028-09 江西龙虎山的正一道教张天师家族,世代相传两件镇山法宝,即玉印和宝剑。据元代道士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汉天师张道陵创立天师道之初,获太上老君降授“三五斩邪雌雄二神剑”与“阳平治都功印”。永寿二年(156),张道陵在临终之前,又将斩邪二剑、玉册玉印授予其长子衡,戒之曰:“此文总统三五步罡,正一之枢要,世世一子,绍吾之位,非吾家宗亲子孙不传。”①天师剑与玉印象征着正一教主的宗教权威,作为教权的凭证与信物,这二种法器有如世俗皇朝的传位玉玺,每一任张天师必须获得上一任天师传授天师剑印之后方可嗣任掌教。 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世祖忽必烈宣命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携祖传的剑印赴京觐见,忽必烈“取其祖天师所传玉印、宝剑观之,语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几,而天师剑印传子若孙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嗟叹久之”②。这里元世祖感叹的是天师剑的生命力远远超出了王朝政权,朝代有更易,而天师剑印却代代相承。 正一道教的天师剑是否如元世祖所认为的那样拥有如此悠久的流传历史?我们翻检唐代之前的古籍,几乎看不到张天师与宝剑的相关记载。不仅汉晋六朝的史料和天师道道团内部流传的道经见不到天师剑的痕迹③,涉及张道陵的仙传文学亦遍寻不着相关记载。比如,最早记叙张道陵创教事迹的仙传——东晋葛洪《神仙传》中的《张道陵传》,隐约说到张天师“得隐书秘文及制命山岳众神之术”,却未具体提及宝剑与玉印。④南朝萧梁时期,博通古今的道教领袖陶弘景曾撰有《古今刀剑录》一书,记述夏朝至梁武帝时期的历代名剑和道家宝剑,书中亦未记载张道陵的天师剑。⑤如果当时道团保存着后世张天师家族所夸耀的天师剑,陶弘景或同时期的道经一定会加以介绍。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以物化的信据形式来象征张天师宗教神威的宝剑叙事,究竟什么时候才形成? 一般认为,张天师世系从第三代天师张鲁之后便湮没无闻;到了唐代中晚期,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世系重新活跃,并构造出自祖天师张道陵以来连续的传承世系。但是张天师世系是何时以及具体如何确立龙虎山的道教祖庭地位的,却一直是道教研究的一大疑点。⑥另一方面,自元代以来,以龙虎山张天师世系为中心的道教叙事又一再强调龙虎山与天师剑印的紧密关联,明代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编纂的《汉天师世家》即云:“上饶龙虎山,相传为真君故栖,玉印宝剑,奕世授传。”⑦ 宋代以后,天师印剑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龙虎山张天师子孙的象征符号,道内文献也在不断地强化这一象征,尤其以元代《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和明代《汉天师世家》的天师剑相关描写最为详细。但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层累造史”,宋元以降的文献关于天师印剑的记载越是详实,可信度越是打折扣。⑧本文认为追溯天师印剑传说的缘起,首先不能依赖宋代以后的道内文献,而应放宽眼界,整体考察宋前“道士与剑”的故事类型,追寻宝剑传说的主角从道士群体逐步落实到张天师身上的演变历程。 一、晋唐时期的道教神剑 在中国古代兵器传说中,剑具有神秘性和咒术性的特点。宝剑,既是权力与超凡能力的象征,比如汉高祖的斩蛇剑、欧阳子的湛卢剑;又是“宝物之精”,譬如“候天伺地、阴阳同光”的干将、莫邪二剑,“宝剑之精、上彻于天”的龙泉、太阿二剑。《吴越春秋》《越绝书》《博物志》等早期典籍记载的剑传说多集中于“冶炼制剑”的主题,传说的主角或为帝王将帅,或为名匠巫师。东晋时期,随着道教在江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道士与剑的传说开始见诸文字。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几处提及道士随身佩戴符剑,《道意篇》云“要于防身却害,当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符剑耳”⑨,《遐览篇》又云“符剑可以却鬼辟邪”⑩。对于东晋六朝时期的江南道士来说,刻有道符的宝剑是他们驱鬼辟邪的必备法器,正如陶弘景的《太清经》(一名《剑经》)所云:“凡学道术者,皆须有好剑、镜随身。”(11) 符剑是道士施展法术的主要工具,所以道士仗剑驱鬼的故事屡见于六朝志怪小说。比如,《录异传》记载会稽道士贺瑀死后,被天吏带到天宫官府,见房中架上有印与剑,贺瑀“取剑以出门”,又后悔云:“恨不得印,可以驱策百神。今得剑,惟使社公耳。”贺瑀获得这把驱策社公的宝剑仅仅过了三天,“果有鬼来,称社公”。(12)这个故事宣扬了宝印和宝剑驱策神鬼的神威,这或许就是宋代以后张天师剑印传说的滥觞。 晋唐时期突出表现宝剑神威的故事类型是“道士剑斩蛟怪”。《抱朴子内篇·登涉》传授“涉江渡海辟蛟龙之道”说:“取牝铜以为雄剑,取牡铜以为雌剑,各长五寸五分,取土之数,以厌水精也,带之以水行,则蛟龙巨鱼水神不敢近人也。”(13)从这段文字大致可见当时道流对于雌雄双剑的信仰心理。在此信仰基础上,多部唐代小说讲述了“许逊斩蛟剑”故事。 中唐时期张鷟《朝野佥载》记载:“西晋末有旌阳县令许逊者,得道于豫章西山。江中有蛟为患,旌阳没水,剑斩之。”斩蛟剑坠入江中,“后不知所在”,到了唐高宗时期,洪州有渔民在扬子江上撒网得一石,“破之得剑一双,视其铭一有‘许旌阳’字,一有‘万仞’字”。果然不久,江西洪州西山上,“遂有万仞师出焉”。(14)这里许逊斩蛟宝剑是一对雌雄剑,正与《抱朴子内篇》的记载相符。大约作于唐元和十四年(819)的《孝道吴许二真君传》也记载了两口许逊剑:“(许逊)升仙后,玉函之中留诗教两卷、犊车一乘、石臼一面、铜剑两口、扇函一具。”(15)许逊的两口雌雄宝剑大概是唐代民众的共同知识,因此唐肃宗时期戴孚的《广异记》记载开元末年太原武胜之在广西静江县“得一铜剑,上有篆‘许旌阳斩蛟第三剑’云”。(16)所谓“第三剑”,说明洪州许逊的雌雄二剑斩蛟故事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别的地方在附会神迹的时候只能在二剑之外另创第三剑。 仗剑斩蛟的道士许逊(旌阳),就是净明道崇奉的祖师——许真君。唐高宗时期,道士万仞、胡慧超师徒在江西洪州大力弘扬许逊崇拜,重修了游帷观等奉祀许真君的道观,《朝野佥载》记录的这个宝剑故事可能采自洪州地区许真君信仰圈的口头传说。许逊的斩蛟宝剑象征着许真君的道教神权,宝剑重现于世,意味着许真君崇拜的复兴,“应属于当时重新振兴的许逊信仰的传说风尚下的产物”(17)。这个故事还隐含着一个“应谶”的故事母题:“万仞剑”与旌阳剑早在西晋时期即成双沉没水中,四百多年后,双剑齐现于世,作为“万仞剑”谶言的呼应,在许真君崇拜的圣地——西山之上,也应谶出现了名为“万仞”的道士。(18)结合许真君信仰发展史,可以看到许逊两口雌雄宝剑和应谶神话的现实指向:在洪州地区积极推动许真君崇拜的道士万仞,名字早就被嵌入古老的许逊遗剑之中,这象征着万仞继承了许真君的神力与权威。 据《孝道吴许二真君传》记载,中唐元和年间,许逊的遗物仍然供奉在游帷观内,“惟二剑,万天师入内,云进上,内中供食”。(19)此句透露出许逊的雌雄剑被主事游帷观的万仞天师作为“祥瑞”宝物进献到朝廷,从高宗时期开始一直在内道场供奉着。 二、帝王权力与道教神剑 许逊斩蛟的雌雄剑被进献,奉纳于皇室内廷,体现了以宝剑作为镇护国家神器的古代政治文化。陶弘景《刀剑录》记载的神剑多数专为帝王铸造,譬如公元440年,“有道士继天师自为帝造剑,因改元为真君”(20)。这里所云“因宝剑而改年号”的历史事件,乃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从道士继天师铸造神剑中得到了“天启(revelation)”,因而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南朝梁武帝即位之后,陶弘景为武帝铸造神剑十三口,均依照道家铸剑法制成,各有“备斋六宫”“皇后服之”“除百邪魑魅”“出军行师”等不同的功用。其中第一把剑名“曰凝霜,道家三洞九真,剑上刻真人玉女名字”,第十二剑名“曰永昌,镇国安社用之,长七尺”,具有明显的镇护国家的象征意味。(21) 常有道士为帝王铸造神器,这是因为东晋以来,道士一直是掌握铸剑核心技术的特殊集团。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介绍了一种与世俗工匠铜剑铸法不同的、结合了道家内炼与外丹的铸剑法,“以金华池浴之,内六一神炉中鼓下之,以桂木烧为之,铜成以刚炭炼之,令童男童女进火”(22)。约作于初唐的道经《洞玄灵宝道学科仪》是一本道士日常修持的手册,其中有一章“作神剑法品”,介绍住在道观的道士制作大剑之法,“凡是道学,当知作大剑法”。剑身须刻篆字、道符与北斗七星,制成之后,要求“此剑恒置所卧床头上栉被褥之间,使常不离身以自远也”。(23)由此可见唐代道士制作和佩戴法剑的普遍现象。然而,从东晋至中唐时期,法剑、符剑虽然屡见道经,却没有一把宝剑被冠以“天师剑”的专用名称。 开元年间,道门领袖、上清宗师司马承祯(647-735)亲自为唐玄宗铸造了两种道教法器,即含象鉴(镜)和景震剑。《道藏》洞玄部灵图类现存《上清含象剑鉴图》一册,收录了司马承祯此次进呈的镜、剑序言与图绘,以及唐玄宗收到明镜宝剑之后的御批诗。(24)据司马承祯的《景震剑序》描述,他铸造的景震剑是一口雌雄共体的阴阳剑。“景”(阳面)代表阳精,剑身刻有北斗七曜五时的天文星象;“震”(阴面)象征阴气,刻有五岳四渎之名。从《景震剑序》后的二幅景震剑图可见,剑茎(手柄)两侧各刻有12字篆书铭文,景面的剑身部位末端刻有一法符,名曰“辛酉符”,震面的对应部位则刻有“庚申符”。(25)这把景震剑的铸造理念,可用序文一语以概之,“剑面合阴阳,刻象法天地”。 可以看到,这种刻有天文星象的符剑形制,仍保留着葛洪时代道士随身佩戴的“天文之符剑”特征,而且沿袭了六朝时期宝剑用于驱鬼辟邪的功能,即《景震剑序》所云:“佩之于身,则有内外之卫;施之于物,则随人鬼之用矣。”与前代的道教符剑较有区别之处,乃是景震剑“剑面合阴阳”的单剑形态,而非《抱朴子内篇》或者许逊那种雌雄双剑。这或许因为景震剑专为唐玄宗佩服而定做,玄宗的御批诗“佩服为身防,从兹一赏玩,永德保龄长”(26)三句可以证明它的定制性质。从现存的唐代文物来看,古代士大夫的佩剑一般是单剑,较少采用道士法剑的雌雄双剑形式。 玄宗的御批诗一再强调镜剑二种神器“宝照含天地,神剑合阴阳”的象征意义,景震剑“阴阳同光”与“法天地”的特质,强化了天子“掌天握地”的神权意味。开元十九年(731),玄宗采纳司马承祯的建议,在天下名岳建立五岳真君祠等道观,以达到道教镇护国家山河的目的。(27)正如福永光司已经指出的,司马承祯进呈的含象镜与景震剑体现了现世帝王统治权力的神威。(28)笔者认为,进呈这两种“含天地、合阴阳”的神器的行为,其实与以司马承祯为首的上清道派以道教理念改造国家祭祀体系的意图是一脉相承的。 含象镜与景震剑应当是一起收藏于内廷,但中唐之后已经看不到景震剑的相关记载。北宋景德二年(1005),大臣吴及向宋真宗进呈司马承祯的含象镜,《进司马天师铸含象鉴表状》宣称宝镜是吴氏“家传累世,掌秘多年”(29)。由吴及的语气推测,在唐宋之交的世乱中,含象镜可能流落到了民间,并被吴及的祖先世代珍藏。而景震剑有可能一直收藏于大内或者江苏茅山的上清宗师手中,因为北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四月,摄政的刘太后(章献明肃皇后)在开封昭应宫亲受上清法箓,她的传度师就是曾为真宗祈嗣、得生仁宗的上清第二十三代宗师朱自英。内道场的道士为此次皇后受箓而依科备办的经箓信物名单中,出现了“四规明照、景震灵剑”的字样。(30)可见作为唐朝国家神器的含象镜与景震剑,在宋代的国家道教科仪中仍保留着国家神权的象征符号意味。 三、晚唐天师剑印的出现 从陶弘景的十三口神剑到司马承祯的景震剑,一直是上清一系的道士在持续积极地运用“神剑—皇权”的象征符号传统,而不是张天师世系的正一天师道道士。这或许与张天师世系在南朝至中唐近四百年的沉寂有直接关系。晚唐时期,随着张天师信仰的复苏,“天师剑”主题叙事开始见诸文字。就笔者目力所及,详细记载天师剑的早期典籍大概是晚唐五代间的高道杜光庭(850-933)所撰写的《道教灵验记》(31)。在杜光庭之前,江南地区张天师子孙的详细活动较少被记录,因此编写于唐天祐元年(905)之前《道教灵验记》的“天师剑愈疾验”故事显得尤有价值: 天师剑,五所铸,状若生铜五节,连环之柄,上有隐起符文,星辰日月之象,重八十一两,尝用诛制鬼神,降翦凶丑。升天之日,留剑及都功印,传于子孙,誓曰:“我一世有子一人传我印、剑及都功箓,唯此非子孙不传于世。”顶上有朱发十数茎,以表奇相,于今二十一世矣。其剑时有异光,或闻吟吼,乍存乍亡,颇彰灵应。至十六世天师,好以慈惠及人,忧轸于物,以神剑灵效,每有疾苦者,多借令供养,即所疾旋祛。邻家夜产,性命危切,亦以此剑借之。既至产家,有神光如烛,闪然照一室之中,堕地而折。经数十年,十八世孙惠钦,性温和,守谦退,与物无竞……(32) 这段记载综合了前代道教剑传说的各种叙事因素,又为后世道经天师剑叙事之祖述,值得一一抉发。 首先是天师剑的形制,“上有隐起符文,星辰日月之象”,这与葛洪时代的符剑以及司马承祯“刻象法天地”的景震剑是一脉相承的。杜光庭在成都隐居期间曾编纂《青城山记》,中有一段提及张天师在蜀地的遗迹:“降剑坛,昔道君授天师阴阳剑处,有隐剑迹。”(33)由于宋元之后的道经提及天师剑皆为“斩邪雌雄二神剑”或“雌雄二剑”,杜光庭所记述的晚唐天师剑可能为阴阳双剑的形制,这又连接上了葛洪和许逊的雌雄剑传统。(34) 其次,道教法剑的灵效主要在“却鬼辟邪”,天师剑亦是如此,《道教灵验记》云其“诛制鬼神,降翦凶丑”。十六世张天师掌教时,天师剑治病的灵效远近闻名。天师剑在一次救治产妇的出诊中,堕地而折,灵应顿失。经过数十年,在十八世张天师手上,断剑被一个神秘的老者施展神术修复完好如初,“识者疑是天师化现,降于人间,自续其剑”。 最后,天师剑是张道陵祖天师的神圣化身,其“顶上有朱发十数茎”的独特形状,对应着张道陵“绿睛朱顶”的奇相(35)。这条记载首次将道教法剑“专名化”为天师剑,解释这个专名的缘起为张道陵祖天师升天之时留下的遗训:“我一世有子一人传我印、剑及都功箓,唯此非子孙不传于世。”此遗训以物据为凭证,确立了张天师子孙代代相传的宗教权力。此外,《道教灵验记》卷十一“刘迁都功箓验”故事中也有一段相似的天师遗训:“昔天师升天于云台山,告示天地万神曰:‘吾升天之后,留太上所赐宝剑、都功印箓以付子孙,救护亿兆’。”(36) 由《道教灵验记》所见,唐玄宗时期象征帝王权力的“镜剑传统”,到了晚唐时期出现了另外一种象征教权的“剑印箓传统”。在这个全新的组合之中,阳平治都功印和都功箓早已见于六朝道经,只有天师剑是新发明的传统。 道教的法印,仿效汉代官府的印玺,广泛用于道士奏状疏文的签押、驱策鬼神、治疗疾病等宗教活动中。(37)自东汉以来,天师道的道士较常用的法印有“天帝使者印”“黄神越章之印”等。(38)张天师世系专用的“阳平治都功印”,可能在六朝时期已经存在。现存的《正一法文传都功版仪》是刘宋时期天师道经典《正一法文》残本之一,此经专门记载了道士升任“都功”时制作“都功版”的版文范本。都功,即天师道二十四个天师治(教区)的职事主管道士,负责监管本治的道民与道士。作为天师道二十四治之首的阳平治(今四川省青林县阳平山),都功道士历来只能由张天师的直系子孙担任。刘宋时的道门领袖陆修静强调说:“阳平治都功版,非天师之胤不受。”(39)唐前的阳平治都功版并非法印,它是由银木制成的木版,长九寸、广五寸,版文分作七行。都功版是制作“都功箓”的印版,道士获得署职都功之后,掌握了都功版,也就拥有了向信徒传授正一法位“都功箓”的神圣教权。在天师道科仪世界的官僚文书体系中,都功版用于印制道箓,都功印则用于行文发遣的签押,这两种法器是互相依存的。《正一法文传都功版仪》一再强调“阳平治都功版”只能掌握于“天师若干世孙”之手,由此推测,阳平治都功印也是世代传承于张天师直系子孙之中。(40) 从六朝至唐代的道内文献来看,阳平治都功印箓已经作为张天师信仰传统的象征符号,在张天师子孙的手中奕世相传。晚唐龙虎山张天师世系兴起之前,见于文献的、但不在龙虎山的张天师子孙尚有十四人。(41)其中开元年间曾担任东都道门威仪使的张探玄(667-742)尤为著名。墓志铭中,张探玄被称为“正一真人道陵师君之胄”,并被褒扬为“斧缋妙门,光传法印,兴复乃烈,是生贞玄”。(42)这里将“法印”作为张氏玄门正统的象征,大概可以窥见“天师印”在开元时期已经是比较固定的天师子孙象征符号。可是在这十四人的相关文献中,同样找不到天师子孙的另一象征符号——天师剑的任何记载。 四、作为汉室象征的天师剑印 现存天师剑的最早记载是上引杜光庭《道教灵验记》的“天师剑愈疾验”,文中说“于今二十一世矣”。摘采写这则灵验记的时间是第二十一代张天师在世时,但当时杜光庭已隐居于蜀地,这则故事可能是他入蜀之前听说的。杜光庭,浙南缙云人,其师应夷节(810-894)在十八岁那年“诣龙虎山系天师十八代孙少任,受三品大都功”(43)。这里提及的第十八代天师张少任名字与《道教灵验记》所记“十八世孙惠钦”不一致,但至少说明杜光庭的道教生涯是与龙虎山张天师有所交涉的。并且从应夷节的入道经历来看,晚唐时期(828年前后)龙虎山张天师子孙的道教影响力扩展到江浙一带,已有浙南道士远赴龙虎山受“正一法位”,张天师向前来受箓的弟子颁授“都功箓”(44),可以推定龙虎山一支的天师子孙已经拥有作为张天师象征的阳平治都功印。此外《道教灵验记》的“刘迁都功箓验”又记,唐咸通九年(868),大商人刘迁“诣十九世天师传授都功箓”,后刘迁身患重症,弥留之际得到都功箓的庇佑而得以生还,“遂被褐修道,精专香火,入龙虎山师奉天师矣”。(45) 到了《道教灵验记》“天师剑愈疾验”记叙的第二十一代张天师,江西龙虎山正处于南吴、南唐的小朝廷统治之下。南唐开国皇帝徐知诰(李昪)的养父、南吴权臣徐温(862-927)曾有过“梦堕井中、得汉天师救助”的经历,龙虎山张天师信仰因此获得当政者的大力褒扬。(46)南唐保大八年(950)陈乔的《新建信州龙虎山张天师庙碑》写于第二十二代张天师掌教时,碑中记述了南唐国主下旨兴建张天师庙的前后经过,颂扬张道陵天师“圣人之符瑞”乃在于“山涌龟蛇之金,匣鸣龙虎之剑”。(47)所谓“龟蛇之金”借指汉代龟纽金印等印玺,在张天师庙的语境之下概指天师印;“龙虎之剑”既呼应龙虎山的山名,也有着雌雄双剑的寓意。(48) 此前研究者指出:“从唐懿宗时的十九代天师到南唐时期的二十二代天师,表明晚唐五代实为龙虎山张天师系的构造期,在此期间明确排定了张道陵后世的顺序。”(49)我们通过考察“天师与剑”叙事的层累递进也看到,“天师剑印箓”的组合逐步稳定为张天师教权象征符号的过程,与龙虎山张天师世系的构造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在这个新发明的象征组合中,神剑,而不是明镜,被龙虎山的张天师子孙选中,似乎是有所寄托的。 在传统政治文化中,传国玺与宝剑被视为汉室正统的象征性符号。汉高祖做亭长时曾以剑斩白蛇,后遂发迹,这把斩蛇剑作为开国之宝代代相传,并且与开国玉玺一起成为汉室的神圣象征。东汉应劭《汉官仪》曰:“(侍中)驾出则一人负传国玺、操斩蛇剑参乘,与中官俱止禁中。”(50)汉代的皇太子即位典礼,国玺与斩蛇剑一起授予太子,象征着皇权的交接。南朝谢眺的《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首句有“炎灵遗剑玺,当涂骇龙战”,李善注本《文选》引用《汉书·礼仪》注释此句:“皇太子即位,中黄门以斩蛇宝剑授。”剑玺作为皇位的凭证,频频出现于唐人诗句中,比如李白的《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并序》歌颂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再造唐室的功绩云:“五让而传剑玺,德让乐推。”(51) 虽然唐玄宗与肃宗曾写有《张天师赞》褒扬张天师,但在晚唐之前,张天师信仰在官方和道团内部还没有成为核心。只有在李氏皇室的中央集权衰微之后,江西龙虎山这样一个偏僻山区的张姓道教家族才会被南方的割据新政权(南吴、南汉、南唐、吴越)看中,张天师家族也重新恢复曹魏以来为皇室证明天命的政教传统。(52)在4世纪的晋宋之交,汉天师张道陵作为汉代正统天命的传递者和守护者的象征传统,曾经是推动中古经教道教形成的主要动力。(53)但在那一波恢复“三张传统”的道教复古浪潮中,道团并未提炼出类似“天师剑印”的象征符号。而到了晚唐五代时期,祖天师张道陵“辅佐汉室”历史传统尤其被移居龙虎山的张天师子孙所借重,他们提出“天师剑印”作为汉天师神圣权力的凭证。在这个全新的象征组合之中,阳平治都功印相当于国玺,天师剑相当于斩蛇剑。“天师”(天子之师)剑印,具有双重象征意义:在道教内部它象征着“唯此非子孙不传于世”的汉天师嫡传血统;在教外则意味着汉室正统的剑玺符命。 从陈乔《新建信州龙虎山张天师庙碑》的文字表述可知,龙虎山张天师世系的“天师剑印”象征符号得到了南唐政权的极大认同。南唐国君李璟看重汉张天师“辅佐汉室”的历史传统,碑文开宗明义说:“皇帝陛下极大道之颓纲,维列仙之绝纽,乃眷正一,属之真人。思与神交,遂崇庙貌。”后文又多次提到张道陵“六世相韩之盛,七叶佐汉之名”的佐国辅政之功,并云“炎汉非刘不王,既闻命矣,逾千越万,绝后光前”,而南唐王朝“爰属大统,土德中兴”,也就是声明南唐皇室乃是继承了汉室正统。碑文总结云:“山涌龟蛇之金,匣鸣龙虎之剑。九苞神凤,窥阿阁以来仪,八翼灵禽,背羽山而戾止。斯则圣人之符瑞也。”天师剑印作为圣人汉张天师降授的“符瑞”,见证了南唐政权“受命于天”的合法性。 五、地方天师剑传说 以上我们讨论了作为张天师教权象征的天师剑在晚唐五代的兴起以及这一叙事与江西龙虎山张天师世系的复兴之间的联系。随着龙虎山天师府影响力的日渐扩大,“天师剑与张天师子孙”是否变成一种结构稳定的文学主题?也就是说,龙虎山天师府的现实影响力是否对天师剑传说的稳定产生了决定性作用?如果可以搜集到发生在龙虎山之外的天师剑传说的异文本,龙虎山张天师世系与天师剑传说的关系就可以得到更为充分的证明。 唐咸通年间(860-874),浙江天台山道士刘方瀛,“常以丹篆救人,与同志弋阳县令刘翙按天师剑法,以五月五日就弋阳葛溪炼钢造剑,敕符禁水,疾者登时即愈”(54)。无需手持龙虎山天师剑,只要依照天师剑法铸造宝剑,即可获得“疾者登时即愈”的治病神力。这个故事反映了晚唐时期天师剑灵验名声的广泛传播。在距离龙虎山天师府约240公里的浙江西南部栝州(今浙江丽水)松阳县境内,与天台山的天师剑法传说相似的时间,也出现了天师剑传说。杜光庭编纂的杂传集《神仙感遇传》卷一,讲述了有位被称为“丰尊师”的道士来到“处州松阳县卯酉山叶天师旧宅观”修道,在一次中元节的黄箓道场上,丰尊师忽然失踪: 逡巡丰(尊师)至,曰:“适天师与三天张天师并降,赐我神剑。令且于山中修道,续有旨命,即出人间,用此剑扶持社稷。”视功德前,果有剑长三尺余,有纸一幅长四五尺,广三尺,与人间稍同,但长阔顿异,非工所制作……昔叶天师尝谓人曰:百六十年后,有术过我者,当居此山。今丰果符其言矣。(55) 这里的“三天张天师”所指应是传授“三天正法”的汉天师张道陵,而“叶天师”系指松阳出生的国师叶法善(616-720)。开元五年(717),叶法善上奏朝廷,将松阳卯山西南的叶氏祖宅辟为道观,获赐额为“淳和观”,亦即本故事的“叶天师旧宅观”,中唐以后道观改名为“安和观”。(56)在《神仙感遇传》之外,唐代文献提到叶天师的宝剑有两处:一是开元五年《唐有道先生叶国重碑》提到“火涤淫祀,剑诛群妖”;(57)二是《太平广记》的“叶法善传”记载叶天师早年寻道访师,“诣嵩山,神仙授剑”。(58)这两条材料泛泛而谈,没有着重渲染叶天师法剑的具体事迹,“神仙授剑”“剑诛群妖”只是一种描写道士的文学套路,天师剑并未成为叶法善道术的标志性象征。 杜光庭的《神仙感遇传》中“丰尊师”一文出现的叶、张天师降授的天师剑,与他编纂的《道教灵验记》里以龙虎山张天师世系为中心的“天师剑印”,均是晚唐发生的天师剑灵验故事。或许受到龙虎山天师剑叙事的影响,叶法善天师剑才逐渐“由虚而实”。丰尊师故事中,虽然神剑是叶天师与汉张天师一起降授的,但文末又特地点明当年叶天师曾预言160年之后(即公元880年前后)会有继承人前来卯山居住。160年后,果然有道士丰尊师应谶而至,获授天师剑,可见故事的叙事目的还是在于利用天师剑的象征符号来证明“叶天师—丰尊师”的道法传承关系。这个故事蕴含着宝剑符谶以及道士应谶的母题,明显与初唐时期“许逊—万仞宝剑”传说有着前后继承的关系。 稍晚于杜光庭《神仙感遇传》的沈汾《续仙传》(59),收入一篇传记“丰去奢”,也讲述了发生于唐僖宗中和年间(881-884)的松阳天师剑故事: 丰去奢,衢州龙丘人也……年三十余,便居处州松阳县安和观,其观即叶静能故乡学道之所。而观北五里有卯山,高五十余丈,相传云,汉张天师及叶静能皆居此山修道。去奢慕前事,登其山结庵以居。后观中道士相率山下居人,为构屋及造堂殿,设老君、张天师像及叶静能真影,朝夕焚修朝礼……(卯)山东南有一方石,阔二丈余,平若砥,盖天然也。去奢常坐其上拱黙静想,一旦感神人,谓之曰:“张天师有斩邪剑二口并瓶贮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谢神人曰:“此石天设,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谬守真而已。托兹山栖获安,久蒙圣佑,丹之与剑,讵可輙取?”神人曰:“但勤修无怠,剑丹自可立致。”后三年,神人乃以剑、丹送于去奢。剑乃张天师七星剑,丹以石匣藏之,一瓶贮之,倾药有斗余,如麻子,红色光明。去奢自服及施人,有疾皆愈……(60) 比之《神仙感遇传》的丰尊师,《续仙传》里的丰去奢获得天师剑的过程更为坎坷,他经受了神人的几次“试炼”方获授汉张天师的斩邪剑二口与灵丹。凭借天师剑与灵丹的神威,丰去奢在浙南一带行医驱邪,道名大起,却招来牢狱之灾,幸好仰仗天师剑灵威的庇佑,最后安全脱险。这里说卯山安和观是“叶静能故乡学道之所”,显然是受到中唐之后普遍混淆叶法善、叶静能二人的民间习惯书写之影响,将叶法善误写为叶静能。(61)从这段记载可知,在道士丰去奢的主持下,安和观在卯山上盖造了堂殿,设立了太上老君、张天师二尊神像,又供奉着创观祖师叶法善的真影画像。 按照道教神权天授模式,宗教领袖取得天神的授命之后才拥有号令一切的权力。东汉张道陵得太上老祖降授“天师”号,西晋魏华存得清虚真人降授《大洞真经》等,皆是照此模式而来。《续仙传》叙述外来道士丰去奢到松阳安和观后,宣称卯山原为汉张天师修炼之处,又得到天师剑适当其时的降授。故事里,来自汉张天师的宝剑与灵丹赋予了丰去奢凌驾于本地传统(叶法善崇拜)之上的神圣权力。象征汉张天师道教正统的天师剑,不仅使丰去奢获得了主持安和观的现实权力,更使他的法术具备了治病劾鬼的神奇法力。 虽然同样是以松阳丰姓道士为主角的宝剑传说,《续仙传》却将宝剑单独归于张天师身上,而且丝毫不提《神仙感遇传》所揭示的叶天师谶语。在民间文学的类型学上,《续仙传》与《神仙感遇传》的宝剑传说其实属于不同的故事类型。《续仙传》与上引杜光庭《道教灵验记》中“天师剑愈疾验”反而属于同一天师剑故事类型,而且丰去奢获授的“张天师斩邪剑二口”与龙虎山天师剑有两处相同:其一,天师剑上刻有星斗符文,而且是雌雄双剑;其二,天师剑的灵验主要体现在治疗上,“有疾皆愈”,“所疾旋祛”。 正因为分属不同的故事类型,《神仙感遇传》里叶天师与张天师授予丰尊师的神剑却是“三尺余”的一口长剑,而且这把天师剑的神圣使命乃在辅佐丰尊师“扶持社稷”,而不是像丰去奢的斩邪剑那样在民间救死疗伤。产生如此不同表述的原因可能是《神仙感遇传》与《续仙传》采自不同人群的口头传说,两者的叙事目的各有不同:前者的叙事着重描述叶天师的预言与丰尊师的应谶,为了突出镇护国家之神威,天师剑的形状更接近司马承祯为唐玄宗铸造的景震剑;后者的叙事重点是汉张天师的神威降授至丰去奢身上,受到晚唐龙虎山天师剑叙事的影响,斩邪剑为双剑的形制。 东晋以来松阳叶氏家族的道教传承近于正一天师道,但是关于叶法善的唐代文献从未宣称他与张天师世系有所关联。(62)晚唐以前提及松阳卯山的典籍也从未记录汉天师张道陵在此山的任何行迹,而到了晚唐五代,无论是杜光庭的《神仙感遇传》还是沈汾的《续仙传》,卯山变成汉天师张道陵降授之所。随着江西龙虎山张天师世系在江南地区影响力的增强,江浙一带的道士远赴龙虎山接受张天师子孙的授箓,并且原来与张天师信仰关系不深的卯山也被道士“加注”了汉张天师的圣迹。那么丰去奢获授的天师斩邪剑二口,是否就是江西龙虎山世代相传的天师剑?天师印剑一世只传一人,非张天师嫡孙不传,这是龙虎山天师剑叙事的中心点,按照《道教灵验记》的记录,天师剑从十六代至二十一代就长伴张天师左右。《续仙传》记录丰去奢在卯山活动的时间大约是880年至910年之间,第二十一代张天师也大致在这个年代活跃,丰去奢的天师剑的正统性无疑是很成问题的。 如果说杜光庭《道教灵验记》中天师剑灵验传说属于道教中央叙事,即“大传统”,那么《续仙传》中丰去奢天师剑传说以及《神仙感遇传》里叶天师与张天师授予丰尊师的神剑则属于地方叙事的“小传统”。这两种叙事并不构成相互否定的矛盾关系,反而是相互补充说明了晚唐五代时期,随着龙虎山张天师世系的复兴,江西、浙江等地开始流传着宣扬张天师神威的天师剑传说。天师剑的灵验传说传播到了松阳之后“在地化”,于是产生了丰尊师的叶、张天师神剑和丰去奢的“张天师斩邪剑二口”。 以上追溯了宋前天师剑叙事的兴起以及这一文学主题流传于各地的异文本。天师剑是正一道教至高教权的象征符号,也是民间宝物崇拜的现实原型。宝物崇拜是普遍存在于志怪小说和明清神魔小说的叙事主题,天师剑也属于宝物崇拜中的一种,与其他类型的道教宝物分享着共同的灵验主题——驱邪与治疗。(63)但是由于特殊的道教信仰背景,天师剑传说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诠释维度。 从故事学的维度出发,我们发现天师剑叙事并非晚唐时期龙虎山天师世系发明的全新叙事,它汲取唐前“道士与剑”类型故事的若干母题,并将这些古老的母题整合在“汉张天师”教主的旗帜之下,赋予了宝剑“天师剑”的专名。 从信仰史的角度又可以看到,由唐玄宗时期上清道派的“镜与剑”,到晚唐龙虎山的“张天师剑印箓”,“政权与教权”的象征符号组合发生了转变,这个转变的背后是龙虎山张天师世系的势力扩张。 从符号学的角度还可以观察到,集结在印玺、符剑之上的政治符号传统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晚唐出现的天师剑与玉印成为具有与“传国玺”同样政治隐喻的教权象征,世代相传直至现代。 传说的背后是信仰;符号的背后是政治。“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几,而天师剑印传子若孙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只有从故事学、宗教学、符号学三个角度去解析天师剑叙事,我们才可以理解当年元世祖何以对着天师剑发出如此感叹。 ①(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十八,见《正统道藏》,第5册,第207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②《元史》卷二百二十,第2867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③传世史籍中关于张道陵的记载,以《三国志·张鲁传》为最早,并无剑印的记载。六朝时期较为详尽记载张天师事迹的道经,如《三天内解经》《大道家令戒》,亦无天师剑记载。六朝道教对张天师创教神话的塑造,可参见刘屹:《神格与地域: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第137—1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④葛洪《神仙传》原书已佚,现存各种版本是后人掇拾,故书中《张道陵传》文字大异。胡守为校释《神仙传校释》(第190—191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系据四库全书本,与《太平广记》卷八、《云笈七签》卷一百九的《张道陵传》完全不同。 ⑤《古今刀剑录》,“丛书集成初编”第1490册,今存一卷,经历代传抄,《四库提要》认为此书“为后人所窜乱,真伪掺半”。但《太平御览》等宋书屡有引文,研究者认为现存《古今刀剑录》“内容的传承之古是可以肯定的”。参见[日]福永光司:《道教的镜与剑》,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7册,第426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⑥傅勤家:《张天师世系考》,见《中国道教史》,第82—86页,商务书局1937年版;柳存仁:《题免得龛藏汉天师世系赞卷》,见《和风堂文集》(中册),第753—7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2卷,第143—14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日]二阶堂善弘:《有关天师张虚靖的形象》,载《台湾宗教研究通讯》2002年第3期;王见川:《张天师之研究:以龙虎山一系为考察中心》,(台北)“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⑦(明)张正常:《汉天师世家》卷二,见《正统道藏》,第34册,第820页。 ⑧道教史研究尚未有专文讨论“天师剑”叙事的兴起,与本文关系较大的前人研究主要有三:一是福永光司的《道教的镜与剑》一文,着重讨论唐玄宗时期司马承祯铸造的镜与剑;二是张泽洪的《论道教的法剑》(载《中国道教》2002年第3期),概括介绍了文献所载道教法剑及其宗教意义;三是王见川在《龙虎山张天师的兴起与其在宋代的发展》一文中简要提出,张天师传承信物印、剑、都功箓,应是在齐梁至唐中叶间形成(参见高致华编:《探寻民间诸神与信仰文化》,第31—68页,黄山书社2006年版)。王见川一文较为留意援引晚唐五代的资料来说明龙虎山天师世系兴起的历史背景,但对于天师剑传说如何从“道士宝剑”类型故事中“专名化”为张天师子孙所独有,缺乏横向的考虑。 ⑨《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九,第177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⑩《抱朴子内篇校释》卷十九,第336页。 (11)《剑经》今已不传,仅见《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一,引《尚书故实》“陶贞白”条,第1769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12)此故事有两种出处:一是梁时无名氏的《录异传》,已佚,今有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本,第4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二是《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四引作《搜神记》,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第182—18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3)《抱朴子内篇校释》卷十七,第308页。 (14)《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一“许逊”,引自《朝野佥载》,第1769页。许逊剑斩蛟怪的故事又见于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二:“晋许旌阳,吴猛弟子也。及遇巨蛇,吴年衰,力不能制,许遂禹步敕剑登其首,斩之。”(第1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5)(19)《孝道吴许二真君传》,见《正统道藏》,第6册,第844页。 (16)《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一“武胜之”,引自《广异记》,第1062页。 (17)李丰楙:《许逊传说的形成与衍变——以六朝至唐为主的考察》,见《许逊与萨守坚:邓志谟道教小说研究》,第11—65页,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版。 (18)郭武认为万仞实即高宗朝受宠的道士万振,后代洪州西山净明道所宣扬的万法师。参见郭武:《〈净明忠孝全书〉研究:以宋、元社会为背景的考察》,第177—1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20)(21)《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三,引自陶弘景《刀剑录》,第1579,1579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22)《抱朴子内篇校释》卷十七,第307页。 (23)《洞玄灵宝道学科仪》卷下,见《正统道藏》,第24册,第776页。 (24)《上清含象剑鉴图》,见《正统道藏》,第6册,第684—686页。又见《全唐文》卷九百二十四。Russel Kirkland.Ssuma Cheng-chen and the Role of Taoism in the Mediaval Chinese Polity.Journal of Asian History,1997,31(2):105—138。 (25)《上清含象剑鉴图》,见《正统道藏》,第6册,第685页。 (26)《上清含象剑鉴图》,见《正统道藏》,第6册,第685页。此诗在《全唐诗》卷三另题为《答司马承祯上剑镜》。 (27)雷闻:《五岳真君祠与唐代国家祭祀》,见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第35—8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Charles D.Benn.Religious Aspects of Emperor Hsuan-tsung's Taoist Ideology//Buddhist and Taoist Practice in Medieval Chinese Society 2,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7:127—145. (28)福永光司:《道教的镜与剑》,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择》,第7册,第413页。 (29)《上清含象剑鉴图》,见《正统道藏》,第6册,第686页;吴受琚辑释:《司马承祯集》,第6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30)《宋天圣皇太后受上清箓记》,收入元代刘大彬《茅山志》卷二十五,见《正统道藏》,第5册,第658页。又,此记即为署名道士朱自英的《章献明肃皇后受上清毕法箓记》,见《正统道藏》,第18册,第42—44页。 (31)杜光庭编纂的仙传集和灵验记,多出自他的耳闻目见,且大部分是发生在江浙、蜀地的“时事”。《道教灵验记》的成书年代下限是唐元祐元年(905)。参见罗争鸣:《杜光庭道教小说研究》,第279页,巴蜀书社2005年版。 (32)“天师剑愈疾验”,见《云笈七签》卷一百二十,第2648—2650页。《正统道藏》本的《道教灵验记》,此条作“天师剑验”,文字相同。 (33)此句系《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十八,见《正统道藏》,第5册,第203页,在“雌雄二剑”之下引用《青城山记》。杜光庭《青城山记》今存一卷,《全唐文》收入,但不见此条记载。 (34)从明代以后的天师剑实物来看,阴阳剑当指插于同一剑鞘的双剑,偏薄的剑身一边平,一边有脊,双剑相合可当一把剑来使用,有时也将两把分开,左右两手各握一把。1949年,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出逃台湾,天师剑亦被其携至台湾。日本学者编修的《道教》第三辑图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刊有台湾道士所用的天师七星剑。 (35)“(张道陵)年及冠,身长九尺二寸,厉眉广颡,绿睛朱顶,隆准方颐,目有三角。”参见《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十八,见《正统道藏》,第5册,第200页。 (36)《道教灵验记》卷十一,见《正统道藏》,第10册,第838页。此条不见于《云笈七签》。 (37)南宋道士金允中编纂的《上清灵宝大法》卷十:“《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阳世之典格也……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俗。”(《正统道藏》,第31册,第398页。) (38)王育成:《道教法印令牌探奥》,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此书结合考古发现与道经资料,较为全面介绍东汉以降的法印,但没有讨论唐宋之间的“阳平治都功印”。 (39)《正一法文传都功版仪》,见《正统道藏》,第28册,第490页。 (40)金允中针对“近时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多矣”的乱态,提出:“晋宋之末,齐修方盛,文檄渐繁,故印篆尤不可缺也。汉天师止以阳平治一印,而至飞升。”(《上清灵宝大法》卷十,见《正统道藏》,第3册,第399页)可见道教科仪文书用印的习惯兴起于刘宋时期,之前的授箓用印只有阳平治都功印一种。 (41)十三个张天师子孙的考辨,参见王见川:《龙虎山张天师的兴起与其在宋代的发展》,第38页。此外《江西道教史》(第95—99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又举出唐高宗年间的张惠郎为张天师第十四代孙。 (42)蔡玮:《唐东京道门威仪使圣真玄元两观主清虚洞府灵都仙台贞玄先生张尊师遗烈碑铭》,见《道家金石略》,第136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43)《洞玄灵宝三师记》,见《正统道藏》,第11册,第557页。 (44)应夷节在龙虎山所受“三品大都功箓”即是阳平治都功箓。唐代天师道上章仪范《赤松子章历》卷二记“正一法位”云:“系天师阳平治,左平炁门下,版署三品大都功。”《道教灵验记》“刘迁都功箓验”也提到“此箓(按:都功箓)初以版署三品”。 (45)《道教灵验记》卷十一,见《正统道藏》,第10册,第838页。 (46)王见川:《龙虎山张天师的兴起与其在宋代的发展》,第41页。 (47)《龙虎山志》卷十二,见《藏外道书》,第19册,第555—558页;《全唐文》卷八百七十六,第91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48)龙虎山的山名本身就有龙虎阴阳相对之意。《太平御览》卷四十八引《信州图经》曰:“龙虎山,在贵溪县,二山相对,溪流其间,乃张天师得道之山。” (49)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2卷,第148页。 (50)《汉官仪》卷上,《汉官六种》本,第137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51)詹瑛:《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卷三十,第431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52)Timothy Hugh Barrett.The Emergence of the Taoist Papacy in the T"ang Dynasty.Asia Major 3rd series 1,1994:89—106. (53)刘屹:《敬天与崇道——中古经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第667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54)“刘方瀛天师灵验”,载《道教灵验记》卷八,见《正统道藏》,第10册,第829页。《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九,第2616页,此条作“道士刘方瀛依天师剑法治疾验”,文字相同。《道藏》本《道教灵验记》卷十一第838页,“刘迁功箓验”有一段异文,“(刘)脩然与(刘)刿复于葛溪制神剑各一口,依藏景石精之法以成”。 (55)杜光庭:《神仙感遇传》卷一“丰尊师”,见《正统道藏》,第10册,第886页。《神仙感遇传》全书不传,《正统道藏》残存五卷,《太平广记》《云笈七签》等书录有部分佚文。 (56)《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方伎传·叶法善传》,第5107—5108页。唐宪宗(806-820年在位)时期,为避宪宗李纯的名讳,淳和观改名“安和观”。参见吴真:《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第1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57)碑文见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04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58)《太平广记》卷二十六,第171页。这一分内容当系引自杜光庭《仙传拾遗》。 (59)《续仙传》经常提及黄巢叛乱之后的混乱世局,由此推测,作者沈汾大约是唐末至五代之间的溧水县(今属江苏)县令,撰写《续仙传》的时间是在唐亡之后。今《正统道藏》第8册收有《续仙传》全本3卷,第251—303页,所记共36人,多为晚唐五代时人。另外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三下,第2523—2480页,载《续仙传》中25人,当系节本。 (60)《续仙传》“丰去奢”,见《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三,第2494—2495页。《续仙传》记载强人囚禁丰去奢,强夺天师剑,时逢“华造兵乱”,时间约为公元893年。丰去奢30多岁便来卯山居住,华造兵乱中,丰去奢入狱,脱险后又在安和观居住了15年余后白日飞升,由此大致可以推测丰去奢活动的年代在850—910年之间。 (61)吴真:《唐代社会关于道士法术的集体文学想象》,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3期。 (62)吴真:《浙南叶氏道教世家的道法传统》,载《上海道教》2008年第3期。 (63)刘守华:《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年版;刘卫英:《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