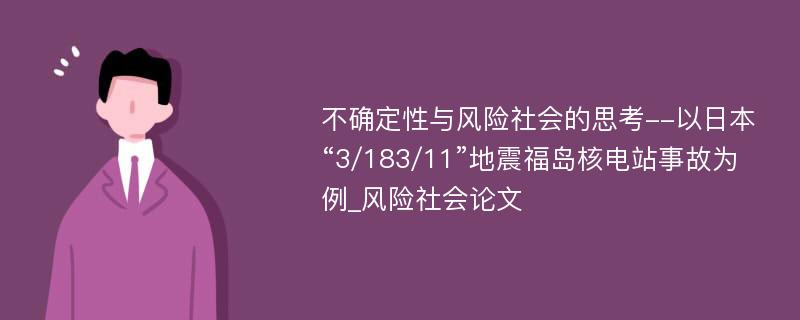
关于不确定性与风险社会的沉思——从日本“3#183;11”大地震中的福岛核电站事故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震中论文,核电站论文,日本论文,不确定性论文,沉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了9级特大地震,随后引发的海啸造成了更大危害,除了数额巨大的财产损失之外,更加让人震惊的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一、三、二、四号机组先后发生爆炸,使日本和邻国一时间笼罩在令人恐怖的核阴云之下。这次突如其来的灾难,不仅让人想起历史上许多损失惨重的大地震,而且也让人想起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泄露事件以及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从人类的认识角度看,自然灾害往往是基于不确定性,即正常自然进程的中断或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人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难以招架。如果说自然灾害一直是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那么在现代社会,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则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不确定性,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不确定性,从而使人类进入了所谓不确定性时代或“风险社会”。
一
很多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不确定性的时代,或称之为“风险社会”和“不安全的时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尔认为,在现代社会,“本体论差异的等级制度的确定性,被自由的有创造力的不确定性所取代”。在这里,新出现的问题包括:“不确定的新政治经济、金融市场、有关食品及其他产品(疯牛病)的跨文化冲突、正在出现的‘风险社区’,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由此,“在人为不确定性的全球世界中,个人生活经历及世界政治都在变为‘有风险的’”。(贝尔,第16、6页)面对新自由主义的扩张,英国学者拉里·埃里奥特和丹·阿特金森指出:“自由放任制度已经为普通百姓带来了一个不安全的时代”,而“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把狼重新关到笼子里,而且从此就不要把它放出来”。(埃里奥特、阿特金森,第21、22页)这些学者都关注和探究了现代社会的“不确定”特征,贝尔认为,“这种不确定性为‘人为的不确定性’”(贝尔,第180页),埃里奥特和阿特金森则相信,在“社会民主主义”的范畴内把放任主义“关进笼子”就可以解决问题。但他们对不确定性的理解远不如马克思深刻:马克思把新的不确定性看作社会历史发展和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确定性进一步深化了:“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本主义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35页)在这里,他们没有把这种“不确定性”看作是人为的,也没有将其看作是可随意改变的,而是视为生产方式变革的产物。
实际上,不仅在社会历史领域,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凸显。据许多科学家的研究,不确定性是客观世界的“常态”。在他们看来,只要有变化就有不确定性,因为“未来本质上具有不确定性,平衡的状态只是例外的情况,物质现象绝非处在平衡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一切具有不确定性,而不是具有确定性”。(沃勒斯坦,第11页)确定性的幻想是近代由牛顿的科学体系造成的,因为这种经典科学体系对世界的运行提供的是常规说明。
在古代,宇宙图景本身给混沌和偶然性留下了空间。按照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观点,不确定性早就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这就是,构成宇宙的最小单位原子在虚空中自由坠落的过程中,会在不确定的时刻和不确定的地点发生某些偏离,从而造成原子之间的碰撞,形成原子之间的不同组合,并由此构成万事万物。正是这种不确定性造就了自然万物,也给了人们某种自由行动的可能性。如果世界只是服从严格的必然性铁律,那么人的选择和努力都将成为不可能。可见在古代,人们对不确定性现象并不那么焦虑,他们把不确定性作为人类不能逃避的必然命运——无论是自然的运数还是诸神或上帝的神圣裁定——加以接受。譬如,那时人们对自然的干预能力有限,在自然灾害和许多疾病面前束手无策,孕妇和儿童的死亡率很高,平均生命年限很低。人们生活在无常之中,但把这种无常作为无法改变的命运的组成部分。
然而,现代人却对不确定性越来越焦虑,越来越难以接受。这既是由于现代人再也不像古代人那样逆来顺受地接受不确定性,也是由于人类自身的活动增加了不确定性的广度和深度。这种变化首先与近代科学的发展有关。一方面,自然科学试图把世界都纳入必然的和可以说明的图景之中,使人们变得难以接受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快了自然和社会变化的进程,人类失去了稳定不变的本体性的家园或基石,因而其生存境遇变得越来越不安定。可见,现代人生存的不确定性焦虑是一种思维方式,甚至是一种生存在漂泊中的精神思乡病。
现代人对生存的不确定感表现为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但其内在的根源却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变化进程之中。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逐和货币拜物教激发了人们的无限欲望,因此现代性需要一种朝向未来的扩张,它使每个人都感觉到有一种流动性的成长。与静止状态的生存相比,“未来的名字是不确定性”。(莫兰,第64页)流动的生存状态和开放的未来可能性,更加突出了不确定性和人们的不确定感,因为变动的未来本质上就是不确定的。
首先,从观念上说,现代性从人对神的反抗开始,人以自己的主体性对抗命运的束缚,人们借助科学的力量开始尝试解释自然现象并且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比如,过去人们认为宇宙是上帝创造的,因而是按照完善的规则运转的。但到了18世纪,人们不再满意于这种说法。例如,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声明他并不需要这样的假说”(梅森,第275页),即在他的体系中已经没有上帝的位置。过去,人们把各种人生的无常都解释为上帝的安排,可是当“上帝死了”之后,人们虽然感受到了破除精神约束的自由感,但也失去了上帝“安排人生”的心理慰藉,尽管这种慰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无奈。
其次,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被割断,人与乡土之间的纽带被削弱,人们的家庭血缘被社会的流动性所稀释,家庭成员不再聚集在一起生活,人口的流动可能使人们深陷“失根”的危机。(汪仲启)全球化时代流动的现代性迫使人们寻找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安全本体基础。可是,文化家园不再是稳定的,不再是可以随时回去寻找和重新体验的地方——不仅家园在不断变动,家庭也变得不稳定了,离婚越来越成为一种“正常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人生存的不确定感既是旧有世界秩序衰落的产物,也是对未来航向无法明确的忧虑。
再次,传统社会的文化变迁缓慢,风俗、习惯、道德规则和价值观的继承性强,而现代社会特别是都市化进程,使原来稳固的社会系统转变成为流动性社会,规则和习俗的继承性减弱,传统的约束和规范作用也弱化了。同质化的传统社会更多的是无意识地被动接受既有文化,而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则迫使人们必须适应不断的变化。无论什么人,“若要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接受社会的可变和开放的形式”。他们“不仅要在自己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中不拒绝变化,而且要积极地要求变化,主动地找出变化并将变化进行到底”。(波曼,第123页)可是,人们在变化中必须思考自己的文化归宿和价值观选择的根基:我们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了无意识接受的传统,精神和道德以什么为出发点呢?人们用什么为道德奠基?在宗教和哲学的意义上,没有了上帝,也没有了先验的绝对理性或形而上学理念,人们的精神文化根基又何在呢?
复次,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和组织力量强化了人们改变自然和社会的能力。如果说过去人们对自然的利用是顺应自然的规律和现成功能的话,那么从原子时代开始,人们已经可以通过技术来逼迫自然释放其所包含的各种潜能。这种对自然的逼迫性索取,既为人类生活带来许多便利和福祉,同时也带来许多的不确定性和潜在危险。广岛的核爆炸是一个明显的里程碑和分水岭:从此之后,即使为和平目的的技术开发也同样潜藏着偶然性事故的可能性,这种偶然事故可能把技术变成人们所说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的核灾难就是典型的警示。日本发生的“3·11”大地震以及地震引起的海啸,如果是在自然经济状况下,它只是自然灾害,可是在现代社会中,它就可能引发新的次生灾难。譬如,福岛第一核电站第1至4号核设施出现的严重故障,就先后引发了核泄露。在这种灾变中,对于福岛人或切尔诺贝利人来说,故乡还在那里,但故乡的面貌已经被彻底改变了;过去的乡愁病(nostalgia)现在被“乡痛病”(solastalgia)① 所取代。
最后,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任何角落的问题和信息都可能一股脑地摆到人们面前。在古代,人们生活在相对隔绝的环境中,仅对自己身边的不确定性有所感受,如“人有旦夕祸福”之类的焦虑;可是在当代,媒体把全世界的不确定性或各种灾难都带到人们眼前,这种量的聚集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不确定性感,不确定性的焦虑成为了公共性的。
二
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强化或深化了不确定性,但重建新的确定性还需要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不可能通过退回到过去解决问题。从最简单的石器开始,技术就是人类之所以是人类的标志,也是人类的宿命。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往往根源于技术的发展和提升。但是,对于技术的发展人们既梦寐以求,也感到恐惧。庄子曾经告诫人们:“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庄子·天地》)但问题是,“机事”或技术是无法摆脱的,也是不能摆脱的。庄子故事中拒绝机械的老翁,不也“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同上)吗?可见,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机械,而在于机械化的程度。我们不能因害怕有“机心”就回到过去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而只能通过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解决技术给我们带来的问题。也许新技术又会带来新的问题或新的不确定性,但是人类既然已经部分地摆脱了纯粹按照本能活着的动物性,那就必须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
技术仅代表着工具理性,因而我们还要给技术加上价值理性的引导。没有价值取向的技术是盲目的,但缺少工具理性的价值也是空洞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曾经发生卢德运动,即工人以破坏机器为手段反对工厂主的压迫和剥削。它的起因在于当时机器的大量使用威胁到了工人的饭碗。不过,工人因机器出现而地位下降并不是机器的罪过,而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机器本来是可以节省工人的体力付出而提升作为人的尊严的,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却成为劳动异化的动力之一。但即使如此,英国也没有退回到以往简单工具或技术的阶段,反而依靠技术革命迅速崛起,成为雄霸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实际上,技术发展了或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作为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社会关系也应该有相应的调整。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97页)科学必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动整个社会的变化。
技术发展了,社会分工就越来越细,社会结构也越来越复杂。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具有不确定性的。社会主义就是试图在承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的技术成果的基础上,消除其破坏性的不确定性,建立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社会主义不反对技术,而是反对没有价值观引导的技术应用。社会主义也不能彻底消除不确定性,因为“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不确定的领域”(沃勒斯坦,第22页),但社会主义应该消除破坏性的不确定性,而推进具有创造力的不确定性。这样,对于不确定性就有了价值的取向。对于这次因美国次贷危机而爆发的金融海啸,许多经济学家都是事后诸葛亮,鲜有学者或政要事前预见到。究其原因,除了问题复杂之外,经济学家们只相信数学模型工具而忽视或脱离社会现实,缺少合理的价值观的引导,也是重要原因;另外,他们也忘记了自己“在其中运作的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质”(《霍布斯鲍姆谈马克思的〈大纲〉诞生150年及其现实意义》,第11页)。正因为如此,在危机爆发后,马克思这个“幽灵”似乎又回来了。
三
显然,人类将永远面对不确定性:人类的认识水平无论怎样提高,都不可能彻底消除不确定性。有人说,“世界未来将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格卡伊、惠特曼,第14页),实际上未来永远是不确定的。但是,未来的不确定性不应该是让我们彻底绝望的理由,因为它实际上也给人类提供了无限探索的可能性:危机与机会共生,偶然性与可能性同在,不确定性与新的希望并存。
首先,不确定性虽然给人带来心理的不安与焦虑,但是它也给人带来新的可能性和新的选择。如果一切都是确定的,那么人生将变成难以忍受的“苦旅”。人们对重复工作感觉到难以忍受,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有了不确定性,才会为人的自我选择、自主安排乃至梦想留下空间。可以说,有了不确定性,才有可能性;有了可能性,才有自由;有了自由,人生才有尊严。
其次,不确定性还促使人们深思。如果一切都是确定的,人们的心智很快就会困顿且失去思考的动力。我们不欢迎灾害和风险,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无法消除不确定性,我们的思维必须包容不确定性。埃德加·莫兰指出,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处在黑夜和浓雾之中,没有人能够预言明天”,但是,“历史至少应该不仅帮助我们认识到人类命运的既被觉得有随机的特点,而且向我们启示未来的不确定性”。(莫兰,第146页)明天固然不可预见,但人们每天都试图计划明天,而且大多数计划也不同程度地实现了,那些不能实现的预见也会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下一步如何做。
再次,不确定性确实有可能给人类带来风险,但风险也迫使人们寻求防止危险出现的办法。莫兰指出:“进步肯定是可能的,但它是不确定的。”(莫兰,第63页)要获得进步,就需要解决现有的不确定性。譬如,这几年在我国或其他地方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就进一步促使我们认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与粗放的单纯发展相比,走科学发展、合理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只能是更加理智、更加富有智慧、更多科学和技术含量的发展。世界的复杂性就在于,总有不确定性的存在。而“伟大的思想家总是作出对复杂性的一个发现”,“必要的思想改革将产生一种关于背景和关于复杂性的思维方法。它将产生一种进行连接和迎战不确定性的思维方法”。(同上,第179页)这就是说,科学发展的思维方式必须是包容性的,它必将超越简单的机械和线性发展的思维方式,给不确定性留下空间,并且考虑如何随时应对不确定性。
最后,不确定性的存在也促使人们思考技术的价值之维。譬如,2011年3月20日的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安全核能的确存在,中国正率先发展钍技术》。文章指出:钍比铀更安全更清洁也更便宜,因为钍这种有银色光泽的金属,必须被中子击中之后才能推动裂变过程。因此,“光子束被切断的那一刻裂变就会停止”。尽管这种技术的前景仍然只在概念中,还远不是现实,但这毕竟是朝向正确价值方向的技术设想。实际上,早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物理学家就研究过钍燃料,它的“中子产额更高,裂变率也更高,燃料周期更长,而且没有同位素分离的额外费用”,还“可以燃烧掉旧反应堆里的钚和有毒废料”。可是,当时钍开发计划在美国被搁置,因为钍不能产生用于核武器的钚。(参见《英报关注中国发展钍反应堆技术》)由此可见,技术没有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是因为价值导向出了问题:有些人把研制核武器置于人类安全和福祉之上了。
总之,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存在,我们必须持历史的态度和发展的观点:既不能因技术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因噎废食,也不能对技术盲目乐观,而应该对技术加上价值观的引导,即技术必须以人为本,以人民的和谐幸福生活为目标,以人类的长久安全发展为旨归。作为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和政府,我们不能只关注资本、产值和利润,而更应关注人民的根本福祉。人类将永远面对不确定性,并且只能在不确定性中审慎地博弈;然而只有持合理价值观的博弈,才是合理与合乎需要的。
注释:
① “乡痛病”是澳大利亚哲学家格伦·阿尔布雷克特(Glenn Albrecht)创造的新词。英文维基百科解释说,它指一种由诸如采矿或气候变化等环境变化造成的精神上或生存性的痛苦。网上的定义是:由于家乡环境发生巨变而产生的痛苦和忧郁。不同于远离家乡的“乡愁”,“乡痛”是一种身在家乡而对以往眷恋的愁痛。2010年2月27日的澳大利亚《信使邮报》写道:“乡愁是对一地的思乡病,乡痛是对热土往昔的怀念。”(参见王其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