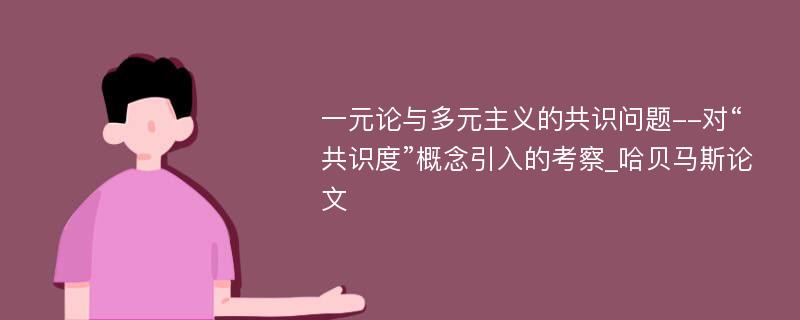
一元与多元之间的共识问题——引入“共识度”概念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识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3)11-0123-07
人类从自然中分化伊始,在丰富多样的社会生产、生活尤其是社会交往中,总是会面临着共识能否达成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说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如古希腊哲人倾向于相信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有一个共同、超验的本源,但是在充满着各种差异、分化和冲突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元,共识能否达成的难题越来越凸显出来(更何况即使是在古希腊,人们也仍然面临着“存在难以被言说”的困境)。“与传统社会结构完全相反,现代社会结构的典型恰恰是‘异质性’和‘分化性’。”①在异质性和分化性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在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可能产生分歧甚至冲突。当然,如果只是私人交往过程中的分歧或者争端,悬置争议、一方妥协都是可供选择的处理方式,没有必要一定求得共识,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没有一定程度的共识,社会生活、社会交往都将面临着诸多障碍。本文拟引入“共识度”这一概念来表征共识主体之间达成共识的程度,试图通过这一概念在一元与多元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诸多社会共识问题的研究寻找新的路径。
一、多元主义对一元主义的挑战
传统社会倾向于认为,虽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对于终极价值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但是,在民族内部、一定的地域范围之内,最终的真理具有相当程度的同质性和统一性。例如在古希腊,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都赞成当善或者恶的一些判断发生冲突时,它们能够按照所有具有理性的人们都能够接受的等级序列进行排序,这即是秉持一元主义的信念。
但随着现代社会的日趋多元,这种普遍性和确定性的基本观点遭遇到诸多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多元主义。在以赛亚·伯林提出价值多元论之后,大批学者加入到价值多元论的队伍中来,其中代表人物有伯纳德·威廉姆斯、斯图亚特·汉普舍尔、史蒂文·卢克斯、约瑟夫·拉兹、托马斯·内格尔、米切尔·斯多克、查尔斯·泰勒、马莎·努斯堡、查尔斯·拉莫、约翰·格雷、理查德·白拉米等等。这些价值多元论学者普遍认为,人类的价值是不可还原的多元和不可通约的,有时甚至会彼此冲突,没有理由把一种价值排在另一种价值之前。这种多元主义的观点无疑对传统社会的普遍确定性观点提出了挑战,人们开始对可以对不同价值进行排序并得到所有理性的人认可这一传统观念产生质疑。
同时,多元主义也不可避免地与西方世界主流的自由主义产生了交集。以约翰·格雷和约翰·凯克斯为代表的多元论者认为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存在着深刻冲突,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所蕴含的价值排序不过是众多可能中的一种,并不比其它的排序具有优先性或说服力。而另一些学者则试图将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如伯林在《自由四论》中,强调多元性及根本价值的不可通约性,而同时又试图将自由主义引入多元论中,因此提出了“消极”自由的普遍优先性。乔治·克劳德在《多元主义与价值多元论》开篇中明确指出该书“是在价值多元论的基础上对自由主义的一种辩护”。②威廉·盖尔斯顿在为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进行辩护的同时,论证了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的兼容性,从而完成了自由多元主义的综合命题。这三位学者虽然论证了价值的多元性,认为多元性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而不是需要克服的问题,但并未走向绝对的相对主义,正如盖尔斯敦所指出的,“尽管多元主义并不把社会和平与稳定看作是所有情形中占统治地位的善,但是仍承认这些善通常有助于构建一种能达致其它的善的框架”,③并且他指出多元论并不摒弃公民团结,而是对团结的要求和多样性的主张之间的关系作出独特的理解。对于多元性所面临的冲突如何解决的问题,伯林和盖尔斯敦采用了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主张在特定背景下作出实用的判断。
在自由多元主义者中,罗尔斯是在中国有着深远影响的学者。罗尔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在社会的稳定是否需要根本的政治原则和价值的统一,并且如果需要的话,在何种情况下达到多大程度的统一的问题上,并不存在着普遍的哲学的解答,但他更进了一步,结果与多元主义渐行渐远。他的观点在某些程度上与哈贝马斯不谋而合。他提出了重叠共识的理念,试图用全体公民所认可的“正义观念”来作为民主社会公民所能接受的政治统一和社会统一最合乎理性的基础。
但也有学者走向了彻底的多元论,例如威廉·康诺利(William E.Connolly)、波尼·霍尼格(Bonnie Honig)、克劳福·杨格(Crawford Young)、钱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尼古拉斯·雷斯彻(Nicholas Rescher)以及社群主义者桑德尔和麦尔金太等。他们对自由主义所持的所谓中立的态度表示质疑,强调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认为人类之善不能被还原为任何一种价值,这些价值之间经常是不相容甚至对立的,同时也是不可通约的。例如墨菲指出,“否定不可消除的对立,致力于普遍的理性共识——是对民主真正的威胁。的确,这会导致诉诸‘理性’背后所不被承认和隐藏的暴力,这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中是常见的。”④雷斯彻认为人们应该知道并接受这样的观点与事实:他人与自身在想法、价值、习俗及行为方式上都是不同的,因此在科学以及真理的理论中都没有必要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宽容、尊重甚至鼓励异见。对桑德尔和麦尔金太等社群主义者来说,任何人都是生活在社群之中的,社群决定着个人的属性,不同的社群具有不同价值观念,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共识只能在社群之内达成。
二、一元与多元之间的共识问题
尽管价值多元主义认为不同价值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并且反对对这些价值进行排序,但实际上多元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多元主义已经把价值多元作为最优的价值来看待了,这与它所主张的不同价值不存在优先性构成了内在的矛盾。另外,如果社会是绝对多元或者应该是绝对多元的话,那么如何建立社会和政治规范及制度?如何形成国家组织?这都是绝对多元主义所无法解释的难题。而另一方面,价值多元的事实又客观存在,传统社会追求确定性、统一性的一元主义理论已经遭遇到极大挑战,现实生活中难以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这也是为什么哈贝马斯设计了理想的交往情景,罗尔斯设计了“无知之幕”,试图通过假设一种理想前提来论证共识问题。
既然绝对的多元主义难以成立,而在差异化的社会中人们之间完全一致的共识也无法达到,那么如何在多元主义的社会中寻求一定程度的共识就成为许多学者关心的问题。事实上,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一些努力,试图寻求多元社会中的合理共识,如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娜·李斯特(List Christian)区分了两种共识:实体层面的共识(agreement at a substantive level)与元层面的共识(agreement at a meta-level),前者指两个及以上个体的偏好及观点相同,后者指两个及以上的个体在某一问题得以概念化的共同维度上达成一致。二者的关系在于,人们可能会在元层面上达成完美一致,但同时在实体层面对此维度最偏好的立场是什么的问题上却不一致。⑤并且他把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的理念归入实体层面共识概念的特殊情形。
澳大利亚学者约翰·戴泽克(John S.Dryzek)和赛蒙·尼迈亚(Simon Niemeyer)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对价值、信仰和偏好上的多元主义所能达到的元共识进行了论证。他们认为多元主义属于简单的层面,而共识则属于“元”层面。共识首先意味着对要做的事情的同意。但同时共识又指有助于解释某种偏好的价值和信念。据此,戴泽克和尼迈亚认为共识应该分为三类:(关于价值的)规范性共识、(对政策之影响的信念的)认知性共识和(关于应该如何行事的同意程度的)偏好共识。并且认为这三类共识都相应地对应着“元共识”的成分。如规范性元共识就存在于对某种价值合法性的认同上具有一致意见,但并未发展到在给定的多种价值中哪一个应该优先的问题上形成一致意见。⑥认知性元共识是指冲突性信念的可靠性以及定义手头问题的标准的相关性上所达成的一致。⑦偏好性元共识是由可选的冲突性选择的本质所达成的一致意见所组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涉及可接受的选择的范围,二是涉及可选的选择被组织起来的不同方式的有效性。⑧
按照克里斯蒂娜和戴泽克、尼迈亚的论述,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的共识是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的,沿此路线深入下去,我们可以引入“共识度”的概念,来说明多元社会中的共识问题。共识度,是指共识主体之间达成共识的程度,它表征共识在达成过程中的量的多少、幅度和范围等的规定性,体现出共识的“边界”特征。按照度本身的概念界定,共识度与其它度一样,在其范围内由无限多的量所构成,在全体一致与多元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共识度越高,越接近主体的一致同意;共识度越低,越接近多元。
一般说来,共识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共识度的可变性。共识具有历史性特征,任何时候都不存在超越历史条件和脱离社会发展的抽象的、永恒的共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同一问题的共识所表现出出来的共识度会发生变化,例如“妇女应该缠足”在一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共识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到现在已经不具共识。即使在共识度较高的自然科学中,例如“地球围绕太阳转”这一问题,地球中心论也一度成为所有人的共识,但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地心说的共识度逐渐下降,日心说的共识度逐渐上升,最终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第二,共识度的多样性。在社会生活不同层面上共识度是存在着差异的。从不同的群体层面看,按照社群主义的观点,共识只能存在于同一社群中,可见在具有同样的文化背景、利益诉求的群体内部,共识度是相对比较高的;而在社群外部,共识度比较低。从涉及共识的具体问题来看,对不同层面的问题也对应不同的共识度。例如,在人类的生态环境问题上,面对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共同的生态危机使得人们对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地球家园的共识度比较高;对于自我价值与自我成就层面,不同的个人既可以把追求真理作为个人的最高价值,也可以把美德作为自己的生命意义,很难达成共识,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也没有必要达成共识。而在同一问题的不同层面上,也涉及共识度的多样性。例如我和你都愿意投票给A候选人,但你投票是因为A能力强,我投票是因为A是我的亲戚,并且你直接给A投票,而我因为没资格直接投票需要说服他人给A投票。如此看来,在愿意给A投票这一点上我们的共识度达到100%,但在具体的手段和目的上共识度却几乎为零。
三、影响共识度的主体、客体及中介因素
影响共识度的因素很多,主体因素、中介因素以及所涉及的客体都会对共识度产生影响。影响共识度的主体、中介以及客体是相互缠绕、非常复杂的,最终的共识度是主体、中介以及客体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影响共识度的主体因素
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个人、群体、民族、国家等各主体领域内部之间都可能涉及共识问题。与传统的主体哲学中的主体概念不同,社会共识的主体是一种主体间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涉及的是通过某种中介,建立起解释、理解、评价、接受、认同直至共识的诸多主体,而不是一种单纯的主—客体关系中的主体,这与哈贝马斯所阐述的交往行为中的主体更加接近。在哈贝马斯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交往过程中并不是互为客体,而是互为主体,在主体间的互动过程中达成共识。所以共识主体之间就体现为一种相互理解、相互同意的关系。共识主体双方作为特殊的认识主体,在相互交流、交往过程中不仅体现出各自的主体性,并且相互承认对方的主体性,通过主体视角的转换达到“视域融合”。事实上,马克思的实践观也内含着此层意思,马克思指出,实践本身“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指出此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缺陷就在于“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⑨,从而强调了实践的交往性特征,这比哈贝马斯的理想设计也更具现实性。影响共识度的主体因素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主体的地位。哈贝马斯在其对话伦理学中,致力于寻找达致具有有效性规范的路径——主体间的交往行为。哈贝马斯认为,主体间的交往行为就是在自由平等人之间以语言为媒介、以共识达成为目的的理性交往。哈贝马斯非常强调参加对话的主体之间的平等性的关系,他所确定的理想言谈语境有三个特征:一是参与的主体是各种共同体,体现出主体间性,并且每一主体都是潜在的参与者,参与与否全凭自身真实的意愿;二是谈论的话题没有限制,原则上一切话题都可以谈论;三是主体之间的平等性,没有人拥有比他人更大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的理性共识度当然是比较高的。但是,这种理想的言谈语境毕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在现实生活中,主体地位的不平等、力量悬殊往往是常态。例如当今世界国与国的关系中,某些强国很难以平等的态度与弱国进行交往,往往更多地采用强制、制裁等方式来解决争端,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实现高共识度。
第二,主体的共识态度,也就是达成共识的自觉意识和:意愿。“人对于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社会活动的支配、调节和控制,都是通过人的自觉意识来实现的。”⑩主体之间达成共识的自觉意识是达成共识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在涉及分歧或争端时,主体双方要愿意倾听、理解对方,不仅陈述自己的见解,也认真倾听对方的意见,期待通过讨论来厘清并澄明问题。达成共识的意愿越高,一般情况下实现的共识度就越高。反之,如果主体以逆反、对抗的心态进行交往,则共识度就会比较低。
第三,主体的范围。在具有接近的价值观的某一社群或共同体内部,能达到的共识度往往较高;而在拥有不同价值观的社群或共同体之间,共识度则往往比较低。
第四,主体的能力特征,包括主体的认识能力和主体的交往能力。不同的个体主体,由于天赋及后天环境、教育因素的差异,在能力结构上有着质和量的差异,“在接收和采集客体有效信息的数量和种类方面,在理解客体信息的正确性和深刻性方面,在处理、传输客体信息的速度方面,在转换和再造信息的预见性和创造性等方面的差距,都是非常明显并为人们所熟知的”(11)。这种能力是主体认识客体的能力,对共识度会产生一定影响。另外,影响共识度的还有主体的交往能力。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共识是要依靠语言为基础的交往行为来达成的,因此,交往主体必须要具备选择陈述语句的能力、表达本人意向的能力和实施言语行为的能力。当然,哈贝马斯所说的共识更接近于理解,然而理解并不必然促成共识,如果只有理解而无接受则不可能达成共识,尤其在价值多元的条件下,理想的理性对话并不必然达致理性共识。因此,主体的交往能力不仅包括语言能力,还包括但不限于胡塞尔所说的“统觉”、“同感”、“移情”等能力。
(二)影响共识度的客体因素
从共识所涉及的范畴来看,我们可以大致将共识分为社会共识、文化共识和政治共识。社会共识主要是指共识主体对某种社会现象的共识,比如同性恋存在的合法性、保护生态环境的急迫性等;文化共识主要是指共识主体对不同民族、宗教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文化要素的共识;政治共识主要是指共识主体对政治理念、政治派别、政治观点的共识。当然,由于人们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几种类别是相互缠绕、相互影响的,在很多时候难以截然分开。
从社会共识来看,由于社会生活丰富驳杂,相应的社会共识度也很难估算和测量,共识度的差异往往较大。例如,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的结果,有64.4%的人认为应该优先保护环境,说明保护环境的共识度是比较高的;而对努力工作能够有着更好生活的问题上,问卷设计了1-10分(1代表努力工作能够带来更好的生活,10代表努力工作并不必然带来成功),其百分比分别是26.4%,19.3%,15.6%,6.4%,7.4%,6.3%,4.8%,6.4%,4.0%,3.5%,(12)结果表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更趋向多元,共识度较低。从文化共识来看,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涉及一些核心的价值理念的共识度往往比较高,例如,在中国,关于家庭在生活当中的重要性,世界价值观调查中98.1%的受访对象认为家庭非常重要或相当重要,(13)这表明在家庭观念比较重的中国社会中,家庭的重要性的共识度是非常高的。从政治共识来看,在民族国家内部,比较而言,对根本的政治制度共识度往往比对具体的政治体制要高。
(三)影响共识度的中介因素
共识的达成还离不开一定的手段或工具,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共识之达成有三种手段:权力、货币和交往。但他认为,前两者是工具理性,产生的结果是策略行为,也就是“协调效果取决于行为者通过非言语行为对行为语境以及行为者之间所施加的影响”,策略行动并不试图与他人建立起对世界的一致理解,而是采取“奖励、威胁、诱导或误导”的方式,这样所带来的一切并不是共识。(14)只有通过理性交往达成的共识才是真正的理性共识,也就是要通过主体间的交往行为,这种交往行为的主体是自由平等的,达成共识的媒介是通过言语行为,而言语行为要遵守真实性、正当性以及真诚性三种有效性要求。但是,在价值多元的条件下,通过理想的理性对话有时仍然不能达到理性共识。对于某些不可调和、或者说调和空间很小的冲突(如根本的利益冲突,对动物权利、安乐死、流产的看法等),很难通过对话来实现共识,哈贝马斯对此提出了通过谈判的手段,如投票、多数人法则作为合法解决争议的方式,但如果采取这种方式,就很难说能继续“交往行动”而不陷入“策略性行动”,并且即使最后的结果被各方视为合法,但与其称之为“理性共识”还不如称其为“理性非共识”。甚至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在公共讨论、理性对话之前,人们可能对自己的需求并不明确,但在讨论过程中,往往更了解自身想要的,从而在普遍价值与根本利益上不仅不能达成共识,反而使冲突更加尖锐化。当然,对此哈贝马斯也提出了他的解决之道,那就是更大的抽象化,例如“从不同的偏好到选择的自由,从对立的信仰到良知的释放,从冲突的价值到隐私的权利”(15)(在这方面哈贝马斯也更接近于罗尔斯),但这种更大的抽象化在实际的充满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差异的公共空间中如何帮助实现理性的共识,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也就是说,尽管哈贝马斯用以言语行为为中介的交往理性为共识达成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路径,并且如果按哈贝马斯所设计的方式,会形成较高的共识度,但在实际生活中,更多的时候,理想的理性交往是无法实现的,要达成共识,权力与货币等其它方式往往也不失为一个选择。以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为例,1918年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其国家制度没有形成较高的共识度,政治竞争和价值观竞争不受节制,最终导致多元社会的颠覆和国家的解体。由此可见,较高的社会共识度对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这往往难以通过理性的交往行为达成共识,只能通过强制或意识形态的建构式灌输,来提高全体社会成员对基本政治制度的共识度。再如,诸如城市行道树的选取品种这类涉及较多专业知识的公共事务,通过投票之类的方式很难达成比较理性的结果,而诉诸专家的意见更为恰当,因此通过说服的方式来提高共识度就显得更为可行。而涉及个人之间的私人事务,共识达成的方式则更为灵活,如两个朋友聚会,一个想去看电影,一个想去咖啡厅,如何解决分歧?完全可以一方强制,另一方妥协,或者万一不能达到最后的意见一致,则搁置争议,取消聚会,各回各家,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四、结语
虽然我们引入共识度这一概念来分析共识问题,但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共识度越高越好。一个无限多元,没有底线共识的社会,必将成为一盘散沙;同样,一个处处追求百分之百共识的社会则必定是一个令人窒息的社会。真正和谐、健康的社会应该在两极之间求得一个平衡。正如凯尔纳与贝斯特所说,“在某些情况下,形成歧见、挑战霸权观点、维护差异乃是最好的选择,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有必要去达成共识,以便促进某种政治或伦理目标的实现。”(16)对正在进行现代化转型的中国社会来说,在哪些层面应该求得高共识度?哪些层面应该更追求多元?高共识度对促进社会和谐、减少社会冲突是否具有积极的影响?限于篇幅,这些问题未在本文中分析,但是可作为今后共识度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贺来:《道德共识与现代社会的命运》,《哲学研究》,2011年第5期。
②乔治·克劳德:《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③Galston:William A.Liberal Pluralism:The Implications of Value Pluralism for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65.
④Moffe,Chantal:"Democracy,Power and 'The Political.'" In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Contest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Political.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248.
⑤List,Christian:Two Concepts of Agreement,The Good Society,2002 Vol.01.
⑥⑦⑧John S.Dryzek,Simon Niemeyer:Reconciling Pluralism and Consensus as Political Ideal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6 Vol.03.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页。
⑩欧阳康:《社会认识论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1期。
(11)欧阳康《论主体能力》,《哲学研究》,1985年第7期。
(12)(13)World Valuse Survey 1981-2008 Official Aggregate v.20090901,2009.World Values Survey Association(www.worldvaluessurvey.org).Aggregate File Producer:ASEP/JDS,Madrid.
(14)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15)Tomas McCathy.Kantian Constructivism and Reconstructivism:Rawls and Habermas in Dialogue.Ethics,Vol.105,No.1(Oct.,1994).
(16)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局,1999年,第3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