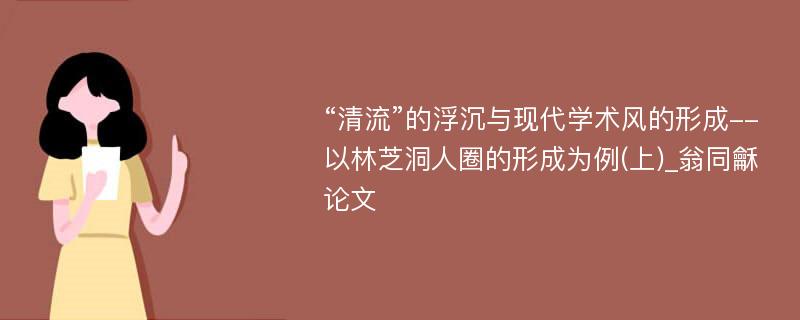
“清流”浮沉與近代學風——以張之洞學人圈的形成爲例(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流论文,近代论文,洞學人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謂“清流”,是古已有之的對清議集團的稱呼,以朝臣(尤其是言官)犯顏直諫爲標誌,却也包含了東漢黨錮、宋代太學生、明末東林黨等泛化的士大夫言論勢力。廣義上的“清議”以太學、翰林院、書院等公私文教機構作爲聯絡場所,往往依托講學、會課、社集等活動溝通聲氣,因而與學術風氣變遷有著天然聯繫。清代懲前明黨争之弊,厲禁結黨言事,朝中言路亦受壓抑。但至道咸以降,不僅朝政日益窳敗,內政外交的新狀况更是層出不窮;加之太平天國之亂後朝廷權威跌落、漢臣督撫崛起,中樞感到有必要利用言路牽制疆臣,藉此營造再圖振作的“中興”氛圍,遂使沉寂二百餘年的言路得到復興。
清季張之洞久任封疆,幕府人才稱盛,随著政治、學術重心由京師向東南督幕的再度轉移,逐漸在其周圍形成了一個以同光之際“清流”士人爲核心的學人圈子。張之洞一派在體制內的文教建樹,更注重學風、學制、文體等對士林社會有普遍影響的因素,其學術思想不具備趨新知識人的專業精神或超前意識,却能依靠“居高明之地”的順勢,集聚人才,蒸成風俗,使新知識、新經驗得以在一番折衷妥協之後向士林社會推廣。本文擬從“清流”浮沉與晚近學風轉移關係的角度,考察晚清張之洞系統對“清流”勢力的同情與援引,藉以揭示近代學術與政治互爲表裹之一側面。
一、另一種中興
外任督撫二十餘年後,光緒三十三年(1907),張之洞重返京師,以軍機大臣管理學部。筆記家言,某日學部尚書榮慶宴請張氏,言及顧、黄、王三儒業已從祀孔廟,外間復有曾國藩從祀之請,不意張之洞當即作色曰:“曾國藩亦將入文廟乎?吾以爲將從祀武廟……天津教案,曾國藩至戮十六人以悅法人,是時德兵已入巴黎,曾國藩尚如此,豈非須祀武廟乎?”此則材料真實與否有待考辨,卻頗能描畫同光清流一代對于道咸軍功一代的自詡:除了洞察形勢的後見之明,更重要的,乃是“文”對“武”、“儒臣”對“大臣”的心理優勢。①
實則張之洞本人亦出身軍功之家。其父于道咸之際知貴州興義府,太平天國亂中辦理團練、轉戰西南,與中興名臣胡林翼、呂賢基、韓超等交游。故張之洞幼年的師承,頗帶有曾、胡一派經世之學的氣味。②然而,功名早達加上族兄張之萬在朝中的人脉,卻讓張之洞從十六歲起就得以從西南兵間脫身,領略到都下學術的別樣境界。
時值咸豐亂世,當曾、胡輩在長江上下用兵火鍛造“中興”之時,另一種學風上的蛻變也開始在京師醞釀。長年居京,熟于中朝掌故,且日後一度成爲張之洞幕僚的沈曾植,就曾從科場風氣變化的角度,追溯這一潮流的興起:
道光之季,文場戾契,頗有幽歧,其還往常集于津要之塗,巧宦專之。而公卿大夫方直者、舉子謹厚步趨守繩墨者、士以學問自負者,恒聞風而逆加檳棄。其名士而擅議論者,尤干時忌,張石洲(穆)、張亨甫(際亮)之流,困躓當時,士林所共記也……蓋自咸豐戊午以後,茲風乃殄,而後單門孤進,遗經獨抱者,始得稍沾稽古之榮。至于同、光之際,二三場重于頭場,則吳縣(潘祖蔭)、常熟(翁同龢)、南皮(張之洞)、順德(李文田)迭主文衡,重經史之學,幾復反乾、嘉之舊。③
道咸時代都下士人交游頗盛,或講求理學、經濟,或鑽研邊疆史地,或以詩古文相砥礪,卻限于少數精英學者的圈子。④其時官場、科場晦澀依舊,被稱爲“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世界”。⑤咸豐八年(1858)戊午,柏葰科場案發,大獄構興,纔使“北闈積習爲之一變”。⑥同年六、七月間,潘祖蔭、翁同龢出任陝甘鄉試正、副考官,旋即外放學政,交卸後主持都下風雅數十年。到同治年間,張之洞、李文田等又相繼外放。諸人在主試時,貶首場時文,重視二、三場之經文及經史時務策,流風所及,幾乎有重返乾嘉學術盛世之勢。沈曾植本人即爲此種科場新風尚的受益者,故數十年後猶津津樂道之。
翁同龢、潘祖蔭以及小一輩的沈曾植等人,均出自京官世家,不僅官場人脉深厚,對數十年來的學風消息,亦瞭然于心。張之洞、李文田則生長邊陲,得以預同光學術之流,除了自身的文采、學養,更有賴于科場因緣。張之洞早年便與常熟翁氏關係密切,翁同書爲其受業師,同書弟同龢、子曾源則爲其鄉試同年。同治元年(1862)張之洞入都會試,早第的翁同龢已升任同考官,見場中一卷文字“二場沈博艷麗,三場繁稱博引,其文真史漢之遺”,便“决爲張香濤”,繼而知其不第,又爲之扼腕。⑦同治二、三年間(1863-1864),翁同書被劾下獄,張之洞曾往探看,並賦詩送其父子出戍新疆。⑧通過結交都下顯宦,代撰章奏,張之洞在京城的“時名”雀起⑨,儘管有同治四年(1865)詹翰大考僅列二等第三十二名的挫折,仍然在兩年後考差時,從擁擠的翰林班中脫穎而出,被派充浙江鄉試副考官,旋又簡放湖北學政。
晚清曾國藩、李鴻章幕下的士人圈子,確立于湘、淮軍征戰的年代,多以地緣或血緣關係爲纽帶。後起的張之洞學人圈,則更看重“門第”、“科甲”、“名士”的出身⑩,起碼在其前期,仍以張氏在京城的交游,以及其前後三次主試、視學建立起來的師生情誼爲基礎。同治六年(1867)在浙江,張之洞多拔取樸學之士,內如袁昶、許景澄、陶模、孫詒讓、譚廷獻、沈善登、沈熔經等人,都與日後學人圈或幕府的建立有直接間接的關聯。至視學湖北時,又與李鴻章相商,仿照蘇州正誼書院課經古例,創立經心書院,專課古學。(11)張之洞汲汲求才的態度,頗有乾嘉老輩遺風,亦得到曾國藩等疆臣褒獎。(12)
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發生,曾國藩“革府縣以謝洋人”的解决方式引起士林非議,以曾氏爲楷模的中興事業漸趨暗淡。與此同時,受益于戡定大亂後的承平氣氛,都下學人的交游與清議卻日益繁盛起來。是年十月,張之洞回京復命,寓南橫街,與位于米市胡同的藤陰書屋相鄰。藤陰書屋是潘祖蔭的書齋,更是彼時京中金石學者的聚會之所。張之洞遂藉此結交潘祖蔭、王懿榮、吳大澂、陳喬森一流金石學者,並與王、吳諸人一道爲潘祖蔭編訂《攀古樓款識》。(13)次年春,春闈甫畢,張之洞投書潘祖蔭,以爲“目前四方勝流尚集都下,今番來者頗盛,似不可無一雅集”,擬以翁、潘爲主,邀集新進學人,款洽一日。最後則改由潘祖蔭、張之洞二人主持,于當年五月初一日在龍樹寺宴集。(14)事後張之洞致信潘祖蔭,羅列當日到者十七人、約而不赴六人、欲約而不及者五人的名單,並依次注明各人所擅長的領域,涵蓋了經學、史學、小學、金石、輿地、書畫、古文、駢文等諸多方面。(15)通過此次雅集,年輩靠後的張之洞獲得了與翁、潘不相上下的組織詩酒文會的資格。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國藩薨于江寧督署,這一年京城士人的交游唱和卻臻于極盛。七月間,李慈銘致信友人,提及:“今春都下,文讌讜頗盛,消寒之後,繼以春游,或排日以看花,或選寺而鬥酒,尋極樂之柰樹,訪花之之海棠,觴咏偶停,策蹇亦出,量松報國,則朱育相從;品藥天寧,則許詢共坐。悵牡丹于崇效,玩丁香于憫忠。雖杖頭或虛,而清談不廢……”(16)但若論與學風轉移的關係,恐怕還當推這一年夏秋間潘祖蔭發起的三次集會:先是在三月前後,吳大澂爲潘祖蔭繪《藤陰書屋勘書圖》(一說秦炳文繪),張之洞、董文焕、陳喬森、李慈銘及滿洲藏書家錫縝各有題咏,多就潘氏隸籍吳縣發想,叙述三吳學脉流入京師的過程。(17)繼而五月中又有“消夏六咏”之唱和,分題拓銘、讀碑、品泉(錢)、論印、還硯、檢書,先後參與者有張之洞、王懿榮、嚴玉森、李慈銘、胡澍、陳喬森六人。至七月初五日,潘祖蔭組織鄭康成生日置酒展拜會,參加者除以上六人外,又增加陳彝、謝維藩、許賡揚、吳大澂、顧肇熙五名。(18)三次雅集的主題,明白宣示了同治末年京師士人的生活趣味與學術宗尚。
同光間,都下的學人唱和,往往在稱頌京師承平盛事的同時,流露對東南文化遭受戰亂破壞的惋惜,或慨嘆“大盗毁江左,書種奄欲絕,天一既雨散,士禮久烟減”(19),或追述“當年劫火天四圍,法物飄零愁慘淒,去年江上屢來往,文采亦遜乾嘉時”。(20)事實上,正是東南書種在劫火中的絕減,反襯了京師學術存亡續絕的意義;也正是戡平大難後的“中興”氛圍,使考訂之學的回潮得免于無用之譏。同光之際的京師學術,作爲“厭亂”心態在文化上的表現,基本上是以“中興”乾嘉考據學爲職志,相較于經世思潮涌動的道咸學術,反而有將學問進一步趣味化、專門化的趨向。其間風氣的因革與擴散,恰如震鈞在《天咫偶聞》中總結的:
方光緒初元,京師士大夫以文史、書畫、金石、古器相尚,競揚榷翁大興、阮儀徵之餘緒。當時以潘文勤公(祖蔭)、翁常熟(同龢)爲一代龍門,而以盛(昱)、王(懿榮)二君爲之厨、顧。四方豪俊,上計春明,無不首詣之。即京師人士談藐,下逮賈竖平準,亦無不以諸君爲歸宿。廠肆所售金石、書畫、古銅、瓷玉、古錢、古陶器,下至零星磚甓,無不騰價蜚聲。而士夫學業,亦不出考據、賞鑒二家外。未幾,盛司成有太學重刊石鼓文之舉;未幾,王司成有重開四庫館之請,蓋駸駸乎承平盛事矣。(21)
此段文字涉及乾嘉以降京師學術的傳承脉絡,卻未提及道咸時期張穆、沈矗、吳廷棟、梅曾亮、曾國藩諸公提倡的經世學風,連主張考訂之學的祁寯藻、程恩澤等人都忽略不計。按照震鈞的叙述,同光學術以翁同龢、潘祖蔭二人爲領袖,直接乾嘉時代翁方綱、阮元一脉的考據、鑒賞之學,下啓光緒年間盛昱、王懿榮等新進學人,逐漸形成彌漫京師各階層的談藝風氣,並以琉璃廠書畫、古玩交易的繁盛爲其表徵。光緒二年(1876)繆荃孫進京,所見琉璃廠朱履雜沓的景象,正可旁證彼時京城學人圈的層級:“舊友日日來廠者,朱子清(澂,朱學勤長子)、孫銓伯(鳳鈞)、黄再同(國瑾)、沈子培(曾植)、子封(曾桐)、徐梧生(坊);若盛伯希(昱)、王廉生(懿榮),間或一至,來則高車駟馬,未及門而已知。至潘、翁諸老,則專候廠友之自送,罕見莅肆。”(22)足見盛昱、王懿榮二人在光緒初年承上啓下的顯赫地位。
光緒前期的京師學界有兩件盛事:光緒十年(1884)七月,盛昱補授國子監祭酒,訪問南學廢壞荒墮之狀况,一舉而清除之;又從乙酉拔貢中補録諸生,“加膏火,定積分、日程,懲荒墮,獎勤樸”,命諸生分輯《通假彙編》,專取清朝經師成說,依照今韵排類,得二十餘册,並撰校專門著作多種,繼而率領諸生校改石經、重刻石鼓,都人詫爲盛事。(23)至光緒十五年(1889),王懿榮上奏請續修《四庫全書》,並請將清代儒臣所撰十三經疏義頒布學宮,引起言官與學官之間的激烈辯論。(24)此前潘祖蔭弟子汪嗚鑾重申許慎從祀之請(25),翁同龢又領銜奏請黄宗羲、顧炎武從祀。(26)盛、王二人致力于在官學系統中引進“國朝經師”的傳統,正與翁、潘老輩提倡許鄭之學、擴充儒學學統的努力一脉相承。
更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翩連而來的學人交游,助長了學術合作與專門研究的風尚。如果說潘祖蔭《攀古樓款識》的成書,仍帶有前代公卿招募學者從事編纂的遺風;那麽像王懿榮之最録《南北朝存石目》,題記中羅列前後十九年中“探索借讀往返商榷者”、“考訂違合剔抉幽隱”者、“亦嘗有事于此”者共十六人,則大多爲同僚朋好之間的平等研討。(27)彼時京師學人之間,藉助南城居住密邇之便,就共同關心的專題,業已形成一種相與討論、互資鏡鑒的學術空間。又如王懿榮家訓飭子女:“于所嬉戲玩物,雖瑣屑不使毁棄暴殄;內室所蓄書畫、碑帖、墨本等物,盛夏時必手自抖曬,防蠹鼠極力,歲以爲常。兒女雖幼稚無知識,于文物戒不敢近也。”亦暗示從“玩物”到“文物”的觀念變化。王懿榮在亡妻黄宜人行狀中提到,自己“好聚舊椠本書、古彝器、碑版、圖畫之屬,散署後必閱市,時有所見,歸相對語,宜人則曰:‘明珠白璧,异日有力時皆可立致之,惟此種物事往往如曇花一現,撒手便去,移時不可復得,後來縱或有奇遇,未必即此類中之此種也。’好極力從臾,購之以爲快,以故裘葛釵釧往來質庫,有如厨笥”云云,在《金石録後序》慨嘆長物易失的言說傳統之外,展現了漢學門第以得長物爲快的觀念。(28)
張之洞與盛、王二人交誼甚深。光緒二年(1876)冬,更在四川學政任上迎娶了王懿榮之妹,在共同的學術好尚之上叠加了姻親關係。後來張之洞外放疆臣,王懿榮在十數年間充當了張氏與京師學界聯繫的紐带。公文旁午之餘,張之洞也會致信王懿榮,詢問京城學界的新動向。(29)然而,同光之際的京師交游,不僅孕育了專門之學與金石之詩,更從中滋長出一股清議的意氣,盛昱、王懿榮均捲入其中,震鈞將二人喻爲東漢黨錮之“厨、顧”,誠爲恰當。(30)至于張之洞,則更善于呼吸領會時代風向,早在盛、王等人流連廠肆之時,便已從京城考據家隊中淡出了身影。
二、作爲門面的“清流”
“不須遠溯乾嘉盛,說著同光已惘然”。(31)同光之交都下的詩酒風流,爲此後數十年間學者、詩人追懷前朝往事提供了素材,後來人抱歷史的同情,更推之爲乾嘉盛事之回復。然而,詩酒生涯的經濟成本,及其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亦不容忽視。同治年間,由于軍功勢力在地方崛起,京官出路日益狹窄,淪爲冷秩。(32)像張之洞、李文田、王懿榮那樣,能够憑藉一己才華攀援望族、補授優差者實占少數。(33)與之相對,長年的交游活動卻養成了整個京官群體對住宅、姬妾、輿馬、僕役、宴飲、歌郎、冶游、郊游、書畫古籍、金石拓片等各方面享受的追求,由此帶來中央機構腐化與京、外官勾結等問題,被認爲是光緒時期京朝政治窳敗的內因之一。(34)
清季游于京師的陳澹然,不僅“極厭考據及六朝人文”,並且平生“最詆翁叔平(同龢),次則張廣雅(之洞)”(35),其筆下的同光學術,通過伶人的視角展開,自是另一副景象:
同治初,髮、捻漸平,京師無事。諸貴人務歌頌,飾太平,宴樂益盛,海內諸奇伶争入都,至則盡屈(程)長庚,稱弟子。諸名士乃獨工楷法,習詞賦、時文攫高科,倨貴甚。上者乃或研訓詁,窮性理,盗古文詞相標榜,號曰“清流”。(36)
此處借用“清流”一詞指代同治年間京師的交游群體,籠括了訓詁、性理、古文辭三方面的士人。“清流”之“清”,不僅是“清議”,更指向京中“諸貴人”生活方式的“情閑”、“清祕”,屬于較爲廣義的用法。按照陳澹然的叙述,從同治到光緒四十餘年間的士林社會,經歷了“清流”、“敢諫”、“洋務”三個群體前後相繼的過程:同治十年(1871)倭仁去世,“性理絕,而訓詁、詞章益勝,厠翰林、坊局、御史臺,則務搜經史上自黄帝以來數千年治法,埋首習章奏,或乃劾權貴小者取直聲,號曰‘敢諫’”;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事起,“醇賢親王銳志建海軍,開津榆鐵道,諸名士始采報說人疏章,號曰‘洋務’”。在陳澹然看來,從“清流”到“洋務”,其底色均爲沉溺訓詁詞章、“喜狎優伶相爾汝”的所謂“名士”,故亦統稱爲廣義上的“清流”。(37)
不過,對于光宣以至民國年間筆記、野史、小說中頻繁出現的“清流”一詞,更爲普遍的用法,卻是指向陳澹然所說的“敢諫”。這種狹義用法最終進入了正史:
論曰:(黄)體芳、寶廷、(張)佩綸與張之洞,時稱“翰林四諫”,有大政事,必具疏論是非,與同時好言事者,又號“清流黨”。(38)
“清流黨”之稱,有“結黨”、“朋黨”、“黨錮”的含義,很可能出自攻擊“清流”者。(39)而與此同時,廣義的“清流”用法並未消失,如翁同龢、李文田、沈曾植等人,在言事方面無甚可觀,甚至成爲狹義上“清流”攻擊的對象,卻也被稱爲“清流”人物。于是出現“南北清流”(40)、“前後清流”(41)等說法,將“清流”與南北、京外、帝后矛盾相聯繫,恐怕也有調和廣、狹兩種“清流”理解的考慮。
《清史稿》對于“翰林四諫”的歸納不盡準確,但張之洞在光緒初年逐漸疏離于翁同龢、潘祖蔭的圈子,最終加入翰林言事一派,卻是事實。一方面,可能由于張之洞意識到自身專門知識不足,在以金石學爲極則的翁、潘圈子中,難以争取到中心地位,故退而以激烈言事來博取新的聲名。(42)另一方面,更應出于張之洞自身的學術選擇。早在與潘祖蔭等討論金石、之時,張氏就已流露對“許鄭之學”的質疑(43),同治十一年(1872)題咏《藤陰書屋勘書圖》,更將自家的治學取向表白無遺:
……我如邢劭不精詳,懶捉禿管施雌黄。窺日觀月各自快,未知南北誰短長。(44)
張之洞作詩長于用典,此處先用《北史》邢劭笑人校書事自嘲(45),繼而化用《世說新語·文學》支道林語:“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觀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46)雖强調南北精、博之間,各有勝處,未較短長,但言下之意,顯然更取“學寡而易核,易核而智明”的南人清通之學。(47)同、光之交,張之洞外放四川學政,拔取楊銳、王秉恩、廖平、宋育仁、吳謙、吳德潚等超卓幹練之士,並組織編輯《書目答問》及《輶軒語》。前者尚可視作京師論學之緒餘,後者則面向士林社會中下層的諸生,二書均以實用爲準的。光緒三年(1877),張之洞入都復命,是年廷議穆宗升祔位次,乃詳稽三代之制,爲潘祖蔭代撰三議以進。陳寶琛在日後提到,張之洞“自是究心時政,不復措意于考訂之學”。(48)
據說張之洞在光緒初年“頗講理學,學術又一變”;(49)其集中致潘祖蔭最後數函,大概也作于此間,有云:“今日必無党禍,何也?有清議然後有黨禍,今也不然,毁譽雜糅,出主入奴而已;清流勢太甚,然後有黨禍,今也不然,偶有補救,互相角力而已。”按此信語氣,似乎自居清議、清流之外,但反復辨別“無黨禍”,又暗示潘祖蔭確有提到張之洞與清流、清議結“黨”的言論。(50)其時與張之洞交游,且以理學、清議著稱者,包括張佩綸、吳可讀、吳觀禮及閩籍的陳寶琛、王仁堪、仁東兄弟等人,活動範圍大概在南城丞相胡同、北半截胡同一帶,與以米市胡同藤陰書屋爲中心的金石學人圈僅一街之隔。諸人不長于考訂,而愛好吟詩、扶乩:“臨乩者自稱净名道人,蓋康乾間詩人吳舍人泰來(原注:企晋)也。每臨乩,輒與同人唱和,不爲休咎之占,而作韋弦之贈,唱酬甚夥。”(51)光緒三年張之洞回京後,與諸人接觸增多,其人清議一“黨”,或在此前後。而光緒四年(1878)以後張佩綸的日記中,時而能見到鑒賞金石的聚會,可知當時都中士人圈子並非界限分明,張之洞游走于二者之間,溝通了不同圈子的風氣。(52)
有清一代,懲明季言論混淆之失,又挾其异族入主的戒心,前中期二百年間言路相當沉悶。時至晚清,在內外變局的壓力下,破例之舉層出不窮,清議勢力興起,同樣突破了“以言爲忌”的祖宗家法。然而,清流中人不斷突破祖制,試探言論限度,卻又是爲了堅守其他各項祖制不受破壞。光緒五年(1879)三月,吳可讀以震駭一時的“尸諫”,要求爲穆宗預定大統,即是針對慈禧太后在繼位問題上的“破例”。“尸諫”之舉極具表演性,吳可讀事先準備好了棺椁、衣冠,並遺書示子,命其速速出京之先,須在“張香濤(之洞)先生、幼樵(張佩綸)、安圃(張人駿)前均致候”,慨嘆“想如前時聚談時,不可得矣”。張之洞此時已成爲吳可讀等清議人物的密友,被托以身後之事。(53)更重要的在于,吳可讀用“尸諫”挑戰了清代宫廷政治最爲敏感的立儲話題,也在最大限度上拉伸了晚清朝臣的言論空間,光緒初年喧赫一時的“翰林四諫”遂接踵而起。
北宋慶曆年間,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四人任諫官,號稱“四諫”。(54)至明成化時,又有“翰林四諫”之謂,指因言事而被黜之翰林院編修羅倫、庶吉士章懋、黄仲昭、莊昶四人。(55)至于晚清的“翰林四諫”,則异說頗多,張佩綸、陳寶琛、黄體芳、何金壽、寶廷、張之洞、鄧承修等都曾被納入。但張之洞、陳寶琛詩句中提到“四諫”,又皆自居其外。陳寶琛詩注且指出“文襄(張之洞)尚未在講職”,不入“四諫”。(56)然則比之宋代“四諫”之全爲諫官,明代“翰林四諫”之僅爲編修、庶吉士,晚清“翰林四諫”的門檻更高,要求必須是經過詹事府遷轉而晋升“講職”者,故其時張之洞與張佩綸私下有“言官不言、講官盡講”之戲目。(57)經過光緒五、六年(1879-1880)間針對崇厚訂約之彈劾,張之洞迅速開坊晋升日講起居注官、侍講學士,正式加入翰林講官主導言路的潮流。
“言官不言,講官盡講”,造成光緒初年清議有別于前代的若干特點:首先,清議產生于翰林講官“清祕無事”的詩酒生涯,繼承了同光之際都下學人的生活方式。張之洞、張佩綸等在言事之餘,仍以金石、書畫、版本、西北地理之學自娛,並將其與議政相結合,向經世的一面發揮,實可看作同治以來京師學術的擴張;與此同時,翁、潘一派主導的學術圈子依舊活躍,中如吳大澂、盛昱、王懿榮等人,亦是重要的清議分子。其次,相對于光緒中期以後“以駡洋務爲清流”的言官末流(58),翰林講官品級較高,大多視野開闊,究心時務,既有與地方督撫及總理衙門進行直接交流的資格,也具備相關學養。如張佩綸與合肥李氏本爲世交(59),在京師鼓吹清議的同時,便已參畫李鴻章在天津的洋務事業,往來書信頗多;又如陳寶琛在中法戰争前“提倡清流”,“于洋務極意研究,曾借譯署歷年檔案”,囑人抄寫。(60)當時盡有“洋務”、“軍功”中人對“清流”的不滿乃至非笑,但清流隊中卻不無依附、藉重洋務的心態,張佩綸甚至在書信中奉承李鴻章爲“清流争附”、“愛護清流”之人。(61)甲申(1884)年由盛昱一疏導致“易樞”事件,圍繞主戰、主和話題,李鴻章、醇親王對朝中清議多有不滿,而張佩綸此時的辯白則更值得玩味:
言論主戰者多,轉于和局有益,願朝廷不以异議爲嫌。(原注:今日又言之興獻:作清流須清到底,猶公之談洋務,各有門面也,一笑。)(62)
翰林清流不僅堅守理學原則,更好講究縱橫捭闔之術,中法戰争時,便曾希望通過和、戰兩派默契配合形成有利的外交態勢。“清流”、“洋務”,在張佩綸看來不過是對外的門面語,而非政治歸屬或學術取向的實質。故張佩綸的“清流”身份,並不妨礙其參與“濁流”李鴻章的幕府;張之洞也能以翰林清祕之官,成爲總理衙門備諮詢的座上客。但另一方面,所謂“門面”又代表著群體發言的立場,必須貫徹到底,不能動搖,不容异類。翰林言事者身處京師士人交游的環境中,其上疏程序亦有如詩酒酬唱,通常由一人出奏,諸人附和,從而给外人造成翰林數人此唱彼和、迹涉朋比的印象。“壬午(1882)以後,言事者尚激切”,(63)奏章之間的前後唱和將言論不斷推向極端,卻未必符合各自治學、處世的本來主張。
當時爲此種“章奏唱和”最爲頻繁者,端推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寶廷四人的小圈子。四人皆投靠提倡理學的李鴻藻門下,與翁、潘漢學一派言事者有對峙之勢。平日書信往來,多用暗語,嗤點朝臣,無所不至。其中張之洞、寶廷稍爲沉穩,張佩綸、陳寶琛則尤主激越。光緒六年(1890)張之洞致信張佩綸云:
橘洲(陳寶琛)詩昨日弟與偶齋(寶廷)争之,至暮不能得。偶齋但懇其停留熟思一日再繕,及今晨竟交卷矣。執事(張佩綸)與橘洲同床各夢,昨日之贊成,實爲鄙人意料所不及。他日設聞扶病閱卷者淒然不怡(眉批:扶病閱卷者謂皇太后),朝減一飯,公必然悔之。自恨愚誠有限,不足以動清聽,惟有愧歉而已。公瑕有勇無謀,奈何奈何。(原注:橘洲亦無他,不過名心耳。)(64)
此札看似論詩,實則議政。當年十二月,東右門護軍毆打太監,觸怒太后,將置重典,張之洞、陳寶琛二人遂交章上奏請裁抑宦寺。陳寶琛附片措辭激烈,遭到張之洞反對,卻仍在張佩綸鼓勵下貿然上奏,一摺一片轟動一時,被稱爲“真奏疏”。(65)其時諸人不僅在一起討論奏疏,且有結課讀史傳,共同編輯《皇朝經世文續編》的打算,張之洞另有一信致張佩綸云:
昨夜思之,若欲有所撰述,他體裁皆不宜,擬爲《皇朝經世文續編》,止須搜羅五十年來奏疏吏牘,並近日名家文集,選擇録之。此體有畔岸,而無偏倚,得尺則尺,漸次推廣,可以求日進之功。惟奏牘須求諸樞曹、史館、內閣、部署,及積年邸赧,亦不易耳。求之難而編之易,多雇鈔胥足矣。然此體有今無古,若以古今通爲一書,思之未得其方,望閣下與伯潜(陳寶琛)見,商度見教爲幸。(66)
當時令清流中人感到煩惱的,乃是“考古”、“讀書”與“經世”之間的關係。張佩綸希望能通過“考古”來尋求解决畿輔水利、厘金、東三省等現實問題,張之洞復信則指出此等皆“考今不考古”之事,只要“稽諸近日奏牘、訪之故吏老兵,期于洞悉近日情形”即可,故有編輯《經世文續編》之議。但與此同時,張之洞也同意“經世之學,讀官書,尤須讀史傳”,主張用計日程功之法看正史、《通鑑》、《通鑑紀事本末》、《通考》、《五禮通考》等史書、政書,每天限讀一二卷,仿照《黄氏日鈔》例作筆記。張之洞特別强調“讀書”與“考古”的區別:“讀書可計日而畢,考一事不能剋期而得。”正是彼時內外局勢的緊迫,促使翰林清流將治學領域從經學轉向史學(乃至掌故經濟之學),將治學方法從長年積累的“考古”轉向計日程功的“讀書”。(67)
然而,講官出身的“清流”無論如何强調經世致用,都還是書本工夫。由經入史固然較翁同龢、潘祖蔭一派的考訂之學向“時務”、“洋務”前進了一步,但研究《通考》、《五禮通考》、《新疆識略》、《蒙古游牧記》等(68),仍然不出道咸以後學人熱衷三禮之學、邊疆史地的趣味,卻始終與李鴻章、曾國荃等外官所熟悉的洋務實際有所隔膜。光緒七年(1881)張之洞莅任山西巡撫,從清流一變而爲督撫,議政立場便大爲轉移。(69)而此時張佩綸致信李鴻藻,仍聲言:“願爲汲戆居中,不願坡仙乞外也……竊謂留心時事者,到處可以歷練,不留心者雖兩司豈少顓頂者哉。”信末還再次强調:“所最畏者出外”,可見清流中人對外官實務之抵觸情緒。(70)光緒十年(1844)中法戰争期間,或是震懾于前此“清流”競言洋務的聲名,或是樞臣有預謀的傾陷,張佩綸、陳寶琛、吳大澂等清流人物紛紛被外派會辦防務,其言論、學術實踐爲事功,卻因戰事不利而淪爲舉朝非笑的對象。
道咸時代,曾、胡、羅以書生行軍成爲幾代人的精神偶像;降至同光,張佩綸、陳寶琛卻以書生帶兵淪爲一時笑柄。同爲“書生”,都講“經世”,所持之政術、學術、風俗實有雲泥之別。光緒十四年(1888)三月末,故人寶廷致函張之洞,回顧“清流”前事,評點群倫,不禁爲之唏噓:
回思昔年同人聚處京華,轉眴風流雲散,升沉各异。老夫子(張之洞)功業顯著,年甫逾艾,建樹有日,必成一代名臣,尚矣。漱蘭(黄體芳)功業未必有成,亦可爲一代直臣。鐵生(何金壽)生直臣,死循吏;亦不枉一世。伯潜(陳寶琛)半途生廢,而年力尚强,獨有後望,且歸隱有資,不出亦可有山林樂。繩庵(張佩綸)有才不能自晦,遂不惜枉尺以求直,尋日後之功名未可致,當前誚謗,已不能免,徒使嫉之者快口,愛之者傷心。(71)
甲申中法之役後,陳寶琛遭罷黜歸里,張佩綸獲罪譴戍塞外,加上前此何金壽早逝,寶廷因納船妓事自劾,翰林清流碩果僅存者,惟有外放疆臣之張之洞與居京退閑之黄體芳二人。寶廷出身宗室,早歲風流,晚年卻較有理學氣味,評論張佩綸“枉尺以求直”,當指其熱心洋務、入李鴻章幕等事。
至六月間,寶廷再次致信張之洞,詳陳病中研究宋學、天算的心得。關于天算,强調必須“推算出一簡實之法,藉可杜西人之妄口,解華人之大惑。不然,日久愈惑,將謂雖聖人亦不知天,以西人爲聖人,從此流弊不可勝言矣”。(72)然而,業已升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卻在回信中正告寶廷:“天算中法實不如西法,經解宋學實不如漢學。”多年的外官閱歷使張之洞突破了京官視野,而清流經驗亦逐漸淡出到從事“時務”、“洋務”背後的義理、原則層面。如張之洞回信中所說:“若能通西法以得自强之術,博漢學以爲名理之資,是西法正爲中國所用,漢學正爲宋學所用。”(73)晚清督撫勢力坐大,在處理地方實務時,不斷面臨“經”與“權”的抉擇,與樞府、京官的矛盾亦随之擴大,不難推想張之洞外放疆臣後的立場移動。但在此語境下,進一步考慮沉澱到記憶深處的清流經驗在此後應對近代新知、重構交際圈子過程中的潜在作用,則是更爲深刻的話題。(待续)
注釋;
①黄濬:《花随人聖盦摭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頁192。光緒末年,黄濬就讀于京師大學堂,該段記載,很可能出于當時北京新學界的傳聞,有一定可信度。
②張之洞:《謁胡文忠公祠二首》其二,龐堅校點:《張之洞詩文集》卷三,詩集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17。又張之洞自撰《抱冰堂弟子記》:“經學受于呂文節公賢基,史學、經濟之學受于韓果靖公超,小學受于劉仙石觀察書年,古文學受于從舅朱伯韓觀察琦。”見苑書義、孫華峰、李秉新主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以下簡稱“河北版”),頁10631。
③《沈子敦先生遺書序》,見錢仲聯輯録:《沈曾植海日樓佚序》(上),《文獻》1990年第3期,頁185。
④參見楚金(瞿兌之):《道光學術》、《道光學術餘議》,《中和月刊》第1、9期,1941年1月、1944年9月。
⑤此爲咸豐三年(1853)曾國藩的觀察,多次見于其書信中,參見《與劉蓉》(咸豐三年十月十五日)、《復龍啓瑞》(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復黄淳熙》(同年十二月),分別載《曾國藩全集·書信一》,長沙:岳麓書社,1994年,頁292、414、431等處。
⑥《清史稿》卷一百八《選舉三·文科》。按柏葰案實有肅順清除异己的政治背景,但“自嘉道以來,公卿子弟視巍科爲故物”,戊午科場案在客觀上的確起到了肅清風氣的作用。參見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3156。
⑦陳義杰整理:《翁同龢日記》第二册,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同治元年(1862)三月二十五日、四月初六日條下,頁196、199。
⑧參見張之洞:《送同年翁仲淵殿撰從尊甫藥房先生出塞》,載《張之洞詩文集》卷二,詩集二,頁31。
⑨李慈銘:《孟學齋日記》甲集首集上,同治二年(1863)四月廿四日條下:“探花張之洞,直隸南皮人……壬子解元,少年有時名,聞其詩、古文俱有法度。近日劉其年劾吳臺壽一疏,傳出其手,筆力固可喜也。”見《越縵堂日記》,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影印本,第4册,頁2338。
⑩陳銳《袞碧齋日記》:“張文襄用人成見甚深,及所甄録,一門第,二科甲,三名士。晚年提倡新學,兼用出洋學生,捨是無可見長矣。”轉引自汪國垣:《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汪辟疆說近代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67。
(11)李鴻章:《復張香濤學使》(同治八年七月),吳汝綸編:《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十一,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2種,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頁746。
(12)參見曾國藩:《復許振禕》(同治十年十一月十一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十》,長沙:岳麓書社,1994年,頁7579。
(13)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卷一同治九年條下,1939年南皮張氏舍利函齋武昌鉛印本。張之洞爲潘祖蔭撰書事,尚可參看潘祖蔭《攀古樓款識自序》(載潘祖年編《潘文勤公年譜》同治十一年條下,光緒間刻本)及劉聲木《萇楚齋三筆》卷六“潘祖蔭撰述及軼事”條(見劉篤齡點校《萇楚齋随筆》頁597,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14)張之洞:《致潘伯寅》第一通,河北版《張之洞全集》第12册,書札一,頁10100。張之洞在本年四、五月間一共寫了七封信給潘祖蔭,商討此次雅集事宜。
(15)張之洞:《致潘伯寅》第七通(同治十年五月初二日)附有名單,見河北版《張之洞全集》第12册,書札一,頁10103~10104。
(16)李慈銘:《致孫子九汀州書》,載《桃花聖解盦日記》己集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初二日條下,《越縵堂日記》影印本第8册,頁5440。地名下劃綫爲筆者所加,原文小注略。
(17)參見李慈銘《桃花聖解盦日記》戊集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二十日條下(《越縵堂日記》第8册,頁5314)、張之洞《潘侍郎藤陰書屋勘書圖歌圖爲秦誼亭作》(《張之洞詩文集》卷二,頁53-54),錫縝、李慈銘詩亦載楊鍾羲《雪橋詩話續集》(石繼昌等整理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八,頁501~502。
(18)據李慈銘《壬申七月五日鄭司農生日集潘侍郎鄭盦記》,附載《桃花聖解盦日記》己集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二十七日條下,見《越縵堂日記》影印本第8册,頁5462~5465。
(19)張之洞:《和潘伯寅壬申消夏六咏·檢書》,《張之洞詩文集》卷二,詩集二,頁62。
(20)嚴玉森無題詩,載《壬申消夏詩》,叢書集成新編影印《滂喜齋叢書》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頁307。
(21)顧平旦整理:《天咫偶聞》卷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71(標點有所調整)。
(22)繆荃孫:《琉璃廠書肆後記》,見孫殿起輯:《琉璃廠小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105。
(23)參見盛昱:《與張制軍書》、楊鍾羲:《意園事略》,分別載盛昱:《意園文略》卷一及附録,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567册影印宣統二年(1910)金陵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247~248、266~268。
(24)參見王懿榮:《四庫全書懇恩特飭續修疏》、《臚陳本朝儒臣所撰十三經疏義請列學官疏》,呂偉達主編:《王懿榮集》卷一,濟南:齊魯書社,1999年,頁29~34。
(25)參見張之洞:《致潘伯寅》(光緒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河北版《張之洞全集》第12册,書札一,頁10107。據張壽安的考察,争取許慎從祀的運動始于乾嘉時期,以陳鱣、任兆麟等人爲代表,至光緒元年(1875)汪鳴鑾再次奏請,次年獲准正式入祀。参見張壽安《打破道統 重建學統——清代學術史的一個新觀察》,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2期(2006年5月),頁75~79。
(26)參見翁同龢等于光緒十二年(1886)二月十五日所上《遵議黄宗羲等從祀文廟摺》、《遵議先儒黄宗羲顧炎武從祀疏》。光緒十一年(1885)江西學政陳寶琛率先上奏,請以黄宗羲、顧炎武從祀,次年內閣會議,遂有此一摺一疏。當時列銜者,尚有潘祖蔭、周家楣、孫詣經、孫家鼐、盛昱、龍湛霖六人,但最終並未獲准。見謝俊美編:《翁同龢集》上册,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47~50。
(27)王懿榮:《〈南北朝存石目〉叙例》,見《王懿榮集》卷一,頁81~82。
(28)王懿榮:《誥封宜人元配蓬萊黄宜人行狀》,《王懿榮集》卷二,頁92~93。
(29)如光緒十七年(1891)前後,張之洞致信王懿榮,打探楊守敬在日本所購書,見《與王廉生》第八通,河北版《張之洞全集》第12册,書札一,頁10127。
(30)《後漢書》卷六十七《黨錮列傳》:“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次曰‘八顧’……次曰‘八厨’……顧者,言能以德行引入者也……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2187。
(31)陳寶琛:《瑞臣屬題羅兩峰上元夜飲圖摹本》,《滄趣樓詩集》卷六,見劉永翔、許全勝校點:《滄趣樓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33。
(32)張佩綸:《復宗載之姊丈》:“京秩無不高寒……惟同年世好有外任者,相率爲饋歲之舉,美其名曰炭敬,上至宰相、御史大夫,莫不恃此敷衍,冷官滋味,豈復可耐?”《澗于集》書牘卷一,《續修四庫全書》第1566册影印1926年張氏澗于草堂刻本,頁410下。
(33)關于翰林簡放學差前後的境遇差別,參見何剛德:《春明夢録》,柯愈春等整理:《話夢録 春明夢録 東華瑣録》,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88。
(34)參閱張德昌:《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0年,頁52~57。
(35)此爲其友人陳衍評語,見《石遺室詩話》合訂本卷七,《民國詩話叢編》第一册,頁106。
(36)陳澹然:《异伶傳》,載張次溪輯:《清代燕都梨園史料》下册,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年,頁727。
(37)當時也有將“清流”與“名士”分開的用法,如前揭何剛德《春明夢録》:“甲申時之清流,甲午之名士,皆翰苑高才也。”見《話夢録春明夢録 東華瑣録》,頁77。用“清流”指張之洞、張佩綸、盛昱一代,用名士指沈曾植、張謇、梁啓超一代。楊國强《晚清的清流與名士》一文正是以這一劃分爲基礎,討論二者的關聯與背離,見其所著:《晚清的士人與世相》,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頁146~214。
(38)《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四,頁12460。
(39)王維江在《誰是“清流”》、《從“清流”到“清流黨”》二文中分析了清末民初作爲政治現象的“清流”,分別載《史林》2005年第3期、2006年第1期。
(40)南、北清流之說,大抵以“四諫”諸人爲“北党”,李鴻藻爲領袖;以李慈銘、盛昱等爲“南党”,翁同龢爲領袖。此說實源自甲申(1884)前後軍機處漢大臣的南、北之争,胡思敬《國聞備乘》卷二“南黨北黨”條、陳衍《石遺室詩話》卷十一“張廣雅詩紀晚清黨争”條等均曾論及。至民國間,在劉成禺《世載堂雜憶》的“龍樹寺觴咏大會”條下,遂演爲“南北清流”之争奪。參見錢實甫點校:《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89。
(41)前、後清流之說,至少有兩種:1)以“南北清流”說中之北黨爲“前清流”、南黨爲“後清流”,如黄濬即認爲:“當時朝中名士,前一輩清流,若張孝達(之洞)、張繩庵(佩綸)等,皆與高陽(李鴻藻)善;而稍後進者,若張季直(謇)、沈子培(曾植),則與常熟(翁同龢)善。”參見《花随人聖盦摭憶》,頁55~56。2)以同光之間(不論南北)爲清流前期,光宣之間爲清流後期,如陳寅恪《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參見《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頁191~192。
(42)《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史部“廣雅堂論金石札五卷”條:“之洞于金石之學本非專門,故其所論不能盡中肯綮。”附載河北版《張之洞全集》第12册,頁10779。
(43)張之洞《論金石札二·金文雜說·致潘祖蔭》云:“今日號稱爲許、鄭之學者,謂爲頌揚許、鄭之學則可,何嘗有講求許、鄭之學者哉。(原注:講經學而名曰漢學,已偏矣;講漢學而名曰許、鄭之學,尤隘也。此皆省事自便之道,非實事求是之道也。)”又《讀經札記二·汪拔貢述學》云:“……將謂孔孟大道、許鄭儒宗,但解編纂《說文》、繪畫《三禮圖》而已乎?(原注:此二事在今日陋俗則爲甚難,在漢儒止是入門功夫耳。)不惟謬議聖傳,抑亦厚誣漠儒之甚矣。使後世以漢學爲詬病者,此輩(汪中)之罪也。”見《張之洞全集》第12册,頁10388、10025。
(44)張之洞:《潘侍郎藤陰書屋勘書圖歌圖爲秦誼亭作》,《張之洞詩文集》卷二,詩集二,頁53~54。
(45)《北史》卷四十三邢劭本傳,見李延壽等撰:《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593。
(46)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55~256。
(47)袁昶《廣雅碎金校語》于此詩題下注云:“此丹經萬卷,不如守一之意……指約而易摻,可爲馳騖無涯之智,薄暮不知所止泊者,腦後下鍼。”附載《廣雅碎金》卷末,《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頁92~93。
(48)見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卷一,光緒三年條下。
(49)譚獻日記光緒四年(1878)十月二十日條下引樊增祥來書語,見范旭侖、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281。
(50)張之洞:《致潘伯寅》,河北版《張之洞全集》第12册,書札一,頁10118~10119。原文小注略。
(51)見張允僑《閩縣陳公寶琛年譜》光緒三年條下,附載前揭《滄趣樓詩文集》下册,頁701。
(52)張佩綸《澗于日記》(臺北:學生書局,1966年影印本)光緒四年(1878)十月十四日:“夜孝達(張之洞)招飲,蹔過伯潜(陳寶琛),至孝達齋已月上矣。同集者汪柳門(鳴鑾)、吳清卿(大澂)、顧皡民(緝熙)及余叔侄,曾君表(之撰,曾樸父)後至,觀清卿所藏薛氏鐘鼎款識拓本。”其中汪、吳、顧三人均爲潘祖蔭圈子的活躍人物。
(53)吳可讀訣兒書,載《花随人聖盦摭憶》,頁132~134。
(54)《歐陽文忠公集》(四部叢刊影元刻本)附録卷第五歐陽發等撰《事迹》:“既而有詔,百官許上封章言事。公(歐陽修)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之患。仁宗增諫官爲四員,先公與蔡公襄、余公靖、今致政王尚書素同時遷用。”然則所謂慶曆“四諫”,乃起于制度上的施設,而非時人泛稱。但因四人均能直諫,後來遂有“慶曆四諫官”之目。如劉克莊《勸學》詩便有“新擢咸淳兩臺端,可繼慶曆四諫官”句。見《後村集》卷三十五,四部叢刊影舊鈔本。
(55)見《明史》卷百七十九章懋本傳,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4751。
(56)參見張之洞:《壽黄漱蘭通政六十》、《拜寶竹坡墓二首》,《張之洞詩文集》,頁128、149。陳寶琛《吳柳堂御史圍爐話別圖爲仲昭題》:“同時四諫接踵起,欲挽清渭澄濁涇。”句下原注:“時稱張(佩綸)、寶(廷)、何(金壽)、黄(體芳),文襄(張之洞)尚未在講職也。”《滄趣樓詩文集》上册,頁167。
(57)張佩綸《復宗載之姊丈》:“前者家兄書來,云胡介卿回浙,有‘言官不言,講官亂講’之謠。其實此二語本香濤前輩與弟戲詞,乃云:‘言官不言,講官盡講。’都人遂以‘雨師勿雨,風師多風’屬對,妄爲傳播,並非事實。”見《澗于集》書牘卷一,頁413下。
(58)甲午戰争後,吳汝綸致信陳實箴,有云:“近來世議,以駡洋務爲清流,以辦洋務爲濁流。”另一函又云:“中國不變法,士大夫自守其虛驕之論以爲清議,雖才力十倍李相,未必能轉弱爲强。”可見時人已將“清流”作爲“洋務”、“變法”的對立面。見吳汝綸《與陳右銘方伯)(光緒二十一年閏六月十一日)、《答陳右銘》(閏六月十二日),施培毅、徐壽凱校點:《吳汝綸全集》第3册,合肥:黄山書社,2002年,頁103、105。
(59)張佩綸《澗于集》詩集卷二有詩題曰:“少荃夫子(李鴻章)六十生日,敬不舉觴,禮也。佩綸與公累世通家,雅托密契……”(頁87下)
(60)見何剛德:《春明夢録》,《話夢録 春明夢録 東華瑣録》,頁85。
(61)參閱張佩綸:《致李肅毅師相》,《澗于集》書牘卷一,頁424下。
(62)張佩綸:《致李肅毅師相》(甲申),《澗于集》書牘卷三,頁482上。著重號爲筆者所加。“興獻”指醇親王,因其爲德宗本生父,用明世宗“大禮議”事影射。
(63)楊鍾羲:《雪橋詩話》卷十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594。
(64)張之洞:《致張幼樵》,載《張文襄書札》(抄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案(以下簡稱“所藏檔”):甲182-371。該信抄本天頭有編集者眉批:“此似謂陳弢庵參內監事。”按此册檔案全部抄録張之洞致張佩綸書信,時段在光緒初年至十六年(1890)間,而尤多收録光緒五、六年前後張之洞與張佩綸、陳寶琛關係密切時信件。
(65)此事本末,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言之甚詳,參見該譜卷一,光緒六年十二月條下。
(66)張之洞:《致張幼樵論學三札》其二,載前揭《張文襄書札》(抄本)。按此三函亦被黄濬收入《花隨入聖盦摭憶》,略有删節,見該書影印本,頁303~304。
(67)見張之洞:《致張幼樵論學三札》其一。稍早張佩綸在書札中聲言:“以目下時會而論,作經生不如究史學,究史學不如講求掌故,練習時務。”見《致宗載之姊丈》,《澗于集》書牘卷一,頁412上。
(68)張之洞《致張幼樵》(又):“《新畺識略》暨條約各種,並《蒙古游牧記》,望借一檢爲幸。”載前揭《張文襄書札》(抄本)。
(69)比如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争時,張之洞雖亦主戰,但其理由已迥异于朝中清議,光緒十年(1884)二月十二日《致張幼樵》云:“中外兵事,鄙意與尊意及京朝諸言事者,迥然不同。諸公意謂法不足畏,我易勝法;故紛紛主戰。鄙人則明知法强華弱,初戰不能不敗,特非戰不能練海防,非敗不能練戰。”見河北版《張之洞全集》第12册,書札一,頁10152。原文小注略。
(70)張佩綸:《致李蘭孫師相》(光緒八年),《澗于集》書牘卷二,頁460下。
(71)寶廷:《致張之洞二通》其一,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原件:SB/818.179/1332:7。
(72)寶廷:《致張之洞二通》其二,出處同上。
(73)張之洞:《致寶竹坡》,河北版《張之洞全集》第12册,書札八,頁10343~10344。
标签:翁同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