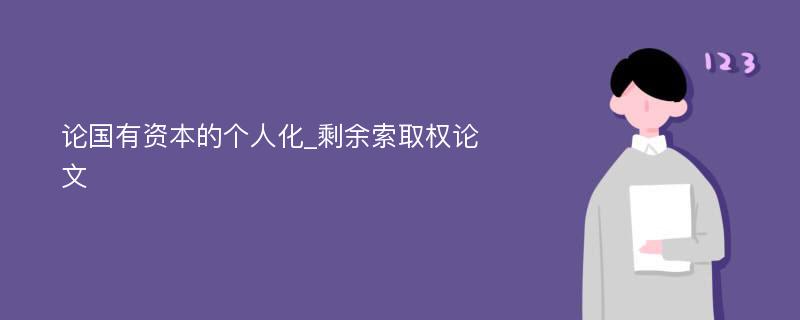
论国有资本人格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传统的国有资本营运方式的改革必须坚持两条原则:(1)资本国家所有;(2)政企分离。在理论探讨和实际操作过程中,经济学家依据这两条原则设计了改革的许多模式,如放权让利,承包制,租赁制,公司法人制等。但所有这些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引致国有资本的人格异化,致使改革陷入了种种误区。本文认为:国有资本人格化是改革走出误区的必由之路,而国有民营模式则是国有资本人格化的一种必然选择。
一、资本人格化的经济条件
一定的经济主体要成为人格化的职能资本,必须具备三个经济条件:
第一,拥有剩余索取权。剩余是企业经营收益扣除其成本费用后的余额。经营收益对成本费用的补偿表现为资本的保值,超过成本费用的补偿而形成的余额表现为资本增殖,因此,资本自行增殖的本性无非就是一定经济主体追求剩余最大化的意志和意识的物化形式。只有当一个经济主体拥有剩余索取权的时候,他才可能将资本最大限度地增殖作为其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成为资本化的人格。可见,剩余索取权是资本化人格形成的内在根据。资本化人格是资本的灵魂,这是因为:(1)它确定了资本运行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殖;(2)它提供了资本自行增殖运动的内在动力;(3)它制约着资本按盈利性、安全性等原则运行,是规范资本运行的内在制约机制;(4)它用是否有利于资本最大限度增殖来衡量资本行为是否合理,并决定资本行为的取舍,是资本运行的自我评价和调控系统。没有资本化的人格,资本行为的规范化是不可设想的。
第二,拥有资本控制权。一定的经济主体如果仅仅拥有剩余索取权,只能成为人格化的观念资本,不能成为人格化的职能资本。只有当拥有资本控制权的时候,才能将资本化人格物化为资本的增殖运动,转化为一种物质力量。在现代经济中,直接推动企业资本运转的是工人、管理人员等,这些自然人的意志和意识与资本自行增殖的本性存在着很大的偏差或对抗。资本化的人格只能通过资本控制权将其意志一层一层地传导给企业所有员工,使其意志上升为整个企业的意志,并按这种统一的意志和意识推动资本进行循环和周转。可见,资本控制权是资本人格化的传导手段。
第三,承担负债清偿责任。企业资本包括负债资本和权益资本两个部分。一定的经济主体只有承担负债清偿责任,才能获得负债的无限清偿责任改变为有限清偿责任。同时,如果负债清偿责任不是一个硬的约束条件,该经济主体就有可能利用资本控制权将负债资本价值转化为企业剩余,对剩余的追求就转化成为负债资本的蚕食和侵吞,该经济主体也就会异化成一种非资本化的人格。可见,承担负债清偿责任是资本人格化的前提。
总之,剩余索取权,资本控制权和负债清偿责任三位一体,使一定的经济主体成为人格化的资本。具备这三个经济条件的经济主体则只能是权益资本所有者。权益资本所有者之所以拥有权益资本的控制权及其剩余索取权,正是因为他拥有权益资本的所有权;之所以拥有负债资本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则是因为他承担了负债清偿责任,而权益资本的是承担负债清偿责任的物质基础。因此,所谓资本人格化,就是权益资本所有者作为“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
二、国有资本人格异化
如果国有资本为权益资本,要实现国有资本人格化,国家就必须成为资本化人格,从而由国家直接掌握企业的资本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并承担负债清偿责任,传统的高度集中的国营企业经营体制正是根据这一原理构建的。诚然,由国家直接经营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中型企业是必不可少的,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表明,由国家集中统一控制全部国有资本的营运是缺乏效率的。首先,国家作为全民资本的代理人和宏观经济管理者不一定能产生资本化的意志和意识;其次,即使国家能产生资本化的意志和意识,这种意志和意识也无法准确地反映客观经济情况;最后,即使国家的意志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千差万别,瞬息万变的客观经济情况,也不能有效地将这种意志和意识物化为资本的增殖运动。企业作为国家的附属物,既无推动资本增殖的动力,也无推动资本进行增殖运动的能力,企业不可避免地出现僵死状态,失去生机和活力。
对传统的国有资本营运方式的改革的第一步是放权让利,其要点是弱化国家的资本控制权,强化企业经营管理权,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企业经济,但它是国有资本人格异化的开端。作为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实际行使者的职工,因不拥有剩余索取权和不承担负债清偿责任,不可能把国有资本的保值增殖作为其经济活动的目标,追求的只是职工收入及其福利最大化,是一种非资本化的人格。随着经营管理权的强化,这种非资本化人格逐渐地物化为资本的运动。资本的运动成为一种与资本的本性相偏离或对抗的人格所支配的经济现象,可称之为资本人格的异化。随着国有资本人格异化、工资和福利不断蚕食企业剩余甚至国有资本,作为推动资本自行增殖工具的经营管理权开始异化成为侵吞剩余和资本的工具。
为了使企业经营管理者人格资本化,我们对国有资本营运方式进行了第二步改革,实行承包制和租赁制,其基本内容是:国家保留资本所有权,承包人或租赁人则拥有资本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并承担负债清偿责任,实质就是企图将包租人设计成一个脱离权益资本的资本化人格。这种设计至少有以下几个无法克服的障碍:(1)既然企业全部资产为负债资产,所谓企业以资产对负债负责,实际上是包租人对负债不负责,其结果只能是包盈不包亏。(2)企业留存收益面临着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留存收益作为剩余的一部分,其所有权应归包租人;另一方面,作为资本增量,其所有权应归资本所有者国家。留存收益所有权的不确定性,使企业丧失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功能。(3)包租人利用资本控制权将国有资本价值转化为企业剩余,在有限的包租期内尽可能将资本价值吮干而给国家留下一个资本空壳,其结果不是资本的保值增殖,而是资本的流失和消亡。可见,脱离权益资本的资本化人格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中则是国有资本人格的进一步异化。
只有权益资本所有者才能成为资本化人格,而国家作为权益资本所有者又不宜于充当资本化人格,这就是国有资本人格化所面临的一个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对国有资本营运方式进行了第三步改革,对国有企业实行公司法人制改造,其基本内容是将所有权二重化:国家作为出资人拥有资本的原始所有权,不对企业资本实行直接控制;企业作为法人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独立地拥有资本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并承担负债清偿责任,成为资本化人格。然而,这一模式只不过是一种理论虚构,同一资本不可能有两个所有权。如果企业的独立性不排除国家作为权益资本所有者对企业的资本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那么,这种经营方式与国家直接经营企业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区别。首先,国家以出资额对企业负责,这种责任是无权利的责任。国家作为权益资本所有者或许有使资本增殖的意志和意识,但因丧失了资本控制权,无法将这种意志和意识物化为资本的运动;其次,企业拥有剩余索取权,这种利益是无人格代表的利益。企业只能成为无人格的资本。资本化的人格为资本的运动提供目标、动力、内在约束机制,自我评价和调控系统的功能统统消失了。最后,职工代理企业行使资本控制权,这种权力是一种无责任的权力。职工以追求其自身收入及其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是一种与资本本性相偏离甚至根本对抗的人格,但他们可以将这种人格物化为资本的运动,使国有资本人格异化走向极端,其主要表现是:(1)收入分配向职工倾斜。当企业收不抵支的时候,职工将首先保障工资支出,而让收支缺口去侵蚀企业资本金和其他债权人利益。当企业收大于支的时候,职工工资就膨涌向上,尽可能蚕食企业剩余,使其趋近于零;如果遇到制度上的约束,使得工资支出无法完全吞噬企业剩余,则尽可能将剩余用于劳保福利性支出和各种奢侈豪华的消费。(2)将企业和社会资产化为职工收入。如:对企业资产耗费不予以足额补偿,虚增企业盈利,再将虚增盈利工资福利化;权力寻租等。
总而言之,国家作为权益资本所有者,如果直接掌握资本控制权,企业则死;如果放弃资本控制权,企业则乱,对国有资本营运方式的改革,已经历了对资本控制权的收与放的几次反复,国有资本的营运始终无法突破死与乱循环的怪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有权益资本人格化问题无法解决。
三、国有民营:国有资本人格化的实现方式
要实现国有资本人格化,使国有资本从死与乱的循环中跳出来,步入自行增殖的轨道,唯一的选择是将国有权益资本改造为国有债权资本,将一定的社会经济主体塑造为资本人格来推动国有资本的运转,即对国有资本的营运实行国有民营方式改造。这一改造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社会经济主体向企业注入权益资本。一定的经济主体要成为国有资本的人格,就必须拥有国有资本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其前提条件是按约定条件承担国有资本保值增殖的责任,权益资本则是承担这种责任的物质基础。同时,一定的经济主体只有注入权益资本从而成为企业的权益资本所有者以后,国有资本价值的升与贬,国有资本营运的溢与损,营业外的收与支等才会必然地表现为该经济主体的增与减,该经济主体对权益增量的追求才会必然地物化为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企业整体资本的增殖运动。
第二,国家以一定的价格让渡资本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资本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让渡以后,国家虽然保留了资本的所有权,但不再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分享企业利润,只能按期获取约定的资本回报,真正实现了政企分离。但是国有债权资本与其他形式的债权资本相比,应具有以下特点:(1)资本形态价值化。国有资本不论以货币形式存在还是以生产资本或商品资本形式存在,都是资本价值的不同存在方式。国有债权资本以价值形式存在,可以避免权益资本所有者对实物形态的资本的掠夺性经营及其他侵蚀行为,也便于国家对资本存量的监管,流动与重组。(2)权益资本所有者对国有资本拥有“永佃权”。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国有资本在有限期间内从企业抽回,企业就不可能有持续稳定的经营,也不可能有长期的经济行为。因此,只要权益资本所有者能确实履行对国有资本的经济责任,他们就能无限期地拥有国有资本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这个意义上,国有债权资本具有优先股的性质,其清偿顺序在其他债权资本之后,权益资本之前。(3)资本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让渡价格指数化。如果资本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让渡价格永久固定,这种让渡就适应不了资本市场的重大变化。因此,必须在一定的让渡期内,依据让渡协议,按物价指数,资金利息率等因素对让渡价格进行指数化调整,以保证这种让渡方式的正常运作。
第三,国家对企业经营风险进行严格监管。因为国有资本在企业总资本中所占比重特别巨大,资本控制权的让渡具有永久性,清偿顺序以在其他债权资本之后,所以,承担着特别巨大的经营风险,而国有资本的债权性质排除了它承担这种风险的责任。因此,国家必须对企业的经营风险进行严格的监管,将其经营风险控制在权益资本范围内,能否将企业经营风险有效地控制在权益资本范围内是国有民营方式能否成功运作的关键,其具体的控制方式是,在企业权益资本中划定一条预警线。企业风险损失冲减权益资本没有超过预警线时,国家对资本的运行不作任何干预。当风险损失超过预警线时,则要求权益资本所有者追加权益资本恢复到法定或预约水平。若权益资本所有者能满足要求,则资本继续自行运转,国家仍不作任何干预。但如果所有者拒绝追加权益资本,则国家首先停止其经营行为,继而收回国有资本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可见,把国有权益资本改造为国有债权资本,并不是国家对资本弃而不管,而只是改变了管理方式,将对资本的直接控制改为对营运风险的监管,权益所有者在风险控制范围内完全自主地推动国有资本运转,这样就真正构造出了一种管而不死的营运模式。
第四,社会经济主体在国家的风险控制范围内自主经营。一方面,社会经济主体拥有资本控制权,有自主地推动资本运行的充分权力,追求自身利益的内在动力和清偿负债的外在压力驱使他们最大力度地推动资本运转,企业因此充满生机和活力,彻底地摆脱了作为国家附属物时所呈现出来的僵死状态。另一方面,社会经济主体拥有剩余索取权,企业剩余成了他们追求的根本经济利益,同时,国家严格地将经营风险控制在权益资本范围内,堵塞了他们利用资本控制权将国有资本价值转化为企业剩余的通道,资本自行增殖成为谋求企业剩余的唯一方式,从而使得这一经济主体必然地将资本最大限度的增殖作为自己的意志和意识,成为资本化的人格,资本化的人格物化为资本的运动,不仅为资本的运动提供了自行增殖的目标和动力,而且为资本的运动提供了内在制约机制,自我评价和调控系统,保证了资本的规范运行,国有资本人格异化所引致的种种表象也就自然消失了,国有资本的运行真正进入到了活而不乱的境界。
构建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国有民营模式则是为解决这一课题所设计的一个方案。这一模式至少有以下两个功能:(1)在坚持资本国有,政企分离的原则的同时,实现了资本人格化。社会经济主体作为人格化的职能资本推动资本自行增殖,国有资本营运从此摆脱了死与乱循环怪圈的困扰,企业成为了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经济主体。没有资本化的人格,企业就会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歪曲反应,各种经济杠杆对企业经济行为的调节就会失灵,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就会紊乱。国有资本人格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塑造了健全的微观经济主体。同样,没有资本化人格,国有资本就会不断流失和消亡,社会资源就会被大量破坏和浪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国有资本人格化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构造了规范的企业组织形式。(2)在资本人格化的同时保证了资本营运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种模式中,国家保留了资本所有权,国有资本的全民性质没有变。的确,国家让渡了资本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容许的。因为,社会主义阶段全民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一般只能限于生产资料的归属关系上,而不可能由全民对生产资料进行直接的占有,支配和使用,除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中型企业以外,也不能由国家代表全民来行使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处分等方面的权力,这些权力只能让渡给部分社会成员来行使。可是,如果采用承包制,租赁制,公司法人制等方式让渡,则必然导致国有资本人格的异化,使全民的利益受到极大的侵害。只有通过国有民营方式让渡这些权力,才能实现国有资本人格化,在机制上保障国有资本按自行增殖的轨道运行。国有资本自行增殖是国有债权保值增殖的物质基础,国家对企业经营风险的严格控制则是国有债权保值增殖的制度保证,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相互配合,使国有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展壮大。可见,这种营运方式不会使全民利益受到丝毫损害,也不会使国有资本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地位有丝毫的动摇,恰恰相反,它是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必然的实现方式。
在现阶段,构建国有民营模式还存在着许多巨大的技术性的障碍,如社会经济主体如何筹集与巨额国有资本相匹配的权益资本金,国家对企业经营风险的监测如何进行实际操作,资本人格化后企业富余劳动力如何安置,等等,我们必须认真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为实现国有资本人格化探索一条可行的道路。
标签:剩余索取权论文; 权益资本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企业控制权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企业责任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