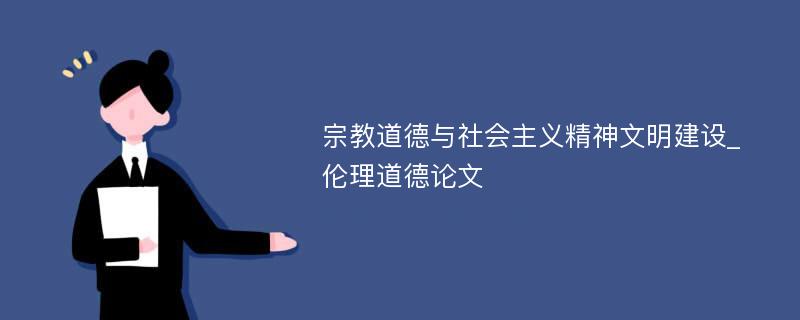
宗教道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文,宗教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令世界瞩目的两大转变:经济体制上,初步实现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在社会结构上,正在经历着由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农业社会向开放的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各种社会关系、社会要素、社会利益都在分化、调整和重新组合,并由此而引起社会文明与道德的深刻变化:原有传统的基础文明和道德准则正在经受考验、筛选和重构;人的主体性、进取性、务实性增强,社会的宽容性、自由度、融摄性增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改革开放的现代化社会,为了不断完善与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体系。没有继承就没有建设,没有变革就没有发展。因此,发掘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资源和共产主义道德资源,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道德准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而宗教道德正是有待开发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道德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宗教道德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精神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重新发掘、提炼、筛选、弘扬,可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1.新中国成立以来47年的实践,早已证明了这一点。经过历次反帝爱国运动和社会民主改革、社会政治运动的洗礼,我国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的社会政治状况早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剥削阶级的控制和影响,成为广大信教群众自办的宗教事业,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各项法律、政策尊重与保护的事业。它们已不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上层建筑的残余,而深深植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土壤,日益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的存在与发展,不仅不存在对社会构成威胁的问题,而且从整体上、主流上看,当今中国宗教还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扩大开放的一条重要渠道。这是当今中国宗教独具的特色,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中国是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爱国爱教是中国各种宗教的优良传统。广大信教群众作为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主人翁、国家的公民,47年来,一直接受着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接受着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与此同时,作为宗教信仰者,他们还理所当然地用宗教的伦理道德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热爱祖国,遵纪守法,与各族人民和睦相处,艰苦奋斗,共建社会主义家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47年来,我国广大信教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自己的伟大实践创造了宗教不断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历史,自觉地调整、提炼、弘扬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适应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与时代并进。他们是成功者。
2.宗教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普遍适用的某些伦理道德。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①a]无论何种宗教都是人的宗教,而不是神的宗教。宗教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一种曲折而特殊的反映,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产物。化天下以宗教,崇道德以信仰,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就我国五种宗教而言,其最初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尽管各不相同;但其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与各自所处时代社会信仰与伦理道德观念陷入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打开宗教历史的篇章,拂去世俗岁月的灰尘,我们发现,当古代社会价值观念伴随着时代发生变迁时,就会与陷入危机的旧的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冲突,就会呼唤与传统价值观、传统伦理道德观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新学说,呼唤解决社会信仰危机与伦理危机的新宗教。佛教、道教、早期基督教、伊斯兰教、基督新教,都是应当时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需要解决,社会价值观念需要变迁,社会信仰与伦理道德需要重建。因此,这些宗教的产生都曾受旧势力的迫害。都对当时的社会进步有过积极的贡献。它们之所以能够凝聚广大信教者并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们所提出的为人类普遍接受的那些宗教道德的感召力。
宗教道德内容丰富,层次不一。既有关于处理人与神关系的伦理道德,也有关于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道德;既有政治伦理道德,也有社会伦理道德,还有家庭伦理道德;甚至其宗教信仰、宗教功修、宗教禁忌、宗教习俗、宗教建筑、宗教服饰等,都无一不被赋予伦理道德的内涵。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落实到一点,即对宗教道德的行为主体——宗教信仰者提出严格的道德要求。
宗教对信教者有高层次的形而上的理想道德要求。人生苦短,乐生畏死是人的本能;追求人生的幸福,追求真、善、美,是人类的共同理想与愿望。宗教满足人们心灵的渴望与祈盼,以其生死观为突破口,试图为人类提供一套信仰化的生命永恒之道。宗教将人的生命价值神圣化,生活过程道德化,要人们以信仰净化灵魂、把握人生、超越自我,以善行走完短暂的人生旅途,不懈地追求真、善、美,实现生命的永恒、精神的升华、灵魂的不朽。于是,宗教便在人们的心灵上造成一种强有力的自我控制机制,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形成一种深层次的制约力量,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树起宗教道德的神圣权威。
宗教对信教者还有一般层次的具体道德要求。各种宗教的教义不同,其伦理价值观念也不尽一致,有主张出世的,有主张入世的,有主张“两世吉庆”的。但同为人间宗教,其信仰主体同是有七情六欲的人,都要食人间烟火,都在人类社会中生活,因此,都要用人类社会道德准则约束人们的行为。各教一般都将人类的行为分为善、恶两大类,要求人们行善避恶。善恶观是各宗教共同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基础。
正是从其善恶观出发,各宗教都分别对信教者提出严格自律、加强道德修养的要求,要人们自洁、守正、淡泊名利,在名利色欲面前要节制而勿放纵,在困难挫折面前要坚忍刚毅而勿灰心堕落,在顺利与成功面前要谦虚谨慎而勿骄傲狂妄,始终保持平和与安宁的心态。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宗教基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要求人们待人以和、以诚、以宽、以情,建立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鼓励朴实、宽恕、尊重、文明、礼貌、团结和睦、敬老爱幼、扶危济贫、劝人行善、止人作恶等美德;讲真情,不讲虚伪,反对抢劫、偷盗、奸淫、杀人越货、欺男霸女、恣意妄为、吹牛撒谎、诽谤诬陷、妒嫉猜测、拨弄是非、轻信谗言、奸诈狡猾、心胸狭隘等行为。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宗教要求人们热爱祖国,热爱集体,遵守法度,服从领袖,勤劳勇敢,勤奋工作,尽职尽责,尽社会义务,建立公平、正义、和谐、安宁的社会秩序;要求人们孝敬父母,慈爱子女,夫妻互爱,兄弟相亲,和睦家庭,友爱邻里;反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丧廉寡耻、违法乱纪、懒惰懈怠、好逸恶劳、同室操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宗教告诉人们,人是自然界中最珍贵的,自然界是为人类服务的,要观察自然,摸索自然规律,合理地开发自然,但不要暴殄天物,挥霍浪费,破坏安宁和谐的人类生存环境。
总之,各种宗教以不同的语言表达的同一种内容是:以加强个人的道德自律求得内心安宁与和平;以善行去谋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安宁与和平。
显然,上述种种宗教道德是人类普遍适用的。正如人需要空气、阳光、水和粮食一样,人类社会也需要这些起码的道德准则。文明的基础是人类以理性征服自我本能的冲动,实现人类的自我控制。宗教不仅从理论的层面告诉人们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当然,不信教者对此会有保留);而且从实践的层面告诉人们应担负的责任与义务,要求人们以道德自律,战胜自我,超越自我,谋求安宁与和平。否则,人类如不能以道德自律,社会就会失序,人类生存环境就会破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律就会兑现。
这些道德准则既然适合各种社会,当然也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实质,就是要求社会全体成员加强社会主义道德自律,自觉地遵纪守法,实现社会的整体和谐与进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固然需要“独立”、“自由”、“坚强”、“重视学识”等个体价值观,但我们更需要“责任感”、“义务感”、“忠诚”、“奉献”、“宽容”、“友爱”、“和谐”、“服从”、“有信仰”、“有理想”等社会价值观,需要人民公仆的服务意识,需要公共道德的权威性。宗教道德恰恰在这方面对其信仰者提出了具体的、普遍适用的伦理要求。这些要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非但并行不悖,而且有其积极的意义:它们有助于抑制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倾向的非理性强化,抑制文化消费的情绪型享受趋向,弥补因社会公共信仰体系缺失引起的公共权威下降的缺憾。宗教道德极强的自律性和可操作性,亦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某些有益的启示;各种宗教关于爱国家、爱他人、尽社会责任与义务等伦理道德观念,不仅适用于信教者,对不信教者亦应是适用的。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宗教在我国某种程度的发展,原因很多,其中根本原因是社会主义社会有适合宗教存在与发展的社会根源、认识根源;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宗教以其深邃的哲理、善良的道德规范、对安宁与和平意境的追求,发挥其独特精神魅力和影响的结果。
3.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道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资源的重要一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所谓“高尚的精神”资源主要有二:其一是“我们党的崇高理想信念、优良传统和作风”;其二“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秀传统和美德。”[①b]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美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居于主干地位。儒家伦理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家伦理思想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体系,体现了儒家重伦理、重社会价值的现实主义精神。其二,是以“礼”为核心的行为道德规范体系,充分体现了儒家道德教化学说中深刻的信仰意识。礼,源于上古时期的宗教祭神活动。《说文解字》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丰。”由此可知,儒家的礼文化,思想内涵是很丰富的,既履行天道以解决人与神的关系,也履行人道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孔子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②b]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③b];孟子讲“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④b]他们都在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要以宗教的信仰精神严谨地对待人生。儒家礼学中的基本内容,如祭礼、凶礼及天命鬼神观等等,都是我国宗法性传统宗教的产物和基本理论;儒家的基本经典《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也无一不具有宗教性内涵。
汉代,汉武帝纳董仲舒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正统地位确立,其伦理观、人生观及基本信仰广泛渗入社会各领域、各阶层。此时的儒家文化呈现出进一步宗教信仰化的特点,其核心内容有三:(1)三纲五常是不变的天道人伦,忠孝是封建道德的最高原则;(2)人生于世要尽人事而听天命,对社会要尽责,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3)思想上有三大崇拜:天命崇拜(君权天授、祸福天定),祖先崇拜(慎终追远、享祭鬼神),圣贤崇拜(尊崇周孔、学由五经)。[⑤b]儒家文化传统在汉代的那些具体表现形态,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经学等等,无一不带宗教色彩。
魏晋南北朝是封建社会统治思想进一步调整时期。在此时期,旧的思想文化结构伴随着社会的分裂、割据而解体,两汉经学让位给魏晋玄学,儒术独尊变成儒、释、道三教并存。隋唐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与这种社会政治局面相适应,儒家的正宗地位再次得到确认,儒、释、道三教趋向融合,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宋元以后,儒、释、道三教互相靠拢,从外部功能的一致性发展为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全真道派将儒、释、道三教融为一体,使道教达至辉煌的顶峰;禅宗加速了儒化过程,令佛教进入在华发展的后期;儒家则大量吸收佛、道教的思想营养以充实自己,完成了儒、释、道三教在理论上的会同与合流,成就了封建宗法制度在理论上的最高峰——程朱理学;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在元代大规模传入中国不久即开始了“附儒以行”的艰苦历程,渐向纲常名教靠拢。降至明清时期,“在思想文化与宗教方面,传统宗法性宗教祭祀制度完备化,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佛教加速与儒学的融合,道教势力走上衰微,民间宗教则极为活跃,伊斯兰教理论上儒化,基督教势力在鸦片战争后迅速扩展。宗教日益多元化,其影响向社会下层和各个文化领域扩散。”[①c]
这就是中国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的关系史。我们介绍这一点,并不是要证明中国宗教就等于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要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是多元的,其中宗教文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中常会发现有宗教道德基因的前提与依据。今天,当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大力发掘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和美德时,理所当然地也要大力发掘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使之有利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对传统的宗教伦理道德体系进行客观、公允而合乎历史逻辑的分析和价值判断,对其历史必然性及该体系中积极、高尚、不可否弃的思想要素给予充分肯定、大力弘扬。这必将有助于加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亲和力,进而强化我们中华民族的政治凝聚力。我们指出宗教道德与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密切关系,目的还在于强调对宗教道德必须有辩证的科学态度。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民主性精华也有封建性糟粕,宗教道德也同样如此。因此,对宗教道德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对繁杂的宗教传统伦理道德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梳理甄别工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继承、发展和弘扬。
二
当今中国的宗教与历史上的中国宗教相比较,社会政治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由旧社会依附封建王权的宗教变为人民群众自办的宗教事业。但宗教道德的社会教化功能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其中的积极因素转化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部分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宗教道德能否转化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部分,关键要看它自身的内容是否适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大致说来,可有下列三种可能性:
1.那些对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伦理道德,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最起码的道德规范,可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待之。例如:基督教、天主教“十诫”中的孝敬父母、毋杀人、毋行邪淫、毋偷盗、毋妄证、毋愿他人妻、毋贪他人财物;伊斯兰教所主张的“当孝敬父母,当优待亲戚,当怜恤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古兰经》4:36)及命人行善,止人干歹,不要傲慢、矜夸、满足自封而要谦虚、谨慎、积极求学等;道教主张的“贵生、养生、无执于世俗功名利禄,外得失之荣辱,遣欢戚之邪情,为利他之善事”;佛教主张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忘我利他,普度众生”等等。这些伦理道德,从形式到内容都与当代我国社会所倡精神文明相一致;特别是各教推崇的爱国家、爱劳动、爱和平、爱他人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道德,对于非信教公民也是完全适用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这些内容。
2.有些宗教道德从概念的形式上看很好,但其内涵则有浓厚的信仰主义因素,需要转变其内涵,赋予其新意。如:讲道德,按宗教的本意,道为“天道”、“神道”、“主道”,德乃“天德”、上帝或真主之德。葛洪《抱朴子内篇》中云:“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范铸二仪、胞胎万类、酝酿彝伦者也。”所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天,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依然要讲道德,也依然可以使用“得道多助”等概念,但一定要剔除其信仰主义的宿命论因素,赋予其新时代的理论哲学内涵。又如,藏传佛教历来讲“护国利民”,其意是讲借助于无边的佛法,藏传佛教具有极重要的社会功能。而今天江泽民同志题此四个字给扎什伦布寺,却赋予了它全新的道德内涵:要求宗教界努力加强自身建设,爱国爱教,坚定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正道,维护社会安定,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庄严国土,利益人民,要继续前进而不要倒退。套用一句俗语,这也是“旧瓶装新酒”罢。这种经过合理转换内涵的宗教道德概念,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3.有些宗教道德,从形式到内容都已过时,根本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格格不入,应该弃之不用。如:各种宗教中那些信仰主义的禁欲主义的伦理道德,那些散发封建主义臭气的歧视妇女的道德说教,什么“存天理、灭人欲”,什么“夫贵妇荣”等等,既不合社会主义时代精神,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应该扫入历史垃圾堆。又如,有些外来宗教过于强调依信仰划分善恶敌友,将宗教信仰置于国家、人民的利益及法纪之上,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容易混淆敌我,做出令亲痛仇快的社会不良行为,亦应注意扬弃。
纵观今日世界,现代西方文明精神正在走向颓废,走向虚伪。他们口口声声高喊“人权”,却念念不忘大搞霸权主义;口口声声大叫“平等、民主、自由”,却大搞种族主义、强权政治、纵欲主义、自由主义。“西方文明”所滋生的种种社会问题日趋严重,走私贩毒、卖淫嫖娼、黑社会势力、恐怖主义活动、贪污腐败、道德沦丧……越来越猖獗。与西方相反,我们的祖国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一日千里地进行社会主义伟大的建设事业。“宗教无小事”。为充分调动广大信教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我们必须努力做好宗教工作,必须全面准确地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正确认识宗教道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一环。
注释:
①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
①b 江泽民1996年1月24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见1996年1月25日《人民日报》。
②b 《论语·季氏》。
③b 《论语·颜渊》。
④b 《孟子·尽心上》。
⑤b 参见牟钟鉴:《中国宗教与文化》,第33页。
①c 牟钟鉴:《中国宗教与文化》,第1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