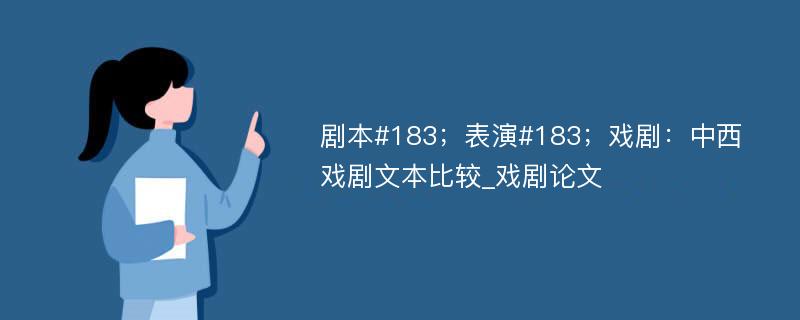
剧本#183;表演#183;剧场:中西戏剧文本观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剧场论文,剧本论文,戏剧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二十世纪的艺术批评中,“文本”无疑是一个使用广泛而又往往使人费解的概念。从语源上看,“文本”(Text)是指版本、正文及相对于注释、考订而言的原文。由此而派生出艺术的文本批评对于对象本身的关注以及为探本求源从事关于原文的考证与校勘。逐渐地,“文本”成为代表作品意义的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内含显示出一部艺术作品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有机的意义世界;不同的版本、不同的阐释就代表不同的意义整体。将“文本”概念引入剧论,对于拓展戏剧阐释空间来说,应该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文本”概念的多义性对应的正是戏剧本体阐释的多样性。“戏剧文本到底是什么?”亦即,戏剧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在哪里得以体现的?戏剧阐释和批评的“原文”或依据何在?对这类问题的不同回答正显示了不同的戏剧文本观念的各自的立场和方法。在中西戏剧创作和批评的实践中,概而言之,大致可归纳出三种类型的戏剧文本观:(一)以剧本作为文本,(二)以表演作为文本,(三)以剧场作为文本。这三种戏剧文本观在中西戏剧史上的演变及其差异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剧本之作为文本:文学性的推重
以剧本作为文本即所谓“剧本乃一剧之本”的观念由来已久且广有影响。在西方,剧诗的观念即把戏剧作为诗之一种,在亚里斯多德《诗学》中就已确立,(却也出于后人对亚里斯多德的误解。这一点容后详述)直到别林斯基在“诗的分类”中还把戏剧与抒情诗、叙事诗相提并论。因而所谓戏剧便只是剧诗人(剧作家)的创造,其本性只在于合抒情性诗的主观性与叙事诗的客观性于一身。剧本作为文学,其题材、主题的选择与提炼,人物性格的展示与描绘等本质上与史诗、小说等并无二致,只是在情节结构、语言表达等方面有着自己的形态特征。一部戏剧史也便只是剧作家与戏剧文学的历史。从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到易卜生、契诃夫,不管他们的剧作的搬演形式有怎样的变化,他们或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追问与展示、或表现出对于人物性格的丰富深刻的描绘、或表现出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揭示;也不管有些剧作是否有过成功的演出,如维克多·雨果的《克伦威尔》等,它们在戏剧史上的地位都不容怀疑。
在中国,也曾经有“词乃诗之余、曲乃词之余”的观念。作为“词余”的戏曲似乎争得了一个与《诗经》、《楚辞》一脉相承的文学正统地位。金圣叹甚至将元杂剧《西厢记》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及《水浒》等并称为“六才子书”被誉其为“天地之妙文”[1]王国维也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为理论前提而推崇宋元杂剧南戏。这对于那种奉诗文为正宗而鄙视戏曲、小说的传统成见无疑有着纠偏补缺的意义。然而,“以文律曲”在中国戏曲史上却并未能成为主导性的观念。因为它并不足以解释戏曲的本体性。
同是以剧本作为文本,强调文学之于戏剧的重要性,在中西戏剧史上却形成了不同的戏剧文学范式。西方戏剧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形成了一套以冲突律、鲜明的悲喜属性和严谨的闭锁式结构为特征的文学范式,并在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这种范式虽经中世纪的长期湮没却不失其光辉。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近现代戏剧无不承其恩泽,历经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以至自然主义的嬗变而一脉相承。在冲突律方面,体现为从命运冲突、性格冲突到社会冲突以至心理冲突的发展;在悲喜属性方面,悲剧和喜剧历来界域分明;只是到了启蒙主义的市民戏剧兴起之后,狄德罗倡严肃喜剧,二者之间才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融合。在剧情结构方面,从索福克勒斯到易卜生基本上都是从矛盾冲突最趋紧张处入手,经“发现”和“突转”将冲突推向高潮,最后走向结局,形成一种完整紧凑的结构模式,(其极端形式当是斯克里布等所制造的“佳构剧”)。这种戏剧文学范式二十世纪以来不断受到挑战和反叛。比如,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戏剧在文学性上主张表现人的更加隐秘的内心世界和本能欲望(梅特林克的所谓“静态剧”理论就主张取消戏剧的动作和冲突);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反对制造幻觉的代言,注重史诗性叙述,追求“陌生化”效应(或曰“间离效果”),认为戏剧不应诉诸情感而应诉诸理性;荒诞派戏剧更以“反戏剧”的面目出现在主张抽象变形以揭示生活的荒谬性,其剧本已蜕变为没有情节发展,没有人物性格甚至没有动作本身而只有某些抽象意念的舞台展示和象征。虽然如此,却并没有造成西方戏剧文学范式的完全倾覆。而在象尤金·奥尼尔那样一些二十世纪杰出剧作家的作品中仍有着西方传统戏剧范式的卓越体现。
相比较而言,中国戏剧文学的发展却有着一个明显的范式的转型。传统中国戏曲的文学成就以宋元杂剧、南戏和明清传奇为代表,其相应的理论阐释虽相对晚熟,但也自成体系、自备一格。宋元以降,有不少卓识之士对戏曲文学的本性有独到的阐发。如明代的徐渭、李贽、汤显祖、王骥德,清代的金圣叹、李渔、孔尚任等。特别是李渔在《闲情偶记·词曲部》中从立主脑、减头绪、审虚实、重机趣、语求肖似、即景生情诸方面对戏曲的文体特征和创作原则的论述已相当完备。到了清末民初,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以“自然”和“意境”来揭示以元杂剧为代表的戏曲文学的本体特征更是相当深刻的理论总结。它们显示出戏曲之文学性不离以抒情写意为特征的中国文学传统而与西方戏剧文学大异其趣。“曲”所体现的歌舞体式决定了戏曲在讲唱文学直接影响下的独特的叙事方式和结构方式。它不讲究情节的曲折多变、冲突的尖锐复杂而追求总体上的神理、意趣、韵味、境界。这种古典式的戏曲文学范式的形成,与清中期以后各地方戏的兴盛并不合榫,且在近代中国的巨大的社会危机中又难以趋时求变。于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西方近现代以写实主义为主导的戏剧文学范式的鼓吹与引进,一种新的戏剧样式——话剧便在中国诞生了。话剧的文学性正体现为以写实的而非写意的手法、以接近生活的本来面貌的对话和行动而非歌舞化的体式、以鲜明的悲剧或喜剧的品格而非传统的神韵格调反映社会人生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在现代中国的启蒙与救亡的变奏中发挥其张扬个性、开启民智、教育大众的作用。这种话剧文学样式的形成相对于传统戏曲文学范式的凝滞,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京剧和各地方戏文学性的相对贫弱无疑具有历史转型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戏剧文学从此得以与小说、诗歌、散文并列成为四大文体类型。戏剧成为新文学营垒中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
中西戏剧文学范式的差异和演变表明:不同的文学传统和文化背景中的剧本文本观不仅有着不同的内涵,在古今戏剧庚续的过程中也并非一成不变,而且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还必然相互影响、不断渗透,不是走向一统,而是走向共存。从而,一方面,以剧本作为文本并非是将戏剧归入某种单一的文学模式,象“五四”戏剧论争中以胡适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那样,他们以“国民文学”、“社会文学”、“写实文学”以及“人的文学”为号召,从西方戏剧文学模式出发,在猛烈批判中国传统戏曲的同时,极力张扬并引进以易卜生为代表的近代欧洲写实主义戏剧,认为后者才是唯一的“真戏”。另一方面,以剧本作为文本也不是将剧本孤立起来,定于一尊,以剧本取代戏剧,以至仅仅从读解剧本中来寻求戏剧的意义,以戏剧文学史的描述来代替对戏剧史的把握。因为,剧本毕竟不是全称意义上的戏剧,剧本的文学性不能代替其戏剧性。
事实上,“剧本文本观”的形成与剧本意识的自觉分不开,而剧本意识的自觉乃是戏剧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没有成功的剧本,确实难以有真正的戏剧繁荣。然而由此却产生了这样一个历史的错觉,仿佛只有创作出成熟的剧本,才有真正的戏剧。于是,剧本的重要性得到充分的肯定,以至强调、提升到“一剧之本”的地步。同时,“剧本文本观”还与戏剧批评的操作策略有关。戏剧作为一种活生生的艺术,其瞬时而直接的观演交流方式决定了戏剧批评的特殊性。戏剧批评往往很难全面地重建对象,尤其是古代戏剧,实际上是不可能恢复当时的观演情形。所以,戏剧批评(包括戏剧研究)所面对的便只能是戏剧的文学样式——剧本了。对剧本文学性的分析和推重便成为戏剧批评的主要内容。唯其如此,中西戏剧史上的“剧本文本观”不仅作为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有其历史的局限,而且更多的与戏剧批评的人为因素有关而有着观念的误置。
(二)表演之作为文本:舞台性的强调
戏剧史的研究已经证明:早在戏剧文学产生之前便已有了戏剧的存在。这就是在规定情境中的演员的当众表演。这种表演最早可以追溯到某些原始巫术礼仪之中,如古希腊的酒神祭典和中国的古傩祭礼。而当它们实现了从娱神到娱人、从驱魔镇邪、祈福延年到演示故事的转变,最初的戏剧便诞生了。并且在戏剧艺术发育成长的过程中,正是由表演而吸附了其它多种艺术因素。比如,为规范表演而有文学底本,为突出表演节奏、强化表演效果而有音乐舞蹈,为显示表演背景而有舞台美术、灯光等。换言之,正是以表演为中心而有机地综合了其它多种艺术因素。由此而产生了一种以表演作为文本的戏剧观念。这种戏剧文本观以表演为旨归,强调戏剧应作为“活”的艺术“立”于舞台之上,戏剧的价值体现在演员与观众的直接的审美交流之中;从而评判一部戏剧的优劣得失也主要基于对舞台表演的分析之上。以表演作为文本的观念仍可从亚里斯多德那里找到它的思想源头。亚氏强调悲剧是“行动的摹仿”,[2]“摹仿的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他总结出的所谓“悲剧六成分”既有偏于文学方面的“情节”、“性格”、“思想”,也有偏于表演方面的“言词”、“歌曲”、“形象”。虽然现存的《诗学》残篇主要是从“诗的艺术”方面立论,偏重于情节、性格、思想,但于表演他也不曾忽视。他把“行动”作为戏剧艺术的核心,并指出须借助人的动作、言词、歌曲、“形象”来表达,已明显肯定了表演的意义。并且,他着重指出:“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亚里斯多德把“形象”置于“六成分”之末,称其“最缺乏艺术性,跟诗的艺术关系最浅”,与其说是他对表演,不如说是他对表演的一些外部技术手段的轻视。他认为表演的主要任务是摹仿行动,而不是炫耀面具和服饰。对亚氏的误解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对他及古希腊传统的重新发现、传译及诠释中产生的。由于古希腊悲剧表演的不可能重现及表现新的时代精神的需要,卡斯特尔维屈罗在《亚里斯多德<诗学>的诠释》中着重论述的是戏剧的题材、语言、目的等。至于表演则仅强调舞台条件和观众意识的限制,要求行动(情节)、时间、地点的整一。这便是后来古典主义戏剧奉为金科玉律的“三整一律”。亚氏作为“行动的摹仿”的表演经卡氏的诠释在剧本文学中被加以具体限定,实际上也就有意无意地取消了表演的创造性和主导性。于是,剧本文学及其中的“性格”、“思想”、结构等便逐渐取代表演而成为近代欧洲戏剧观念的中心。后来虽然如狄德罗、黑格尔等也有关于表演艺术的一些论述,但欧洲毕竟晚至十九世纪后期才出现成熟的体系化的戏剧表演理论。
与西方的情形不同,东方戏剧较早地体现出表演艺术的自觉。印度的《舞论》和日本的《风姿花传》都以对表演艺术的独到论述见长。中国古代曲论对表演的强调更是比比皆是。王骥德指出:戏曲应“并曲与白而歌舞登场”,“其词格俱妙,大雅与当行参间,可演可传,上之上者也;词藻工,句意妙,如不谐里耳,为案头之书,已落第二义。”[3]李渔也指出:“填词之设,专为登场。”登场敷演,是戏之为戏的根本,否则只能置诸案头。优秀剧作家应该“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4]王国维更确切地指出:“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5]在歌舞化的体式中表演故事是戏曲艺术的本体性所在。“歌舞”、“故事”与“表演”三者不是先后彼此的关系,而是三位一体。舍其一不足以言戏曲。较之亚里斯多德的“悲剧六成分”说,王国维从另一方面比较合理地解决了表演与剧本文学之间的内在矛盾。如果说,在亚氏那里表演是从属性的,是为了“摹仿行动”,须服从情节的安排、性格的描绘,那么,在王国维这里,表演即是其自身。它合故事(内容)歌舞(形式)于一体。戏曲剧本须适合表演才能献诸场上。所以,戏曲表演有其自身的主导性与创造性。应该指出,王国维已明显受到西方近代戏剧观念影响,但他的戏曲表演观则主要是与王骥德、李渔等一脉,是由中国戏曲自身的传统所决定的。在中国古代,“戏”“剧”的语源即具有表演的意义。“戏”,《说文》:“从戈”,戈者,兵也。清俞樾认为有“角力”之义。“剧”(劇)由“虎”、“豕”及表示利器的“刂”组成,“表示两匹猛兽或猛兽那样凶猛的对立双方龇牙格斗的情景”。[6]因而“戏”“剧”所显示的就是角力、杂技、歌舞、游乐之事。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优伶的记载也远远早于戏曲文学的产生,如优孟、优施等。他们以谐趣娱人,逢场作乐,即兴发挥,并不必有所本,也不拘于某种现成的格式。在宋元以前的百戏、歌舞、杂剧中,优伶表演完整的故事,即便不少见,也是比较不自觉的。正是由于表演经验的长期积累,歌舞表演相对早熟,宋元之际一俟与讲唱文学相结合,便诞生了中国戏剧史上高度成熟的戏剧形态——杂剧和南戏。而宋元杂剧南戏、明清传奇主要是以剧本形态流传至今,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难免产生这样一个错觉,似乎只有这些灿烂的戏剧文学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但即便如此,表演艺术自宋元以来在中国戏剧的发展中仍是脉络分明。仅就表演声腔体制而论,从元杂剧的一人主唱到南戏及传奇的各角色的对唱,从曲牌体到板腔体,从四大声腔的更替到花雅争胜、京剧形成,生、旦、净、丑等不同的角色行当的运气行腔、程式套数,各有渊薮,声腔体制的嬗变既有继承庚续,又有创造革新。很明显,象京剧这样以演员为中心、以唱念做舞为特征的十分烂熟的演剧形态,如果没有上千年无数艺人的锻造琢磨、传承积累是不可想象的。与表演艺术的传承相一致,中国古代演剧观也较早走向成熟。宋元之前姑且不论,仅元一代就既有专录剧作家作品的錘嗣成《录鬼簿》,也有专论宋元戏曲演唱体制和方法的燕南芝庵《唱论》和以记述戏曲演员为主的夏庭芝《青楼集》,可见并不因为戏剧文学的成就而掩盖了人们对演剧艺术的看重。甚至胡紫山《黄氏诗集序》系统论述演员“九美”,[7]已是相当成熟的表演艺术论。嗣后,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潘之恒《鸾啸小品》,特别是王骥德《曲律》、李渔《闲情偶记·演习部》等对戏曲表演艺术多有精深的论述,形成以“传神写意”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演剧理论体系。[8]
相对于剧本文本论,以表演作为文本强调舞台形象的创造之于戏剧的重要性体现了对戏剧艺术本体认识的趋近。把戏剧视为一种表演艺术较之把戏剧视为一种文学艺术当然更接近戏剧的本质;演员作为戏剧的直接载体以其言词(包括演唱),行动演示故事较之剧本以语言为载体间接地以代言体叙述故事也自然更属于戏剧的原生态。所以,作为表演艺术,“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动作是支配戏剧的法律。”[9]作为戏剧表演的“动作”在中国戏曲中体现为以“唱念做打”熔为一炉的歌舞化体式,配以适度夸张的服饰、脸谱等,表现出高度“写意”化的风格,而与西方戏剧表演经逐渐分化,以生活化的言语、行动来表现的“写实”倾向大异其趣。所以,中国戏曲表演以高度程式化为特色,承认“作戏”,突出“虚拟”,讲究“传神”。而西方戏剧表演虽有“体验”派与“表现”派之分野,却均以生活的本来样式为准的,在“摹仿生活”的原则下,前者更注重内在心理的依据,后者更讲求外在形态表现的自我控制与自我监督。或者说,前者强调的是表演中的情感投入,后者强调的是表演中理智的参与。在演剧形态上,中国戏曲以表演为文本,形成了以演员为中心的演剧体制(即所谓“角儿制”),演员表演成为舞台的主体,成为戏剧艺术魅力的核心,并且决定了戏曲“听戏”、“看角”的独特的审美方式和数百年口传心授的艺术传承方式。而西方戏剧,尽管也有其表演艺术的传统(如中世纪的民间演剧和意大利即兴喜剧对表演的重视),但即使在产生了比较系统的表演理论之后,演剧形态仍以遵从剧本的规范为主,表演艺术并未能取得相对独立的发展。近代以来,西方戏剧舞台形象的创造似乎更依赖于包括灯光、舞美等在内的镜框式舞台的设计,以此在舞台上营造逼真的生活空间。这种写实性空间中的演员表演难免受其拘限,使得表演仅成为舞台艺术整体的一个部分而已。
基于以上讨论,可以说,表演文本观在中国戏曲的艺术实践中有着更多的体现。它强调“戏”在台上,而不只是在剧情的悬念中。因而演员在舞台上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成为观众的观赏对象。不过,其畸形发展则是对“技”的偏嗜压倒对“艺”的品鉴。戏剧批评也偏于对舞台表演的感受体验,容易流于“印象式”而缺乏理性深度。而在西方戏剧中,表演理论相对晚熟,其舞台表现并未形成对表演的特别偏重。虽然在近代以来的一些商业性演出中也曾出现过“明星制”(并且影响到电影),但其舞台表现的主导方面仍是为展示剧本的规定情境而综合演员表演、舞美设计等各种艺术手段于一体,剧本的规范性与舞台监督的协调性仍普遍地得到尊重。所以,到了二十世纪,以西方戏剧为先导很自然地走上了一条追求整体性的道路。
(三)剧场之作为文本:整体性的追求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梅宁根剧团第一次采用导演而使他们的演出轰动欧美剧坛。后经法国戏剧家安德烈·安托万所创办的自由剧院的正式采用,导演制得以在现代戏剧中普遍确立,从而开始了一个新的戏剧时代。导演制强调以剧场意识为核心,把戏剧演出作为一个艺术整体来处理,要求舞台上所有演员的表演、布景、灯光、道具和音响效果等都服从于一个总体的构思;并且把观众作为剧“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使其参与到戏剧艺术的整体创造之中。由此而形成了二十世纪以来的一种以剧场作为文本的戏剧观念。
剧场作为一种物理空间古今中外都是存在的,只是在不同形态的戏剧中各有差异。从古希腊悲剧的圆形露天剧场到西方近现代有镜框式舞台与间隔有致的座席排列的封闭式剧场,从中国古代的勾栏瓦肆、歌台庙会到现代实验小剧场,其特点和功能显然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有演员和观众的共同参与,有一种共时性的、不断被创造的艺术空间。也就是说,作为戏剧的本质要素的剧场,可以不必有正规的舞台和座席,不必有灯光、布景、音响设备,甚至不必有一般的建筑设施,但必须要有演员和观众双方的参与和交流。从古老的驱魔娱神的傩戏到现代诸多的街头剧、广场剧都有着哪怕最原始最简单的剧场的存在。
然而,何以在导演制兴起之后“剧场”才开始观念上的自觉,成为一种艺术追求的目标呢?
艺术史上有一明显的事实:某一门类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往往与该门类艺术的自觉分不开,而艺术自觉又依赖于艺术自身的积累。中西戏剧史上,“剧场”虽古已有之,但如前所述,在人们尚普遍地把戏剧视为“诗”(文学)或视为“戏”(表演)的时代,“剧场”的意义和功能并不为人们所认识,自然也就处在戏剧观念之外。导演艺术的兴起正是基于剧场意识的觉醒。英国戏剧家戈登·克雷早在1905年就指出:戏剧这种艺术既不依附于剧作家的剧本,也不依附于以明星演员或“演员—经理”为中心的表演,而是在导演的统一构思下,通过剧场艺术家的通力合作,创造出完整、统一、和谐而又富于诗意的独立的剧场艺术。[10]这里,剧场显然不再是仅仅作为一种由舞台和观众席所构成的物理空间,而是一个包容了剧本、表演、舞美及观众的交流反馈等多种因素在内所营造的艺术整体。而剧场艺术的核心和灵魂便是导演。所以,戈登·克雷特别强调导演应该“具备多种品格于一身,以便成为剧场的能手”。[11]导演之于剧场,犹如将军之于战场。将军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必须基于他对于战场的了如指掌,知己知彼,运筹帷幄,方能决胜千里。同样,导演须对剧场规律有深刻的理解,在读解剧本的基础上,以激发观众的欣赏热情为旨归,组织演出,调动灯光、音响、舞美,协调一致,才有可能创造出整体、持久、和谐的剧场艺术。
现代导演艺术的发展正是以剧场作为文本而显示出独特的艺术追求的。在安托万的自由剧院,戏剧成为生活忠实的写照,舞台和观众之间被一堵透明的“墙”即所谓“第四堵墙”隔开,展示在观众面前的是各种真实的生活中的人物场景、矛盾冲突及其一切细微末节,它要求观众置身剧场,从大幕开启就沉浸于剧情之中,而不应有丝毫的松懈与走神。安托万指出:导演作为“戏剧演出的忠实的仆人”,“不仅应当使剧情合于结构,而且要决定它的真实个性并创造出它的氛围。”[12]这种“氛围”真实而自然,对观众来说足以造成一种生活幻觉。因而这种自然主义的剧场艺术往往由于追求逼真精细而失之于琐碎。到了莫斯科艺术剧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导一种心理现实主义戏剧,强调剧场艺术的整体性,强调通过演员出于其“有机天性的下意识的创作”以达到对生活的心理深度的再现;用真实的情感体验去吸引、感染观众,激发观众的共鸣。从而使现实主义的剧场艺术取得了高度的成就。
与安托万及斯坦尼的旨趣相左,莱因哈特和梅耶荷德以表现主义、象征主义为鹄的而别开生面。莱因哈特是位剧场的革新家。他接受了瓦格纳的“总体艺术”的观念,不但善于将剧本台词变成戏剧舞蹈中的动作、节奏和情调,勇于实践当时尚处于争论之中的阿庇亚的灯光布景设计,而且在观演关系上努力寻求能直接打动观众感官的戏剧样式,从古希腊戏剧到东方戏剧他都有所借鉴。莱因哈特的剧场“没有幕布分隔着舞台与观众席”,“没有细小的、勉强约束而不能互通的舞台镜框来分隔戏剧动作和外在的世界,动作自由地流过整个剧场。”“可以说,密切的接近就是这个剧场的新的特征。它把观众变成戏剧动作的一部分,抓住他全部的兴趣,加强了他所感受的效果。”[13]梅耶荷德更直接构成了斯坦尼的对立面,他反对以舞台再现生活而张扬“剧场性”,以“假定性”、“象征性”取代对生活的体验摹拟。他从意大利即兴喜剧和东方戏剧(包括中国的京剧)中汲取灵感,以“构成主义”的布景方法和“生物力学”的演员训练方式组织一系列演出。他的剧场不用幕布,没有镜框,“对观众的呈现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他坦白地把观众作为观众,同时又把他们作为戏剧的一种活力。这戏剧是要整个的剧场、舞台、座客共同来创造的。但它们对于观众的呈诉,是不用人生再现的直接语句,而是藉暗示,经过象征表达的情绪,从抽象所引发的智慧,这一些间接的媒介来呈诉于观众的。”[14]梅耶荷德对剧场艺术的多方探索虽不及斯坦尼体系完备,但对于现代剧场的革新却极具启发意义。
布莱希特史诗剧的倡导与实践也是在剧场艺术的革新探索中脱颖而出的。它与亚里斯多德戏剧传统的背离,与其说在剧本文学方面,不如说更重要的是在戏剧总体观念特别是在剧场意识方面。史诗剧在观演关系上强调“间离效果”,努力破除生活幻觉,认为戏剧不应煽动观众热情,而主要诉诸观众的理智,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从而“把观众变成观察家,唤起他行动的意志”,并“促使观众做出抉择。”[15]史诗剧的剧场意识主要体现在“布局”上。“采用适当的陌生化手法解释和表现布局是戏剧的主要任务。”“布局”是“一切动作性的过程的总结构,其中包括构成观众的娱乐的‘直陈’和冲动”,“布局由剧院全班人员——演员、布景设计师、脸谱制造师、服装设计师、音乐师和舞蹈设计师共同来解释、创造和表现。”[16]这里,布莱希特的“布局”观念显然已不是亚理斯多德所谓的“情节的安排”的意义,而是意味着在剧场艺术的总体上对亚理斯多德传统的全面超越。布莱希特正是以其独具一格的编导实践对现代戏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十世纪西方戏剧中在剧场艺术方面锐意创新并产生了巨大反响的还有阿尔托的“残酷戏剧”和格罗托夫斯基的“质朴戏剧”。阿尔托期待并营构出一种“神圣的戏剧”,主张戏剧应该回归原始神话,崇尚巫术和礼仪,应该象“古代的通俗戏剧”那样,“直接用心灵来领悟和体验”。这种戏剧不依附于文学,而是运用戏剧自身的语言(不仅仅是对话,甚至包括歌舞、杂耍等),运用多种古老的艺术手法,展示“生命的痉挛、创造力的升腾以及人对文明传统的抗拒”,并且强烈地刺激观众,从而造成令人战栗的残酷的剧场效果。[17]这便是“残酷戏剧”的由来。残酷戏剧在剧场形式上取消了台上台下的界限,把整个演出的场地,包括观众席,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来处理,使得观众不再是安静地坐着看戏,而是全身心都受到感染和冲击。传统的戏剧“结构”在这种剧场空间里得以“解构”,甚至所指与能指相互易位。正是沿着阿尔托的路子,格罗托夫斯基倡导“质朴戏剧”,强调观众与演员的直接“对峙”(Encounter)。戏剧的本质不在于剧本,不在于音乐、布景、灯光、道具等,而只在于演员的“当众表演”。必须剥夺戏剧的一切非本质的东西,使戏剧真正成其为戏剧。“质朴戏剧”主张舍弃演员身体以外的一切外在条件,仅仅以其深刻细腻、自我通透的形体动作与观众一起创造具体的剧场时空。演出就是在剧场时空中制造演员与观众的心灵潜层的精神冲突。[18]
无论人们怎么评价,二十世纪以来具有先锋性和实验性的剧场探索对于促进戏剧艺术的发展来说还是功不可没。特别是小剧场戏剧在抵御商业化侵袭、抗衡随着现代技术发展而日益发达的影视剧方面,坚持本体,独僻蹊径,显示出戏剧自身的魅力,以致风靡欧美并波及东方剧坛。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以来,以剧场为文本的艺术探索也正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基础上相互汲取、相互融合的产物。从莱因哈特、梅耶荷德、布莱希特到阿尔托,他们或多或少都从日本的能乐、中国的京剧以至印尼的巴厘剧中受到过启发,汲取过营养。而东方剧坛,日本新剧和中国话剧的形成,中国京剧和在传统歌舞伎基础上产生的日本新派剧的剧场艺术的革新,无不受惠于西方戏剧观念的引进。这种互惠式的以剧场为核心的探索与革新正契合了十九世纪末叶以来“新戏剧”思潮对于戏剧艺术整体性的追求。它一方面体现为对西方“剧本文本观”的积极扬弃,另一方面体现为对东方戏剧(如中国京剧)的“表演文本观”的汲取与超越。导演的艺术不再唯剧本为是,而是从剧本的选择及体现中进行新的阐释和再创造。导演对剧场整体意蕴的开掘,不再仅仅依靠剧本的台词,而更倚重演员的形体动作,以至综合运用音乐、灯光、服饰、舞美造型等艺术手段。也就是不再仅仅依靠文学语言,而是更注重发挥戏剧自身的综合魔力,以独创的戏剧“语言”来表达对世界的理解。并且不是单向度的教化或取悦于观众,而是把观众作为剧场的一个有机因素,调动观众主动地参与到戏剧中来。从而使剧场不再是空间意义上的“场”,而是在观演的互为主体中,在多种力量的协调下,形成情感交流往复、充满“诱意”与“解放”(河竹登志夫语)的艺术的“场”。这样,对于剧场艺术整体性的追求就不是趋向“单一化”,而是寓丰富性于其中。二十世纪中西戏剧演出手法、形式、风格的多样化便是明证。
总之,“戏剧文本”不是一个静态的、已成的概念。无论是对于创作还是对于批评,“戏剧文本”所代表的立场的设定和视野的界阈在中西戏剧史上往往是动态的、开放的,其意义内涵处在不断变化、不断增生之中。所以,我们对“戏剧文本”的把握也就不应该持固守和胶着的态度。本文便是旨在通过比较描述以揭示中西戏剧史上三大戏剧文本类型的差异与得失,而没有也不准备对“戏剧文本”这一概念作出具体界定。这不仅是出于写作策略上的考虑,而且也可以说正是本文的一个“立场的设定”。
注释:
[1]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
[2]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下引同。
[3]王骥德《曲律·论剧戏》
[4]李渔《闲情偶记·词曲部》
[5]王国维《戏曲考原》、《宋元戏曲考》
[6]河竹登志夫《戏剧概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7]胡紫山《紫山大全集》卷八。
[8]参见夏写时《论中国演剧观的形成》,《戏剧艺术》1985年第4期。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64页。
[10]参见戈登·克雷《论剧场艺术》,中译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译者的话”;第25页。
[11]参见戈登·克雷《论剧场艺术》,中译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译者的话”;第25页。
[12]安托万《在第四堵墙后面》,《西方名导演论导演与表演》,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
[13]引自张庚《戏剧艺术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105页。
[15]诺里斯·霍顿语。转引自张庚《戏剧艺术引论》,第106页。
[16]布莱希特《关于革新》和《戏剧小工具篇》第六十五、七十节。《布莱希特论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页、第34-37页。
[17]参见张仲年《戏剧导演》第十章,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8]参见张仲年《戏剧导演》第十章,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