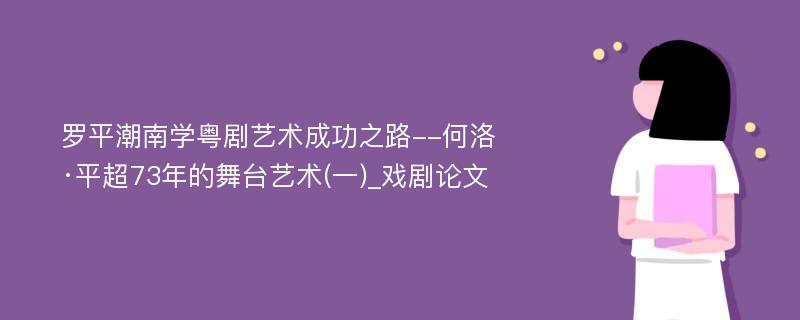
罗品超南派粤剧艺术成功之路——贺罗品超舞台艺术七十三年〔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论文,粤剧论文,成功之路论文,十三年论文,舞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粤剧艺术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革。有许多著名粤剧艺术家在这个历史性变革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使粤剧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鱼龙混杂的不稳定发展状态中,拨正了发展路向,走向高层次,走向了世界,获得了真正的“推陈出新”。在其间,有一位亲身经历了粤剧艺术七十多年盛衰变迁的表演艺术家罗品超先生。他以其卓越的艺术实践,在粤剧改革的时代大潮中乘风破浪,写下了承前启后发展新粤剧的瑰丽篇章;并正以85岁的高龄,在赴美定居后,依然精神焕发,致力于振兴粤剧,并以粤剧作为文化使者,积极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为此,他受到了欧美以及东南亚广大炎黄子孙和友好人士的崇敬,受到了国内及国外各界的好评。罗品超是近世粤剧发展中继承与发展南派文武生艺术的大师,是长青不老的粤剧革新的传奇人物。岂止“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壮哉罗品超!
罗品超先生在戏剧美学上的成就,为世界戏剧界所公认。由此,有必要从美学欣赏的视角,对罗品超的南派粤剧艺术进行探析。
罗品超成为一位粤剧南派文武生的艺术大师,有他七十多年来迂回曲折发展的艺术道路。我想先从我所了解的罗品超的艺术道路或艺术历程,提供一些简要的回顾,或许有助于大家认识这位大师的历史地位和美学价值。
中国拥有丰富的民间戏曲剧种,各个剧种又都有其不尽相同的历史发展过程。近百年来,许多戏曲剧种仍然植根于深受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影响的农村,因而它们除具有人民性及民间艺术色彩较浓之特色外,封建意识和小农经济等因素,无可避免地对它们产生直接影响,决定了其文化品位,其发展无可讳言是封闭式的而不是开放式的,变革较为缓慢。“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戏曲的变革作用较微,对此鲁迅亦曾站在展望新文化发展趋向的高度,对某些旧京戏不适应新时代文化思潮,有过评议(可惜他来不及跟进对中国旧剧改革,作出更系统探析)。二十年代末,左翼文化运动营垒中电影戏剧界的先驱田汉、洪深和欧阳予倩等先生,率先把视野从中国话剧领域,进而拓展到京剧、桂剧及粤剧。这是中国戏剧史上,戏曲文化领域开始受到新文化运动曙光照耀的历史时刻。这对于粤剧的变革,对于罗品超的成长,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我们决不应忽视。与当年粤剧界许多伶人不同的是,罗品超(同时也有两广戏剧人士黄鹤声及陈酉名、卢敦、李晨风等先生)有幸进入了欧阳予倩先生为所长的广东戏剧研究所歌剧和话剧的行列,成为该所下属学校的青年学员,接受了田汉、洪深和欧阳予倩等老师的教诲,从理论到实践,接触到左翼戏剧运动新思潮的新信息。罗品超以一个青年戏曲艺人,在文化低潮的年代,投身在以反帝反封建为旗帜的中国新文化运动行列之中,大量吸纳了先进的文化观念,以及以古今中外文艺戏剧宝藏来滋养自己。进步戏剧美学观的种子,无疑已由欧阳予倩老师种植在罗品超的心坎中;自然,种子仍待日后发芽。
我对罗品超先生早期从艺的以上印象和评析,在陈酉名兄的《罗品超表演艺术的价值取向》〔2〕及《广东戏剧研究所的前前后后》〔3〕中,得到了切实的印证。
在《罗品超表演艺术的价值取向》中,有些忆叙,有力地说明了罗品超当年接受了进步文化思潮的熏陶,奠定了他的进步戏剧美学观。酉名兄说,在欧阳老师排《杨贵妃》时,请了西洋舞蹈家排野趣群舞,以表现安禄山部落,排《皮革马琳》时,亦有纯真民族乐舞,罗品超都很专注学习。“粤剧功底,京剧气势,西洋舞风,对他(罗品超)的后来表演艺术,都可以看得出或隐或显,有所影响;但同时也感觉到,他没有改变姓氏,还是岭南一朵清馥的‘琼花’。”
酉名兄又在《广东戏剧研究所的前前后后》中记述,当时戏剧研究所属下演剧学校,中国话剧的先驱田汉受聘为名誉校长,洪深为校长。田汉为学校写了几副对联,其中两联为:
(一)三百载余韵流风,读莎翁乐府名篇,高举人生明镜。
六十年销歌歇舞,集岭表艺林才俊,重开戏剧先河。
(二)歌场战场,记曾为义战驰驱,瘦狗岭边留热血。
天听民听,准备替吾民喊叫,回龙桥畔试新声。足见当年罗品超所接受的教育,具有多么浓烈的时代感与民主精神。罗品超在话剧《小英姑娘》中成功扮演反帝的工人王皮鞋匠,是他早期的演出作业,但对他其后艺术道路的影响深远,不可估量。
之后,罗品超难舍粤剧,决意留在南方而没有随欧阳老师去上海发展。于是自三十年代初到1951年约二十年的漫长日子里,罗品超在粤港及新加坡等海外各地,进行了粤剧领域及电影影坛双栖式的艰苦的艺术探索。在艺术实践中他既得到正面的经验,也体验了不少负面的教训。可贵的是,他在思想操守上二十年如一日,始终不忘新文化运动在他心灵上种下的“根”,他无论在艺术生涯顺境或逆境中,始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遵循欧阳予倩及田汉等老师给他指引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路向。他在美学上既没有丢弃戏曲(粤剧)的现实主义美学传统,没有随波逐流让艺术堕入庸俗化或市侩化,他同时亦寻求在银幕上及舞台上向现代化试步的阶梯,谨慎地开展他的粤剧艺术的变革,使他所参演的粤剧,在风云幻变政治气候冷暖无常的动乱年代中,不脱离前进的时代步伐,依然根植于人民的审美喜爱。或者可以说,这一段的罗品超,在艺术上是冷静的,但决不是保守的或盲动的。由于罗品超较长时期奔走香港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文化艺术崇尚开放的地区演出粤剧,又曾同时投入相当精力主演过近八十多部粤语影片(尤其象《玉面霸王》、《洪熙官》、《我若为王》、《黄飞鸿》及《方世玉打擂台》等义侠武打片),罗品超具有与其他戏曲艺人不同的从艺经历,他的戏剧美学走向趋于开放,趋于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结合。
我有幸正式结识罗品超先生,是在1952年冬,他归国后随广东省代表团晋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戏曲观摩会演。是年我也是刚从香港归国不久,那时正在中央宣传部学习,我被邀去帮忙乐队伴奏,得与平易近人的名演员罗品超先生结交。当我从陈酉名兄处进一步知道罗品超过去曾从师欧阳予倩老前辈等经历时,我对罗品超的美好印象更为深刻,自此开始了我们之间四十五年的珍贵友谊。罗品超在1952年晋京,得以再拜欧阳予倩老师师门,获得了已身为新中国戏剧运动领导人的欧阳老指引;而翌年,我亦奉调入欧阳老师为院长的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担任教职,我与罗品超先生亦可算同门同师之谊!由是,我对欧阳老师给予罗品超美学思想影响的理解,自然有机会更为深入了。
如果说1952年之前二十年,罗品超是在艺术上处于漫长探索的时期,在1952年之后,则是在新中国党和政府“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改革方针照耀下,在欧阳老师的悉心教导下,艺术上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即自觉地进行粤剧艺术革新的时期,他翱翔在一个广阔的天地。欧阳老师给他的指引,依我看来,就是:“立足传统,开拓视野,紧跟时代,服务人民,求真善美,发展粤剧。”罗品超以一个精力旺盛、朝气蓬勃的粤剧革新者的雄姿投入工作,成绩斐然。
(二)
自1952年全国第一次戏曲观摩会演至“文革”之前,粤剧艺术的改革成绩显著,经历了巨大的进展。自然,也常常因为对粤剧传统历史之有关认识与评估,在许多当事人中间,各有不尽相同的观点;而且处理问题,时有失误,无辜伤害过人,因此前进的道路并不是笔直的,有顺畅时候的愉悦,也有争议时候的不快甚至严重阻梗。如1956年《山东响马》被错误打击之事即一例。罗品超身处粤剧改革的前列,自然甘苦备尝。但是,他是一个品性十分纯真的人,也是刚直不阿的,他坚持改革,不随波逐流。他象田汉和欧阳老师前辈那样,只要他认准是合乎真理的事情,他会不声不响,忍受着种种非议,埋头埋脑去做,务求出实践成果并以其成果来证实他的美学理想是正确的,是合乎人民的利益的,是合乎艺术发展规律的。罗品超在1952年到1965年(即“文革”前夕)的十多年来,在粤剧艺术革新中,可以说是心怀大局,坚韧不拔,不计较个人得失,思想开放,严于实践,建树良多,功不可泯。他不但在个人艺术上努力革新,还带动了粤剧界一代又一代的艺员,共同合作,汇集了大家的才智,一起投入艺术革新。他的艺术思想日趋开放,他是力求使粤剧传统与现代美学思想相结合的先行者之一。
在这个新时期,罗品超自觉地在艺术实践中贯彻了“三并举”和“两条腿走路”的繁荣戏曲艺术、丰富粤剧上演剧目的方针。他不是片面地盲目地对传统剧目进行“复制”照搬;也不是粗暴地另起炉灶,背离粤剧本剧种的艺术规律,在移植借鉴兄弟剧种剧目时把南派艺术丢光,一式照抄北方剧种的艺术程式,改使粤剧姓“京”,或改姓“非驴非马”之类,面目全非。他以发展的观点,同时作改编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及探索现代戏的努力。他立足于南派粤剧艺术的根基,探索新时代新粤剧的新舞台演艺美学规律,使粤剧既保持其传统色调,又有多样化的发展。他所主演的剧目既保高质量,又丰富多姿,在数量上每年都出几部新戏,十分可观。这就是大家都记忆犹新的他领衔的珠江粤剧团年代,及其后他参加广州市粤剧团和广东粤剧院领导工作年代总的演艺趋向。罗品超在新时期逐步形成了个人艺术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罗品超在创演粤剧现代戏及继承发展传统南派粤剧艺术这两个方面的卓越贡献。在这两个方面,无疑他得天独厚,具备个人优越条件,积累有前二十年的丰富的舞台与银幕两个领域之经验,在新时期的奋力艺术实践中又进而取得了新的成果。在当年各兄弟戏曲剧种中,这两方面兼而得之者并不多见。以我有限的学识,我联想到的恐怕可以京剧北派名师李少春先生(京剧的文武老生)和粤剧南派红星罗品超先生(粤剧的文武生)相提并论,南北辉映,各尽其美。因之我早在当年已有“南罗北李”之颂誉;现在想来,我觉依然贴切。当然,建国后各剧种名家林立,不胜枚举,这个比较只是就一南一北两位有卓越成就之文武生与文武老生的演艺特色有类似处而言,并无突出夸张某一二位艺术家之意;顺此说明,只为有利于比较研究而已。从一个观众或研究者的审美角度看,我特别喜爱李少春的《白毛女》、《摘星楼》及《红灯记》等戏;也喜爱罗品超在《红花岗》、《春香传》、《五郎救弟》、《山东响马》、《林冲》以及《荆轲》、《山乡风云》等戏中所创造的完善艺术形象。
与其说在珠江粤剧团之时,罗品超主演或主持现代戏《小二黑结婚》、《雷雨》及《祥林嫂》(还有移植朝鲜戏《春香传》),一如某些剧种那样对戏曲编演现代戏只不过是光凭一股热情的尝试;不如说罗品超在五十年代初率先编演现代戏,是在默默地验证他前二十年在舞台与银幕上扮演“时装戏”之经验;可以说他在艺术思维上是较为开放大胆的。他在继承话剧《小英姑娘》,电影《太平洋上的风云》、《叱咤风云》、《黄飞鸿》、《洪熙官》、《我若为王》等演出的“传统”技法。我认为罗品超已开始着眼于对现代人物形象的深化,早超越于尝试了。我相信我的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因为我自五十年代中叶调入文化部中国戏曲研究院,在梅兰芳院长领导下工作。我的分工与中南剧种联络较多,得常到广东了解戏改现状,有幸经常观赏罗品超的演出并面聆教益。我自信对罗品超表演的印象与观感,是从实际出发的。在此不能不提及,因在建国初期,为广东粤剧三十年代那段发展历史的特殊性(即所谓“商业化”的滥编滥演倾向),在某些理论层面上,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面评估,导致对粤剧三十年代时期曾经演出的现代题材戏(受文明戏影响较深),或香港粤语片的表演技艺经验,被笼统贬损,而不是倡导有分析地从积极方面去总结汲取。以至有的艺术家当年在面对新现代戏时,明知是在轻车熟路,可“继承”自己过去的某些有价值的演艺经验,但却理不直,气不壮,绝不敢公开讲出真话,甚至甘愿割断历史,“避之则吉”,唯恐自我批判之不够深刻!据我所知,例如直到1960年,具有丰富表演经验并演出过不少时装戏的粤剧大师马师曾先生,应邀赴京参加“梅兰芳表演艺术研究班”讲学时,他示范演出粤剧《斗气姑爷》片断,讲稿亦十分小心谨慎,字斟句酌(当时他与林小群在班内示范演出,我因兼任该班辅导员曾被指派去协助马先生备课,并为他筹备演出服装及借用粤式铜水烟袋等小道具)。比起当时上海沪剧总结传授现代戏《星星之火》表演经验,毫不忌讳其深受文明戏演艺传统之影响,并形成了沪剧现代戏表演的一套娴熟技法,粤剧就似乎“英雄气短”,感到怅然若失了。也许这可能是本文题外之话,且问题后来已解决。不过,我前面说及的罗品超五十年代表演现代戏时是在默默地验证他前二十年在舞台与银幕上扮演“时装戏”之经验,如果我的观感不谬,那便可以说明,罗品超在新时期的表演艺术,是不曾割断自己的“传统”经验,且加以发展的!因而他自《小二黑结婚》和《春香传》,到《红花岗》,到《山乡风云》的形象塑造,都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独成“一格”,而不是偶而一试,搞话剧加唱,或描红学写“人之初”。
这“一格”是什么?我认为就是罗品超的南派粤剧表演技艺,在演出现代戏方面亦具有的独特艺术风格。这在他扮演的《红花岗》一戏中手车工人张胜,和《山乡风云》里本是贫苦农家出身、曾误入歧途但终于弃暗投明反霸革命的黑牛,艺术风格表现得尤觉突出。如果拿罗品超所塑造的舞台形象张胜及黑牛,与六十年代差不多同期出现的“革命样板戏”(全国划一钦定的“铸模”模式)之“中心”人物的表演风格比较(在此仅作风格之比较),就可非常清晰地感到罗品超在那个年代,不媚俗,能坚持独特的南派风格,确实可贵。我们常议论所谓“南腔北调”。我认为“南腔”就应是“南腔”,“北调”就应是“北调”,方可各显其美,观众也都可接受;但如果硬把“南腔”变成“北调”,或者将“南腔北调”放在一起,硬要观众把榴梿(东南亚热带水果,有奇味)拌炸酱面吃,当然会引出观众欣赏的逆反心理,不免反胃呕吐。我想说的是,罗品超在那段晦涩的日子里,并没有摁着观众脖子硬要他们吃“榴梿拌炸酱面”,确属可敬可佩,确实显出了他在艺术美学上的造诣日趋深厚。
论述至此,重反正题。我认为在这个时期,更值得重视的是罗品超坚持全面地在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各个方面,对南派粤剧艺术进行了精心的继承和发展。他的舞台艺术,全面闪烁着南派粤剧艺术的迷人风格。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能文能武的、博古通今的、色彩鲜明的南派粤剧文武生。
自1953年罗品超和少昆仑、文觉非整理及主演《山东响马》起,罗品超倾力发掘南派粤剧艺术传统,已见端倪。虽历重重坎坷,几起几落,但他并未改辕易辙。1957年前后,他精心排演《梁天来》、《黄萧养》及《罗成写书》、《五郎救弟》、《虎头牌》等戏;1959年后又在《林冲》、《荆轲》及《平贵别窑》等历史剧和传统戏的反复磨炼中,更有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南派粤剧文武生的表演及唱腔艺术,风格渐见完美。下面我将粗浅探讨罗品超先生的南派粤剧艺术风格之特征和美学表现形态。班门弄斧,仅向专家和内行艺术家请教。
(三)
通过我对罗品超舞台艺术的审美,我想以下列五句话来概括我对他的南派粤剧艺术风格的美学印象:
力度浑厚,拙大雄放;
棱角鲜明,大朴不雕;
气壮神闲,抑扬畅达;
时代精神,民族筋骨;
南派泰斗,文武状元。
罗品超的表演力度浑厚,给人一种刚劲粗犷的美感享受。他的台风拙大雄放,塑造人物动感较强,形体动作却不随意夸张。他更多着眼于力度的表现,系列身型(如入窑震抖靠旗、独脚跨枪以翎子醮血写书)的功夫扎实,迅即使人感到人物的形象具有一种沉甸甸的力量。正所谓拙大雄放,拙而雄劲。看来他是善于贴近生活,来设计舞台动作的;不为追求形体浅层次圆熟优美,而故作大量技巧修饰。其实以他的丰富艺术经验和娴熟技巧,他是可以把舞台动作“磨”得更“好看”的,但他不取此法。所谓大巧若拙,有时反在拙上见功力。例如在《蝴蝶杯》的“藏舟”一场,他饰演的田玉川并没有追求在舟中虚拟表演之精美俊逸的身段,他之形体动作极其简朴。我想他是为了更巧妙地衬出渔女凤莲复杂的心情起伏,衬托出此时此刻两位陌生男女,在黑沉沉的江中共对凤莲老父惨死尸骸的沉重气氛。我想这就是大巧若拙,拙反见精也。我们在《山东响马》及《黄飞虎反五关》、《荆轲》中,都常常欣赏到罗品超这样的南派粤剧风格。如《山东响马》的“打和尚”,每场均打断一根木棍,且有“铲椅子”等绝技。在《荆轲》中,小处如绕道观众席上场时,不时反抬右手,反抚所负宝剑的剑柄,动作虽轻微但具见力度。大处则如“刺秦”一场,荆轲一直取舞台正中位置,动作很小,却显其大巧若拙的功力。罗品超气静神清,站如铁塔,他正面面对秦始皇暴虐如狼的张牙舞爪,其侧则助手秦舞阳慌张失态,极不稳定,这两者皆反衬出荆轲的拙大雄放。他不是在应付艰难局势,而是力求宾夺主位,首先以气势压倒强敌,在气宇间大见荆轲的智谋侠义之风。秦皇乍然靠前观图,荆轲巍然不动,待他轻轻贴近秦皇耳朵吐出一句“好地方”,便即把秦皇吓得怯然后退两步。此处表演更觉精彩,力贯全场,真是壮哉荆轲!
罗品超的南派粤剧艺术风格特色,具现在他的表演和唱念技艺之中。自然,他的表演和唱念技艺(通常说的是戏曲各艺术流派的“四功五法”,即“唱、念、做、打”和“手、眼、身、发、步”的组合运用),是从属于他对人物形象的独特视角、深层理解和精心之演绎设计的,从属于他的美学理想——贴近新时代潮流与发扬南派传统巧妙相结合的。
我拟再以《荆轲》一剧为例,剖析罗品超的美学理想(或美学追求)。罗品超在此剧中,曾经过多年琢磨,塑造了义侠荆轲的完美形象。形象的美感在于气势,在于力度,在于粗线条泼写,在于棱角鲜明,大朴不雕,在于粗犷而又洒脱,在于狂放而不野乱,在于重义轻生而又深具人文精神。他的美学理想在于表现荆轲抗秦献身之壮志。依照他对人物的独特视角所及和深层次的理解,于是他安排了系列富有南派风格的技艺设计,从人物内在到外部形态加以表现之。他在“狂歌”、“借级”、“易水送别”及“刺秦”等场次中,应该认为是以实带虚,以叙事带抒情,以主要人物际遇为主线,大量发扬了南派粤剧文武生表演与唱念艺术的特点,演出了香馥的南派风格!
必须看到,自“文革”后的近十多年来,罗品超眼界更加广阔,思想境界更高。他与导演紧密合作,对历史形象的视觉更加具有特色,他既忠于历史(不搞那种“时髦”的“戏说”历史),又站在新时代开放的潮头,从真、善、美视角反观历史人物的道德价值与历史取向,剖示其中对现代生活可能具有的某方面的积极意义。付诸舞台形象,引导观众从他所理解和演绎的历史形象中,获得美育享受,接受艺术美的熏陶,既拉近了历史也贴近了新时代。他不惜反复修订自己的艺术思维,成功地塑造了荆轲、罗成、林冲及薛平贵等形象。无怪这些形象都能常演常新,越演越美,为海内外观众所接受,好评如潮。至于罗品超是如何具体运用南派粤剧传统技艺于各部戏剧之中的,许多论文均有精辟之论述,在此这方面似可从略,不必重复细说。不过我仍须郑重引述周恩来总理对南派粤剧艺术的重要评价,藉以评估罗品超发展南派粤剧艺术风格之意义,亦可作为对南派粤剧传统简要的介绍,以利于下一辈的进一步继承与发展。
广东粤剧院原副院长林榆先生在《新珠谈粤剧传统艺术》〔4 〕一文中,整理记述了粤剧前辈武生新珠(原名朱晓波,1893—1968)生前所谈南派粤剧的精辟见解,此文有文献价值。新珠说:“南派师承于少林派,前辈演员经过勤学苦练,融汇变通、提炼美化成为舞台上的表演艺术和自己的武技。”“南派武打的花式很多,我知道的有手桥、刀枪、把子、一零八桩手、六点半棍、行者棍、双头棍、昂口刀、杀手锏、禅拐、佛掌、双鞭、单刀鞭、长线拳、花拳、连头、拦门寨(三叉)、双枪、锁喉枪等。”〔5〕新珠记述了1956 年他随广东粤剧团赴京演出,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时的情景:“他问我学过什么武戏,我说我学过南派的武戏。他很高兴,鼓励我们说,京戏打北派,粤剧打南派,这就是百花齐放,希望粤剧下一次来北京多带一些南派的武戏来。”(引文着重点是本文作者所加)这些记述,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南派粤剧是十分重要的。这又使我联想起在此时四年之后即1960年,罗品超和少昆仑、郎筠玉等著名演员参加我国国家级的准备赴印尼演出的一个艺术团,在北京彩排审查的情景。罗品超带去的南派折子戏有《醉打蒋门神》和《罗成写书》等,令人瞩目。记得当时我是参加组织和接待该团工作的,彩排了数场,有一场是在东四八条中国戏曲研究院四楼小礼堂(该团因当时国际形势关系,彩排后并未出访)。当时文化部领导茅盾、欧阳予倩、梅兰芳及张庚、周贻白等名家均参加审看,对罗品超的南派艺术一致赞赏。周总理的勉励,促使了罗品超对南派粤剧艺术的刻苦钻研。此事,酉名兄在《罗品超表演艺术的价值取向》中,已有叙述,在此不赘。
罗品超对南派粤剧文武生表演和唱念艺术的继承与发展,能达到崇高的境界,为世界所公认,其中有何经验可寻呢?
我认为有一个主要的经验是,他的艺术创造,不是象某些戏曲演出那样,每场戏都在“翻版”过去的演出模式,而是围绕形象的创造,不断更新(那怕是微小的更新)。他的每场演出都是一次创造。他扶掖了七、八代旦角演员,共同合作演出他的首本戏,对每一代旦角“拍档”,都是耐心引导,把戏重新排练一遭的。因此他与不同合作者同台,又有新创造。因此,他的演出常演常新,越演越美。我想归纳一下他的这方面的经验,俾作参考:
(1)罗品超创造南派粤剧艺术形象, 不是借人物之壳来表演技艺,而是每场演出都投入创造,务使形象保持全新,不是重复旧的,更不旧瓶装新酒。
(2)他的形象创造是有目的的,具有合目的性。 凡人物形象舞台行为的线索,思想脉络,都是如此,运用技艺而不玩弄技艺。
(3)他对任何形象的创造, 其设计都不脱离南派粤剧艺术的传统手法,不脱离粤剧特有的以实带虚、写实为主和多用分幕形式等艺术规律。他对南派粤剧艺术传统及其他中外艺术都有丰富的信息储存。他的艺术头脑象一个开放性的信息储存库。他随手拈来便可把信息加以重新组合,进行有限度的而不是滥取滥用的推陈出新。这个限度,就是不突然而来或不超越于当时广大观众的审美之约定俗成。由是,他取得了他的舞台艺术的艺术价值(相反假若没有限度,距离广大观众审美习惯太远,使观众不能接受新的约定俗成,便不能完成其舞台艺术的艺术价值)。
(4)他对人物是进行深层次的挖掘, 因此对形象的演绎时能具有深刻性和特异性。演绎形象时,他又做到了较好解决内容与形式的矛盾统一,因而能够产生美感。
(5)他还十分注重形式美与意境美的统一,即协调。 由于他与导演亲密无间地合作,所以这方面的成就显著。意境美是通过形式美来表现的,但形式美在某种情况下(如几个角色之间相互妨碍,或几段表演的份量失去平衡),不一定与意境美统一。两者协调,固然应有导演指引,然而更多的是由演员去制约。因为在戏曲舞台演出中,演员的行动是由演员即时直接制约的。在这方面,罗品超做得特别好,如《荆轲》中有许多群戏,都是由于他制约而获得形式美与意境美的统一的。他的做法是以意境美为主导,去创立形式美。广大观众通常都是因为感到形式美与意境美的统一,才开启了产生美感的心理条件,才能获得审美之愉悦。
以上只不过是我对罗品超南派粤剧文武生艺术的审美心得。罗品超先生的经验,仍有待进一步的总结和推广。
祝罗品超先生健康长寿,他的南派粤剧艺术长青不老!
注释:
〔1〕本文为作者1997年5月在广东省文联、广东省文化厅主办的“罗品超表演唱腔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2 〕见林涵表主编“金三角洲文化丛书”第一辑《罗品超舞台艺术七十三年》。
〔3〕见《中国现代话剧教育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本,第87页。
〔4〕引自《花蕊夫人/林榆剧作·论艺集》,花城出版社1995 年版本,第243页。
〔5〕据罗先生说,尚不止这些, 南派功夫在少林武术中皆可见其师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