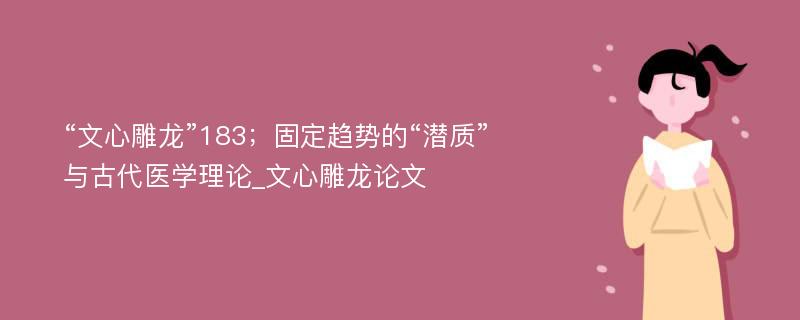
《文心雕龙#183;定势》之“势”与古代医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定势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3)03-0080-04
截至目前,对《定势》之“势”的研究涉及本源考证、内涵界定、特征辨析、原因探究、“势”与其他因素关系辨析、定势原则与方法探析、“势”论和“定势”价值地位考察等。研究视角有训诂学、语言学、兵法、政治学、书画理论、修辞学、现象学等,甚至有“影响”研究,对“势”及文心“势”论的认识不断趋于全面幽微,为研究文艺理论领域的“势”论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但也许是由于其理论内涵丰富多样、高深难辨,对“势”的理论认识和阐释仍然存在着朦胧含混、交叉缠绕、众口不一的状况,而且尚有忽略或者没有涉及之处,有待学术界进一步细考。
《文心雕龙》中所涉人身体的构成部分非一般之全,基本涉及人体有形、无形和生理、心理的各个重要方面,所涉医论的术语或句段更普遍存在,其全面的“身体医学比喻”,全然一个“活”的生命体叙事,不借助医学知识和理论几乎是无法企及的。《文心雕龙》把整篇作品作为一个和谐整一的生命体,把文学创作作为作家精神、血气、情志等抒发表现的结果(如苦虑劳情说、为情造文说、发愤说),认为作品优劣好坏犹如人的健康与生病,是和人的形、脉、气、血、五脏六腑、神、韵等各方面是否和谐流通、相生相制密切相关的。在《文心雕龙》中居重要地位的“势”亦在此之列,而在众多的研究中,尚无论文或者专著花笔力着重讨论《定势》之“势”与古代医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没有学者专门探讨“势”所蕴含的古代医学层面上的内涵。
关于“势”与医论的关系,已有人稍作涉及。彭建明指出,作者的生理年龄、劳惫程度影响血气精力,而产生气势的正负效应。他认为:“《养气》篇承王充的‘养气’之书十六篇而来,把养生延寿之学、古代医药的荣卫理论以及气功的腠理、胎息之说融为一体,指出写作文章应有通畅平静的心态,健旺清和的血气。”[1]贡巧丽、王晓芳则把“势”解释为文体的“症候”[2],但她们并未作深入观照,解出医论视角下“势”的独特内涵。
《文心雕龙》中各篇的“赞曰”都具有概括全篇的作用,《定势》篇的“赞曰”如是说:“形生势成,始末相承。湍回似规,矢激如绳。因利骋节,情采自凝,枉辔学步,力止襄陵。”形为生、势为成,二者是先后相承接的,是和谐一致的,像急流的回旋自然如圆规、像箭头的射出自然如直线一样自然而然。“赞曰”告诉我们两点:(1)势的自然性是全篇的总旨归,(2)势的形成是组成文章的内容、形式诸多要素因利骋节、自然合力作用的结果。
对自然之势的强调,涵盖全篇,学界已多有论述,无须赘语。而对和自然之势密切相关的“体”需要进一步来品味。《定势》篇开篇即说:“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此处的体之势是一种以情为根据、以体为依托的自然而成之势,进一步说就是“乘利而为制”之势,它“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是顺其便利而形成的。“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圆形的物体自然便于转动,方形的物体自然利于平稳,皆循形之便利,以自然的形之势类比体之势。在讨论模仿经书或《离骚》创作从而使文章自然呈现相应的势时,刘勰仍然用了比喻:“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仍然以形之势类比体之势。从《定势》篇普遍存在的以形之势类比体之势的意义上看,“形”和“体”是等同互换的。而刘勰这样的论述并不存在思维的混乱,恰是有其思维根源的。在古人眼中,一切都是生命化的,万物都可以人的生命化视角来审视,人也可以被物(富有生命的)化地审视。人们发现,自己“像他者中的一个实体一样在世界里”[3],这样,便建立起了古人论述过程中在人和物之间任意穿梭转换甚或类比的思维基础。正因为刘勰把文章视作和人一样自然而然的生命体,才有了他不断地拿物的形之势类比文(即人)的体之势的论述。所以体在《定势》中首先是指人化文学作品整个的生命体之体,其他含义皆由此生发引申而出。而势则是文学作品生命之体自然而然呈现或具备的一种整体效应、状况或特征等。
“体”与势“始末相承”是由哪些要素形成的呢?由“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是以绘事图色,文辞尽情,色糅而犬马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可知“体”首先含“情”和“文辞”。由“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密会者以意新得巧”可知“意”是为其一。“宫商朱紫,随势各配”,宫商音律和色彩搭配亦在其中。“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虽然势由规则和自然契机相参合,由音节和文采相杂糅而形成,但好比五色的锦缎,还要以各自的本色为底子。其中的规则强调的是体对势的相应的规定性,自然契机仍然强调的是势形成的自然而然,“节”和“文”则是构成“体”的组成部分。“刘桢云:‘文之体势实有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余,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谈,颇亦兼气。”结合紧接其后之文可知刘勰并没有否定“气”在形成势的诸因素中的作用,只是否定了刘桢对阳刚之气势的片面推崇。所以仅从《定势》篇来看,“体”包含情、气、辞、意、宫商、节、文、朱紫等。由体而成之势是为体势,但在“体”成势的过程中,还包括对定“体”的本色的遵循、对“杂体”的铨别和“随变而立功”。所以在《文心雕龙》中“体”并非指一,至少有时指构成“体”的要素,有时指已成经典可作规范的“体”,也有时指可作规范的“体”和随变而立功之“体”的合体。
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经典普遍认为,一个健康的生命体,应形全机能、气血充盛、经脉循行、荣卫顺畅、津液濡润,应言辞畅达、应答自如、言意相符、音声爽利自然、情思和悦不郁等,这样才是富有生命魅力和生生潜力的生命体。参考《文心雕龙》中其他篇章论述情、气、辞、体等的内涵及其在为文谋篇中的地位,从《定势》篇“体”之情、气、辞、意、节、文、宫商、朱紫等的状况,便可见出一个健康和谐、充满生命魅力的生命体,正应了“中国艺术的生命化特征,正是通过大量的‘气’论、‘势’论、‘韵’论表现出来的”[4]的论述。条贯和谐的生命整体是创作追求的崇高目标。统观《文心雕龙》全文,这种生命整体之美可以像人的个性一样多种多样、多姿多彩、不分优劣。健康之势或病势是生命整体所体现出的综合状况,是多样而复杂的。
“言势殊也”道出了势的多样性。有顺应自然、“并总群势”而成的“总一之势”,有雅势、郑势,有刚势、柔势,有奇势、正势,相对于总一之势而言,我们暂且把被兼通适用的刚柔、奇正等每个单“势”称之为“兼势”。刚与柔、奇和正是可以兼解俱通、随时适用的,雅郑则不可兼通,究其原因除了有刘勰征圣、宗经思想影响外,恐怕和刘勰受医学养生思想上求雅鄙郑,在利于养生的音乐、文学等方面崇雅抑郑以及在人物品评中无法对一个人的气质进行雅郑对立评判等不无关系。所以相互对立的雅郑共篇,则会形成与总一之势相离的“离势”。还有因“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以致陷入形式主义和因“趋近”、“适俗”而造成的“讹势”、“怪势”。虽然作为“势”的效应、美的奇正是不分优劣的,但文辞的奇正安排是有度的要求的。精心文辞要做到“执正以御奇”,避免“逐奇而失正”,类似于把“想彼君子”颠倒为“君子彼想”、把“衫同草绿,面似花红”反正为“草绿衫同,花红面似”的现象则是有害于“势”的,这种形式上的颠倒制造出意义上的混乱,就会造成“讹势”和失体之“怪势”,会导致“势流不反,文体遂弊”的文坛病变出现。中医讲,气血在十二经脉中从手太阴肺经始到足厥阴肝经终复又流注到手太阴肺经,如此流注,如环无端,一旦身体某些部位发生病变,则会出现气血阻滞,严重者甚至导致其流而不返,精气竭绝而亡。《文心雕龙》和中医理论在“流不反”方面的阐述异曲同工。《附会》篇所说“若首唱荣华,而媵句憔悴,则遗势郁湮,余风不畅”也是借用中医理论术语述说文辞使用不得力而带来的文势滞涩不通、郁结不调的病症。离势、讹势、怪势皆为“病势”,离、讹、怪作为重要的病机或病症术语出现于《黄帝内经》、《伤寒论》、《脉经》、《甲乙经》[5]等古中医文献中。比如《难经》“二十四难”中有六阳气俱绝则阴阳相离,阴阳相离则会出现腠理泻、绝汗出等气先死的征兆。由此也可管见刘勰在整个《文心雕龙》理论阐述中受中医理论影响的一致性、一贯性。文有“总一之势”,一篇之中,多种“兼势”虽可以“兼解以俱通”、“随时而适用”,但要“随总一之势各配”。“定势”正是既要做到任势,有总一之势,又要在兼解俱通、随时适用的独创时避免离势、讹势、怪势,实现自然之势。
学者普遍认同的“势”定而不定的特点与篇名《定势》之定有些微区别。定而不定之“定”是说凡成功的无病之文,都有与文体相应相伴而生的“势”,无一例外;“不定”是说“势”是“活的”,是丰富多样的,是可以“并总群势”、“兼解以俱通”、“随时而适用”的,不是不可通变因革的。《序志》言“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以御群篇”,《尔雅·释诂》有“图,谋也”,《小雅》也有说虑、图皆谋也。由此可推知《定势》即图势,《定势》之“定”指的是“势”的选择、创作生成的过程和结果,“势”定而不定是“图势”过程中所要遵循的指导原则。“势”定得如何,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整篇作品的成功与否。
循体而成、随变而立功之势是如何定的呢?首先要“任势”,强调定势要顺其自然。在此基础上,方可“并总群势”、“兼解以俱通”、“随时而适用”。“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言势分刚柔而无优劣之别。自然之道是中医理论的基础,强调健康生命体是符合阴阳平衡、刚柔并济、五行生克制化等自然之道的,治则方药也都讲自然之道,它强调将病体调整至阴阳平和、自然而然的和谐健康状态。《黄帝内经》将人分为刚型人、柔型人,并指出刚型人易致刚症病,柔型人易致柔症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不但病机、诊法讲辨别刚柔,治法、方药配伍亦讲以柔制刚、以刚制柔、刚柔并济等辩证论治。刘勰“刚柔适用”即以中医刚柔之用类比文学之势的刚柔“随时”调配安排。
中医认为人体有十二正经和奇经八脉。一方面十二正经遍布全身,在周身作上下循环运动,关涉整个生命体里里外外的生死荣华,诊脉也主要以十二正经为据来辨明疾病和死生;奇经八脉不入十二脉,不拘于十二经,“人脉隆盛,入于八脉,而不环周,故十二经亦不能拘通也”[6]。十二正经有表里、阴阳的相配和脏腑的络属,奇经八脉不直属脏腑,又没有表里配合关系。这些是奇正不关的一面。另一方面十二经气血盛满则会灌注于奇经八脉,并且奇经八脉的许多分支分散于全身上下,和十二正经经络相互贯通,共同作用于全身,此时奇正又相和谐共融于整个生命体。由此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理解刘勰所说“奇正兼通”了,也可以明白刘勰为什么要强调“执正以御奇”、反对“逐奇而失正”了。
中医重色,认为不同的内脏反映于外,会使面部甚或身体相应部位的皮肤呈现相应的本色、真色,同时相应的肤色还会因季节、气候的不同而发生正常的生理性变化,而不同部位的病症亦会使身体相对应部位的皮肤呈现出不同的病色。故依据个人本色,望面色、舌色、爪甲色、眼色、身体皮肤之色等可以判断病位、断证诊病。如《灵枢·五色》有:“青黑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说明不同颜色反映疾病的不同性质。色诊中望色从来不离辨泽,《灵枢·五色》说:“五色各见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浅深;察其泽天,以观成败;察其散抟,以知远近;视色上下,以知病处;积神于心,以知往今。”中医认为面部皮肤之色泽是脏腑精气外荣的表现:面色荣华润泽为脏腑精气不衰的表现,属无病或轻病;面部色夭、晦暗枯槁缺乏润泽则为脏腑精气已衰,是重病之候。如《素问·五脏生成》所述白色的正常面色为“如以缟裹红”,其善色(轻病色)为“如豕膏”,还有润泽度,其恶色(重病色)为“如枯骨”。又如《黄帝八十一难经》第二十四难有手太阴肺经气绝则会出现皮枯毛折,手少阴心经气绝则脉不通、血不流,色泽去。再比如中医认为舌部色泽荣枯是衡量肌体正气盛衰的标志之一,是估计疾病的轻重和预后的根据等。色之泽是生命体健康和谐、富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五色正常俱备,荣华满面,皮肤、爪甲等润泽无瑕是为健康之体、如玉美颜。
刘勰《定势》之势要“各以本采为地”,强调了本色对于势的重要性,而且这种“本色”是由“节文互杂”而成的,和中医学意义上的“本色”是类比关系。对本色的这种强调,在古代文献中除了中医,较多的便是画论。但画论更多的仍然是从绘画的逼真、生命性角度出发强调其色、泽的。同时刘勰也强调“朱紫”诸色的和谐搭配,要“随势各配”。从“讲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看,此“新色”已非仅含色彩之色,而是由情、辞、气、意、节、文、宫商、朱紫等和谐构成的富有创新性的文章生命体的“成色”,是色的生成的升华。由此可见“色”在刘勰论文体系中的重要性和他对色的创新性生成的强调。刘勰在强调“色”的同时,他也没有忽略色之泽。他认为“势实须泽”,并且针对陆机先是“尚势而不取悦泽”,后又认识到须取悦泽,作以“可谓先迷后能从善矣”的评价。健康生命体具有正常的新陈代谢和无限生成的潜力,也正是出于对生命健康美、和谐整体美、创新生成之潜力美的强调,他强调色的创新性进而强调势之泽采。
不论是从任势还是从刚柔、色泽或总一或兼通、随时适用等论定势,都可见定势、势的真正内涵。
如何鉴“势”?《知音》言“观千剑而后识器”,《神思》言“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指出郁、乱之文病,须得博见、贯一诊治。医家要求习医者要博见多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四书五经、诸子方略、史书文集皆通,从医更要一以贯之,不可“受师不卒,妄作杂术”,更要多看多听多习,取象比类,多多积累经验,由意达悟。和刘勰所论恰相契合,观、博见是整体上的为文、鉴文能力培养之法。在具体诊法上,《难经》“六十一难”说:“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巧。”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对于批评对象不仅常常是“望而知之”[7]的,望、闻、问、切作为中医诊法也被刘勰改造、化用于创作之中。在中医诊法视角下,我们可以找到《文心雕龙》中所诠释的诊文断症的总办法,即《知音》篇之“六观”。它既是《文心雕龙》批评的总方法,又是鉴势的具体之法。结合诸家注译本,借鉴黄维梁对“六观”进行的符合刘勰衡文精神的修饰增益性的“现代化”解释[8]的精神,又对位体、宫商、置辞、事义、通变、奇正进行中医学视角的符合刘勰衡文精神的“修饰增益”。
在四诊中,望诊包括全身望诊(望神、色、形体、姿态等)、局部望诊(望头面、五官、躯体、四肢、皮肤等)、舌诊、望排出物、望指纹[9];闻诊大致包括听声音、语言、呼吸、咳嗽、肠鸣、呻吟和嗅气味等;问诊一般包括问现病史、既往史、个人生活史(生活经历、工作地位变化情况、精神情志、饮食起居、婚育状况)、家族史等[9];切诊即脉诊,通过切脉可揣知人全身的脏腑功能、气血盛衰、阴阳虚实等综合状况。借此类比解读“六观”之内容,望位体、置辞,闻宫商,问事义、通变,切奇正,并不牵强。望位体指审鉴作品之“体”如何,其“体”之势是不是自然之势、总一之势,兼势怎样,有否离、讹、怪;望置辞即审察作品的文字锤炼、色泽构成和修辞、文采等,便于进一步审鉴体之势的整体状况或特点。闻宫商即听音律节奏是否符合雅正的规范(刘勰重雅轻俗,更倾向于把雅正作为规范)。问事义即叩问、辨析作品的题材、情理、意义等;问通变即叩问、辨析作品题材、情理、意义、修辞、“体”、势等方面的继承和革新。切奇正即切循、辨别势之或奇或正或奇正兼解俱通而成的总一之势的整体状况或特点。总之“六观”是通过对人化文学生命体的整体和局部的共同关照来鉴势的。
中国古代不像西方有严格细密的行业、专业划分,各行业或专业少有壁垒门户之见。无论何行业,皆可谈为文之理。文学批评对其他行业、学问的吸收、兼容更是广泛而充分开放的,故带来文学理论的不断衍生、创新。现代中国文论所面临的“失语”、“滞后”等症,与当今专业化所带来的条块分割、相对封闭不无关系(当今通识教育亦与我国古人为学基础之广厚相去甚远)。当今人们对古代文论的许多术语、理论难以理解,是否因尚未找到其内涵的直接理论来源所致,也值得作进一步考究。因为鉴于中国古代人化批评传统的客观存在,以及中医作为古代士人特别是儒家士人知识储备中自然组成部分的史实,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大量的理论、范畴都和医论脱不了关系,所以对医论、艺理相互关系的全面探究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我们也不可拿医论做僵硬、呆板的随意比附,以免带来文论领域更多的混乱和不必要的争议。
(2011年7月初稿,经多次修改,2012年5月定稿。2013年1月再次修改。诚挚感谢恩师党圣元先生在论文的关键环节所给予的反复修改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