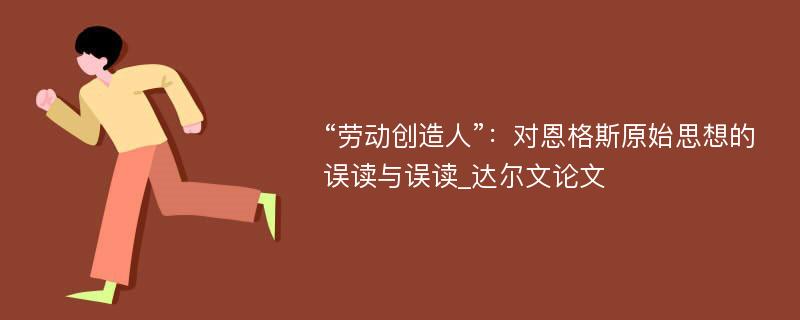
“劳动创造了人”:对恩格斯原创思想的误读和曲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误读论文,创造了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通行着一种说法:“劳动创造了人”是恩格斯提出的科学论断。该说以古人类学家、中科院院士吴汝康为代表,他以1932年、1950年和1955年出版的三个《自然辩证法》中译本(以下简称前三个中译本)对恩格斯关于劳动与人的起源、生成和形成关系的观点译文为依据,在《人类的起源和发展》(1965年)中说:“自从恩格斯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指出人类能够从动物状态中脱离出来的原因是劳动以后,人类学的研究又有了很大发展,收集到的资料愈来愈丰富,完全证明了恩格斯的科学论断”[1]67。由此,“劳动创造了人说”作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一直被视为圭臬,陈陈相因,不仅至今仍为大多学人接受和沿用,而且还充斥于诸多学科领域,成为一个基石性的原理和命题,影响了几代人。
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恩格斯关于人的起源、生成和形成的思想,发端于1876年《自然辩证法》第二束中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以下简称《作用》),完善于他晚年期间,在1891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第4版。解读《作用》、《起源》及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文本,笔者发现:
1.恩格斯主张的“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550中的“人本身”,与“劳动创造了人说”中的“人”,是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是指介于猿与人之间的“过渡性生物”——“正在生成中的人”[2]552-553,在质的规定上仍属于动物。后者是指“从动物状态中脱离出来”[1]67的原始人,为现代人的祖先。所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不等同于“劳动创造了人”。
2.恩格斯对人猿相揖别的过程作了完整概括,并依次提出了三个反映从猿到人转变的概念:“攀树的猿群”[2]555、“正在生成中的人”和“完全形成的人”[2]554。他认为,从猿转变为人,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统一”[3]18的结果,“劳动”只是其中的一种组合因素。在适应和遗传引起“攀树的猿群”机体变异的意义上说,劳动创造的“人本身”生命形态——“正在生成中的人”,“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4]45。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只有实行“杂乱的性关系”[4]45,从而改变交尾期雄者间为争夺交配权而进行的打斗方式,以此保证“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4]45。这种过渡,以扬弃杂乱的性关系代之而出现的血缘婚姻家族——人类的“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5]20为终结,标志着人的完全形成。
显然,“劳动创造了人”非恩格斯本意,而是后人附加在他名下的一个错误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告诉我们,他们理论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6]73,理论的内容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7]241,理论的落脚点是实现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8]649。不言而喻,这座人学大厦矗立的基石是他们关于人的起源、生成和形成的思想。由是而论,正本清源,拨开层层迷雾,颠覆“劳动创造了人说”,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现实意义。
二、前三个中译本误译了恩格斯观点
原著的翻译是研究的基础。如前所述,“劳动创造了人说”的恩格斯著作根据是1932年、1950年和1955年出版的《自然辩证法》中译本。那么,这三个中译本是怎样译述恩格斯观点?译文是否表达了恩格斯的本意呢?搞清楚这两点,有助于厘定“劳动创造了人说”的真伪。
笔者统计,截至2009年12月,《自然辩证法》的中译本出版过七个。视版本译文的异同,前三个为一类,后四个为另一类。
第一个中译本是1932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杜畏之本。该译本《从猿到人》的开篇段落(下同,笔者注)对恩格斯观点的译文是:在从猿到人的进化中,“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劳动创造了人类”。[9]415第二个中译本是1950年北京的三联书店出版的郑易里本。该译本《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对恩格斯观点的译文是:“我们甚至可以在某一种意义上说:劳动创造了人类自己。”[10]189第三个中译本是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曹葆华、于光远、谢宁本。该译本《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对恩格斯观点的译文是:“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说: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11]137可见,这三个中译本对恩格斯观点的译文基本上相同,即“劳动创造了人类”。
第四个中译本是197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本。该译本《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对恩格斯观点的译文是:“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2]149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许良英先生指出,第四个中译本是“对1955年版本的译文略作了一次校订而成”[13]369。经过比照可以看出,第四个中译本订正了第三个中译本“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的讹误(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第五个中译本是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于光远等译编本。该译本《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对恩格斯观点的译文是:“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3]295由此可见,第五个中译本修订了29年前第三个中译本对恩格斯观点译文的舛错,而与第四个中译本相吻合。正如译编者在《后记》中说:“平时翻阅通常大家使用的这个译本时(指第三个中译本——笔者注),我觉得译文还存在一些缺陷,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动手校译和重编。在1973年到1974年之间,我才有可能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根据1962年狄茨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二十卷所载原文,对以前的译文从头到尾重新校译了一遍,每页都有不少改动。1977年我请范岱年、陈步同志再对照德文本和英译本帮助我把这个校正稿又仔细校了一遍。经过这样的校译,译文有了较大的改进,表述得更准确了些,也减少了一些译得不太恰当的地方。”[13]519第六个中译本是1995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该译本对恩格斯观点的译文与第四个中译本一致,在此不赘。如同《编者的话》所说:“收入选集的全部文献都根据原文重新校订。”[7]2第七个中译本是2009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该译本对恩格斯观点的译文同于第四个中译本和第六个中译本。应当强调的是,“为了保证译文的准确性,课题组根据最权威、最可靠的外文版本对全部译文重新作了审核和修订”。[2]1由是而论,这是目前能够准确表达恩格斯原创思想的权威译本。
综上所述,前三个中译本对恩格斯观点的译文不足为训。因此,“劳动创造了人说”也就失去了原著依据,是不成立的。
三、“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不等同于“劳动创造了人”
虽然前三个《自然辩证法》中译本误译了恩格斯的观点,也就意味着“劳动创造了人说”失去了原著依据,但是,随着后四个中译本的面世,学术界对修订版恩格斯观点的译文解读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为“肯定说”。例如,黄庆在《劳动创造了人》(1972年)中说:“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概括了当代的科学成就,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光辉著作,科学地论证‘从猿到人’的历史过程,创立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伟大理论。他指出人类所以从动物界分化出来,是由于劳动的结果;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起着决定的作用。”[14]58蒋孔阳在《美学新论》(1995年)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讲劳动创造了美的同时,又讲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因此,人和美都是劳动创造的。”[15]18吕世荣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命题》(2011年)中说:恩格斯“明确地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他依据当时的材料,叙述从猿到人发展过程的主要阶段,说明人这一物种是劳动的产物”。[16]二为“质疑说”。例如,朱长超在《是劳动创造了人,还是劳动选择了人?》(1981年)中说:“恩格斯在《作用》一文中试图用劳动创造人这一命题来否定达尔文学派关于自然选择使猿变成人的论述,但是,恩格斯在文中对劳动的定义和劳动创造人这两个命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矛盾。”[17]44龚缨晏在《关于“劳动创造人”的命题》(1994年)中说: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命题是不符合生物学研究成果的,是缺乏生物学基础的”。[18]38汪济生在《“劳动创造人说”的现代科学审视》(2003年)中说:“就‘劳动创造人’这一学说而言,应该说比较系统完整的表述,出现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本著作中……‘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是明显地带有政治色彩的学术命题。从今天实证科学所达到的水准来看,在讨论人之成人的最根本原因时,它已明显地失去了能起界定作用的学术价值。”[19]255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笔者以为,上述“二说”的症结,皆在于把“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等同于“劳动创造了人”,曲解了恩格斯的本意。
那么,何为恩格斯的本意?又应当怎样解析它呢?
(一)恩格斯本意揭示
恩格斯关于劳动与人的起源、生成和形成关系的表述,始见于《作用》文本的开篇段落。那么,恩格斯的本意是在怎样的语境中确立的呢?为了准确地揭示和把握,兹将这一完整段落摘录如下: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550
从这段完整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贯穿其间的关键词是“劳动”。劳动不仅是财富源泉的构成要素、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从猿到人的转变中也凸显了作用。在此,恩格斯以简练的语言,精辟地阐发了劳动与财富、劳动与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以及劳动与人的起源、生成和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而显露出他的本意。
首先,如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抨击拉萨尔之流的谬论:“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20]298一样,在《作用》中,恩格斯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和立场。在他看来,所谓“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不仅在理论上是偏颇和荒谬的,而且它以“政治经济学家说”的面目出现,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此,如果不加以戳穿,也就等于承认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现实对立中,无产阶级不需要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从而掌握生产资料,仅凭出卖劳动就可以获得财富,摆脱贫困地位。显然,这是资产阶级学者在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剥削工人合法化做理论上的辩护,对蓬勃发展的国际工人运动来说,无疑是十分有害的。因此,恩格斯针锋相对地驳斥说:“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
其次,人类生活基本条件的构成,其学理依据在于自然科学的生命学说。恩格斯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成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20]422自我更新也就是新陈代谢,即同化、异化作用:摄收和分解养料,存活、成长;主体自我复制,生育子代,以此维系种的存在和生成进化。自然界只有一种生命,生命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人作为地球上生命链接的高级形态,与动物不同之处,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6]82。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显现了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人类生活基本条件的构成,换言之,也就是人的生命生产的组合方式,内含“劳动”与“生育”两个要素。在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6]80。38年后的1884年,在《起源》中,恩格斯把他与马克思阐发的上述思想,概括为“两种生产理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4]16。就“劳动”与“生育”的相互关系而言,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其功能在于解决“吃、喝、住、穿”这个人的第一需要,因而称之为“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虽然如此,如果舍弃了“生育”这个要件,即人口的蕃衍,劳动本身则不能构成人的生命生产的全部条件。其理据在于,由于生育的作用,使人类得以子孙绵延,后继有人,并且通过世代的接续,将劳动智能加以累积、传承和提升。如此持续演进,不仅推动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由蒙昧时代的“一把粗笨的石刀”跃升为工业时代的蒸汽机,而且也使人类的本性不断得到改变,直至进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状态。[6]294因此,对于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而言,“劳动”与“生育”二者对立统一,有机作用于人类生命活动的全过程,相互依存,不可或缺。
再次,恩格斯在这里以财富和人类生活基本条件的构成作为范例,内在深意,旨在昭示人们应当用辩证的思维去观察自然和分析社会现象,以此指导对人的起源、生成和形成问题的研究。因此,用辩证的思维去观察自然和社会,探讨人的起源、生成和形成,恩格斯作出了科学的论断——“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不言而喻,这既是《作用》文本立意的支点,也是恩格斯在这个层面表述的本意所在。
(二)恩格斯本意解析
审视“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肯綮之处在于对其中的“某种意义”为何意义、“劳动”对“人本身”生成的“创造”作用是什么以及“人本身”是哪种生命形态的解读。笔者以为,从中可以析出三层涵义。
其一,“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之“某种意义”,并非空泛语词,确切地说,它针对达尔文学派的人类起源理论而言。恩格斯肯定了该学派主张的关于由低等动物至高等动物再链接到人的进化论观点。
1859年,达尔文划时代的科学著作《物种起源》问世。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生物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规律——进化论。这是继牛顿首次进行无机界天、地宏观运动大综合后的又一次更高层次的科学大综合,即无机界与有机界运动的大综合。无疑,进化论沉重地打击了宗教神学的特创论、目的论和形而上学的物种不变论。对此,马克思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20]131。《物种起源》没有专门讨论人类的起源,只是在结论中指出,人类的起源和他的历史将会得到阐明。显然,达尔文既然已证明高等生物是由低等生物进化而来,处于象牙之塔的最高级生物——人类,当然概莫能外。《物种起源》出版不久,就在英国展开了一场围绕人类起源的大论战。达尔文学派的代表人物,生物学家赫胥黎从比较解剖学、发生学、古生物学等方面,具体阐述了动物和人类的关系,确定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首次提出人猿同祖论。他认为,没有理由怀疑人类起源的一种情况是从类人猿逐步变化而来,另一种情况是和猿类由同一个祖先分枝而来。
1871年,在众多科学家已完全接受物种进化的思想之后,达尔文认为时机成熟,必须也完全可能详尽论证人类的起源也遵从同一自然选择规律,以攻破神创论的最后堡垒,使人类从神学的超然地位回归到自然谱系。于是,他发表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在该书中,达尔文用翔实的资料,进一步论证了人类和类人猿的亲缘关系,指出人类是由古猿逐渐进化而来的,再次肯定人猿同祖论。
对达尔文所创立的学说和他列举的科学证据,恩格斯指出:“机体从少数简单形态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态一直到人类为止的发展序列,基本上是确定了”[12]176。在达尔文理论的基础上,海克尔经多年研究,建立了种系发生学,描绘了生物进化系统图(亦称生物系谱树)。他认为,生物进化的生命活动的根本特性是遗传和适应。生物通过遗传把祖先特征和由适应环境引起的变化传递给下代,逐渐形成新种。遗传和适应的交互作用造成了生物进化。对海克尔的贡献,恩格斯也同样给予肯定。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他分别指出:“最近,特别是通过海克尔,自然选择的观念扩大了,物种变异被看做适应和遗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里适应被认为是过程中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被认为是过程中保存变异的方面。”[21]411这样,生物就“由于遗传和适应的不断斗争而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进化到人”[12]189。
其二,在适应和遗传引起机体变异的意义上而言,所谓“劳动”对人本身生成的“创造”作用,弥补了达尔文学派单纯由生物学角度说明从猿进化到人的理论缺陷。
由于达尔文等人的世界观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夹杂着唯心主义的因素,自发的辩证法带有形而上学的痕迹,致使他们只看到了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并不能科学地解释古猿是怎样演变成人的。达尔文学说用生物进化的规律来论证人类的起源和发展,把人和动物简单地等同起来。可是,人毕竟不是一种普通动物,人同动物之间既是远亲近戚关系又有本质区别。这种区别在于“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2]559所以,人类的起源和发展,有其独特的规律,完全用进化论来说明是片面的。因此,恩格斯在肯定达尔文学派人类起源理论正确方面的同时,还深刻地指出:“甚至达尔文学派的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家们对于人类的产生也不能提出明确的看法,因为他们在那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认识不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2]558。基于适应和遗传引起机体变异的前提而言,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创造了人本身”。
概括地说,恩格斯所说的劳动对“人本身”生成的“创造”作用,是从三个方面确立的。
第一,劳动使古猿手脚分工,直立行走。恩格斯指出,如果说摆脱了林间攀援方式的古猿直立行走一定先成为习惯,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才为必然,那么就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手在此期间已经越来越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了。”它们采摘植物果实、挖掘块根,捕捉小动物,拿着天然的木棒和石块抵御天敌。因此,“手变得自由了,并能不断获得新的技能,而由此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所以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但是,手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只是整个机体的一个肢体。凡是有益于手的,也有益于手所服务的整个身体,而且这是以二重的方式发生的。所谓“二重的方式”,是指“达尔文所称的生长相关律。依据这一规律,一个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总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态息息相关”。因此,人手的逐渐灵巧化以及与之保持同步的脚在直立行走方面的发育,由于相关律的作用,无疑会反过来影响机体的其他部分。[2]552
第二,“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恩格斯指出,古猿在获取食物、抵御天敌的生命活动中,需要群体成员的相互协作,在“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时,产生了表明意向的简单音节和手势。随着活动内容的日益复杂,语言便不断完善和丰富起来。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古猿的发音器官和听觉器官也同步得到了进化。[2]553
第三,“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由于劳动,手足分工,直立的姿势使脊柱托住头部,视野扩大了,促进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发达起来,以便接受更多的信息,为猿脑进一步发展成球形创造了条件。由于劳动,使直立行走的古猿获取了从使用天然工具到制造打猎和捕鱼工具的能力,这就使它们的食物来源由少数种类的果实发展到多种植物,又发展到肉类和熟食,摄入机体的养料也愈来愈多样化。这种“除吃植物外也要吃肉的习惯则大大促进了正在生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肉食对于脑的影响”,从而使脑髓得到更丰富的营养,为脑量的增大和脑结构的复杂化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条件。由于劳动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进展,随着语汇的丰富和语言的发展,作为思维器官的大脑,机能也就更发达了。大脑的发展以及思维能力的进步,“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2]554。
其三,“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中的“本身”一词,不是蛇足赘语。恩格斯将此处的“人”后缀“本身”二字,意在标识“人本身”这种生命进化形态与同猿最终分离的人的区别,同时也是对一个理论追问的回应:由适应、遗传和劳动合力作用创造的“人本身”不等同于完全形成的人。那么,在恩格斯看来,“人本身”是何种生命形态,他又是怎样对其属性定位的呢?
在《作用》中,恩格斯对人猿相揖别的过程作了完整概括,提出了三个反映从猿到人转变的概念:“攀树的猿群”、“正在生成中的人”和“完全形成的人”。笔者以为,以此为参照尺度,则可对“人本身”的指向和属性作出准确定位。依据当代古人类学的成果可知,恩格斯讲的“攀树的猿群”,是人类和现代猿的共同祖先,现在已经发现的这种古猿的化石中,有在埃及发现的原上猿化石和埃及古猿化石,前者距今3500万年—3000万年,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类人猿化石,后者距今约2800万年—2600万年,地质年代是在第三纪的渐新世。此外,则是在法国以及欧、亚、非三洲陆续发现的森林古猿化石,其生存年代距今约2300万年—1000万年以前,地质年代属第三纪的中新世,一部分已跨入上新世。这些古猿都是林栖动物,是成群生活在树上的攀树的猿群,它们用四足行走而能臂悬行动。恩格斯讲的“正在生成中的人”,是指从猿到人过渡期间的生物,它们是人类的直接祖先。目前已知的“正在生成中的人”的早期代表是腊玛古猿,生存年代距今约1400万年—800万年。一些人类学家认为,腊玛古猿已基本能用两足行走,并能使用石块和木棒等天然工具。而且,与森林古猿的形态比较,腊玛古猿的吻部远为短缩,犬齿较小,齿列呈弯弓形,这些都更接近于人类,表现出从猿到人过渡的趋势。“正在生成中的人”的晚期代表是南方古猿,生存年代约为550万年—100万年前。南方古猿主要有两个类型,即南方古猿纤细种(亦称非洲种)和粗壮种。南方古猿纤细种的主要特点是:颌突出,没有下颏,头盖低平,额向后倾,脑容量为600毫升。这表明它与森林古猿的形态相比已有了进一步发展。目前,多数人类学家认为,人类是从南方古猿纤细种发展而来的。恩格斯讲的“完全形成的人”,是指同猿最终分离的直立人,即具有血缘家族结构的社会边界的人。在中国,习惯上把直立人称为猿人。其生存年代距今约170万年或150万年前至30万年或20万年前,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早期至中期。[22]7
基于以上三个概念的解析可以确定,“人本身”这种生命进化形态,既不是从猿到人转变过程的起点——“攀树的猿群”,也不是过程的终端——“完全形成的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性生物”——“正在生成中的人”。笔者的这种界定以援引恩格斯的相关表述作为依据。如前所述,“人本身”生命形态的三个特征:手脚分工、直立行走、语言和大脑思维功能,是由适应和遗传与劳动的共同作用决定的。既然如此,我们则可从恩格斯对相继具有这三个特征生命载体的称谓中得到印证:“正在生成中的人”是“人本身”的代名词和同义指称。
首先,恩格斯指出,如果说我们的遍体长毛的祖先直立行走先为习惯后成必然,就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手在此期间已经越来越多地从事其他活动了。”但是,手所能做出的一些动作,“在开始时只能是非常简单的。最低级的野蛮人,甚至那种可以认为已向更近乎兽类的状态倒退而同时躯体也退化了的野蛮人,也远远高于这种过渡性的生物”[2]552。毋庸置疑,这种“过渡性的生物”是专指“正在生成中的人”。其次,恩格斯在解释“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成因时指出:“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中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2]553再次,恩格斯指出,真正的劳动(指狭义的劳动——笔者注)是从制造打猎和捕鱼的工具开始的。“但是打猎和捕鱼的前提:是从只吃植物过渡到同时也吃肉,而这又是转变成人的重要的一步。”所以,“这种正在生成中的人离植物界越远,他超出动物界的程度也就越高”。“除吃植物外也要吃肉的习惯则大大促进了正在生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肉食对于脑的影响;脑因此得到了比过去丰富得多的为脑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因而它就能够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发育起来。”[2]556
无须赘言,作为从“攀树的猿群”到“完全形成的人”的过渡性中介,“正在生成中的人”“亦此亦彼”:既有接近于“完全形成的人”的生理特征,诸如直立行走、语言和思维功能,又没有“同猿最终分离”。毫无疑义,前者是因为“正在生成中的人”具备了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功能,后者是由于它还没有实行和终止杂乱的性关系,不是社会边界的人。因此,它“非此即彼”,仍属于动物种类。
四、“正在生成中的人”转变为“完全形成的人”的标志
人类起源于动物,自然就存在一个由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时期。那么,作为“过渡性生物”——“正在生成中的人”,如何转变为“完全形成的人”?转变终结的标志又是什么呢?
在《作用》中,恩格斯提出了“完全形成的人”是“同猿最终分离”的人,“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因素社会”的观点。[2]554由此,也可以说,“社会”的出现,是人的完全形成的标志。但是,由于《作用》文本的“中断”,我们看不到“正在生成中的人”是如何转变为“完全形成的人”以及“社会”又是怎样出现的表述。什么原因呢?不外乎三种情况:1)《作用》在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文本只是一个片断,或许手稿恩格斯没有写完;2)恩格斯逝世后,手稿在由马克思小女儿爱琳娜,继之伯恩斯坦保存期间,可能遗失了其余部分;3)恩格斯在写作《作用》(1876年)期间,当时原始社会的研究尚处在神话和宗教的传说阶段,还不能提供这方面的科学成果。前两种可能尽管目前尚不能排除,但笔者倾向于后一种情况,因为它符合恩格斯关于人的起源、生成和形成思想的发展轨迹。
1877年,美国学者路·亨·摩尔根出版了科学巨著——《古代社会》,“他从亲属制度出发,恢复了与之相应的家庭形式”[4]26,从而为学术界提供了一把打开原始社会这座迷宫大门的钥匙。马克思在1880年至1881年间抱病批阅了该书,形成了他的人类学笔记——《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为了实现马克思的遗愿,恩格斯充分利用了他的战友对《古代社会》所作的摘要和批语并结合自己的多年研究,于1883年出版了《起源》。在1891年问世的第4版中,他又根据当时的最新成果作了重要修订。
在《起源》(第4版)中,恩格斯在《作用》的基础上,对“正在生成中的人”向“完全形成的人”的转变作了详尽而完备的阐述,进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完全形成理论。他指出:“像正在形成中的人这样一种没有武器的动物①……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4]45如前所述,“正在生成中的人”作为介于猿与人之间的“过渡性的生物”,在质的规定上仍为动物属性,从进化谱系上说,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长臂猿科的南方古猿。虽然它具备了直立行走、语言以及能够使用和制造简单劳动工具等诸功能,但在生命活动的第二种方式,即种的蕃衍上,仍要受高等动物规律的支配。因此,恩格斯指出:“在较高等的脊椎动物中,据我们所知,只有两种家庭形式:多妻制和成对配偶制;在这两种家庭形式中都只许有一个成年的雄者,只许有一个丈夫。雄者的忌妒,既联结又限制着动物的家庭,使动物的家庭跟群对立起来;由于这种忌妒,作为共居生活较高形式的群,在一些场合成为不可能,而在另一些场合则被削弱,或在交尾期间趋于瓦解。”[4]45-46
稍有生物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哺乳动物成年雄者的忌妒,表现为雌性发情期雄性间的激烈冲突,这是一种以胜者赢得交配权的种的蕃衍方式,可以保证把它的强壮基因遗传给子代。不言而喻,冲突意味着彼此对立、互不相容,茕茕孑立,孤然一身。作为摆脱林间生存方式直立行走于陆地的南方古猿,依然是大自然生物链的一个环节,置身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生态环境之中。为了存活,一方面,它们要采集渔猎,以维系生命的代谢;另一方面,又要自卫防身,免遭诸如狮、豹等食肉兽类的伤害。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仅凭石制器具与天敌单打独斗,既不可能有所获,也不可能使自身安然无恙。那么,怎样形成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呢?恩格斯认为,“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没有忌妒,则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只有在这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转变。”如何实现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和忌妒的消除呢?只有实行“杂乱的性关系”,因为杂乱的性关系是“同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4]45-46
进而,人们又要问,什么是杂乱的性关系?为什么说南方古猿实行这种交配方式是“同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呢?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所谓杂乱,是说后来由习俗所规定的那些限制那时还不存在。”也就是说,“现在或较早时期通行的禁例在那时是没有效力的。我们已经看到,忌妒所造成的限制是怎样崩溃的。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确定的话,那就是:忌妒是一种较后发展起来的感情”。[4]45-46可见,所谓杂乱的性关系,是指没有忌妒心理,没有血亲观念,没有习俗规定加以某种限制的两性关系。显然,南方古猿的成年雄者间只有消除忌妒,相互宽容,结成群团,才能形成一种质变的合力,既可自保,又能照抚“妻小”,遂有工具的更新和换代,继续在地球舞台上上演生命进化的活剧。显然,所有这一切唯以实行杂乱的性关系为前提,这是适者生存的表现。这种关系为群团的形成和稳定注入了向心剂,它是“正在生成中的人”进行时的本质特征,也是南方古猿这样的动物能进化为人的内在规定。
毫无疑问,如同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一样,杂乱的性关系又是一把双刃剑,它为自然选择规律所排斥。不言而喻,杂乱的性关系所造成的不育和畸变的恶性循环将导致种的灭绝,不适时摆脱与终止,同样会被大自然所淘汰,从而退出地球舞台。显而易见,是否实行杂乱的性关系,是区别“正在生成中的人”与“完全形成的人”特质的一个标志,也是横亘于从猿到人生命链接进程中的一座界碑。准确地说,杂乱的性关系为人类的生育蕃衍机制所禁入,否则,根据分子生物学的观点,人类进化的足迹就不会从非洲发祥地遍布于世界五大洲,地球村也不能像今天这样人满为患。因此,随着杂乱的性关系被加以限制和禁例,有序而规范的两性交媾方式的确立,宣告了婚姻制度的发端和从猿转变为人“过渡期间”的终结,杂乱的性关系就此成为史前史的陈迹。诚然,杂乱的性关系作为南方古猿所独具的一种状态和行为,已随着它进化为人而消失,考古发掘难以还原昔日的真实。然而,正如恩格斯所阐释的那样,尽管我们没有找到这种杂乱性关系状态的直接证据,但是,现有人类婚姻史的资料,却可以提供极为有力的间接证明。这种间接证明,其一是群婚制,即整个一群男子与整个一群女子互为所有,很少有忌妒余地的婚姻形式。其二是多夫制,这种形式更是直接同一切忌妒的感情相矛盾。“不过,我们所知道的群婚形式都伴有特殊复杂的条件,以致必然使我们追溯到各种更早、更简单的性关系的形式,从而归根结蒂使我们追溯到一个同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关系的时期”。人类最初的婚姻制度——血缘婚配,就是从这种杂乱状态中发展起来的。[4]45-46
血缘婚配结构了血缘家族。马克思认为,血缘家族是人类的“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5]20。它的特点是按辈分规定婚姻集团,即同辈男女互为夫妻。这种“哥哥抱着妹妹做新娘”的兄妹婚,排除了父女和母子之间的性关系。这就足以说明,血缘婚配是对杂乱的性关系扬弃的质变,以此确立了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人伦。在这里,“道”有男女交合之意;“伦”的本义则为“辈”。在一个家族内,恩格斯将其划分为四个范畴:祖、父、己和子。但是“父亲、子女、兄弟、姐妹等称呼,并不是单纯的荣誉称号,而是代表着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这些义务的总和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4]40由是而论,婚配规范及亲缘关系在原始社会中起着决定作用。“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4]16人类始初,家族系列与社会组织是一致的、等同的,家族即社会。由此可见,血缘婚配形成了起初的“唯一的社会关系”——亲属系列;亲属系列架构了“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血缘家族;家族成员之间既有血缘关系,又有姻亲关系,且都统一为社会关系。社会是人的存在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23]734毫无疑义,社会是“完全形成的人”的标志所在。“完全形成的人”终结了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
[收稿日期]2013-03-12
注释:
①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作用》(第514页)和第4卷《起源》(第29页)中皆称谓“正在形成中的人”。但是,在1995年版第4卷《作用》(第379页)中称谓“正在生成中的人”,在《起源》(第30页)中又称谓“正在形成中的人”;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第9卷《作用》(第553页)中称谓“正在生成中的人”,在第4卷《起源》(第45页)中又称谓“正在形成中的人”这两处的称谓实际上是相同的意义,却没有统一的提法,是版本的一个瑕疵。
标签:达尔文论文; 恩格斯论文; 生物起源论文; 动物进化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物种起源论文; 自然辩证法论文; 科学论文; 起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