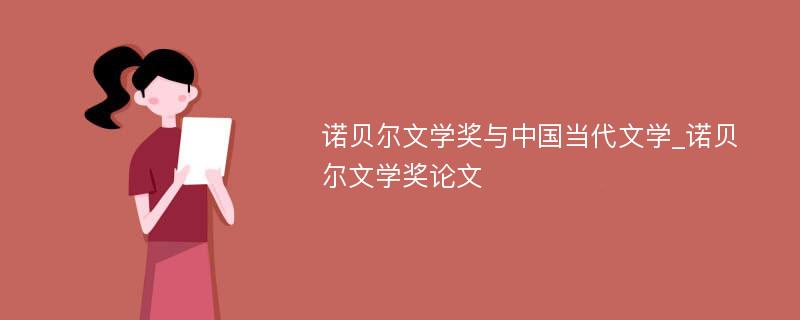
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当代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贝尔论文,当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文学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诺贝尔奖情结或焦虑始终在折磨着中国作家的神经。文坛每一年都会为获奖者而激动,尤其是本土作家入围提名的年份。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借获得提名的传闻而热销就颇具喜剧性。
由于中国文学的长期缺席,中国作家获得“零的突破”的人选就成了巨大的悬念,甚至有人未雨绸缪,考量谁最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学。这种思维的潜台词是:如果一旦有中国作家获奖,就意味着中国文学获奖。
一
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有种种不足,它在发现天才的同时,也遮蔽和埋没了更多的天才,像卡夫卡、乔伊斯、托尔斯泰、哈代、博尔赫斯、易卜生、普鲁斯特、契诃夫、里尔克、高尔基、左拉、瓦雷里、布莱希特、斯特林堡、曼杰什坦姆、阿赫玛托娃等大师都被遗漏。英国的罗素、德国的欧肯、法国的柏格森凭借其哲学著作,政治家丘吉尔因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而获得文学奖,泱泱大国中国却一直缺席。为此,有连篇累牍的论著在追问中国作家没能获奖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1.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向欧洲和美国的过度倾斜,使诺贝尔文学奖遭受了猛烈的批评。在迄今为止的104位获奖者中,欧洲22个国家79人获奖,美国10人获奖,亚洲3个国家4人获奖,拉丁美洲5个国家(地区)6人获奖,非洲3个国家4人获奖,大洋洲1人获奖。但是,最近二十多年,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正在努力地摆脱这种不平衡。诺贝尔文学奖正在不断地拓宽自己的精神版图,将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不起眼的小国家的文学纳入自己的视野。这种趋势为中国文学带来了契机,也使得中国文坛变得更加焦躁不安。
2.政治偏见。诺贝尔在遗嘱中规定,文学奖颁发给“文学家,他曾在文学园地里创作出富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的作品”。诺贝尔文学奖无法脱离政治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其最突出的偏向恰恰是其政治趣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身不由己地奉行了一种“中立国”的政策。文学奖获得者大多来自北欧和一些较小的民族国家,他们在政治立场上保持中立,文学成就显得平庸,缺乏独树一帜的创新和探索。1938年获奖的赛珍珠是争议的焦点,评论家认为瑞典文学院之所以选中她,是由于评委们“不愿意过度干预欧洲事务或触怒世界当权人物”。在对待苏联作家时,瑞典文学院的趣味显得更为褊狭。五名获奖者为蒲宁(1933)、帕斯捷尔纳克(1958)、肖洛霍夫(1965)、索尔仁尼琴(1970)、布罗斯基(1987),除了肖洛霍夫之外,要么是“流亡者”,要么是“叛徒”,要么是持不同政见者,三人流亡异国,一位拒绝流亡却选择了自我放逐。 1964年,萨特发布拒绝受奖的声明,批评诺贝尔文学奖在冷战中偏向西方阵营,或对东方阵营的叛逆者青睐有加,在近年的获奖者中,2003年度获奖者库切因对南非的现状不满而愤激地移居澳大利亚,2004年度获奖者耶利内克有着鲜明的反右翼立场,2005年度获奖者哈罗德·品特旗帜鲜明地反对伊拉克战争,2006年的获奖者奥罕·帕慕克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时的言论引发了轩然大波,他说:“对于20世纪针对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的大屠杀,土耳其政府是有罪的。”“理想主义”被理解成反抗极权,批判腐朽的秩序,当然不应被指责为误入歧途,但是,意识形态的因素确实会严重地干扰评奖的结果。
3.语言障碍。复杂的象形文字和简洁的字母文字在传情达意上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将汉语文学翻译成字母文字,那些言外之言、象外之象、意外之意往往丧失殆尽。汉语作为一种意境性语言,与讲究层次感与逻辑性的英语相比,具有一种重视整体感应的模糊美感,那种朦胧的、灵动的美学效应很难被移植到译文之中,像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飘逸”和“旷达”之间的微妙差别,外语就很难传达。
二
“中国作家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有多远?”这是每年的获奖人选公布后反复纠缠我们的一个老问题。诺贝尔文学奖始终不渝地推举文学的理想主义品格,强调作家必须以永远的怀疑精神挑战权威和传统,正如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所言:“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开场合这么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独立意志与批判精神的匮乏,是中国当代作家的普遍性缺失。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作为政治附庸的文学无法独立发声,作家也罕有例外地沦为时代主潮的应声虫。在新时期初年思想解放大潮的裹挟之下,作家的个性意以逐渐复苏,探索激情也如冲破栅栏的骏马自由驰骋。遗憾的是,启蒙情境的破裂和市场大潮的涌动,使脆弱的精英梦想跌落幻灭的深渊。面对蔓延的精神废墟,众多作家笔下都流露出一种四顾茫然的颓唐和引而不发的沉痛。从王朔以降,油滑的风格成为文学的精神基调。因为受过信仰的蒙蔽而怪罪于信仰本身,进而以“不信”为宗旨,这导致了虚无主义的泛滥。从“五七”一代、知青作家群、先锋作家群、新写实作家群到所谓的“新生代”,他们在叙事和修辞风格上越来越喜欢反讽,喜欢戏仿,喜欢拼贴,喜欢玩大杂烩,喜欢故弄玄虚地装深沉,喜欢两眼空洞地喊无辜,喜欢高举“后现代”的旗帜标榜自己的“虚无”。“虚无”成了一些人既攫取种种权利又推卸种种责任的借口,表面是阴阳怪气的冷嘲,背后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共谋。作家们对英雄、神圣、理想都难免表现出一种嘲弄的冲动,对于现实的无奈总是欲说还休,牵涉到责任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如果说盲信曾经是“五七”与知青代群的悲剧,那么,不信是“文革”前后出生的代群的共同悲剧。当不信成为一种思维定式时,这种惰性逐渐地蚕食了“信仰”的能力,既然无法相信一切,他们也就无法相信自己,自私与自恋也往往是对自己不自信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且,更年轻的写手如“80后”过早地陷入商业写作的泥潭,前景堪忧。因此,有人推测如果上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中国作家无法获奖,中国文学跻身诺贝尔家族的梦想还将延宕下去。
反思当代中国文学,一个突出印象是原创性的匮乏。“十七年”时期,中国文学被笼罩在俄苏文学的阴影之中。“文革”之后,与世界接轨的冲动使西方的文学话语被轮番操练,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历时性的审美潮流在中国成了共时性的文化景观,模仿西方作家的风格似乎成了文学的惯例。对外来文学资源的膜拜,以及“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践踏,使得当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极为隔膜。在“新”与“后”的时尚话语的轰炸之下,众多文化和文学新人高举“打倒”、“超越”、“告别”的旗帜,宣判旧历史的“终结”和“死亡”,这种断裂性思维加剧了传统文化与文学遗产面临消亡的危机。中国文学要得到世界的尊重,关键是要向世界提供“人无我有”的独特奉献。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英语的版图不断扩张时,越来越多少数族群的语言正在消亡,审美经验也呈现出逐渐趋同的一体化倾向,世界文学资源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种情景下,中国文学如何发掘传统资源,如何在与外来资源的对话中,通过对传统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孕育仅仅属于中国的艺术形式,这是中国作家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只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生发出别样的审美情趣,犹如在黑暗尽头的辉煌日出,照亮全新的视野和无限的可能性,为世界提供无可替代的艺术享受。当这样的一天到来时,就不再是中国文学哭着喊着去追逐诺贝尔文学奖,而是这一奖项主动来拥抱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在诺贝尔文学奖家族中的缺席,也不再是我们的遗憾,而是这一奖项的耻辱。
中国当代作家的另一个普遍性缺陷是艺术生命的短暂,众多作家因为外部环境的制约和自身的人格缺陷,在世俗和功利的围追堵截中,纷纷折服于权和钱的威力,把写作作为利益交换的一种工具,成为寄生的工匠和夭折的天才。中国当代的不少作家把文学当成了流浪的痛苦灵魂的收留所,但文学显然无法容纳作家更为入世的人生志向。当代作家几乎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文化忧患意识,经世致用与匡救时弊的动机成为其创作的文化内驱力,现实主义的地位之所以牢不可破,长盛不衰,这根源于作家普遍地把文学作为介入现实的工具。在本质的层面,文学是“无用”的,川端康成认为自己是“无用之人”,并自以为其文学是“怠惰者的文学”,我认为这种理解非常契合文学的本体。在当代文学史上,对于那些拥有政治抱负的作家而言,其文学观念烙有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突出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在价值选择上通过文学“求势”而非“求道”,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忽视文学的审美意义。第一次文代会以后,专业作家制度逐步建立起来,新中国成立前一些依靠稿费生存的作家,譬如老舍、巴金等也被纳入体制,被委任到文艺组织、文学研究等相关岗位。从此以后,作家在创作上取得一定成绩后被提拔为文学机构的行政领导,很长时间内一直是一种惯例。王晓明对此有言:“人们一直都在喟叹,说20世纪的中国没有大作家。就拿七十年来的那些富于才华的小说家来说吧,他们都能不同程度地获得一份独特的人生感受,却又似乎都无力使这份感受进一步深化。有的人要经过多次试验和调整,才能谱出一支比较完整的旋律,这以后就筋疲力尽,只能一遍遍地重复这个旋律。有的人比较幸运,一上手便能奏出一曲新颖的旋律,可以后也就每况愈下,技巧虽然圆熟了,激情却日益消退。当然,那种因为分心去维持剧场的秩序,终其一生都谱不出一曲合调的旋律的人,数目就更多了。”不少作家在成名之前还能全力以赴地投身于独立的艺术探索,一旦靠写作获得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可,便不满足于成天沉浸在文字游戏之中的枯燥生活,开始将生命耗费在无聊的会议与频繁的应酬之中,创造力急剧萎缩。伟大的作家把写作当成通往自由的道路,但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渴望的似乎恰恰是那种身心受到种种限制的权力、金钱与声名的枷锁。至于那些为数不多的坚守文学理想的作家,又常常不幸地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自我重复的怪圈,被传媒的围困、外部舆论的压力和内在的焦虑所困扰,缺乏那种将自己抛入没有精神归宿的、无所适从的境地的坚韧与决绝。正如尤金·奥尼尔在谈到剧本《与众不同》时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只有在达不到目的时才会有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从而才能找到自我。在绝望的境地里继续抱有希望的人比别人更接近星光灿烂、彩虹高悬的天堂。”正是那种永不放弃的持续探索精神,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的。
三
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项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积累的奖项,尽管有不少瑕疵,但其地位是无法撼动的。在纷繁复杂的外部因素的干扰之下,它在评奖程序上严格遵守既定的评选规则,始终如一地忠实于理想主义的信念,确保艺术标准的独立性,极力弘扬文学的批判精神。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恰恰是中国的文学评奖所欠缺的。反观新时期以来的全国性文学评奖,缺乏长远的眼光,停停办办,显得随意和草率,那种因人设奖、因人修改规则的做法,践踏了必要的程序公正,杀鸡取卵,严重地损害了自身的声誉。最典型的是茅盾文学奖对《白鹿原》的改写要求,一种权威性奖项是对它所严格奉行的价值和审美标准的弘扬,作为一种追求完美的文学理念实在是无可非议,但如果它必须让获得这一奖项的不完美的作品付出“改写”自己的代价,那么它就与文学发展所必需的宽容性和丰富性背道而驰。一种审美标准如果沾染了“改写”别人的冲动,它与权力意志的距离就形同虚设了。茅盾文学奖饱受诟病的是其经过一名评委提议、两名评委附议就可以随时增加候选篇目的规则,评奖规则始终保持这一条款,意在避免遗珠之憾。正因如此,名目繁多的评奖往往都不能坚持独立的艺术判断,使艺术标准成为其他更加强势的文学评价体系的附庸。一个文学奖项在选择的同时,总是首先要思考如何放弃,但是,只要它一直坚持一种标准,那么,它就应该得到尊重。基于此,诺贝尔文学奖漏选的遗憾恰恰是其独特的美丽。我们的奖项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标准,像芦苇一样随风摇摆,玩弄平衡游戏。
另一方面,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评奖制度中,排座次的等级意识成为一种指导思想,一些文学组织和文学机构更是以一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市侩逻辑来评价文学,并且将获奖与否与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挂钩,文学本身的尊严反而成为可有可无的点缀。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奖项都是评奖年限内的新作奖,往往不考虑作家在创作上的总体成就,而且奖项设置颇有排排座分糖果的味道,这就很难避免在矮子中拔将军的弊病。文学评奖是不同的政治倾向、审美判断、文化趣味相互撞击的过程,评委们在求同存异的妥协中,往往牺牲了那些艺术特色最鲜明、形式探索最激进的作品,成全了那些四平八稳的、能被普遍接受的作品,因而,中庸趣味的作品往往能最终胜出。
说白了,一个作家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获奖尤其是大奖固然能获得超额的象征资本,但一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依然无法阻挡时间的无情淘洗,何况那些依靠不择手段攫取各种奖项来壮胆的小丑呢。萨特在《我拒绝一切荣誉》一文中说:“显然,一个作家不可能在一个给定的时间里对其余的人来说是最优秀的。他最多只是最好的那些人中的一个……按一种等级制度的次序来安排文学的整个观念是一种反对文学的思想……等级制度毁灭人们的个人价值。超出或低于这种个人价值都是荒谬的。这是我拒绝诺贝尔奖的原因,因为我一点也不希望——例如——被看成是跟海明威名次相当。”或许,正是由于国内的文学奖项普遍地缺乏公信力,国人才会对诺贝尔文学奖如此狂热,心态才会如此复杂。
标签:诺贝尔文学奖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诺贝尔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作家论文; 诺贝尔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