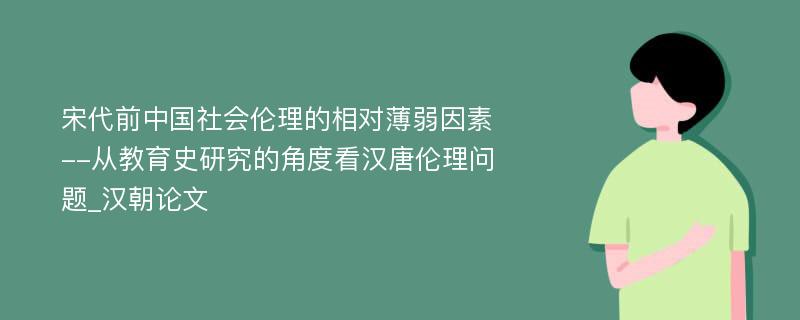
宋以前中国社会伦理相对薄弱的教育因素——从教育史研究的视角看汉唐时期的伦理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汉唐论文,薄弱论文,中国社会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34(2007)04-0023-(08)
一、引论:教育担保伦理所需的若干条件
古代教育要担保伦理的实现需要具备若干条件,这可以从宋代以后中国社会宗族伦理的经验中得到证明,也可以从犹太社会宗教伦理的经验中得到证明。这些条件大致包括:
第一,社会对伦理与道德教育有效的组织程度。如犹太教与基督教社会是通过宗教共同体来提供伦理教育的;而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则是通过宗族共同体来提供伦理教育,并且它还得到民间书院和国家教育的有效辅助和补充。
第二,有比较固定和系统的伦理道德教育内容,并有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经典对这些内容加以概括和提示。如《旧约》之于犹太社会,《新约》之于基督社会;宋代的蒙学、小学以及更高阶段的官学和私学都更加重视儒家经典中的伦理道德内容。
第三,整个社会在接受伦理或道德教育方面的广泛程度,也可以理解为普遍有效的伦理教育在大多数个体身上的体现。这是前两个方面的必然结果。这一点,无论是在犹太、基督社会,还是宋以后中国社会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证明。
第四,个人受教育的有效程度及其对家庭的影响。这不仅从个体本身理解,而且是将个体放在家庭、家族、宗族延续的连续体中来理解。一个能维系伦理教育连续性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的伦理社会。同样,宗教或宗族社会的经验能够充分证明这一点。
对有关宋以前社会基层伦理的教育因素的考察大致可以参照这样几条标准。
二、先秦时期的教育状况及其对于基层伦理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教育包括官学(国家教育)、私学(民间教育)和家教或族学(家庭与家族教育),这样一种格局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
1.官学或国家教育
西周的学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学”,是为上层统治集团的贵族子弟所设,有完整的小学和大学体系。按《礼记·王制》,能够进入大学的唯有“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另一类是“乡学”,即地方学校,是专为下层管理者或平民的子弟而设,仅有小学。如想进一步深造,则需通过严格的“选士”或“取士”制度,事实上,也只有极少数人进入国学。而无论是国学,还是乡学,又都属于官学,也即所谓“学在官府”。以上这样一种状况表明,西周的教育有着十分明确的等级性和阶级性。正如许多教育史研究者所指出的,其最终目的,就在于培养贵族子弟成为具有统治能力的封建统治继承者,至于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奴隶则无入学受教育的权利。[1](P36~37)[2](第一卷,P75~76)
2.私学或民间教育
西周时期是学在官府,但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的巨变和解体,原有的教育制度也同样不复存在了。于是就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现象。[3] 原先官学中的教师,此时也纷纷流落民间,这也就是《论语》中所说的:“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论语·微子》)于是,私学兴起。如孔子,有“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4] 而春秋时期私学教育的对象,也不可能再像西周那样有严格的等级之分,而是无分贵贱,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应当说,这种教育下移的状况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是有益的,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伦理道德观念的教化。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种私学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它的非制度特征,因此其影响也必然是有限的。
3.官学或私学的教育内容
夏商两代不可详考,周代的一般教育内容当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中,礼、乐应属于伦理和道德的内容。至于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兴盛,百家争鸣。各家对教育的理解非常不同,并不存在统一的伦理教育内容。
4.家庭或家族、宗族教育
商周时期,作为社会基层的主要是独立的小家庭。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些位于社会底层的小家庭不可能有更多的教育。但另一方面,在商周时期,家族或宗族教育已经出现,其最典型的形式就是周公对周王室和贵族的种种教诲与诰文,这其中包括以“孝”为核心的宗法伦理规范,也包括周公“敬德保民”的宗教天命思想。但需要指出的是,商周时期的家族或宗族是非常有限的,其主要集中于王室及其分封贵族,并且到了春秋以后其逐渐消灭而普遍趋于小家庭的形态。而到了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又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上层伦理观念特别是“孝”观念的影响。
综观先秦的伦理教育状况,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1)在统治集团,有相应的伦理道德教育内容,但这些内容基本上是与社会基层或大众相割裂的,并不会产生普遍意义的影响。(2)在大众层面或社会基层,由于受教育者十分有限,伦理与道德的影响应当也是有限的。(3)以上两点表明,这一时期的伦理与道德教育还是一种与地位和权力相应的昂贵的“消费品”,社会尚处于对少部分人来说具有伦理意识和道德自觉的时代。(4)但作为与家庭或家族生活密切相关的“孝”及“悌”观念应当已经形成并逐渐具有比较普遍的性质,这样一种观念不仅有现实生活的基础,也可以通过专门教育之外的更为丰富的途径获得,并且这一观念成为后世伦理教育内容的重要源泉。(5)就整个这一时代或社会而言,规范的伦理教育内容尚没有形成。
三、两汉时期的教育状况及其对于基层伦理的影响
两汉时期,制度性的教育重回国家日程。这一时期以及以后的教育,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些方面来加以考察:
1.官学或国家教育
一般认为,两汉官学可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中央官学中有太学、鸿都门学和宫邸学,其中太学相当于大学水平的教育,宫邸学相当于小学水平的教育,而鸿都门学大致相当于一种艺文类的专科学校。东汉后期,作为大学教育水平的太学招募太学生人数至3万人。地方官学中包括郡国学、县道邑校、乡庠、聚序。但按照顾树森的说法,“汉代的地方小学,在开始的时候,尚未正式成立制度。直到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始确立地方学校制度。”且“政府所注重的,多属于‘学’和‘校’两种学校,而‘庠’和‘序’等小学性质的学校,并未能长期地设立。”[1](P72)在教育内容方面,小学应当是接受基础伦理教育的地方。汉代的庠、序均置有《孝经》师一人。但如前所见,这一教育的制度性可能存在着问题。汉代官学中的太学虽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但实际是经学。汉代经学始于武帝时期,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始置五经博士。五经分别为《易》、《书》、《诗》、《礼》、《春秋》。至东汉光武时期,“《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5](《儒林列传》)经学有今古文之分,其中今文经学偏重于微言大义,古文经学则侧重名物训诂。但无论是今文,还是古文,实际已经将儒家经典作为权威性知识来对待,且繁琐可谓其一大特征。当年桓谭的《新论》就曾记载:“秦近君能说《尧典》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汉书·儒林传》中也说:“信都秦恭延君……守小夏侯说文,恭增师法至百万言。”于是,一部《尚书》篇名的阐述足足花了10多万字,而第一篇开头的4个字即解释了3万字,全书章句更多至百万言。由此足见经学之远离社会伦理实践。这样一种状况显然也为统治者不满。对于汉代统治者而言,其对于通经致用的企盼其实一直笼罩在云里雾里。今文家之间的争论也罢,今文家与古文家之间的争论也罢,对于统治者而言无疑都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在杨终向章帝的建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5](《杨终传》)按《中国哲学发展史》一书作者的解释:儒家经义的“大体”不外乎如何有效地维护君权和父权这两条。而由于当时许多经师寻章摘句,把人们的注意引向一系列琐碎无聊的争论,这个“大体”受到了破坏。[6](P476)显然,这所谓的“大体”就是伦理问题。
2.私学或民间教育
私学也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书馆,主要科目是识字,以及最基本的经典如《孝经》、《论语》,其程度相当于小学。另一类可称作经馆,学习内容则与官方太学相同。一些学生小学之后欲继续深造,却又因大学所在京师路途遥远,且名额有限,于是遂入乡间闾里的经馆学习儒家经典。由此也导致经馆的“兴盛”。但实际上,私学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这包括:(1)在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上,私学(主要是经馆)与官学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正如《中国教育通史》的作者所指出的:“教育的目标和教育内容的主导方面和官学并无原则区别。”尤其是经馆教育之目的,当时的经学大师夏侯胜曾一语道破玄机:“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经术不明,不如归耕。”[7](2)在教育对象上,《中国教育通史》的作者指出:“私学教育师生主要是封建社会的中上阶层”,“其对象都是中上层地主仕宦家族的子弟,至于一般劳动人民,连最起码的私学教育也难有享受的权利和机会”,“在官学教育中劳动人民没有地位,在私学教育中也常常受到排斥。这是汉代教育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整个封建社会教育的一个基本特点。”[2](第二卷,P121,P126)(3)同时,私学教育的质量也存在严重问题。《中国教育通史》的作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指出:“私学教育的教师、教材得不到切实保证。往往是有师则有学,无师学也废;教材多由教者自定,能教什么教什么,确有专长的不少,不称职者也大有人在。私学教育缺乏必要的规章制度。私学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是其突出的优点,但无必要的规章毕竟是一种缺陷。私学教育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虽有不少教师忍饥受寒仍讲学不辍,但无经费保证教学会有严重困难。”[2](第二卷,P126,P127)而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方向或侧面深刻影响着社会伦理教育的普及。
3.家庭教育
有关家庭伦理教育的内容在教育史研究中涉及较少,但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史的研究获得相应的信息。据社会史的研究,在两汉时期,“孝”以及以“孝”为核心的小家庭观念仍是主要的伦理观念,而这也正是家庭现实生活形态在观念上的反映,同样也应当是家庭伦理教育的结果。《孝经》作为蒙学读本对家庭教育有着积极意义。而汉人对母亲的尊重又是汉代“孝”观念的一个特点。阎爱民指出:汉人对母亲极为敬重,这是因为女性寿命一般高于男性,所以奉养母亲是理所当然的事,与寡母别居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和政府的制裁。[8](P274)此外,“孝”这样一种基于家庭伦理的观念也会得到国家律法的支持。阎爱民在研究中归纳了汉代治不孝之罪的种种内容,包括:图谋或实行弑父、迁母、逼姑、致死父兄族党、妻后母、诬祖和诬告父母、与大父母和父母争尊及轻慢等等。并且,不孝之罪属于重罪。[8](P338)但我们仍要看到在社会底层此类教育仍是非常有限的,按毛礼锐的说法,就是“最多只能受到一点极初步的”“伦理道德教化”。[2](第二卷,P121)同时,我们又要注意作为小家庭的社会现实对观念所造成的另一方面的影响。如阎爱民指出,汉人家庭有普遍的不同财的现象,包括夫妻财产的相对独立性、父子不同财、兄弟不同财。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及其观念事实上又导致进一步的伦理观念与现实问题,包括夫妻关系不稳定、对老人赡养的不利、在兄弟之间造成种种矛盾等等。[8](P276~282,P292)这些问题既是家庭伦理问题,也是家庭伦理教育问题。
4.国家意识形态
这里有必要一提《白虎通》。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开了一个白虎观会议,其结果即是《白虎通》。《白虎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说到底,《白虎通》是以当时的思想文化作为背景,企图对儒家经典做一番更为概括的解释。这在一定意义上不啻是对整个以往繁琐的经学教学效果的否定。然而《白虎通》同样也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白虎通》共包括43个专题。从内容来看,其深受当时谶纬神学的影响,或者可以说,就是以谶纬神学作为基础。于是一部《白虎通》实际上变成了汇聚谶纬神学思想的大杂烩。正如《中国思想通史》作者所指出的:“根据《白虎通义》所引的经传看来,它是尽其杂糅混合的能事的,它把《易》、《诗》、《书》、《春秋》、《礼》、《乐》、《论语》、《孝经》以及各种逸文,和图谶纬书混合在一起,望文附会,曲解引申,特别是谶纬,构成《白虎通义》的依据。”“如果把《白虎通义》的文句和散引于各书中的谶纬文句对照,各篇都是一样的,百分之九十的内容出于谶纬。”[9](P229)结果赶走了一个繁琐,却进来了一个迷信。显然,这又与伦理道德的本质无关。《白虎通》中固然有所谓三纲五常六纪之类的内容,如“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三纲六纪》)“五常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情性》)并且,《白虎通》甚至还有还原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的意图。然而,这些意图或是内容实际都被其中的谶纬神学所冲淡了。不仅如此,更重要的则如《中国哲学发展史》所说:事实上,“白虎观会议以后,作为统治思想的神学经学盛极而衰,开始走向没落,同时,逐渐兴起了一股强大的怀疑神学经学的社会批判思潮。”[6](P697)结果是《白虎通》以神学为基础的学说体系也迅速湮灭了,连同其中三纲五常六纪的内容。而通过上述对《白虎通》所作的概要的考察,我们基本能够排除其在当时对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的意义,而这样一种意义有可能在主观臆想中被人为地夸大。
若对两汉时期教育之于伦理的关系做一番归结,我们大致能够得出如下印象:(1)由于汉代社会基本是核心小家庭的社会,而非家族或者宗族的社会,因此社会本身只会提出与家庭相应的伦理要求,而不会产生与家族或宗族这样一个作为具有更广泛社会意义的伦理要求。(2)在家庭教育方面,“孝”及“悌”观念仍具有最为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小家庭的原因,也出现相应或相反的伦理问题。(3)官方在蒙学与小学方面着力不足,重视有限。因此,蒙学与小学教育可能主要还是依赖于民间的私学,其教学内容主要以《孝经》为核心。但一如前见,汉代的私学在学制、师资、经费方面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伦理方面教育的落实或普及也自然会存在问题。(4)即便是那些有条件的私学,其受教育者也多为上中阶层,而作为大众层面或社会基层的一般劳动者,受教育的机会十分有限,其中也包括伦理与道德的内容。(5)官方最感兴趣的是经学教育。而在今古文的争执中,经学或者沦为注解政治的工具,或者演变为纯粹的学术,或者蒙上谶纬神学的面纱,却唯独与先秦儒家伦理道德修养的本意相距十万八千里。(6)《孝经》与《论语》在一定程度上构成这一时期较为规范的伦理教育内容。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状况及其对于基层伦理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充满动荡、朝代不断更迭的时期。这一时期与两汉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有一定的时代特点。
1.官学或国家教育
整个魏晋时期的官学教育与两汉的官学教育基本上是陈陈相因。魏承汉制,所兴办的仍是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的太学。两晋亦承汉魏之制,太学依旧得到重视。若有区别则是西晋时期除太学外,又增加国子学,同样为中央官学。孙培青指出,国子学的创立“旨在维护门阀士族的利益和尊贵”,“是为了满足士族阶级享有教育特权,严格士庶之别的愿望。”[10](P130)因此,国子学一如太学,于社会基层教育及伦理的建立几无意义。魏晋时期也有相应的地方学校,但这些地方学校每每因得不到国家制度的保障而形同虚设。南北朝时期的官学教育因其政治上的动荡与制度上的破碎总体来说更显支离和衰落。南朝总计近170年,共历宋、齐、梁、陈四朝。其中宋、梁两朝较长,教育方面亦稍有起色,在内容方面依旧是重视官学的五经教授。至于齐、陈则基本是亦步亦趋,模仿前朝。总的来说,南朝的教育是处于一种断断续续的状态。北朝同样经历了北魏、北齐、北周三个朝代。与南朝不同的是,这些朝代都属于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因此总体来说都处于吸收和消化汉族文化的状态。三朝均建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内容也均以经学为主。总的来说,正如毛礼锐、沈灌群的《中国教育通史》中所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战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复杂,以及王朝的频繁更迭,因此,封建官学教育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而由于这样一种时兴时废的状态,其教育质量是不高的。[2](第二卷,P304,P309)
2.私学或民间教育
官学弱,私学兴,这或许是一种规律,春秋战国是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如此。《中国教育通史》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学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两晋与南北朝时期,也有人数上千的学校。如西晋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书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食衣。”[11] 毛礼锐认为,这种私学不仅有固定的图书,而且为学生筹办衣食,已很近似后世的书院,或可说是书院的萌芽。[2](第二卷,P336)但就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学应当没有逾越两汉的水平。
3.道、佛类内容进入私学甚至官学的教育
这势必会导致与传统儒家思想的冲突,主要是儒佛之间的冲突。如当时几次大的争论,包括沙门敬王之争、白黑论之争、夷夏论之争以及神灭论之争等等。毋庸置疑,佛教学说及其观念的进入的确造成了当时整个社会伦理观念的混乱。
4.家庭与家族教育
家庭教育一方面与两汉时期有连续性,这就是注重小家庭,轻视大家族;但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一些“聚族”现象,包括形成了一些较大的家族或宗族。这样一个生活现实也同样会在观念及其教育上有所反映,其特别表现为如下两点:第一,这时社会上一些大的家族开始出现一些家训类的教育方式。据李卿的研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见于史籍记载的家训名篇有:西晋王祥的《遗令》、夏侯湛的《昆弟诰》、北朝魏收的《枕中篇》、张烈的《家诫》、甄琛的《家诲》、颜延之的《庭诰》、刁雍的《行孝论》等。而最为著名的当是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这种方式的教育构成了这一时期教育的一大特色。从训诫的内容来看,主要有劝学、修身、立志、处世等。[12](P188~190)但也应当看到这些家训大都仅出自一些较大家族,带有明显的个体性或局部性,还没有对整个社会形成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第二,根据李卿的研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出现了家族创办的学馆,这类似于后世的族学,但仅有一例,见于《北史》卷十七《景穆十二王传上》的记载:景穆帝阳平王新成之孙拓跋子孝,“性又宽慈,敦穆亲族。乃置学馆于私第,集群从子弟,昼夜讲读。并给衣食,与诸子同。”李卿认为,这表明此时由家族所创建的族学并未真正兴起。[12](P188)与此相关,“当时整个社会中宗族观念一般不浓厚,宗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普遍较为淡薄,形同路人。因此可以说,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观念并非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浓厚。”[12](P211)
现在我们可以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伦理教育状况做一小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主要有如下特点:(1)与汉代社会相同,主流生活形式仍是核心小家庭的社会,因此,基层伦理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2)家族或者宗族形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不是主流形式,因此没有对社会包括伦理教育形成普遍而深刻的影响。(3)官学是间断的,并且教育质量受到影响。私学继续维系并在局部有所发展,但总体而言没有逾越两汉的水平。在教学内容上,儒经的学习与两汉并无区别。(4)虽然此时学校教育仍以儒家经学为主,这实际也是以前传统的一种自然延伸,但由于玄学、佛教的流行,儒家经典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已经逐渐被迫退居到次要地位。(5)不仅如此,佛道思想及其经典的深入,尤其是佛教观念在整个社会的传播,事实上还造成了传统儒家价值观的混乱甚至颠覆,例如对于儒家以孝悌为核心的伦理观念的动摇。
五、隋唐时期的教育状况及其对于基层伦理的影响
隋唐两朝对教育都十分重视,最突出地表现在官学和科考中。
1.官学或国家教育
隋代的中央官学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唐代的中央官学在隋代中央官学的基础上又加了一门律学。不过,与儒家经典有关的主要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其相关资料主要保存在《隋书·百官志》和《新唐书·选举志》等文献中。按顾树森和孙培青的研究与统计,隋唐两代以上三学招收学生数额如下:隋国子学140人;唐国子学300人;隋太学360人;唐太学500人;隋四门学360人;唐四门学1300人。学习内容为九经,其年限安排分别是《礼记》、《左传》为大经,各习3年;《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各习2年;《周易》、《尚书》、《公羊传》和《谷梁传》为小经,各习1年半;《孝经》、《论语》作为基础,各习1年。显然,这样一种学习内容、年限以及有限的人数完全属于一种精英教育。在地方官学方面,隋唐均设立有州县学。按顾树森和孙培青的统计,其中经学一科的招收人数为:京都府学80人;大中都督府学各60人;下都督府学50人;上州府学60人;中州府学50人;下州府学40人;京县学50人;畿县学40人;上县学40人;中县学35人;下县学25人。以上全部相加不过530余人,即使有出入也在550人左右。[1](P114~115)[10](P156~157)州县学校学生多为庶民子弟,课程亦读九经,但程度较低。应当说,无论是在学生人数和学习内容上,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都有相似性。对于国家学校也即官学的这样一种状况,顾树森有一段概括:唐代学校虽甚发达,但中央设立的各类学校,绝大多数是为统治阶级的子弟而设的。即地方设立的学校,虽然有庶民的子弟可以参加,但其程度仅限于中小学方面,很少有机会可以上升到中央设立的学校。至于劳动人民的子弟,则根本谈不上受什么教育。[1](P116)虽然今天看来,顾的评价可能多少有一些那个特定时代的印记,但应当说,其总体判断是不错的。另孙培青也指出:唐朝政府明文规定了各级学校招生的身份标准,将教育的等级性以法令的形式加以制度化。达官显贵的子弟依家庭的品级可以进入专门为其设置的贵族学校;一般庶民百姓的子弟只能进入水平较低、待遇较差的学校。前者大都进入了以讲授儒学为主的学校,毕业后就成为各级各类封建官吏的候选人;后者只能进入一些专科性的学校,接受专业知识的教育,毕业后成为一名专业人才。教育的等级性、阶级性由此可见一斑。[10](P160)孙培青的上述看法与顾树森的看法是一致的。
2.私学或民间教育
除官学外,按毛礼锐和孙培青的研究,隋唐亦有私学。但毛礼锐和孙培青的研究包括相应的材料几乎可以用为数寥寥来形容。而其他学者对此似并未涉及,如顾树森的《中国历代教育制度》、陶愚川的《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这或许能够说明,这一时期的私学并不见得发达,即便有一些私授学业者那也是任何社会所普遍具有的现象,而作为具有规模性、制度性的私学在这时并未出现。
3.科举制度
讲隋唐的教育当然不能不涉及科举制度。按毛礼锐对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的比较:九品中正制取士是“重门第”,而科举制取士则是“重才学”。[2](第二卷,P493)又按孙培青的说法:隋唐以前的选士制度是以荐举为主,考试为辅;隋唐以后的科举制是以考试为主,荐举为辅。[10](P160)不过隋国运短暂,科举制的真正完备是在唐代。唐代科举考试主要有六科,分别是: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其中明法、明书、明算属专科类,而秀才一科因及第者甚少,故实际以明经和进士两科为最盛,不过,天宝年间,进士已开始偏向诗赋。王炳照认为:一般而言,明经科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代表了官学教育的基本方向和目标;而进士科以文章诗赋为考试内容,代表着社会文化思潮和私学教育的方向。唐前期,明经一科录取人数多,及第几率大。但伴随着儒经修习所显现的弊端,以及吟诗作赋之风的弥漫,进士一科愈来愈受到士子的青睐,从而成为取士的主要科目。[13](P214)科举制的创立,意在打破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取士的流弊,应当有其积极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科举取士方式的出现,学校教育反而逐渐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此种风气自武则天时始,而后学校教育日渐衰落,形同虚设。[1](P122~123)[10](P167)这当是科举制度对教育的最大冲击和消极影响。
4.伦理观念的混乱,儒家学者的担忧及批评
如前所见,佛、道给传统儒家伦理观念所带来的混乱自魏晋南北朝始。到了隋唐时期,涉及核心伦理观念与价值观念的抵触可说有增无减。而这集中反映在韩愈的有关论述中。如《谏迎佛骨表》中讲:“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韩愈又在其《原道》中数落佛教对于儒家伦理的罪过,即“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其结果必然是“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面对这种种混乱与困境,韩愈在《原道》的结论中认为必须采取强硬的措施,即“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应当说,以上韩愈的担忧与批评也与教育密切相关。用韩愈的话说,这是关系到儒家的“道统”究竟是否能够延续的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对隋唐时期的伦理教育状况作一番小结:(1)隋唐时期的社会基层生活方式并没有改变,即仍以小家庭为主,家族或宗族生活的形式并未出现,因此不可能像宋代以后那样提供族学、族训一类伦理教育的途径与方式。(2)官学较之前代有很大的发展,但教学内容也并没有改变,即仍是经学的内容与方式。(3)私学总体而言并不如前代发达。(4)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受教育对象仍是社会的中上阶层,而作为社会基层教育薄弱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或者说没有途径得到改变。(5)科举制的出现,为士子设定了新的向标,但其更注重知识和才华,与伦理则并无实质关系。同时,科举还有削弱教育的倾向。(6)历经数百年佛、道主要是佛教观念的冲击,已经给传统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使得原本就有限的基本伦理面临巨大的危机。
六、结论:对影响宋以前社会基层伦理教育状况的基本或总体判断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最终对宋代以前的教育历史及其状况作如下概括:(1)以汉唐时期为主的官学或国家教育,主要是基于培养人才的考虑,因此偏重于大学性质的教育,如汉代的太学、隋唐的国子学、太学,其内容主要为经学。包括蒙学在内的小学在国家教育政策中并没有地位。(2)受官学的导向和影响,汉唐时期的私学也偏重于经学教育。小学在私学教育中虽有一定的地位,但由于其民间性质,师资和经费都难有保障。(3)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作为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普通大众都难以接受有效的教育。(4)因此,绝大多数普通大众只能通过家庭获得一点教育,但由于这些普通大众的家庭往往世代都没有接受教育,因此其对后代也基本谈不上什么教育,往往至多是一点生活和生产的技能。(5)在与教育密切相关的国家意识形态方面,无论是汉代的经学,还是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不断强化的佛教,都对先秦儒家学说的精髓或本质造成侵蚀。
以上教育状况当然包含伦理教育的内容,也必然深刻地影响社会或现实的伦理生活,其体现在:(1)官学中的伦理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充其量只是作为一种附属品,并且蒙学教育不被重视。(2)私学中有一定的伦理教育资源,但远远不足分配给社会的大众层面。(3)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大众而言,由于缺少正规而系统的教育,因而也就缺少正规而系统的伦理道德教育,如此,伦理道德观念也就无法在社会普遍的范围内通过受教育者本人而产生直接的影响。(4)基于家庭的教育能够提供一定的“孝”的观念,但同时应注意小家庭的社会现实也会对“孝”观念形成消极或负面影响。(5)国家意识形态对先秦儒家学说的精髓或本质造成侵蚀主要反映在伦理观念方面,其中特别是佛教教义造成了传统儒家伦理和价值观念的严重混乱。(6)直至唐代,如后世宋代的家族共同体在基层社会并未出现,因此与这种共同体相关的伦理教育及其观念也并未出现。
总之,通过考察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初步的结论:从周代起形成的一套与伦理密切相关的礼制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所形成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会对以后中国社会产生影响,但在宋代以前,或在宗族共同体普遍形成之前,在以宗族共同体为基础的一整套教育途径出现之前,也就是说在教育普遍落实之前,其在上层社会可能是完整的,但在底层社会则是破碎和残缺的。简言之,宋以前中国社会的伦理是相对薄弱的。
标签:汉朝论文; 白虎通义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论语论文; 南北朝论文; 孝经论文; 国学论文; 尚书论文; 汉唐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