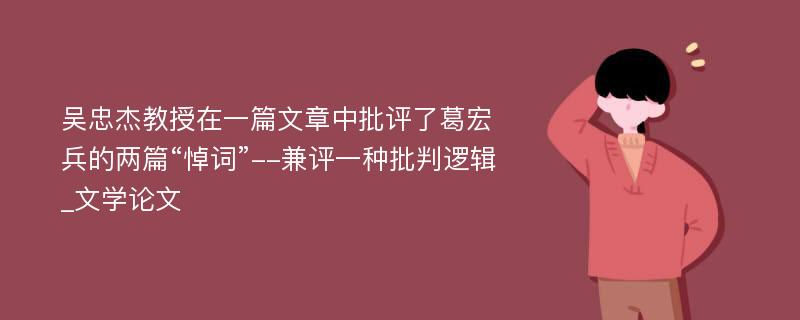
吴中杰教授撰文批评葛红兵两篇《悼词》——评一种批评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悼词论文,两篇论文,逻辑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史总是要不断地重写的,对作家作品也不应该有固定的看法。每当文学观念发生变化的时候,都会引起批评家们对已有定评的文学现象作出新的评价。这并不奇怪。但是,这种评价应该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否则他自己就难免会成为批评对象。世界上没有指点一切而不受别人指点的人物。卞之琳有诗云:“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就表现出这层关系。批评家在评衡作家时,读者必然也在评衡你本人。他们要看看你的秤星是否钉准,量具是否合适?
近年来,重评文学史的论著很多,指责名家的文章亦复不少,有的具有说服力,有的却令人看得莫名其妙。近读葛红兵的两篇大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和《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写一份悼词》,感到有“横扫一切”之势,逻辑极其混乱,简直是强词夺理。然而此等文章却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它在思维方式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值得作为个案来进行剖析。
文学批评,还是政治伦理批评?
文学批评,顾名思义,应是对作家、作品以及其他文学现象进行文学上的批评。虽然文学思潮往往与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有联系,作品水平的高低也与作家的人格力量密切相关,但文学批评的侧重点毕竟应在文学上,所以新批评派很强调文学批评的文学性。但是《悼词》的批评重点显然不在文学性上,而是在政治伦理上,同时兼及个人道德。
作者一开始就提出,他要寻找“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一种伟岸的人格”,然而他说:“很遗憾,我找不到。我宁可认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是王实味、遇罗克、张志新、顾准……虽然他们当中有的人可能一生都没有写什么文学作品,可是他们的人生就是一篇完美的诗章,他们写出这样的作品,难道不能叫文学大师吗?”诚然,这几位战士的人格都很伟大,他们为追求真理而历尽苦难,不屈不挠,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但是,人格伟大是一回事,是不是文学大师则是另一回事。连《悼词》的作者也承认,他们当中有的人可能一生都没有写过文学作品。然而,没有写过文学作品,或者偶而写过一点文学作品的人,怎么能够称得上“文学大师”呢?如果以人生诗章为选择标准来进行评论,那么你所论述的就不是文学史,你所从事的也不是文学批评。也许,这个悖论太明显了,面对别人提出的批评,作者实在无法辩解,所以在一次答记者问时,就改口道: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并非真的就是说他们是‘文学大师’了。”看看原文,语气是这样肯定,哪里是什么“比喻的说法”呢?
俗语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世界上要寻找一个无懈可击的人,是找不到的,不管他是作家或者不是作家。即使是《悼词》中所推崇的那几位,恐怕也都是有缺点的,并非“无懈可击”。报上不是已有张扬他们缺点的文章出现了吗?然而,即使这些缺点是事实,这也无损于他们的伟大。因为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是只须观其大节,考察其主要之点,而不必责备求全的。《悼词》的作者不但要责备求全,而且所责往往不是作家的缺点,有时倒恰恰是他们的优点。这只能说是作者的批评标准有问题。比如,为要“揭穿”关于鲁迅的“爱国主义神话”,作者指责道:“然而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他不是怯懦吗?”这种指责,看起来义正词严,其实却暴露了作者既不了解中国革命,也不了解鲁迅思想,却硬要将自己的错误思想强加于人的霸道作风。稍知道一点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在中国或外国,暗杀都是革命党人曾经采用过的手段,但实践证明,这虽然是英勇行为,却并非一种正确的革命策略,不可能对敌人进行根本性的打击。鲁迅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切了解,他反对赤膊上阵,主张壕堑战,提倡韧性的战斗精神,这正是他的深刻之处。而《悼词》作者却反而指责他不去执行错误路线,这岂非是非颠倒,正误混淆?而且,退一步说,即使是某项正确的行动,也不能责成人人都去做。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抗击日本侵略者,是民族大义所在,人人应该出力。但是,并非人人都要上前线,如果将所有的人都驱上战场,要求大家都拿起枪来冲锋陷阵,那么,全国倒反而会陷入混乱之中,抗日战争也无法进行了。
借用鲁迅的话来说,持这种激烈论调者,其实是“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脱离社会无视历史的酷评
《悼词》的作者实在是一位酷评家。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所谓“酷”,是指“苛刻”的意思,并非时下青年流行语中含有“俊”、“帅”之意的“酷”。
《悼词》的酷评,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脱离特定的社会环境,对作家提出非份的要求。
比如,文中指责钱钟书道:“钱钟书这样的人,他在文革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呢?他实行的是乌龟哲学,驼鸟策略,他假装专心于学术,对周遭正在发生的惨无人道的事情视而不见,强权之下,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人格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有什么资格做‘文化昆仑’?”值不值得骄傲,有没有资格做“文化昆仑”,是另一回事,但我以为,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钱钟书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以沉默表示抗争,实在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当然,他还有不沉默的时候。张志新式的烈士是值得尊敬的,但我们不能责成人人都去做烈士。只要不去同流合污,保存自己决非懦怯行为。如果按照《悼词》所说“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的逻辑,那么,我们对这位作者不去指责施暴者,而却要求手无寸铁的人赤膊上阵,是否也可以说是帮凶行径呢?《悼词》的作者不是很崇尚西方的现代民主观念吗?照这种观念看来,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决不能作无谓的牺牲。他们在战场上陷入绝境时,是允许投降的,做过俘虏的人也并不低人一等,并不受到歧视。《悼词》作者所崇拜的萨特,在1940年就做过战俘,他在德国战俘营中并没有以死来抗争,这一节,又该作何评价呢?但萨特于次年获释后,仍从事反法西斯斗争。萨特还是萨特。
至于《悼词》中所说沈从文和萧乾在运动中互相揭发,一直结怨很深,我不知道是否确有其事,尚需核实。因《悼词》中道听途说、张冠李戴、信口开河之事很多,不可轻信。如文中批评唐弢说:“‘文革’中他在四川坐牢的时候写交代材料,对鲁迅就采取了揭疮疤的方法”,而实际上唐弢在文革中根本没有在四川坐过牢,当然也无从在四川牢中揭发鲁迅了;又说鲁迅和梁实秋进行过“关于抗战文学的争论”,并指责“鲁迅在这场论争中根本不在理上,可能是因为许久找不到敌手,所以主动招惹一回罢了”,但“关于抗战文学的争论”发生在30年代末期,批评梁实秋的是孔罗荪等人,其时鲁迅早已安息在上海万国公墓中,不可能到重庆去“主动招惹”谁,更谈不上言之有理无理了。但是,在政治运动中,师生、同学、朋友、乃至夫妻之间相互揭发之事,却的确是很多的。这虽然也反映了当事者性格的软弱,但多半还是环境逼成的。《悼词》作者说:“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性命上的理由,逼迫他们这样互相揭发。”我实在羡慕他的福气,没有经历过那些运动,没有身受过当时那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但是,若要评论当时之事,至少也应该了解一下当时的社会
二是无视当时的历史条件,苛责过去的作家没有达到今天的要求。
人,总是历史地存在着,因此必然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评估一个作家的贡献,主要应看他对前人发展了些什么,与同时代作家相比高出些多少,或者有什么不同于他人的独特之处。而不应该拿今天接受者的要求去要求过去的作家,更不能虚悬一个标准去衡量作家。《悼词》的作者特别重视文学作品的“语感”,而且特别欣赏王朔作品的“语感”,这自然有他的自由,但他以本人所喜欢的语感来否定他所不喜欢的语感,就未免像苏东坡所批评的那种人,有点“好使人同己”了。对于从新文学运动初期直到40年代的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冰心、庐隐、巴金、赵树理、张爱玲等人,《悼词》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只有对老舍,表示网开一面,因为他是用北京语写作,而对于鲁迅,则更多所非难,说:“鲁迅作为一个绍兴作家,他的文白杂糅,半阴不阳的文字实在别扭,像是和读者扭着劲。”殊不知,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守旧势力相当强大,提倡白话文者被讥为“引车卖浆者流”,先驱者的工作相当艰难,他们筚路蓝缕,开启了白话文学的道路。有些人写得幼稚一点也是难免的,但几位大家,却写得很好,如鲁迅、胡适、周作人等。当然,他们也有局限性,这一点,鲁迅自己就说得很明白:“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写在〈坟〉后面》)这段话,把文学发展情况和各代作家的历史任务都说得非常清楚,可见前驱者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而后来者如果自以为在“语感”上或其他方面超过了前人,就非难起前人来,那真有点数典忘祖了。古人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如果抛开了历史观念来看问题,那么后人也会自以为是地嘲笑今日作家的语感的,包括《悼词》作者所推崇的作家。因为历史总是在前进,文学总会有发展的。
昔日的幽灵在现实中游荡
在不同的批评家之间,难免会有不同的批评标准,但在同一批评家笔下,却应该有统一的准绳。令人眩惑的是,《悼词》作者所用的批评标准却相当混乱。一会儿,拿这个标准来否定这一部分,一会儿,又拿那个标准来否定那一部分,标准可以不一,而目的却是一致的,即全盘抹杀20世纪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以便他可以写两篇《悼词》。
比如说,《悼词》作者一方面是明确地反对“拿来主义”的,他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所存在的问题,都归咎于“拿来主义”,说:“‘拿来主义’的急功近利的引进观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文体的症结所在”;“鲁迅式的‘拿来主义’是二十世纪中国文论思维的一个重要的症结,它使中国人的文论探索显得急功近利,使‘创新’没有成为真正的否定本体论意义上的‘创造’。”但另一方面,却又以西方的理论标准来规范中国文论:“我所要求于文艺理论的,是具有完善的理论结构,具有独立的范畴系统,具有周延的历史阐释力的体系,例如黑格尔式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学说体系,而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所讲的文艺思想、理论观念、美学立场,……”这不显得自相矛盾吗?
鲁迅的“拿来主义”是针对当时外国人的“抛给主义”或“送来主义”而发的。中国由于长期闭关自守,远远落后于世界强国,国门一旦被英国的大炮打开,各国势力蜂拥而至,把中国当作倾销商品的市场。“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鲁迅提出了“拿来主义”,说:“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拿来”当然没有“独创”那么冠冕堂皇,但既然我们远远落在人后,不跟上世界潮流,又谈何创造?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要强调与世界接轨的原因。没有拿来,你又何以晓得世界上有个黑格尔,更何况他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学说体系”,更无从向文艺理论界提出建造黑格尔式理论体系的要求了。所以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两个“自”字,很值得深思。
当然。要真正拿来有用之物,亦非易事。鲁迅说过,那些具有自由平等气息的外来思想,在中国“实没有插足的余地”,他把中国比作一个黑色的染缸,说是任何外来的东西一掉进这个染缸里,都会被染成黑色,失却本来面目。引进的东西尚且如此,何况还要拒绝拿来呢?我看,在《悼词》作者的脑子里;旧意识就太多了一些,虽然他挥舞的是新的旗帜。比如,那种“横扫一切”的架势,那种历史空白论的调门,那种以政治标准来涵盖一切,而这政治标准又订得十分狭窄的做法,那种无视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况而作出的酷评,那种批评逻辑的混乱和强词夺理乱加人罪的锻炼周纳方法,以及那种要人死而不要人活的伪革命主义,等等,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并不陌生,这是当时流行的观念形态和常用的整人手法。不幸的是,这些东西却被文革时期刚刚出生,在运动中还不大懂事的人所继承了。《悼词》作者的批评方法和思维逻辑与那时的整人方法和锻炼周纳的逻辑是多么想似啊!这是集体无意识的积淀,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
其实,文革中的大批判模式和整人手段;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制度的产物。这只要看看历代帝王酷吏的行径,就可明白。20世纪的历次政治运动,继承和发展了此种套路,使其臻于完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种种作为,只不过是集其大成而已。“文化大革命”虽然早已经宣布结束,而且被明文否定,但是,深层的文化结构如果不加以改变,长期形成的旧有思维模式就难以涤除,因为此类思维模式的存在,就是以这种文化结构和与此相关的政治体制为基础的。此类思维模式和整人手段,本应充分揭露,彻底清算的,只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深入彻底。巴金曾经建议成立文革博物馆,也是要大家不要忘记这场浩劫的历史,从中吸取教训的意思,可惜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而错误的东西余毒未尽,就必然会在其中发酵,继续散发毒菌,到得一定的时候,说不定历史的悲剧还会重演。某些新生代人物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鲁迅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对历史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是刻不容缓的了。这种总结,不仅要在政治层面上进行,而且还应深入到思维模式中去。
标签:文学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葛红兵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