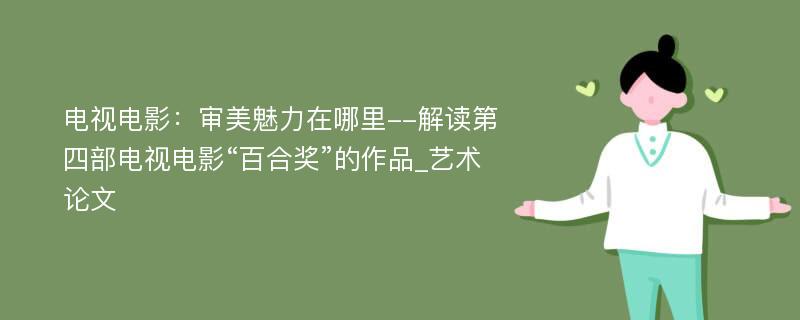
电视电影:审美的魅力在哪里——观第四届电视电影“百合奖”作品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电视论文,电影论文,札记论文,第四届论文,百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初夏时节,蓦然回望,但见又一度“百合”新葩绽放,姹紫嫣红,气象喜人。以2003年度电视电影作品总的面貌来看,在110部的总产量里,有60部作品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并进入了“央视”收视率的前30名,占电视电影总播出作品的半数以上;而其中贴近现实的作品则在其播出总量里占到了73%。笔者注意到该年度一些领衔、获奖之作,大多出自年轻艺术家之手,作品在结构的张力、形象的深度以及风格、样式的多元性探求等方面,均堪与电影相媲美,同时也显示出了一种可贵的艺术创新的锐气。
匆匆五六年的时光,中国的电视电影由蹒跚学步而渐趋成熟,并锐意求新而自成一派气象。自1999年迄今,每年生产电视电影的总量在100部上下(在2000年竟达131部),这大体上相当于我国各电影制片厂家(含民间影视制作公司)摄制电影故事片的年度总和。近五年来CCTV—6总共制作了600余部电视电影作品,播出总量达544部,其中如《法官老张轶事》、《情不自禁》、《王勃之死》、《古玩》、《劲舞苍穹》等等,其艺术个性的穿透力以及镜像的质感和韵味,至今仍为大家津津乐道、称赞不绝。电视电影在如此短短的数年间,竟能“从无到有”,并创下了如此出人意料的佳绩,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从电影与电视两个巨人的肩膀上“站立”起来
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电视电影以投资低、风险小、技术新、制作周期短的特点而成为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的“轻骑兵”,它在发挥审美想象以及张扬艺术家主体性的创造力上,显示了一种无可替代的优势。
有人曾说,电视电影是站在电影与电视两个巨人的肩膀上诞生的,其镜像语言和艺术品质,显然具有“扬电影故事片之长而避电视剧之短”的兼容性。随着数字化高清晰度技术发展的趋势,电视电影既可以在数字影院的大银幕上按照电影的方式放映,又能在比银幕更大、更广、更具大众“亲和力”的电视空间里(包括数字和光纤电缆传输),进行无远弗届的传播。而在未来的审美流变中,它显然将不懈地向银幕的影像素质和叙事的审美境界日渐靠拢、提升,并且能与之比肩而立;同时,它将和电视剧“快餐式故事消费”的模式,保持一种清醒的距离。尽管目前我们尚不能对电视电影的艺术特性作出更为准确的界定,但是,电视电影作为后起之秀,它在现代传媒空间里无可取代的文化强势及其审美潜力,则无疑受到了有识者的垂青和人们普遍的关注。
将形象上的每一点都化成灵魂的眼睛
年轻而富于艺术个性的创作者,其叙事观念追求一种现代性和开放性,是不会以“故事的快餐化”为满足的。一部电视电影离不开一个好故事,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作为艺术对现实的关注和把握,侧重的则是如何达成故事的审美化。好故事之所以具有艺术的张力并感人肺腑,显然并不单凭感官式的外部动作的刺激,也不是靠故事的纯技巧性(如悬念吊紧、情节跌宕)的编织,更要紧的是,如何经由创作者主体的生命体验和情感浸润,从而赋予故事以人文的、审美的底蕴。黑格尔老人说得好:“艺术也可以说是要把每一个形象的看得见的外表上的每一点都化成眼睛和心灵的住所,使它把心灵显现出来。”(《美学》第一卷)一个好故事的结构张力,大约正是寓于斯又成于斯的。
特别是面对全球性的文化语境,我们如何能发掘出独特的、为他域文化所无可替代的本土人文资源、人文亮点,并将这种“人文亮点”转化为审美化的故事,呈现出其自身立于世界之林而独张一帜的文化的、审美的魅力,这堪称是极具挑战性的一个现代审美课题。
人们看到,《野狐梁的女人》、《法官老张轶事之审牛记》以及具有革命历史传奇性的《曾克林出关》,它们的故事结构之“核”,无不呈现出清新而独特的本土人文底蕴,并透现出内在心灵性的张力,即便置诸全球性的空间里,它们也不是以其“泛主流”的意识形态书写为特征,而是真实地呈现在文化/审美上有容乃大、情采焕然的艺术感染力。《野狐梁的女人》和《审牛记》,讲述的都是平常、平实的农村故事:一个是写人的生命在沙漠化环境中十分独特的“韧”性的生存;一个是写农村里因“丢牛”、“寻牛”而闹到法庭,打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审牛”官司。这两部作品的“事”,都落实在被制约于古老农耕文明的诸般“看得见的”叙事点上;而透过这些叙事点,真正令人心悸的则是“人”的命运和性格,于是这些“事”,都化成了“灵魂的眼睛”。
《曾克林出关》属于革命历史题材里“中国名将系列”的一部作品,创作者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的背景上,跳出了一般侧重写赫赫战功或战略成败的刻板套子,却以富于传奇性的浓墨重彩,着力塑造了曾克林威猛、刚烈、生龙活虎的军人性格。影片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曾克林所部与苏联红军之间,从陌生到建立共识和情谊的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在“故事”细节的一个个“点”上——比如曾克林缴获来一辆敌军的吉普车坐上就敢开,一开便撞墙;再如他在与苏军谈判中竟敞怀连饮十二大杯白酒而酩酊大醉,以此竟从苏军司令员那里换来了急需的十二座军械物资仓库——凡此种种,无不艺术地折射出那一个特殊历史年代的社会风貌,同时让人看到了一个刚烈而富有智慧的中国名将的人性风采,艺术地升华出一种震撼心灵的冲击力。
艺术风格标新立异、多元竞胜的可喜趋势
常听人们批评当下电影市场低迷不振,电影风格、样式单调、单一,然而在电视电影创作领域,却另有一番风景。我们年轻而富于创新锐气的艺术家,近年来在电视电影风格、样式的多元性上作出了别具新意的探求。
《乔二中彩》、《黄河行歌》,都取材于当下农村的现实,主创者却善于从改革开放后因受商品经济冲击而引发的农村现实关系的深刻变化中,敏锐地捕捉并提炼出鲜活而别具新意的艺术形象来。其中《乔二中彩》选择了风俗喜剧的样式,作品描写农村青年乔二进城打工,摸彩竟中了大奖(一辆捷达轿车),不料为争夺“大奖”归属以及如何分利等等,竟在村子里和自己家里引发出一连串的喜剧纠葛,随着情节的推进,一层层揭示了金钱对于纯朴的乡风以及邻里、人伦亲情的扭曲,在令人开怀解颐的笑声中,却潜藏着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在取材于都市众生相的作品里,《马世清离婚》和《咱得有辆车》不止以颇具喜剧情趣的样式强化了作品的观赏性,并且,创作者对生活、对底层的小人物,分明有着慧眼独具的洞察和亲切的体验,作品里自然也就浸透着一种真切的人文关怀之情。《微笑》与《乡医》这两部作品,则对于2003年春夏那场惊心动魄的抗击“非典”的斗争,从城市、农村两个侧面捕捉到了许多真实感人的形象,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人民的记忆”。特别是《微笑》中所刻画的“白衣天使”蒋琳医生的形象(由王姬饰演),临危受命,后因感染病毒而辞世,创作者着力从人性的深度上呈现出她内心世界的美,令人铭记难忘。
本届“百合奖”的另一个收获是,依据“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名篇改编的《贞贞》和《为奴隶的母亲》,它们为我们对文学名著进行改编和再创作,无疑积累了不乏文化建树意义的实践经验。这两部作品,以原著人物塑造的文学成就为基础,通过影像造型语言的二度创作,更生动、更形象地揭示了人物命运和性格发展的独特轨迹,艺术地折射出历史岁月的刻痕和沧桑,从而达到了一定的审美概括力。这两部作品,采用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改编方式,一种是对原著持较严谨态度的改编模式,基本遵循原著的主要人物关系及其结构框架,根据柔石同名小说改编的《为奴隶的母亲》,将作家笔下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浙东一带农村里的“典妻”悲剧,从现代的视角给予了具有相当冷峻而沉重的艺术再现;另一种则属于在忠实于原著文学精神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再创作的模式,如《贞贞》即以文字标示,这是“取材于”丁玲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原著的历史背景是上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创作者将女主人公贞贞曾遭到日军强暴而沦为慰安妇的“命运线”予以重新梳理,并增加了若干传奇性的重要人物和情节,以朱老四为首的山寨草莽匪徒自发地奋起投入抗击日军的战斗,贞贞在逃出日本兵营后曾在山寨栖身,并与朱老四产生了感情,后来,她亲自目睹山寨被鬼子血洗,朱老四等人全部惨遭屠杀,这一段人生经历,有力地展示了贞贞在忍辱负重中性格的成长。贞贞最后全身绑上了炸药,重新走进日本兵营,舍生取义,与鬼子兵同归于尽。贞贞的形象,是含着沉甸甸的历史悲怆性而被升华到悲剧美的高度的。这样的改编,无疑是付出了非同寻常的艺术劳动的,因而也是值得予以充分肯定的。
拍摄和制作,半数实现“数字化”
说到上述作品艺术创新的努力和开拓时,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本年度入围“百合奖”的25部作品里,用高清晰度技术摄制的作品共有17部,占了半数以上(在全年总量110部作品里,用高清晰度拍摄的作品共有52部,约占近半数)。由于在数字化技术上支持力度的强化,电视电影在影像造型的技术/艺术素质上乃得以步步提升,它与用35mm胶片拍摄的大银幕影像之间的差距已渐趋缩小,显然,这就为电视电影制作者提供了艺术创造的较大自由度,本文上面所涉的大部分作品,显而易见,与这一创造的自由度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