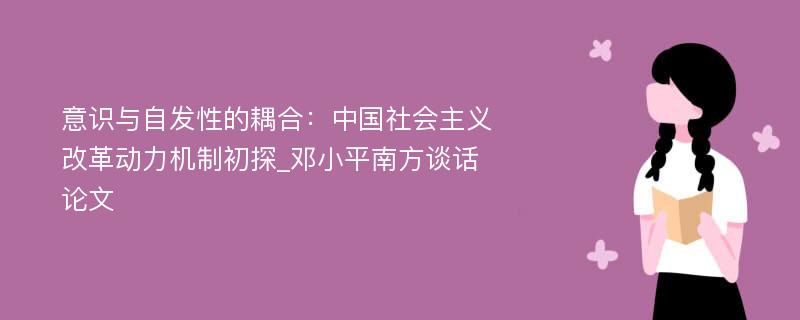
自觉与自发的耦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动力机制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觉论文,机制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本世纪7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改革在中国终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渐次推进和不断深化的全面改革,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拓新境界的强大发展动力。认识到这一点,并进而去深入思考与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运动本身的动力机制,对于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在规律,应该是有价值的。
本文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历时20年不竭推进并仍在向着既定目标继续深化的内在动力机制,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导力量与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有胆有识之士的高度自觉,同广大人民群众中经常发生的强烈要求改变现实生活状况的广泛自发之间的有机耦合。耦合本来是一个物理学上的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在此借用来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动力机制,可以看到,自觉与自发的耦合,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产生不竭动力的内在机理。
(一)
执政党主导力量的高度自觉,首推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众所周知,被誉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最自觉的推动者。人们从他在1975年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极力推行以整顿为名义的改革试验,就可以感受到在内心驱动邓小平一往无前的正是那种高度的自觉。他在1976年末至1977年初,“经过反复考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39页。),要求重新出来工作,同样是基于那种高度的自觉。当他又一次在党和人民的推戴下重新出来工作以后,就更加自觉地大声疾呼:“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150页。)当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以后, 更是一次又一次地明确表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每当改革的进程遇到阻力,碰到难题, 或是处在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总是由他出来排解和推动。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新老交替,形成新的领导集体的过程中,提出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要用人们公认的改革者”,“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在他88岁高龄那年的南方谈话中,仍然鼓励处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同志们“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页。),要求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372页。),继续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推向前进。
执政党主导力量的高度自觉,还可以从与邓小平协力担当改革决策重任的一批知名的老一辈领导人的身上,从那些处在实际工作领导岗位上的负责人勇于拨乱反正开拓进取的工作实绩中,从党内从事思想理论工作的专家学者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的字里行间,从那些为党的领导进行改革决策而提供各种咨询及各种思路的人们所从事的大量必要的基础性调研工作中,得到体现和证明。有了这一系列的高度自觉,才能保证来自于邓小平的第一推动力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得以传导和放大,产生有效的实践功能。
(二)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一个伟大历史人物的高度历史自觉,一旦能够转化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向着同一历史方向的社会实践,那么促成这种转化的就不会仅仅是这个历史伟人个人的自觉。其中必定会在社会的各个不同层面上,得到众多不同程度的自觉者的响应和共鸣,使得这种历史的自觉经过逐级的巩固,得以转化放大,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切实的推动力。但是,人们却往往不大注意,除了处在社会的显著位置和关键岗位上的自觉者外,在社会的基层,在普普通通的人民群众当中,也总是有一批“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自觉者,历史决不应该无视他们。本文在关注和思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势在必行的强劲动力时,把眼光也尽可能多地投向人民群众中的那些高度自觉的有胆有识之士。他们以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乃至宝贵的生命和自由权利的代价,极力向世人证明,旧的那一套所谓的“社会主义”搞不成,不改革死路一条,以下仅举几例为证。
《民主与法制》杂志曾在1986年第4期, 以《九死一生献国策》为题, 详细披露了四川省雅安地区一位名叫李天德的中年知识分子, 在1975年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期间,冒死向中共中央和人大常委会递送《献国策》万言书,要求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天德在《献国策》中深刻反思了反右扩大化与“三面红旗”的问题,痛斥了种种“左”的行为;并尖锐指出了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要求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还建设性地提出了12个方面的国策,实际上是要求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进行全面的改革。
这份超前的思考,是李天德在逆境中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真思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的心血结晶,也是他所具有的高度自觉性的真实写照。他19岁那年在重庆大学冶金系念书时就被错划右派。以后的岁月中他又因不改忧国忧民的初衷而两次被错误判刑,1972年10月刑满,戴“反革命”帽子在四川苗溪茶场管制劳动。在劳改期间,他坚持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一些世界哲学名著,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他曾在一份所谓的《反省书》中写道:“对于我个人的言行,勿需反省,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我坚持我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各国共产党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党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由于李天德当时的身份和《献国策》万言书的内容,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立即被捕入狱,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后经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复议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获平反昭雪。历史最终承认了《献国策》的价值和李天德的胆识。负责对李天德落实政策的四川省委组织部长在调阅了曾被作为“反革命罪证”保存下来的《献国策》后,不由得连声道:“好,好,真是个难得的人才!”1985年4月, 这份《献国策》被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征集收藏。《人民日报》海外版曾以一则短讯向全世界报道。
像李天德这样普通而又不凡的自觉者在社会主义中国并非绝无仅有。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悠久历史传统,并且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早就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为立国的最高准则的人民共和国里,类似于这样的具有高度自觉性的优秀公民并不罕见,仅仅在团结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的《“文革”洗冤录》中, 就收录了好几位。王正志是其中的又一个典型。
王正志是成都大学统计系65级学生,共青团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在成都闹市区散发写明真实姓名地址的传单,痛斥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而被拘捕,1968年1月判为无期徒刑。 他自觉地把刑期变“学期”,在狱中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写出了20多万字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体会和有关文章,率直地提出了对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他在其中一篇题为《谈经济建设及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文章中写道:“革命胜利后,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重心,是国家一切任务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转。”他在文中还具体提出了许多建议,例如尽快培养一批具有新思想、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恢复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奖励制度;下放管理权限,扩大地区和企业的自主权;允许在国家统一计划前提下的自由竞争;在农村,加强生产责任制,允许“三自一包”;等等。他的这些观点,1975年以后也出现在邓小平的一系列谈话讲话中。1978年底以后又出现在党的文件和报刊杂志的社论中,并且逐步变成为党和国家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中实行的新政策,终于成为中国人民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然而,在1968年,这些观点却是一位不到20岁的大学生用戴着手铐的手,在牢房里写出来的。
王正志的事例,再一次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力量。可以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所获得的理性智慧和精神力量,是所有真正具备自觉的改革意识和大无畏胆略的人们所共有的特性。有了这一特性,地位悬殊,年龄迥异,阅历不同的人,往往都可以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问题上达到共同的认识,产生高度的契合。
从上述实例中,还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性自觉,早已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中酝酿生发。邓小平不是孤立的,李天德不是孤立的,王正志也不是孤立的。这就是为什么1975年邓小平推行的全面整顿作为改革的前奏,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奏效;为什么1978年底以后的改革浪潮能够在中国全面兴起和不可逆转的一个答案。
(三)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顺利起步和蓬勃开展,除了具有不可缺少的理性自觉之外,还在于这种理性自觉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状况和中国人民的现实要求,同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基于自己的切身感受而自发地进行变革,或要求变革原先那一套“社会主义”的做法和愿望相契合。使自觉得到了自发的呼应和证明,也使自发得到了自觉的引领和支持,最终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积聚和迸发出强劲的推动力。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首先从农村改革成功起步,就是自觉与自发耦合的一个典型例证。改革从农村开始并不是什么人事先设计好的。农村改革由安徽省的农民率先挑头,也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定动员和亲手发动。而是因为在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和旧的那一套经济运行体制下,农村与农民的贫穷更甚于城市与其他人口。其中,安徽农村更是受到“左”倾错误折腾的重灾区。事实证明,“左”的错误危害往往要比自然灾害尤烈。1989年12月,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乡村三十年》的书。这本近百万字的专集,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与中共滁县地委在1981年共同商定的一个科研项目,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实录了安徽省凤阳县在建国以后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从记载中,人们可以实证地了解到,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而刮起来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生活特殊化风),是怎样直接导致了农业生产力的大破坏、大倒退。正是生产的严重窘迫,迫使农民群众自发地搞起了“责任田”,其实那就是50年代中期就曾经在广西、浙江、安徽的一些地方出现过的包产到户。 到1962 年10月中旬,安徽农村就已有84.4%的生产队自发实行了“责任田”(注:吴象:《“要吃米找万里”民谣的来龙去脉》, 载《炎黄春秋》1994年第8期。)。农民普遍感到有奔头,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耕畜农具增加,庄稼种得足,管得细,长得好,收得多。然而,农民群众的这种自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当时却得不到来自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支持和肯定,反倒被认为是刮了“单干风”,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而遭强行压制。尽管从基层到中央都有不少干部和党组织上书、争辩,提出正确的建议,但是从1962年8 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革命”的调子越唱越高,但农民的日子却越过越糟。
以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为例,20户农民几乎岁岁填不饱肚子,年年有人外出讨饭。住的是破房,十多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常常是一家人只有一条外出穿的裤子。更为严重的是,小岗村的人心也被“阶级斗争”搞散了。从1958年到1978年几乎年年是“算盘响,换队长”,在台下的斗台上的。20户人家几乎都当过生产队长,但是人心始终拢不到一起,生产仍然搞不上去。面对1978年的那场百年未有的大旱灾,小岗村农民为求生存别无选择, 自发地再冒风险偷吃“包产到户”禁果。 1978年11月24日,当时的生产队长严宏昌做好了“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召集了一次平时很难召集的群众会。20户人家除两户无人在家外,18户的户主立下一纸“分田到户”的合同书,个个签名按下指印,人人赌咒发誓,永不反悔。就是有了这个自发的合同,小岗村从过去最难缠的穷队,一跃冒尖。1979年全年的粮食产量相当于过去5年的总和, 人均产粮1200斤,油料作物的总产量比这个村实行农业合作化以来20多年的总和还多,全年人均收入即达到400 多元人民币(注:见拙著:《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中国社会主义之路》,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6 月版,第191页。)。小岗村一举脱贫,令人刮目相看,令人重新思量。
小岗村的农民是幸运的。他们自发选择生存出路之日,正是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时。经过几番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严肃较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始了重大调整,中国的历史进程开始了重大的转折,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自觉力量也开始逐渐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占据主动,成为主流。因而,当小岗村等地的“包产到户”面对姓“资”姓“社”的重重质疑,和当时的中央文件仍然明确规定的“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的禁令,在凤阳县却能够得到县委书记陈庭元的大胆支持,在安徽省又能够得到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充分肯定和鼓励推广。在中央,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大力赞同。1980年春,陈云见到万里,合掌抱拳,高兴地说:我完全赞成农村政策方面的那些做法(注: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251页。)。 在农村改革引起激烈争论,并在一些地方出现反复的关键时刻,又是邓小平出来讲话,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支持和肯定了安徽农民的改革创举,为全国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
1980年5月31日, 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页。)这个讲话传到安徽时,一些农民心中犹如石头落地,有的流着眼泪说:“邓大人真是我们的大恩人!”(注: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251页。 )万里就曾经动情地说:“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1980年春夏之交的斗争,没有邓小平的那一番谈话,安徽燃起的包产到户之火,还可能会被扑灭。”(注: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人民出版社1995年10 月版, 第251页。)
当然,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确立的正确领导也是幸运的。就在党自觉地作出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之时,在中国人民中就已经有那么一些农民群众自发地为新的时期新的道路提供了新鲜的创造和成功的经验,使得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能够得到具体的回应,从而就能不断地以实践为依据,在政策上和理论上不断地调整原有的结论,反映崭新的认识,逐步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从局部走向全面,从浅层次不断深化,开拓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境界,展示了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前景。这就是自觉与自发耦合的力量。
(四)
自觉与自发的耦合,也就是党心与民心的沟通。这种耦合与沟通不仅是社会主义改革必需具备的动力机制,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列宁在创建和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早就深刻地体会到:“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注:《列宁全集》第26卷,第259页。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种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注:《列宁全集》第3卷,第483页。)实践证明,在世界上曾经存在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尤其是其中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数,同广大的人民群众相比较,始终只占少数。如果忽视了人民群众自发的努力,也就有可能会忽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自发的努力,执政党治国的路线方针政策都难以正确地制定和真正地落实。在人民群众的自发的努力之中,永远蕴藏和不断创造着自觉的因素和自觉的基础。
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领导的自觉程度,又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自发创造是得到保护引导还是遭受压制摧残。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制度和领导体制的现有特点所决定的。具有高度自觉性的共产党人在推动历史车轮向着既定奋斗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务必要始终注意把自己的自觉同人民群众的自发相沟通相耦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胜利坚持20年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意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邓小平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中多次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2月版, 第30~31页。)这也就是自觉与自发的耦合。只有像邓小平那样,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这种耦合。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新征途上,自觉与自发的耦合,党心与民心的沟通,应该继续成为自觉的共产党人始终注意营造与维护的必要的动力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