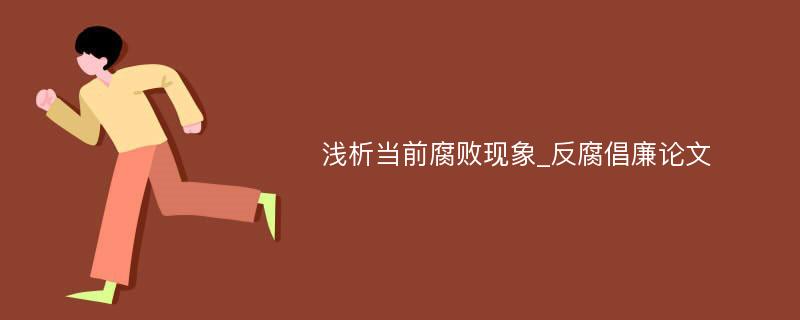
当前腐败现象初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腐败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斗争形势如何,怎样分析符合实际情况?江泽民总书记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在这个问题上要讲两句话:一句是,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廉洁奉公的。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广大党员、干部同群众团结奋斗的结果,反腐败斗争也是有成效的,这些都是基本的事实。另一句是,在党内、在国家机关中确实存在着腐败现象,有些方面还在滋长和蔓延、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深感忧虑,迫切希望采取坚决措施加以解决。我们不能否定党的主流是好的,也不能低估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江总书记的上述分析是实事求是的。
新时期腐败现象滋生蔓延总的特点是起伏性。所谓起伏性,是指腐败现象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呈现时起时伏、时高时低的状态。据资料统计,从1982年至1989年间,处分违纪人数有三个高峰,两个低谷。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当诱发腐败的因素强于抑制腐败的因素时,腐败现象就会呈上升趋势;当诱发腐败的因素与抑制腐败的因素势均力敌时,腐败现象就呈平缓态势;当抑制腐败因素强于诱发腐败的因素时,腐败现象就会呈下降态势。
新时期腐败现象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经济违法案件上升,金额越来越大。
1957年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贪污犯罪率极低,一般年份的发案仅有两三千件。1976年至1996年贪污犯罪呈上升态势,平均侦破贪污案件均为1万件以上,多的年份达2万件以上。1994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案件高达30793件,比上年上升69.87%。1995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经济违纪案件又比上年上升14.64%。从1993年至1996年5月,全国金融系统共查处的8000多件案件中, 80%是万元以上的大案。上百万、上千万的违法违纪案件也不时出现。
第二,领导违法案件增多,发案层次升高。
以前,如果县处级干部因经济问题受制裁,影响就很大,例如广东省原海丰县委书记王仲。现在,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违纪违法案件中,不但卷入了一般党员干部,还涉及地(厅)级、省(部)级干部。据统计,1992年10月至1997年6月共处分省(部)级干部78人。1996 年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和地(厅)级以上干部,分别比上年增加了20.25%和8.17%。1997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县(处)级以上干部的案件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2.46%, 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的案件增长49.52%。
如果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领导干部犯错误有如下特点:一是从层次上的分布看,位显权重者发生频率较高。据江苏省某市的一份材料分析,犯错误的县(处)级领导干部中,正职干部犯错误的占全部正职干部总数的6%,而副职干部犯错误的占全部副职干部总数的3.3%。相比之下,正职要高出2.7个百分点。在同样职级的岗位中,居于权力较重岗位的干部犯错误的数量也明显较多,往往比较容易成为别人拉拢腐蚀的对象。二是从年龄上的分布看,年高年少者发生频率较高。据统计,上海市1994至1996年被查处的局级干部中,59岁上下的竟占三分之二。江苏省1995年处分的12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中,50 岁以上的有80名,占犯错误干部总数的66%。浙江省检察机关1996年1-6月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犯罪案件中,50岁以上的有29人,占50%。一些老同志为革命辛苦一辈子,劳苦功高,但在即将退休之前却没有经受住考验,抓住“即将作废”的大权捞上一把,最终落得泪洒黄昏。而一些仕途较顺的年轻领导干部,由于受党内政治生活的严格锻炼不够,容易飘飘然昏昏然,忘乎所以。这些人盲动性较大,胆子也大,一旦违纪违法大多是大案。
第三,顶风作案现象严重,新发案突出。
尽管加大了反腐败打击力度,但仍然有人铤而走险。检察机关1994年查办的案件中有60%左右是当年作案的。1996年纪检监察机关累计办案的179569件中,当年立案的168389件,比上年增加8.3%。 有些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大肆顶风违纪违法。如1991年首钢特钢原总经理管志诚因索贿、受贿、贪污人民币150多万元而被判处死刑。但是, 就在管志诚被处决后不到两个月,继任者杨立宇等又受贿7000元,后来在一笔业务中受贿150多万元。1995年1月,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总经理阎健宏,因贪污受贿被送上断头台,但继任的总经理向明序,又在不满一年的时间里因受贿、赌博、嫖娼而被捕。
第四,团伙、群体作案,窝案、串案增多。
这种团伙群体作案涉及人员多,案情复杂,往往有一案带多案、查处一个带出一串的特点。山东省泰安市因查办一起经济诈骗案带出了包括市委书记胡建学在内的市委、市政府多人违法违纪案,涉及5 名地(厅)级干部,10多名县(处)级干部,有近30人被逮捕。1990年广东省英德县查处了县公安局局长张文列受贿30万元的严重经济犯罪案后,以此为突破口共挖出经济违法违纪分子221人,内有科局级以上干部60 多人。团伙群体犯罪,往往是手段隐蔽狡猾,欺骗性大,不易被识破,一旦被发现又互通信息,建立防线,转移证据,互相保护开脱,从而增加了查处案件的难度。
第五,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富了“和尚”穷了“庙”。
一是信贷中以贷谋私严重。人情信贷、有偿信贷(吃回扣)、行政命令信贷等,造成大量呆帐和死帐出现。二是在经济承包中包盈不包亏。盈了,个人多得;亏了,国家补偿。三是借机在多种经营或人员分流办公司中,变国家资金为集体资金,变集体资金为个人所有。四是在合资或合作企业中让利私分。五是“小金库”挖“大金库”,领导想怎么挥霍就怎么挥霍。六是借搞股份制之机,低估低评国有资产。七是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国外,归个人所有,中饱私囊。如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原负责人于志安,私自将该公司以他的名义在海外注册的1370.5万股的股份转移,本人潜逃国外。再如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向国外转移巨额资金,然后带一家8口人外逃。
第六,腐败分子触角伸向新的领域,腐败行为向新的领域拓展。
在改革开放中,新的经济领域拓展到哪里,腐败分子的触角便伸向哪里,如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股票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高科技市场等。如1996年金融系统涉及金额100 万元以上的经济案件就有115件,其中千万元以上的有19件,总计金额达18亿多元。 大多为挪用、贪污、贿赂犯罪。涉案的支行行长副行长、支公司正副经理、分行行长共有188人。一些金融系统的工作人员, 利用电脑等高科技手段作案,增加了破案难度。
第七,由经济领域向司法和领导机关蔓延。
80年代初期,腐败的“源头”始于生产、经营型的经济部门,紧接着波及的是与生产经营部门密切相关的社会服务性部门。接着又波及到管理短缺的生产资料和其它生产要素的部门。再接下来便波及到对生产、经营和服务性事业单位的活动行使监督管理的经济监督部门,以及行政执法部门。最后,逐渐渗透到司法机关和党委领导机关。这是一个很值得引起警觉的现象。腐败现象侵蚀到专政机关,一些执法执纪人员执法犯法,有的贪赃枉法,循私舞弊,这使得神圣的国家权力蒙受到玷污。在组织人事工作中,一些人投机钻营,跑官要官,甚至重金买官,卖官鬻爵,性质恶劣,影响极坏。上述现象说明腐败现象已渗透到很深的层次。
第八,由沿海地区向边远地区辐射。
我国改革开放是从沿海地区开始,再逐步向内地和边远地区发展,于是消极腐败现象也由沿海向内地和边远地区辐射。80年代初,沿海地区贪污犯罪发案率比内地高,更大大地超过边远地区,而后内地经济犯罪案件迅速增加,最后连一些边远地区、甚至穷困地区的贪污犯罪也越来越多。开始时罪犯贪污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特大案件,一般都发生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现在内地和边远地区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案件也屡见不鲜,贪污手段也更加隐蔽化、智能化。通常在沿海地区新出现的贪污贿赂犯罪手段,经过一定时期会在内地和边远地区出现。
第九,道德败坏案件大幅度上升。
1995年上海市因道德败坏受到党纪处分的有237人,其中嫖娼136人,比上年上升61.9%。1996年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案件15003件,比上年增长11%。近些年来,享乐主义、 拜金主义逐渐在领导干部中蔓延,利用权力搞权色交易、搞不正当两性关系的大有人在。色,往往是领导干部中最薄弱的环节,最易被攻破。社会上的一些不法分子,往往是通过诱之以色打开缺口的。
第十,先进模范人物违法案件增多。
吉林省总工会原副主席薛景文、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武汉长江动力集团总经理于志安、甘肃省机械厅原厅长李连维等违法违纪分子,原来均是全国劳模、“五一”奖章获得者和各类先进模范人物等,但最终都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走向犯罪。
第十一,搞感情投资,编织关系网。
一些犯罪分子惯用的手法是勤打点,施厚礼,联友谊。他们对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掌管实权的人员,百般殷勤照顾,挥霍国家的钱寻找靠山,网络关系,建立自己的“保护区”。如腐败分子刘金生先后将集体企业的8辆小轿车, 分别送给陈希同及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长期使用,用物质享受网络关系。
第十二,腐败“黑数”比例不小。
所谓腐败“黑数”,是指有违纪犯罪存在,但违纪犯罪统计上却没有的违纪犯罪数。有一些掌握一定人财物权力的党员干部,暗中贪污受贿,已堕落成腐败分子。他们善于伪装,台上反腐败,台下搞腐败。有的腐败分子既不是群众举报揭发出来的,也不是专门机关调查出来的,而是因小偷光顾才把问题暴露出来的。
以上所分析的新时期腐败现象的几个特点触目惊心,但并不表明腐败问题已是“不治之症”,而是为了使人们对腐败现象有一个更加清晰和全面的了解,找出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内腐败现象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这对于预防和惩治腐败,促进廉政建设,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