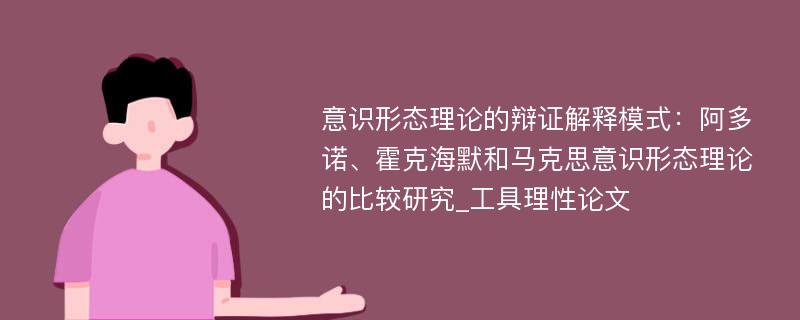
意识形态理论的“辩证”阐释模式——阿多尔诺、霍克海默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马克思论文,理论论文,多尔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013-05
一、意识形态理论的本体论维度:启蒙精神或工具理性是否为一种本体论的存在
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看,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的意识形态理论坚持“启蒙精神”或“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化,即把启蒙精神以及其在现实层面的具体体现工具理性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性的存在;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则没有赋予启蒙精神和工具理性以本体论的意义。前者在讨论具有本体论性质的启蒙精神和工具理性问题时,所涉及的批判对象(即意识形态批判目标)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对象有相似之处,即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然而,首先,前者主要是从德国近现代哲学的批判(如阿多尔诺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以及霍克海默对近代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批判)入手,上溯到对德国古典哲学(包括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的。其次,前者在对哲学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时,是将主要批判点放在了传统哲学思想所具有的非同一性特征以及非批判性特征,而马克思则将焦点放在了传统哲学(尤其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所具有的唯心主义色彩上(尽管阿多尔诺在进行非同一性批判时,也多少涉及到了对黑格尔等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的批判,并还因此而被西方学者称为“唯物论”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兴趣却并不在对唯心主义性质的揭示上)。第三,在进行这样的意识形态批判时,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纯粹哲学的“天上”层面,而是将批判理论付诸“尘世”生活,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入手,深入分析了导致精神文化层面异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经济根源,而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则仅仅停留于艺术美学等文化工业层面(尽管他们在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时,将批判的矛头都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异化了的和意识形态化了的被操控的世界)。
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在意识形态的本体论维度,主要是从批判德国近现代哲学(如阿多尔诺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以及霍克海默对近代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批判)开始构建其意识形态理论的。当然,这一构建工作的基石,就是赋予启蒙理性或工具理性以本体论式的存在意义。他们所说的“启蒙”,并非仅仅指起源于17-18世纪的那场特殊的启蒙运动,“而是泛指人类社会在近现代的理性化进程中所发生的所有强调理性至上性和人对自然的技术征服的启蒙运动或思想解放历程”。在他们看来,“以理性和技术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对自然的统治权为宗旨的启蒙最终走向了反面,走向了理性的启蒙的自我毁灭和理性对人的统治的悲剧”。[1] (P133-134)也就是说,启蒙理性意识形态化了,并变成了工具本身,因此,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就是对启蒙理性或工具理性进行批判。
他们所进行的这一批判活动本身不仅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经过卢卡奇改造后的“物化”概念)那里借用了“异化”概念用来表达启蒙精神的意识形态化,而且还沿用马克思的批判路径,将对现实的批判延伸到对这一现实的理论根源——即对哲学思维根源的探讨之中。也就是说,他们都将理性认识或启蒙精神的意识形态化视为是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必然产物。由此,对启蒙精神或工具理性的批判,在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这里也就演变成了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
阿多尔诺指出,“当代哲学最终在海德格尔这里以一种貌似革命的形式与资本主义制度、物化世界达成共谋”。“为了能够实现对海德格尔哲学的内在批判,‘用它自己的力量来反对自己’”,阿多尔诺采取迂回战术,把批判的锋芒首先指向了克尔凯郭尔及其生存概念。在他看来,克尔凯郭尔并没有“‘击败’黑格尔的同一性体系”,哲学人类学“不过是人类学生存论维度上的内在化的异化史观”。克尔凯郭尔不是把唯心主义祛除了,而是把它“内在化”了。“现实的异化不是作为一种历史形成的‘恶’受到了批判和扬弃,而是作为人的新的本性被肯定下来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妨说,阿多尔诺是在为《德意志意识形态》补写‘圣克尔凯郭尔’章”,因为克尔凯郭尔“生存哲学的逻辑结构其实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史观是极其一致的:异化是历史地形成的人的生存状态,人的本质不是消失了,而就存在于异化之中,只不过是以颠倒的形式存在着罢了,因此,我们不是要在异化中认识、领会人的本质,而是要通过对异化的认识扬弃异化,回复人的本质、找寻到生存的意义”。就此而言,克尔凯郭尔的理论是黑格尔学派解体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支,在阿多尔诺看来,“现象学体现了一种新的‘哲学精神的努力’,即在‘唯心主义体系消解之后并沿用唯心主义的工具,自主理性力图获得关于存在的超主观的有约束力的规则’”。[2] (P129-153)
关于唯心主义,在阿多尔诺看来,尽管“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现代哲学在外在形态上已经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古典哲学有了巨大差别”,但“现代哲学并没有因此能够逃脱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窠臼”。因为,在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看来,“科学的理念是研究,哲学的理念是解释”。“真实的哲学解释不遭遇已存在于问题之后的混合的意义,而是突然地、暂时地照亮它,同时消耗它”。因此,“哲学的现实性、真正哲学性的解释是‘揭谜’。这个谜就是资本主义永恒化或历史的自然化问题”。然而,“最重要的是,哲学的真正使命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去改造海德格尔哲学,‘哲学意识的真实改变才能成功’”。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认为,“黑格尔对康德进行的批判的主要功绩,在于他着手‘将从内容方面进行思考的权利与能力再次给与哲学’这个课题”。而且,在他看来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也具有“在思想中”“避开内容的倾向”。[2] (P184-193)
可见,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都是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他们发现了各种唯心主义与资本主义实践及其意识表现形式之间的同一性或共谋关系,从而对其客观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行了深刻批判。黑格尔之后的几乎全部西方哲学流派都囊括进了他们的视野。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严守马克思(同时也是黑格尔)的立场,将文明的进程同时视作启蒙的进程”,“启蒙只能凭借自身的手段,即控制本性的精神来超越并实现自我”,因此,“哲学就是‘通过概念而超越概念的努力’”。他们在进行这样的批判时,所遵循的“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并且他们寄希望于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则尝试着将保守主义者们对文明所进行的反启蒙批判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理论中去”。也就是说,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试图将启蒙批判这一传统重新应用到批判性的社会理论,也就是某种极端化的启蒙中去”。[3] (P8-9)
从上述关于阿多尔诺、霍克海默与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诸多方面所存在异同点(特别是差别之处)上,我们不难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为何没有赋予意识形态化了的“启蒙精神”或“工具理性”以本体论的色彩了。
二、意识形态理论的认识论维度:主客体二分法与“辩证法”和“否定”问题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认识论基础是反对主客体二分法,为此,他们还指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错误的反映论思想,即坚持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说,认为这是对主体性的质疑;但同时,他们又以自己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结果得出结论说,现代工业社会里,人的主体性被片面地摆到了新的神话的地位,因此,目前的任务是要偏向客体的方面(主要是阿多尔诺的观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们认为主体和客体本来就是不可分离的,而且是具有非同一性的,因此,任何关于主体和客体同一的理论(包括反映论或符合论)都是错误的和虚假的,并因而都是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
建立在这样的认识论基础上,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的意识形态理论展开了对“辩证否定”的新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一种绝对的否定(即“大拒绝”式的或总体性的批判)。这样一来,也就不难理解他们关于“辩证法”和“否定”的理解,和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和否定之间有多大的差距了。
有些学者看来,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重建自己的辩证理性阐释模式时,就像是“张起‘限定的否定’、‘模仿’、‘非同一性事物’等概念之帆,在忧郁的波涛中自由自在地行驶”,并因此而试图“超越”“古典的主体概念的崩溃,而最终达到了新的主体概念‘非同一性主体’”。[4] (P4)如果说“‘作为战斗着的唯物论者’的霍克海默以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为问题,其立场是对乍一看抽象的、普遍的理论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进行有意识批判的整体意识形态批判”,那么阿多尔诺则“是站在更为内在性的理论立场上”,即他认为,“相对于理论的社会现实不是存在于理论之外的,而是存在于理论内部”的。因此,要“去探求理论自身在无意识情况下所记录的社会性现象的痕迹”。为此,他求助于本雅明和弗洛伊德,在前期对现代思想——启蒙理性或工具理性思想进行梳理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祛意识形态之魅的新哲学的任务问题:在他看来,过去“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像黑格尔哲学所体现的那样,根据理性把现实作为一个总体去把握”,但实际上只是一种幻想。因此,现在应该是面对“哲学的现实性”这一问题的时候了。即“哲学已经不能解决‘存在’与‘全体’这一根本问题”,而是要以“解释”的立场,为“哲学打开与个别科学间相联系的一条道路”。这里所说的解释,就是一种“解谜画”式的态度。也就是说,哲学的任务“不是去探究隐藏在现实中的意图,而是‘解释无意识的现实’”。“哲学将个别科学取得的成果作为新的谜,作为没有密码的‘解谜画’去探究”。这样一来,阿多尔诺就试图“通过内在的批判”来“‘消解’古典问题”。然而我们知道,“哲学所面对的各种历史问题和理念,与著作外部的历史现实决不是毫无关系的”,因此,阿多尔诺认为“通过哲学解释取消古典问题,就必须要对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现实进行变革”。于是,在《哲学的现实性》中,阿多尔诺“将这种变革现实的思想命名为‘唯物论’,把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语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作为相关的哲学理论进行引证。而且,这种理论(解释)与实践的互相联系,毫无疑问就是‘辩证法’”。而在此意义上,所谓的“辩证法”,就是“彻头彻尾的意识相对于同一性的非同一性”。[4] (P41-56、150)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视阈中,实践唯物主义一直是贯穿始终的主线,而实践唯物主义所坚持的是在实践中坚持主客体的互动关系,并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强调客体的第一性和主体的第二性。但这并不是否定主体性,反而是对主体性的科学认识,因为这是在坚持唯物论基础上的对主体能动性的科学的、可操作性的强调。尽管有学者也认为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也强调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性,但他们的那种缺乏唯物论基础的并因而也是缺乏实践精神的主客体互动性永远只能是一种空想。所以,他们在理论上左右摇摆与对主体与客体的强调以及一方面在理论上拒绝主客体二分法和反映论,另一方面又在理论论述中不得不运用着自己所反对的认识论观点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科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对“辩证法”和“否定”范畴有着与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不同的理解:辩证法不再仅仅被理解为革命或批判,而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否定也不仅仅再是绝对否定,而是包含着肯定因素的否定,是否定之否定,是一种扬弃。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这是在试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制定的关于文明发展史的范式稍加变化,以便人们能够理解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形成的不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而是某种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他们试图揭示:“从进步到镇压的社会辩证法中无法找到‘自然的’出路,因为上演着这一辩证法的舞台正是人类主体自身。在人变成主体的过程中,已经注定了对人的罢黜,这仿佛是一种着了魔的辩证法。因此假设当历史发展到某一个时刻,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可以给每个人自由和丰衣足食的阶段,此时也就不存在能够得到社会财富并获得解放的主体了”。因此,对于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而言,“启蒙辩证法就是理性历史的辩证法。理性的历史之所以是辩证的,是因为在文明的史前史之中,理性从一开始便受到了统治和意志的感染,获得了自持”。在解释理性和统治的统一时,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试图从康德和尼采的眼光(认识论批判)出发来看待马克思,而与此同时又试图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眼光(唯物主义)出发来看待康德”。[3] (P155-156)在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论维度的这一矛盾性,必然导致其最终在方法论上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之间走向不同的关注领域。
三、意识形态理论的方法论维度:从“音乐拜物教”到“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的意识形态理论从其上述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出发,坚持一种“冬眠式”的艺术美学解放之路(如阿多尔诺关于音乐拜物教的分析);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从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坚持将意识形态批判付诸物质实践领域(马克思对资本、商品和货币拜物教的分析),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活动)来推翻意识形态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美好家园。
由于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的“哲学纲领已和自身的困境互相纠缠在一起”,因此他们的新哲学既然“是对问题的解谜”,而这种解谜又“以问题的消除而结束,而消除各种问题的最终途径,必须是对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进行变革”。但是,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最终并没有寄希望于“无产者通过社会革命实践进行变革”。[4] (P56-57)也就是说,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想实际化为无产阶级与政党的存在,而是对事态进行了内在的批判”,尽管他们“是在由实践的现实变革而带来的哲学的自我扬弃这种古典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延长线上,思考‘哲学’的”,但“只要哲学是对更好的生活、更正确的生存而进行的沉思,实现这个目标就成为了哲学的任务。与通过实现所带来的现实取得一致,才是哲学的真正目标”。[4] (P84、144)
于是,艺术、美学以及文化领域便成了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展开意识形态批判的“实践”领域。他们把“艺术看作是社会总体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操纵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而扮演的却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所以,当他们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反艺术”特征之时,他们实际上就是以艺术的形式在进行其意识形态批判的。与此同时,他们又赋予艺术以否定异化社会的社会责任。但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所批判的并不是艺术本身,而是特定社会和历史环境下的艺术的异化形式,也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艺术”。[5] (P178-193)
由此出发,阿多尔诺还提出了“音乐拜物教”概念。他“按照马克思的方式,认为拜物教不仅是心理学范畴,它也是经济学范畴,其根源在于由交换价值而不是由使用价值统治的社会中的商品特性”。阿多尔诺“模仿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过程——从商品的消费追溯到商品的生产,并在对于生产过程的分析中,发现商品拜物教的奥秘——也从文化工业的消费上溯到文化工业的生产过程”。然而这样的分析却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乐观的实践态度,因为在阿多尔诺看来,“艺术并不能做到它所要做的事情,并不能实现它想要达到的理想。艺术所能做到的只是否决或否定它在其中构成一部分的那个异化了的社会”。因为,艺术本身已经被异化了、被操纵了,一句话,被意识形态化了。看来,“艺术一方面作为异化的意识构成统治者的同谋犯,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为否定异化而否定它自身。艺术的矛盾地位使它保持下来,使其自身履行既否定社会又保存自身的责任。然而,保存艺术自身又必然导致保存现有社会,因为现有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恰恰是艺术”。[5] (P194-197)
因此,阿多尔诺“反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艺术仅仅归结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形式。”他认为,“如果把艺术只归结为一种反映形式、一种意识形态,那就等于忽略了艺术的独立的自在性。艺术具有一种珍贵的本质,就是可以独立于社会现实而存在,并引导人们在为未来的理想奋斗的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真正的艺术是合法的利益的代表形式,是人类的未来幸福的表达形式”。在阿多尔诺看来,“作为一个整体,艺术的空想可以把人类领到遥远的、幸福的未来,因而可以无限地否定现实,使人们领略到现实的可恶,因而痛恨一切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艺术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它的功能应与人类理性和情感的功能相适应;它远远地超出物质的功能”。——然而他关于艺术异化的分析,又表明:“阿多尔诺在反对反映论的同时,又不自觉地把反映论应用到自己的理论分析中”。[5] (P198-199)为此,阿多尔诺认为“在现时代,艺术与美学历史地具有了认识真理的功能,但是它们不应当‘在现存世界的梦想中忘却,而是要以形象的力量去改造它’,即它们应当成为现实革命的前奏”。“音乐之于阿多尔诺,犹如经济学之于马克思”。在他看来,“音乐的解放、人类的解放”才是人类脱离同一性苦海的必经之路。[2] (P36-37、57)
可见,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坚持的是一种建立在艺术美学层面上的文化解放论(尽管他们也对资本、商品和交换等经济现象以及政治统治形式做了十分类似唯物主义的分析,但他们做这一分析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政治经济领域的这些异化或意识形态化现象,而是为了说明进行冬眠式文化艺术革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马克思则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物质实践解放观(马克思对资本、货币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不仅涵盖了政治经济领域,而且也涉及到了精神文化领域甚至是宗教领域,其分析的目的最终落脚点依然是物质生活实践而非精神领域)。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差异,反映了其在意识形态批判最终目的上的天壤之别:对于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来说,或许批判本身对于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说已经足够了;而对于马克思来说,批判只不过是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出发点而非结果,其最终结果是要将人类引入自由和解放之境,而且,为了这一目标,马克思还为我们指明了现实可行的或者说具有可操作性的路径。而在这一点上,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却多少显得力不从心。因为稍微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尽管艺术美学之路(即文化的祛意识形态化之路)多少对于我们今天的“物欲横流”的商品化世界有警醒作用,但同时也只能是一种安慰剂,因为缺乏物质生产力的最终发展,即物质的解放,所有的精神的和意识的解放都将最终落空。
标签:工具理性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霍克海默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辩证思维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认识论论文; 唯心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