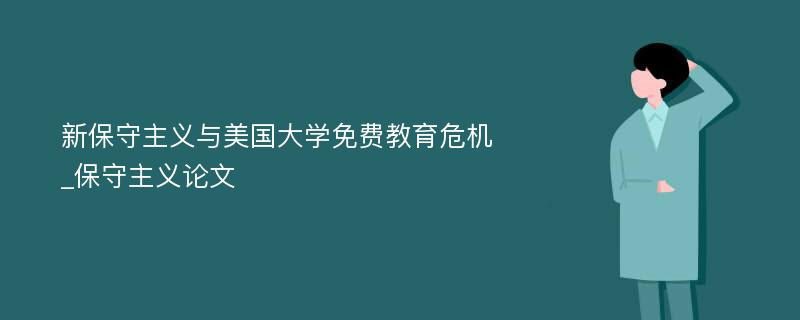
新保守主义与美国大学自由教育的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美国大学论文,危机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中,能够在形式上继承源自古希腊的西方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传统,并有所发扬光大的,或许不是有着800多年传统的欧洲老校,而是当下新保守主义势头正劲的美国。对于自由教育究竟该如何理解,多少年来众多的美国学者也看法不一,并在其中揉入了各种美国所特有的实用主义成分。如目前在学术界依旧如日中天的自由派认为,自由教育就是一种强调文理兼通、知识广博、多元价值并存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或者不妨说是一种综合素质教育,正如哈佛文理学院前院长罗索夫斯基所谓通识教育的四大标准或指向:批判性思考能力、广博的知识、对他文化的广泛理解和基本的专业能力等。[1]但是,眼下试图以道德至善、经济自由而君临全球的美国共和党政府得势,揭示了一个或许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作为一个曾经标榜为多元文化熔炉的典范,美国似乎正与早期威尔逊曾推销的多元共存的国际主义秩序渐行渐远,一个更推崇绝对和一元的新帝国形象正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而这同时也表明,自二战以来,美国自由派所倡导的多元主义、兼容并包的大学自由教育理念,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危机。本文拟尝试对这一危机发生的文化背景、历史脉络予以全面的梳理。
一、美国大学自由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内在冲突
美国颇为自负的历史学家布尔斯廷在其煌煌巨著《美国人》中曾言,不可否认,美国文化的起点是欧洲正统的加尔文清教传统,但是,早期移民来到新大陆时所面临的艰难困境,迫使他们不得不注重实际。宾州贵格会至善论在现实中的到处碰壁,佐治亚州宏大社会福利计划的乌托邦蓝图的破产,都预示着在这块新大陆上,一种求实、顺应自然和诉诸自明之理的新美利坚精神即将破土而出。这种精神状态基于两种看法,一是“人们为其行动提出理由远不如行动本身重要;为错误或未知的理由而行动得当胜过以模棱两可的结论去掩盖一种体系化的‘真理’;深沉的反思并不一定产生最有效的行动”。二是“经验的新颖之处必须自由地融入人们的思想”。[2]也就是说,从清教徒踏入美洲大陆的那一刻起,“行动”和“经验”就已经成为他们摆脱英国保守文化和欧陆玄思理论传统的双桨。由此几经辗转和历尽艰辛,在经过皮尔土、詹姆斯和杜威等人的精心总结、概括、抽象和理论化之后,一个彻头彻尾体现了美国本土精神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理论体系终于瓜熟蒂落。
美国大学所独有的自由教育理念,也就是伴随着实用主义哲学体系瓜熟蒂落的过程而浮出水面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信奉实用主义哲学的哈佛大学校长埃略特,第一次为老欧洲大学中传统的自由主义教育模式(即美国早期的耶鲁模式)敲响了丧钟。埃略特提出,传统的以古典课程为主、带有浓厚宗教色彩并注重人的精神训练的自由教育模式,对于现代美国人没有丝毫实践价值。在他看来,为适应美国当时急遽变化的社会环境,同时维护社会民主制度,年轻人“除了需要选择一门学科通过全面的学习以为未来的职业做准备以外,还应拥有反映人类情趣的所有学科领域的通识性知识(general knowledge)”。[3]1909年,埃略特的继任者洛厄尔上任后,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大学应该实施的是“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在此,洛厄尔第一次对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与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进行了区分。他认为,传统的自由教育贯穿于本科生教育的全过程,而通识教育的目的则在于开拓学生关于知识的深度和广度。[4]很显然,埃略特和洛厄尔所倡导的通识教育,在本质上已经与传统的自由教育理念分道扬镳。它尽管也多少带有一定的价值偏好,如洛厄尔所言,其目的在于塑成美国的共同特性、以及在知识和文化上的相对一致性,但是,由于它更强调其作为专业化前期的知识准备,因此,这实际上已经预示了与后期大学愈加细化、四分五裂的专业化格局的形成和知识整体性的瓦解相伴随,“通识”本身也将成为一个问题。
20世纪60到70年代可谓是美国高等学府中自由派以及激进的左派气势如虹的时期,在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轰轰烈烈的社会背景下,美国大学自由教育的价值取向开始真正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传统和共性更多地成为人们批判和拷问的对象,相反,变化和多样性在人们看来更能反映民主社会的本质。强调变化和多样性,一方面把边缘和弱势群体的文化和价值诉求提升到与传统主流价值对等的地位,从而带来了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全面扩张;另一方面,在纷乱多元的价值导向下,与美国社会当时混乱的社会情景相仿,自埃略特以来的美国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大学通识教育也在课程的膨胀中多少走向了混乱和无序。这种格局难免要触动一些保守主义者始终敏感的神经,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整个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呈现出“向右转”的整体趋势后,自由派的“多元并存”也开始受到严峻的挑战。
二、新保守主义及其大学自由教育的主张
1983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荷西(Jr.Hirsch)在其《文化遗产》一书中,首次向自由派的教育主张发难。他谴责道,由于目前大学缺乏共同的课程,美国社会正面临着丧失它的“文化凝聚力”的危险。为此,他认为:“我们必须把更多的学生同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以及那些让我们凝聚于一起的理念联系起来。”然而,什么是美国的共同文化?卢卡斯(Christopher J.Lucas)认为,荷西的主张其实与美国著名的永恒主义代表人物艾德勒(Mortimer Adler)的思想一脉相承。[5]提到艾德勒,这里就不得不说起上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年轻的校长赫钦斯。赫钦斯曾经以永恒主义享誉当时美国的大学教育界。他认为,大学应该开展普通教育,普通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在他看来就是训练人的理智,理智也就是美德,这种理智精神来源于西方的传统,因此,也只有回归到传统当中,通过设置以西方经典名著为主的课程计划,教育才能达到培养人的理智的目的。为此,他与艾德勒一起在芝加哥大学精心构建了一个百卷名著计划。尽管该计划在芝加哥大学最终还是破产了,但是他的大学普通教育思想却由此在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甚至得到部分高校的认同。芝加哥、哥伦比亚、圣约翰、劳伦斯和圣·玛丽等大学或学院直到今天,还部分地保留了西方名著教育培养计划。而更意味深长的是,此后被称为共和党“教父”的著名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以及众多如今政界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如沃尔福维茨(Paul Wolfowitz)也出自芝加哥,以至于使人感觉到今天的芝加哥俨然是新保守主义的大本营,看来这些都并非仅仅是偶然的巧合。
列奥·斯特劳斯在今天的美国已不再是一个寻常人物。作为一位二战期间从德国避难来美的学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虽然还名不见经传,但如今在共和党主政的时代却光芒四射、声誉显赫。斯特劳斯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相信人类社会存在普遍的、绝对一元的价值标准,而这个绝对的价值标准必须回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文化资源中才能找到,如苏格拉底关于人类幸福完满生活、柏拉图对普遍正义和善的一元理解。他认为,普遍的正义来自“自然法”,而不是自霍布斯之后近代政治哲学转向中的“权利”。故而,与赫钦斯的主张一样,斯特劳斯也主张大学的自由教育只有回归西方文化的源头去汲取养料,才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理解西方文化的“有教养的人”。正如他在1959年关于《什么是自由教育》的演讲中所提到的:“自由教育就是关于文化和指向文化的教育,它的最终产品就是有教养的人”,然而,什么是文化?斯特劳斯不无讥讽地指责:自由主义特别是相对主义关于多元宽容的观点让我们迷失了方向,因为这无疑于在说,文化就好像“对花园的营护可以由园子里的垃圾,由那些空的锡杯和威士忌酒瓶,由那些写满字的被随手扔在园中的废纸构成”。因此,他认为,自由教育要提供给学生好的文化,这种文化在本质上还是西方文化。尽管其他文化也可能有可取之处,但是,我们因语言的困扰而别无选择。故而,真正的自由教育就是要人们去与西方传统中的伟人们进行精神交流,去倾听伟人的思想,在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伟人的交流中,达致“完美的人格”和“人性的卓越”,去“养成我们的谦逊而不是谦卑”,去“培养我们的勇气并以之冲破知识分子以及敌人的浮华、廉价、喧嚣、鲁莽和无知的世界”。说到底,“自由教育就是赋予我们以对美好的体验”。[6]显然,如果说赫钦斯关于普通教育的经典尚且是西方从古希腊到近现代所有的名著,那么,斯特劳斯则更进一步,他主要指涉古希腊的传统。换言之,比起赫钦斯的理性主义,斯特劳斯的教育主张则更具有一种保守主义、古典主义和绝对主义色彩。
斯特劳斯关于自由教育的保守主张虽然在20世纪60、70年代被自由派以及偏左的激进派强劲的势头所掩盖,但是它却成为一股潜流,一旦时机成熟便迅即蔓延开来。在20世纪80年代整个美国“向右转”的大背景下,它便迅即浮出水面,除前面提到的荷西以外,最著名的保守主义自由教育代表人物莫过于布鲁姆(allan Bloom)。阿兰·布鲁姆是深得斯特劳斯真传的大弟子,在20世纪80年代他以一本《美国精神的关闭》(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而名噪一时。在该书中,布鲁姆以其深厚的西方哲学家底,历数美国民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崛起所带来的价值相对主义的罪恶,进而痛责道:“六十年代为大学带来的是万劫不复的灾难”,“我所听到的诸如‘伟大的开放性’、‘更少僵化’、‘摆脱权威的自由’等等,所有这一时期所谓好的东西都空洞无物,根本不能体现到底什么应该是大学教育的观点。”[7]另一方面,他又对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予以激烈的抨击,认为美国大学已经成为一个职业研习所,学生为职业而来,教授们都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目光狭隘,既不关心不同学科和领域彼此之间的联系,也不能对学生的人生与关于民主生活的价值困惑提供指导,“而最严峻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对好的伟大名著抱以拒斥的态度”。在他看来,所谓自由教育就是要学生仔细研读那些被普遍认可的经典文本,“这些伟大的书籍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只有在这些古典文本中,学生才能感受到如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当代社会中它所具有的活生生的深刻内涵。“一个好的自由教育计划,就是要培养学生对真理的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激情,对每所大学而言,根据自己的特定条件设计这样一系列的课程并不是难事,……难就难在教师不能接受它。”[8]为此,布鲁姆指出,当代人类可能生活在一个相对于其他任何时代都更需要真诚地阅读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时代,这些经典的客观与真实之美依旧存在,因为它们反映了人类的本质。而人类的本质具有共同性,因为至少在当代,我们人类依旧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这里所谓共同性,就是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对善的共同关注,它是“惟一真实的友谊”,是“惟一真实的善”。而在如今更需要哲学、。一个属于美国的时代,美国的大学就应是一个一致性与友爱共存的场所,它应该承担起如政治上对整个人类世界自由之命运的责任。[9]
如果说荷西和布鲁姆仅仅是站在学者的立场来为大学自由教育“回到传统”而营造声势,那么,里根时期的美国教育部长贝奈特(William J.Bennett)则作为政界知名人物与之遥相呼应。1988年贝奈特刚一出山,就在西海岸少数族裔居多的知名学府斯坦福大学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麻烦。是年,斯坦福大学教师们要求将一门一年级本科生必修的名为“文化、理念和价值”的“西方文化”课程(该课程在20世纪80年代初名为“西方文化”,后在学生的反对下更名为“文化、理念和价值”),用不再强调15本经典名著的“妇女、少数族裔和有色人种”课程来替代,对此,贝奈特大为不满,他谴责教师们的动议是把大学课程平庸化、琐碎化,而斯坦福的教师们也反唇相讥。该事件由此在全美引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笔头大战,诸多大的报刊媒体都参与了论争。[10]参与这一论战的不仅有激进的左翼,更多的是作为美国学术界主流的自由派。也就是由此开始,与美国政治、文化界中的情形一样,关于自由教育的保守派与左派、自由派之间持久的论争,也不妨称之为“文化战争”(culture war)在高等教育界也拉开了序幕。
三、美国大学的自由教育究竟会向何处去
关于美国大学的自由教育取向之争,我们不妨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映特定时期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转向的晴雨表。20世纪初,取代了传统自由教育的普通教育概念浮出水面,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美国实用主义本土文化开风气之先的时代背景。也正是因为对老欧洲传统的彻底反叛,才促成了美国后期激进主义文化的崛起。它虽然发端于20世纪初,但是直到60年代方才达到巅峰。作为这场规模空前的文化运动的重大成果是,在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被扫清后,美国大学中的自由派和左派精英知识分子逐渐站稳了脚跟。然而,在此整个过程之中,保守主义并未真正放弃自己的阵地。正如艾德勒所言,如果说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教育是对极端乏味和空洞、形式主义色彩浓厚的传统教育的反动,那么,这种反动到了40年代却把美国教育带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因此,现在该是钟摆向回摆动的时候了。对于进步主义的主张,永恒主义并非是彻底的抗拒,而是对它误读传统的一种修正。这种修正在艾德勒看来,就是一种在传统和变化之间持中间立场,重新理解经典在当代的现实价值和意义。[11]只是20世纪40年代甚至到60年代与其说是一个需要反思的时代,毋宁说是一个依然让人对变化感到亢奋的高歌猛进的时代,这也是为何列奥·斯特劳斯在美国学术界长期默默无闻的主要原因。
20世纪80年代,在经过60年代的激进文化革命之后,面对多元文化主义以及相对主义的全面泛滥,美国社会中吸毒、堕胎、种族暴力、枪械失控、儿童色情、同性恋和家庭暴力等等有违传统基督教道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大多社会中上阶层对此极为不满,于是保守主义者借机祭起“启蒙”的大旗,利用大众媒体的力量在瞬息之间异军突起。里根的共和党政府崛起就是这一风向转变的产物。不过,此时的保守主义已非彼时的保守主义,相对于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们采取了一种对自由派(包括柏克式的旧保守主义)多元宽容和对左派的激进绝不妥协的强硬态度。如库尔斯(James Kurth)1992年在新保守主义的期刊《国家利益》上撰文指出的:在当代,美国需要再进行一场新的国内“战争”,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不仅通过强调遗产的传承,而且要依靠美国化的大众教育重塑美国共同、一致的文化,恢复它曾经在世界舞台中的主导地位。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库尔斯在此所谓的信念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强有力的精英统治、物力、暴力、金钱和文化整体性的基础之上。[12]他所谓的战争其实就是文化战争,它的矛头所指,在国内即是自由派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左派的平等主义,在海外,就是亨廷顿所谓的与西方文化相冲突的其他文明,以及弗朗西斯·福山所谓与美国民主相悖的政治制度。它的观点虽然极端并且在大学中很难有市场,然而如甘阳所认为的,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美国大众中却很有蛊惑力。[13]而且,它也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财大气粗的右翼传播媒介不遗余力的支持。
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极端的新保守主义关于大学自由教育回到经典,而不是回到美国自身传统的极端倾向,在20世纪80年代后渐成气候。除荷西和布鲁姆的论著外,各种相关的其他新保守主义论著也纷纷出笼,如威力斯希尔(Bruce Wilshire)的《大学的道德崩溃、专业主义、纯净与冷漠》,史密斯(Page Smith)的《扼杀精神:美国高等教育》,金伯(Roger Kimball)的《终身制的激进分子:政治是如何搞垮我们的高等教育的》,波珀(David E.Purpel)的《教育中的道德和精神危机》等,这些论著都在美国文化界和高等教育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次新保守主义的崛起,实际并非是美国传统如耶鲁的中庸保守主义的复兴,它其实意味着新保守主义的主张又走向了钟摆的另一个极端。显然,对于这种盛气凌人的宣战,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左派都不会无动于衷。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小布什入主白宫后的今天,随着9·11事件后国际形势的逆转,这种论争的火药味日渐浓厚,甚至到了相互谩骂的程度。早期曾是斯特劳斯的弟子也是布鲁姆的同学,但后来却成为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的罗蒂就公开表示:对于布鲁姆、贝奈特和荷西等人的主张我会肆无忌惮地嘲笑。斯坦福的普莱特(Mary Louise Pratt)教授责难道:“布鲁姆之流珍视一种狭隘、具体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被认为是普遍的可以为每个人所享用,然而,它实际上只属于那少数在语言风格和族类上具有一致性的有地位的世袭阶层。”显然,它是带着种族主义的标识,“很少有人会质疑贝奈特和布鲁姆的意图并非是指美国人封闭的心灵,而是美国的大学”。普莱特哀叹道:这分明是“西方无情帝国主义的扩张”,毫无疑问,布鲁姆的著述在“知性上是极糟糕的”,而贝奈特的《回到遗产》则简直“更是糟糕透顶”。著名的左派教育学家吉鲁(Henry A.Giroux)则抨击道:“在更一般意义上,布鲁姆和荷西代表着新的精英主义在近期内所发动的一种文化攻势,他们以优势和权力阶层的视角重写过去、建构当代,他们蔑视多元主义的民主内涵,提出了一种文化一致性的样式。在该样式中,差异被置于历史的边缘地带,被放到弱势阶层的博物馆。”盖蒂斯(Henry Louis Gates)则声称,“所谓回到经典意味着:我们的人民要重新回到被奴役、被剥夺发言权、被视而不见、失去代表资格的秩序当中”[14]。
即使相对温和的一些自由派分子对于新保守主义的主张也同样表示公开的蔑视。尽管新保守主义与诺齐克、哈耶克的个人自由主义在经济学意义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但他们在关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立场却并不完全相同。如格雷(John Cray)所言,自由主义的两种哲学其实都强调文化和政治多元价值的宽容,只不过一种是把宽容视为通向真理的手段,而另一种则把宽容视为和平的条件。前一种虽然强调终极的善,存在一种人类共同的文明,但反对文化和政治的强制;而后一种则把不同生活方式作为善的生活的多样性标识,因而坚持一种“权益之计”和“重叠共识”。[15]可以说,直到今天,强调多元价值宽容的自由主义依旧是美国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主导价值取向,而自埃略特以来美国大学中具有本土实用主义特色的自由教育或普通教育理念及其课程建构,正体现了这一主导价值选择。事实上,在自由派中,今天也很少有人会把西方文明斥之为一种文化霸权,只不过是他们能够在关注西方文明的同时,对于其他文明以及各种新生事物更具有一种容忍和开阔的胸怀而已。始终是自由派精英大本营的哈佛,包括旧式保守主义的耶鲁,以及大多其他美国研究型大学,它们对自由教育的理解都大致体现了这种精神。因此,至少到今天,在美国学院派精英分子中,新保守主义回到经典、回到传统道德一致性社会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
就目前而言,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学术界、知识界中绝非主流,杨名杰指出,在理论上的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人物加起来也不过20多个人,几个研究机构和几个刊物。[16]如果由此而断定美国大学的自由教育不会出现变化恐怕也过于乐观了。新保守主义者固然在知识界还不是主流,但是,他们目前却成为保守的共和党的思想智囊团,因此他们借国家和公意的利器,特别是有明显保守主义倾向的小布什政府在教育领域所施加的影响依然不可小视,更何况,在目前美国大众文化日趋保守,信奉基督教的人们日益增多的特殊社会背景下,他们还有着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
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已经显示出自由派和左派在逐步退却的迹象。80年代的“惟英语”(English Only)运动对于自由派和左派的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双语教育不啻是致命一击。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把孩子从学校带回“家庭学校"(home schooling) 运动的兴起,以及宗教性的私立学校发展迅猛的势头,似乎都表明新保守主义绝非是美国的旁支末流。自8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政府新自由教育政策从表面上看是在教育中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效率,然而在深层上却通过强调责任和绩效把新保守主义的文化主张渗透到日常教育生活之中。总之,以上种种迹象,对于美国大学中主流的通识或自由教育理念而言,显然不是好兆头。
然而,如果新保守主义的主张真正成为教育领域的主导思潮,这对美国的大学而言是否就是一个好兆头?恐怕也未必。回到开篇,美国真正的本土哲学是实用主义,目前主流的自由教育精神和理念其实正是美国本土哲学的产物,它的生命力也正在于此。而新保守主义的原生态与其说是美国式的,毋宁说它更像是老欧洲近代自由教育理念的死灰复燃。也许历史总是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一个国家在进入它君临天下的巅峰状态之时,它的精神总难免带有保守性和封闭性。然则这种保守和封闭对于美国、对于整个世界,以及美国的大学究竟是一件幸事还是悲哀?我们尽管暂时无法看到,但结局和命运似乎不难预料。
这或许也将会再次应验艾德勒的钟摆理论,当新保守主义思潮走到极端之时,恐怕也是它走向衰落之时。只不过,因为如今美国的文化转向更多地来自于大众文化的因素,对此,学术界的自由派和左派精英们不能不进行全面的反思。正如美国的自由职业学者和作家吉考比(Russell Jacoby)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所言,目前美国的右派兴起以及社会文化危机乃是因公共知识分子的缺席所致,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知识分子以激进的方式重构了美国的政治和社会,但是,他们如今却都退回到学术的象牙塔中,放弃了自己在政治和公众文化中的角色。[17]而颇意味深长的是,如今新保守主义所抱怨的正是左派主导学术界,以至于他们难以获得终身教职的格局。然而,他们却在大众中赢得了自己的市场。在另外一本专著《教条的智慧》中,吉考比提到,其实无论是新保守主义还是左派,他们目前对于大学自由教育的论争都带有目光短浅的偏见,双方所争执的无非都是大学所应提供的课程和书籍等等,新保守主义攻击目前大学的核心课程缺乏有机的整体性,而另一方则斥之为有精英主义的偏向。事实上,双方都打错了靶子。岂不知美国大学目前自由教育的大杂烩式的菜单式课程的真正制造者不是激进分子,也不是多元主义,而是市场,是一个对金钱和实践技能有独特偏好的“不自由的社会”(Illiberal society)。[18]而一个悖论是:新保守主义在文化领域主张“经典”、“遗产”、“高雅艺术”、“共同文化”以及“真理”等等的同时,又恰恰对经济领域完全的市场法则情有独钟。这种张力的存在恐怕也表明,新保守主义的主张在逻辑上存在一个自身无法摆脱的陷阱。
标签:保守主义论文; 斯特劳斯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美利坚大学论文; 美国教育论文; 大学课程论文; 通识教育论文; 布鲁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