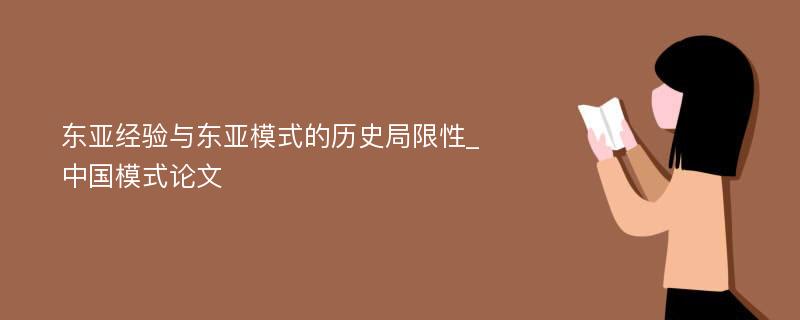
东亚经验与东亚模式的历史局限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局限性论文,模式论文,经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习与知识创造是东亚模式的精髓,这是我国创造“中国模式”需要借鉴的最重要的经验。但学习并不是简单的模仿,知识创造更是因时因地而异。由于东亚模式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作为其潜意识结构和无意识技能,虽然其精髓对东亚地区具有普适性,但其具体架构无疑具有历史局限性。事实上,作为熊彼特意识上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东亚模式正处于重大转折时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表明,任何时期都不存在某种固定不变的经济发展模式,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体制发展模式调整滞后的结果。正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欧经济在制度和政策上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一样,东亚模式的革新也势在必行,但它决不会像新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趋同于英美体制。
这里,有五个重要问题值得深入研究。第一,阿锐基所谓世界积累中心正向东亚转移的论述是否成立?东亚的未来发展在世界体系中面临着哪些结构性制约条件?第二,由于东亚模式起源于冷战时期特定的时空背景,它存在着哪些历史局限性?例如,为什么说它是追赶而非跨越式发展模式?东亚地区在政府作用、金融体制、企业和产业组织、科技发展等制度创新方面存在着哪些局限性?第三,如何更深入地理解东亚模式的精髓,在以信息革命为基础的“朝代转变”之中,东亚地区如何使之得到创造性的发挥?第四,为什么说20世纪末席卷东亚的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它如何揭示了传统的“雁阵模式”因中国市场未能发挥潜力而在市场规模上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这对中国乃至所谓世界积累中心向东亚的转移意味着什么?第五,冷战时期特殊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孕育了东亚的兴起,而东亚模式的追赶性质是否为中国在21世纪的后来居上又创造了特殊的历史机缘?什么样的历史和特定情境才能使中国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我们认为,只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才能深刻地理解东亚模式的性质,深刻地认识我国在21世纪如何才能开创东亚模式的新格局。
首先,东亚模式未能涵盖中国大陆。让我们从阿锐基的《漫长的20世纪》谈起。阿锐基认为,世界资本积累中心正逐渐从美国向东亚转移。他在对全球经济的周期性运动进行观察时,使用了“漫长的世纪”这个概念,据此他划分了四个体系积累周期:(1)热那亚周期(从15世纪到17世纪初);(2)荷兰周期(从16世纪末贯穿到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3)英国周期(从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4)美国周期(从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并指出了向东亚周期过渡的趋势。阿锐基的讨论主要是以美日关系为对象,在有关中国的论述中,正如卢荻所指出的,阿锐基就像许多比较优势阶段论者一样,简单地把中国大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工业化视为东亚区域积累体系的延伸。阿锐基的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关“中国奇迹”的一种主流解释认为中国实行的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卢获对此提出了批评,他指出,以高科技产品占全部出口制成品的比例来看,在1997年,中国的同一指标不仅远高于发展水平相近的印度,而且超过中等发展水平的巴西,这不是比较优势理论所能轻易解释的。他认为,“中国奇迹”的发生主要是归因于建立在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之上的庞大内需市场。
我们认为,除了阿锐基对东亚内部发展动力及其历史缺乏深入研究外,他所使用的“漫长的世纪”这个概念也过于宏观,以致于无法把握长波运动对东亚格局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一般说来,在长波下降期,除了较短的时滞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不仅下降,而且,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产品的需求也会减少。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除东亚、东南亚和印度以外的第三世纪普遍地出现了严重的衰退,而1997年爆发的东亚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然而,正如特勒科特所指出的,“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欠发达国家却最低程度上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在长波上升期,中印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满足于自给自足,当它们在长波下降期延迟对国内外市场力量开放时,净债务占GDP非常低的比例和相对高程度的自给自足就成为难得的优势,这使福特制和前福特制增长可以相对不受国际收支平衡的阻碍而展开”。在以前对东亚金融危机的研究中,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因素的重要性。换言之,中国大陆免受金融危机之苦并不单纯是尚未开发资本项目的原因。而东亚和东南亚的过度投资和生产过剩因美国和区域内市场的有限吸收能力而加重时,虽然中国大陆市场潜在力是巨大的,但因区域内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合作仍停留在低层次上,中国市场对东亚整体发展的潜在贡献远未发挥出来。这主要的并不是因为“中国的低人均收入水平阻碍了原先出口到高收入经济的产品转向这个市场”,而是由于中国大陆与东盟乃至四小龙在世界市场上的全面竞争,这种竞争又因人民币的两次贬值使之利用中国市场几乎无利可图。由此可见,20世纪末席卷东亚的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金融危机,说明了中国市场的迅速成长对东亚地区是何等重要!我们认为,区域内各国与中国的全面合作将成为阿锐基所谓世界资本积累中心从美国向东亚转移的重要基础,世界体系学派由于专注顶层活动而对生产领域欠缺研究使他们无法认识到这一点。
在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在未来东亚发展的新形势下,既往的东亚经验相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来说存在着那些历史局限性。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需求规模是大国发展的路径与小国或地区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受市场规模的制约,发展中小国或地区由于受国内需求的制约,其生产就可能达不到规模经济。战后初期杨叔进先生曾在联合国亚洲经济委员会工会过,他在谈到参与制定韩国发展计划的经验时指出,当时的韩国要建立一座大炼钢厂,国内销售量连一半也达不到,所以韩国不得不走出口导向的道路。但大国国内市场规模的发展足以使企业生产达到规模经济并在企业间展开竞争,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化完全可以靠国内市场的扩张而实现。因此,仅靠出口导向,中国就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在这方面,美国自19世纪末以来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即它们不是建立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之上,而是追求一种更加开放的经济模式。
其次,东亚经验的历史局限性还在于其发展模式只是追赶而非赶超模式。赶超模式的核心是在追赶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制度创新和科学技术跨越到原先领先者的前面。在制度创新方面,日本模式曾作为后福特制组织的先导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广泛赞誉,但现在看来,它实际上是原有技术经济范式在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的突变,它与建立于新的信息技术经济范式之上的硅谷模式和现在美国正在出现的蜂窝式企业组织模式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科学技术方面,四小龙由于规模所限,他们不可能通过基础研究实现跨越式发展;但对大国来说,这完全是有可能的。然而,由于忽视基础研究和缺乏适应高新技术的制度创新,与20世纪初的德美两个大国赶超英国相比,日本在跨越式发展方面是相当不成功的。这与东亚模式产生于冷战时期有较大的关系。
此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我国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对其条件进行深入研究。然而,虽然我们并不否认阿锐基对整个21世纪的展望,也不否认有种种迹象显示出世界资本积累的中心在21世纪有可能从美国转移到东亚,但我们认为,目前的东亚尚未形成阿锐基所谓作为历次世界积累中心转移基础的“真正的组织革命”。无论是阿锐基的“多层转包合同制”、塞姆的“灵活泰勒制”,还是我们所提出的东亚式后福特制,都是起源于冷战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虽然它对东亚地区的兴起来说是极富创新性的制度创造,但这些组织创新并不能完成跨越式发展的历史重任。以日本为例,当它在20世纪80年代末完成追赶阶段后,目前已持续10年的长期经济危机揭示出了组织和制度改革的广泛要求。与20世纪初英国被后来居上的德美两国在高新技术上所超越有很大不同,美国在信息革命上所具的优势,说明它仍将主导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上升波。因此,东亚模式只是追赶而非赶超模式,相对于所谓世界资本积累中心从美国向东亚转移的“历史趋势”来说,东亚模式无疑具有严重的历史局限性。造成这种历史局限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亚模式尚无法提前涵盖中国大陆对东亚地区在21世纪才能产生的创造性贡献。换言之,离开中国大陆,世界资本积累中心就不存在从美国向东亚地区转移的可能性。20世纪末席卷东亚的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金融危机说明了中国市场的迅速成长对东亚地区是何等重要。冷战时期特殊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孕育了东亚的兴起,而东亚模式的追赶性质给中国在21世纪的后来居上又创造了特殊的机缘。我们的直觉是,正如20世纪世界资本积累中心从英国经过德国最终转移到美国一样,东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重任将更多地需要中国来担当,最终导致积累中心发生转移的组织革命很可能就会发生于中国。但由于传统的思维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仍制约着我国创造力的发挥,这种过程将是非常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甚至有可能绵延至21世纪末。
最后,东亚模式未能包含生态发展这个关乎人类前途的宏大主题。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东亚模式不可能包含生态发展或“可持续发展”的要素,这是遭到所谓“后现代”发展理论责难的一个原因。然而,东亚模式虽未包含人与自然共存的意蕴,但它确实在其模式中隐含着以本土知识为基础把“传统”与“现代”智慧相结合的胚胎,这是“后现代”发展理论所未能意识到的。“后现代”发展理论的批判虽然深刻,但他们对正遭受“不发展”之苦的发展中国家并未提出任何具体可行的对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道路就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它应该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寻求新的出路,在吸收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如果世界资本积累中心移向东亚地区的话,那么这个历史责任就是“中国模式”。
对于我国在21世纪的发展道路来说,如果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就必须超越东亚模式的历史局限性。我们认为,如果把注意力放在模仿西方工业化的福特制道路上,我国不仅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且,这必将加重全球生态危机。因为我国的生态、地理、文化和历史为我们发展信息和生物技术比其他国家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我国在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进行准备和下一次力争实现后来居上还是非常有希望的。但由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在不同层次上包容从前福特制、福特制、后福特制到更高级后福特制跨越的“时空压缩”,因此,“中国模式”必须是致力于跨越但又兼收并蓄的多样化和生态发展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