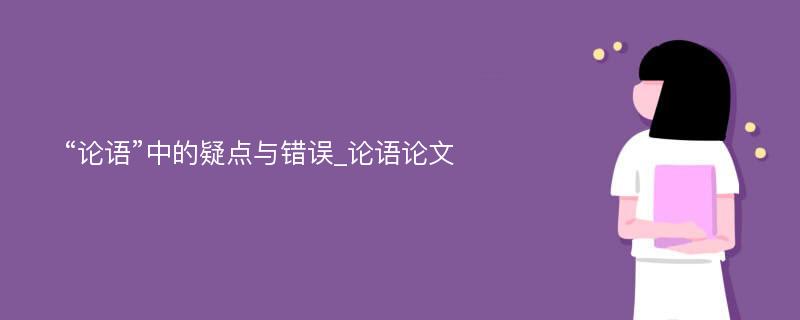
《论语》故训疑误举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训疑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跟其他的儒家经典一样,从汉代到今天,解释《论语》的文献之多,可谓是“浩如烟海”。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再高明的学者,也会囿于个人的学识和时代的局限,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错误。即便如此,这些问题或错误,也仍然是训诂学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训诂学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层面,有语言的层面,有思想的层面,还有心理的层面。其中语言的层面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核心的层面,又可以包括词语、语法、篇章,甚至版本文字等问题。本文试图从这些方面出发,对《论语》的故训作一些整理,归纳其特点,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希望对《论语》的解读,对训诂学,都能有所裨益。
一
有些问题,前人其实已经得出了正确的解释,但是后人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真正理解前人意思,因而继续有新的说法,反而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论语·卫灵公》: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这一章中的“参”字,并不好理解,过去有很多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
(1)《集解》引包咸注:“言思念忠信,立则常想见参然在目前,在舆则若倚车轭。”这是把参理解为“参然”。但是“参”在句中应该是个动词,不是状态词,这一解释在语法上就不能成立。不过,皇侃的《论语义疏》本,这一句作“立则见其参然于前也”,多一个“然”字,疏云:“参犹森也。森森满亘于己前也。”则此字读为森。但“见其参然于前也”,与下文“见其倚于衡也”就不平行了。1973年出土的定州汉墓竹简本(不晚于公元前55年)也没有“然”字(注:《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然”字应该是后人觉得“参”字义不可通,而根据包咸注或皇侃疏加上去的衍文。
(2)《礼记·曲礼》:“离坐离立,毋往参焉。”孔疏:“离,两也。若见彼或二人并坐,或两人并立,既唯二人,恐密有所论,则己不得辄往参预也。”朱子《论语集注》认为《论语》的“参”就是《曲礼》的“参”。但《曲礼》的参,据孔疏,是参预的参,很难用于《论语》,所以清代学者还是不信,继续有新说。
(3)王念孙曰:“参字可训为直,《鄘风·柏舟》释文引《韩诗》曰:‘直,相当直也。’今作值。故《墨子·经篇》曰:‘直,参也。’《论语·卫灵公》篇‘立则见其参于前也’,谓相直于前也。包咸曰‘参然在目前’,《释文》‘参,所今反’,皆未安。”(《经义述闻》卷三十一)《柏舟》:“实维我特”,《韩诗》“特”作“直”,这个“直”只是“值”的假借字,“值”与“特”上古音义都非常接近。所以训“参”为“直”,其实只有《墨子》一个孤证。但是《墨子·经篇》的“直,参也”这句话缺乏上下文,具体是什么意思,并不清楚。所以王氏的解释也没有坚强的证据,恐怕是站不住的。
(4)俞樾《群经平议》谓参字也作厽,厽也是累土为墙的厽字(音垒)(注:朱熹、王念孙、俞樾诸家之说,见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67页。)。参于前,即积累在前的意思。这种解释是改字了,实际是认为参字是厽字的误读。而且,说忠信、笃敬积累在前,也有点不像话。
以上各家的解释,即使改动原文,也还是诘屈难通,难以成立。所以,我们有必要寻求一种新的理解。
要理解《论语》的“参于前”,关键是先要理解,在人前面的,其实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忠信,一个是笃敬,加上人,就是三者。所谓“参于前”,就是忠信与笃敬立于人前,与人并立为三,所以说“参于前”。这个“参”仍然是动词,与“倚于衡”正相对。在先秦时代,参字有并立的意思,它表示三者并列。《战国策·齐策二》云,犀首欲败张仪连横之谋,设计假说与张仪有怨,请卫君调停:“卫君为告仪,仪许诺,因与之参坐于卫君之前。”高诱注:“参,三人并也。”参字在先秦时代经常用为数词“三”,表示“三者并立”的意思是从它作为数词的意义引申而来的。《礼记·曲礼》:“离坐离立,毋往参焉。”此之“参”其实也是这个意思。“离”通“丽”,是两者在一起;如果再加一个,就成为三者。《曲礼》是说,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说些很私密的话,所以“毋往参焉”,不要去加入他们,成为三人在一起。孔疏释为参预虽不能说错,但并不准确,没有揭示其真正内涵。朱子《论语集注》说:“读如‘毋往参焉’之参,言与我相参也。”其实朱子的意思,很可能也是“和我成为三”,而不是孔疏“参预”的意思,因为朱子是知道“参”字有“三者并立”的意思的。《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朱子《中庸集注》:“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因此,朱子的《论语集注》也很可能已经得出了“与我并立为三”的正确解释。这是“参”的最直接的训释,文从字顺。后人可能是受了孔疏“参预”之说的干扰,忽略了朱子的正确解释,所以继续有新说。
二
有时候,一个词语所指的对象可能包含着几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但是单独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不是这个词语的意思,只有这几个组成部分构成的整体,才是它的真正意思。清代小学发达,学者对于词语的意义往往辨析得非常细致,也非常精确。但有时候原文的意思可能很简单,阅读者考虑得太多,辨析过细,误以为有很特殊的意思,反而作出了错误的解释。孔子说“过犹不及”,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最好的评价。大概这种“求之过深”的错误,往往是学问好、善于思考的人反而容易犯。《雍也》篇: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陋巷”,是指简陋或狭窄的巷子。一条巷子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巷子的小路,二是小路两边的住宅区,这两者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由于着眼于不同的角度,具体的所指可以不同,有时候指的是这条小路,有时候指这个巷子两边的住宅区。例如说某个人住在某条小巷里,当然不是说他住在巷子的道上,而是指他住在路边的住宅中。所以《广雅·释诂》云:“巷,居也。”《释宫》又云:“巷,道也。”巷可以指巷子两旁的住宅区,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巷”有一个意思,是指巷子中人所居住的具体的某一间宫室,就有问题了。王念孙说:
古谓里中道为巷,亦谓所居之宅为巷。故《广雅》曰:“巷,居也。”《论语·雍也》篇:“在陋巷。”巷即谓隘狭之居,即《儒行》所云“一亩之宫,环堵之室”也。故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孟子·离娄》篇亦言颜子居于陋巷也。曹植《谏取诸国士息表》曰:“蓬户茅牖,原宪之室也;陋巷箪瓢,颜子之居也。”(注:“原宪之室”,当作“原宪之宅”,王氏引文有误。士息,魏晋时指士兵之子。应璩《与尚书诸郎书》曰:“陋巷之居,无高密之宇;壁立之室,无旬朔之资。”则陋巷为隘狭之居明矣。《庄子·列御寇》篇:“处穷闾阨巷。”闾亦居也。故穷闾或曰穷巷。《秦策》曰:“穷巷堀门,桑户桊枢之士。”《楚策》曰:“堀穴穷巷。”《韩诗外传》曰:“穷巷白屋。”《史记·陈丞相世家》曰:“家乃负郭穷巷,以弊席为门。”则巷为所居之宅亦明矣。今之说《论语》者,以陋巷为街巷之巷,非也。(《经义述闻》卷三十一)
王念孙是因为人所居不可能在巷子的道路上,因此不取巷子“里中道”的意思(也就是街巷之巷),而说成是居住的宫室。这是把街巷的两个组成部分割裂开来看。人当然只能是住在某一间宫室里,但这并不说明“巷”的意思就是指那间宫室,而不是指整个道路和两边的住宅区构成的整体区域。这是词语的概念和所指之间的差别。《论语》说“在陋巷”,是从颜子所居的大环境(巷子)着眼的,《儒行》说“一亩之宫,环堵之室”,是从所居的小环境(宫室)着眼的,这是从不同的角度说的,并不能说明“巷”的意思就是“宫”或“室”。曹植说“蓬户茅牖,原宪之室也;陋巷箪瓢,颜子之居也”,居也只是居住的地方,并不是确指宫室;应璩说“陋巷之居,无高密之宇”,更可以说明“陋巷”指的是这个住宅区,而不是哪一个宫室;《庄子》“处穷闾阨巷”,闾是里门,巷是里中道,这是用里门和里中道来指代居住的地方,是借代的修辞手法,也不能说明闾和巷都有宫室的意思;《秦策》和《楚策》的“穷巷”都是指巷子,“堀门”才真正指代所居宫室;《韩诗外传》“穷巷白屋”,穷巷中包含白屋,而不是重复的并列关系;《史记》把“穷巷”与城郭连言,也不可能指宫室。所以,王氏所举的例证,都不足以证明巷子有宫室的意义。王说混淆了居住的整个区域和具体的某间宫室之间的关系,割裂了一个意义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是不能成立的。这大概也可算是智者千虑之失吧。
三
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必须有一定的语法规则,才能方便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语法规则受到人的逻辑思维的制约,总的来说,它不应当违背人类思维的逻辑。但是语言现象是错综复杂的,现代语言学已经注意到,语言的表达虽然受到逻辑的制约,但是语言与逻辑并不是一回事,不是所有的语言现象都完全符合逻辑,语言当中存在着很多将错就错而不能用逻辑解释的约定俗成的现象。例如现代汉语中常说的“恢复疲劳”、“打扫卫生”、“告诉他别去,他非去”等等。在古代汉语中,其实也会有这种现象。《阳货》篇就有这样一个例子: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患得之”的意思,不是害怕得到,而是担心得不到。从逻辑上讲,这是错误的表达,正确的应该是“患不得之”。《荀子·子道》:“小人者,其未得也,则忧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与《论语》意思相同,而言“不得”。又王符《潜夫论·爱日》:“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也是“患不得之”。宋代沈作喆《寓简》:“东坡解云:‘患得之’,当作‘患不得之’。予观退之《王承福传》云:‘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济其生之欲者’,则古本必如是。”(注: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222页。)这就是根据逻辑判断语法。但是这一判断是否可取,却值得怀疑。何晏的《论语集解》:“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何晏很尊重语言现象,他说楚地方言如此。焦循《论语补疏》说:
古人文法有急缓。不显,显也,此缓读也。《公羊传》“如勿与而已矣”,何休注云:“如即不如,齐人语也。”此急读也。以得为不得,犹以如为不如。何氏谓楚俗语,孔子鲁人,何为效楚言也?”(注: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222页。)
焦说很有道理,《公羊传》的例子说明,古代汉语确实有肯定与否定表示同一意思的现象。不过焦循对何晏的批评也许还可以商榷。何晏说楚地方言如此,应该是何晏那个时候,楚地方言中还有这样的说法,并不是说孔子用了楚语。这种肯定和否定表示相同意思的现象,在现代汉语中也有,例如:
他那一脚那么狠,差一点踢死他。
他那一脚那么狠,差一点没踢死他。
这两句的意思完全一样,都是没把人踢死。但一句说“差一点”,一句说“差一点没”。所以《论语》的这个“患得之”,表示“患不得之”的意思,也是可以成立的。在《论语》中,还有一个很相似的例子,《里仁》篇: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富贵,是人所欲得,贫贱,却不是人所欲得,但本章都说“不以其道得之”。从逻辑的角度讲,也有问题,正确的应该是:贫与贱“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以其道得之”一定不符合语法,不能说。
从语言交际的实用性来看,这种用肯定和否定表达同一种意义的现象,并不利于交际,因此语言中不会很多。在古代汉语中,有些本来是肯定意义的情态动词,也可以表示否定的意义,但是这种意义是通过反问语气表示的,例如“敢”。《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陈公子完奔齐,齐侯使之为卿,辞曰:“羁旅之臣,幸若获宥,及于宽政,赦其不闲于教训而免于罪戾,弛于负担,君之惠也。所获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谤?”杜预注:“敢,不敢也。”《国语·晋语八》:“今执政曰,不从君者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烦司寇?”韦昭注:“敢,不敢也。言不敢忘死而叛其君,烦君司寇以刑臣也。”《公羊传·隐公元年》“如勿与而已矣”这句话,如果在口语中直接说出来,也许会伴随着某些特定的语气,可惜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了。
四
语言单位都是处在一定的上下文中。有时候,要理解一个语词、一句话的意思,关键并不在于这个词、这句话本身,而在于它所处上下文中的另一个相互制约的语言单位。这种单位往往是整个段落或篇章的关键部分,我们可以叫它“文眼”。找到了文眼,我们就知道了整个段落或篇章的中心意思,从这个中心意思出发,再来考察要研究的这个词、这个句子的意思,可能就会涣然冰释了。《子张》篇: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这一章的“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这句话并不好理解,古代的注释也都含糊其词。《集解》引包咸注:“言先传大业者,必先厌倦,故我门人先教以小事,后将教以大道也。”此注似乎没有涉及“孰后倦焉”。皇侃疏:“言先王大道即既深且远,而我知谁先能传,而后能倦懈者邪?故云孰先传焉孰后倦焉。”邢昺疏:“言君子教人之道,先传业者必先厌倦,谁有先传而后倦者乎?”邢疏是采皇疏。朱子《集注》:“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为先而传之,非以其本为后而倦教。”此注增加了很多意思,与原文相差较大,而且把“倦”解释为“倦教”,也是增字为说。刘宝楠《正义》:“言谁当为先而传之,谁当为后而倦教。”并引“诲人不倦”以证倦有倦教的意思。但是“诲人不倦”的倦也只是疲惫的意思,“教”的意思是“诲”传达的,不是“倦”。因此,朱子与刘氏之说并不能成立(注:诸家之说见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320-1324页。)。
要正确理解这句话,我们必须注意到与它相关的另一句话,就是作为本章总结性的最后一句话:“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这是本章的“文眼”,是子夏要表达的中心意思。子夏认为,普通人是很难善始善终的,很难坚持到最后;有始有终,只有圣人才能做到。从这个意思出发,来看“孰先传焉,孰后倦焉”,我们就知道只有皇侃和邢昺的解释才是比较接近原意的。但即便意思正确,在语言上总觉得还是缺了点什么,有点不太通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指出这句话其实是用了互文的修辞方法,完整的表达应该是“孰先传焉,孰先倦焉。孰后传焉,孰后倦焉”,意思是:先传授的,就会先厌倦;后传授的,就后厌倦。所以开始的时候先教弟子最基本的东西,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教以大道,这样就能使弟子不容易对大道产生厌倦情绪。如果一开始就教以大道,弟子可能很快就会对大道厌倦了。所以下文说:“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子夏认为应该有一个对于教学次序的选择。《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也是对教学次序的论述。包咸云:“言先传业者,必先厌倦,故我门人先教以小事,后将教以大道。”他只解释了一半,即“孰先传焉,孰先倦焉”,不过,基本的意思还是正确的。
另外,“本之则无,如之何?”这句话的读法似乎也还可以商榷,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读法应该是:“本之则无如之何。”这不是个问句,而是陈述句,“无如之何”是一个语言单位,表示“拿他们没办法”的意思。言子夏之门人,都学些微末小节,至于根本性的大道,就没法再要求他们了。《卫灵公》篇:“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无如之何,也就是“末如之何”。
五
有些错误的解释是因为根据了错误的版本。《雍也》篇:
子曰:“不有祝蛇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孔子曾经说“御人以口给,……焉用佞”(《公冶长》),“是故恶夫佞者”(《先进》),可见他是很讨厌佞的。但是当时世道太坏,如果一个人有宋朝那样的美,就不得不用祝鮀那样的佞,才能保护自己免受伤害。这一章本来很容易理解,其中的“而”字是表示转折的连词,文从字顺,但是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七“而”下引《论语》此文,却说“而”犹“与”:
言有祝鮀之佞,与有宋朝之美也。皇侃疏:“言人若不有祝鮀之佞,及有宋朝之美,则难免今之患难也。”及亦与也。
这一解读真可谓诘屈聱牙,非常别扭。既然“而”按照通常意思解释完全是通的,为什么王氏要别立新说?就是因为他根据了错误的版本。王氏所见的皇侃疏文作“及有宋朝之美”,其实这是错误的版本。在国内,皇侃《论语义疏》在宋代以后就失传了,今天能见到的《义疏》,是清代从日本传回来的。日本怀德堂本《义疏》云:
祝鮀,能作佞也。宋朝,宋国之美人,善能淫欲者也。当于尔时,贵佞重淫,此二人并有其事,故得宠幸而免患难。故孔子曰:言人若不有祝鮀佞,反宜有宋朝美,若二者并无,则难免今世之患难也。(注: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0页。)
皇侃的解释与我们的理解不同,是不是合理,另当别论,然而他的意思却很明白:“祝鮀之佞”与“宋朝之美”本来都不是好事,但是在那个时代,却为人所看重,二者都可以使人免于祸患,所以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祝鮀之佞,反而应该具备宋朝之美,如果两者都没有,就难免被人害了。其中相当于王氏所引的“及”字的地方,怀德堂本作“反宜”二字。作“及”字,上下文根本就读不通,显然是“反”之误字;“反”表示转折,正是“而”的常用意义。可见,王氏是根据了错误的版本作了错误的解释。
六
在语言的层面上,我们基本上可以有一个是与非或合不合语法的判断,因为语言毕竟是一个社会现象。但是在思想的层面上,就会出现多种解释的可能,而且每一种解释可能都是合理的,我们也很难判断到底哪一种解释符合思想家原来的意思。这并不意味着对思想的解释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至少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理解文本,从多方面探讨思想家思想的可能性,这样的理解也许更完善,更有价值。例如《雍也》篇: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先难而后获”,前人解释为先劳苦,后得到收获,即“先事后得”(《颜渊》)之意。例如《集解》引孔安国说:“先劳苦而后得功,此所以为仁。”这种解释在语言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思想上似乎境界并不高,先干活,后享受,一般的人也都是先事后得,是不是都能够算作“仁”?不过,这句话还可以有更好的解释,就是劳苦之事在人之先,收获之事在人之后,也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的境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云:“凡忧患之事欲任,乐事欲后。”(注:《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证明先秦儒家确实早已有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够得上“仁”的标准,恐怕就没有人会怀疑了。
另一方面,对文本思想的解释本身,也是产生新的思想的途径。不论古今中外,后代的思想家往往会通过阐释前代思想家的作品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例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就是借《孟子》的字义训诂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杰作。《论语》也是宋儒阐释其理学的重要文献依托。不过,这方面已经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兹不赘述。
七
在思想的层面上,我们至少还有思想家的语言表述作为依托。如果更进一步,在心理的层面上又如何呢?这已经完全超出了过去的训诂学研究的领域。在这里,我们不妨尝试着探讨《论语》中孔子的某些言论背后的心理特点。
我们知道,孔子对于女子是有偏见的。《阳货》篇:
予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孔子为什么会有这种偏见?这首先是跟当时的社会条件相关。男尊女卑是当时的普遍观念,孔子有这种思想并不奇怪。不过,“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可不是一般人都能说出来的话,孔子说这样的话,应该跟他的某些个人经验有关。这一偏见,是因为在他心里,一直有着一个深深的家族创痛。
研究孔子,研究《论语》,我们必须在脑子里牢固树立一种“贵族社会”的观念。家族血缘和礼仪是这种社会的明显特征。人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无论是个人的生活还是思想,都会不可避免地带上血缘、家族、礼教的痕迹。孔子的思想,与他的家族出身有着密切的关系。了解孔子的先世,对于理解《论语》的思想非常关键。
孔子是鲁国人,但他是宋国国君的后裔,而宋又是殷商的后裔。武王克商之后,封微子于宋。孔子对于自己是商人也有很强的认同感。《礼记·檀弓上》记载其将逝世时,子贡来看他:“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这一出身对于孔子的文化立场有很深的影响,使得他的眼光往往不限于他生活其中的鲁国文化,而是采取了三代兼容并包的立场。《论语·卫灵公》篇云:“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根据《左传》、《史记》、《孔子家语》的记载,孔子的先世如下:
微子……宋湣公——弗父何——宋父周——世子胜——正考父——孔父嘉——木金父——睪夷——防叔——伯夏——叔梁纥——孔子
宋湣公嫡长子弗父何,次子名鲋祀。湣公死,立其弟炀公,鲋祀弑炀公,而欲立弗父何,弗父何不受,鲋祀乃自立,为宋厉公。故《左传》称孔子:“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昭公八年》)孔子对于能以天下让的先贤有着特殊的尊敬,例如《泰伯》篇:“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这也许跟其祖先能以国相让有一定关系。
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与孔子最为相像。第一,正考父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三世为卿,而孔子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正是辅佐贤明的君主。第二,正考父曾经整理商代的史诗,今存于《诗经·商颂》。《商颂·那·叙》云:“《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国语·鲁语下》也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整理古代的文献,正是孔子一生最大的事业。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正是绍述其先人之事业,可见其先祖对于孔子的影响之深。
正考父之子孔父嘉,字孔父,名嘉。孔子氏“孔”,就是以其字为氏。孔氏家族在孔父嘉时,盛极而衰,而衰落的导火线就是孔父嘉的妻子。《春秋·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左传》云:“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这一事件成为孔氏自盛而衰的转折点。如果在今天,我们会把这个犯罪事件归咎于华父督,但是在那个时代,孔父嘉没有看好自己的妻子,也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杜预注云:“称督,以弑罪在督也。孔父称名者,内不能治其闺门,外取怨于民,身死而祸及其君。”(注:《左传·桓公二年》云:“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已杀孔父而弑殇公,召庄公于郑而立之。”是杜所谓“外取怨于民”。)此后孔氏继续为华氏所逼,被迫奔鲁。可以想见,这一事件在孔氏家族中造成的创伤是多么刻骨铭心!其后,孔氏对于女子的要求很严格,见于记载的就有“孔氏三世出妻”之称:孔子出妻,其子孔鲤也出妻,鲤子子思又出妻(注:参见《礼记·檀弓》篇的相关记载及孔疏。)。如果明白了孔子对于女子的偏见是源于深深的心灵创伤,今天的女性也许会对孔子的女人观抱一丝宽容之心吧!
在心理层面上,古代文献中很难有直接的证据,我们只能从现有的材料出发,进入一个高度推测的领域。这一领域虽然不是过去的训诂学所关心的,但它无疑也是理解古代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许我们现代的“新训诂学”应该把这种“心理训诂学”包括进来。如果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人类本身的话,那么我相信,这种心理层面的探索,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