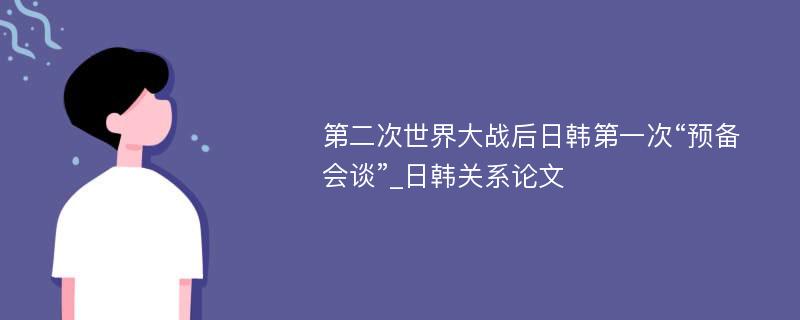
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日韩“预备会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首次论文,日韩论文,世界大战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04)02-0087-1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未能参加《对日和平条约》之签署的韩国,为解决日韩两国之间存 在的各项悬案,前后举行了七次正式会谈。本文要论及的日韩“预备会谈”就是,日韩 为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而进行的预备性会谈。韩国方面把该会谈同第一次日韩正式会谈 并称为第一次日韩会谈。日本方面则分称日韩“预备会谈”和第一次日韩正式会谈。日 韩“预备会谈”是战后长达14年之久的日韩会谈的序幕,与第一次日韩正式会谈亦有内 在的联系。本文拟主要探讨日韩会谈这一序幕。
一、韩国成立到日韩会谈前的两国关系的发展
1、韩国成立以后日韩关系的发展
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以后,美国试图使日本在某种程度上承认韩国的新政 权。这与美国作为其冷战政策的一环,在亚洲推行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密切相关[1] 。美国认为,为了确保韩国这一冷战的孤儿,从长远来看,必须加强韩国同日本的政治 、经济关系。而且,对日本来说韩国也具有潜在的、重要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上的价值[2 ]。出于这种的考虑,韩国政府成立以后不久,1948年10月19日,盟国日本占领军总司 令麦克阿瑟(Gen.Douglas Mac Arthur),把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邀请到了日本。在到 达日本之际,李承晚发表声明称:“韩国愿意忘记过去,努力同日本建立新的关系。如 果日本人成功地铲除军国主义因素,两国将恢复互惠的贸易关系”[3](P24)。
此后,1949年1月4日,作为韩国政府与盟国对日占领当局的联络机构,韩国在日本东 京设立了驻日代表部,3月26日开始,盟国占领当局与韩国政府举行通商会谈,4月23日 ,分别签署了“占领下的日本与韩国的贸易协定”及“占领下的日本与韩国的金融协定 ”。
1950年2月16日,应麦克阿瑟的邀请,李承晚再次访日。在到达日本之际,李承晚发表 声明称:“为就改善韩日关系的可能性同麦克阿瑟元帅及日本政府当局举行会谈而来到 日本”。接着,李承晚强调,为对付共产主义势力,韩日有必要采取共同的安全保障措 施,并表示“愿以这次访日为契机进一步推动韩日合作”[3](P24)。在这次访日过程中 ,李承晚同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国占领当局的要人举行会谈,并在盟国占领当局的斡旋下 ,还同日本首相吉田茂、前首相币原喜重郎、参议院议长佐藤尚武、日本银行总裁一万 田尚登等日本政财界要人进行了会晤。访问结束以后,2月18日,回国之前李承晚发表 谈话称:通过会晤“了解到以吉田首相为首的日方领导人真心地热切期盼两国之间的友 好。我期待有机会日韩两国在共同的理想与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清算过去,在充分认识到 正在逼近两国人民身边的危险的基础上,基于宽容的精神处理两国之间存在的各项共同 问题”[3](P24)。
李承晚一向认为,实现韩日“邦交正常化可能对日本有利,而对韩国则不利”[4],他 此次之所以对日采取如此积极的态度与行动,毋庸置疑,与美国强烈希望日韩尽快改善 关系有密切的关系。当时李承晚正在考虑筹建称之为“太平洋同盟”的类似象北大西洋 组织(NATO)那样的反共地区同盟[5]。
2、韩国被排斥在对日媾和会议之外与日韩两国的会谈准备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加快了对日单独媾和的步伐。韩国方面积极要求 以盟国的资格参加对日媾和会议,并在和约上签字。对此,日、英以韩国并非是对日交 战国为由,加以反对。于是,是否邀请韩国参加对日媾和会议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
1951年6月,韩国政府向其驻日代表部发出训令,要求做好举行韩日会谈前准备工作。 据当时任韩国驻日代表部参事官的葛弘基的回忆,其训令内容如下:
“①为政府能够举行韩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之会谈,同盟军总司令部(SCAP)方面和日本 政府进行交涉的同时,在当地收集可收集到的会谈资料。②须同时进行在日侨胞的国籍 问题与船舶归还问题的交涉。③在这次会谈中,韩国方面须以事实上之盟国一员列席会 谈”[6](P51)。
同年6月底,李承晚任命申性模为驻日公使的同时,直接受命其做好韩日会谈之准备。 申性模到任以后,为履行上述韩国政府的训令及李承晚的指示,留用正准备回国的、擅 长英语的葛弘基,开始同盟国日本占领当局进行有关交涉。葛弘基每周同盟军总司令部 外交局长西博尔德(William J.Sebald)等主要官僚举行两三次会晤,协商与举行韩日会 谈有关之事项[6](P51)。
1951年7月9日,美国正式通告韩国“只有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并在1942年1月的‘联 合国家宣言’上签名的国家才能参加对日和平条约的签署。因此,韩国不能成为签署国 ”[7](P1111)。韩国被排除在对日和约的签署国之外。日韩会谈遂成不可避免之事。
于是,同年7月20日,韩国政府以帮助驻日代表部工作为名,派俞镇午和林松本到日本 。但是,其真正目的是“为日韩会谈作基础调查”[8](P272、273),为即将举行的会谈 做准备。
当时韩国政府尚未完全放弃通过“对日媾和会议”解决日韩间悬案问题的打算。因此 ,当时韩国方面尚未打算通过日韩会谈解决日韩之间的所有悬案,只想通过日韩之间的 会谈解决因暧昧的法律地位在日本社会引发各种问题的在日朝鲜人问题[9](P12)。另外 ,该问题也是盟国占领当局与日本政府一直感到头痛的迫切希望尽快解决的问题[10](P 139)。由于当时美国也期待通过“对日和约”解决除在日朝鲜人法律地位问题以外的其 他各项日韩之间的外交悬案问题,所以,也主要劝告日韩两国通过谈判解决在日朝鲜人 问题。
韩国方面,考虑举行日韩全面会谈是1951年8月以后。当时韩国不能参加对日媾和条约 的签署已成定局,且《对日和平条约》的最终方案也已经出台。1951年8月底,韩国驻 美大使梁裕灿,同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举行会谈以后称:“ 在旧金山签署各项条约以后,在适当的时机大韩民国打算同日本缔结媾和条约。但,现 在为此未作任何准备”[11](P139)。韩国认为:“亡命中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对日宣 战的同时,[韩国]就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这与认为占领下的菲律宾与日本、占领下的 法国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是一样的道理”[12]。因此,韩国以媾和的方式同日本建立 外交关系是毫无疑问的[12]。
对韩国方面要求同日本举行全面会谈,缔结媾和条约的要求,美国和日本分别采取了 不支持和反对的态度。1951年9月4日,日本外务省有关人士称:“日本与韩国之间不存 在签订媾和条约的必要性。日本与韩国没有发生过战争,所以日本政府承认韩国政府即 可”[13]。这表明,在如何看待日韩会谈的问题上,从一开始日韩之间就存在着较大的 认识上的差异。
1951年9月8日,在朝鲜战争的战火中,美国一手操纵的对日媾和会议在旧金山召开, 签署《对日和平条约》,实现了所谓的“对日多数媾和”(事实上的单独媾和)。旧金山 “对日和平条约”,虽然规定:日本承认“朝鲜(亦或“韩国”,英文为“Korea”笔者 )的独立”,并承认南朝鲜美军军政厅对在韩日本及日本人财产所作的处理等,但也留 下诸多日韩之间尚需谈判解决的外交课题[14]。
3、美国积极斡旋日韩会谈
“对日和平条约”签署以后,美国为推动其亚洲“区域一体化”的冷战政策及完善其 东北亚战略防共防御体系,在日韩之间积极进行斡旋,促使两国尽快进行会谈解决各项 悬案,建立邦交。
1951年9月10日,盟军总司令部(SCAP)向韩国驻日代表部递交备忘录,要求韩国在60天 内就日本向韩国移交朝鲜籍船舶问题进行会谈。同年9月25日,盟军总司令部外交局长 西博尔德又向日本政府递交备忘录,要求“日本政府与韩国政府,从10月8日开始,在 总司令部外交局会议室,在总司令部的观察员列席的情况下,就在日朝鲜人的法律地位 问题进行协商”[3](P38)。对此,日本吉田内阁当即表示同意。但是,对此韩国政府则 要求把会谈时间推迟到10月下旬。同时,还要求在议题中增加船舶问题和渔业问题。盟 军总司令部也表示同意韩国的上述要求。
1951年9月10日,盟军总司令部向日本政府递交备忘录称:韩国方面希望把会谈内容扩 大到“有关议题的确定及会谈方式的研究”等方面,“为解决日韩之间存在的所有悬案 问题进行两国间的交涉”。为此,希望推迟进行原定于10月8日举行的会谈。希望日韩 两国“从10月20日开始举行会谈”。同年10月11日,日本政府就盟军总司令部的上述备 忘录表示:同意从10月20日开始,就“在日朝鲜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进行会谈。该问题 的会谈结束以后,可以就韩国方面所希望的上述问题举行会谈[3](P38)。
二、日韩预备会谈(1951.10.20~12.22)
1、出席会谈的双方代表与正式会议上的会谈
1951年10月20日,日韩预备会谈在盟军总司令部外交局会议室举行。当时,日本吉田 内阁主要关心的是“在日朝鲜人问题”。韩国李承晚政权主要关心的是为解决日韩之间 “所有悬案问题”打基础,作为现实问题主要想通过会谈解决“朝鲜籍船舶”的归还问 题和日韩渔业权问题。
出席日韩预备会谈的日方首席代表是外务次官井口贞夫,交替首席代表是外务事务官 千叶皓。代表有:入国管理厅执行部部长田中三男、法务府民事局主干平贺健太、外务 省管理局总务课课长后宫虎郎、外务省条约局局长西村熊雄、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倭岛英 二、外务事务官大野胜巳、大藏省事务次官舟山正吉、水产厅长官盐见友之助、运输事 务次官牛岛辰巳、外务省条约局法规课课长佐藤日史、外务事务官兼赔偿厅次长川崎一 郎、运输省海运调整部部长国安精一、永野正一、石田正等。
出席日韩预备会谈的韩方首席代表是韩国驻美大使梁裕灿,交替首席代表是韩国驻日 代表部公使申性模。代表有:高丽大学总长俞镇午、殖产银行行长林松本、法务部法务 局局长洪琎基、外务部政务局局长金东祚、海运局局长黄富吉、海运局监理课课长文德周、水产局渔捞课课长池铁根、驻日代表部参事官葛弘基等[3](P38、39)。
10月20日,盟军总司令部外交局长西博尔德以观察员的身份与会,并担任日韩预备会 谈的司会。第一轮正式会议会谈一开始,司会西博尔德在致辞中称:“希望会谈取得能 够奠定两国友好基础的成果”。接着,日方首席代表井口贞夫致辞称:“能有机会就因 和平条约生效而产生的在日韩国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进行协商,感到非常荣幸”。日方表 明了在会谈中准备着重解决在日韩国人法律地位问题的基本立场。
韩国首席代表梁裕灿则在致辞中说:“希望取代过去的敌对和不正常关系,建立建设 性的、互惠的关系。希望共同努力解决各项问题,在这基础上建立新的信赖关系”[3]( P39)。与此同时,梁裕灿“以似乎准备要起诉的口气进行演说”,“痛斥过去近40年日 本对朝鲜所采取的行动”,并提出了“能使日本达到破产程度的巨额对日赔偿要求”[1 5](P249)。也就是说,韩方从一开始就强调了在会谈中准备“清算过去”的立场。从会 谈一开始,日韩两国的立场就呈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在第一轮正式会议上的会谈中,双 方还决定以英语为会谈用语,议事录则以盟军总司令部观察员所作的记录为蓝本,经日 韩双方讨论,确定记录内容。
在此后的正式会议上的会谈中,韩方率先提出,设立“在日韩人国籍及待遇问题的分 委员会”,推进有关该问题的交涉。同时,还要求把正在另行举行的有关旧朝鲜籍船舶 的归还问题也纳入到日韩会谈。对前一个问题日韩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对把有关朝 鲜籍船舶的归还问题也纳入日韩会谈一事,日方一开始则表示了反对的态度[9](P21)。
10月24日举行的正式会议上的会谈中,韩国方面重新提出把(1)在日韩人国籍及待遇问 题;(2)船舶问题;(3)将来之协调方法等三项作为会谈议题。对此,日方也表示了同意 。10月25日举行的正式会议上的会谈中,双方为处理在日朝鲜人国籍及待遇问题、船舶 问题等设立委员会之事举行会谈。10月26日设立了“船舶问题委员会”,10月30日设立 了“国籍处理和待遇委员会”。同时还决定,在正式会议上的会谈中着重进行会谈议题 以及“有关将来双方协调之方法”等问题的交涉。
11月8日举行的第6轮正式会议上的会谈中,韩国方面提议“为使日韩双方就两国之间 存在的所有悬案问题进行交涉”提议,除上述两个委员会以外,还增设(1)请求权;(2) 渔业;(3)海底电缆;(4)通商航海条约;(5)其他问题等委员会,并立即着手进行上述 委员会上的会谈。对此,日方以“没有准备”为由表示拒绝,表现出消极和拖延时间的 态度[9](P22)。
11月12日,召开的第7轮正式会议会谈中,日方进一步明确了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 生效之前,至多进行与两国邦交正常化有关之会谈的态度。对韩国方面提出的其他问题 ,日方则采取了“暂且听着”,不加以评论的态度。日本的意图是极力避免在占领状态 下同韩国进行会谈,尽量拖延时间等待和约生效,以便在恢复国家主权的有利条件下同 韩国进行会谈。
然而,会谈进行一个多月以后,“日本受诸多国际因素的影响,虽然不是出于本意, 但开始转变了态度”[9](P23、24)。11月28日举行的第9轮正式会议上的会谈中,日方 撤回“没有准备”的发言,同意预计在1952年2月上旬举行的日韩正式会谈(即“第一次 日韩会谈”)中,就(1)建立基本关系;(2)解决财产及请求权问题;(3)缔结通商航海条 约;(4)缔结渔业协定;(5)分割海底电缆;(6)其他问题等悬案问题举行会谈[9](P24) 。
12月4日举行的第10轮正式会议会谈中,西博尔德、井口贞夫、梁裕灿相互确认,于19 52年2月举行的日韩正式会谈(“第一次日韩会谈”)中解决上述问题之后,结束了日韩 预备会谈中的正式会议上的会谈。但是,“船舶委员会”及在日朝鲜人“国籍处理与待 遇委员会”上的会谈一直持续到日韩举行正式会谈(“第一次日韩会谈”)为止。第一次 日韩会谈开始以后,上述两个委员会中的会谈直接纳入到了第一次日韩会谈。
2、“船舶委员会”上的会谈
所谓的船舶问题,就是旧朝鲜籍船舶的归还问题及1945年8月9日及此后在朝鲜海域的 船舶归属问题。如上所述,10月26日,日韩成立“船舶委员会”以后,从10月30日开始 双方在日本运输大臣接待室举行了有关船舶问题的会谈。截止到1952年4月1日,该委员 会共举行了33轮会谈[9](P41)。
出席“船舶委员会”日方委员有:外务事务官兼赔偿厅次长川崎一郎,运输省海运调 整部部长国安精一,运输省总务课课长龟山信郎,运输省班轮课课长川毛一郎,
ADVISER小山健一,大藏省管理课课长横山正臣,大藏省第二国有财产课课长牧野诚一 ,副委员有:赔偿厅总务课课长服部五郎,运输省船舶局簦记测度课富冈延一,运输省 海运调整部特殊财产课福井重孝等。
韩方委员有:法务局局长洪琎基,海运局局长黄富吉,海运局监理课课长文德 周,水产局渔捞课课长池铁根,韩国驻日代表部政务部三秘韩奎永,副委员有:外务部 政务局第一课课长陈弼植,大韩海运公社船舶部部长尹常松,大洋水产总务部部长郑华 一等[16](P4-6)。
在前四轮船舶委员会的会谈中,双方就会谈的议题进行了交涉。韩国方面,以1945年1 2月6日颁布的有关在韩日本及日本人财产处理之南朝鲜美军军政厅“法令·第33号”及 1948年9月11日签订的“美韩有关财政及财产协定”,1951年9月10日盟军总司令“备忘 录”等文件为依据,在11月6日举行的船舶委员会第4轮会谈中,提出了:A.“有关1949 年8月9日为止拥有朝鲜籍之船舶的归还事项”;B.“有关1945年8月9日或在其后在韩国 海域,而现在回到日本之船舶的归还相关之事项”等两项提案,要求日本就上述船舶的 归还问题举行会谈。针对韩国方面的提案,日方则提出了:C.有关根据盟军总司令部的 指示,停战以后日本借给韩国之5艘船舶的归还事项,D.有关因侵犯麦克阿瑟线(注:麦 克阿瑟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占领当局为日本渔船之出渔在日本列岛周边设置的禁 渔线,先后有三次扩张。)被韩国拿获之(日本)渔船的归还事项等两项提案。经日韩双 方协商同意把A、B、C三项作为议题,进行会谈[16](P4、42)。
11月13日举行的“船舶委员会”第6轮会谈中,韩国方面要求日本履行1951年9月10日 盟军总司令部“备忘录”第2168号(SCAPIN-2168),要求归还与之相关的朝鲜籍船舶。 对此,日方表示,盟军总司令部“备忘录”所依据的是1945年9月25日颁布的南朝鲜美 军军政厅“法令·第33号”,我们将研究该军政厅法令的立法宗旨,直到有关船舶及领 海主权问题获得解决为止,我们对韩国方面的提问和要求不能进行回答[9](P41、42)。 也就是说,日方采取对美军军政厅“法令·第33号”的立法依据和尚无定论的领海界限 提出疑问的会谈战术拖延了会谈。
但后来日方的态度有所缓和。日方同意对韩国方面要求归还的船舶进行实际调查,并 于11月20日举行的第11轮会谈中,向韩方提出了有关朝鲜籍船舶的清单。韩方接受该清 单以后,立即对其中已证实该船是朝鲜籍的19艘船舶提出了归还要求。与此同时,韩方 认为除此之外在日本尚有更多的朝鲜籍船舶。对此,日方要求韩方“提供具体的新的朝 鲜籍船舶清单”。日方称:如果韩方不提出具体的新的朝鲜籍船舶清单,那么基于“船 籍主义”的旧朝鲜籍船舶问题就认为获得解决。但基于“领海主义”的1945年8月9日及 以后在朝鲜海域之船舶的归还问题,以及停战后根据日本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指示借给韩 国的5艘日本船舶的归还问题,在总体上获得解决之前,日本不能向韩国引渡船舶。
当时,因战后的混乱及朝鲜战争等原因,韩国方面已遗失大部分资料,很难提供具体 详细的资料,却要求韩国提供具体详细的资料,其目的在于迫使韩国不得不自动放弃一 部分船舶的归还要求,从而达到把韩国的船舶归还要求限制在最低限度内的目的。
第12轮会谈到第16轮会谈中,日韩双方主要针对“法令·第33号”的立法依据问题展 开了辩论。在此后的会谈中,韩国方面提出了有关B项1945年8月9日及此后在韩国海域 之船舶的清单及唯一的证据釜山港供水日志。日方则提出了C项借给韩国的5艘船舶的归 还要求,和D项因侵犯麦克阿瑟线而被韩国扣留的日本渔船的清单和归还要求。对日方 要求归还的借给韩国的5艘船舶,韩方认为该船舶属朝鲜籍船舶范围,因此表示拒绝归 还。对此,日方则认为上述船舶是根据盟军占领当局的指示借给韩国之日本政府所属船 舶,强烈要求韩国归还上述船舶[9](P42、43)。
为了打破上述僵局,1952年4月1日举行的第33轮“船舶委员会”会谈中,日方提出了 “避开有关船舶归属问题的议论,在援助韩国海运发展的宗旨下,日本方面提供若干船 舶为前提协商达成妥协是何?”的提案[17](P38)。具体说:“日本方面从日本国内购买 ,相当于在A项议题的会谈中同意归还韩国的15艘5610吨朝鲜籍商船及9艘336吨渔船, 把它移交给韩国”。但“上述移交于去年9月11(10?)日SCAPIN(盟军最高司令部备忘录) 及在韩美军军政厅法令第33号并不相干,且对两国之间的请求权问题也不产生任何影响 。上述移交作为日韩经济合作的一环,采取日本赠与韩国的形式”是何的提案[16](P44 )。也就是说,日本吉田内阁避开归还船舶的法律上的义务问题,向韩国提出了以“经 济合作”的名义,利用“赠与”的方式解决”旧朝鲜籍船舶问题的建议。但是韩国方面 拒绝了日方的这一提案。在这里,日本首次提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理同亚洲各国之 间之各项悬案的重要外交形式——“经济合作方式”。
以“赠与”、“无偿援助”、“有偿长期低息贷款”等名目的所谓的“经济合作”方 式,避开有关战争责任及殖民统治责任的法律追究,处理日本同亚洲各国之间“赔偿” 、“财产请求权”等问题,恢复和重建日本同这些亚洲国家(或地区)的邦交关系,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亚洲外交的重要形式和特色。这也是日本解决日韩关系问题的基本 立脚点。
3、日韩在“国籍及待遇委员会”上的会谈
1951年10月26日,成立“国籍待遇委员会”以后,从10月30日,即新的日本《出入国 管理法》即将生效的前两天开始,日韩双方举行了有关国籍待遇问题的会谈。截止到同 年底该会谈进入休会为止共举行了21次会谈。
出席“国籍及待遇委员会”日方委员有:田中三男、平贺健太、入国管理部部长铃木 、事务官神原、今井、佐治等。韩方委员有:俞镇午、洪琎基,金东祚、金泰 东、李一雨、韩奎永、金永周等[9](P16)。
在“国籍待遇委员会”的会谈中,日韩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对待在日朝鲜人问 题上。在会谈中,日方只想确认在日朝鲜人拥有韩国国籍,以便“对日和约”生效以后 ,给予在日朝鲜人以一般外国人的待遇,适用针对一般外国人的一切限制。对此,韩方 则认为,在日朝鲜人是日本社会中具有特殊背景的特殊的外国人。因此,要求给予在日 朝鲜人以比一般外国人优越的待遇。对韩方的上述主张,日方认为这是“无理的主张” 而加以拒绝。但韩方则辩称:“韩国并没有要求对所有的韩国人以比一般外国人优越的 地位。对1945年8月9日以后进入日本的韩国人给予一般外国人之待遇没有任何异议。但 是在这以前开始居住在日本的韩人(朝鲜人)是与现在(在日本)的一般外国人不同,拥有 特殊的背景与地位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韩国)只要求确认这一既成事实”[9](P30)。
日韩预备会谈开始以后,日方在正式会议上的会谈中就在日朝鲜人的国籍问题,提出 提案称:(1)对日和平条约生效以后在日朝鲜人脱离日本国籍取得韩国国籍;(2)以户籍 为基础决定在日朝鲜人的国籍;(3)在日朝鲜人取得日本国籍,则须依据日本国籍法履 行必要的手续。对日方的这一提案,韩方认为:有多少人拥有本国国籍,有多少人加入 日本国籍的问题,在国际法上属于“国内问题”,所以这一问题不能成为国际会议的议 题。与此同时,韩方认为韩国政府在国际法上对在日朝鲜人具有保护的义务,所以,呼 吁在日韩会谈中着重讨论在日韩人的待遇及法律地位问题[9](P31)。因此,此后日韩在 “国籍及待遇委员会”上主要围绕在日韩国人的待遇及法律地位问题展开了交涉。
在“国籍待遇委员会”的会谈中,韩国方面要求日本政府把在日朝鲜人作为“特殊的 外国人”即作为日本殖民统治产儿,给予特殊照顾[18](P128)。11月2日及6日举行的“ 国籍待遇委员会”上,韩国方面要求对1945年8月9日以前开始居住在日本的朝鲜人(1) 赋予永主权;(2)不适用强制遣送条款;(4)赋予内国民待遇;(5)对回国者携带的动产 及汇款采取特别措施加以照顾。
对韩国方面的上述要求,日方称:“对日和平条约”生效以后准备给在日韩国人以与 一般外国人相同的待遇,并愿意在即将缔结的日韩通商航海条约中给予韩国人以最惠国 国民待遇。对此,韩方则认为:最惠国国民待遇是对将来进入各自国家的对方国民的待 遇问题,现在不是议论它的时候。现在需要作出决定的是从停战以前开始居住在日本的 特殊的外国人——有关在日韩人的待遇问题。在日韩人,目前在日本享受除参政权以外 的和日本国民同等的待遇,即内国民待遇。韩方要求日本将来继续给予在日韩人以同样 待遇。对此,日方认为:对在日朝鲜人给予永久的内国民待遇,等于在日本国内承认“ 双重外国人”的存在。这在国际法上也没有先例,因此,实在难以接受[9](P36、37)。
对在日朝鲜人赋予永住权的问题上,日方从一开始就坚持了“不能让在40来年的特殊 时期(指日本对朝鲜进行殖民统治时期——笔者)产生的没有先例的既成事实永远延续下 去”的立场[18](P77)。后经日韩双方舌战,日方有所后退,主张对在日朝鲜人赋予永 住权时,要根据日本“出入国管理令”逐一审查申请永住权的朝鲜人,(1)是否为人善 良;(2)是否拥有或掌握独立维持生计的资产或技能;(3)永住日本是否符合日本国的利 益等以后,决定是否赋予在日朝鲜人以永住权。(4)受理永住申请时准备征收2000日元 的手续费。但经双方又一番舌战之后,一些问题上日方又作出了让步。日方同意:只要 韩国政府的驻日代表部发给登记证明,日本政府在把该证明与外国人登记簿加以对照以 后,如果能够确认该韩国人确实从1945年8月9日以前开始居住在日本,那么不对其进行 任何审查,也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就赋予永住权[9](P32、33)。
对在日朝鲜人问题上,另一个成为日韩会谈焦点的问题是强制遣送出境的问题。在“ 出入国管理法”的有关强制遣送出境的条款中,将可能适用于在日朝鲜人的条款是有关 “贫困者、流浪者、残疾人等对日本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成为负担的人”的强制遣送条 款。当时,约有6万在日朝鲜人,依日本政府的“生活保障法”,接受日本政府的生活 救济,其年救济额达66000万日元。日本政府计划把这一部分接受救济的在日朝鲜人逐 次强制遣送出境。但又称:即使是生活贫困者,如果不接受救济费,也可以排除在强制 遣送出境的对象之外。
在这一问题上,韩方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如果韩国接受日方的主张,同意日方停 止救济贫困的在日朝鲜人,那么贫困的在日朝鲜人将免受被强制遣送出境的处理。但是 ,这样做不仅使实际生活依靠救济的赤贫的在日朝鲜人陷入困境,而且也将“给在日本 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提供攻击韩国政府的绝好的素材”。“当时在日朝鲜共产主义者把日 本政府向在日朝鲜人提供生活救济,宣传为他们与日本政府斗争的结果”。因此,如果 通过日韩会谈取消这项日本政府的生活救济,那么很明显该问题将立刻成为反对韩国政 府的在日朝鲜人攻击韩国政府的绝好材料。不甘心让日方随心所欲地强制遣送在日朝鲜 人出境的韩国政府,于是提出:(1)继续对生活贫困的在日韩人以生活救济;(2)对接受 (日本政府)生活救济的在日韩人,直到他们在经济上能够自立为止,在一定期限内不适 用强制遣送出境的条款[9](P34)。
对此,日方则提出:(1)同意今后一年继续进行生活救济。在这以后虽然继续进行生活 救济,但根据同韩国签订的国际条约进行的救济仅限于一年,而后日本自主进行;(2) 今后一年内如果出现因贫困需要强制遣送出境者,(日本政府)将事先同韩国政府协商, 若韩国方面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就不打算强制遣送出境[9](P33—36)。
对在日朝鲜人回国时所携带动产及汇款问题,日方一开始主张:根据日本出口贸易管 理令及汇兑管理法加以限制。重量限制在4000磅以内,汇款限制在10万日元以内。对此 ,韩方则主张:(1)回国者自由搬出财产,对其数量及种类不加任何限制;(2)对所搬出 的财产不征收任何税金;(3)但禁止以搬出财产的名义进行走私贸易或偷运鸦片、火药 禁运物品,并为取缔上述行为日韩两国进行合作[9](P39、40)。对韩方的上述主张,日 本大藏省、通产省等表示强烈反对。但是,急于把更多的在日朝鲜人送回韩国的日本政 府,最终原则上同意了韩国的主张,只是要求,(1)对上述特别待遇设置期限;(2)由双 方专家举行会谈,签订详细的有关防止走私贸易、汇款等方面的协议[9](P40)。
如上所述,在“国籍及待遇委员会”的会谈中,日韩双方的很多主张很快有了接近。 这也是1951年12月22日,日韩预备会谈结束以后日本有关媒体报道称:日韩已达成原则 协议的原因[19]。
1952年2月15日,第一次日韩会谈开始以后,“国籍及待遇委员会”的会谈直接转入第 一次日韩会谈,继续进行。第一次日韩会谈中“国籍及待遇委员会”的会谈从第22轮到 第36轮(最后一轮),共举行了15轮会谈。这些会谈中,虽然日韩双方没有达成新的妥协 ,但为起草有关国籍及待遇问题的共同协议草案,也是双方全力以赴的结果,1952年4 月1日,双方达成妥协,在搁置分歧的情况下达成了“有关在日韩人的国籍及待遇的日 韩协议案”。
三、日韩“预备会谈”的成果及会谈中暴露出的问题
1、“预备会谈”的成果
日韩“预备会谈”在确定日韩正式会谈的时间及会谈议题等方面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且在“船舶问题”和在日朝鲜人的“国籍及待遇问题”等委员会的会谈中双方的折衷取 得了一定进展。但日韩“预备会谈”,并没有取得美国所期待的成果,未能彻底解决日 韩“船舶问题”和在日朝鲜人的“国籍及待遇问题”。
2、“预备会谈”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在预备会谈中,日本除在日朝鲜人问题、船舶问题等个别问题以外,对其他问题均采 取了尽量等待媾和条约生效,以便日本恢复主权以后再进行交涉的姿态。因此,会谈显 得缺乏热情,且相当散乱。韩国方面把这些完全归咎于日方缺乏诚意,指责日方企图把 会谈拖延到对日媾和条约生效为止[20]。韩方还警告日本:这种缺乏诚意的态度和行为 “不仅会对将来的韩日两国关系投下阴影,也会给自由阵营带来不幸”[21]。
那么,当时韩方是否对日韩预备会谈充满了热情呢?那也不见得。据同李承晚关系密切 的女诗人毛允淑回忆:接到美国希望韩日举行会谈的劝告以后,李承晚非常生气地说“ 我有许多必须做的事情,韩日会谈不过是其中也许轮到第11轮才能考虑的问题”[22]。 当时,朝鲜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连韩国政府机构也避开战乱被迫迁往釜山办公。在 这种形势下,日韩会谈对韩国政府来说,无论是从时机上讲还是从精力上讲,都并非是 最佳时期。
另一方面,在日韩预备会谈中,日韩双方在有关日韩问题的妥协方式上也存在重大的 差异。即韩方主张一揽子解决日韩之间的悬案,而日方则主张渐进地、分阶段地达成妥 协的方式,解决日韩之间的悬案问题。日方把日韩之间的悬案问题分为,对日媾和条约 的生效之前解决的问题和此后逐步加以解决的两大类问题。日方希望首先在属于前者的 在日朝鲜人国籍及待遇问题上达成妥协,使有关该问题的协议与媾和条约同时生效,并 同时实现日韩邦交正常化。韩方则考虑到自身的实力和处境,利用日本尚未摆脱占领, 美国对日韩会谈尚有相当影响力的时机,争取一揽子解决日韩悬案,以便问题以有利于 韩国的方式获得解决。但是在日韩预备会谈中双方都未能实现预期的目的。各项悬案移 交到了第一次日韩正式会谈。
收稿日期:2003-12-12
